张謇与南通地方自治模式兼论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调适.docx
《张謇与南通地方自治模式兼论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调适.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张謇与南通地方自治模式兼论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调适.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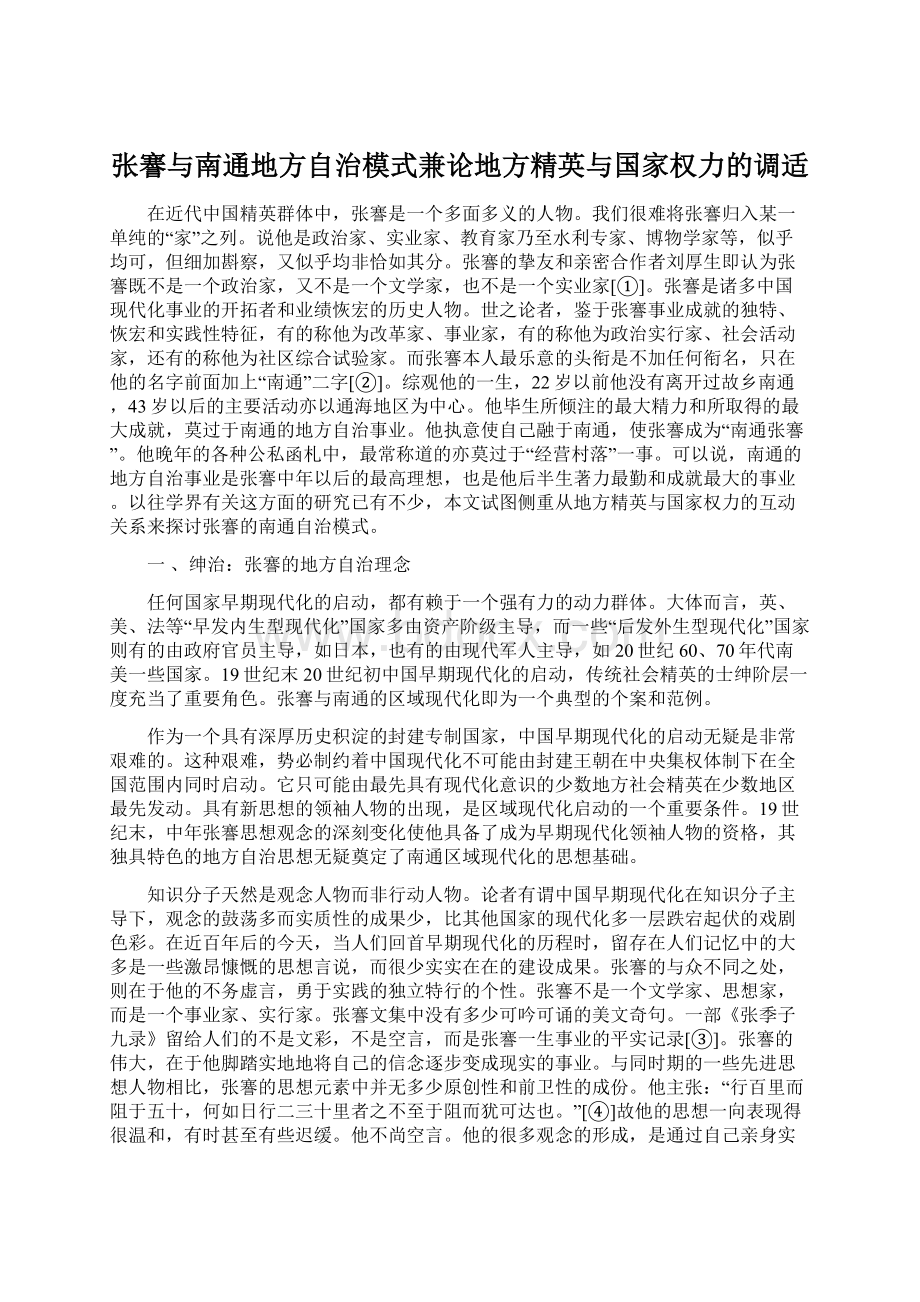
张謇与南通地方自治模式兼论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调适
在近代中国精英群体中,张謇是一个多面多义的人物。
我们很难将张謇归入某一单纯的“家”之列。
说他是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乃至水利专家、博物学家等,似乎均可,但细加斟察,又似乎均非恰如其分。
张謇的挚友和亲密合作者刘厚生即认为张謇既不是一个政治家,又不是一个文学家,也不是一个实业家[①]。
张謇是诸多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业绩恢宏的历史人物。
世之论者,鉴于张謇事业成就的独特、恢宏和实践性特征,有的称他为改革家、事业家,有的称他为政治实行家、社会活动家,还有的称他为社区综合试验家。
而张謇本人最乐意的头衔是不加任何衔名,只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南通”二字[②]。
综观他的一生,22岁以前他没有离开过故乡南通,43岁以后的主要活动亦以通海地区为中心。
他毕生所倾注的最大精力和所取得的最大成就,莫过于南通的地方自治事业。
他执意使自己融于南通,使张謇成为“南通张謇”。
他晚年的各种公私函札中,最常称道的亦莫过于“经营村落”一事。
可以说,南通的地方自治事业是张謇中年以后的最高理想,也是他后半生著力最勤和成就最大的事业。
以往学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本文试图侧重从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来探讨张謇的南通自治模式。
一 、绅治:
张謇的地方自治理念
任何国家早期现代化的启动,都有赖于一个强有力的动力群体。
大体而言,英、美、法等“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多由资产阶级主导,而一些“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则有的由政府官员主导,如日本,也有的由现代军人主导,如20世纪60、70年代南美一些国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传统社会精英的士绅阶层一度充当了重要角色。
张謇与南通的区域现代化即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和范例。
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封建专制国家,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无疑是非常艰难的。
这种艰难,势必制约着中国现代化不可能由封建王朝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启动。
它只可能由最先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少数地方社会精英在少数地区最先发动。
具有新思想的领袖人物的出现,是区域现代化启动的一个重要条件。
19世纪末,中年张謇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使他具备了成为早期现代化领袖人物的资格,其独具特色的地方自治思想无疑奠定了南通区域现代化的思想基础。
知识分子天然是观念人物而非行动人物。
论者有谓中国早期现代化在知识分子主导下,观念的鼓荡多而实质性的成果少,比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多一层跌宕起伏的戏剧色彩。
在近百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回首早期现代化的历程时,留存在人们记忆中的大多是一些激昂慷慨的思想言说,而很少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
张謇的与众不同之处,则在于他的不务虚言,勇于实践的独立特行的个性。
张謇不是一个文学家、思想家,而是一个事业家、实行家。
张謇文集中没有多少可吟可诵的美文奇句。
一部《张季子九录》留给人们的不是文彩,不是空言,而是张謇一生事业的平实记录[③]。
张謇的伟大,在于他脚踏实地地将自己的信念逐步变成现实的事业。
与同时期的一些先进思想人物相比,张謇的思想元素中并无多少原创性和前卫性的成份。
他主张:
“行百里而阻于五十,何如日行二三十里者之不至于阻而犹可达也。
”[④]故他的思想一向表现得很温和,有时甚至有些迟缓。
他不尚空言。
他的很多观念的形成,是通过自己亲身实践后,逐渐总结提炼出来的。
他的“村落主义”和“地方自治”主张的提出,即经过了一个实践和总结的过程。
张謇在前半生的人生舞台上,主要扮演的是一个苦修举业和侧身幕府的传统士人角色。
甲午战争以前,张謇只是一个具有爱国心和某些开明倾向的封建士大夫。
尽管此前“西潮”早已不断冲击中国,而早年张謇的思想感触并不敏锐,甚至显得有些滞后。
追溯张謇“地方自治”观念的形成历程,不难发现其思想资源中富有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养料。
早在甲午前的十年间,作为乡绅的张謇所进行的各种“经营乡里”的活动,诸如办理通海花布减捐,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事业,提议平粜放赈和建立社仓,恢复溥善堂等慈善机构等,已经萌现了后来他所倡导的“地方自治”三大部类即实业、教育、慈善的端绪[⑤]。
应该说,早年张謇“经营乡里”的活动,与他当年作乡绅时的身份基本上是相契合的。
张謇以状元之尊下海办厂,本是张之洞创议和促成的。
对于奉命办厂,张謇最初还经过了相当激烈的思想斗争。
有意思的是,张謇毅然决定办厂的一个重要动因,竟是要为“病在空言”而为世所轻的书生争一口气。
他说:
“余自审寒士,初未敢应。
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
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暗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与合。
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约自牖,责在我辈,屈己下人之谓何?
踟躇累日,应焉。
”[⑥]在这里,张謇充分表现出一个传统士人在投身商海前的自我困扰和自我调适的心态。
除了立誓要为书生争口气外,张謇投身实业的另一个动因,是为了兴办教育,筹措教育经费。
其后张謇以实业、教育、慈善作为其地方自治规划中的三大支柱,实际上在张謇心目中,实业只是达成地方自治的前提和手段,教育、慈善才是其地方自治的最终目标。
张謇后来曾这样解释实业、教育与慈善三者之间的关系:
“以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
”[⑦]1921年,张謇在致南通县长的一封信中更为明白地谈到:
“查地方自治,以进增社会之能率,弥补人民之缺憾为其职志。
而进行之事业,属于积极之充实者,最要为教育;属于消极之救济者,最要为慈善。
教育发展,则能率于以增进;慈善周遍,则缺憾于以弥补。
”[⑧]其时,日人驹井德三在实地调查张謇的事业后,亦断论说:
“惟张公所怀之理想,数十年始终一贯,表面以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标榜,里面则醉心于教育及慈善事业之振兴。
”[⑨]实际上,以教、养二端作为地方自治的中心目标,并未超出中国传统士绅“兼济天下”的义务和职责范围。
1901年,清廷在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下,被迫宣布推行“新政”,允许官员士绅提出改革意见。
张謇趁此机会,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一本长达数万言的《变法平议》,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其中关于府县议会方面的建议,大致反映了此时张謇在地方自治方面的某些设想。
他说:
“国有兴革,何以使民不疑?
国有征敛,何以使民不怨?
兴革视民之俗,何以杜其疑而使之和?
征敛视民之力,何以平其怨而使之服?
权衡枢纽,必在议会。
”[⑩]张謇眼中的议会功能,不过是协助政府释民疑,平民怨,而非伸民权。
《变法平议》中所拟定的府县议会议员,至多不过5人,而且选举人与被选举人限于“有家资或有品望”的绅士。
张謇认为,绅士通过地方府县议会,可以“释民教之争”,“通上下之情”,并且筹设学堂、警察以及农工商各类公司,实现地方自治的目的。
张謇寄望于乡绅肩负地方自治的主要责任。
此外,张謇还主张“胥吏必用士人”。
在地方衙门中,胥吏作为知县的手足和辅佐,执行实际的行政事务。
乡绅与地方衙门交涉,常常通过胥吏为中介。
但由于吏道大坏,胥吏势必妨碍乡绅在地方社会中的活动和基层权力的行使。
张謇的建议无疑也是为了扩张乡绅在地方自治活动中的权力。
“胥吏必用士人”中的“士”,自然是指下层乡绅。
张謇此时虽然尚未明确接受地方自治这一新观念,但他设想中的地方政治蓝图,即是由上层乡绅组成府县议会参与议事,再由下层乡绅执行地方实际行政事务。
1903年,张謇东游日本70天。
此行他重点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和实业。
地方自治自然也在他的关注之列。
访日结束之际,他发表感想说:
“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
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
士大夫生于民间,而不远于君相,然则消息其间,非士大夫之责而谁责哉?
”[11]张謇再次强调士大夫在官民之间沟通上下的“媒介”作用。
他认为,日本的成功,“其命脉在政府有知识能定趣向,士大夫能担任赞成,故上下同心以有今日。
”[12]
东游回国以后,张謇更坚定了在南通推行地方自治的信念。
日本之行也促使张謇积极投身于立宪运动。
此时国内舆论界对地方自治的宣传已日趋热烈。
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在提倡和宣传地方自治的主张。
一向务实的张謇没有积极参和到当时地方自治的文字宣传浪潮中去,尽管他早已服膺地方自治的主张,而且早已有意识地在其通海家乡开展地方自治事业的经营建设,但他明确将其事业汇总于“地方自治”的名目之下,则是1905年以后的事[13]。
其后,清政府颁行《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张謇虽然感奋地方自治章程的正式颁行,但他更痛感地方自治经费忙无所向而将流于形式。
他以自己正在举办中的南通自治事业为例,预测一县筹办自治所需经费至少当在百万以上,清政府要求地方从“公款公产”和“公益捐”中自筹,实际上各县早已“竭蹶不遑”。
张謇于是断论,这场地方自治势将衍为“不自治不可,欲自治不能”的局面。
“届时政府调查,必谓我人民自治程度之果不足,果不足则贻误实行立宪,我人民将尸其咎矣。
”[14]张謇在南通的地方自治事业之所以从举办实业入手,即在于他痛感“自治须有资本”。
从南通的实践中,张謇总结地方自治有“三难”:
一是集资难,二是求才难,三是御侮难[15]。
前两难不难理解,而后一难乃指社会环境的阻力。
张謇一直将地方自治的重任寄望于地方士绅。
他谴责中国数百年来不准士绅干预地方公事的旧规,认为这一传统导致公正士绅规避承担地方应兴应革之事的责任,也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上下悬隔,“行政人与社会,几几如冰炭之不复相入,以演成今日之现象。
”[16]张謇所称的“社会”,实指绅界而言。
他认为,“日本勃兴,其最初之起点,由社会影响所被者为多。
”而中国则是“行政人”摧折“社会”,“反对社会”,甚至“解散社会”。
他认为,立宪制度应是“社会处立法之地位,地方官处执法之地位”,“官与绅共其责成”[17];他说:
“往者中国专制之世,社会与政府分,有政府而无社会,……今朝廷既已宣布九年立宪,社会将与政府合,有社会乃有政府”[18];政府与社会应处于一种既相联合又相抗衡的互动关系,“社会监察政府,政府亦监察社会”[19],亦即官权与绅权,官治与绅治既相颉相颃而又相辅相成。
张謇理想中的地方自治制度,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要伸张“绅权”。
他把“绅”作为一种介于官、商和官、民之间,并能沟通官商和官民关系的中介力量。
张謇自己在这方面以身作责,自立榜样。
宣统三年(1911),张謇在《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中这样写道:
“立宪云者,通政府与人民之隔阂也。
……人民之于政府蓄疑久矣。
积疑生忌,积忌生谤;政府即有善良政策,而无术可使人民相谅,……謇十四年来,不履朝籍,于人民之心理,社会之情状,知之较悉;深愿居于政府与人民之间,沟通而融和之。
”[20]本来西方原创的“地方自治”制度,乃奠立于主权在民,人民有参与政治权利的原则基础上。
而在张謇的观念中,地方自治实际意味着“绅治”。
他在总结南通的“地方自治”成就时即称:
“走抱村落主义有年矣。
目睹世事纷纭,以为乡里士夫,苟欲图尺寸以自效者,当以地方自治为务。
地方自治条理甚繁,当以实业教育为先。
盖犹孔子富而教之之义,使地方无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
走施诸南通,近30年,薄有成效。
”[21]张謇明白宣示他的“地方自治”乃基于孔子的“富而教之”思想。
他的理念中不乏儒家经籍中的三代盛世的影像。
据张孝若回忆,在古人中,田畴和顾亭林是其父心目中除孔子之外最为敬仰的两位先儒。
东汉末年,乱世中的田畴率族人及随从数百人聚居山野种田为生,辞官不就。
张謇既不得志于庙堂,只好“遁居江海,自营己事”,处处以田畴自况[22]。
这也正是他追踪前贤,既不能兼济天下,又不愿独善其身,只好蛰居海滨,经营其“村落主义”。
在世事纷纭的环境下,他呼吁“乡里士夫”人人奋起,各自效力于地方,为地方事业做几件实事。
张謇自己一直以“儒者”自居。
他认定自己是“在商言儒”,“言商仍向儒”。
他创办大生企业,他办垦牧公司,其出发点是为了弘扬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仁者爱人的大义。
他曾对其挚友刘厚生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
……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23]。
他自称很钦佩宋儒程朱阐发的“民吾同胞,物吾同与”的精义,但他不满程朱说而不做的作风。
他想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替书生争气”。
张謇晚年,常将“地方自治”与“村落主义”相提并论。
如他回顾南通“地方自治”的推展过程时称:
“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一二人,后由各朋好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事未有成,而时不可再。
”[24]论者多以为张謇抱持“村落主义”要早于“地方自治”,如章开沅先生认为:
“张謇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从日本考察回来以后,便把他历来主张的村落主义与具有近代观念的地方自治结合起来。
”[25]但据笔者初步查证,张謇文集中最早提及“地方自治”一词,大约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而提及“村落主义”则是民国以后的事。
民国元年张謇在致袁世凯的一封信中谈到:
“謇自前清即矢志为民,以一地自效。
苏人士嗤为村落主义。
……顾謇之一身,无求于世久矣,尤无求于政府。
彼谮人者恶乎知之?
抑謇之所以辞国、省会,而终以村落主义自享也。
”[26]也就是说,“村落主义”最初不是张謇自己提出来的,而是别人嘲笑强加于他的,但他最终却引以自享。
越到晚年,随着南通地方自治事业的辉煌,张謇对“村落主义”由自享进而自豪。
在张謇晚年的公文私札中,“经营村落”、“村落主义”时常与“地方自治”交相并称。
事实上,张謇理念中的“地方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传统士大夫博济天下和修齐治平的理想,与真正近代意义上的人民自决自主和参政议政的“地方自治”判然有别。
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村落主义”比用“地方自治”来表述他的思想更为恰当。
1920年,当其留美归来的儿子张孝若倡导成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由“南通人民自动自决自卫”的自治会时,张謇最初明确表示反对,只是不胜其子的反复陈说,才点头许其试办一下。
在张謇看来,民智未开,民众知识才力均不足以担当欧美式的地方自治。
南通自治会成立一年以后,他的疑虑依然未消,一方面,他希望他的事业后继有人,同时又不相信普通民众的知识能力,“日望传人,而又惴惴焉虑或不胜传”[27]。
1921年,张謇在《呈报南通地方自治第25年报告会筹备处成立文》中这样写道:
“儿子孝若,年少资浅,近被地方公推,组织南通县自治会,其范围亦如謇所办之事业。
但彼由各团体之赞助,此只发生于一二人;彼为近20世纪世界之大潮流,此为前25年个人之小计划。
抚今思昔,不禁惘然。
”[28]张謇显然清楚地认识到他儿子所倡导的自治,与他本人所经营的自治,名同而实异。
儿子所倡导的奠立于民治基础上的自治切合20世纪的世界潮流,而他本人所经营的“自治”,不过是一个士大夫独力支撑下的个人意志的产物。
受过西方自由民主思想薰染的张孝若对其父的自治事业更有一番清醒的认识。
他认为南通的事业只是一人一家的事业,而不是全体南通人民自动自决的事业。
所以他发起组织南通县自治会,其目的就是要将“以前个人统系的南通”,变为“全县具体的南通”;将“被动的南通”,变为“自动的南通”;将“从前个人自治模范的南通”,变为“以百二十万人之才智公同发皇”的南通;“所说之话,须百二十万人人人所欲言;所做之事,须百二十万人人人所欲为”[29]。
显然张孝若所倡导的地方自治,才是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
而张謇所称的“地方自治”,虽然袭用了西方地方自治的名义和某些形式,但其精神内涵实际上仍是儒家的道德教化和社会伦理。
章开沅先生在《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一书中曾指出:
“张謇已经决定性地进入了资产阶级这个新兴的社会群体,他的思想、言论与行动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断绝与原先隶属的士人群体的千丝万缕联系,在很多场合,他作为绅士的自我意识甚至还要大于作为资本家的自我意识。
”[30]实际上,中年以后的张謇一身扮演的是实业家和士绅领袖的双重角色。
世之论者无论将张謇冠以各种“家”的头衔,也不应该忘记他作为士绅领袖的身份。
张謇后半生的思想和事业,与其士绅领袖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是密切相关的。
在很多场合,张謇扮演士绅领袖的热情,远在扮演实业家的角色之上。
亦因为此,张謇的“地方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绅治”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和地方自治的历程中,近代资产阶级尚处于生命发育的襁褓时期,作为中国传统精英阶层的绅士以其固有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感,肩负起新时代的重托,充当了启动中国现代化的动力群体是势所必然的;“以绅权孕育民权”,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过渡时期社会阶级结构演化的必然现象[31]。
梁启超“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的主张,即在某种意义上预言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
20世纪初年张謇主导下的南通地方自治无疑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
二、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调适
一般而言,地方精英为维系其支配地位,必须控扼下列各项资源:
(1)物质资源,如土地、商业财富、军事力量等;
(2)社会资源,如社会影响力的关系纽带、家族群体、结社等;(3)个人资源,如专长技能、领导能力、宗教或魔术力量等;(4)象征资源,如名分、名望、特殊生活方式等[32]。
张謇出身于江北一个富裕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没有一般名门望族那样可资利用的世袭血缘资源和豪门世家那样的物质基础。
就张謇而言,在中年以前,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场屋蹉跌、侧身幕府和经营乡里的普通乡绅,其个人能量、社会资源和物质资源均极其有限。
转折的契机,自然是他的状元及第。
状元的尊荣,无疑奠立了张謇成为南通士绅领袖的坚实基础,但张謇确立其地方最高权威有一个发展过程,除了状元这块金字招牌所具有的名分名望的象征资源外,尚有赖于其它政治和社会权力资源的衬托和补充。
在社会资源方面,张謇早年“经营乡里”的活动,从多方面扩展了他的社会交往圈,联系了官绅之外的多种社会力量,奠定了自己在通海地方社区的良好形象。
在政治资源方面,张謇一生中真正任实缺官的时间虽不过三四年光景,自嘲“在官半日”,也自称“不愿居八命九命之官”,但张謇一直与官场政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謇本人虽未曾直接进入政治权力核心和卷入政治斗争漩涡的中心,但先后参预和介入过清末民初中国所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活动,在张謇的头上,也始终闪烁着来自官绅商学各界的各种耀眼的桂冠,诸如翰林院修撰、总理通海商务、总理两江商务局、学部谘议官、商部头等顾问官、江苏教育会会长、苏省铁路公司协理、江苏谘议局议长、农工商部大臣、东南宣慰使、两淮盐政总理、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农商部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会长等。
这些大大小小的来自国家与社会各界的头衔和职务无疑大大地提高了他在全国官场士林的声誉,也壮大了他在地方社会的声威,自然为他的南通地方事业创造了极其有利的社会条件。
张謇利用游学、游幕和短暂的仕宦之机,广泛结交政、军、商、学各界名流要人,上自中央大员,中而地方督抚,下至州县长吏,旁及地方士绅和实力派人士,纵横交织着一张由地缘、学缘、业缘、职缘、友缘等组成的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
这自然是构筑张謇地方权威的重要社会资源。
对一个地方自治领袖而言,其事业的成功与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于如何处理好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国家权力与地方精英之间的矛盾与紧张,是地方自治过程中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
而张謇在南通地方自治事业的成功,却创造了一个国家权力与地方精英关系相对调适的范例。
清末民初,中国政局变幻无常,但并未影响张謇与历届政权中枢的关系。
张謇中年以后的主要精力均倾注于他的地方自治事业。
为了使其地方自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他周旋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以求得局部的苟安。
他对政治的认识和种种肆应措施,均以其地方自治事业为转移,无论是赞同或反对,都和发展其地方事业相联系。
他惧怕局势的动荡不宁。
清末之际,他主张立宪,反对革命,寄希望于东南督抚们的支持和保护,以至提出东南互保的主张。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赞同共和,是因为“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
旋后他支持袁世凯上台,因为他害怕南北分裂酿成内战。
即使在北洋军阀混战年代,他也不惜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对各派政治力量采取平衡战略,也是为了维持南通一隅的局部平安[33]。
张謇自谓“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通官商之邮”。
对官,他是商界领袖,利用商人群体的诉求和支持,可以一争权益;对商,他有“奉旨总理通海商务”的头衔,依恃官府的权威,可以平抑来自地方保守势力的阻挠。
张謇的地方自治目标,其出发点不是要在政治上建立一个与中央权威相抗衡的由个人主宰的地方独立王国,而是在国家政权“暗蔽不足与谋”的情况下建立一个“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的人民安居乐业的新“村落”。
他一再强调:
“治本维何?
即各人抱村落主义,自治其地方之谓也。
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
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
”[34]正因为此,张謇的地方自治是从经济而非政治入手改造社会,以实业、教育、慈善作为其地方自治的三大支柱,着力于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无意于基层政治的控制和改造。
即使在人才的培养上,他也只注重农工商实业人才,而无意于法政军事人才。
张孝若即谈到他父亲创办过各类学校,惟对于法政和军事两种学校自始至终坚持不办[35]。
清末民初,中国设立最多的是法政类专门学校。
而张謇颇不以为然。
他认为这些法政毕业生“其于社会,非徒无益,而又甚害焉。
鄙人心痛之!
是以南通建设师、农、工、商、医各专门学校,而不敢及法政,诚慎之也。
”[36]尽管张謇也曾介入和参预了这个时期多次全国性的政治活动,但并未公开抵制过国家政权对南通的政治控制,也无意改造南通农村的基层政权结构。
在他看来,“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各有分工,他所致力的主要是地方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
作为地方自治领袖,尽管他实际分割和侵夺了不少国家在地方政治过程中的支配权力,但形式上通海几县的行政权一直为地方官府所掌控。
在1895-1927年间的绝大部分时期,南通几县行政官员的任免虽事先多与张謇有过商讨,但主要还是由上级官府来定夺。
就南通而言,除张詧在民国初年一度出任县知事外,张謇家族成员没有直接执掌过南通县印;地方军事权力方面,民初张詧一度出任县民军总司令,但平定地方后便迅速交权。
总之,通海几县地方军政权力基本上一直掌握在官方之手,张謇并未抵制国家行政机能在南通的发挥。
当然,一个区域现代化的成功,必须建立在相应的地方权威基础之上,否则阻力重重,以至导致事业失败。
在这方面,张謇也许没有刻意去侵夺对南通地方的政治控制权,却实现了对南通地方的实际控制。
早在民国初年之际,就有人将张詧称为“通州土皇帝”[37]。
到20年代初,正值南通事业的黄金时代,张謇在南通的权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南通土皇帝”的徽号也加到了张謇头上。
地方上的亲民之官,例如历任通、如、海、泰各县的县长、警察厅长、局长和镇守使之类,到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张謇,甚至南通警察厅厅长办案亦常向张謇请示[38]。
以张謇为首的地方精英集团还通过一些地方自治组织来实现对南通的实际控制。
通崇海泰商务总会与上海、南京、苏州总商会并列为江苏四总会。
该会成立于1904年,范围遍及南通、海门、如皋、崇明、泰县、泰兴、东台等数县商务,会员多达数万人。
自成立直至20年代中期,该会正副会长始终掌控在张謇兄弟和其他大生企业领导人之手,其职能包括联络工商,调查商情,受理商事纠纷,保护工商业利益等,实际独揽大通海地区的工商管理大权。
故商会虽在地位上较同级行政组织为低,而实际权力却足以与后者相颉颃[39],有时甚至越权干涉行政,势压县府。
有人回忆说:
“当时南通有些乡下人不明大礼,有什么纠纷,往往不到县公署,而到三先生(指张詧)主持的农、商两会去告状。
三先生一见公事便批,批起来还洋洋洒洒一大套,颇有《樊山判牍》的味儿。
地方上有什么问题,三先生主持时,大半不凭事理解决,而是闹意气的居多。
因此,南通大多数地方人士,对于张先生武断乡曲,意气自喜的作风,都极为反对。
”[40]
其时,日人驹井德三曾这样描述张謇的权威:
“今江北一带,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