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史第一谜案揭秘.docx
《中国明史第一谜案揭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明史第一谜案揭秘.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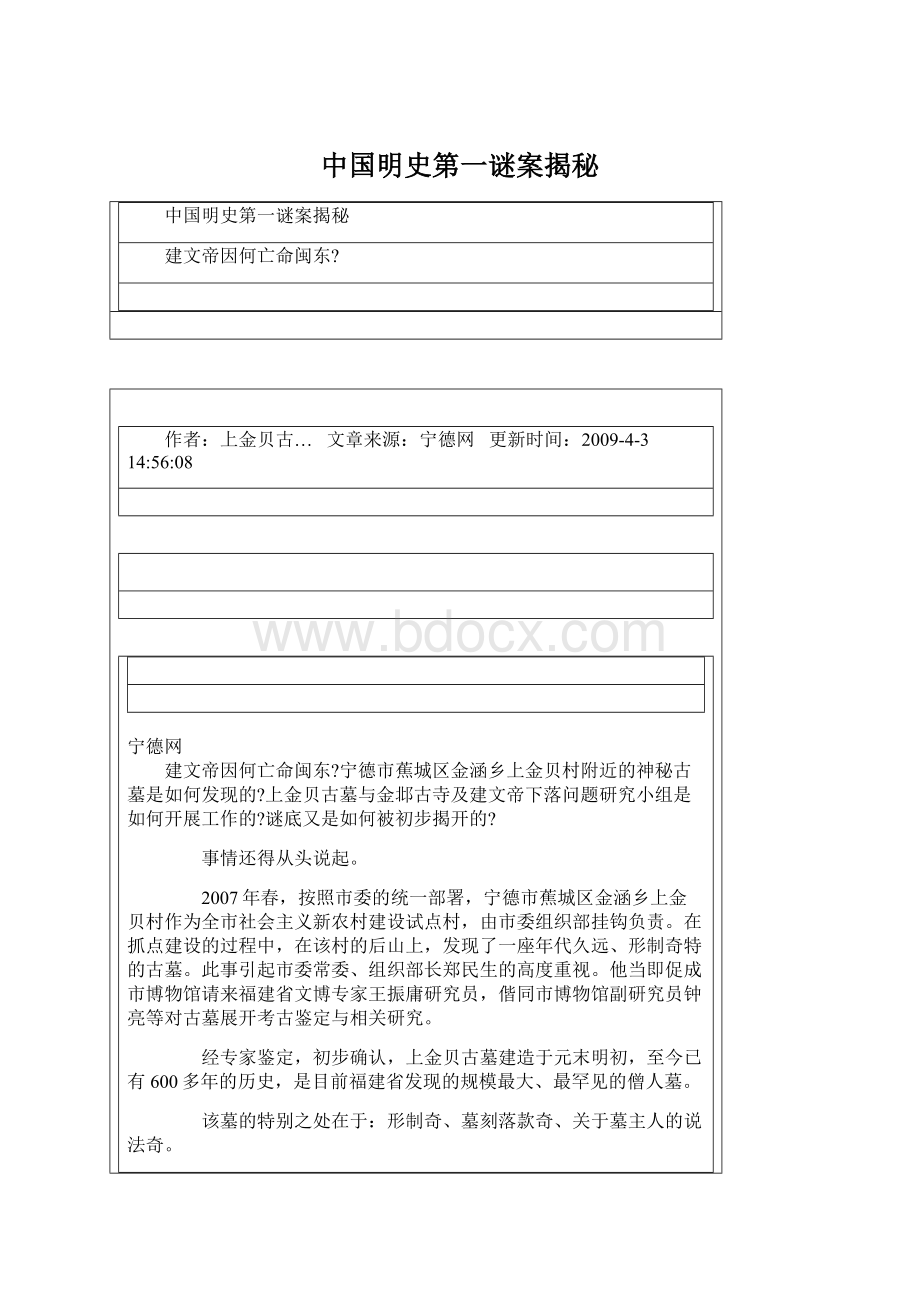
中国明史第一谜案揭秘
中国明史第一谜案揭秘
建文帝因何亡命闽东?
作者:
上金贝古… 文章来源:
宁德网 更新时间:
2009-4-314:
56:
08
宁德网
建文帝因何亡命闽东?
宁德市蕉城区金涵乡上金贝村附近的神秘古墓是如何发现的?
上金贝古墓与金邶古寺及建文帝下落问题研究小组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谜底又是如何被初步揭开的?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2007年春,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宁德市蕉城区金涵乡上金贝村作为全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由市委组织部挂钩负责。
在抓点建设的过程中,在该村的后山上,发现了一座年代久远、形制奇特的古墓。
此事引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民生的高度重视。
他当即促成市博物馆请来福建省文博专家王振庸研究员,偕同市博物馆副研究员钟亮等对古墓展开考古鉴定与相关研究。
经专家鉴定,初步确认,上金贝古墓建造于元末明初,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福建省发现的规模最大、最罕见的僧人墓。
该墓的特别之处在于:
形制奇、墓刻落款奇、关于墓主人的说法奇。
形制奇。
第一,僧人去世后,一般建塔不建墓。
此墓给人的印象是上葬墓,却又标示为“塔”,颇为另类。
第二,墓的整体宏伟壮观,格局非同一般。
墓葬坐北朝南,临海琚山,龙珠高照,双鲤朝天。
三进的布局,九级的台阶,丈八高的拜亭,三丈六阔的墓坪,处处体现出一种缩小了的皇家气派。
第三,墓的各种构件精致豪华,寓意深刻,尤其是墓顶上那一颗莲花座托着的火龙珠,使人们不由的联想起整座墓形犹如一个“炆”字。
墓主朱允炆五行缺火,所以墓顶用一“火龙珠”罩顶。
同时,这一“火龙珠”又是墓主朱允炆的象征(由“沧海珠”推测而来),“莲花座托着火龙珠”则象征着仙逝后的墓主朱允炆已升入天界,龙归沧海。
第三进是奇特的圆形圈椅状主陵,象征着龙椅——皇位。
龙椅前圆形印状舍利塔则象征着玉玺——皇权。
第二进两边厢的“双鲤朝天”,“鲤鱼”象征着追随建文帝出亡的众臣与不愿归顺新主而逃散的众大臣。
“天”即“天子”之意,象征着建文帝,所雕刻的鲤鱼不同于寻常建筑场上的鲤鱼那样头朝天,尾向地,而是尾朝天,头向地,成跪拜状,寓意十分明确:
随侍的众臣与逃散的众臣依旧臣服与朝拜他。
第一进那高大的拜亭与宽阔的墓坪,以及两边厢那没有尾巴的龙头龙身与裙摆,则象征着墓主人虽不在位,但依旧是皇宫内院的主子与群龙之首之意。
整座墓给人一种处处暗藏着玄机的感觉,它既深刻地揭示了墓主人的特殊心理,又明白地向后人传达了造墓人的心思,真可谓高明之至。
显然,这样的墓葬不是寻常和尚所能够拥有的,而身为奴才的太监又不致于如此张扬。
因此,王振庸研究员认为,墓主人拥有非同寻常的身份,拥有十分可观的财富。
墓刻落款奇,该墓舍利塔墓刻落款为“御赐金阑佛曰圆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之塔。
”但没有镌刻朝代和纪年。
对此,王振庸研究员的解读为:
“御赐金阑佛”是指墓主,因墓主袈裟是皇帝所赐。
“圆明大师”应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第三代”是孙辈之意,与“朱允炆 是朱元璋之孙”暗合。
“沧海”是法号,暗喻神州一统的帝王心理。
“珠”是俗家名字的后一字,是“墓主姓朱,本是帝王之意”。
我们研究小组的解读稍有不同,我们认为,“御赐金阑佛曰圆明大师”这句话应该连在一起读,不能断开,整句话的意思应为“玉皇大帝钦赐予袈裟的佛尊称为圆明大师的。
”理由是,稍懂一点中国皇帝史的读者应都懂得,太凡开国之君,都认为自己是天上玉皇大帝派往下界为王,不是凡人。
尤其是对外宣传更强调这一点。
他们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玉皇大帝所赐,包括身上穿的。
朱元璋当过和尚,自然认为自己身上的所穿的袈裟是玉皇大帝所赐。
而塔碑上朝代、纪年的有意空缺,恰恰印证了墓主人不能为人道的特殊而神秘的身世。
鉴此,王振庸研究员认为,该古墓有可能就是600多年来史学家苦苦寻找的明朝建文皇帝朱允炆的陵寝。
关于墓主人的说法更奇。
该墓除了“皇帝”说之外,还有“僧人”说与“太监”说。
“僧人”说者认为该墓墓主人是元大德间金邶寺住持止云沧海禅师的墓,但证据不足。
笔者认为,若是止云沧海禅师的墓,为何不在舍利塔碑刻上镌刻上“沧海云禅师之塔”,而镌刻着“沧海珠禅师之塔”。
显然是说不通的。
“太监”说,系在上金贝村周边乃至邻近的周宁、古田、屏南、福安等县(市、区)广为流传的说法。
少数人传说金太监是金国(指后金,即元朝)人,姓谢,曾当过太监。
持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为金邶寺已故住持妙通和尚,及寺里的僧人。
多数人传说金太监是明朝太监,或说他是永乐皇帝下派监造支提寺大雄宝殿的,之后在宁德出家,并葬于上金贝的;或说他是为皇帝押送御赐物品到支提寺的,归途病逝于金邶寺,就近安葬的。
还说,金邶寺就是因为建了这座“太监墓”,才被朝廷派兵焚毁的。
持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为原宁德佛教协会会长陈石文居士及上金贝村的畲族群众。
我们研究小组附带研究与考证了这后两种说法。
据《支提寺志》《宁德县志》(清乾隆版)《周墩区志》(民国版)和新编《周宁县志》《柘荣县志》载,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派钦差中使周觉成,护送皇帝手书“华藏寺”匾额到支提寺,并留寺监造大雄宝殿。
后改任闽东银场督办太监。
其人死后墓葬在柘荣县黄柏乡天星寺后山。
显然,监造支提寺大雄宝殿的是“周太监”,而不是“金太监”。
又据《支提寺志》《长溪琐语》和支提寺现存的明代木刻《支提寺全图》说明文字载:
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朱棣曾遣使三宝太监郑和监运皇太后所赐千尊铁佛至支提寺。
可见,史书与志书上记载的监运御赐品到闽东来的太监是郑和,而不是这个“金太监”。
那么,到底明初朝庭里有没有“金太监”其人呢?
这个金太监到底有没有来过闽东呢?
我们研究小组经过艰苦细致地查找,果然在《明代的宦官》一书中找到了金太监其人。
此君叫金英,安南人。
十三岁入宫作太监。
历侍明太宗、仁宗、宣宗、英宗。
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时升任司礼监右监丞。
我们的判断是,如果蕉城区金涵乡上金贝周边地区的关于金太监的传说属实(仅指金太监有到过闽东一事),那么,应该是在这一时间点。
而且,金太监到闽东来应是来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可能与建文帝的事有关)。
他的行踪是不会载入史册的。
所以,后人是不可能从正史方志中窥见他的踪影的。
同时,也正是这一点,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建文帝确曾亡命闽东,上金贝古墓主有可能是建文帝。
而金英其人后半生结局如何,我们这儿不妨稍带一笔,向大家作个交代。
明正统七年(1442),金英升任司礼监太监。
明景泰三年(1452),又升任南京守备太监。
死后墓葬南京。
所以,我们研究小组也认为,这座“僧不僧,俗不俗;官不官,民不民;皇不皇,王不王”的神秘古墓墓主应是建文帝无疑。
据说,考古专家曾挖开坟墓地宫,里面空无一物。
地宫发现多个盗洞,说明陵墓多次被盗。
部分研究小组成员认为这墓是阴阳坟中的阴穴,应该还有一处阳穴。
目前正在探索之中。
以上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神秘古墓是如何发现的,以及古墓“奇”在何处?
“秘”在哪里?
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研究小组和我们的研究工作。
自从“上金贝古墓里躺着建文帝”一文见之于报端后,马上激起了市直机关一批有识之士的极大兴趣。
强烈地政治敏感性使这些同志意识到,这项工作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性与寻秘热问题,而是一个事关闽东的发展大局的问题。
在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民生的极力促成与大力推动下,“宁德市上金贝古墓与金贝古寺及建文帝下落问题研究小组”便应运而生了。
参加研究小组完全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是一种志愿者行为,宗旨是:
只讲奉献,不讲报酬;重在参与,不求辉煌;周末行动,各司其职;聚散无常,机动灵活。
研究小组由最初的5个人,护展到现在的30多人,而且还延伸到4个县直机关。
研究小组的工作得到了市委组织部的大力支持与郑民生部长的适时指导与引导,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始终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轨道前进。
我们研究小组把主题确定为:
揭开明史第一谜案——明建文帝下落问题探讨。
主要意图和目的是:
通过研究古墓与古寺,寻找建文帝由浙入闽的证据,寻找建文帝入闽时的初始目的地的证据,寻找建文帝因何亡命闽东,最终隐跸金邶寺的证据。
同时,兼顾寻找古墓被盗而散落民间的文物以及与建文帝亡命闽东有关的文物,以证明古墓墓主就是600多年来,中国史学家苦苦寻找的明朝建文皇帝朱允火文的陵寝。
以达到揭开这一历史谜团之目的。
同时,借机以提升宁德市的文化品位与知名度,为环三都澳发展战略挖掘与增添一新的旅游资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
至于研究的方向,我们认为,凡事都有个起始与开端的问题。
要做好这篇大文章,还是应该踏踏实实,从头做起。
任何投机取巧式地做学问都是不可取的。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问题,争论了几百年,参与争论的史学家不下几百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因此,极需我们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避开纠缠,直奔主题。
对于“自焚说”“折衷说”“出亡说”,我们赞成“出亡说”。
对于古墓的“僧人说”“太监说”“皇帝说”,我们倾向“皇帝说”。
对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三大巨著,我们则把浏览、搜索与查阅重点放在《续修四库全书》。
果然,在《续修四库全书》中,我们找到了明末遗民查继佐编著的《罪惟录》一书,找到了有关建文帝下落的二十三种说法,找到了被历朝历代专家忽略了的“二十三说”中的两说,即“由温州入闽说”与“在福州雪峰寺和郑和会面说”。
这是我们研究工作的第一个突破。
我们循着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我们在听取雪峰寺副住持明生法师的介绍和查阅了《雪峰山志》后,对雪峰寺第六十七代住持洁庵禅师的身世与传奇故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我们发现,永乐中,不但郑和到过雪峰寺,而且胡滢也到过雪峰寺,且福建镇守太监冯让等多名要员也到过雪峰寺。
显然,这一现象绝非偶然,其中必有内在原因,尤其是胡滢的行动。
为此,我们仔细研究了《雪峰山志》的编纂者,明代徐勃所写的关于洁庵禅师的小传以及明成祖派出寻找建文帝的胡滢为纪念洁庵禅师兴寺功绩而写的碑文,觉得此中大有文章。
第一,徐勃写的洁庵禅师小传中明确记载了洁庵禅师从小在宁德(今蕉城)三峰寺(今南峰寺)、安仁寺当过小沙弥。
而胡滢所写的碑文在简介洁庵禅师的身世时,则不写这段经历。
显然,细心的胡滢似乎在掩盖什么。
第二,徐勃写的洁庵禅师的小传中,明确记载了洁庵禅师曾经拜谒过南京钟山灵谷寺住持谦禅师,并入门为徒,得其真传,后被朱元章钦命为泉州开元寺住持。
永乐二年(1404)朝京回榕旋被众山长老推举为雪峰寺住持。
而胡滢的简介中则省去了诸多细节,突出了洁庵禅师在杭州昭庆寺的经历,只点灵谷,不言钟山,其用意十分明显且深刻。
显然是不想让人们详细了解洁庵禅师的身世,尤其是不想让人们知道洁庵禅师在宁德的经历。
很显然,在当时的宁德(蕉城)方面一定隐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是因为建文帝隐跸在金邶寺)。
第三,徐勃言洁庵禅师的师傅叫“谦禅师”,而胡滢则云其叫“巽中禅师”,其用意也是十分明确的。
他不愿人们了解洁庵映禅师的师傅惠明谦禅师的详细与真实的情况,以免引起人们的联想。
联想到洁庵禅师曾在宁德三峰寺、安仁寺当过小沙弥,在泉州开元寺当过住持,我们感觉到,这个洁庵禅师与建文帝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于是,我们把查找与寻访的视线相对集中到了洁庵禅师这个与建文帝关系密切的关键人物身上。
我们二上浙江,到宁波天一阁,目的是为了这个。
我们找遍市内的古田、屏南、周宁、寿宁、福安、蕉城的10多个乡镇,目的也是为了这个。
我们在金涵乡上金贝村及其周边地区掘地三尺,目的还是为了这个。
我们之所以把查找与寻访“志乘之支流”,即由私人编的乡志、村志、山志、寺志、琐记、杂记等作为我们研究工作的重点,是基于以下几种原因考虑的;第一,正史与官修地方志,历朝历代的专家学者都研究透了,我们是难以超越的。
第二,明成祖在夺取政权之后,有组织地进行了一次文化清洗活动,借编写《永乐大典》的名义,搜求天下图书,把所有涉及建文帝的文字资料与图书,作了个彻底的清理。
同时还严令各级官吏,作出与之相应的行动。
此举导致今日国人难以见到建文帝的任何手迹。
如果上金贝古墓墓主确是建文帝,那么永乐帝以至他后续的几任皇帝,对闽东的文化历史与图书资料的清理和控制也一定是十分严厉的。
我们从明代编的嘉靖版《福宁州志》与万历版《福宁州志》不约而同地残缺《寺观》《杂记》两卷即可窥见一斑。
从清代编的《福宁府志》《建宁府志》《温州府志》以及闽东各县县志中,找不到一个字的有关建文帝事迹的记述,也可窥见一斑。
这种情况,在苏南与浙西是不存在的。
可见,对永乐皇权来说,当时的福宁州全境是个“重灾区”,清理可谓是彻底的。
我们认为,其清理的时间点应该是永乐中或永乐二十一年或永乐二十二年,抑或稍晚些。
永乐年间对当时的福宁州的文化清理与控制影响了尔后几个朝代,直至今日,我们还可感觉到它的影响与危害。
比如,建文在位四年间,福宁州所辖各县中进士者有10多人,但是,民国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仅收录1人(黄宜)。
清编《宁德县志》仍记载黄宜与另一名进士姚熊为“洪武三十二年进士”,而未用建文年号。
以至新编《宁德地区志》也采纳《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说法,造成历史严重失真。
这些,也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建文帝确曾亡命闽东,上金贝古墓墓主有可能是建文帝。
我们这种“剑走偏锋,由偏入手,不问正史,只重小乘,绕道而走,直奔主题”的研究办法果然有效。
我们相继找到了《雁荡山志》《太姥山全志》《长溪琐语》《支提寺志》·《支提寺全图》(《支提山志》因被香港某寺庙僧人“借”去,一时无法取得),并加以研究,从中又有了新的发现。
第一,从《长溪琐语》中,我们找到了永乐五年(1407),三宝太监郑和监运千尊铁佛的记载。
第二,从找到的《支提寺全图》(明代木刻)的文字记述中,也印证了上述史实。
郑和到达支提寺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送御赐品的问题说明早在永乐五年时建文帝及其手下活动已引起永乐帝和锦衣卫密探的注意。
只是找不到建文帝真身,没有证据不能对金邶寺动手,只能监视而已。
第三,《太姥山全志》中,发现了有关洁庵映禅师的师傅慧明谦禅师的资料。
慧明谦禅师系明福宁县劝儒乡(今福鼎市)桐冈人,俗姓李,原在太姥山昭明寺出家,师从志宏禅师。
明洪武十六年(1383),被朱元璋钦命为南京钟山灵谷寺住持(洁庵禅师是明洪武十九年到钟山灵谷寺拜师的)。
圆寂后塔葬于太姥山摩宵庵前。
这一资料的发现,无异于雪中送炭,又为建文帝亡命闽东与上金贝古墓主皇帝说又添一新证。
大家可以想一想,慧明谦禅师是闽东福鼎人,洁庵映禅师从小在闽东宁德(今蕉城)的三峰寺、安仁寺出家。
他们对闽东的情况是再熟悉不过了。
何况洁庵映禅师还当过泉州开元寺住持、福州雪峰寺住持,领袖福建省宗教界。
建文帝想要复国,就需要取得洁庵映禅师的支持与保护。
因此,我们认为,建文帝入闽的初衷与目的之一,就是寻找先在泉州开元寺任住持,后至福州雪峰寺任住持的洁庵禅师,以争取他的支持与保护。
查继佐《罪惟录》一书中的记载,证明建文帝已经找到了洁庵禅师(是永乐二年以前在泉州开元寺找到的,还是永乐二年以后在雪峰寺找到的,我们正在探索与研究之中)。
而《雪峰山志》中记载的,永乐十五年冬郑和到雪峰寺,永乐十七年冬胡滢到雪峰寺,永乐十六年洁庵禅师受方处高人指点迷津,毅然辞去雪峰寺住持一职,并随即离开雪峰寺。
《雪峰山志》与胡滢所撰碑文都说他退隐钟山灵谷寺。
而我们则认为他没有回南京,而是到金邶寺建文帝那儿去了。
何以见得?
因为洁庵禅师辞职一事本身就说明了洁庵禅师早先已答应建文帝的请求,并参与了建文帝的复国活动,为他的活动提供过支持与保护。
不然,他何须突然隐退。
作为一代高僧的他,既然参与了建文帝的复国活动,是决不会半途而废的,是决不会弃建文帝而不顾,退隐钟山灵谷寺的。
因为那不符合高僧的人格与做事准则。
所以,我们认为修于明季的《雪峰山志》是受胡滢的碑文的影响而这样写的,而胡滢的碑文则是欲盖弥彰。
洁庵禅师圆寂后,既未归葬雪峰寺塔林,亦未归葬南京钟山灵谷寺,此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论断。
另外,雪峰寺副住持明生法师在向我们介绍雪峰寺的历史情况时也说,寺内僧人代代相传,洁庵禅师是个神秘的僧人,大家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一点,与寺志及胡碑所记大相庭径,但却佐证了我们的观点。
此也正是胡滢要留下一篇碑文加以说明此事的原因所在。
我们认为,刘伯温后人的指点(下文会论述到)是建文帝选择闽东宁德(蕉城)作为复国的根据地和大本营的第一因素,而洁庵禅师的闽东情结则是第二因素。
正是这两条,构成了建文帝亡命闽东的主要原因,也正是这两条,成为上金贝古墓墓主系建文帝的两条有力证据。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凭着朱元璋生前与慧明谦禅师、洁庵映禅师师徒二人的交情(二人都是朱元璋钦命的住持),朱元璋临终前将朱允炆托咐给洁庵禅师是完全有可能的。
正因如此,注定了洁庵禅师是没有理由拒绝朱允炆的。
对朱允炆来讲,获得洁庵禅师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他开展活动与举事就没有经济上的保障,因为只有寺庙才能够向他提供这一支持。
从建文帝仙逝后墓葬的豪华程度就可窥见一斑。
而就洁庵禅师来讲,他也确实做到了。
他对建文帝的保护和支持是倾尽全力的。
我们推测,甚至永乐二十一年建文帝仙逝后的丧事与墓葬有可能都是他一手操办的。
因此,研究慧明谦禅师与洁庵映禅师也就成为我们研究小组的工作重点。
发现洁庵映禅师与建文帝的特殊关系,这是我们研究工作的第二个突破。
我们在市内各县的调查与寻访中,发展了一个奇怪现象,永乐年间(初步判断为永乐中或永乐二十一或二十二年),在闽东通往周边的浙南、闽中的古官道两侧,有几十座寺庙同时被毁,几千名僧人同时被杀。
对这一曾经发生在闽东大地上的历历惨案,正史与官修地方志虽然没有一个字的记载(其他年代被毁的寺庙都有记载),但是,民间与宗教界都代代相传此事。
那些至今还静静地躺在被毁寺庙遗址的泥土里和荒草丛中的大量的明代的石碑、石槽、石柱、石础、石臼及明代的砖瓦和陶瓷碎片似乎在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当年这一幕幕人间惨剧的发生经过。
历史是割不断的,它也是无法永久掩盖的。
这一状况引起了郑部长的高度重视,他要求研究小组设法核实这一历史资料。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细致的调查、挖掘与实地堪察,根据当地群众的口碑资料与我们看到的现状(大量倒复的石柱、东倒西歪的石槽、石碑、石础、石门臼,以及大量的瓦片、瓷器、陶器碎片(全部都是明初及其以前朝代的),我们认为闽东境内被毁寺庙计有古田县的瑞岩寺、香林寺、显得寺,屏南县的灵峰寺、宝岩寺、后院寺,周宁县的灵鹫寺、云门寺、凤山寺、灵峰寺、瑞龙观,蕉城区的祭山寺、天王寺、金邶寺,寿宁县的九峰寺、凤阳寺、平溪寺,福安市的兴庆寺、狮峰寺,福鼎市的昭明寺等。
这只是一个大约的数字,实际被焚毁的决不止这么多。
因为福鼎、霞浦、柘荣、福安等县(市)还没展开全面调查,浙南、闽中的情况也不知道,只知道罗源县的中房寺也是在相同的时间内,以相同的理由被焚毁。
其中,最典型的是周宁县咸村镇中川村的素有“一龟二凤三支提”之称的凤山寺,一夜之间,全寺990多名僧人踪影全无。
这些僧人是死是活、或逃或被杀,村里人竞然一无所知,堪称怪事一桩。
还有寿宁县武曲镇的凤阳寺,毁寺杀僧之后,又把周边的5-6个村庄烧了个一干二净,村民(原住民)无一幸免。
这些被毁寺庙在被毁的时间上是惊人的一致,都在永乐年间(应是永乐中或永乐末年,因为据上金贝的畲族村民讲,祖上人都说,金邶寺就是因为那座太监墓造了之后,朝廷震怒,才派官兵捣毁了坟墓,烧掉了寺庙);在地点上是惊人的一致,大部分都在以金邶寺为圆心的周边地区的古官道两侧;在被毁原因(当然是官方宣传的)上也是惊人的一致·(都说这些寺庙僧人行为不轨,在寺内挖掘地道,建造密室,坑害良家妇女)。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些寺庙的确多建有密室,部分还挖有坑道,例如周宁县咸村镇云门寺后山即有一坑道口,至今仍由2米多长的条石封口;屏南县棠口乡三峰寺后山上,也有类似的条石封口的坑道口;寿宁县武镇凤阳寺后山,据说也有一条密道(即坑道)通向山上的“山寨”;还有,罗源县中房寺也有密室与坑道通向“山寨”。
……显然,这不是一种单个的行为,而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行为。
因此,当时的被朝廷摧毁的决不是一、二座寺庙,而是一个接一个地被“定点清除”与“连锅端”。
用僧人坑害良家妇女这一借口毁寺杀僧,最易引起群众的愤怒与同情。
这是一个既聪明又残酷的做法。
聪明之处就在于一箭双雕,既达到了逐步摧毁建文帝及其手下辛苦建立起来的复国据点,消灭了建文帝留在寺庙的影响和踪迹,同时又掩盖了朝廷一直在宣传的建文帝已“自焚”而亡的“自焚说”。
朱棣和手下的骗术,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是有效的,在现代就行不通了。
人们把整个行动连成一片来看,破绽立马就显现出来了。
“不可能所有的寺庙、全部僧人都在干这缺德事,这显然是一个借口”,众人都异口同声这么说。
可是,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什么600多年来,历朝历代的官府、百姓、史学家们都在保持缄默,一句不吭?
原因何在?
这是值行我们加以研究的。
这一现状是客观存在的。
它的存在,一方面印证了清代谷应泰编写的《明史纪事本末》一书中对朱棣的评述:
“朱棣率军攻破金川门,大开杀机,大杀建文旧臣宿将,从开国元勋到列侯,诸司官吏衙役,进士、儒臣、监生、地主、僧道,一直到平民,一有牵连,立刻丧身灭门,杀得气氛恐怖,朝野寒心”。
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建文帝亡命闽东确有其事,上金贝古墓墓主是建文帝。
在闽东地面上毁寺杀僧这一历史事件,应是建文帝亡命闽东的第三个有力证据。
这是我们研究工作的第三个突破。
在赴省外与市内的外调工作告一段落后。
我们开始着手疏理手头所掌握的资料。
我们对600年来,史学界开展的研究建文帝下落问题这一课题的全部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整理出了《关于明史第一谜案:
明建文帝下落问题研究概况》这第一份综合性资料。
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比较系统研究建文帝下落问题这一历史课题的,一是明末清初的史学家查继佐,一是清初的官僚出身的史学家谷应泰。
这两个人,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查继佐的代表作是《罪惟录》(原书名为《明史》,书中的《建文逸记》部分,列举了建文帝下落问题的二十三种说法,并对二十三说作了全盘否定。
查继佐认为这二十三说主要来源于两部伪书,一是托名为史仲彬著的《致身录》,一是托名为程济著的《从亡随笔》。
查继佐还对《致身录》提出了“十六辩”。
查继佐与《罪惟录》的缺点是对二十三说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与客观分析,而是一概否定。
这显然不是一个史学家应有的治学态度。
但是,清代以后的学者编写明代史书,多从《罪惟录》中取材,所以该书仍不失为研究明史与建文帝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而谷应泰所著的《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卷》中对建文帝下落问题的记述,大部分照搬照抄《致身录》与《从亡随笔》的内容,不加分析研究地记载了建文帝云游四海(江苏、浙江、湖北、贵州、云南、四川、青海、广西、广东)39年的经历,并认为建文帝活了64岁。
谷应泰与《明史纪事本末》的缺点是十分明显的。
尤其是对明代的重要历史事件暨对与建文帝下落问题有关的郑和下西洋一事未作记载,对明清之际的史事也避而不谈,是十分不应该的。
还有,作者受“天命论”思想的影响,在记述“燕王起兵”一事时就表现的十分明显。
这也是一大缺憾。
《明史纪事本末》虽然缺憾较多,对后代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以致一部分明史研究专家误入岐途。
但是,由于它比清编《明史》要早80多年,又是综合了许多明代史料编纂而成的,兼之陈古鉴今,内容丰富,仍不失其史料价值。
后人考订明史之作,对它多所取资。
上述两部代表性专著的优点与缺憾,主因是受时代与历史的局限,兼之统治者的压力与信息的不发达,还有朱棣及其后人的刻育歪曲和掩盖。
有关建文帝的史料的大量失真,也是这个原因。
所有这些,造成两位史学家和尔后的一些研究者的失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至于两人以后的几百位史学家对该问题(指建文帝下落问题)的探索与研究,陷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怪圈,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