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民事强权概念决定性因素及其发展.docx
《欧洲民事强权概念决定性因素及其发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欧洲民事强权概念决定性因素及其发展.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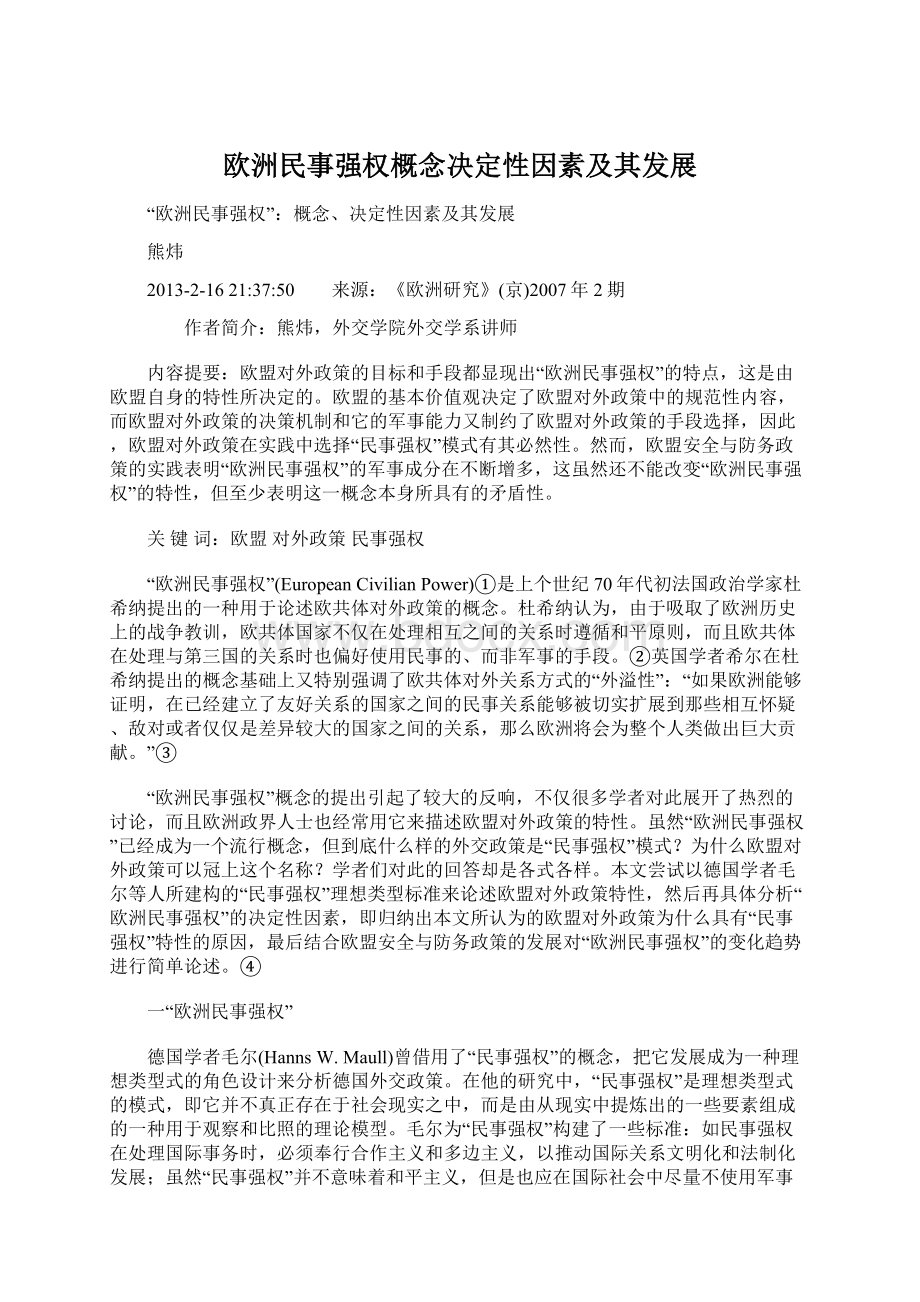
欧洲民事强权概念决定性因素及其发展
“欧洲民事强权”:
概念、决定性因素及其发展
熊炜
2013-2-1621:
37:
50 来源:
《欧洲研究》(京)2007年2期
作者简介:
熊炜,外交学院外交学系讲师
内容提要:
欧盟对外政策的目标和手段都显现出“欧洲民事强权”的特点,这是由欧盟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欧盟的基本价值观决定了欧盟对外政策中的规范性内容,而欧盟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和它的军事能力又制约了欧盟对外政策的手段选择,因此,欧盟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选择“民事强权”模式有其必然性。
然而,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实践表明“欧洲民事强权”的军事成分在不断增多,这虽然还不能改变“欧洲民事强权”的特性,但至少表明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
关键词:
欧盟对外政策民事强权
“欧洲民事强权”(EuropeanCivilianPower)①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法国政治学家杜希纳提出的一种用于论述欧共体对外政策的概念。
杜希纳认为,由于吸取了欧洲历史上的战争教训,欧共体国家不仅在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时遵循和平原则,而且欧共体在处理与第三国的关系时也偏好使用民事的、而非军事的手段。
②英国学者希尔在杜希纳提出的概念基础上又特别强调了欧共体对外关系方式的“外溢性”:
“如果欧洲能够证明,在已经建立了友好关系的国家之间的民事关系能够被切实扩展到那些相互怀疑、敌对或者仅仅是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欧洲将会为整个人类做出巨大贡献。
”③
“欧洲民事强权”概念的提出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不仅很多学者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且欧洲政界人士也经常用它来描述欧盟对外政策的特性。
虽然“欧洲民事强权”已经成为一个流行概念,但到底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民事强权”模式?
为什么欧盟对外政策可以冠上这个名称?
学者们对此的回答却是各式各样。
本文尝试以德国学者毛尔等人所建构的“民事强权”理想类型标准来论述欧盟对外政策特性,然后再具体分析“欧洲民事强权”的决定性因素,即归纳出本文所认为的欧盟对外政策为什么具有“民事强权”特性的原因,最后结合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对“欧洲民事强权”的变化趋势进行简单论述。
④
一“欧洲民事强权”
德国学者毛尔(HannsW.Maull)曾借用了“民事强权”的概念,把它发展成为一种理想类型式的角色设计来分析德国外交政策。
在他的研究中,“民事强权”是理想类型式的模式,即它并不真正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而是由从现实中提炼出的一些要素组成的一种用于观察和比照的理论模型。
毛尔为“民事强权”构建了一些标准:
如民事强权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必须奉行合作主义和多边主义,以推动国际关系文明化和法制化发展;虽然“民事强权”并不意味着和平主义,但是也应在国际社会中尽量不使用军事手段,武力只是在自卫、集体防御、维护集体安全和人道主义目的下才可以使用,而且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国际关系的“文明化”;作为“民事强权”,它的外交政策还应努力推动超国家机构的发展,并且愿意向超国家机构让渡主权。
⑤与此类似,德国学者于内曼和舍尔尼希在分析欧盟对外政策时,也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所谓“民事强权”模式代表的是欧盟对外政策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虽然现实中的欧盟对外政策并非完全如此,却是应该努力做到的方向:
有意识地放弃传统的权力政治方式;积极促进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文明化”;促进西方民主和人权理念的实现。
⑥
按照上述学者的观点,“欧洲民事强权”实质上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理论模式,它体现了欧盟对外政策的价值观追求和自我定位,而且作为一种韦伯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工具,他们所建构出的“欧洲民事强权”模式标准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欧盟对外政策目标、手段和效果的实质性要素。
从欧盟对外政策的实践来看,欧盟官方文件中所体现的自我认知比较明显地凸现了想要成为“欧洲民事强权”的意愿。
⑦欧共体自诞生之日起,即确立了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秩序性目标,这首先是指欧共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想,即欧共体不仅仅是一个为了处理经济问题而建立的欧洲国际组织,它还是一个在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基础上构建的共同体。
⑧自上个世纪70年代始,欧共体不满足于只在内部关系中实现民主、法治和人权原则,进而主张在发展与第三国关系时也尊重此种原则,以推动所谓国际关系“文明化”进程。
⑨冷战结束以后,欧盟政治家更加强调全球治理的世界秩序理念,主张通过社会经济手段和法治化手段实现国际稳定。
⑩在2003年6月出台的《欧盟安全战略报告》中,民主、法治化和“善治”是其世界秩序目标的核心内容。
以价值观和规范性的标准来衡量,“欧洲民事强权”模式始终是欧盟(欧共体)对外政策所要实现的整体战略目标。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欧盟发展了一系列经济、外交手段,并且通过对外经济政策、联系国政策、发展援助政策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将这些对外政策手段整合成多层次和多元化的体系。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欧共体就开始以经济手段作为开展对外政治关系的工具,比如用签订贸易协定的方法吸引东欧国家以起到渗透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在欧盟对外政策中,经济和政治结合得越来越紧密。
欧盟在发展与第三国的经济关系时,尤其是在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对政治性条件强调得越来越多。
欧盟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大量财政援助,仅在1998年这种直接援助的金额就达到600亿欧元。
这些财政援助首先是被用于与欧盟地理上邻近的地区,欧盟附加的条件是那些得到财政援助的国家必须实行西方式民主和保护人权。
(11)
贸易、经济合作和联系国协定也日益成为欧盟对外政策的工具。
欧盟与第三国签署的几乎每一个经济合作协定和联系国协定都包含有“政治对话”的内容。
开启与第三国的类似协定的谈判往往是一个政治决策过程,但不一定是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框架下开始的,欧盟坚持要求对象国首先必须先满足经济和政治的条件。
启动谈判和对签署协定的考虑即是表达了欧盟对该国的政治支持,而协定内容也进一步反映了欧盟对该国的鼓励和肯定。
(12)如欧盟同东欧国家签订的“欧洲协定”就突出体现了欧盟的这种政策倾向,该协定具有明显的政治条件性,要求联系国继续政治和经济的改革,遵守法治国家和人权原则等等。
尽管形式上它是一个经济协定,但又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
(13)
1993年6月,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公布的新成员国入盟标准,再次强化了欧盟对外政策的政治原则:
哥本哈根标准要求申请国必须具有保障民主、法治、人权和尊重与保护少数民族的稳定的制度;具有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和应对欧盟内部竞争压力和市场力量的能力;具有履行成员国义务的能力,包括保证恪守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目标。
(14)
欧盟对外政策中的外交手段带有鲜明的合作型外交战略特点,表现在欧盟外交对多边主义、对话和调停等手段的偏好。
虽然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并非总用“一个声音”说话,但据韦塞尔斯的统计,从总的趋势来看,欧盟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共同立场和共同外交行动是逐年增加的。
(15)《马约》签订以后,欧盟外交日益活跃,为许多地区的和平进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根据不同的情况,欧盟扮演的外交角色也各有不同,其中既有穿梭斡旋工作,也有直接参与的外交调停。
在应对地区性危机方面,欧盟在冷战后投入越来越多的注意力。
欧盟理事会任命了很多特别代表参与地区危机的处理。
1996年,欧盟指派莫拉蒂诺斯(MiguelAngelMoratinos)与中东和平各方保持密切联系;前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FelipeGonzalez)被委任为欧盟特别代表直接参与1998年科索沃问题的解决;2001年,欧盟又委派阿什当(PaddyAshdown)为高级特别代表关注波黑问题的解决;至2005年,欧盟在全球各种关键的冲突地区如巴尔干、摩尔多瓦、非洲大湖区、中东、南高加索和阿富汗共派遣了8名特别谈判代表参与危机斡旋,负责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与冲突各方之间的联系以及协调欧安组织、联合国和欧盟各机构在应对地区危机上的协调工作。
(16)
欧盟在世界各地都大力支持地区性合作,而且努力使这些合作进一步机制化。
代表性的例子有:
旨在促进中东欧国家之间缓和边界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的“巴拉迪尔计划”、1994年签订的促进中东欧国家转型的“法尔计划”、1995年签订的《欧洲稳定公约》,以及欧盟倡导的重建巴尔干的《东南欧稳定公约》等一系列地区合作计划。
(17)在发展与其他地区和国家关系上,欧盟建立了一种所谓“集团对集团对话”形式,在这种对话机制下,欧盟开展了与东盟国家、中美洲国家、海湾国家的对话。
虽然这种集体对话形式的外交效果还很难估计,但是对于欧盟来说,它至少起到了构建世界政治中的集体身份的作用。
依照毛尔等人建立的标准来看,欧盟对外政策在实践中的目标和手段都比较符合“欧洲民事强权”理论模式的要求,即以民事、合作和多边主义手段促进国际关系“文明化”发展,通过社会经济手段和法治化手段来实现国际稳定。
二“欧洲民事强权”的决定性因素
欧盟对外政策在长期实践中所体现的特点即是“欧洲民事强权”模式的实质性要素,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对于大多数研究“欧洲民事强权”的学者来说,众说纷纭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欧盟对外政策为何是“欧洲民事强权”的问题上。
许多标榜“欧洲民事强权”的政界人士和推崇观念因素的学者偏好用欧盟的基本价值观来解释“欧洲民事强权”形成的原因。
根据曼内斯的研究,欧盟的基本价值观因其历史背景、政治架构和人权、法制等宪法性规范而呈现出其特有的独特性。
(18)在欧共体成立之时,欧洲人民普遍把民族主义当作引起世界大战灾难的罪魁祸首,因而欧共体从一开始就是要构建一个能够超越国家主权观的安全共同体,这个安全共同体内部的基本价值观可以不受民族主义的限制而互相包容,成员愿意合并他们的民族国家资源以维护和加强西方的自由与民主。
也有学者认为,只有坚持和强调这些价值观,欧盟各成员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认同”才有可能转化为欧盟对外政策的“集体认同”。
他们比较了荷兰、德国、法国、丹麦等国的对外政策“认同”,分析了它们在欧盟对外政策意义上相互兼容的可能性,发现丹麦难以接受德、法的超然一等地位,丹麦不愿失去其“北欧”和作为“联系者”地位的特殊身份;同时,法国的“欧洲作为第三种力量”的目标也难以和其他国家的“认同”相兼容。
(19)因此,“欧洲民事强权”模式的价值观基础还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各个成员国的功能性作用。
虽然欧盟在价值观上的特点决定了欧盟对外政策中的规范性内容,但是如果要解释“欧洲民事强权”的成因的话,仅仅依靠观念因素还无法保证欧盟对外政策必定形成“欧洲民事强权”模式。
正如德国学者登宾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无论从民主和平论、还是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价值观因素都不能构成“欧洲民事强权”模式的因果解释。
(20)而且,由于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欧盟成员国依旧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欧盟成员国各自的外交政策特点就不容忽视。
虽然德国、奥地利国内有着很强的“民事强权”公共舆论支持,可是传统的权力政治思想在法国和英国仍然比较流行,(21)这样一来,欧盟外交政策的思想观念基础就变得相当复杂,其对外政策的“民事强权”特点就难以用价值观因素来解释。
不过即便如此,欧盟的基本价值观依然不可替代地成为欧盟对外政策中的规范性内容,它不仅决定了欧盟对外政策目标中的规范性成分,而且也从观念上影响了欧盟对外政策的方式和手段。
事实上,决定欧盟对外政策“民事强权”特性的更多的是欧盟对外政策决策机制上的特点,即行为体的多样性和决策层次的复合性决定了其对外政策具备了“民事强权”模式的合作型外交手段特征。
在欧盟对外政策的决策体系之中,非国家行为体、压力集团、政党、成员国议会、欧盟议会、成员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没有哪一种行为体占据决定性地位。
相反,对外政策是它们之间互相协商、妥协的结果。
在长期的一体化进程中,谈判、协商和集体决策已经成为欧盟主要的决策方式。
科拉曼通过研究认为,欧盟对外政策是上述各种行为体在多个层次上通过跨国、跨政府、国际等各种互动模式形成的。
(22)
普特南在其关于外交谈判双层博弈的经典研究中指出,国内利益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使得国内层次博弈变得更为复杂,由此可能有助于国际层次上的合作,因为它使得该国在国际合作中的“赢集”(winsets)的边界具有灵活性,随着谈判的形势变化和时间有可能发生较大的改变,从而使最初不可能达成的合作进入“赢集”之中。
相反,在国际合作中,利益同质性程度高的国际行为体的“赢集”的边界较为固定,因为既缺乏内部在相关问题上的争论和冲突,也不用担心所谓“跨国共谋”的建立。
(23)欧盟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联合体(Staatenverbund),在其对外多层决策体系中,成员国利益的多样性和异质性都很突出,对共同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其内部不同利益的冲突和协调导致对外政策上具有更强烈的合作倾向。
此外,对政治组织的输入输出及组织过程的研究也指出,在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中,否决权以及享有否决权的行为体的特点和数量对政策输出的倾向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具有否决权的行为体虽然无法保证其理想政策的输出,但却完全能够防止过于偏离其理想点的政策得到通过。
而更为有趣的是,否决权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它的实际使用,而在于它的存在本身就影响了相互作用的行为体的政策行为。
因为考虑到别的行为体A具有否决权,行为体B在政策倡议等各方面必须考虑到A的可能反应,为了使其动议成为政策,就要事先将A的利益和偏好考虑在内。
这样,政策输出的结果就具有了更多折衷的特征,具有否决权的行为体数量越多,更多的不同利益与偏好就必然体现在政策输出的结果中,因而折衷性也越明显。
在欧盟的决策过程中,尤其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各欧盟成员国政府理论上都享有否决权,因此欧盟对外政策集体决策的最后输出结果往往是温和与不走极端的政策。
比如在研究欧盟为何较少使用强制外交手段而经常采用合作型战略的时候,史密斯就认为,欧盟的经济和商业利益考虑只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这也是欧盟成员国政府取得妥协和一致意见的需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温和与合作型战略能够为大多数成员国所接受。
(24)因此,只要欧盟的决策机制保持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特点,那么在实践层面上的欧盟对外政策就会显现出比较明显的合作型战略特点。
欧盟决策机制的结构影响了欧盟对外政策中最为关键的特点,寻求共识的压力使得欧盟对外政策的过程变得相对缓慢,规则与程式化的约束又让欧盟对外政策决策过程在欧盟层次决策带有官僚政治特征,各官僚系统互相之间牵制和制约,最终得到的是妥协的结果。
与此同时,欧盟机构的路径相互依赖特性则决定了它的外交决策难以发生极端的改变,(25)这就又再次强化了欧盟对外政策输出结果的温和与不走极端的特性。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欧盟自身的军事能力状况也决定了它在实践中选择“民事强权”模式。
长期以来,军事力量的缺陷一直是欧盟对外行动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
自1999年科索沃危机之后,欧盟决定建立自主防务力量,虽然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进展有诸多不顺利之处,但是欧盟在对危机管理任务的部署能力上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执行军事民事相结合的任务方面,欧盟也已积累了一些经验。
然而与美国相比,其军事力量依然十分有限,这种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改变。
对于欧盟来说,如果要在世界政治中进一步发挥作用,离开了美国的帮助,它在军事手段上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欧盟具有的比较优势领域还是在它所宣扬的“民事强权”模式,这也正是埃贡•巴尔所称的“弱者的强项”。
巴尔指出,由于欧盟的虚弱,所以它才不得不坚持国际政治中的摈弃武力原则,约束强者和强调国际法原则,而且历史经验证明,这种战略是有效的。
(26)
因此,所谓的《欧盟安全战略报告》在实质上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战略”报告,它更像是欧盟宣称其世界秩序目标和对外行为规范的“文明力量”角色设计。
(27)《欧盟安全战略报告》描述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际关系的传统行为体依旧在发挥作用,但是跨国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也增大了。
在新的安全威胁下,世界和欧盟主要面临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武器以及失败国家的威胁。
它为欧盟设定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在欧盟的邻近区域建立安全地带和推动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发展。
在《欧盟安全战略报告》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看出“欧洲民事强权”模式的核心要素,即国家关系民主化、不以武力方式解决冲突、促进世界政治的法治化和多边主义制度的发展等原则。
总之,欧盟的基本价值观、决策机制的结构特点和军事能力特性共同决定了欧盟对外政策的“民事强权”模式。
在上述三个决定性因素当中,价值观因素决定了“欧洲民事强权”的规范性内容,而决策机制和军事能力的限制则从现实性上决定了欧盟对外政策手段的选择。
只要欧盟自身的上述特性不发生改变,那么欧盟对外政策的“民事强权”特征就会持续存在。
三发展趋势
虽然“欧洲民事强权”已经是有关欧盟对外政策的政治话语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宣扬“欧洲民事强权”、特别是强调其中的规范性因素已成为欧洲政治家在对外交往中抢占道德制高点的一种主要策略,但是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欧盟对外政策实践发展,“欧洲民事强权”的决定性因素显现出了一定的变化趋势。
这主要是指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发展所带来的欧盟军事能力和安全政策领域的决策机制变化。
英、法两国在1999年倡议的“圣马洛宣言”开启了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进程。
1999年12月,欧盟理事会赫尔辛基会议决定建立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这被认为是欧洲一体化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赫尔辛基会议决定建立一支60000人的欧洲军队,同时提升其军事能力。
2001年12月召开的欧盟莱肯会议宣称,欧盟“现在能够执行一些危机处理行动”。
欧盟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主性的军队,而且它的军事力量具有了对外干预能力和干预特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防御性功能。
与此同时,欧盟在理事会层次上开始建立一系列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决策机构。
关键性的决策将由一个“政治和安全委员会”做出,另外建立的“军事委员会”向政治和安全委员会提供军事上的建议,同时建立的“军事参谋部”负责计划和实施具体的军事行动。
(28)伊拉克危机爆发之后,德、法、比、卢四国在2003年4月共同做出决定,建立共同的军事计划和指挥结构,虽然这只是部分欧盟国家的意愿,但它毕竟迈出了建立欧盟军队司令部的第一步。
此后出台的《欧盟宪法条约》则进一步规定,“欧盟成员国承诺逐步提高其军事能力”,成立“欧洲军备、研究和军事能力的机构”,“在获得第三国帮助的情况下,欧盟军队可以在其领土上进行反恐行动”。
在机制上,欧盟部长理事会具有在第210条框架内实施行动的决策权,这被理解为“即便个别成员国政府不愿参加军事行动,但是其他国家依然可以执行该项行动”。
(29)虽然欧盟的军事能力仍有巨大不足,《欧盟宪法条约》也未获批准,然而上述现象却至少反映了欧盟成员国加强军事能力和外交与安全政策决策机制的意愿。
如果按照两分法的分类来衡量,欧盟的“欧洲民事强权”要素中的“民事”成分显然在减弱,而“军事”趋势却在增强。
从欧盟对外政策的实践来看,“欧洲民事强权”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因为“欧洲民事强权”的传统外交政策手段毕竟有其成效上的限度。
长期以来,“欧洲民事强权”在发展与第三国关系时依靠提供“成员国”身份和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合作等手段。
然而随着欧盟的不断扩大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出现,欧盟对邻近国家的吸引力也在逐渐减弱。
据西方媒体报道,近期加入欧盟的国家在取得成员资格后并未充分遵守欧盟的重要原则和价值观,欧盟接纳新成员的政治成本变得很高。
(30)所以,“欧洲民事强权”在现实政治条件下增加“军事”成分是题中应有之意,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反映了“欧洲民事强权”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即它即便是寻求所谓“文明化”、“和平的”和“法制化”的目标,但是又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军事手段。
因此,欧盟对外政策在实践中势必如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不久前在其一篇文章的标题中所归纳的那样——“给‘民事强权’装上牙齿”。
他称欧盟是“结合军事手段和民事手段处理地区危机的榜样”,承诺德国将在其欧盟轮值主席国任期内对“军事”和“民事”手段同样重视,进一步大力推动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
(31)如此看来,较之以前欧洲政治家主要强调和平手段特性的“欧洲民事强权”,现在的欧盟的确是一个处于变化之中的“民事强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欧盟对外政策的目标和手段都显现出“欧洲民事强权”的特点。
这是由其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欧盟的基本价值观决定了欧盟对外政策中的规范性内容,而它的决策机制及其军事能力又制约了手段的选择,所以欧盟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选择“民事强权”模式有其必然性。
然而,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实践表现出“欧洲民事强权”的军事成分在不断增多,此种趋势虽然尚不能改变“欧洲民事强权”的特性,但是它至少表明“欧洲民事强权”概念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
注释:
①“CivilianPower”有两个常见的中文译名,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学者一般使用“民事强权”的译法,参见陈志敏和古斯塔夫•盖拉茨:
《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
》,北京:
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6页。
而从德文“Zivilmacht”翻译过来的学者经常使用“文明强权”的译法,参见[德]贝娅特•科勒-科赫等:
《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顾俊礼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这种区别来自于这个概念本身的包容性和模糊性。
即使是欧洲学者也经常为这个概念而困惑。
按照本人的理解,如果在使用的时候主要强调与“军事”相对应的意义时,中文译名不妨采用“民事”;但若强调国际政治规范和国际关系的“文明化”和“法治化”时,也可以采用“文明”的译法,毕竟德国学者毛尔等人在发展和扩充这个概念的时候主要借鉴了犹太裔德国社会学家艾里亚斯的“文明”概念。
这个概念的另一个易引起歧见之处是对“Power”的中文翻译,本来人们惯常把它翻译成“强国”或“大国”,但是欧盟又不是一个国家,如若翻译成“力量”似乎又嫌太弱,欧洲学者现在还在争议所谓“CivilianPower”和“CivilianForce”的区别。
因此,本文权且使用“强权”的译法,虽然它在我们汉语中颇有贬义的意味。
②Fran{D7R805.JPG}oisD{D7R806.JPG}chene,"Europe'sRoleinWorldPeace",inR.Mayneed.,EuropeTomorrow:
SixteenEuropeansLookAhead,London:
Fontana,1972,pp.67-94.
③ChristopherHill,"EuropeanForeignPolicy:
PowerBloc,CivilianModel,orFlop?
",inReinhardtRummeled.,TheEvolutionofanInternationalActor:
WesternEurope'sNewAssertiveness,ColoradoandOxford:
WestviewPress,1990,p.55.
④本文所指的欧盟对外政策是宽泛意义上的概念,即欧盟对外政策既包括《欧盟条约》第一支柱内的内容,也包含《欧盟条约》在第二支柱范围内的外交政策内容。
在欧盟研究中,欧洲学者通常区分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的概念,对外关系包括所有欧盟和其他国家、国际机构的关系,诸如对外贸易、发展援助政策、对外环境政策等等;而外交政策则是指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中的核心事务,主要是指欧洲政治使用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领域涵盖的内容。
我国学者也曾撰文指出这种区分对于认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重要意义,参见冯仲平:
“关于欧盟外交政策的几个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4期,第7-10页。
⑤参见熊炜:
“论德国‘文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