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风格论.docx
《文学风格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学风格论.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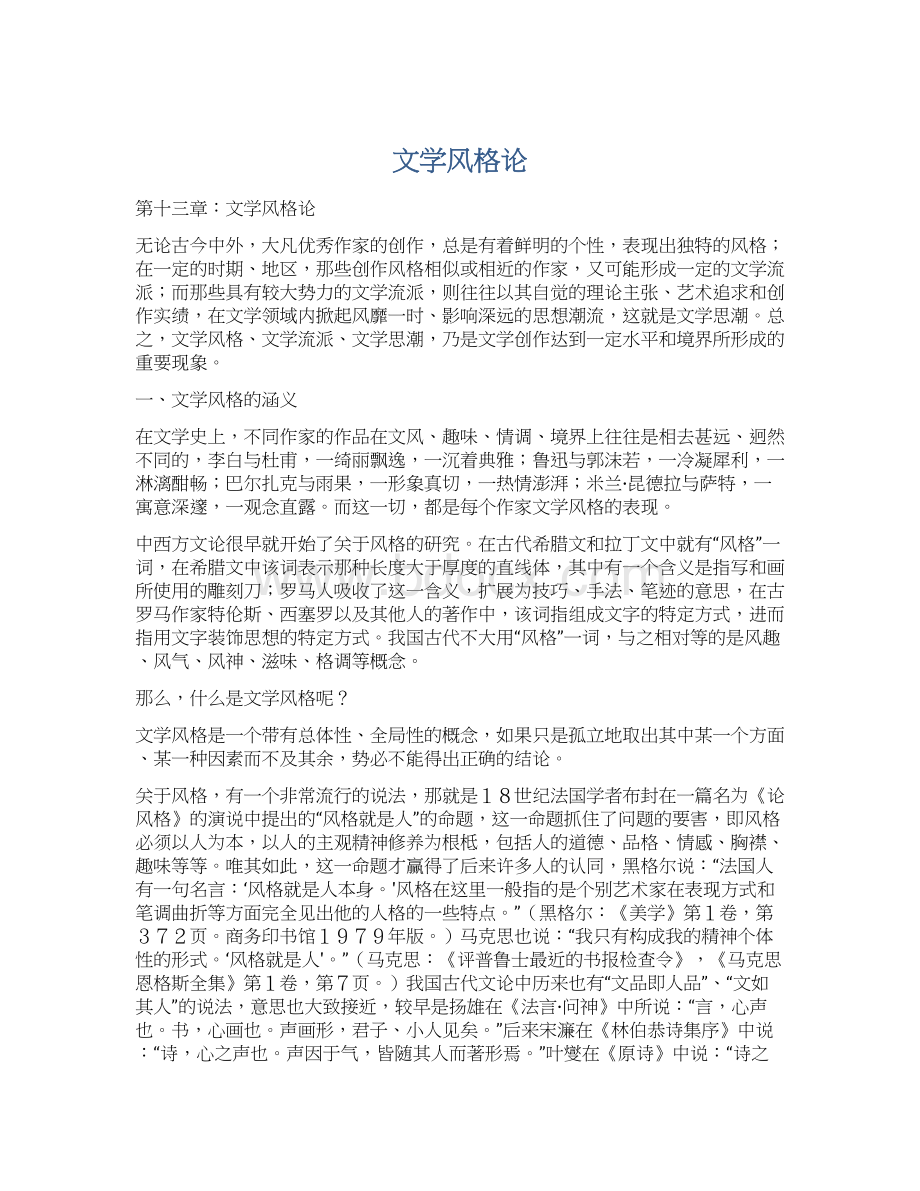
文学风格论
第十三章:
文学风格论
无论古今中外,大凡优秀作家的创作,总是有着鲜明的个性,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在一定的时期、地区,那些创作风格相似或相近的作家,又可能形成一定的文学流派;而那些具有较大势力的文学流派,则往往以其自觉的理论主张、艺术追求和创作实绩,在文学领域内掀起风靡一时、影响深远的思想潮流,这就是文学思潮。
总之,文学风格、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乃是文学创作达到一定水平和境界所形成的重要现象。
一、文学风格的涵义
在文学史上,不同作家的作品在文风、趣味、情调、境界上往往是相去甚远、迥然不同的,李白与杜甫,一绮丽飘逸,一沉着典雅;鲁迅与郭沫若,一冷凝犀利,一淋漓酣畅;巴尔扎克与雨果,一形象真切,一热情澎湃;米兰·昆德拉与萨特,一寓意深邃,一观念直露。
而这一切,都是每个作家文学风格的表现。
中西方文论很早就开始了关于风格的研究。
在古代希腊文和拉丁文中就有“风格”一词,在希腊文中该词表示那种长度大于厚度的直线体,其中有一个含义是指写和画所使用的雕刻刀;罗马人吸收了这一含义,扩展为技巧、手法、笔迹的意思,在古罗马作家特伦斯、西塞罗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该词指组成文字的特定方式,进而指用文字装饰思想的特定方式。
我国古代不大用“风格”一词,与之相对等的是风趣、风气、风神、滋味、格调等概念。
那么,什么是文学风格呢?
文学风格是一个带有总体性、全局性的概念,如果只是孤立地取出其中某一个方面、某一种因素而不及其余,势必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于风格,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那就是18世纪法国学者布封在一篇名为《论风格》的演说中提出的“风格就是人”的命题,这一命题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即风格必须以人为本,以人的主观精神修养为根柢,包括人的道德、品格、情感、胸襟、趣味等等。
唯其如此,这一命题才赢得了后来许多人的认同,黑格尔说:
“法国人有一句名言:
‘风格就是人本身。
'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
”(黑格尔:
《美学》第1卷,第372页。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马克思也说:
“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
‘风格就是人'。
”(马克思: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
)我国古代文论中历来也有“文品即人品”、“文如其人”的说法,意思也大致接近,较早是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所说:
“言,心声也。
书,心画也。
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后来宋濂在《林伯恭诗集序》中说:
“诗,心之声也。
声因于气,皆随其人而著形焉。
”叶燮在《原诗》中说:
“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
”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也说:
“诗品出于人品”。
以上这些论述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文学风格乃是以作者主观的人格修养为根基,作者的人格修养常常能够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有什么样的作者,便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以何种人格修养作为根基,作品便会呈现出何种品位、趣味和格调。
文学风格不仅以内在的人格修养为根基,而且要通过客观的、物化的形象和形式表现出来,缺少这种外在的形象和形式,文学风格仍然不能成为现实的存在,文学创作是“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的过程,因此文学风格乃是“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刘勰:
《文心雕龙·体性》。
)的产物,或者说是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
而这种外在的形象和形式本身也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作家要形成风格,一件要事就是必须做到对于这种客观的艺术规律的顺应和契合。
正像在文学史上经常看到的那样,作家在创作中如果采用不同的题材或体裁,则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风格。
表现工业题材与表现农村题材的作品风格不一,描写市民生活与描写校园生活的作品风格殊异,小说的风格不能与戏剧一致,诗歌的风格也总是与散文有不小的区别,这都是常识范围内的事,即使是同一个作家,如果他表现不同的题材,或采用不同的体裁,最终所呈现出来的风格也会迥异其趣。
瑞士学者沃尔夫冈·凯塞尔说: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
同一作家的两部作品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内容。
在某种程度之下,很难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重新认识那位曾经写作戏剧的创造者。
……另外一个明显的例是歌德的《葛兹·封·伯利欣根》和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我们还可以再加上这些年代各式各样的抒情诗。
假如我们利用这种解释来帮助,说这刚好是关系到各种不同类别的作品的事情,让风格的差异可以理解,那么我们至少必须承认,在各种类别中有一些规定风格的力量。
”(沃尔夫冈·凯塞尔:
《语言的艺术作品》第372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但是不管这客观的方面如何切要,它也不能是孤立存在、与主观因素相睽离的,而是必须始终受到作家内在的人格修养统摄的,客观的艺术规律只是在作家人格修养的规范之下才能发挥作用,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的生命只是受到作家情感和智慧的灌注才能显得光彩熠熠。
德国学者威格纳特将风格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比成衣服和肢体的关系,他说:
“风格并非安装在思想实质上的没有生命的面具,它是面貌的生动表现,活的姿态的表现,它是由含蓄着无穷意蕴的内在灵魂产生出来的。
或者,换言之,它只是实体的外服,一件覆体之衣;可是衣服的褶襞却是由于起因于衣服所披盖的肢体的姿态;灵魂,再说一遍,只有灵魂才赋予肢体以这样或那样的动作或姿态。
”(威格纳特:
《诗学·修辞学·风格论》,《文学风格论》第15-16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
关于风格,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把风格理解为文辞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特点。
亚里斯多德主要在修辞学的领域内讨论风格问题,古印度的毗首那他认为,风格只是连缀词句的特殊形式。
我国古代文论也常常以文辞形式作为划分文学风格的依据,曹丕《典论论文》说: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陆机《文赋》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刘勰《文心雕龙·定势》说: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
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
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
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
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
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
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
”由此可见,文辞形式确实是构成文学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仅此也还是不够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那怕是同一种体裁形式,在表现不同的内容题材时,也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
试看下面的两首唐诗,一是王维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一是王昌龄的《塞下曲》:
饮马度秋水,水寒风似刀。
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
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
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虽然这二者均属五言律诗,但有谁能说它们的风格是一样的呢?
另外,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虽然同属散文,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与契诃夫的《海鸥》虽然同属戏剧,萨特的《恶心》与加缪的《局外人》虽然同属小说,但其风格都是相去甚远的。
可见在文学风格的概念中在肯定形式的意义的同时还不能排除内容的作用,毋宁说文学风格恰恰是内容与形式的水乳交融。
在这一点上,前苏联学者米·赫拉普钦科的一段论述值得首肯,他说:
“艺术作品的风格组织中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形式的独特性,而且还有内容的某些方面的独特性。
人们经常称为形式的东西——诗情语言、情节、结构法、韵律等等,——所有这一切,在一般意义上,都包含在风格之中,可是,除此之外,风格还包括揭示思想、主题的特点,对人物的描写,艺术作品的语气的因素。
……应该着重指出:
标志出风格来的,不是这些或那些个别的形式和内容的因素本身,而是它们的‘融合体'的特殊性质。
”(米·赫拉普钦科:
《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第141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对什么是文学风格下一个定义了:
文学风格从本质上说,是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的有机融合体,它是作家在主观方面的个人独特性在创作过程及其物化的成果——作品中的体现,它不但在作品的形式上,而且也在作品的内容上表现出来。
这里还须指出的是,一般作家虽然在创作上都可能显示出某种个性特点,但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对于文学创作来说,风格是较高的、甚至最高的要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够称得上风格的个性特点起码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
一是这种个性特点具有开创意义,它必须成为某种起点,并有力地影响着以后的文学风尚,像李白、杜甫的诗,辛弃疾、李清照的词,关汉卿、王实甫的戏曲,都曾起过开一代风气的作用,从而都是有风格的。
二是这种个性特点必须非常鲜明和清晰,它不应是含糊不清、朦胧暧昧的,而应是让人不假思索和一目了然的。
鲁迅在30年代十分险恶的斗争环境中为了避免种种麻烦,在发表杂文时常常不得不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但是无论是广大读者还是国民党文化特务,仍然能够分辨出他的作品,正说明了其杂文创作有着极其鲜明的风格。
三是这种个性特点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贯串在作家的一系列作品中,不能说一个作家写了一两篇有特点的作品就有了风格,风格应是一个作家的一批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
像海明威“硬汉小说”的风格就不只是靠一两篇作品确立的,而是靠《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等一大批作品而蔚为大观的。
正因为需要这样几个条件,所以文学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也是作品达到较高境界的尺度,无论哪一个作家,都应以形成自己的风格为最高目标,说一个作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或说一部作品显示了某种风格,对于这一作家、作品乃是一种最高的褒奖。
二、文学风格的成因
文学风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总的说来,主要有社会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在实际起作用的时候,这两个方面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不分彼此的,这里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才将其分开来加以分析。
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往往从根本上影响着文学风格的形成,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军事斗争、阶级状况、民族关系、文化背景等都可能对作家的创作个性产生制约作用,并最终在文学风格上体现出来。
例如所谓“魏晋风骨”,就是在特定的社会状况下形成的一代诗风。
魏晋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各个统治集团之间的相互倾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民不聊生、饿莩遍地。
由于农民起义的有力打击,汉王朝的统治行将崩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也开始动摇,而知识分子在这失序的社会状态中却解除了思想禁锢,滋生了离经叛道的倾向,敢于直接暴露社会黑暗,大胆表达内心意愿,于是他们往往击节高歌、直抒胸臆,其作品勃发出慷慨多气、悲怆激越的风致,形成了特有的风力和气骨,表现出刘勰所说的“雅好慷慨”、“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刘勰:
《文心雕龙·时序》。
)的特点,涌现了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一大批优秀的诗歌作品。
试看曹操的《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从中不难了解所谓“魏晋风骨”与当时社会状况的因果关系。
再如法国18世纪启蒙文学以浓厚的哲理意味而形成鲜明的风格,便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18世纪启蒙运动以推翻封建统治和破除神学伪说为己任,以照亮思想、启发理性为宗旨,标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在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宣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将理性悬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崇尚自然、崇尚人性,主张在现实中建立起一个“理性的王国”。
而当时一批启蒙运动的斗士也就是作家,他们都致力于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学形式对深奥难解的哲学道理加以阐释,做了大量普及和推广的工作,以唤醒人民起来反对封建制度、封建贵族和宗教迷信,因此像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的《波斯人信札》、《布鲁图斯》、《拉摩的侄儿》、《爱弥儿》等作品哲理化风格的形成,便表现出共同的文化特点,或者说它们本来就是整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