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必修二管子行解.docx
《人教版必修二管子行解.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人教版必修二管子行解.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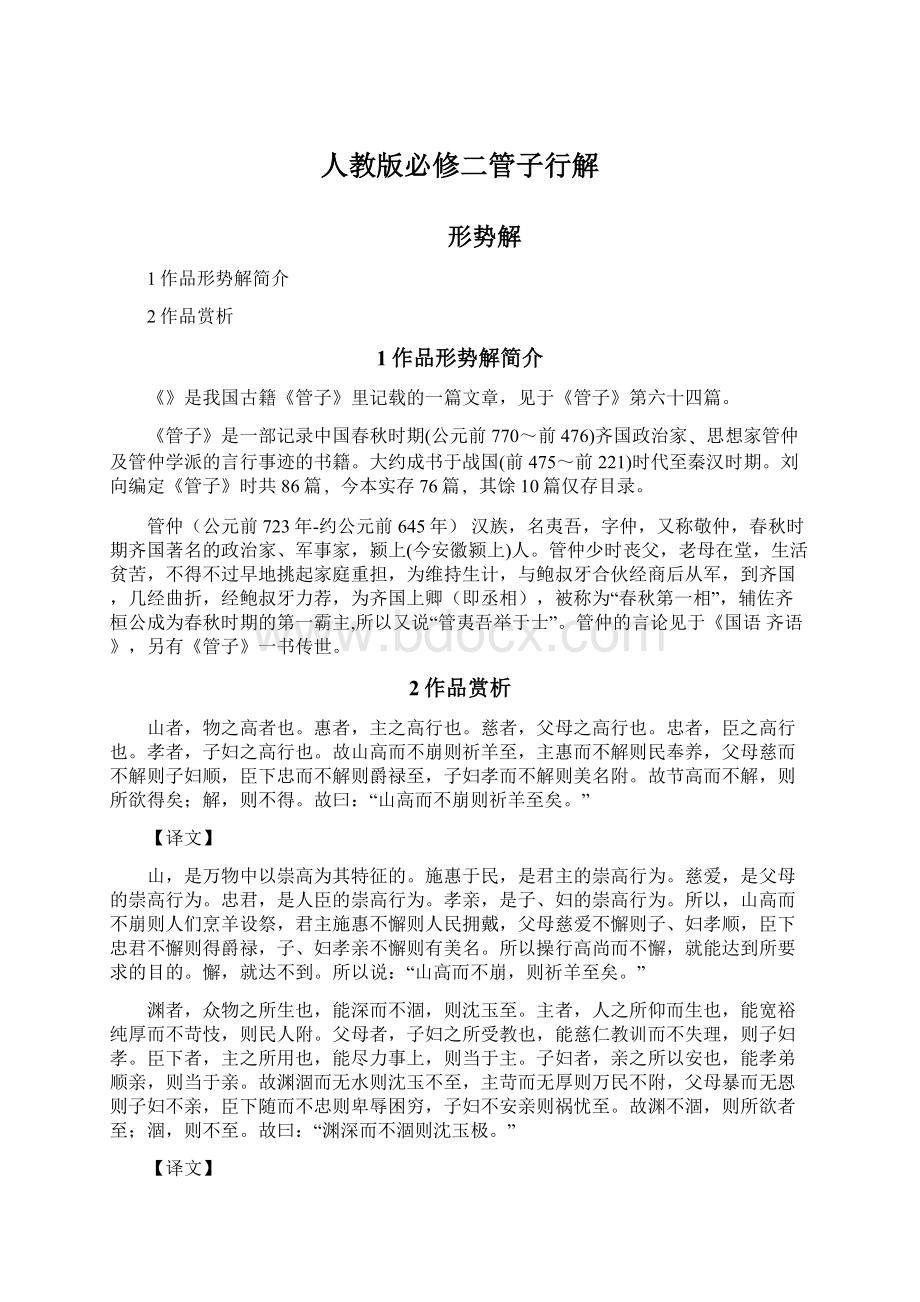
人教版必修二管子行解
形势解
1作品形势解简介
2作品赏析
1作品形势解简介
《》是我国古籍《管子》里记载的一篇文章,见于《管子》第六十四篇。
《管子》是一部记录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的书籍。
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
刘向编定《管子》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
管仲(公元前723年-约公元前645年)汉族,名夷吾,字仲,又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
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
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2作品赏析
山者,物之高者也。
惠者,主之高行也。
慈者,父母之高行也。
忠者,臣之高行也。
孝者,子妇之高行也。
故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则民奉养,父母慈而不解则子妇顺,臣下忠而不解则爵禄至,子妇孝而不解则美名附。
故节高而不解,则所欲得矣;解,则不得。
故曰:
“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
”
【译文】
山,是万物中以崇高为其特征的。
施惠于民,是君主的崇高行为。
慈爱,是父母的崇高行为。
忠君,是人臣的崇高行为。
孝亲,是子、妇的崇高行为。
所以,山高而不崩则人们烹羊设祭,君主施惠不懈则人民拥戴,父母慈爱不懈则子、妇孝顺,臣下忠君不懈则得爵禄,子、妇孝亲不懈则有美名。
所以操行高尚而不懈,就能达到所要求的目的。
懈,就达不到。
所以说:
“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
”
渊者,众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则沈玉至。
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宽裕纯厚而不苛忮,则民人附。
父母者,子妇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训而不失理,则子妇孝。
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尽力事上,则当于主。
子妇者,亲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顺亲,则当于亲。
故渊涸而无水则沈玉不至,主苛而无厚则万民不附,父母暴而无恩则子妇不亲,臣下随而不忠则卑辱困穷,子妇不安亲则祸忧至。
故渊不涸,则所欲者至;涸,则不至。
故曰:
“渊深而不涸则沈玉极。
”
【译文】
渊,是众物生长的地方。
渊深而水不枯,人们就会来投玉求神。
君主,是人们所仰望而赖以生活的,能宽大纯厚而不苛刻刚愎,人民就会归附。
父母,是子、妇都要接受其教育的,能慈爱教训而不离开正理,子、妇就会孝顺。
臣下,是为君主服务的,能尽力事奉君上,就合君主的心意。
儿子儿妇,是安养父母的,能孝悌顺亲,就合父母的心意。
所以,渊枯竭而无水,投玉求神的就不肯来;君主苛刻而不宽厚,百姓就不肯归附;父母残暴而无恩,子妇就不亲;臣下怠惰而不忠,就遭到屈辱困难;子妇不安养双亲,祸患就要来临。
所以,渊水不枯竭。
所要求的就可以来到,枯竭,就不会来。
所以说:
“渊深而不涸,则沈玉极。
”
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
治之以理,终而复始。
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
治之以法,终而复始。
和子孙,属亲戚,父母之常也。
治之以义,终而复治。
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
以事其主,终而复始。
爱亲善养,思敬奉教,子妇之常也。
以事其亲,终而复始。
故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
主不失其常,则群臣得其义,百官守其事。
父母不失其常,则子孙和顺,亲戚相欢。
臣下不失其常,则事无过失,而官职政治。
子妇不失其常,则长幼理而亲疏和。
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乱。
天未尝变,其所以治也。
故曰:
“天不变其常。
”
【译文】
天,覆育着万物,控制着寒暑,运行着日月,安排着星辰。
这是天的常规。
天总是依理行事。
终而复始。
君主,统治万民,治理天下,统率百官,这是君主的常规。
君主总依法治事,终而复始。
和睦子孙,团结亲戚,这是父母的常规。
父母总是依义行事,终而复始。
敦敬忠信,这是臣下的常规。
臣下应当以此事奉君主,终而复始。
亲爱且善养父母,尊敬并接受教导,这是子妇的常规。
子妇应当以此事奉双亲,终而复始。
所以,天不失其常规,寒来暑往就恰当其时,日月星辰就正常有序。
君主不失其常规,群臣就行其正义,百官尽其职守。
父母不失其常规,子孙就顺从,亲戚就和睦。
臣下不失其常规,办事就没有过失,而且官吏称职政务得治。
子妇不失其常规,就长幼有序,而亲疏和睦。
所以按常规办事就治,不按常规办事就乱,天从来不曾改变它的常规,因而总是处于“治”的状态。
所以说:
“天不变其常。
”
地生养万物,地之则也。
治安百姓,主之则也。
教护家事,父母之则也。
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
尽力共养,子妇之则也。
地不易其则,故万物生焉。
主不易其则,故百姓安焉。
父母不易其则,故家事辨焉。
臣下不易其则,故主无过失。
子妇不易其则,故亲养备具。
故用则者安,不用则者危。
地未尝易,其所以安也。
故曰:
“地不易其则。
”
【译文】
地,生养万物,这是地的法则。
治理和安定百姓,这是作君主的法则。
指导和监护家事,这是作父母的法则。
对君主正谏死节,这是作臣子的法则。
对父母尽力供养,这是作子妇的法则。
地不改变它的法则,所以万物生长。
君主不改变他的法则,所以百姓安宁。
父母不改变他的法则。
所以家事得治。
臣下不改变他的法则,君主就可以没有过失。
子妇不改变他的法则,双亲就被奉养得周到。
因此,遵照法则办事就平安,不遵照法则办事就危险,地从来不曾改变它的法则,因而总是处于安定的状态。
所以说:
“地不易其则。
”
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
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
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
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
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
赏赐刑罚,主之节也。
四时未尝不生杀也,主未尝不赏罚也。
故曰:
“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也。
”
【译文】
春天,阳气开始上升,所以万物发生。
夏天,阳气完全上升,所以万物成长。
秋天,阴气开始降临,所以万物收敛。
冬天,阴气完全降临,所以万物藏闭。
故春夏生长,秋冬收闭,这是四时的节令。
赏赐刑罚,这是君主的节度。
四时从没有不实现生杀的。
君主从没有不进行赏罚的。
所以说:
“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也。
”
天,覆万物而制之;地,载万物而养之;四时,生长万物而收藏之。
古以至今,不更其道。
故曰:
“古今一也。
”
【译文】
天,覆育而控制着万物;地,承载而生养着万物;四时,生长而藏闭着万物。
从古至今,从来不改变这个常规。
所以说:
“古今一也。
”
蛟龙,水虫之神者也。
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
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
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
蛟龙待得水而后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
故曰:
“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
”
【译文】
蚊龙,是水虫当中的神灵。
有水,神就立;失水,神就灭。
君主,是天下有权威的人。
得人民拥护就有权威,失去人民,权威就消失。
蚊龙得水而后才有神灵,君主得人民拥护而后才有权威。
所以说:
“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
”
虎豹,兽之猛者也,居深林广泽之中则人畏其威而载之。
人主,天下之有势者也,深居则人畏其势。
故虎豹去其幽而近于人,则人得之而易其威。
人主去其门而迫于民,则民轻之而傲其势。
故曰:
“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
”
【译文】
虎豹,是兽类中最凶猛的。
它们居住在深林大泽之中,人们就畏其威力而看重它们。
君主,是天下最有势力的人。
深居简出,人们就害怕他的势力。
虎豹若离开深山幽谷而与人接近,人们就会把它捕起来而无视它的威力。
君主若离开朝廷而与人民靠近,人民就轻慢他而不怕他的势力。
所以说;“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
”
风,漂物者也。
风之所漂,不避贵贱美恶。
雨,濡物者也。
雨之所堕,不避小大强弱。
风雨至公而无私,所行无常乡,人虽遇漂濡而莫之怨也。
故曰:
“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
”
【译文】
风,是吹拂万物的。
风吹起来不避贵贱美恶。
雨,是淋湿万物的。
雨,下起来,不管大小强弱。
风雨是至公而无私心的,风吹雨下,没有既定方向,人们虽然遇到风吹雨打也不会发出怨言。
所以说:
“风雨无向而怨怒不及也。
”
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
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
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
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而令乃行。
故曰:
“贵有以行令也。
”
【译文】
人君之所以做到令行禁止,一定是因为“令”发在人民所好的方面,“禁’’行在人民所恶的地方。
人之常情没有不爱生而恶死的,也没有不爱利而恶害的。
所以君主发令是使人生存和对人有利,命令就能推行;君主行禁是禁止杀人和禁止害人,施禁就能制止。
命令之所以能够推行,必须是民乐其政,才能够推行下去。
所以说:
“贵有以行令。
”
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亲上者,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
故德泽加于天下,惠施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万民欢尽其力而乐为上用。
入则务本疾作以实仓廪,出则尽节死敌以安社稷,虽劳苦卑辱而不敢告也。
此贱人之所以亡其卑也。
故曰“贱有以亡卑。
”
【译文】
人君之所以能使百姓尽力而亲近自己,必须为天下致利除害。
所以要把德泽加于天下,恩惠施于万物,使家庭得以安居,群生得以养育,这样,万民便愿意尽力而为君主效劳。
他们在家里努力耕作以充实国家仓廪,在战场尽节杀敌以保卫国家疆土,即使劳苦卑辱也是不敢叫苦的。
这就是地位低的人可以忘其卑贱的原因。
所以说:
“贱有以亡卑。
”
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体累而寿命损。
人惰而侈则贫,力而俭则富。
夫物莫虚至,必有以也。
故曰:
“寿夭贫富无徒归也。
”
【译文】
起居有定时,饮食有定量,寒热得当,则身体好而寿命长。
起居无定时,饮食无定量,寒热调配不当,则身体弱而寿命短。
人要懒惰而奢侈则贫,勤劳而节俭则富。
事情是不会凭空而至的,一定有它的原因。
所以说:
“寿夭贫富无徒归也。
”
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
故曰:
“衔令者君之尊也。
”
【译文】
法立而人民乐从,令出而人民接受,法令合于民心,就象符节那样的一致,君主就尊显。
所以说:
“衔令者君之尊也。
”
人主出言,顺于理,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
民受其辞则名声章。
故曰:
“受辞者名之运也。
”
【译文】
君主出言合理,合于民情,臣民就接受他的指示。
臣民接受指示则君主的名声显赫。
所以说:
“受辞者名之远也。
”
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
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
故曰:
“上无事而民自试。
”
【译文】
英明君主的治理天下,使人们安定而无所干扰,使人们安闲而无所劳累。
不干扰,人民会自动守法;不劳累,人民会自动工作。
所以说:
“上无事而民自试。
”
人主立其度量,陈其分职,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则民循正。
所谓抱蜀者,祠器也。
故曰:
“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
”
【译文】
人君建立法度,公布职责,明确规范来统治他的臣民,而不是无用说话指挥,臣民就按正道行事了。
所谓抱“蜀”,指的是祭器。
所以说:
“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
”
将将鸿鹄,貌之美者也。
貌美,故民歌之。
德义者,行之美者也。
德义美,故民乐之。
民之所歌乐者,美行德义也,而明主鸿鹄有之。
故曰:
“鸿鹄将将,维民歌之。
”
【译文】
锵锵而鸣的鸿鹄,是长得很美的飞鸟。
因为美,所以人们歌颂它。
德义,是一种行为上的美。
因为德义美,所以人们喜悦它。
人民所歌颂喜悦的,乃是美貌和德义,而明君和鸿鸽恰好具有这些。
所以说:
“鸿鹄将将,维民歌之。
”
济济者,诚庄事断也;多士者,多长者也。
周文王诚庄事断,故国治。
其群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
主明而国治,竟内被其利泽,殷民举首而望文王,愿为文王臣。
故曰:
“济济多士,殷民化之。
”
【译文】
“济济”,指的是诚实庄重而果断;“多士”,指的是许多有才德的人。
周文王诚庄事断,故国家安定。
他的群臣明理佐助君主,故君主英明。
君主英明而国家安定,国内都得到他的好处和恩泽,殷民也举首而拥护文王,愿意作他的臣民。
所以说:
“济济多士,殷民化之。
”
纣之为主也,劳民力,夺民财,危民死,冤暴之令,加于百姓;憯毒之使,施于天下。
故大臣不亲,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愿为文王臣者,纣自取之也。
故曰:
“纣之失也。
”
【译文】
殷纣王为君,劳民力,夺民财,危害人民性命,把残暴的法令强加于百姓,又把惨毒的使臣派往天下各地。
所以大臣不亲,小民怨恨,天下背叛而愿为文王的臣民,这是纣王的自作自受。
所以说:
“纣之失也。
”
无仪法程式,蜚摇而无所定,谓之蜚蓬之间。
蜚蓬之间,明主不听也。
无度之言,明主不许也。
故曰:
“蜚蓬之间,不在所宾。
”
【译文】
不合乎法度规范,摇摆而没有定见,叫作飞蓬一样没有根据的言论。
这种言论,英明君主是不听的。
就象对于没有法度的言论一样,英明君主是不赞成的。
所以说:
“蜚蓬之问,不在所宾。
”
道行则君臣亲,父子安,诸生育。
故明主之务,务在行道,不顾小物。
燕爵,物之小者也。
故曰:
“燕爵之集,道行不顾。
”
【译文】
行“道”,君臣就亲近,父子就和睦,生命就繁育。
所以明主的职责,在于行“道”,而不在小的事物上。
燕雀,是事物中的小东西。
所以说:
“燕雀之集,道行不顾。
”
明主之动静得理义,号令顺民心,诛杀当其罪,赏赐当其功,故虽不用牺牲珪璧祷于鬼神,鬼神助之,天地与之,举事而有福。
乱主之动作失义理,号令逆民心,诛杀不当其罪,赏赐不当其功,故虽用牺牲珪璧祷于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与,举事而有祸。
故曰:
“牺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
【译文】
明主的行动合乎理义,号令顺乎民心,诛杀与罪行相合,赏赐与功绩相称,所以他虽不用牛羊玉器祈祷于神鬼,鬼神也会帮助,天地也会支援,办什么事都得福。
昏君的行动不合理义,号令逆乎民心,诛杀与罪行不相当,赏赐与功绩不相称,所以,虽用牛羊玉器祈祷于鬼神,鬼神也不帮助,天地也不支援,办什么事都得祸。
所以说:
“牺牲珪壁不足以享鬼神。
”
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
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
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
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
故曰:
“主功有素,宝币奚为?
”
【译文】
君主的功绩,就是使国家富强。
所以,国富兵强,诸侯就服从他的政令,邻邦也惧怕他的威力,虽然不用珍贵的宝币交结诸侯,诸侯也不敢侵犯他。
君主的罪过,就是使国家贫弱。
所以,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然用名器重宝来交结邻国,也不免于灭亡的祸患。
所以说:
“主功有素,宝币莫为?
”
羿,古之善射者也。
调和其弓矢而坚守之。
其操弓也,审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发而多中。
明主,犹羿也,平和其法,审其废置而坚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举而多当。
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
射者,弓弦发矢也。
故曰:
“羿之道非射也。
”
【译文】
后羿,是古代的善射者。
他调和好弓箭而坚持掌握着。
他操弓时,审明其高下,掌握必能射中目标的规律,故能百发百中。
明主就象后羿一样,调和其治国的法度,审明其当废当立而坚持实行,掌握必治的规律,所以能做到多办事而事多办好。
规律,使后羿必能命中,使君主必能治国。
射箭的表面动作,不过是弓弦发出箭枝而已。
所以说:
“羿之道,非射也。
”
造父,善驭马者也。
善视其马,节其饮食,度量马力,审其足走,故能取远道而马不罢,明主,犹造父也。
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伤。
故术者,造父之所以取远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
驭者,操辔也。
故曰,“造父之术非驭也。
”
【译文】
造父,是善于驭马的。
他爱护自己的马,调节它的饮食,度量马力了解它的速度,所以能驶行远路而马不疲累。
明君也同造父一样,善于治理他的民众,度量民力,了解他们的技能,所以建立了事功而人民不感到疲困。
所以,技艺方术,使造父驶行远路,使君主建立功名。
至于驭马的表面动作,不过是掌握马的缰绳而已。
所以说:
“造父之术,非驭也。
”
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
明主,犹奚仲也,言辞动作,皆中术数,故众理相当,上下相亲。
巧者,奚仲之所以为器也,主之所以为治也。
斫削者,斤刀也。
故曰:
“奚仲之巧非斫削也。
”
【译文】
奚仲的制造车器,方圆曲直都合乎规矩钩绳,所以机轴都很合适,用起来牢固快速,成器坚固持久。
明君同奚仲一样,言词动作,都合乎方法策略,所以,各项治理都很适当,上下互相亲近。
“巧”,使奚仲能制成车器,使君主能治好国家。
至于木材的砍削,不过是刀斧的动作而已。
所以说:
“奚仲之巧非削也。
”
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
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
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
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
故曰:
“召远者使无为焉。
”
【译文】
人民,有利则来,有害则去。
人民趋利,就象水往下流一样,不管东西南北。
所以,要招来民众,先创造对他们有利的条件,虽不招而民自至。
如对他们有害,虽招而不来。
所以说;“召远者使无为焉。
”
莅民如父母,则民亲爱之。
道之纯厚,遇之(有)【真】实,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矣。
莅民如仇雠,则民疏之。
道之不厚,遇之无实,诈伪并起,虽言曰吾亲民,民不亲也。
故曰:
“亲近者言无事焉。
”
【译文】
统治人民要象父母一样,人民自然会亲近和爱戴。
以纯厚来治理他们,用实惠来对待他们,虽然口里不说我亲近人民,人民也是会来亲近的。
如把人民当作仇敌一般统治,人民自然就会疏远。
治理他们不以厚道,对待他们没有实惠,欺诈和虚伪都用上了,虽然口头上说我要亲近人民,人民也是不会亲近的。
所以说:
“亲近者言无事焉。
”
明主之使远者来而近者亲也,为之在心。
所谓夜行者,心行也。
能心行德,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矣。
故曰:
“唯夜行者独有之乎。
”
【译文】
明君能使远者来而近者亲,作用在于内心。
所谓“夜行”意思就是“心行”。
能做到内心行德,天下就没有人能够与之抗争了。
所以说;“唯夜行者独有之乎。
”
为主而贼,为父母而暴,为臣下而不忠,为子妇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
大失在身,虽有小善,不得力贤。
所谓平原者,下泽也,虽有小封,不得为高。
故曰:
“平原之隰,奚有于高?
”
【译文】
作君主的,害人;作父母的,残暴;作臣下的,不忠;作子、妇的,不孝。
这四项是人的大过失。
有大过失在身,虽有小的优点,不得称之为贤。
所谓平原,是指低洼的地面。
虽有小的土堆,不能算作高。
所以说:
“平原之径,奚有于高。
”
为主而惠,为父母而慈,为臣下而忠,为子妇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
高行在身,虽有小过,不为不肖。
所谓大山者,山之高者也,虽有小隈,不以为深。
故曰:
“大山之隈,奚有于深?
”
【译文】
作君主的,惠民;作父母的,慈爱;作臣子的,忠君;作子、妇的,孝亲。
这四项是人们的大德。
有大德在身,虽有小过,不算不肖。
所谓大山,是山中最高的。
虽有小沟,不算作深。
所以说:
“大山之限,奚有于深。
”
毁訾贤者之谓訾,推誉不肖之谓讆。
訾讆之人得用,则人主之明蔽,而毁誉之言起。
任之大事,则事不成而祸患至。
故曰:
“訾讆之人,勿与任大。
”
【译文】
毁谤诽议贤者叫作“訾讆”,吹捧不肖之徒叫作“誓讆”。
“訾讆”之人得用,君主的聪明就被蒙蔽,而毁谤或者吹捧的谗言就起来了。
若是任用这种人管理大事,那就把事情办坏而祸患临头。
所以说:
“訾讆之人,勿与任大。
”
明主之虑事也,为天下计者,谓之譕臣。
譕臣则海内被其泽,泽布于天下,后世享其功久远而利愈多。
故曰:
“譕臣者可与远举。
”
【译文】
明君考虑事物,为天下全局打算,这叫作谋虑远大。
谋虑远大则海内都受到他的恩泽,恩泽施布于天下,后世享受他的功业,愈久远而利益愈多。
所以说:
“讠无巨者可与远举。
”
圣人择可言而后言,择可行而后行。
偷得利而后有害,偷得乐而后有忧者,圣人不为也。
故圣人择言必顾其累,择行必顾其忧。
故曰:
“顾忧者可与致道。
”
【译文】
圣人总是选择好可以说的话而后才说,选择好可以做的事而后才做。
苟得其利而有后来之患,苟得其乐而有后顾之忧,圣人是不做这种事情的。
所以圣人“择言”一定考虑其后顾之累,“择行”一定要考虑其后顾之忧。
所以说:
“顾忧者可与致道。
”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适主意而偷说,备利而偷得。
如此者,其得之虽速,祸患之至亦急。
故圣人去而不用也。
故曰:
“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
【译文】
小人,不用正道来讨人欢喜,他总是迎合君意而苟且取悦于君,追求财利而苟且得其财利。
这样的人,得利虽然很快,祸患的来临也很急。
所以圣人总是远离他而不使用的。
所以说:
“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
举一而为天下长利者,谓之举长。
举长则被其利者众,而德义之所见远。
故曰:
“举长者可远见也。
”
【译文】
办一件大事而为天下取得长远利益的,叫做“举长”。
举长则受益的人众多,而德义的影响深远。
所以说:
“举长者可远见也。
”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万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载万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众人得比焉。
故曰:
“裁大者众之所比也。
”
【译文】
天的材器大,所以能兼覆万物;地的材器大,所以能兼载万物;人君的材器大,所以能容纳各种事物而使众人信赖。
所以说:
“裁大者众之所比也。
”
贵富尊显,民归乐之,人主莫不欲也。
故欲民之怀乐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厌也,而民怀乐之。
故曰:
“美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
”
【译文】
贵富尊显,使人民拥戴感激,君主没有不愿意的。
问题是要求人民感怀自己,一定要行德而不厌倦,人民才可以感怀。
所以说:
“欲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
”
圣人之求事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
故义则求之,不义则止。
可则求之,不可则止。
故其所得事者,常为身宝。
小人之求事也,不论其理义,不计其可否,不义亦求之,不可亦求之。
故其所得事者,未尝为赖也。
故曰:
“必得之事,不足赖也。
”
【译文】
圣人要干一件工作,首先问它是否合于理义,并估计其可能性。
合于“义”则做,不合于“义”的则不做。
有可能则做,没有可能则不做。
所以他所做到的事情,常常是宝贵的。
小人做一件事,不问它是否合乎理义,不估计可能与不可能。
不义的做,不可能的也做。
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是靠不住的。
所以说:
“必得之事,不足赖也。
”
圣人之诺已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
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
故其诺未尝不信也。
小人不义亦诺,不可亦诺,言而必诺。
故其诺未必信也。
故曰:
“必诺之言,不足信也。
”
【译文】
圣人对一件事情的承诺与否,首先问它是否合于理义,并估计其可能性。
合于“义”则承诺,不合于“义”则不承诺;有可能则承诺,没有可能则作罢。
所以他的诺言没有不兑现的。
小人则是不义也承诺,没有可能也承诺,一张口就一定承诺。
所以他的诺言是未必兑现的。
所以说:
“必诺之言,不足信也。
”
谨于一家,则立于一家;谨于一乡,则立于一乡;谨于一国,则立于一国;谨于天下,则立于天下。
是故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
故曰:
“小谨者不大立。
”
【译文】
谨慎对待一家的事情,则可在一个家庭里有所建树;谨慎对待一乡的事情,则可在一个乡里有所建树;谨慎对待一国的事情,则可在一国里面有建树;谨慎对待天下的事情,则可在天下的范围有建树。
因此,谨慎处事的范围小,则其所建树的范围也小;谨慎处事的范围大,则其所建树的范围也大。
所以说:
“小谨者不大立。
”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
飺者,多所恶也。
谏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体也。
主恶谏则不安,人飺食则不肥。
故曰:
“飺食者不肥体也。
”
【译文】
海不排斥水,所以能够成为大海;山不排斥土石,所以能成为高山;明君不厌恶人民,所以能实现人口众多;士不厌学,所以能成为圣人。
{此食},就是挑拣食品太严重。
纳谏,是为了安定君位的;吃东西,是为了强壮身体的。
君主怕人进谏,君位就不安定;人们挑拣食品,身体就不肥壮。
所以说:
“{此食}食者不肥体。
”
言而语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无弃者。
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
无弃之言,公平而无私,故贤不肖莫不用。
故无弃之言者,参伍于天地之无私也。
故曰:
“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矣。
”
【译文】
一讲话就讲道德忠信孝梯的,这是不能废弃的话。
天公平而无私,所以美与恶无所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所以小与大无所不载。
不能废弃的话,也是公平无私的,所以贤与不肖都可以应用。
所以,不能废弃的语言,是同天地一样无私的。
所以说:
“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也。
”
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