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写作是与读者战斗.docx
《阎连科 写作是与读者战斗.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阎连科 写作是与读者战斗.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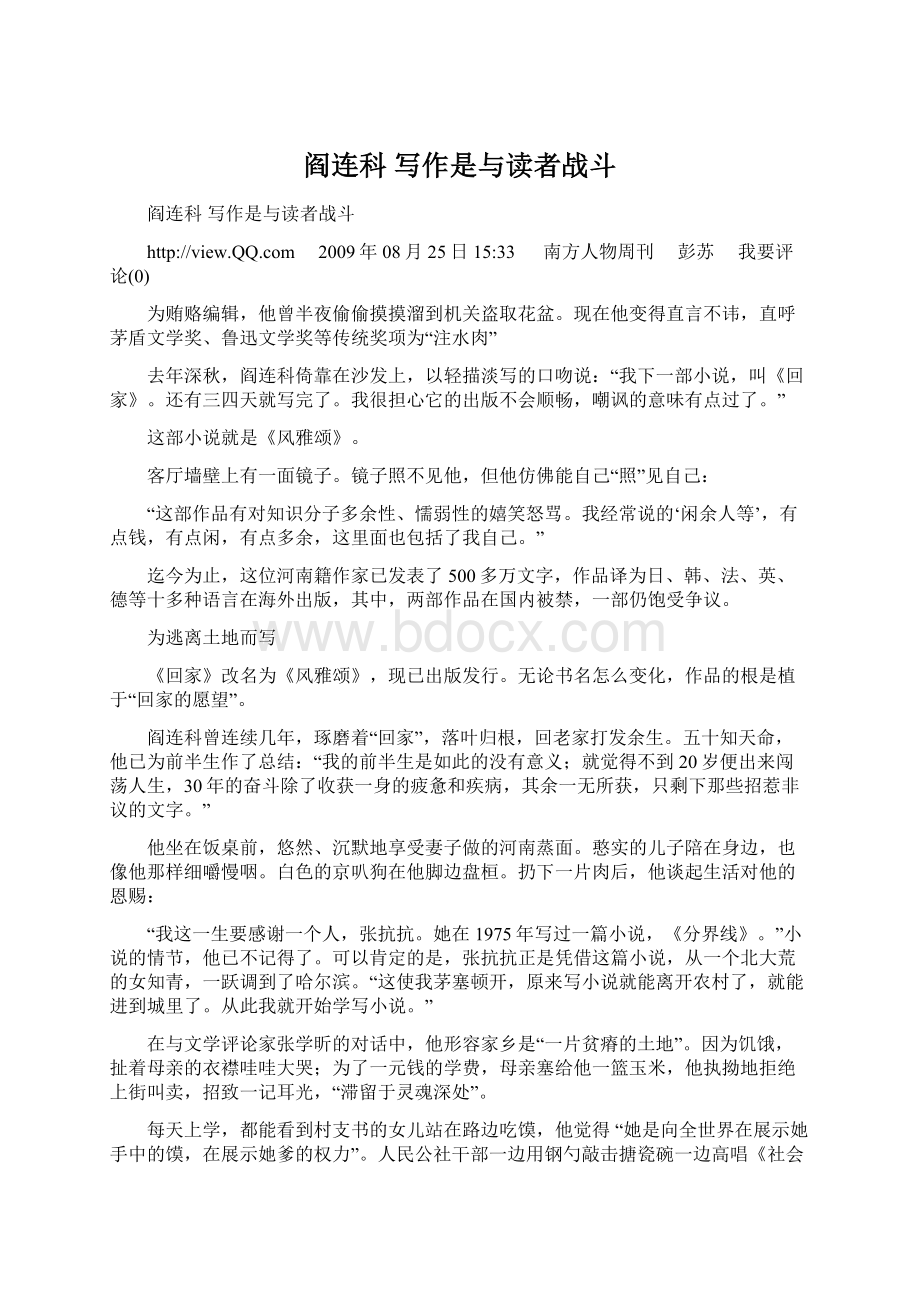
阎连科写作是与读者战斗
阎连科写作是与读者战斗
http:
//view.QQ.com 2009年08月25日15:
33 南方人物周刊 彭苏 我要评论(0)
为贿赂编辑,他曾半夜偷偷摸摸溜到机关盗取花盆。
现在他变得直言不讳,直呼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传统奖项为“注水肉”
去年深秋,阎连科倚靠在沙发上,以轻描淡写的口吻说:
“我下一部小说,叫《回家》。
还有三四天就写完了。
我很担心它的出版不会顺畅,嘲讽的意味有点过了。
”
这部小说就是《风雅颂》。
客厅墙壁上有一面镜子。
镜子照不见他,但他仿佛能自己“照”见自己:
“这部作品有对知识分子多余性、懦弱性的嬉笑怒骂。
我经常说的‘闲余人等’,有点钱,有点闲,有点多余,这里面也包括了我自己。
”
迄今为止,这位河南籍作家已发表了500多万文字,作品译为日、韩、法、英、德等十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其中,两部作品在国内被禁,一部仍饱受争议。
为逃离土地而写
《回家》改名为《风雅颂》,现已出版发行。
无论书名怎么变化,作品的根是植于“回家的愿望”。
阎连科曾连续几年,琢磨着“回家”,落叶归根,回老家打发余生。
五十知天命,他已为前半生作了总结:
“我的前半生是如此的没有意义;就觉得不到20岁便出来闯荡人生,30年的奋斗除了收获一身的疲惫和疾病,其余一无所获,只剩下那些招惹非议的文字。
”
他坐在饭桌前,悠然、沉默地享受妻子做的河南蒸面。
憨实的儿子陪在身边,也像他那样细嚼慢咽。
白色的京叭狗在他脚边盘桓。
扔下一片肉后,他谈起生活对他的恩赐:
“我这一生要感谢一个人,张抗抗。
她在1975年写过一篇小说,《分界线》。
”小说的情节,他已不记得了。
可以肯定的是,张抗抗正是凭借这篇小说,从一个北大荒的女知青,一跃调到了哈尔滨。
“这使我茅塞顿开,原来写小说就能离开农村了,就能进到城里了。
从此我就开始学写小说。
”
在与文学评论家张学昕的对话中,他形容家乡是“一片贫瘠的土地”。
因为饥饿,扯着母亲的衣襟哇哇大哭;为了一元钱的学费,母亲塞给他一篮玉米,他执拗地拒绝上街叫卖,招致一记耳光,“滞留于灵魂深处”。
每天上学,都能看到村支书的女儿站在路边吃馍,他觉得“她是向全世界在展示她手中的馍,在展示她爹的权力”。
人民公社干部一边用钢勺敲击搪瓷碗一边高唱《社会主义好》昂首迈进食堂的模样,更让他发誓,“如果不能离开农村,就要当个村干部。
”
14岁时,他第一次进城,满目新鲜;40岁后,老友李洱在《阎连科的ABC》中写道:
田湖镇终于到了,那是著名的两程故里,也是阎连科的出生地。
阎连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手有点哆嗦,脸上有一种兴奋,也有一种羞涩。
我们还坐在车里张望,阎连科已经下了车,他要脚踏实地,在田湖镇的街头走一走。
为成名成家而写
1979年,阎连科发表了严格意义上的处女作——《天麻的故事》。
等到1982年,文学的功能在他这里“升华”了——“我几乎是毫不犹豫、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把写作的目的,‘升华’到了成名作家。
”
阎连科说,20多岁的自己极其渴望名利,“就像找不到媳妇的光棍渴望得到美女的爱情。
”
那会正是20世纪的80年代。
“是一个追求写作的人成名成家的最好时期,是文学的一个盛唐,是作家的天堂岁月。
”纯文学上的“改革”、“反思”、“寻根”、“先锋”等潮流纷纷涌现:
史铁生因《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午餐半小时》一举成名;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与《爸爸爸》被视为寻根小说代表作;莫言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轰动文坛。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说:
“相对于同时代的作家而言,阎连科无疑是大器晚成。
”“当时,文坛上还特别流行着‘系列’小说,几乎每个小有名气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系列’。
”为了追风,阎连科一口气创作了他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瑶沟系列”、“和平系列”。
“几条线同时出击。
仿佛自己多有能耐似的。
不细想,不修改,写了就发。
弄得几年下来,满天下的杂志上都是自己的小说,如‘劳动模范’一样。
”
事实上,这是对创作的一种伤害:
数量胜于质量。
10个中篇,讲述同一个故事;10个故事,塑造了同一个人物。
一个作家在80年代的状况决定了此后文学史对他的评价程度,这是新时期文学论述中的一个特点。
那一系列作品使阎连科在很长时间内,未被当代文学史所接纳。
即使1997年发表的《年月日》已让他声名鹊起。
1978年刚入伍时的阎连科(右)
寻找土地,为自己而写作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记述过这段时期的阎连科:
“由于过度疲劳,年纪轻轻就得了腰椎病。
得病后他在腰上绑一个用钢板做的宽大腰带继续写。
不能在桌前写,就趴在床上写,结果又引发颈椎疼痛,最后只好到残疾人机械厂订了一张特殊(座位半躺着)的椅子,前面固定着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
”
1991年,一天早晨阎连科起床时,左腿麻木,无法下地。
以后相当长的日子里,他都处于半瘫痪状态,无法提笔。
“我真是太不珍惜自己的那一点精力与才华了。
浪费了太多时间,甚至累垮了我的身体。
”
这许是命中注定的转机。
他开始反省过去写作的无意义,翻开以前无心阅读的书籍:
托尔斯泰、加西亚·马尔克斯、屠格涅夫……
“我才意识到因为写作,断送了我的身体。
但是不能写作,我却没有活着的意义。
写作早已融入我的生命,甚至是我活着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
”
年过三十,阎连科清醒了。
为贿赂编辑,他曾半夜偷偷摸摸溜到机关盗取花盆。
现在他变得直言不讳,直呼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传统奖项为“注水肉”。
他不再是“瑶沟系列”里对自身命运困惑的少年,语言不再重复九流人物的故事,视野也不再局限于军旅中的和平。
他创作了小说《日光流年》。
“这篇小说萌动于一次旅行,在火车上听别人说河南林县有一个地方的人许多都得了食道癌,活不过四五十岁。
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一部长篇小说产生了,所有想了10年、20年的东西杂七杂八地在这一刻都联系到一块了,如一团乱麻在一瞬间理出一个头绪来。
从1995年初动笔,到1998年底结束。
最初脑子里闪过人对于死亡的恐惧与抵抗,至于完成之后,它究竟表达了什么,就不由自己了。
”
《坚硬如水》被他视为“转折之作”。
文中,他为男女主人公——高爱军和夏红梅,文革中一对无限上纲上线、疯狂革命的男女挖掘了一条地道——一条汇聚爱情、死亡和革命的地道。
人物间死去活来的命运,贯穿着地道的两极。
而贯穿全文的却是他对那个特定时期的特定语言的熟悉——他曾熟背了10年的《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毛主席诗词》。
“我必须写点什么了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阎连科的写作特点是他对农村变化的体验,以及怪诞的想象力。
”他更指出,“正因为阎连科无法控制他想象力的井喷,而导致对小说整体结构的失衡。
同时,那些具有爆炸性的题材,反而阻碍了他对人性的深挖。
”
“文学评论家们会看,不见得会写。
我们会写,不见得会评论。
”阎连科不动声色地这样评价。
他想后半生过得“受活”一点。
《受活》是他通过梦想走进现实的小说。
发表后他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一次采访。
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他接到了上级电话,命令他从军队转业,一偿他长久之“夙愿”。
“我是彻底地‘受活’了。
”阎连科的面相平和,创作完《丁庄梦》时内心无所依附的痛苦和绝望已荡然无存。
《丁庄梦》始于1996年——艾滋病刚被曝光,他在“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人的家中,为听到的一个细节惊悸:
“她告诉我,农民当年被采完血后,会因过量卖血而瘫倒一旁。
这时,血头就会提着这些农民的双腿,像提只被打死的动物一样上下抖动,等到血走到头上,农民清醒过来后,又会回到地里干活去了。
”
缄默中他觉得“必须写点什么了”。
现实远比想象残酷。
一个血头亲口对他说,开始采血时还会用瓶装,但考虑成本高,就改用廉价的装酱油、醋的塑料袋儿,接下去想再省成本,就反复使用塑料袋。
因为经常在村里的水坑洗袋子,坑里的水变红了,养得蚊子巨肥无比。
“那个地方在河南以东。
”每每问及“丁庄”的原型,阎连科总是含糊其辞。
从2004年开始,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那个地方”。
“回家后,如隔尘世,起码花上一周的时间,才能缓过气来。
”
他的老友,《花腔》的作者李洱回忆道:
“《丁庄梦》出版以后,我以为他去的次数会少一些了,不料,他还是经常去。
年前,有一次我碰到他,发现他情绪很坏,原来他刚从艾滋病村回来。
他每次回来,情绪都会坏上几天,因为他在村里结识的朋友又死了几个。
他向我讲述村边已经连成了一片的坟。
他甚至考虑是否收养一个艾滋孤儿。
”
但与他同去艾滋病村采访的记者,曾在手记中描述了一个害怕与艾滋病人握手,不愿接过病人手中的杯子,每晚要跑回县招待所安歇的阎连科……
“阎连科本人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他复杂而又简单,暴戾而又温柔,慧黠而又忠厚。
”李洱如是说。
北京,阎连科家中。
他现在还用手写方式创作,严重的颈椎病让他不得不在特制的小桌板上写字图/姜晓明
为抵抗恐惧而写
“说到底,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抵抗恐惧,大概是我目前写作的原因。
”
“少年时候,我曾崇拜三样东西,一是权力;二是城市,19岁时,第一次坐车去洛阳,看到楼那么高,姑娘那么漂亮,就渴望这一辈子能娶个城市姑娘做老婆,能住在城市的高楼里,而且住得越高越好;三是崇拜健康,从记事起,家里一天也没少过病人,因此,就从小渴望自己长大后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永远活着,长生不老。
”
“现在,我为之奋斗的三样东西,都成为了我的恐惧。
崇拜权力——40多岁了,回到老家,还害怕我们村村长,老远见了就忙着给他递烟。
崇拜城市——在城市的大街上害怕警察朝自己敬礼;躲在小胡同里走路,害怕从小胡同里窜出来一个高干子弟。
崇拜健康——偏偏自己一身的毛病,总让你想到残疾与死亡。
”“对不起,我有点累了。
”阎连科的语气有点歉然,他的眼皮略微耷拉着。
曾几何时,一旦闲静,他就逼问自己写作的意义。
“像一个法官威严地审逼一个不能控制自己去偷盗的孩子。
也许,那个法官得到他理想的回答;也许,那个孩子被逼问至死,也无法回答自己偷盗的理由。
可是,被自己逼问久了,就渐渐明白了一个问题:
写作也许是一种对人生的偷盗。
也许是一种在死亡的笼罩下,偷盗生命的过程。
”
们经历过一个不讲人话的阶段,我想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一部作品。
”
人物周刊:
《风雅颂》中,浓缩个人经验的描写占多大比例?
你不觉得书里对知识分子的评价过于偏激?
阎连科:
这部小说本来要取名为《回家》。
讲的是一个在城市里生活的老教授,与妻子生活多年却没有共同语言,在城市找不到根。
于是回到故乡,即使与过去的情人相遇,他最终还是无法获得心灵上的满足。
看了初稿的朋友都说书名不妥,便挖空心思地改成了《风雅颂》。
我知道,这样做难免有些附庸风雅,可一时又没有更为贴切的书名,也就只能这样罢了。
肯定是有些偏激。
大家都说每个作家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他的精神自传。
这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部小说除了说回家,还有其他复杂的成分,至少对我身上的那种嬉笑怒骂的习性揭露还是很充分的。
比如说,当年让我一天之内转业,我还在电话里假装地问,还要不要我去听课?
还说了非常好、非常感谢组织之类的话。
这其实就是一种懦弱虚荣的表现。
但要我在领导面前骂人、拍桌子,我没有这个能力。
这种骨子里的懦弱、明哲保身的思想,也和从小的生存环境有关,和从最底层爬上来的经历有关。
人物周刊:
你曾说过,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在城市里无论呆多久,都是找不到根的,现在还这样?
阎连科:
我想这种漂泊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几代人的事,是世世代代从乡村出来的人,都依然或是没有充分表达的一个问题。
我常说,看你在这块土地上有没有根,一是看这块土地上,埋没埋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二是看你对这个城市爱恨与否,在这个城市里面,有没有过自己爱的人。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你就和这座城市没有发生根的联系。
人物周刊:
你说过你见过无数爱情的虚幻,你对那种虚假的爱情反而感到一种真诚,但是对真诚的爱情反而害怕?
阎连科:
因为我觉得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塑造那种感天动地的爱。
中国人没有那种爱,中国人的爱是柴米油盐。
为什么我们老写想象中的爱,说得简单点就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没有,我们才需要塑造。
如果生活中有那种惊天动地,感天动地的爱情,就没必要在文艺中塑造和表达。
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已经无趣到无法想象。
大大小小,男孩女孩,包括我的孩子,都不太会信那种所谓真实的爱情。
我是不太会上网的,可是周围的人都在上网,包括在农村。
什么网恋,一夜情,两个人跑出去,过几个月领着孩子回来,最后离婚,一团乱麻。
人物周刊:
你在作品中并不吝于对性进行大量描写,你怎样看待性?
阎连科:
人是多面性的。
我们在白天见到的一个人,是阳光的一面,是看得见的一面。
可是夜里,一个人看不见的一面,阴暗的一面,它也是存在的。
而性就在这里面。
它是我们白天看不见的,它是肯定存在的,又是人性中深具代表的一面。
但如果只为了写性而写性,而没有挖掘性后面的内涵,那就十分无聊与浅薄。
伟大的作品都有种病态的存在
人物周刊:
你对自己在80年代纯文学昌盛时期,没有形成个人的写作特点,持什么看法?
阎连科:
实际上今天所有的作家重新进入文学史非常难,我们谈文学史就是从80年代开始。
但是,这段时期都与我没有关系。
因为80年代初,我没有独特的贡献,现在要受到关注很难,难就难在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当时,我的写作是非常传统、老式的,是在步别人的后尘。
之前写的小说百分之八十、九十都是垃圾。
写得再多,和真正的文学没有关系。
还有一点很重要。
我在最初学习写小说时,阅读的都是50年代的作品。
生活的环境没有和文学有关的因素,没有任何人能引导,注定我的写作起点非常陈旧非常低下。
读书也是需要机缘的。
当时,余华他们谈博尔赫斯的时候,我在制造垃圾,没时间看书或者看不进去。
但是当我有病,躺在病床的时候,就彻底安静下来了。
再去看马尔克斯、卡夫卡、博尔赫斯、胡安·鲁尔弗的《人鬼之间》,就真的看进去了,能感受到了。
我的小说的变化就是从疾病和阅读两方面开始,所以,我常说,伟大的作品都有种病态的存在。
人物周刊:
你觉得今天的读者和作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阎连科:
我觉得写作是与读者战斗。
我现在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你的小说必须要超出读者的想象,你写完了一篇小说,不是超过读者想象,读者就会抛弃你。
第二,是你的想法必须来自于头脑,来自于生存的灵魂,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读者都会抛弃你的,或者是你都会被读者打败的。
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写作的时间变长,我觉得我写作的疲惫状态已经慢慢来临,会慢慢有一种瓶颈的刺激,但第一你必须特别忠实于你的内心,第二是必须让内心和这个世界有关系。
人物周刊:
你说过,在写作上你一直在寻找那种不存在中的存在。
你也说过,现实主义不存在于生活与社会,只在于作家的内心世界?
阎连科:
我举一个例子。
我大哥有个孩子,很早就死掉了。
按我老家的风俗,他死后,要找个死掉的女孩和他安葬。
这样,我大哥就找了一个死去的女孩,在2004年的三四月份,把两人一起合葬进祖坟。
当时河南大雪纷飞,天气特别冷。
结果我看到,在那孩子棺材的一块红布上,爬满了小花蝴蝶。
这种天气下,从哪儿来的那么多蝴蝶?
那时候,很少见到这样的事情。
有5到10分钟的时间,那些蝴蝶才飞走了,瞬间就消失在大雪中。
这让我想到了“化蝶”。
我想创造这个词的人,可能他就遇到过这种事情。
总之,你说它不存在,它就不存在。
你说它存在,它就存在。
我不会再去遵循我们生活的客观现实和逻辑——“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有昨天,之所以有昨天是因为有前天”,我不会再去遵循这个了。
人物周刊:
张颐武指出,你和你同时代的作家都存在一个问题:
由于时代教育背景的特殊性,世界观还囿于二元对立的单一?
阎连科:
对我来说,二元对立,三元对立,四元,五元,……摆脱是不容易的,经历,视点,认识只能如此。
我不是也不会去摆脱,这是非常清楚的。
要摆脱不是我这一代人的事,而是下一代人或更下一代人的事情。
人物周刊:
到目前为止,你在创作上有没有什么遗憾?
阎连科:
最大的遗憾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给搞垮了。
这对写作的确是一种冲击,文学非常奇特,当你有感悟时,你没有能力去实践了。
还有就是浪费掉了一个人读书的最好阶段。
如果把身体健康和写作让我选择的话,我一定会选身体健康。
人物周刊:
如果不写作,你又怎么改变你的命运?
阎连科:
有时我在想,难道真的当了名作家就有意义?
在农村,许多人打打麻将、说说笑话、生生孩子、超生两个孩子,我会忽然觉得,他们生命的意义比我一点都不差。
你即便去当个总统,当个领袖,那么你的生命就比一个农民有意义吗?
这是不可能的,是我们升华了生命的意义。
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其实都是等同的。
现在,我觉得有一大批像我们这种人,对生命的认识既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又落不到地面上,这是生命中最痛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