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立ちぬ汉语译文简体中文.docx
《风立ちぬ汉语译文简体中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风立ちぬ汉语译文简体中文.docx(3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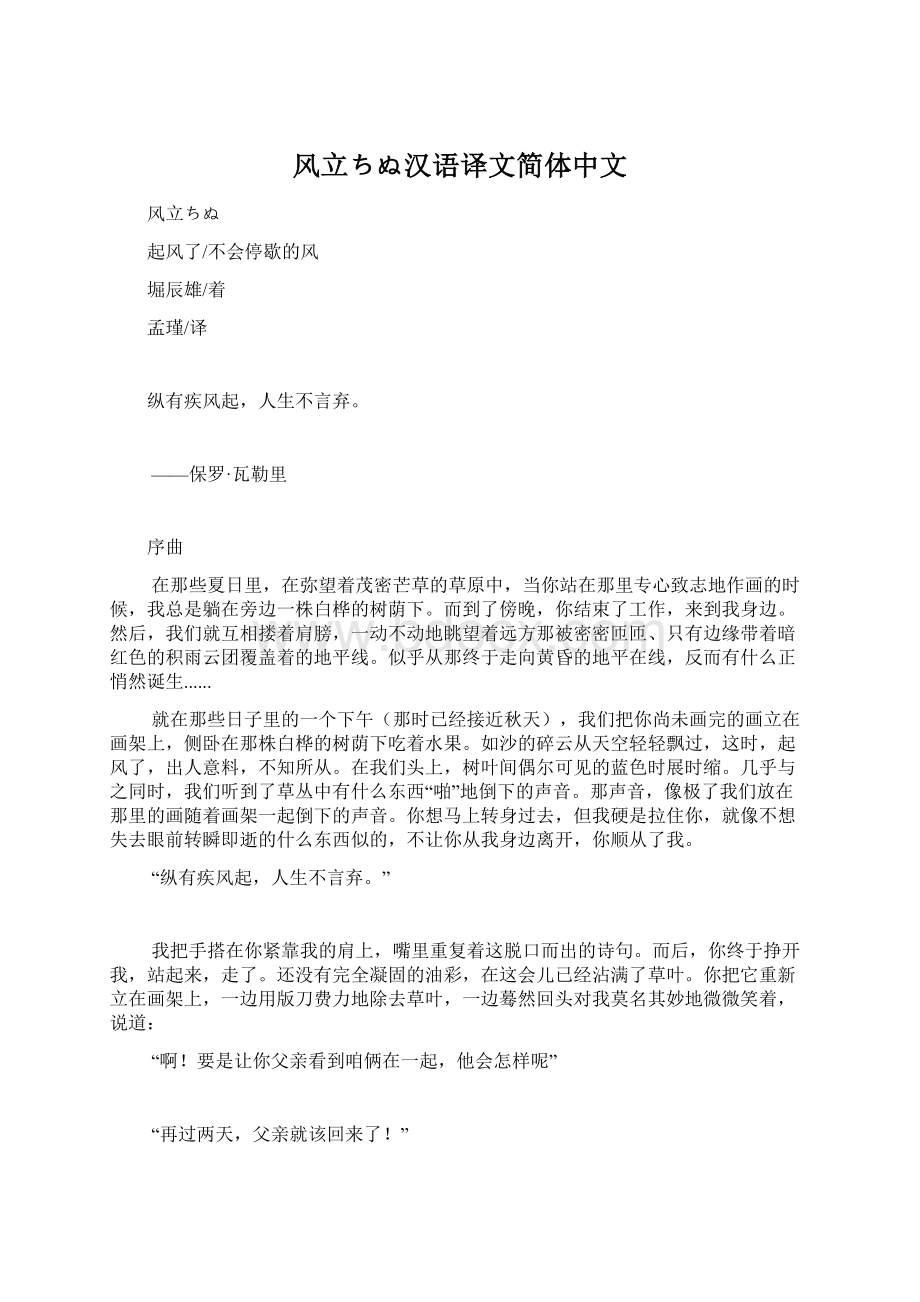
风立ちぬ汉语译文简体中文
风立ちぬ
起风了/不会停歇的风
堀辰雄/着
孟瑾/译
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
——保罗·瓦勒里
序曲
在那些夏日里,在弥望着茂密芒草的草原中,当你站在那里专心致志地作画的时候,我总是躺在旁边一株白桦的树荫下。
而到了傍晚,你结束了工作,来到我身边。
然后,我们就互相搂着肩膀,一动不动地眺望着远方那被密密匝匝、只有边缘带着暗红色的积雨云团覆盖着的地平线。
似乎从那终于走向黄昏的地平在线,反而有什么正悄然诞生......
就在那些日子里的一个下午(那时已经接近秋天),我们把你尚未画完的画立在画架上,侧卧在那株白桦的树荫下吃着水果。
如沙的碎云从天空轻轻飘过,这时,起风了,出人意料,不知所从。
在我们头上,树叶间偶尔可见的蓝色时展时缩。
几乎与之同时,我们听到了草丛中有什么东西“啪”地倒下的声音。
那声音,像极了我们放在那里的画随着画架一起倒下的声音。
你想马上转身过去,但我硬是拉住你,就像不想失去眼前转瞬即逝的什么东西似的,不让你从我身边离开,你顺从了我。
“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
”
我把手搭在你紧靠我的肩上,嘴里重复着这脱口而出的诗句。
而后,你终于挣开我,站起来,走了。
还没有完全凝固的油彩,在这会儿已经沾满了草叶。
你把它重新立在画架上,一边用版刀费力地除去草叶,一边蓦然回头对我莫名其妙地微微笑着,说道:
“啊!
要是让你父亲看到咱俩在一起,他会怎样呢”
“再过两天,父亲就该回来了!
”
一天早晨,我们正在森林里漫无目的地散步,你突然说出这句话。
我沉默着,似乎有点不高兴。
于是,你一边看着我,一边用略带嘶哑的声音开口说道:
“那样的话,就不能再这样散步了。
”
“散散步还不至于被限制吧”
我还是有点生气,虽然在我身上感到了你带着几分关心的视线,但是相比之下,我似乎更在意头上树梢发出的娑娑声响。
“父亲非常不愿意看到我们在一起。
否则,他就让我离开他。
”
我终于用近乎焦躁的眼神回头看着你。
“那么说,我们要就此分手了吗”
“可是……没有办法啊。
”
这样说着,你努力地微笑着,试图证明你真的主意已定。
啊!
那时你面庞的颜色、甚至你嘴唇的颜色,都是那么的苍白!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看上去已经把一切都托付给我,可……”
在裸根横七竖八越来越多的狭窄山路上,我让你走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以苦苦思索的姿态,极其艰难地走着。
那一带看上去树丛很深,空气冷飕飕的,到处都有沼泽侵凌。
突然,我头脑里闪出这样一个念头,你在今年夏天才偶然遇到我,你对我这样的人都那么顺从,那么对你父亲以及包括父亲在内、不断支配着你的所有人,该不会都像这样,不,该是更多、更多地,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完全交付出去的吧
“节子!
如果你就是这样的姑娘,我会更加更加喜欢你的。
等我对生活有了更可靠的把握,无论如何都会娶你的。
所以,你只管一直在父亲身边,就像现在这样……”
我一边对自己暗自说着这些话,却一边想征求你的同意似的突然抓起你的手。
你任由我那样抓住你的手,然后,我们就这样手牵着手,在一片沼泽前止步伫立,一言不发,用一种说不出的心情注视着。
阳光费力地穿过无数枝条交错的低矮灌木的缝隙,稀稀落落地洒在我们脚下深浸着的小沼泽最底部,洒在树根下生长着的羊齿草之类的杂草上面。
那团穿过树隙投到那里的光影,被似有似无的微风娑娑地摇动着。
此后两三天的一个傍晚,我在餐厅里看到你和来接你的父亲一起就餐。
你无情地用后背对着我。
一定是因为你在父亲身边,使你几乎无意识地做出这样的姿态和动作,让我感到了从未见过的、像小女孩儿一样的你。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出去散步,回来后又信步徘徊在无人的旅馆院子里。
野百合散发着香气,我漠然地凝望着旅馆还发出灯光的两三个窗口。
不知不觉间,好像起雾了。
窗口的灯光似乎对雾有着恐惧,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
而在我以为整个旅馆将一片漆黑的时候,轻轻的一声窗框响,一扇窗户缓缓地打开了。
一位身穿着蔷薇色睡衣的年轻姑娘,紧紧地抓着窗框探出身来,那就是你……
我终日闷在旅馆里,开始处理自己长期以来为你而中断的工作。
我自己都想不到,我竟能平静地埋头于工作。
不知不觉间,一切转入另一个季节。
于是,终于要出发的前一天,我走出旅馆去做久违的散步。
秋天使森林的一切杂乱不堪,几乎让人感到陌生。
叶子稀疏的树木,让远方不见人影的别墅阳台从树木丛中探将出来。
菌类湿乎乎的味道和落叶的气味混杂在一起。
这种意想不到的季节变换——和你分手后不知不觉之间如此逝去的时间,令我感到诧异。
在我心中的某个地方,有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离开你只是一时的。
所以,是否因此而使得这样的时间推移,也变得具备了对我而言与以往迥异的意义呢……这些事情,直到我事后清楚地确认之前,一直令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恍惚。
十几分钟后,我走出一片树林的尽头。
从那里便突然开阔起来,远远的地平线遥望如带。
草原上生长着一片茂密、弥望的芒草,我步入其中,在旁边一株白桦树荫下躺着。
白桦的叶子已经开始变黄,那就是在那个夏天的每一天,我一边凝视着你作画,一边像现在这样躺在这个地方。
当时几乎总是被积雨云遮盖的地平线,现在则是不知何去的远山,在随风摇摆着雪白穗稍的芒草之上,一座座清晰地展示着它们的轮廓。
我着力凝目注视那些远山的身姿,以至于将它们尽数默记。
无形之中,一种感觉渐渐地浮现在自己的意识之上。
我确信,一直在自己心中隐藏着的、大自然造化给自己的判定,今天终于找到了。
……
春
三月已至。
一天下午,我一如既往的悠闲的散步,顺便拜访一下节子家。
结果,在刚一进门旁边的树丛里,节子的父亲戴着匠人的大草帽,一只手拿着剪刀,在整理一片树木。
我认出了他,就像小孩子一样分开树枝,一边走近他的身旁。
互道了几句客套话以后,我就一动不动地、好奇的看着他工作。
就这样,完全潜身于树丛中,就会发现到处的小枝头上总有些白色的东西不时地闪耀,那是含苞待放的花蕾。
“这阵子,它们也变得神气多了。
”
节子的父亲突然向我这边抬起头,说起这几天刚刚和我订了婚约的节子的事来。
“要是天气再变得舒适一些,就让她换个环境试试,怎么样”
“那应该会是不错的……”我吞吞吐吐地说着,装作从刚才开始一直被眼前一粒闪闪发光的花苞所吸引不能自已的样子。
“有没有什么好地方呢这几天我正在物色一下——”节子父亲并不介意我的样子,继续说着。
“节子说,不知道F的疗养院怎么样。
可是听说,你好像认识那里的院长啊。
”
“诶……”我一边有点儿心不在焉似的回答着,一边把刚才发现的那朵白色花蕾拉到了眼前。
“可是,那种地方,一个人去能行吗”
“好像都是一个人去的呀。
”
“但是,节子是不能自己一个去的吧”
节子的父亲保持着那种莫名的为难表情,但看也不看我这边,猛然向自己眼前那棵树的一个枝条剪去。
看到这里,我终于忍不住了。
我说出了唯一能想到的、节子父亲等着我说出的那句话。
“那么,我们一起去也不妨。
现在手头儿做的工作,到那时也正好可以结束了……”
我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把好不容易刚刚抓到的那条带着花蕾的树枝再次轻轻放开。
同时,我发现节子的父亲的脸色豁然开朗了起来。
“那样关照的话,是最好不过了。
只是……太对不住你了……”
此后,我们谈论了那家疗养院所在的山岳地区的情况等等。
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话题落在了节子父亲正在整理的盆栽上了。
两个人现在相互感受到一种共同的情感,使得无边无际的话题都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节子起床了没”过了一会儿,我若无其事地试探问道。
“喏,大概已经起来了吧……请!
没关系的,你从这儿穿过去吧……”节子父亲用拿着剪刀的手,示意我要往庭院的木门走。
我费力地从树丛中钻出,推开被常春藤缠绕得有些难开的木门,径直穿过院子,朝着此前一直当画室用但现今却仿佛已被隔绝的病房走去。
节子好像一开始就知道我来了。
但似乎没有想到我会从这个院子进来。
她在睡衣上披了一件色彩鲜艳的短外褂,就这样一边躺在长椅上,一边在手中把玩着一顶此前从未见过的、带着细缎带的女士帽。
透过法式门,我注视着她,渐渐走近,而她好像也发现了我。
她下意识地动了一下,似乎想站起来,却依旧躺着,把脸朝向我,略带羞涩地微笑着,注视着我。
“你没睡吗”
我在门口一边有些胡乱地脱着鞋子,一边打着招呼。
“是想起来看看,可是转眼就累了。
”
这样说着,她用疲惫无力的手势,把那顶只是漫无目的地在手里把玩的帽子随意的扔在紧靠身边的梳妆台。
但是,帽子没有扔到的地方,落到了地板上。
我走过去,弯下腰拾起帽子,脸几乎要碰到她的脚尖。
这回,我自己就像她刚才那样把帽子拿在手里把玩。
后来,我终于开口问道:
“拿出这种帽子来做什么”
“这帽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戴了……是爸爸昨天买回来的……我爸是不是有些怪”
“这个……是你爸帮你挑的么你爸真好……怎么样把帽子戴上试试”
我半开玩笑地做出把帽子往头上戴的动作。
“不,别这样……”
她这样说着,做出一副厌烦的样子,抬起半个身子,似乎要避开。
随后,像是要解释一下似的露出梨涡浅笑,同时,仿佛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用明显消瘦的手,整理起有些凌乱的秀发。
那无意识的、极其自然的、韵味十足的女孩子的手势,简直就像在爱抚着我一样,让我感受到了几乎透不过气来的性感的魅力。
而那动作竟然使我不由自主地把视线移开。
过了一会儿,我把一直拿在手里把玩的帽子悄悄地放在旁边的梳妆台上,然后所有所思地陷入沉默,视线继续避开她。
“你生气了”她突然抬起头看我,小心地问道。
“没。
”我终于把目光转到她那边,然后前言不搭后语地冷不丁说道:
“你爸爸刚说了,你真的想去疗养院么”
“想啊。
这样呆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
要是能早点好了,就哪儿都可以去了。
可……”
“怎么啦怎么说起这件事来了”
“没什么。
”
“不要紧,你说吧。
……你不应该告诉我吗你不是说了也让我一起去吗”
“不是这个意思。
”她突然想打断我。
但是我没有理睬。
用一种跟最初不一样、愈发认真但又有些不安的语气继续说:
“不……即使你告诉我:
你不来也可以。
我也会照样跟你一起去的。
可是,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有点儿担心……
我在和你这样在一起以前,曾经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和一个像你这样的可爱的姑娘,去了一个寂寞的山中,过着只有两个人的生活。
我不是跟你坦白过有这么一个梦么哎,那个山间小屋的故事……我还问你在这种山里我们该怎么住,当时你笑得好天真。
其实我觉得,这次你提出要去疗养院,是不是因为我那个梦让你不知不觉动心了……是不是……”
她努力地微笑着,默默听着。
忽然,她干干脆脆地说:
“那种事情,我早就忘了。
”
然后,用一种不如说是安慰的眼神凝视着我,说:
“你总是时不时冒出些出人意料的东西啊……”
过了几分钟,我们带着就像我们之间根本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的表情,一起珍惜地望着法式门外的草坪。
草坪上绿意盎然,处处翻腾着水汽……
*
到了四月,节子的病情看起来有些逐步接近恢复期了。
那恢复着实缓慢,缓慢得令人焦躁不安。
而正是如此艰难的迈向恢复的一步一步,反而令人感到一种真实。
对于我们来说,这甚至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依靠。
一天下午,我去到她的家,恰好她父亲出门在外,节子一个人在病房里。
那天,她的心情似乎相当的好,非常难得地把总是穿在身上就不换的睡衣,换成了蓝色的罩衫。
我看到她这装扮,下定主意把她拉出去到院子里。
虽然有些许风,但也是柔柔的,令人心旷神怡。
她略带不自信的笑着,但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提议。
于是她的手搭在我的肩上,走出法式大门,谨小慎微地迈着步,战战兢兢的来到了草坪。
沿着灌木的围墙,走进各种外国品种混杂在一起、枝桠交错、难分彼此、枝繁叶茂的园林。
在这一片繁茂之上,到处都白色、黄色、淡紫色的小花蕾含苞欲放。
我止步于这繁茂的一处。
暮然想起去年秋天她告诉我花卉名称的情景。
“这个应该是紫丁香吧!
”我一边把头转向她,一边半带询问地说。
“那可不是紫丁香。
”她依然把手轻轻搭在我的肩上,有些过意不去地说。
“哼……那么,你一直都在误人子弟。
”
“我倒是没有撒什么谎.,那也是拜人所赐。
……只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花了。
”
“什么呀,眼看这花就要开了。
现在才坦白这事!
莫非那个也是……”我指住旁边的树丛。
“那是什么”
“金雀儿”她把枝条拿在手里。
我们这时挪到这片树丛前边。
“这个金雀儿可是真的。
看,有黄色、白色两种花蕾哦!
这边白色的,据说是相当稀有的。
那可是我父亲的骄傲啊……”
交谈着这些无足轻重的事情,节子的手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肩膀。
与其说她是累了,倒不如说是出了神,靠在我的肩上了。
然后,我们就这样久久的相视无语。
仿佛这样就能够原封不动地挽留这个花开吐芳的人生更久一些。
柔和的微风偶尔从对面的灌木墙缝隙里挤出,宛如被控制的呼吸,抵达我们前面的树丛,将树叶微微的抬起,然后行将过去,将现在的我们原封不动地留在这里。
突然,她把脸埋在自己搭在我肩上的手中。
我发现她的心脏比平时跳得更加强烈了。
“累了”我柔声问她。
“不是。
”她小声回答道。
但我感受到她的体重,缓缓地压到我的肩上。
“我身体这么差。
总觉得对不起你……”她的耳语很轻,与其是说我听到了,不如说是我感受到了。
“你是这样的柔弱,更让我感到怜爱。
你怎么不明白呢……”我在心里焦急地呼唤,但表面上却故意装出什么都没听见的样子,一动不动,没有应答她。
她忽然仰起脸,抬起头,渐渐地,手也离开了我的肩膀,一边走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宛如自言自语一样,含含糊糊地说:
“为什么我……这个时候……还表现得这么懦弱……这些日子,不管病得多重,我都没有胡思乱想,但是……”
沉默,令人忧虑地延长着这些话。
沉默中,她猛地抬起头。
我还以为她要注视我,她却再次把头低了下来,用略微抬高了的中音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想活下去……”
然后,她用听得见但又听不见的声音补充道:
“因为有你……”
*
那是我们两年前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夏天。
我不经意间脱口而出、而后也无缘无故地喜欢吟诵的诗句:
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
这句诗,突然间又为我们找回了那段时候一直都已忘怀的时光——换言之,人生最重要的、从人生自身到更加生动鲜活、更加烦恼苦闷的、快乐的每一天。
我们开始为月末去八岳山麓疗养院做准备了。
决定抓住那位相交不深的疗养院院长常常进京的机会,在出发之前请他看看节子的病情。
这一天,好不容易请到那位院长来到郊外的节子家。
接受了第一次检查之后,他说:
“问题不大。
嗯,得到山里苦个一两年吧!
”
院长给我们留下这些话,就匆匆忙忙的回去了。
我把院长送到车站,想从他那里听到只能告诉我的、关于节子的更准确的病情。
“这个……这种事情,不要跟节子说。
她父亲那边,我想在近几天跟他详细谈谈。
”
院长说这些开场白之后,带着几分痛苦的表情,非常详细地向我说明了节子的情况。
“你的脸色不也是非常难看吗我顺便也检查检查你的身体。
”他难掩同情地跟我说。
我从车站回来回到病房,节子的父亲依旧躺在节子身边,开始和她商议着挑选去疗养院的出发日期之类的事情。
我依旧带着无精打采的表情,加入到他们的讨论之中。
“可是……”不一会儿,父亲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一边站起来一边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说:
“已经恢复得这样了,只要夏天过去,一切应该都会变得很好的啊。
”说着,就走出了病房。
只剩下两个人了,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沉默了起来。
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春日黄昏。
我刚才觉得莫名的头疼,而这种疼痛的感觉越来越加深了。
于是,我不想引起注意,悄悄的站了起来,走到玻璃门边,把半边门打开一半,便靠在了门上。
就这样,我一动不动地发呆,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空虚的眼神投向背面腾起一片薄雾的树丛里边,心里想着:
“真香啊,那是什么花的香气……”
“你在干嘛”
我的背后,传来节子略带沙哑的声音。
这声音突如其来的把我从这种恍惚麻痹的状态下唤醒。
我背对着她不动,用假装出来的、若有所思似的语调,断断续续地说:
“我在想你的事情、山里的事情、还有在那里我们要过的生活。
”
而这样不断地说着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竟觉得直到刚才才真的在想这些事情。
是的,那以后,我好像也思考了这些事情。
“到了那边,真的应该有各种事情发生的……但是,人生这个东西,就像你一直做的那样,可以把一切都交给他。
如果能这样,就一定会把我们也许想都想不到去祈求的东西赐给我们。
”我心里这样想着,反而被一些细微的印象彻底吸引进去,而自己却丝毫没有注意到。
庭院还微微地亮着,而当我注意到的时候,房子里已经完全变得昏暗起来。
“要把灯打开吗”我回过神来问道。
“还是别开了……”她的回答声比刚才更加沙哑了。
良久,我们都没有说过话。
“我有些喘不过气来了,草的气味太浓了。
”
“那……我去把门关了。
”
我用近乎悲伤的语调这样应和着,抓住门把手,把门拉上。
“你……”这一次,她的声音听起来几乎就是中性的,“你刚才在哭吗”
我做出吃惊的样子,突然转向她。
“谁哭了……不信你看看我。
”
她甚至不想从床里把脸转向我,尽管天色昏暗,难以确认,但是她看上去是在全神贯注地看着什么东西。
而当我担心地把视线追过去的时候,却看到她在凝视着上空。
“其实……我也知道……刚才院长说了些什么……”
我想马上回答些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只是轻轻地再次关紧门,出神地注视着即将黄昏的庭院。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背后深深的叹息。
“对不起。
”她终于开口了。
那声音虽然仍有些颤抖,但比以前镇定了许多。
“这些事情……请你不要太过在意,我们……今后能活多久就多久吧……”
我转过头,看见她悄悄地把指尖放在内眼角上,一直没有移开。
*
四月下旬一个微云的早晨,节子的父亲把我们送到了停车场。
我们好像出发去度蜜月一样,当着父亲的面,非常高兴地乘上了前往山岳地方的火车的二等车厢。
火车缓缓离开了站台。
车后,只留下父亲一人努力装作若无其事地站着,他的后背已经微微前屈,仿佛突然变老了。
完全离开站台后,我们关上车窗,一下子表情变得寂寞起来,在二等车厢空着的一个角落坐了下来。
我们膝盖和膝盖紧紧的贴在一起,仿佛这样就能够相互温暖对方的心……
风雪黄昏
我们乘坐的火车一次次地攀上高山,沿着深深的溪谷奔跑,然后花了很长时间的横穿后,大地突然开阔起来,在经过了一个有很多葡萄园的台地以后,终于奔向山岳地带。
在这似乎没有尽头的、顽强地不断的攀登的途中,天空变得更低了,刚才看起来还是被束成一团的漆黑云朵,不知何时四分五裂地浮动起来,仿佛要直压我们的眼前。
空气也开始彻骨地寒冷起来。
我束起上衣的衣领,不安地守望着想把身子全埋在披肩里、闭着眼睛的节子,她脸上写满的与其说是疲劳,不如说是有些许兴奋。
她时而漠然地睁开眼睛看我。
最初,两个人每次还互相用眼睛对视微笑着,而后便只是互相不安地对视,马上又都把视线移开。
然后她又闭上了眼睛。
“怎么好像冷了起来,是不是下雪了”
“才刚过了四月,也会下雪吗”
“诶,这一带就是不能保证不下雪的。
”
虽然才三点左右,窗外已完全变得昏暗。
我凝望着窗外,发现到处排列着无数没有叶子的落叶松,间或混着些枞树。
我们已经过了八岳山脚,而眼下就应该看到的像山的东西却还是无影无踪。
火车在山麓那个和小仓库没有多大区别的小站停了下来。
车站上,有一名穿着“高原疗养所”标志的号衣、上了年纪的勤杂工来迎接我们。
我用胳膊架着节子,走向车站前久候多时的、又旧又小的汽车。
在我的臂弯里,我感觉到她有些踉跄,但却装出没有察觉的样子。
“累了吗”
“不累。
”
和我们一起下车的几个当地人,在我们周围窃窃私语着什么。
而当我们乘上汽车的时候,那些人便在不知不觉间,与其他村民混杂在一起,难以辨别,消逝在村落之中。
我们的汽车穿过简陋的小屋连成一列的村庄,刚一进入,在那无穷无尽扩展开来、直至遥不可及的八岳山脊、凹凸不平的斜坡前方,我们看到了一幢背靠杂木林、有着红色屋顶和几个侧楼的巨大建筑物。
“是那个吧!
”我一边用身体感受着车体的倾斜,一边喃喃自语道。
节子只是微微地扬起脸,用略带忧郁的眼神,木然地看着它。
到了疗养院之后,我们被安排到最里边、背后就是杂木林的那幢住院楼的二楼第一号病房。
简单检查之后,节子被命令马上上床躺下。
在油毡铺地的病房里,除了勤杂工刚刚送来的几只行李箱,就是被漆成飒白的床和桌椅。
只剩下两个人之后,我久久都不能平静,不时来到专门分配给陪护人的狭窄不堪的侧室,漠然的环顾着这令人感觉无遮无拦的室内,又数次走近窗户,专心观察天气的变化。
风费力地拖曳着漆黑的云,时而从背后的杂木林挤出尖锐的声音。
我一度走到阳台,做出一副很冷的样子。
阳台没有任何隔断,一直通向那边的病房。
我满不在乎地走去,窥望着每一间病房。
正好在第四间病房,可以透过半开的窗子,看到一位患者在睡觉。
于是,我马上就匆匆忙忙的回来了。
终于,灯亮了。
然后,我们围坐在护士送来的饭菜前。
那是我们第一次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就餐。
就此而言,有些冷清。
吃饭的时候,外面已经漆黑一片,所以也没有注意到什么,只是突然间觉得不知为什么四周忽然寂静了下来,原来不知何时天空飘起了雪。
我站起身来,把半开的窗子再关紧一点,然后,把脸凑到那玻璃跟前,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雪花沉沉下坠——以致于那玻璃因为我的气息而起了雾。
过了许久,我离开那里,并转向节子说:
“哎,你怎么啦……”
她依旧躺在床上,目光如炬地仰望住我的脸,却把手指放在嘴唇上,仿佛又不想对我说出那些话。
*
疗养院在宏大延绵、深褐色的八岳山麓由陡及缓处向南而立,并列地伸展着几行侧翼。
山麓的倾斜继续延伸着,使得三三两两的山村也都倾斜着,最后被无数的黑松树彻底覆盖,终止于视野之外的山谷。
从疗养院南向开放的阳台望去,可将那一带倾斜的山村和褐色的耕地尽收眼底。
而且如果是晴朗的好日子,在环绕的村庄和田野、排列紧密、无边无际的松林之上,总能看见自西而东的南阿尔卑斯山脉和它的几个支脉,在自己生成的云海中若隐若现。
到达疗养院的第二天早晨,我在自己的侧室里醒来。
小窗框中,晴澈的蓝天和几座雪白的、鸡冠似的山峰,宛如从大气中突然诞生出来似的,出人意料地呈现在眼前。
而躺着时看不见的阳台及屋里的积雪,沐浴着突然到来的、春意盎然的阳光,似乎正在不断地散发着水蒸气。
大概有点睡过头了,我急忙跳起来,走进隔壁的病房。
节子已经醒了,裹在毛毯里,一脸绯红。
“早啊!
”我也感觉到自己的脸也在涨红,轻松的说:
“睡得好吗”
“好。
”她对我颌首示意,“昨天吃安眠药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点头疼。
”
我做出那种无所谓的样子,劲头十足地把窗户以及通往阳台的玻璃门全部打开。
眼睛被光晃得一时间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
而当眼睛慢慢适应之后,逐渐看见被雪埋住的阳台、屋顶、原野、树木,上腾着轻盈的水蒸气。
“而且,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她在我背后开始说了起来。
我马上感觉到她似乎在努力说出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
就像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时一样,她现在的声音也略带沙哑。
这次轮到我转向她,把手指放在嘴上,不让她说出声来……
不久,护士长匆匆忙忙、表情亲切地走了进来。
护士长就是这样每天早晨一个病房一个病房的逐个看望患者的。
“您昨晚休息得好吗”护士长用亲切的语调问道。
节子什么也没有说,老老实实地点着头。
*
这种山中疗养院之类的生活,本身带有一种特殊的人性,那是从一般人看来已经无路可走之处开始起步的。
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也拥有这种似乎很陌生的人性,是从刚住院不久就被院长叫去诊断室、给我看节子患部X光照片的时候开始的。
院长把我带到窗边,仿佛我也得看似的,把照片的底板对着阳光,一一加以说明。
右胸的几根白花花的肋骨清晰可辨,但左胸的肋骨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宛如神秘黑花一样的病灶。
“病灶比想象的还要大,没想到会变得这么严重了……这样的话,恐怕是当下医院里第二严重的重症了……”
我从诊断室回来,感觉着院长这番话在耳边絮绕,却不知为什么像一个失去了思考能力的人一样,只是把那个刚刚看过的神秘黑花清晰的呈现于意识世界之上,仿佛它与那番话根本没有关系。
无论是与自己擦肩而过的白衣护士,还是已经开始在四周的阳台上做日光浴的裸体患者,病房的嘈杂,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