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溪的《中鉴录》及其思想史意义有关明代儒学基调的转换.docx
《王龙溪的《中鉴录》及其思想史意义有关明代儒学基调的转换.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王龙溪的《中鉴录》及其思想史意义有关明代儒学基调的转换.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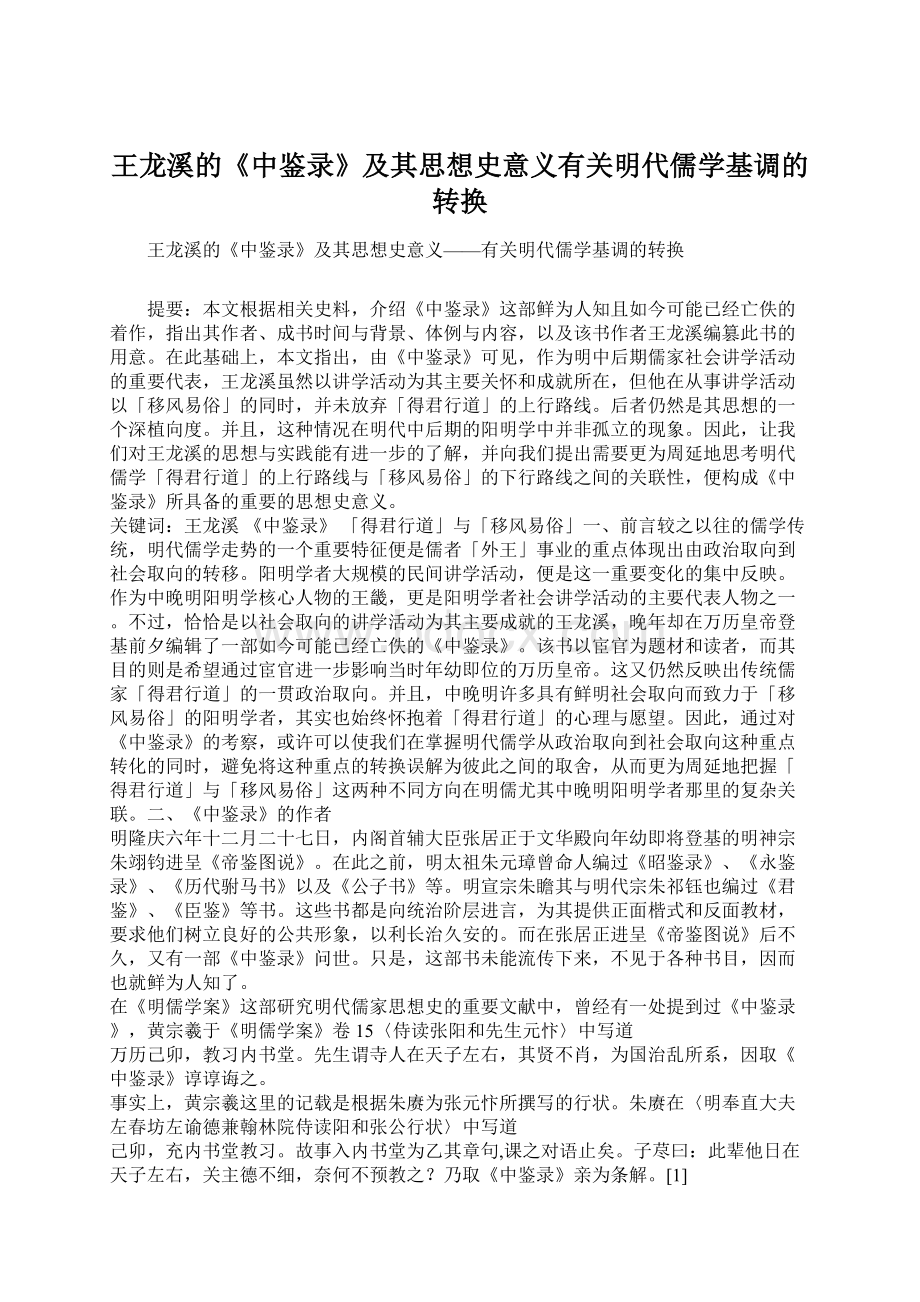
王龙溪的《中鉴录》及其思想史意义有关明代儒学基调的转换
王龙溪的《中鉴录》及其思想史意义——有关明代儒学基调的转换
提要:
本文根据相关史料,介绍《中鉴录》这部鲜为人知且如今可能已经亡佚的着作,指出其作者、成书时间与背景、体例与内容,以及该书作者王龙溪编篡此书的用意。
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由《中鉴录》可见,作为明中后期儒家社会讲学活动的重要代表,王龙溪虽然以讲学活动为其主要关怀和成就所在,但他在从事讲学活动以「移风易俗」的同时,并未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
后者仍然是其思想的一个深植向度。
并且,这种情况在明代中后期的阳明学中并非孤立的现象。
因此,让我们对王龙溪的思想与实践能有进一步的了解,并向我们提出需要更为周延地思考明代儒学「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与「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之间的关联性,便构成《中鉴录》所具备的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关键词:
王龙溪《中鉴录》「得君行道」与「移风易俗」一、前言较之以往的儒学传统,明代儒学走势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儒者「外王」事业的重点体现出由政治取向到社会取向的转移。
阳明学者大规模的民间讲学活动,便是这一重要变化的集中反映。
作为中晚明阳明学核心人物的王畿,更是阳明学者社会讲学活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不过,恰恰是以社会取向的讲学活动为其主要成就的王龙溪,晚年却在万历皇帝登基前夕编辑了一部如今可能已经亡佚的《中鉴录》。
该书以宦官为题材和读者,而其目的则是希望通过宦官进一步影响当时年幼即位的万历皇帝。
这又仍然反映出传统儒家「得君行道」的一贯政治取向。
并且,中晚明许多具有鲜明社会取向而致力于「移风易俗」的阳明学者,其实也始终怀抱着「得君行道」的心理与愿望。
因此,通过对《中鉴录》的考察,或许可以使我们在掌握明代儒学从政治取向到社会取向这种重点转化的同时,避免将这种重点的转换误解为彼此之间的取舍,从而更为周延地把握「得君行道」与「移风易俗」这两种不同方向在明儒尤其中晚明阳明学者那里的复杂关联。
二、《中鉴录》的作者
明隆庆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于文华殿向年幼即将登基的明神宗朱翊钧进呈《帝鉴图说》。
在此之前,明太祖朱元璋曾命人编过《昭鉴录》、《永鉴录》、《历代驸马书》以及《公子书》等。
明宣宗朱瞻其与明代宗朱祁钰也编过《君鉴》、《臣鉴》等书。
这些书都是向统治阶层进言,为其提供正面楷式和反面教材,要求他们树立良好的公共形象,以利长治久安的。
而在张居正进呈《帝鉴图说》后不久,又有一部《中鉴录》问世。
只是,这部书未能流传下来,不见于各种书目,因而也就鲜为人知了。
在《明儒学案》这部研究明代儒家思想史的重要文献中,曾经有一处提到过《中鉴录》,黄宗羲于《明儒学案》卷15〈侍读张阳和先生元忭〉中写道
万历己卯,教习内书堂。
先生谓寺人在天子左右,其贤不肖,为国治乱所系,因取《中鉴录》谆谆诲之。
事实上,黄宗羲这里的记载是根据朱赓为张元忭所撰写的行状。
朱赓在〈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阳和张公行状〉中写道
己卯,充内书堂教习。
故事入内书堂为乙其章句,课之对语止矣。
子荩曰:
此辈他日在天子左右,关主德不细,奈何不预教之?
乃取《中鉴录》亲为条解。
[1]
仅就朱赓这一最初的记录以及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的转述来看,很容易让人以为《中鉴录》的作者便是张元忭。
但是,在徐阶和赵锦的记载中,均明确指出《中鉴录》的作者是张元忭的同乡兼师辈王龙溪。
王龙溪是王阳明的高第弟子,在明中后期的中国思想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徐阶在其〈王龙溪先生传〉中写道
公着有《大象义述》、《丽泽录》、《留都》、《岘山》、《东游》、《南游》诸《会记》,《水西》、《冲玄》、《云门》、《天山》、《万松》、《华阳》、《斗山》、《环濮》诸《会语》,《罗念庵东游记》、《松原晤语》、《聂双江致知议略》、《别曾太常》、《赵瀔阳漫语》、《答王敬所论学书》以及《中鉴录》凡数十种。
而赵锦在为龙溪写的〈墓志铭〉中也同样说道
所着有《龙溪先生全集》二十卷、《中官中鉴录》七卷、《大象义述》、《念庵东游记》及诸《会语》行于世。
尽管前引朱赓和黄宗羲的记载有可能让人以为张元忭是《中鉴录》的作者,但那毕竟是读者自己的联想,细读文句,其实并不能断定。
徐阶和赵锦均与龙溪交往密切,所说自非虚言。
此外,在龙溪给张元忭的一封回信中,更直接说明了《中鉴录》乃龙溪所作。
领手书并诸论学稿,具悉明定造诣之概。
既膺起居之命,内馆主教势不得兼。
所云《中鉴录》,未敢为不朽之作。
区区两三年纳约苦心,庶几自尽。
内馆之设,事几若微,于圣躬得养与否,所系匪轻。
不知相继主教者能悉领此意,不做寻常套数捱过否?
由此可见,张元忭是看过《中鉴录》并给予很高评价的。
而将龙溪的这封信与前引朱赓、黄宗羲的记载相对照,也就自然很清楚《中鉴录》的作者是谁了。
只是,《中鉴录》虽或如赵锦所说,在当时曾经一度「行于世」,但如今却可能已亡佚,无法让我们得观其详了。
不过,所幸龙溪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曾多次提到过《中鉴录》。
在《王龙溪先生全集》中,卷九至卷十二部分为龙溪与友人的通信汇编,其中有〈与陶念斋〉、〈与耿楚侗〉、〈与朱越峥〉、〈与赵瀔阳〉以及〈与曾见台〉这五封书信是专门有关《中鉴录》的。
由于这五封书信对《中鉴录》的基本相关情况已有较明确的说明,以下,我们便以之为基本依据,并结合其它的材料,对《中鉴录》的相关情况加以介绍,既为史海钩沉之一则,同时也对其所具有的思想史意义略做提示。
为了既保持这五封书信的整体性,避免在后文局部引用时割裂其内在一贯性,同时不占用正文的篇幅,我们将这五封书信做为附录列于文末,以资参照。
三、《中鉴录》的成书时间
除了第四封书信之外,龙溪这五封信都是以「圣天子睿智夙成、童蒙之吉」来开头的,第一封《与陶念斋》更是明确指出「天子新祚」,而就《与耿楚侗》中所谓「迩者元老有《帝鉴》」来看,我们可以判定龙溪《中鉴录》之成书当是在万历皇帝登基不久,张居正进呈《帝鉴图说》之后,因为龙溪卒于万历十一年,所谓「天子新祚」,不可能指万历以后的皇帝。
再者,陶念斋(1527─1574,名大临,字虞臣,号念斋,谥文僖)于万历皇帝登基时迁礼部右侍郎兼学士,负责给年幼的神宗讲学,这和龙溪信中所谓「执事任养蒙之贵,其功贵豫」亦恰相吻合。
赵濲阳在万历元年担任侍读,朱越峥也在万历元年升任礼科都给事中。
从龙溪给这些人内容大体相同的书信来看,均可以推断龙溪的书信应当是写在万历登基不久的时候。
另外,龙溪在给陶念斋的信中谓《中鉴录》「寄麟阳世丈处,可索取观之」,给耿定向的信中称「吾丈遵养逢时,帝心简在」,而万历元年二月耿定向晋工部屯田主事,九月晋尚宝丞,万历二年八月晋尚宝少卿,万历三年晋太普少卿、督察院右检都御史之后,五月即因母卒奔归。
陶念斋于万历二年即卒,赵锦亦于万历二年迁南京右都御史。
因此,龙溪写给这些京中任职的朋友们的信,至少应在万历二年之前,万历皇帝正式登基之后,大概在万历元年左右。
而《中鉴录》的完成,则当略早。
至于编篡的时间,则约有两三年之久,这在前引龙溪给张元忭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所谓「区区两三年纳约苦心」。
万历皇帝初登基时,颇显示出圣明天子的端倪,赢得了朝野的广泛赞誉。
因此,龙溪在〈与朱越峥〉中声称:
「圣天子睿智夙成,得于传闻,宛然帝王矩度。
」并且,在几乎每一封书信的开头都用的「睿智夙成」来形容万历,的确反映了当时举国上下对神宗皇帝的普遍佳评和殷切希望。
毕竟,在传统中国社会,再没有什么比有可能出现一位圣明天子会更令儒家知识分子感到欢欣鼓舞的了。
龙溪《中鉴录》的问世,正是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四、《中鉴录》的体例与内容
即便《中鉴录》如今已佚,我们无法得观其详,但是凭借附录所列龙溪的书信,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到《中鉴录》的基本体例和内容。
龙溪在《与陶念斋》和《与朱越峥》中说《中鉴录》分三册,前面我们所引赵锦为龙溪写的墓志铭文则指出《中鉴录》有七卷。
而根据龙溪所写的书信来看,则龙溪曾经请耿定向为《中鉴录》做序言,请曾同亨为《中鉴录》做跋语,请朱南雍、赵志皋予以修正,并请耿定向、赵志皋「梓而行之」、「刻布以传」。
当然,这些人是否将龙溪之所托付诸实际,现在已不得而知。
但是,从我们在开头曾引《明儒学案》中张元忭取《中鉴录》教诲内廷宦官的记载,以及龙溪书信中所谓「有稿在王龙阳处」、「托龙阳奉览」和「寄麟阳世丈处」这一类的话可见,《中鉴录》至少曾经在龙溪的一部分同志道友们中间传阅过。
[10]由此可知,龙溪的《中鉴录》共分七卷三册,除了正文之外,或许还包括耿定向的序、曾同亨的跋。
不过,我们在耿定向和曾同亨现有的文集中并未见到相关的文字。
当然,这并不足以推断《中鉴录》实际上没有得以刊刻流传。
因为赵锦明确指出龙溪的《中鉴录》曾经与其它的文字一道「行于世」,既然龙溪其它的那些文字都有刊刻,便很难说单单《中鉴录》未有刊刻。
此外,根据前文朱赓为张元忭所做行状中的那段文字,张元忭用来教导宦官的事发生在万历己卯,亦即万历七年,那时距龙溪完成《中鉴录》已有六、七年的时间了,如此则更难说他使用的会是龙溪的未刊手稿。
关于《中鉴录》的基本内容,龙溪在《与朱越峥》一书中则有较明确的说明,所谓「不肖因篡辑春秋以下历代诸史宦官传,得其淑与慝者若干人,分为三册。
其言过于文而晦者,恐其不解,易为浅近之辞;其机窍过于深巧者,恐启其不肖之心,削去不录。
我国朝善与恶者,亦分载若干人。
首述太祖训谕教养之术、历代沿革之宜。
又为或问,以致其开谕之道,个人为小传,以示劝阻之迹。
」由此可知,龙溪的《中鉴录》基本上是一部人物传记的选录,它取材于一直到明代为止的各种史书,从历代有关宦官人物的传记中选择善恶两方面有代表性的若干人物,每个人物作成小传。
但龙溪并非只是就原文加以节录汇集,而是进行了文字上的更易与修饰。
并且,龙溪以或问的方式加上自己的按语,从而使之不仅仅是事实的记录,还包括对这些人物的行为进行价值上的评判。
这样一来,对于宦官而言,《中鉴录》似乎便具有了某种范例的意味。
五、《中鉴录》的目的龙溪为什么要编篡《中鉴录》这样一部书,这在他写给不同人物的书信中也有明确的交代。
在〈与耿楚侗〉中,龙溪称「迩者元老有《帝鉴》,独中官无鉴,似为缺典」,而在〈与朱越峥〉中则进一步指出:
「凡我大小臣工,守令有鉴,台谏有鉴,辅相有鉴。
迩者复有《帝鉴》,独中官未有所鉴,似为缺典。
」不过,龙溪作《中鉴录》却显然不是为了单纯解决「缺典」的问题,而是为了教化内廷的宦官,如〈与陶念斋〉中所云「开其本心之明,示以祸福利害之机」,〈与
耿楚侗〉中所谓「开其是非之本心,警以利害之隐机」。
甚至连具体的方式,龙溪都已有筹算,所谓「择此辈可与言者,无意中授以一册,递相传玩,少知劝阻,兴起善念,拂其邪心」。
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的话,甚至教化中官仍然还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并不在于教化中官本身,而是希望通过中官的作用,达到对年幼的新天子的「养正」之功。
有了贤明的天子,儒家一贯的政治理想才能得以实现,家国天下才会在和谐有序中健康发展,欣欣向荣,这恐怕才是龙溪最终的用心所在。
虽然明太祖朱元璋有见于以往历史上宦官干政的祸患,从而为以后立下了内臣不得干预朝政的祖训。
但是,朱元璋自己因胡惟庸案而于洪武十三年废相,不仅使专制主义在传统中国社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也为后来宦官干政较之以往历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埋下了体制上必然的祸根。
正如黄宗羲所言「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
[11]到万历时期,宦官对朝政的干预甚至把持,已经根本不再是一个有可能对治的问题,而早已成为各种实际政治运作所必须由之出发的前提之一了。
有明一代宦官专权,如王振、刘瑾、魏忠贤之类,几乎是稍知历史者皆耳熟能详的。
而张居正之所以能够排挤掉高拱而成为内阁首辅大臣,很大程度上便是得到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帮助。
[12]至于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之后所经历的政治上的艰难险阻、风云变换,除了部分朝臣妒忌阳明的赫赫军功而担心权力的重新分配,以及学术上归属不同所导致的门户之见这些因素之外,相当程度上也与宦官直接相关,既有太监张忠之流的构陷与刁难,以致演出了明武宗在阳明擒获朱宸濠之后还要御驾亲征的荒唐一幕,也有太监张永等人的护持与帮助。
[13]诚如孟森先生所谓:
“明中叶以后,朝廷大事,成败得失,颇系于阉人之贤否。
”[14]因此,对于内廷宦官的作用,除了对于历史前鉴的了解之外,亲炙阳明的龙溪无疑不能不了然于心。
尤其对于年幼的皇帝,尽管有侍讲大臣承担启蒙教师的职责,这些侍讲大臣也往往多是如龙溪所谓的「海内忠信文学之士」。
但是,亦诚如龙溪所言,毕竟「外廷公卿进见有时」,年幼的皇帝则「日处深宫,与外廷相接之时无几」,「食息起居,不得不与中官相比昵」。
当然,这种状况并不合理,乃是「势使然也」,所谓「三代以降,君亢臣卑,势分悬隔。
」不过,尽管并不能简单地将儒家在政治上化约为只知维护现状的保守主义,因为在既存政治─社会无道之极的情况下,儒家是主张「汤武革命论」的,但在通常情况下,儒家的变革之道的确往往是从既定的存在结构出发因势利导,以求渐变,而不是打破现有的结构,另起炉灶。
所以,在龙溪看来,既然现实的情形是:
「在内所赖,全在中官。
盖幼主深处宫闱,舍此辈无与周旋承事,导之以正则吉,纳之于邪则凶。
」那么,「吾人欲引君道,舍中官一路,无从入之机」,便恐怕是在所难免的了。
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士大夫所代表的清流,与宦官集团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自汉代以来,彼此之间的紧张时时演化为冲突与对决。
在龙溪完成《中鉴录》的万历初年,虽然儒家清流与宦官集团之间还并未发展到如晚明东林党人与宦官集团之间形成大规模冲突,以致演出一幕「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地步,但至少以清流自居的儒家人物,除非朝廷公务,一般也是绝不屑与宦官有所往来的。
不过,历史上的宦官除了汉代的十常侍、明代的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大奸大恶之外,虽多阴险邪曲之辈,却也不无忠义良善之士。
[15]我们从附录所列龙溪几封书信中的措辞可见,尽管龙溪对中官一类人在价值层面上亦难免不持较为负面的评价,此固历史情势所使然,但同时龙溪也指出:
「此辈伎俩,染习虽深,然未尝无是非本心,利害未尝不明」,甚至将他们比做「缀衣虎贲之士」。
儒家心学一脉发展到王阳明的良知教,极大限度地高扬了人的道德主体性,肯定了每一个人都内在地具有良知本心,以为成圣成贤的先天根据。
现实型态上每一个人都难以达到圣贤境地,但从潜能上讲却又每个人都是圣贤,所谓「人人心中有仲尼」。
在这个意义上,宦官虽然在生理上有异常人,却仍不例外。
况且,儒家士大夫出于自觉不自觉的歧视心里,将宦官视为异类,不与之交通,也往往是令宦官们自甘陷溺,并造成儒家士大夫与宦官彼此紧张冲突的原因之一。
正如龙溪所言:
「此辈并生天地间,是非利害之心,未尝不与人同,但溺于习染,久假不归。
况吾辈不能视为一体,自生分别,有以激之。
彼此势离,则情间而意阻,未尝开以是非,导以利害,譬之迷途之人,甘于离陷,欲其回心向善,不可得也。
」因此,在龙溪看来,基于儒家「万物一体」、「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念,教化中官,使其「同心向善」、「回心向主」,显然应当是有其可能性的。
而就所收到的对于君主的「辅理之益」、「匡弼之劳」,与外廷朝臣相较,更是「功可百倍」这一点而言,则教化中官便更有其必要性。
不过,即便「人性本善」是北宋道学兴起以来几乎所有儒家知识分子的基本肯认,且王阳明一派的良知教又几乎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信念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龙溪同时代的士人,即使是同属阳明学阵营的儒家学者,在都能认识到宦官对于皇帝影响之大的情况下,恐怕却未必都会像龙溪那样将宦官作为政治诉求的对象。
毕竟,视儒家清流与宦官集团即便不是势同水火,至少也是泾渭分明,这一点自汉代以降至龙溪所处的明中期,似乎早已成为儒家士子们的文化心理结构或「心灵的积习」了。
龙溪之所以能有《中鉴录》之作,不避忌以宦官为政治诉求的对象,希望通过宦官的作用来培养一位圣明的君主,除了其「优世之微忱」、「芹曝之苦心」之外,与其力斥乡愿,提倡「自信本心」、「不以毁誉为是非」的「狂者之学」这一思想向度,恐怕也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16]
六、《中鉴录》的思想史意义即使《中鉴录》这部书的具体内容我们目前已无法了解,但是对于其思想史意义而言,或许我们前文的考察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分析基础。
至少自宋代以来,儒家士大夫的讲学活动便随着书院等民间社会组织的建立而逐渐发展,不过,这种以「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而非「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为特征的讲学活动,要到了明代尤其阳明学的讲会活动兴起之后,才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尤其阳明学者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点,与先秦孔孟以来以君主为说教对象的传统已经有所差异。
[17]明代高度专制的政治体制与氛围,是促成这种转变的外部压力之一,而当时儒家士大夫动用地方各种资源能力的强化,以及逐渐繁荣的社会经济,[18]也为大规模的社会讲学活动提供了条件。
[19]不论讲学活动其实仍以士大夫阶层为主,就某种意义而言,即便是向来以民间化着称的泰州学派,也不过是表明了阳明学的普及,并不意味着士大夫阶层构成讲学活动的主体以及讲学活动始终以儒家的经典文献为基本内容这一性质有所改变。
[20]但是,无论如何,阳明学者讲学的空间与对象,其重心的确是由庙堂转向了山林。
王阳明事功赫赫,但他却一再强调讲学活动才是他的究心所在。
[21]而作为明中期讲学活动的核心人物,龙溪本人几乎献身讲学活动的一生,对此也恰恰可以提供最佳的佐证。
王龙溪一生大部分时间是致力于阐扬王阳明的致良知教,他在各地讲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年过八十仍不废出游。
所谓「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莫不以先生为宗盟。
年八十,犹周流不倦」。
[22]当有人劝他高年不宜过劳外出时,龙溪回答说
不肖亦岂不自爱?
但其中亦自有不得已之情。
若仅仅专以行教为事,又成辜负矣。
时常处家,与亲朋相燕昵,与妻奴佃仆相比狎,以习心对习事,因循隐约,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觉者。
才离家出游,精神意思便觉不同。
与士夫交承,非此学不究;与朋酬答,非此学不谈。
晨夕聚处,专干办此一事。
非惟闲思妄念无从而生,虽世情俗态亦无从而入。
精神自然专一,意思自然冲和。
教学相长,欲究极自己性命,不得不与同志相切磨、相观法。
同志中因此有所兴起,欲与共了性命,则是众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
男子以天地四方为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
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此原是孔门家法。
吾人不论出处潜见,取友求益,原是己分内事。
若夫人之信否,与此学明与不明,则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强也。
至于闭关独善,养成神龙虚誉,与世界若不相涉,似非同善之初心,予非不能,盖不忍也。
[23]
由此可见他对于讲学活动的热衷,甚至颇具宗教精神。
但是,恰恰是堪称明代讲学活动典范的龙溪,其思想却隐含着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层面。
这是以往绝大多数研究龙溪的学者们所忽略的。
而前面对有关《中鉴录》的考察,正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
万历皇帝登基时,龙溪已是七十六岁高龄的人了,[24]而此时他将自己篡辑的《中鉴录》委托先师之子带到京师,并不厌其烦地分别写信给京中任职的道友们,甚至连「无意中授以一册」这样传播给中官的具体方式都考虑在内,显然充分说明了他通过中官以「得君行道」的强烈愿望与良苦用心。
对此,本文开头所引龙溪五封书信的内容以及我们前面进行的分析已足资为证。
而在给当时在京任职的邹守益之子邹善的书信中,龙溪更是明确将对幼年天子的「养正」之功视为「第一义」。
所谓
迩来京师事变日新,有如轮云。
天子新祚,睿智夙成。
童蒙之吉,所以养正,不可不熟为之虑。
须复祖宗起居注、宏文馆旧制,选用忠信有学之士十余辈,更番入直,以备顾问而陪燕游,方为预养之道。
闻冲年气淑,侭好文学,时与讲官接谈,机犹可入。
不知当事者以此为第一义不?
[25]
由此可见,作为以「移风易俗」为目标的「下行路线」之重要代表人物的龙溪,恰恰仍然深怀着强烈的「得君行道」的心愿,围绕《中鉴录》所发生的一系列行为,也正是这种愿望的体现以及「上行路线」的实行。
并且,尽管龙溪完成《中鉴录》并试图通过京中任要职的道友们使这部书刊刻流通且发生实际的作用是在「睿智夙成」的万历刚刚登基之时,但龙溪给张元忭的信中所谓「区区两三年纳约苦心」,却又显示出虽然万历新一代王朝的开启或许是龙溪推出其《中鉴录》的直接的外部契机,但龙溪早在面临有可能出现一位圣明君主之前,便已经有编篡《中鉴录》这样一部书,以便通过宦官去影响君主的打算了。
这一点更加说明,龙溪「得君行道」的意愿,又绝非万历登基这一事件所激发的偶然之举、应时之作,而是其思想深层的一个基本面向。
龙溪委实不汲汲于科举、从政,这由其生平可见,[26]即便在担任行政官员期间,他甚至仍然不忘与吏曹部中的同事相约连群论学。
[27]在龙溪的集子中,也完全没有「策论」之类的文字,有的只是良知教义理的阐发以及各种讲学活动的记载,认为龙溪一生以讲学为其成就所在以及关怀的重点,或许并不为过。
但是,不论短暂的从政经验或许是构成是龙溪不得不将说教的对象由庙堂之上的君主转向儒家知识分子和社会公众的客观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明代的高压政治迫使儒家知识分子开拓出「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这自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儒家尚未能对政治与道德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有所反省和简别的情况下,[28]龙溪显然不可能真正放弃「得君行道」的心愿;在传统君主制的政治结构之下,若不通过帝王这一权力的枢纽与核心,任何的「道」都几乎无法得以落实,对此,龙溪也不可能缺乏充分的认识。
我们提出《中鉴录》这部鲜为人知的撰述加以讨论,在知识性的历史考察之外,正在于揭示《中鉴录》所反映的龙溪思想的一个深植向度。
当然,这一向度与其以「移风易俗」为目标的讲学活动并不互相抵触,它所能够说明的关键在于:
龙溪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在长期的高压政治之下,虽然已经开辟出通过多种形式的讲学活动「以学为政」、「移风易俗」这种推行儒家政治理想的曲折、间接的道路,但同时依旧始终怀抱着出现圣明君主的希望和企盼。
一旦稍具条件,这种内在的心愿便立刻会转化为现实的行动。
非但龙溪围绕《中鉴录》所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是如此,张元忭亲自采用《中鉴录》教导宦官的行为,所谓「亲为条解」、「谆谆诲之」,则无疑更是这种心愿的具体落实。
当然,这种心愿及其表达往往以失望而告终,万历皇帝后来的表现,便直接对此提供了注脚,但这或许正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一贯精神的一种表现吧。
事实上,龙溪《中鉴录》所反映的那种「得君行道」的愿望,在明中后期的儒家知识分子中并非孤立个别的现象。
周海门所作〈天真讲学图序赠紫亭甘公〉同样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
盖即学即政,自昔未有判为两事者。
降及后世,兹风始湮。
师有专门,相多无术。
虽有宋真儒辈起,而时位所拘,事功亦未有与着述并着者。
盖自政学分离,而大道使不得为公。
千余年来,无有善治。
圣人之所为优,其虑远矣。
惟兹昭代,乃有阳明,直接千圣之宗,复燃长夜之炬,挺身号召,到处朋从。
当秉钺临戍,而由讲廷大启。
指挥军令,与弟子答门齐宣。
窃谓自孔子以来,未有盛于阳明,是岂阿语哉?
迄今百有余年,复见我紫亭甘公。
公默体性真,密修至行。
抚循全浙,惠洽风清。
延儒倡道,一切步武阳明。
……虽然,阳明更有未了之案,留俟我公者。
阳明寄居闲外,未获一日立朝。
相业未彰,人用为恨。
公且内招,指日掌宪。
持铨居正,本赞丝纶,则阳明未有之遇也。
……世之忧国忧民者不乏,而忧学之不讲于朝署之间,鲜不谓迂,非公无能辨此者。
率帝臣王佐之典刑,守泥山之家法,以毕阳明未竟之用,为千古一快!
[29]
这篇文字是写给甘紫亭的。
当时在浙江担任地方官的甘紫亭奉召入阁,面临被君主重用的机会,于是周海门便写了这样一篇情见乎辞的文字。
文中深以阳明在世时未能入阁受到朝廷的重用为憾,[30]甚至明确表白了认为阳明应当秉执「相业」的看法,所谓「阳明寄居闲外,未获一日立朝。
相业未彰,人用为恨。
」而将殷切的希望寄于了同阳明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的甘紫亭。
[31]周海门是龙溪的传人,[32]他这里直接以讲学于朝署之间、政学合一为儒家古来一贯的传统,并不以单纯的民间讲学为满足,同样是表露了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尤其阳明学者虽然迫于政治情势而开辟了社会讲学的道路,但却并未放弃将儒家之道「上行」于「朝署」的任何机会。
另外,罗近溪是明中后期与王龙溪齐名的讲学人物,他讲会时经常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