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间的辩证法共10页.docx
《居间的辩证法共10页.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居间的辩证法共10页.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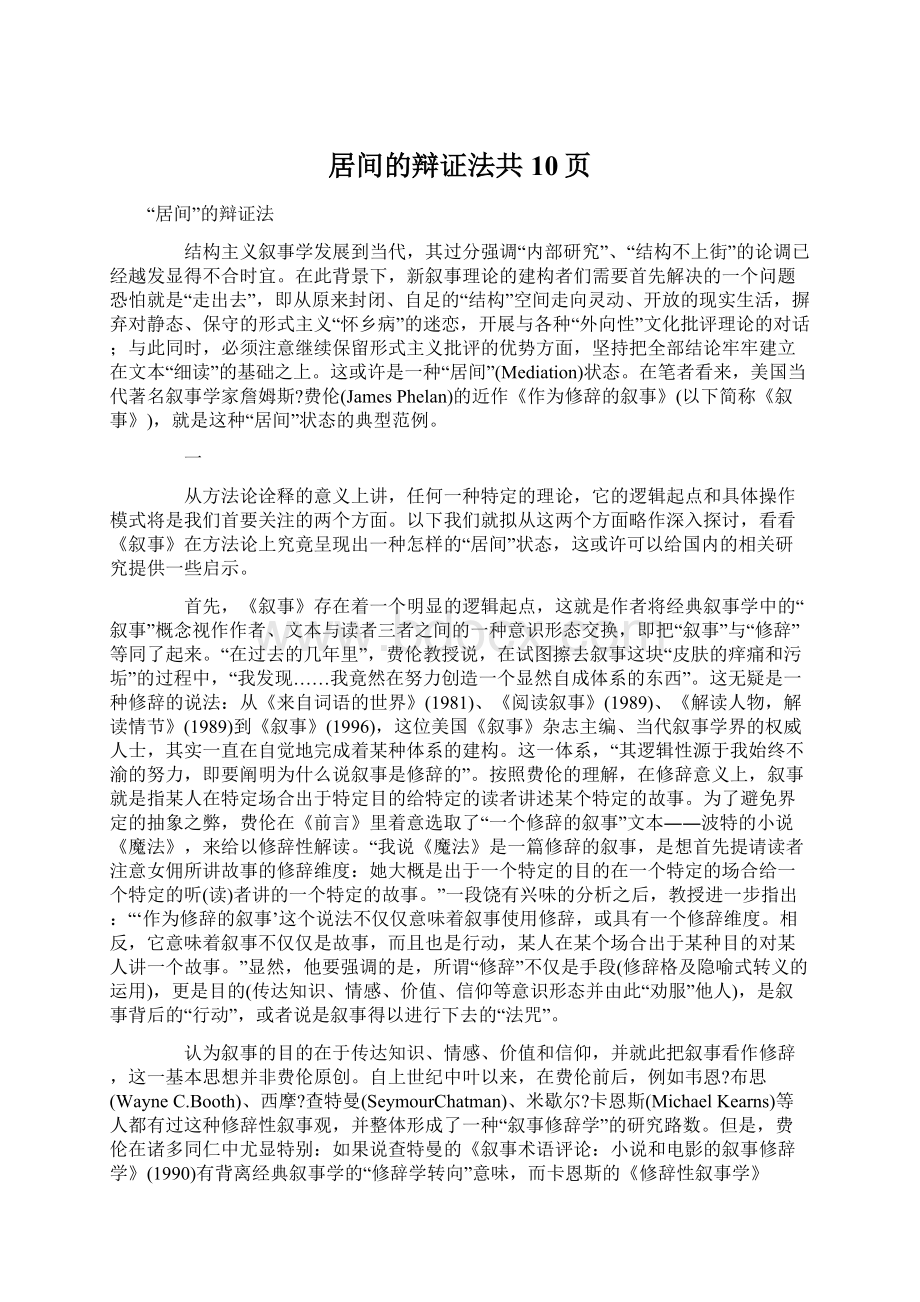
居间的辩证法共10页
“居间”的辩证法
结构主义叙事学发展到当代,其过分强调“内部研究”、“结构不上街”的论调已经越发显得不合时宜。
在此背景下,新叙事理论的建构者们需要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恐怕就是“走出去”,即从原来封闭、自足的“结构”空间走向灵动、开放的现实生活,摒弃对静态、保守的形式主义“怀乡病”的迷恋,开展与各种“外向性”文化批评理论的对话;与此同时,必须注意继续保留形式主义批评的优势方面,坚持把全部结论牢牢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
这或许是一种“居间”(Mediation)状态。
在笔者看来,美国当代著名叙事学家詹姆斯?
费伦(JamesPhelan)的近作《作为修辞的叙事》(以下简称《叙事》),就是这种“居间”状态的典型范例。
一
从方法论诠释的意义上讲,任何一种特定的理论,它的逻辑起点和具体操作模式将是我们首要关注的两个方面。
以下我们就拟从这两个方面略作深入探讨,看看《叙事》在方法论上究竟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居间”状态,这或许可以给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叙事》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逻辑起点,这就是作者将经典叙事学中的“叙事”概念视作作者、文本与读者三者之间的一种意识形态交换,即把“叙事”与“修辞”等同了起来。
“在过去的几年里”,费伦教授说,在试图擦去叙事这块“皮肤的痒痛和污垢”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竟然在努力创造一个显然自成体系的东西”。
这无疑是一种修辞的说法:
从《来自词语的世界》(1981)、《阅读叙事》(1989)、《解读人物,解读情节》(1989)到《叙事》(1996),这位美国《叙事》杂志主编、当代叙事学界的权威人士,其实一直在自觉地完成着某种体系的建构。
这一体系,“其逻辑性源于我始终不渝的努力,即要阐明为什么说叙事是修辞的”。
按照费伦的理解,在修辞意义上,叙事就是指某人在特定场合出于特定目的给特定的读者讲述某个特定的故事。
为了避免界定的抽象之弊,费伦在《前言》里着意选取了“一个修辞的叙事”文本――波特的小说《魔法》,来给以修辞性解读。
“我说《魔法》是一篇修辞的叙事,是想首先提请读者注意女佣所讲故事的修辞维度:
她大概是出于一个特定的目的在一个特定的场合给一个特定的听(读)者讲的一个特定的故事。
”一段饶有兴味的分析之后,教授进一步指出:
“‘作为修辞的叙事’这个说法不仅仅意味着叙事使用修辞,或具有一个修辞维度。
相反,它意味着叙事不仅仅是故事,而且也是行动,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
”显然,他要强调的是,所谓“修辞”不仅是手段(修辞格及隐喻式转义的运用),更是目的(传达知识、情感、价值、信仰等意识形态并由此“劝服”他人),是叙事背后的“行动”,或者说是叙事得以进行下去的“法咒”。
认为叙事的目的在于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并就此把叙事看作修辞,这一基本思想并非费伦原创。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在费伦前后,例如韦恩?
布思(WayneC.Booth)、西摩?
查特曼(SeymourChatman)、米歇尔?
卡恩斯(MichaelKearns)等人都有过这种修辞性叙事观,并整体形成了一种“叙事修辞学”的研究路数。
但是,费伦在诸多同仁中尤显特别:
如果说查特曼的《叙事术语评论:
小说和电影的叙事修辞学》(1990)有背离经典叙事学的“修辞学转向”意味,而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1999)又显“语境论”的空疏的话,费伦的《叙事》倒更像是布思《小说修辞学》(1961)的精神同路,那就是对叙事学阵地的坚守;与此同时,开阔的学术视野(既吸收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的思想资源,同时也注意吸纳当下文化研究各派的诸多洞见)和对“读者”与“语境”的注意(后经典叙事学首要强调的正是读者和语境),又使他能适应于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从而为叙事学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
这一独特的“居间”风格体现在叙事观上,一是对经典叙事概念作了上述基本性的修辞理解,这是共性;二则更有其具体之所指,这是个性。
“在本书中,当我谈论作为修辞的叙事时,或谈论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修辞关系时,我指的是写作和阅读这一复杂和多层面的过程,要求我们的认知、情感、欲望、希望、价值和信仰全部参与的过程。
”具体来说,叙事的“修辞”乃是对作者、文本和读者之相互作用、影响、交流关系的一个隐喻。
“修辞含有一个作者,通过叙事文本,要求读者进行多维度的(审美的、情感的、观念的、伦理的、政治的)阅读,反过来,读者试图公正对待这种多维度阅读的复杂性,然后做出反应”;在这样一种意义交换的语境中,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界限模糊,作者代理、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间交互、协同作用,构成了作为修辞的叙事内在的动力机制。
二
上述个性化的洞见很自然带来一种“反基础论的、伦理的、意识形态的和以读者为取向的修辞方法”Ⅲ(第27页):
它扩展了叙事的概念,大胆地将“读者反应”纳入到叙事本体;更为重要的是,它强调作者、文本和读者间交互、协同作用及其效应的动态进程,企图藉“作者代理一文本现象一读者反应”的系统化思路演绎出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动力学话语模式。
该话语模式的具体操作如下:
(一)在作者代理与文本现象处于一定张力之处,聆听“隐含作者”的声音
“隐含作者”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所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
费伦对“隐含作者”意义的构建,始终是在作者代理与文本现象有机联系且往往处于一定张力的地方。
在作者与文本的交接点上,“隐含作者”无疑是意义交换的“联络官”:
作为隐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形象,它一方面是“现实作者”的“第二自我”,负责叙事的组织安排并嵌入特定的价值;另一方面又不以作者的真实存在或史料为依据,而以文本为依托。
据此,“修辞阅读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构建隐含作者的意义”。
以《永别了,武器》为例,费伦把构建隐含作者的意义比喻是聆听隐含作者的“声音”。
小说中,隐含作者海明威的声音始终潜藏在叙述者腓特力的声音之后。
在我们的主人公经历与战争、与卡萨玲、与这个破坏性世界的一连串不稳定性关系的故事进程中,费伦认为,海明威同时还建构了具有细微变化但却也清晰可辨的一个声音进程。
在这一进程中,作者代理与文本现象始终保持着某种张力:
“尽管腓特力从头到尾都保持着明显可辨的同一文体,但他的声音却不然”,它始终不由言说者的主观意图所控制,文本符号总是“无意”中见证着叙述者言说的“不自觉性”,从而把意义引向另一个方向;相反,当腓特力逐渐放弃自己的价值观而采取了卡萨玲的声音特征――那也是海明威的声音特征――的时候,张力的空间才被感觉到明显缩小。
上述张力展现的是由叙述者的声音与海明威的声音之间的距离所建立起来的一种话语内部的不稳定性,这就为我们聆听隐含作者的声音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实际上,聆听隐含作者的声音也就是相信一种“作者式阅读”:
读者与作者共同认为叙事作品存在的目的就是以某种方式打动读者,于是读者接受作者的邀请,按照特定的社会规约来“默契”作者的意图、“还原”文本声音调配者也即是隐含作者全部的意识形态。
正是抓住了“隐含作者”之于作者代理与文本现象有机联系的“中介”或“整合”意义,费伦对《永别了,武器》、《名利场》、《我的老爸》等若干文本的分析才显得机智生动,极富说服力。
(二)在文本现象与读者反应错综交织之间,分离出“四维度读者”的价值
叙事作品的形式不仅是构成作品的方法,它同时也是形成作品意识形态内涵的重要部分;批评对于形式的重视,就是要在本文与文化间,找到一条意义由内向外延伸、意识形态由显而隐拓展的合法化通道。
在费伦看来,重新分离出拉比诺维茨所提的“四维度读者”的各自独立的价值,可以担当起对作品进行文化、意识形态剖析的重任。
在《永别了,武器》的解读过程中,因为秉持“以读者为取向”的阅读立场,费伦明确指出,腓特力与海明威之间声音的距离“并不是通过特殊的语言符号表示,而是通过我们对二者之间价值差异的意识得知的”。
这里,阅读意识即指处于不同阅读层次的“四维度读者”:
(1)实际的或有血有肉的读者,即社会身份、特性各异的你、我、他;
(2)隐含的或作者的读者,即作者假设的理想读者,能重建作者意图并对故事、人物的虚构性有清醒的认识;(3)叙事读者,即叙述者为之写作的想象读者,观察着故事世界里的一切并认为这是真实的;(4)理想的叙事读者,即叙述者希望为之写作的理想读者,完全认同叙述者的全部言说。
费伦沿用并突出拉比诺维茨的“四维度读者”观,意图很明确:
自己的修辞方法需要廓清叙事策略与读者反应之间细致而错综的纽结关系;离析出多种“读者”将能够确立不同的阅读意识之于叙事分析的各自独立的价值,从而更深一层地说明叙事是通过修辞所进行的一种“交换”行为。
依照费伦的初衷,批评工作即阅读一部叙事作品从而揭示隐含的意识形态内涵,至少需要批评主体同时在两个甚至多个“读者”的立场上多视角地展开,因为我们只要翻开书页,便有两种或多种阅读意识在脑海里同时存在。
当我们站在“叙事读者”的立场上时,我们进入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世界;当我们站在“作者的读者”立场上时,我们进入的是由语言构成的、具有多声部特征的社会群体;“作者的读者”对“同故事叙述”的价值观念进行判断,而“作者的读者”之价值观念的评判者,则是“实际的或有血有肉的读者”……比如读洛里?
穆尔的《如何》。
修辞阅读不仅发现了叙述者关于其读者的假设(叙事读者)与作者关于其读者的假设(作者的读者)之间的距离,同时还推导出有着个体差异的不同的实际读者对第二人称叙述“你”的复杂定位做出的不同反应;此外,对于先前略去的“理想的叙事读者”维度,费伦认为它同“叙事读者”也有明显的不同,需要将二者分离开来:
因为在第二人称叙述中,“叙事读者”有时与“你”(理想的叙事读者)等同,有时又会从旁边观察“你”,在情感、伦理和价值等层面与“你”保持一定的距离。
借助于分离“四维度读者”各自独立的意义价值,《叙事》对文本现象与读者反应错综交织之间所隐含的各种意识形态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揭示,条理清晰。
(三)在作者代理、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交互协同作用之际,突出本方法“以文本中心”的动力学特质
在费伦的方法论中,对“隐含作者”意义的建构和对“四维度读者”价值的分析服膺于一个更大的原则:
系统化的互动性,也就是对作者、文本和读者间交互、协同作用及其效应的动态进程的强调。
“活动、力和经验是修辞理论家的重要术语。
”
三
进一步的探究可以发现,《叙事》在突出理论自身的动力学特点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作者一种“文本中心主义”的情结。
回到引言所提到的“居间”。
引入此概念代表了笔者对费伦乃至整个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理解:
(1)在具体方法的层面上,“后结构”的新叙事理论建构者们基本上都能做到“兼收并蓄”,至少是对新语境下出现的新方法采取宽容的姿态,并力图在不同层次(社会的、政治的、语言的、空间的、心理学的……)间建立联系――《叙事》也有如此之特点,是谓“居间”;
(2)在精神立场的层面上,“后学家”们常常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在“经典”和“后经典”之间游移、滑动的“骑墙”特点,既面对着种种“后理论”的巨大诱惑,同时又割舍不掉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形式主义情结――很难说费伦不是这样,是亦谓“居问”。
然而我们说,从来就没有绝对不偏不倚的中间派,作为一种风格的“居间”在精神的归宿上,最后必然要倒向一边。
从《叙事》透露的信息来看,费伦最后倒向的是布思,而不是查特曼或卡恩斯:
(1)作者与文本的扭结点――“隐含作者”是内在于文本的。
费伦在书中采纳了布思“隐含作者”的概念及其基本内涵,认为作者意图之于文本意义的重要性仍然是第一位的;同时,“作者意图”不是指外在于文本的现实作者的意图,而是以文本为依托、内在于文本的隐含作者的意图。
在另一个地方,费伦不无诙谐地把现实作者和隐含作者比喻成“土豆”和“薯条”的关系,以此来重申布思所强调的隐含作者与现实作者的区别原则,并捍卫了文本中心的立场。
(2)“四维度读者”的反应,是以文本的修辞设置为潜在原因的。
在分列的“四维度读者”中,除了实际的或有血有肉的读者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