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分析语言学模式的兴衰.docx
《音乐分析语言学模式的兴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音乐分析语言学模式的兴衰.docx(3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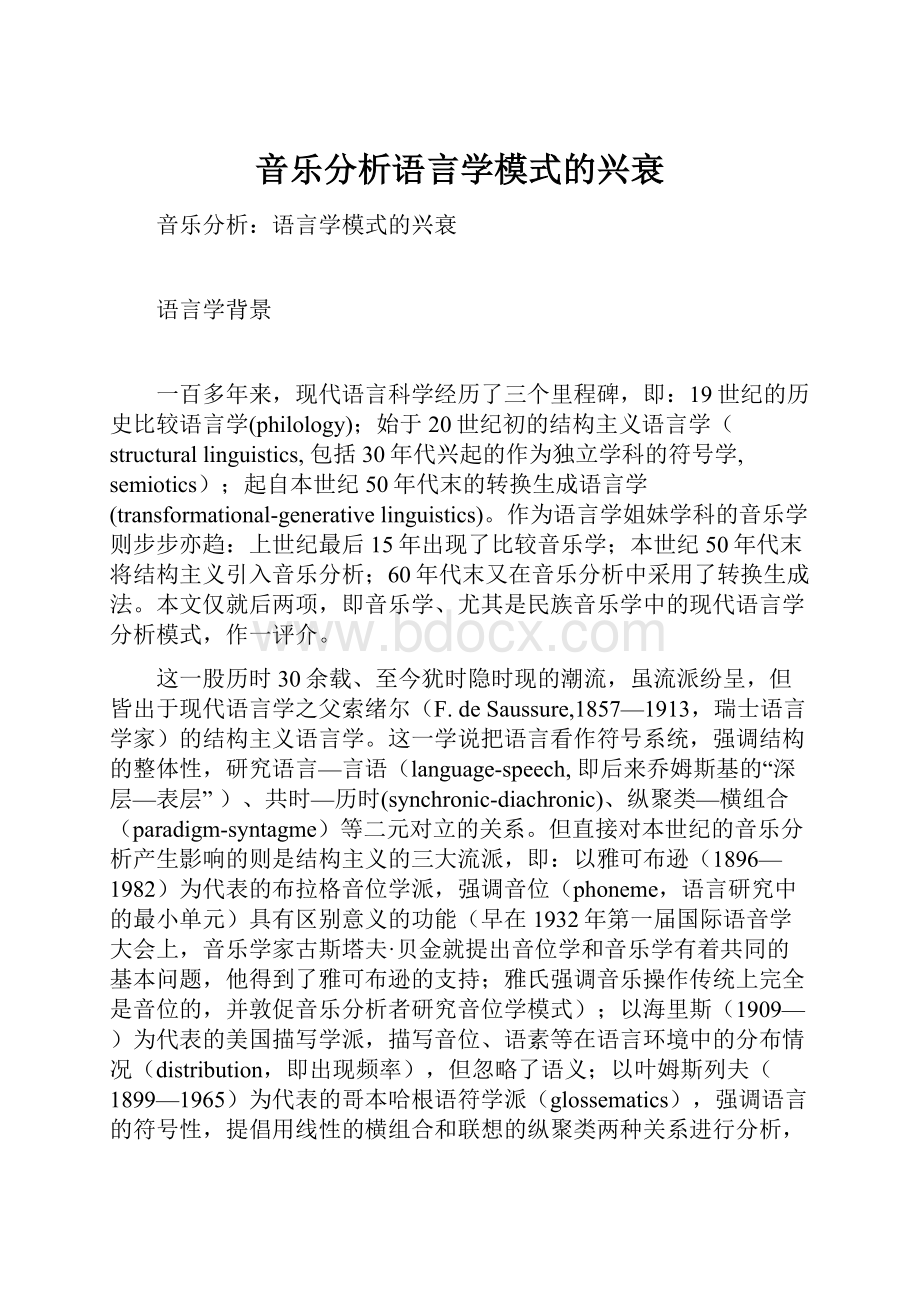
音乐分析语言学模式的兴衰
音乐分析:
语言学模式的兴衰
语言学背景
一百多年来,现代语言科学经历了三个里程碑,即:
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philology);始于20世纪初的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linguistics, 包括30年代兴起的作为独立学科的符号学,semiotics);起自本世纪50年代末的转换生成语言学(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linguistics)。
作为语言学姐妹学科的音乐学则步步亦趋:
上世纪最后15年出现了比较音乐学;本世纪50年代末将结构主义引入音乐分析;60年代末又在音乐分析中采用了转换生成法。
本文仅就后两项,即音乐学、尤其是民族音乐学中的现代语言学分析模式,作一评介。
这一股历时30余载、至今犹时隐时现的潮流,虽流派纷呈,但皆出于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deSaussure,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这一学说把语言看作符号系统,强调结构的整体性,研究语言—言语(language-speech, 即后来乔姆斯基的“深层—表层” )、共时—历时(synchronic-diachronic)、纵聚类—横组合(paradigm-syntagme)等二元对立的关系。
但直接对本世纪的音乐分析产生影响的则是结构主义的三大流派,即:
以雅可布逊(1896—1982)为代表的布拉格音位学派,强调音位(phoneme,语言研究中的最小单元)具有区别意义的功能(早在1932年第一届国际语音学大会上,音乐学家古斯塔夫·贝金就提出音位学和音乐学有着共同的基本问题,他得到了雅可布逊的支持;雅氏强调音乐操作传统上完全是音位的,并敦促音乐分析者研究音位学模式);以海里斯(1909—)为代表的美国描写学派,描写音位、语素等在语言环境中的分布情况(distribution,即出现频率),但忽略了语义;以叶姆斯列夫(1899—1965)为代表的哥本哈根语符学派(glossematics),强调语言的符号性,提倡用线性的横组合和联想的纵聚类两种关系进行分析,同时排斥语义,也主张分布主义的分析法。
可以说,描写分布主义影响最大,有时就是结构主义的代称。
音乐分析可用结构主义方法,是因为音乐也是一种语言,可以从语言学、音位学、语法这三方面进行形式结构的分析;还因为音乐关注各种乐思之间的相互关系(横组合的分布),而同时性和再现则可将各种乐思直接并置起来(纵聚类的音位对立—区别性特征)。
同结构主义不可分割的是符号学。
符号学虽由索绪尔提出,但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则是由美国学者莫里斯(1938)所创。
现代符号学尤指对符号体系的分析:
不仅是视觉形象和词语,也包括非语言的声音、姿势、行为、服饰、物品以及构成交际的所有其他类型的符号,即含有信息的代码。
音乐也属于社会符号系统的范畴。
用符号学分析音乐意在严格的科学客观性。
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音乐分析往往简化各种非语言因素(如音乐的社会联系)、而突出音乐的自然语言性。
具体操作有两个步骤:
先将音乐结构分割成不能再分的形式单元(符号),此谓“切分”(segmentation),然后按相互关系检验这些单元,即以寻求共性为目标的“置换” 、“归类” ,总称为“分布” (distribution)。
符号本身无意义,只有按它们在构成音乐结构的关系网上的位置(音位)才有意义。
这些符号出现在时间进程中,形成音乐语法。
音乐符号学直到70年代初才在法语国家真正形成独立的学科,且至今不衰。
除了结构主义三大学派,对音乐分析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所运用的结构语言学模式(1963)以及描写学派海里斯的弟子乔姆斯基所创立的转换生成语言学(1957、1965)。
前者仿照雅可布逊的音位学,将各种神话变体收集起来,并找出其中的基本成份,即神话素(音位),然后建立起它们深层的共同原型。
他模仿音乐总谱多声部的形式而对具体神话的列表分析尤为音乐分析所仿效。
后者则向结构语言学—分布主义提出挑战,而建立了深层—表层的概念、以及深层通过转换法则生成表层的程序;60年代中期又引入了语义学。
在音乐分析中,一般表现为骨架旋律(深层)通过音乐语法转换生成出旋律的即兴形式或各种变体(表层)。
如同乔氏的转换过程体现了人类学习语言的能力,旋律的转换则显示了人类对音乐的认知—创造过程。
此外,最令音乐分析者乐道的是齐氏的树形图分析程序。
下面拟以年代为框架,详述音乐的语言学分析模式——分布主义,转换生成法,符号学——所经历的互有重迭的三个阶段。
50—60年代:
兴起
较早系统地提出结构主义音乐分析方法、从而推动了这一潮流的是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
他在1958年以布拉格学派的音位学程序为模式,陈述音乐切分成份(musicalsegment,或称音段)的分布。
即从一音乐实体出发,区分出一些有意义的特征,即称作“音位”的最小单元,然后在整体结构中重新分布这些区别性的因素。
如分析旋律和节奏,从最小单元起直至循环复现的序列(即语素,morpheme),并注意音位变化、语素变化,最后离析出乐句和段落。
内特尔把在这些层面中重新安排材料看作是使音乐分析客观化的手段,从而将“调性” 与“和声” 这类西方概念的主观判断降低到最小程度。
内特尔这一简短建议首先得到了语言学家布赖特(1963)和留威(1966)的响应。
布赖特论及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三大范畴,他指出:
“音乐如同语言那样表达,音乐表演如同语言学信息,所包含的东西不止是每个声音的物理特性。
” “语言与音乐之间的两大类联系是在它们在歌唱中的互相影响以及它们结构的类似。
”他的这些说法显然多是从语义学出发的,而“结构的类似”则是指音乐的语法性。
关于音位学对乐音的直接影响,即音位在音乐中的反映,他以印度南部古典音乐中泰卢固人的Padam歌曲为例,指出音符时值长短是与歌词音节长短相对应的。
60年代在音乐结构主义分析方面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是比利时语言学家 留威(NicolasRuwet)。
他基本上遵循美国描写学派海里斯的“分类的分布主义”(taxonomicdistributionalism),强调基于重复单元的切分法,即在诸如动机和乐句这类结构单元中明确地建立起它们的形式关系。
他所提倡的程序如下:
将音乐流分割成可区分的单元,并将这些切分成份一一重写出来、以分离出结构(尤其是重复)中的类似形式,并按同其他切分成份的关系(联系、补充或排斥)分布组合,最终用字母和数字重述这一音乐流。
如分析一首中世纪吟唱诗人的歌曲,可这样操作(1972):
直接先从乐谱上切分出“层次I”(用B表示重复成份,X、Y表示不重复成份):
X(小节1-4)+B(小节5-8)+Y(小节9-28)+B(小节29-32)
为了按字母顺序排列,又鉴于Y小节数过多,故将X改写为A,Y改写为C+D+E+F+G,于是“层次I”变为:
A+B+C+D+E+F+G+B
再按乐谱中的音型异同对这一中间层次进一步切分,产生“层次II”——最低的层次——之中“可区分的最小单元(音位)” :
A+x+a B=y+b C=z+a D=w+b E=v+a’’ F=?
G=z’+a’=C’
根据“对等”原则,(A+B)、(C+D)和(C’+B)这三对切分成份可看作同一结构的不同呈示,属“对等类”:
x y
{ }a { }b
z w
即x与z、y与w按分布主义的原则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至于(E+F)这一对,E(即v+a’’)类似于上图中{xz}a,F在音型外表上也象B或D。
由此将“层次I”聚合重述成最高一个层次——“层次0” :
(1)+
(1)+(1’)+
(1)或
(1)+
(1)+
(1)+
(1)或
(1)+
(1)+
(2)+
(1)
此外,留威在分析单声部歌曲中还运用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俄狄甫斯神话图表的模式,也以图表展示了音乐分析中相应的纵聚类,即把相关的序列尽可能一一按纵列形式写出,从左向右、从上到下都能读出意义来,这样,结构特点一目了然。
早在60年代初,列维—斯特劳斯分析神话的图表就被引入了音乐分析。
突出者如科恩1962年对斯特拉文斯基《管乐器交响曲》总谱的分析,采用了纵聚类—横组合的图式。
他从总谱中切分出有区别性特征的片断(切分段),将它们当作列维—斯特劳斯式的“提示句” ,然后给每一断标上大写字母。
由于斯氏的节奏和旋律所赖以进行的背景(和声、声区、音色)一般都比较稳定,故分析时大多只须在声区里写出基本和弦的音高、并注明乐器即可,很少需引用主题轮廓线的(例外者仅有下面谱例中的B段)。
(谱例一:
切分段一;切分段二)
科恩又将代表每一片断的字母单独列表,其中X和Y代表两个不同、但又分别类似其他片断的过渡段。
垂直地逐栏看,表现出不同结构层次的连接和大致的表层音乐进行,相当于神话分析图里的横组合;水平地看,则相应于神话图表中的一个个纵栏,即同一类片断的纵聚类一深层结构。
留威1962年分析德彪西音乐时所用的也是上述方式。
追随留威分布主义程序的还有阿罗姆(1969),他分析的是非西方的音乐,所离析出的音乐特性的分布和对置更多。
图一:
将谱例一中的字母列表
[A] A A
[D] D D
[C] …… ……
[B] B B B
[E] E(E)E(E)EX
[F]
切分段一 切分段二
自1967年以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逐渐对音乐分析产生了巨大影响。
早期重要的有布瓦莱(1967)对墨西歌东部特佩瓦印地安人一种仪式歌曲—思想歌(thought-song)的研究,他将无词的歌曲动机当作转换生成语法中的元素,而且每一音高序列都有相应的内含语义信息,如同口语中的语言代码。
他的转换语法是要表明旋律序列、节奏序列如何表达语义信息。
他的结论得到了当地人的赞同。
可是布瓦莱没有说明转换语法是否适用于音符不具特定词义的音乐,因而特佩瓦思想歌只是音乐用作语言代码的极端例子。
另一种转换生成法见于萨丕尔(1969)对西非迪奥拉族福格尼人葬礼歌语法的研究。
在分析中,他用了主位和客位两种对立的视角,即用转换记谱法、结合当地歌曲结构的用语。
他用乐句结构规则来表达所有葬礼歌所共有的特征,用转换规则表达所有可能的变体赖以生成的方法。
西方传统的记谱法是“规定性的”(prescriptive),而记录非西方的音乐则用“描述性的”(descriptive)方法,即需要增加西方音乐中所没有的表现音乐事项和细节的符号。
这一区别可比作语言学里的语音学和音位学的区别。
语音学涉及实际声音(话语),音位学将这些声音组织成一种体系、并带有一定数量的区别性单位(文字)(语音学—音位学[phonetics-phonemics]的区别出自50年代布龙菲尔德的描写语言学,60年代又由这一学派的另一代表K.L.派克以“客位—主位”[语音学—音位学的缩略形式,etic-emic]引入人类学)。
描述性的音乐记谱(语音式)标出所有乐音及所有区别;规定性记谱(音位式)则将任意的或可预料的变体组合起来,以列出一条列有区别意义的单位(如音高、音长等)。
同语言学的发展方向相反,民族音乐学已从音位或记谱(主位)转向语音式记谱(客位)。
这也许是因为,“规定”是文化“局内人”的范畴,而从事民族音乐学的主要是“局外人” 。
70年代:
高潮
这一时期,分布主义、转换生成法和符号学并存。
最有影响的人物是跨越这三个领域的纳蒂埃(J.J.Nattiez)以及将转换生成语法引入音乐人类学的布莱金。
除了列维—斯特劳斯(1971)对拉威尔《波列罗舞曲》著名的结构主义分析外,音乐结构主义的其他著述者主要是纳蒂埃(1972)和阿施(1972)。
纳氏的讨论是纲领性的,强调结构主义的纵聚类法是音乐符号学发展的逻辑模式。
他主要关心方法论,声称民族音乐学若采用“发现程序”(discoveryprocedure,分布主义术语,旨在建立起基本的范畴、单位和关系以充分描写话语的语法结构)、从而将音乐实体转变成音乐语法,那未该学科的科学地位将会增强。
阿施开始时声称人类学方法的必要性,但仅以单调的规则列举了加拿大斯拉维印地安人各种击鼓舞曲的音响结构。
继承60年代末的转换生成法的有:
李多夫(1972)研究印尼的一种排锣(Kulintang),尝试以纯数学的写作程序对其进行旋律生成的描述,他的转换是一维的、纯形式的(数理语言学),目标不专门在民族音乐学上,而是在音乐理论上。
切诺韦思和比(1971)展示出使新几内亚音乐语法具体化的三种模式:
音乐流程图、公式与几何模式。
他们从派克的描写语言学程序出发,又以生成法则重新分析。
这一程序目的在于让外国人以一给定的音乐体系作曲、并帮助民族音乐学学者预料该体系将产生的所有语法正确的旋律。
上述转换方式不象转换语言学那样从理论上演绎音乐的本质或最佳分析方法。
真正从这一理论问题出发的论文为数不多,仅有林德勃洛姆和桑德伯格(1970)以及布莱金(1970,1971)。
前者沿自然科学的途径,讨论了音乐理论的目标,创立了用生成法描述旋律的理论起点。
后者则最与众不同,从人类学观点出发,以南非文达人的音乐为例,讨论了乔姆斯基的“能力”(Competence,指人们无意识的语言知识或知识系统)和“运用”(Performance,指可观察到的语言行为或文化行为)、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转换等理论概念,试图说明音乐结构与社会范畴相互作用的理论实质。
他的分析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关于深层、表层以及转换生成的概念与关系,布莱金在《人具有怎样的音乐性?
》(1973)中有详尽的讨论论。
他认为已知的音乐语法规则是表层的东西,转换生成的过程即是按照这些规则深层的认知过程(包括语义和逻辑)来安排乐音,而认知过程就是转换过程。
语义能产生不同的结构原则,如文达人的儿童歌曲常由歌词(语义)确定节奏动力和旋律轮廓。
除了音乐与认知互为表层—深层外,音乐本身也可分出表层—深层。
如一首文达儿童歌曲,有两种不同旋律变体,但它们共同的深层结构却是一种“和声”进行,而且两个变体互为对方的“和声” 。
如果转换的原则相同,音乐结果在表层上也相似,它们赖以产生的基本概念模式可能不同,一个旋律的总体格局也许比其所用乐音的多寡更有意义。
如两首歌曲表层旋律所用乐音相同,但分别源于五声和七声音阶。
布氏第三种深层—表关系表现在音乐创造(music-making)的过程中。
他认为音乐创造的过程并非总是在音乐的表层旋律上,许多生成因素不在音乐上。
如文达人的音乐创造——生成表层音乐,取决于对基本概念、模式的使用与转换,而这些概念与模式是作为个人成熟过程的一个部分而无意识地获得的。
深层结构反映了在社会环境里无意识创造音乐的过程。
这同梅里亚姆(1964)的认知—行为—乐音的模式十分相似。
布莱金认为分析音乐本质上就是描绘成套的不同的创造行为:
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音乐的行为导致了声音的产生。
布莱金在微观分析中引入宏观分析,但却没有建立起一套具体的转换生成规则。
70年代中期以后,转换生成法还见之于纳蒂埃(1975)、库帕(1977)、凯勒(1977)、贝克尔(1979)等人的分析中。
纳蒂埃创造了多种表现模式,其中包括乔姆斯基的树形图(分析布拉姆斯《间奏曲》Op119,no.3),
(谱例二:
上:
分析一;下:
分析二)
以及结合分布主义的节奏因素分类表(分析德彪西《绪任克斯》)和旋律因素分布表(分析瓦雷兹《积分》)。
库帕用简单清晰的语法生成了大量正确的印度拉伽音阶。
他在生成中用了不完整的树形图:
谱例二
凯勒则用树形图研究西方调性音乐。
他的TC(主调结束)=NP,DP(属调延长)=VP,树形图完成时,在终端写出表层的音乐。
(这方面的研究直到80年代还在继续[莱达尔,1983]。
)
贝克尔总结了爪哇皮影戏中为打斗伴奏的佳美兰音乐——其中有八首代表性乐曲——怎样从深层的骨架旋律(balunga)向表层生成的语法。
70年代的第三潮流是音乐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崛起;为了区别于60年代留威分布主义中的符号学,70年代的符号学有时称作“第二代符号学” 。
首先是布瓦莱(1971)建立了民族音乐的符号学概论。
他以莫里斯塑造的符号交际的本质(1938)为基础,讨论了莫氏学说的三个分支——符号结构学(syntactics,研究符号本身结构)、语义学(semantics,研究符号所指事物的意义)和语用学(pragmatics,研究怎样用符号去交际)——以及从这三种方向进行音乐交际的可能性。
这一视角的目标是在民族音乐学中产生“对音乐行为的各种认知维度更深刻的洞察。
”布瓦莱对音乐符号学的研究一直延续到80年代(1982)。
但“第二代符号学”的主要代表是领导蒙利特尔大学音乐符号学研究小组的纳蒂埃。
当时符号学研究中关于分析的方向有争论:
是从大单元起、在小单元上完成;还是从小单元切分、按共性而逐渐构成大的形式单元。
留威了来个折衷——从中间层次开始,而纳莱埃这一派则从小单元出发。
他的主要贡献在于雄心勃勃地综合了源于现代语言学模式的音乐分析技巧,发表了那本著名的《音乐符号学基础》(1975)。
他的思想主要来源于留威等人的符号学—分布主义、音乐学和认识论以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
他那本书中几种分析的音乐学的起点是留威60年代的观念(纳氏称为“留威I” );而1975年时的留威已“抛弃了音乐学的独创性、回到了乔姆斯基的正统观念(纳氏称为‘留威II’),” 这一转变恰恰是受了纳氏那本书的影响;此外留威(1975)按照语用学的灵活性进一步发展了符号学。
运用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分析的,还有赫恩顿(1974)所提出的一种可用于任何音乐的分析法,并以马耳他音乐中一例加以检验。
1972年召开于多伦多的民族音乐学年会是语言学分析运动的顶峰。
会上宣读了一大批有关这一题目的论文,但当时大多未正式发表。
70年代中期之后,这一潮流逐渐衰减下去。
回顾这一运动,观其参加者之众、涉及学科之广,在音乐学术史上是空前的。
如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学者卷入进来:
普通音乐学(纳蒂埃、鲍尔斯),语言学(布赖特、留威、库珀),人类学倾向的民族音乐学(布瓦莱、布莱金、赫恩顿),音乐学倾向的民族音乐学(切诺韦思和比),音乐理论(李多夫)以及人类学(斯普林格、德宾)。
高潮后的反思
正是在1972年那次大会上,布莱金一个人批评了正处于顶峰的音乐结构主义,他认为结构分析强调了逻辑单元与其文化脉络的分离。
他说:
“音乐远远不止是一种文化游戏或心灵无意识活动的表达,若不注意音乐的社会维度,对乐音最严格的结构分析就不可能恰当。
任何音乐体系的规则都是从区分音乐与非音乐开始的,规则似乎是武断的。
但没有同感,就不会有意义,在这一点上规则也是社会的。
因为社会行为也服从于规则,可见音乐—社会的交际体系的规则之间可能有关系。
我看这正是民族音乐学作为独立学科而存在的基本的正当理由” 。
后来还有两位最重要的批评者,即费尔德(1974)和鲍尔斯(1980)。
费尔德指出,如此运用语言学的符号和术语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空壳,不是在形成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而是在运用语言学的标记符号和术语的形式。
这些分析充满了树形图、短语标记、派生规则、二元对立以及诸如此类的,而且多不涉及基本理论层次上的问题(除布莱金、林德勃洛姆和桑德伯格等以外)。
这些语言学模式并没有使民族音乐学科学化,而是在玩抽象游戏。
事实是,人们创造音乐,为其他人创造、也和其他人一起创造,民族音乐学理论应设法说明这样的事实(梅里亚姆,1964)。
因此,局限于声音结构的语言学模式是否能恰当地解释民族音乐学的事实?
20世纪人类学表明了,正是环境(context)是民族志的方法和描述中唯一最关键的认识论上的可变项。
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显然亦是如此。
费尔德赞同布莱金和梅里亚姆的观点,最有力的民族音乐学理论所需要的是:
能够从形式上说明声音结构与其创造者—聆听者的环境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正如布莱金所言(1970):
“基本的问题是描述生成一个作曲者或社会所产生的声音型式的所有因素;解释作为文化中人类经验的符号和象征的音乐,将音乐形式同其社会内容、文化内容联系起来。
”
民族音乐学向语言学学习的,应是科学理论的本质—演绎法同资料及原理的关系。
使民族音乐学科学化,即是建立一套音乐技术理论的问题,通过这一理论可以演绎、分析文化中的音乐。
这里的“分析”是指离析出某个社会可以接受的、适合其文化的音乐以及这种音乐的文化逻辑。
费尔德的批评反映了民族音乐学的分裂:
一派认为代码的自律结构构成了对一种现象的解释,另一派认为环境与代码的相互作用是需要解释的。
此即音乐学倾向的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倾向的民族音乐学的分裂。
对费尔德的意见——音乐分析要考虑其文化环境,鲍尔斯稍加纠正。
他认为费尔德对“在文化之外考虑乐音”有强烈的理论偏见,这一偏见来自梅里亚姆(1964)和布莱金(1973)。
如同语言,音乐没有创造它的人,当然无法存在。
但如同语言的某些使用,“有些音乐有时以自律的方式似乎解释起来更有效。
“什么时候、在什么程度上,音乐可以在社会、文化背景之外解释,部分地取决于研究目的,部分地取决于该音乐在文化中的作用。
有些音乐离开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可能更容易,如西方和印度的艺术音乐是两个突出的例子,而另一些音乐与文化、甚至物质背景联系紧密,以致在背景外无法理解。
因此民族音乐学这不应该仅从原则上贬低抽象的音乐分析。
社会语言学家也并不抛弃抽象的语言学分析和抽象模式,他们仅仅将这些东西结合到更广泛的领域中去。
文化是象征,语言是钥匙,但这把钥匙对某些语言和音乐更有效。
鲍尔斯认为,在有些文化里,音乐的结构方法类似语言结构(如印度古典音乐);在另一些文化里又相当不同,更多受制于舞蹈、仪式和情绪。
正如萨克斯所言,音乐可分为源之于词(Logogenic)和源之于情(Pathogenic)这样两种。
鲍尔斯在其长文的最后部分回顾了历史,认为语言学模式用于音乐只是利用语言—音乐类比的学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
这一历史包括德国文艺复兴和巴罗克时代的学者对中世纪初期音乐和修辞的关系的研究。
在欧洲及其他一些文化中,音乐家和理论家长期用语言作为音乐解释和作曲教学的模式。
鲍尔斯的结论远远超出了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
“慎重地用于音乐分析的语言模式能够基本上、而不是肤浅地帮助音乐诸学科,就像过去一千多年它们不止一次地所做的那样。
”对于这一历史,还可以加上历史音乐学传统中大量论述声乐作品里词曲关系的文论。
如费尔德、鲍尔斯等人,内特尔(1983)也认为,不加批判地任意将语言学方法用于音乐分析常常会失败;音乐与语言之间的类似是重要的,但二者在本质上和许多方面都不同,运用分析体系时须有所改变,如固守语言学、模拟其严格性,则会掩盖音乐学的需要。
可采用语言学中有用的,如音位和语素、转换和生成、主位和客位,而去其无用的,这样似乎比坚持类比更好。
尤其是音乐的专门知识及其基础理论能够减轻对语言学的过分热情。
鲍尔斯分析了对语言学模式过分热情的人往往有三方面的不足:
一是似乎不熟悉分析的音乐学;二是比较的基础不足(民族音乐学的比较很少是多文化的,往往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种音乐同一种模式、或同研究者本人的音乐的双边比较,类似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而现代语言学里则是语族中多种语言的比较,不是同借来的模式对比、而是相互比较);三是对音乐分析史上早已肯定的语言学模式的悠久传统不感兴趣。
内特尔在评介了费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