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蛮和茅绥民族志里的他者.docx
《荆蛮和茅绥民族志里的他者.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荆蛮和茅绥民族志里的他者.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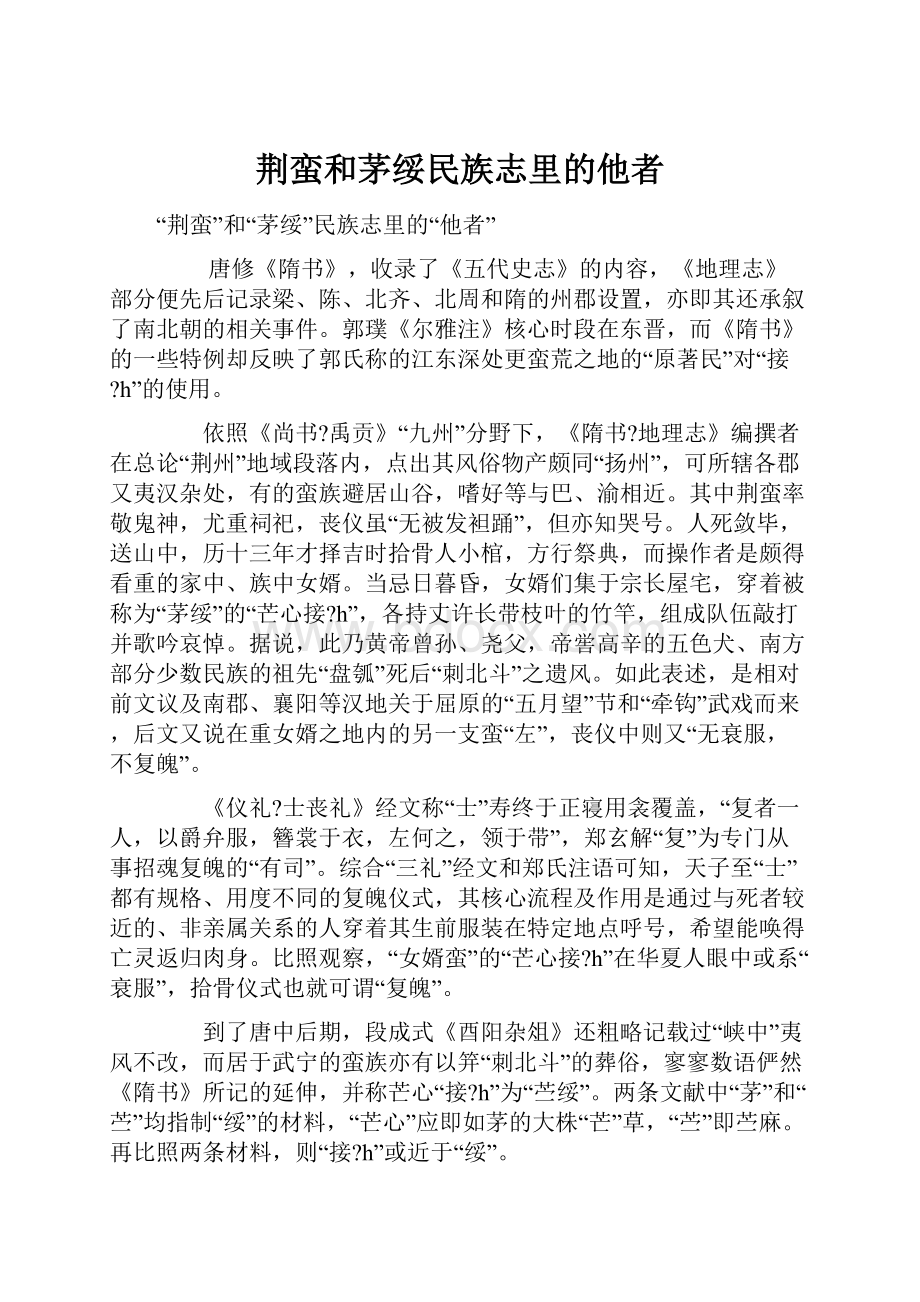
荆蛮和茅绥民族志里的他者
“荆蛮”和“茅绥”民族志里的“他者”
唐修《隋书》,收录了《五代史志》的内容,《地理志》部分便先后记录梁、陈、北齐、北周和隋的州郡设置,亦即其还承叙了南北朝的相关事件。
郭璞《尔雅注》核心时段在东晋,而《隋书》的一些特例却反映了郭氏称的江东深处更蛮荒之地的“原著民”对“接?
h”的使用。
依照《尚书?
禹贡》“九州”分野下,《隋书?
地理志》编撰者在总论“荆州”地域段落内,点出其风俗物产颇同“扬州”,可所辖各郡又夷汉杂处,有的蛮族避居山谷,嗜好等与巴、渝相近。
其中荆蛮率敬鬼神,尤重祠祀,丧仪虽“无被发袒踊”,但亦知哭号。
人死敛毕,送山中,历十三年才择吉时拾骨人小棺,方行祭典,而操作者是颇得看重的家中、族中女婿。
当忌日暮昏,女婿们集于宗长屋宅,穿着被称为“茅绥”的“芒心接?
h”,各持丈许长带枝叶的竹竿,组成队伍敲打并歌吟哀悼。
据说,此乃黄帝曾孙、尧父,帝喾高辛的五色犬、南方部分少数民族的祖先“盘瓠”死后“刺北斗”之遗风。
如此表述,是相对前文议及南郡、襄阳等汉地关于屈原的“五月望”节和“牵钩”武戏而来,后文又说在重女婿之地内的另一支蛮“左”,丧仪中则又“无衰服,不复魄”。
《仪礼?
士丧礼》经文称“士”寿终于正寝用衾覆盖,“复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领于带”,郑玄解“复”为专门从事招魂复魄的“有司”。
综合“三礼”经文和郑氏注语可知,天子至“士”都有规格、用度不同的复魄仪式,其核心流程及作用是通过与死者较近的、非亲属关系的人穿着其生前服装在特定地点呼号,希望能唤得亡灵返归肉身。
比照观察,“女婿蛮”的“芒心接?
h”在华夏人眼中或系“衰服”,拾骨仪式也就可谓“复魄”。
到了唐中后期,段成式《酉阳杂俎》还粗略记载过“峡中”夷风不改,而居于武宁的蛮族亦有以笄“刺北斗”的葬俗,寥寥数语俨然《隋书》所记的延伸,并称芒心“接?
h”为“苎绥”。
两条文献中“茅”和“苎”均指制“绥”的材料,“芒心”应即如茅的大株“芒”草,“苎”即苎麻。
再比照两条材料,则“接?
h”或近于“绥”。
“绥”可指“车中靶”,《礼记》称人君上马驭车时“取贰绥”,唐孔颖达释为正副两条“登车索”。
还可指一种旌旗,所谓“有虞氏之,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郑玄对《礼记?
明堂位》这句话的理解认为“绥”应当写为“?
q”,读如“冠蕤”的“蕤”。
《周礼?
天官》曾记“夏采”司职天子大丧时,以生前冕服“复”于始祖之庙,“乘车建绥”复于四郊。
综合郑注、贾疏,“建绥”乃指制造、树立画有日月、带?
q去旒的“大常”旗。
矮、旒用牛尾、羽毛制作,缀在?
H上,“复”时为了与生前区别,并仿效上古有虞氏仅有矮的旗帜,便去旒。
《说文》释“?
q”为“系冠缨垂者”,“蕤”也可与“垂”字联系起来,指“草木华垂貌”,段玉裁认为还能引申指物下垂的状态,冠蕤就是结系冠帽后下垂的缨带。
那么,回到“茅绥”上,或许有人要议论:
这“绥”、“?
q”,或“接?
h”,不还是帽子?
若再了解一点前文说的“爵弁”能以冠帽名代称整套服装的话,这样的推理似乎可以成立,而且“礼经”还记载吊丧用素布模仿爵弁,加麻绳缚发作“经弁服”。
于是,很显然,此种猜测还将认同:
回归到唐代《隋书》的编写者那儿,结合“复魄”行为,即要证明生前蛮人所穿的衣服也可叫做“接?
h”。
的确,认同“帽”的存在,仍无法否认“接?
h”是衣服,甚至无法否认“女婿蛮”就是着植物纤维等做的、包括所谓“帽子”的整套“丧衣”举行祭奠,而其下垂缨带即《仪礼?
丧服》经传中的“冠绳缨”。
现代有铜鼓研究者便倾向于选用“整套”丧服的讲法,并找到了可能的图证――在那面流落欧洲、珍贵非常的“开化鼓”,以及相当一部分有记载、可查见的实物鼓面主晕中均出现鹭鸟晕环,以及头顶类似长毛羽冠,身或腰下披挂氅衣及裳的羽人形象,并辅以一类划船行进的描绘。
鹭鸟与鼓的关系《诗经》和《隋书?
音乐志》均可溯及三代,并曾被奉为“鼓精”。
当然,赵宋以来,也普遍将其群集次第飞翔的情景与百官行进的有序队列联系起来。
加之一贯认为的“鹭舞”观念,古人对鹭鸟的观察早已由捕鱼的生物状况提高至拟人水平,进而升华出一套完整的伦理美学思路。
目前,研究界将最初的“万家坝”铜鼓早期类型定在商末、春秋初,断代上似乎能与经典内的文字记叙对应起来:
鹭鸟纹样主要由“石寨山型”起延续至“西盟型”,均为装饰母题之一,其核心时间跨度为战国至唐,并影响到近代。
特别是最晚近的西盟型鼓早期标本,鼓面已稳定呈三圈主晕,“饰图案化羽人纹、鹭鸟纹、小鸟纹和四瓣花纹”。
进一步看,铜鼓鹭纹在“冷水冲型”出现的秦汉时期便具备了向几何程式化的演变趋势。
不过,研究者普遍借助汉地材料、“经传”的描述进行估计,尤其在分析“羽人鹭舞”图中,将之指认成南方民族与祭祀相关的乐舞或兵舞等,并伴有“华夏中心论”倾向。
回头再看《隋书》对荆蛮的记载,我们认为:
作为全套丧服的“芒心接?
h”与铜鼓图纹的确有一定内在关联,甚至可能近似汉代起崇奉“竹王”的“僚人”部族传承而下的“贯头衣”。
他们起先活动区域主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魏晋时部分北迁入川,与川中东部、长江中游沿线的蛮族互动,进而连成一片,最终被唐初等史书编撰者所“捕获”。
可,如此的不稳定路径并不代表荆蛮、僚人等必然存在“接?
h”的称呼,仅能初步说明他们那般着装与汉地有雷同之处,比如对于鹭鸟长羽的处理、编制和服用等,进而体现出不同民族间在造物关系网上的强烈呼应。
至于晋室南迁,在此时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中介角色,山季伦身上的“白接雒”可能恰好就是其遗迹和明证。
另外,中国浩瀚史籍内还有一处关于高句丽唐初用秫韬猪发造“接?
h”的记录值得注意。
它出现干时人“雍公睿”为张楚金撰写的骈体类书《翰苑》第三十卷“蕃夷部?
高丽”条所作注语内,在解说其风俗“佩刀砺而见等威,金羽以明贵贱”时,征引了陈大德贞观十五年(641)前后写就的军事报告《高丽记》称:
该国也能造锦,紫地缬纹为上,其次有五色锦、云布锦,还造白叠布,青布也很不错,“又造鄣,日华言接簸,其毛即H猪发也”。
中国现代研究者认为,“鄣”、“日”合为一词,指类似帽子的物件。
我们觉得,“鄣日”其实指的是遮挡阳光的动作和效果,如宋玉《高唐赋》日“扬袂鄣日”。
清人说“鄣”同“障”,换言之,由于古代典籍借代与省称,令不明就里者混淆误之以为专名。
《宋书?
五行志》载,西晋惠帝元康(291-299)中,天下商、农通着“大鄣日”,史官为了点出其时曾有一目失明的赵王司马伦篡位,以及之前那些模棱两可的冥冥暗示,便借童谣,即以所谓“诗妖”式的比附唱道:
“屠苏鄣日覆两耳,当见瞎儿作天子。
”唐代编《艺文类聚》时,保存下了另一位萧梁人刘孝威的“行”,与“鄣日”更紧密关联的是这句――“插腰铜匕首,鄣日锦涂苏”。
最末两字也是个理解原意的切入点。
实际到了赵宋后的几种主要传本里,还出现了与“屠苏”混用的状况。
而被后人怀疑并非唐人李贺作的一首诗也出现过“涂苏”的身影,南宋人解这个“苏”为锦帐的“流苏”。
而早前北宋庞安时《总病论》中表述“屠苏酒”药方名称的逻辑估计同样是从流苏出发,引向当时版筑的暖阁,进而定其义为平顶的临时建筑。
不过,再仔细揣摩李时珍界说“屠苏酒”方名的办法,称苏乃鬼名,屠即杀鬼而割除病灶,尽管牵强倒也能给人启发:
以上变化,只有“苏”系中心,屹立不摇。
《说文》释“苏”为“桂荏”,即紫苏草。
“屠”在《广韵》中属平声“鱼”部,发音与“除”的“直鱼”一致,又音“徒”的“同都”切。
“涂”在平声“模”部,与“徒”同条,又音“?
”的“宅加”切。
可见,“屠”、“?
T”两字起码在北宋的发声上便有交集,也就容易出现同音异体字的混用。
参考《广韵》记录“涂”的几个意思“涂泥”、“涂饰”等,我们认为,所谓“屠苏”也可能系“涂苏”的音误,本指在建筑物上或锦帛上涂绘、织绣紫苏草一类的植物图样。
刘孝成“行”句中,“插腰”对“鄣日”,乃述宾、主谓结构,仅为句法或短语层面的问题;形容词“铜”对“锦”,“匕首”对“屠苏”,相叠后便实现了形容词或名词与不稳定短语构成复音专名组合的“造词过程。
当然,关于“苏”系“流苏”的解释也令人思索。
中古时期,“帽”的概念受“礼制”冠服问题的约束日趋模糊,而近似兜鍪的“务”和小儿、蛮夷的罩头衣才是其原型。
但,纵使“士”及之上的“贵者”服冠,贱者用巾,这都与原始的罩头巾、“帽”还保持有一定的造物相关度。
帻因在冠下,用以缚发固冠,至西汉文帝后便上下通行。
司马伦鄣日护目的,应仅指在冠等外附加苏草织成的物品云云,当然更有可能是布帛做的遮挡物件,唤做“锦屠苏”。
其状似下垂的流苏,或者就是白头顶而下的披幅,上面还绘、绣有仙草等祥瑞纹样,而与现代的“帽”是有差异的。
至于高丽,“雍”氏正史引文已谈到他们初期服用像“弁”那样的冠,即插鸟羽的“析风”。
后来恐怕也受中国影响,“帻”成为贵者首服,并尚装金银“鹿耳”,贱民却保留用“析风”。
而《高丽记》作为最后一处出现的注语,我们理解并非是在说明首服问题,却是描述他们其他的织、造技术,以及由此所制成的日常用品。
换言之,H猪毛“鄣”称为“华言接?
h”的,可能是一种特别的挡、阻器具。
当然,对“华言”的理解也可以有不同。
从现代眼光看,人们更会联想到“在中华而言”的义项,但古代史料内,确实还存在其他例证,即指虚华无实,如有花叶但无根基的言辞。
尤其是《晋书?
范宁传》中评价王弼、何晏“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一句,更可见语义上的引申方向。
若与接簸连用,恐怕谈及的乃某物设下的虚障,以之区分、隔断,类似于“蕃”等的用途,这也很符合猪毛编织品的材质属性。
如此,高丽的制作在唐中期前也成就了“接?
h”作为实物存在的最后的间接反映,再往下,它蜕变成文人遣词造句当口儿拈来炫技、逞能的虚幻“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