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小说主题意蕴的矛盾指向.docx
《论萧红小说主题意蕴的矛盾指向.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萧红小说主题意蕴的矛盾指向.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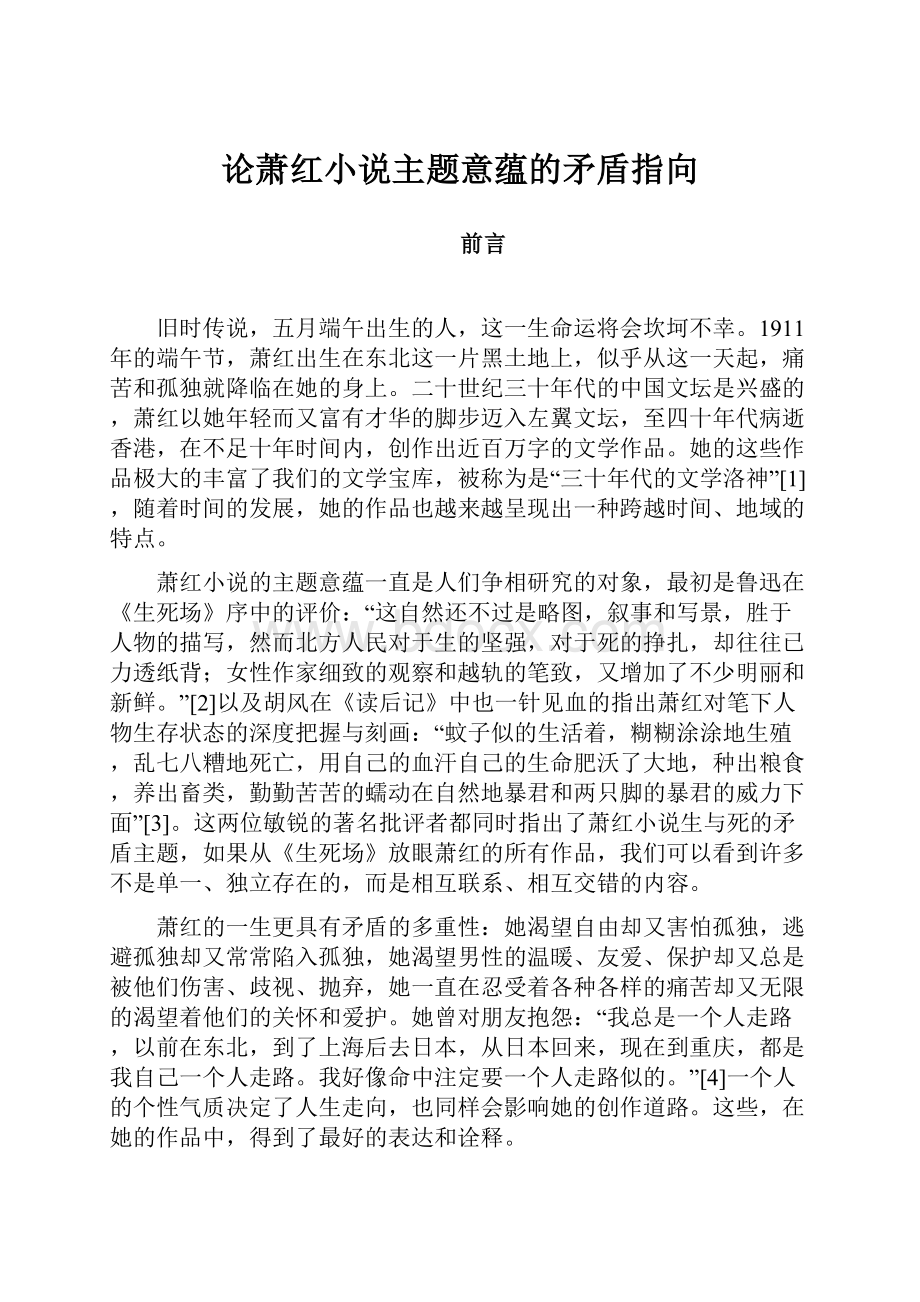
论萧红小说主题意蕴的矛盾指向
前言
旧时传说,五月端午出生的人,这一生命运将会坎坷不幸。
1911年的端午节,萧红出生在东北这一片黑土地上,似乎从这一天起,痛苦和孤独就降临在她的身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是兴盛的,萧红以她年轻而又富有才华的脚步迈入左翼文坛,至四十年代病逝香港,在不足十年时间内,创作出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
她的这些作品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文学宝库,被称为是“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1],随着时间的发展,她的作品也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跨越时间、地域的特点。
萧红小说的主题意蕴一直是人们争相研究的对象,最初是鲁迅在《生死场》序中的评价:
“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2]以及胡风在《读后记》中也一针见血的指出萧红对笔下人物生存状态的深度把握与刻画:
“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的蠕动在自然地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3]。
这两位敏锐的著名批评者都同时指出了萧红小说生与死的矛盾主题,如果从《生死场》放眼萧红的所有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是单一、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交错的内容。
萧红的一生更具有矛盾的多重性:
她渴望自由却又害怕孤独,逃避孤独却又常常陷入孤独,她渴望男性的温暖、友爱、保护却又总是被他们伤害、歧视、抛弃,她一直在忍受着各种各样的痛苦却又无限的渴望着他们的关怀和爱护。
她曾对朋友抱怨:
“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
我好像命中注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4]一个人的个性气质决定了人生走向,也同样会影响她的创作道路。
这些,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和诠释。
一、拒绝相信却又幻想爱情
萧红个人的情感是比较悲苦的。
从离家出走到被迫与未婚夫王恩甲同居并被很快抛弃,到后来萧军的用情不专、大男子主义、家庭暴力等,都让萧红痛苦着、挣扎着,直至最后的远走他乡。
再到后来端木蕻良的自私、怯懦、做事缺乏责任心以及最后的独自逃生,这些亲身经历使萧红对爱情抱着怀疑态度,但她却又像孩子一样的渴望着被爱。
在《生死场》中,萧红写了几段痛苦的爱情,那里的妇女们无法感受到爱情的魅力,她们对爱情的向往只会化成泡影。
金枝怀着对爱情的向往,被成业的歌声所陶醉,但她并没有得到爱情的抚慰。
成业对她毫无爱情可言,只是一次次的占有她,把她当做泄欲的工具,就连后来她怀孕了,也不放过她。
成业对金枝没有多余的言语,也不存在温柔的关怀。
当金枝告诉他已怀有身孕时,成业的表现是“完全不关心,他小声响起:
‘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
’”[5]一句“反正是干啦”展现出的完全是小农意识加土匪情节的占便宜和打、砸、抢心态,不在意对方的感情,也不管后果如何,只在意自己现在的所得。
这句话界定了两个人只是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
婚后不久,金枝也陷入了成业婶婶的境遇中,挨打挨骂,如同小鼠一般的怕丈夫。
在金枝生下女儿后,成业更加烦躁,每天带着怒气回家,又是吵又是闹,认为妻子和女儿拖累他,最后残忍的将仅出生一个月的小金枝摔死。
这还哪有一点的爱情可言,连人都不是,虎毒还不食子呢!
福发婶在婚前对爱情也充满了向往,但是婚后丈夫对她却冷漠了,她在情爱缺失的婚姻生活中饱受痛苦,以致让她再也不相信爱情,再也不相信男人的甜言蜜语了。
女人的地位是极低的,无论是女人的工作、生活状态,还是生育,仿佛都充满了动物性,完全不像人的状态。
在《生死场》中,萧红用了大量的笔墨来写乡村女人的生活场景以及他们无意义、动物性的生育和死亡。
在小说的一开篇,麻面婆的“忙”就被表现的极为充分,在正午“汗水如珠如豆”地洗衣服,“用泥浆浸过的手去墙角拿茅草”,烧饭,翻柴堆找羊,她就想台上的小丑,像牛,像母熊,像猪,像一捆稻草,萧红用一系列比喻深刻的刻画了麻面婆生活的非人性,工具性,受压迫和不自觉。
她的生存是动物性的,是自然地而非自觉的,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月英的丈夫在她瘫痪并丧失经济和性的价值时,以灭绝人性的方式加速了她的死亡。
赵三在王婆服毒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及时的抢救,而是直接跑到城里去买棺材,在王婆嘴角流出一些黑血发出响动时,他却担心是死尸还魂,于是用扁担狠狠地“扎实的刀一般的切在王婆的腰间”[6]……这些男人完全不把女人当成人,怎么会存在爱情和温暖呢?
像这些女人,“不仅是压迫者的奴隶,也是被压迫者的奴隶,是奴隶的奴隶。
”[7]
这多少是因为萧红在自身经历中,比其他人更加体会到爱情的不真实,从而导致了她对爱情的怀疑和拒绝。
但是,另一方面,萧红,却又像孩子一样的渴望着被爱和温暖。
童年时期,无论是生母还是继母,父亲或是祖母,都没有让她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只有祖父的慈爱关怀着小萧红,这使得萧红在不相信爱情的情况下依然渴望着,从萧军到端木蕻良,这些也可以看成是她在寻找自己的情感支撑点。
在《小城三月》中,她描写了一段非常纯粹的爱情,它讲述的是正值青春年少的女主人公翠姨,在传统道德规范的压抑下偷偷地向往和憧憬着爱情,最终无力挣脱陈规陋习忧郁而死的故事。
小说先用诗意的笔触描写了春天的景物,“原野已经绿了…河冰发了…小城里被杨花给装满了…春来了……”[8]这些似乎都预示着新的开始,似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春天,等待新的尝试。
美好的东西人人都会渴望,尤其是美好又美妙的爱情,于是“我”美丽窈窕、情窦初开的翠姨在这美好的季节开始暗恋“我”的堂哥哥了。
虽然翠姨美丽聪明、沉静端庄、会吹笛子,言谈举止都显示出淑女风范,但是由于翠姨的母亲是一个再嫁的寡妇、受人歧视,所以翠姨自己也对此感到自卑,她心里牢记着这一点。
在“我”家住的日子,她在一个比较宽松和自由的环境,接触到了“我”和堂哥哥这样的洋学生,后来办嫁妆又去了哈尔滨,所以对于男女平等并尊重女人的文化和文明有了向往,在这种情况下,她爱上了似乎能代表新的文明的“我”的堂哥哥。
在整篇文章中,翠姨爱着“我”的堂哥是一个惊天的秘密、无人知晓,连堂哥自己本人也无法把握。
这场爱情就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发生在一个女人内心的独角戏,它是一个女人内心深处对爱情所有的向往和渴望,渴望着在新的文明中被尊重,被爱护,被关心。
这也是萧红的理想追求。
翠姨从爱上堂哥到最终抑郁而终,她经历了难以言说的情感痛苦和心理折磨。
她是爱着堂哥,但是她也清楚地知道自己作为寡妇的女儿这一事实。
到临终前,在我的堂哥奉我母亲之命去看望翠姨时,唯一在家的堂妹也着急着跑去找她们的祖父,在难得的二人空间中,翠姨任然没有说出自己的感情。
她在爱情与吃人的文化规范中苦苦的折磨着自己,直至最后也没有突破。
二、否定却又怀念童年温暖
萧红的童年可以说是缺失的。
除了祖父给她以温暖,似乎其他的人都没有过。
那时候的萧红,在一个冰冷无情的家庭中过着不正常的生活,缺少温暖和爱护。
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地主家庭里萧红很不受欢迎,她从小就没有像其他孩子得到过父爱和母爱,他们对他总是十分刻薄和冷淡,这让萧红幼小的心灵受到巨大的伤害,成为她心头永远无法抹去的疤。
在散文《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中,她诉说了自己亲身的感受,“没从他身边经过,我就像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向下流着。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9]同时,祖母也很恶毒,萧红喜欢用手指头在窗纸上捅小洞玩,她就专门拿针来扎萧红的手指头。
在这个冰冷的家庭里,只有祖父比较疼爱萧红,“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10]
由于自身童年温暖的缺失体验,这对于萧红以后的心理、思维和言行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萧红的许多作品中,对于孩子在童年时期父爱母爱这一块的描写就比较苍白。
如在《生死场》中,二里半家的山羊跑丢了,他宁可让自己的儿子罗圈腿大热天冒着中暑的危险,也要把山羊找回来,他舍得孩子却舍不得一只羊。
王婆十分爱惜自己的土地和庄稼,农忙时她为了收麦子,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以致三岁的女儿小钟被摔死在铁犁下,她却丝毫不感到悲伤。
“我听一听她的肚子还有响,那和一条小狗给车压死一样。
我也亲眼看过小狗给车轮压死,我什么都看过。
……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
会嚎叫吧?
起先我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是,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
”[11]在王婆的眼里,孩子的分量还不如麦田。
金枝由于和成业恋爱心事重重,摘菜时心不在焉而误摘了自己家地里的青柿子,便遭到母亲的踢打和怒骂。
冬天,乡村的孩子因为天冷手脚冻裂,却没有棉帽、靴子这些防寒用品,有一次,平儿偷穿父亲的靴子被王婆抓到,她像对待敌人一样夺回了靴子,因为她认为一双靴子能够穿上三个冬天,绝不能让儿子给糟蹋了,母亲珍惜靴子竟胜过爱惜儿子,平儿只好光着脚踩在雪地上,结果脚冻坏几天都不能下床走路。
可见,母亲珍惜靴子竟胜过爱惜儿子。
在萧红的笔下,父母对于孩子的重视程度完全比不上对于物质的重视。
这些像动物一样的人们,丝毫体会不到人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些人的眼里,人的性命就像荒草,像野花,他们将土地、菜园、牲畜视如生命,爱过生命,甚至一株茅草都超过人的价值。
父母对于孩子完全没有那种高于一切的珍惜,孩子在童年时期完全感受不到来自父母的温暖和关怀,这也许就是萧红自身童年经历的一个反映。
但是,在《呼兰河传》中,我们又可以感受到,虽然萧红的童年是寂寞、冷清的,只有祖父的爱和田园自然的陶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随着自身经历的坎坷和不断的漂泊,对童年生活和后花园世界的回忆,成为萧红寻找自身精神家园的主要途径。
祖父则是她童年回忆中的中心人物和童年生活中唯一的情感寄托。
成年后的萧红在越行越远的人生旅途上,一步一回头地深情的遥望着故乡,在往昔的岁月中寻找旧时的足迹。
在散文《祖父死的时候》、《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以及《呼兰河传》中,她深切的回忆了他与祖父相处的点点滴滴和骨肉深情: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
祖父已过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
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12]
这些回忆的文章,都是在她体会了人生苦味之后,饱尝了无家、思家之痛,由眼前的不幸而希求从祖父那里找到感情的慰藉、用以抗拒现实的冷酷。
如果说萧红的祖父是她童年的中心人物,那么她家的后花园算是她童年生活中最重要的地方。
这个后花园类似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曾给萧红以无限的愉悦和情趣。
她在那里不但可以逃避家里紧张的气氛,而且能和大自然发生亲密的接触,领略到大自然的博爱。
这里也是她与一生中最深爱的祖父共同生活的空间,是她童年最快乐的“摇篮”。
一方面是从父母亲那里得到的冰冷和冷漠,一方面是祖父给予的温暖和爱,这让萧红在揭露否定童年温暖的同时,却又不得不怀念祖父,只有在经历了人生坎坷,体验了孤独和寂寞之后,才会对曾经拥有的童年怀有无限的怀念。
三、否定生育又对母爱深沉表达
生育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件伟大和光荣的“创造行为”,是一件值得骄傲和高兴的事,孩子能让她们感到为人母的幸福。
然而在萧红的笔下,生育是女性的一大痛苦和灾难,给她们带来的是无尽的痛苦和折磨。
萧红自身也经历过两次生育,但都没有尝到为人母的喜悦和幸福感,她对生育痛苦的描写也许是来自她个人的切肤之痛——她在贫病中生下孩子,却又被迫送人。
也许,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痛苦之后,萧红对生育的描写也在不知不觉的受到影响。
《王阿嫂的死》中,萧红这样描写王阿嫂被张地主踢打后早产的情景:
“等到村妇挤进王阿嫂屋门的时候,王阿嫂已经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声,她的身子是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血泊中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
王阿嫂的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虽然闪光而不能活动,她的嘴张得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
”[13]在《生死场》中写了三个村妇的分娩,其中最惨的是五姑姑的姐姐,因为怕“压财”,土炕上的柴草被拿掉,产妇“像条鱼似的光着身子”在灰尘中爬行,嚎叫,“恐怖仿佛是僵尸,直伸在家里”,而她的男人,竟闯进屋子吼叫“快给我拿靴子”、“你装死啦”,还用大水盆里的凉水浇她,并“一点声音也不许她哼叫”,一整夜的痛苦和挣扎,没有得到丈夫的一点点安慰和怜惜,反而换来一顿丧失人性的暴打,最后产妇产下一个死婴,横在血光之中。
“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
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进去!
”[14]原本神圣的生命诞生成了一种罪行,女人在受着刑法,以生命作抵押,男人没有一点的体恤之情,还要施加打骂,这是多么痛苦的灾难,自然性别造成的劫难更加上男人的粗暴和冷漠,构成了女人生命非人境地与悲剧性质。
金枝由于早产,在炕脚受着刑罚,二里半的傻婆娘生孩子时,痛苦的滚转着,高声叫着:
“肚子疼死了,拿刀子快把我肚子给割开吧!
”[15]李二婶子因为小产,连自己的命都快保不住了。
从萧红细腻的笔触描写中,我们可以发现生育完全就是一种摧残女性的残酷行为,没有一点人性化的色彩,对于女性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萧红的笔下的女性形象大都是被压在社会底层的童养媳、寡妇、弃妇、少女,她们本身就受着来自社会各层面的压迫,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男尊女卑、以男人为天为一切的封建男权观念,女人的命运就更加悲惨。
刚到胡家的小团圆媳妇壮实而健康,脸黑乎乎、笑呵呵的,天真活泼、充满生机,就因为别人看不惯她,她不符合人们心中的规矩,于是婆婆就严加管教,“给她一个下马威”,想把她教成一个“规矩”的好人来。
谁知这个用八两银子换来的媳妇竟然不听管教,哀号着要回家,换来的却是更加残酷的对待:
婆婆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脚心,直到最后变成婆婆不顺心后习惯性发泄的动作,挨打的对象!
到最后生病,求医问药,然后跳神,当众洗热水澡,最后被折磨,痛苦的死去。
还有月英,那个美丽,却在生病后被丈夫虐待致死,王大姑娘最终的结局,我们都看到女人悲惨的命运以及对此的无力反抗。
萧红用直面现实的描写,展示了一幅幅女性苦难生存的现实图景,表达了她对可怜可悲的女性命运的深切体验和对潜在巨大社会毒害力量的批判,女人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如何体会到爱情,又如何体会到生育所带来的幸福感?
在社会习俗、男人所“赐加”的痛苦上,还要经历自然所赋予的“惩罚”,不得不说这样的命运任谁都会觉得痛苦。
但同时,在《桥》这篇小说中,我们却又能感受到母爱的深沉和伟大。
它讲述了农村妇女黄良子家的不幸遭遇。
由于家庭生活贫穷,黄良子舍下自己才一岁多的儿子,到富人家做奶娘。
看到富人的孩子她就想到了自己的儿子,而她却不能亲自照顾小良子,富人家的孩子有吃不完的东西,而自己的儿子却常常饿的没有东西吃,她感到心酸,想从富人家拿点东西给自己的儿子吃。
由于她家和富人家隔了一座桥,桥又很旧,连桥板都没有,她回家给儿子送东西无法从桥面上通过,每次都要绕过很长的一段路。
为了防止被富人发现,她飞奔着回家,而后迅速返回。
有时她就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往对面喊一声,拣了馒头、饼干之类的东西扔过去给儿子吃。
后来,桥修好了,可以从上面通过了,小良子为了吃馒头就自己走过桥对面找妈妈,结果掉下水沟给淹死了,黄良子家痛苦不堪。
整篇文章中,都可以感受到深沉的母爱。
虽然“自己那个孩子黄瘦,眼圈发一点蓝,脖子略微有点长”,看起来像枯了的树枝,可是她总是觉得“比车里的孩子更可爱一点”,隔着桥她还很暴躁的叫孩子的爹给孩子擦鼻涕,恨不得自己过去,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工作,自己嘴里唱给小主人的儿歌。
到后来小良子死了,作为母亲的黄良子的悲伤和难过显而易见:
“于是肺叶在她的胸的内面颤动和放大。
这次,她真的哭了”。
[16]自己的孩子再不乖,再不可爱,母亲也总是偏爱他,而自己的孩子死了,母亲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它会像一个飘忽不定的梦一样一直萦绕母亲的周围,不会散去。
这也是萧红对她曾经的孩子的一个迟来的“追悼”吧!
四、抨击国民劣根性又对这些弱者充满同情
《呼兰河传》构思于“七·七”抗战爆发之后,1937年年底开始动笔于武汉,1940年12月完成于香港。
“《呼兰河传》对于萧红来说,其意义之大是怎么估计都不会多分的。
这部杰作,是萧红个体生命最绚烂的一次闪光,是她情感、性格、个性、心理最集中的呈现,也是她杰出的艺术才华与大胆的创造精神最有力的证明。
”[17]它并非是作者对故乡的简单回忆,或是远离现实斗争的个人孤寂情怀的叙述,而是在这回忆中掺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深入到整个民族的灵魂深处,是萧红以现代人的眼光冷静的观照自己熟悉的生存环境,以时代先觉者的敏锐把笔锋伸向民族灵魂的深层,深刻而尖锐地抨击国民的那种愚昧、怯懦、自私、麻木,发掘国民的劣根性,以期达到思想启蒙的作用。
自萧红1934年11月30日在上海第一次见到萧红,到鲁迅1936年病逝,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她与鲁迅建立起来深厚的友谊,这使她不仅在文学写作上收获颇多,而且鲁迅那些忧国忧民的思想她也深得其传。
“鲁迅对萧红一生的意义之大,超过了其他任何人,这不仅体现在思想、性格、文学创作等方面,也体现在感情、心理、人生追求等方面。
”[18]她和鲁迅一样,把改造民族灵魂当成文学创作的中心主题,她的目光也始终是投向乡土中国最底层的普通人。
在《呼兰河传》中,没有英雄式的人物,没有浩大的场面,没有历史的主角,活动在其间的只是芸芸众生,而一直经久不息的是看客群的存在。
“看客”是最庞大的一个群体,《呼兰河传》中几乎无所不在,他们是站在大泥坑边看着种种悲剧边袖手旁观的一群,是赶着看“五大文化”盛举的一群,疯女人、跳井的、上吊的,他们饶有兴致地看;卖麻花、卖豆腐的,他们也饶有兴致地看。
看客们眼睁睁地看着老胡家娶了健康的小团圆媳妇,又眼睁睁地看着小团圆媳妇在“洗热水澡”过程中被活活折磨致死;看着王大姑娘在凄凉的秋夜中难产死去,又要用绝望的眼光看冯歪嘴子上吊、投河、自刎,还要看冯歪嘴子儿子的“非死不可”。
看,成了呼兰河城群体人物重要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娱乐方式以及传播流言绯闻的特有方式。
他们不仅看着他人的命运,而且也看着自己的人生。
看客群的书写,标志着作家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不仅仅停留在表层的野蛮陋习上,而且深刻揭示了国民文化心理和深层人格,以及这些人内在生命力的枯萎。
作家以大量的民风习俗为背景,揭示“看客”们深层的文化根源及其行为的无意识,着力表现了他们由于苦难闭塞而造成的自身的悲剧。
萧红通过“看客”的众生相、社会相,揭示了呼兰河城人经历的苦难人生,他们对待生活、生命、命运的态度和采取这种态度的心理基础及思维形态,在历史文化批判中,蕴含着改造国民灵魂的愿望。
小说第五章小团圆媳妇的“洗澡”与死是最悲惨的一幕,这时群体人物几乎全上场了。
小团圆媳妇在热水中拼命挣扎,大声呼叫的时候,人们熟视无睹,还帮着浇热水。
当她气若游丝、命丧黄泉的时候,东家的婶子、二姨,西家的大娘、三婶,又一起蜂拥求助。
直至小媳妇被烫死,竟有心慈的人流下眼泪。
对于这些群体人物,萧红没有采用疾言厉色式的正面批判,没有把这一悲剧简单指向小团圆媳妇的婆婆。
作者认为呼兰河城的人们多是善良的,他们照着仍然是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考而生活;他们有时显得麻木,有时也许显得愚昧而蛮横,但他们并没有害人或自害的意思;他们是按照他们认为最合理的办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们痛恨他们,但同时正如矛盾先生在《〈呼兰河传〉序言》里写道:
“我们只觉得这婆婆也可怜,她同样是‘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考而生活’一个牺牲者。
她的‘立场’,她的叫人觉得可恨而又可怜的地方……由她自己申说得明明白白的。
”[19]
有二伯是萧红笔下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有阿Q式的自我嘲弄、自我宣泄,他和老厨子一样都是仆人,却相互不同情,经常吵骂。
最令人可叹的是有二伯常用主子的思想对待周围和他一样的弱者,他不同情小团圆媳妇的遭遇,反而说“介(这)年头是个啥年头?
小团圆媳妇也不像个团圆媳妇了。
”[20]对于王大姐和冯歪嘴子也无半点同情,竟责备王大姑娘不该找个磨倌,应该找个穿绸缎的。
勤劳的有二伯,一生受尽歧视和嘲弄,可他却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的同类,自觉维护封建传统观念。
这阿Q式的奴性,正如列宁所说:
“身为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还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辩护和粉饰。
”[21]探索我们民族出路的萧红,对此尤为痛心疾首。
家中老迈“弱势”的祖父给她的温暖和爱也让成年后的萧红对以有二伯为代表的底层人民和社会弱者有着无限的同情。
在许多作品中,虽然她在无情揭露着那些底层人民的劣根性,同时却又对他们怀着无限的同情。
《呼兰河传》在写“多余人”有二伯偷东西、扯谎、骂人等等不堪入目的毛病的同时,萧红却又对他充满了同情。
在《家族以外的人》中,作者用充满稚气的话语,回忆了昔日同伴有二伯,他无家无业,无儿无女,是一个游离于社会团体之外的边缘人,这一点是造成他悲剧一生的最根本原因。
他不但得不到主人的善待,就是同为奴隶的下人们也瞧不起他,时不时地要耍弄他一番以排遣无聊的生活。
生活是残酷的,有二伯六十多岁了还遭到主人的殴打,遭此凌辱的有二伯想到了死,但他的“自杀”又成了人们的笑料,因为他只不过是想借此引起人们对他的同情与尊重。
萧红通过有二伯“自杀”的可笑突出他的不自知,深层里却由于这种可笑反衬出了有二伯一生的凄楚。
尤其是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可笑源于残酷的生存现实与有二伯摆脱困境的强烈愿望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时,一种浓郁的悲剧感就会涌上心头。
有二伯是孤苦的,他寂寞无告的灵魂只得和雀子、大黄狗倾诉,因为这些生物无欺、真纯。
有二伯喜欢和这些生物说话,是因为有二伯只剩下这无力的语言和他无助的心灵相依相偎。
人活在世上总要有一点温存的寄托,虽多少带点虚无,但毕竟是抓得住的一点实有。
最后他孑然一身,孤老穷死,就像那条被李寡妇冷落而死的花狗。
有二伯最突出反映了萧红面向民众的两种态度:
同情(哀其不幸)和鞭挞(怒其不争),这同样也是鲁迅批判国民性思想的一种承接。
磨倌冯歪嘴子和王大姑娘这对青年夫妻,默默恋爱,不吭不响地成了家。
这无疑是对封建传统婚俗尖锐的挑战。
作者几乎没有描写他们的恋爱经历,王大姑娘一出场,便已是磨倌媳妇并已做了第一个孩子的母亲。
到她第二个孩子出世时在一个冷清寂寞的秋夜难产死去。
他们成为异类被隔离出呼兰河城,为人们所驱逐。
萧红在这里展示了整个呼兰城人的精神文化心理,揭示其病因,表现作家深切的救赎病态灵魂的情绪,同时又带有深深的无奈之情。
年轻丈夫冯外嘴子并没有被艰难凄惨的生活以及妻子的死而击垮,他顽强地活了下来。
虽然人们都用绝望的眼光看他,“他虽然也常常满满含着眼泪。
”但“他觉得在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
要长得牢牢的。
他不管他自己有这份能力没有他看看别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他觉得他也应该这样做。
于是他照常地活在世界上,他照常地负着他那份责任。
……他喂着小的,带着大的。
”[22]在别人眼里没有长大的孩子,在他眼里却似乎一天比一天大,他感到很欣慰。
冯歪嘴子没有感到绝望。
他不问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目的是什么,只是凭着原始的朴实的信仰在苦苦倔强地活着。
他在萧红笔下是一个有意识的、能够进行自我判断的个人。
在这个人物形象身上包含着一种原初的对生命的珍视,虽是不自觉的,却深深扎根于潜意识深处,在此,小说在笼罩着呼兰河小城的灰云中闪露出了一丝阳光。
磨倌对活着的本能追求,对生存的坚执,已经不单单是具有个体的意义,在他身上,折射出的是整个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最终动力,是古老民族延续的根基。
只是萧红笔下这种执著于现实存在的思想、反抗绝望的人物毕竟太稀少了。
五、对生命感伤悲凉又依依不舍
萧红的一生似乎除了童年时期给她爱和温暖的爷爷和她的后花园之外,就只有和萧军同居三年里有过欢乐和温暖,剩下的时间里都是永不停滞的漂泊,一次次的出走,让她像海上的浮萍,永远找不到归宿。
从1927年到1942年间,萧红有过15次以上的“离开”,所到之地包括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