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姐.docx
《刘小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刘小姐.docx(4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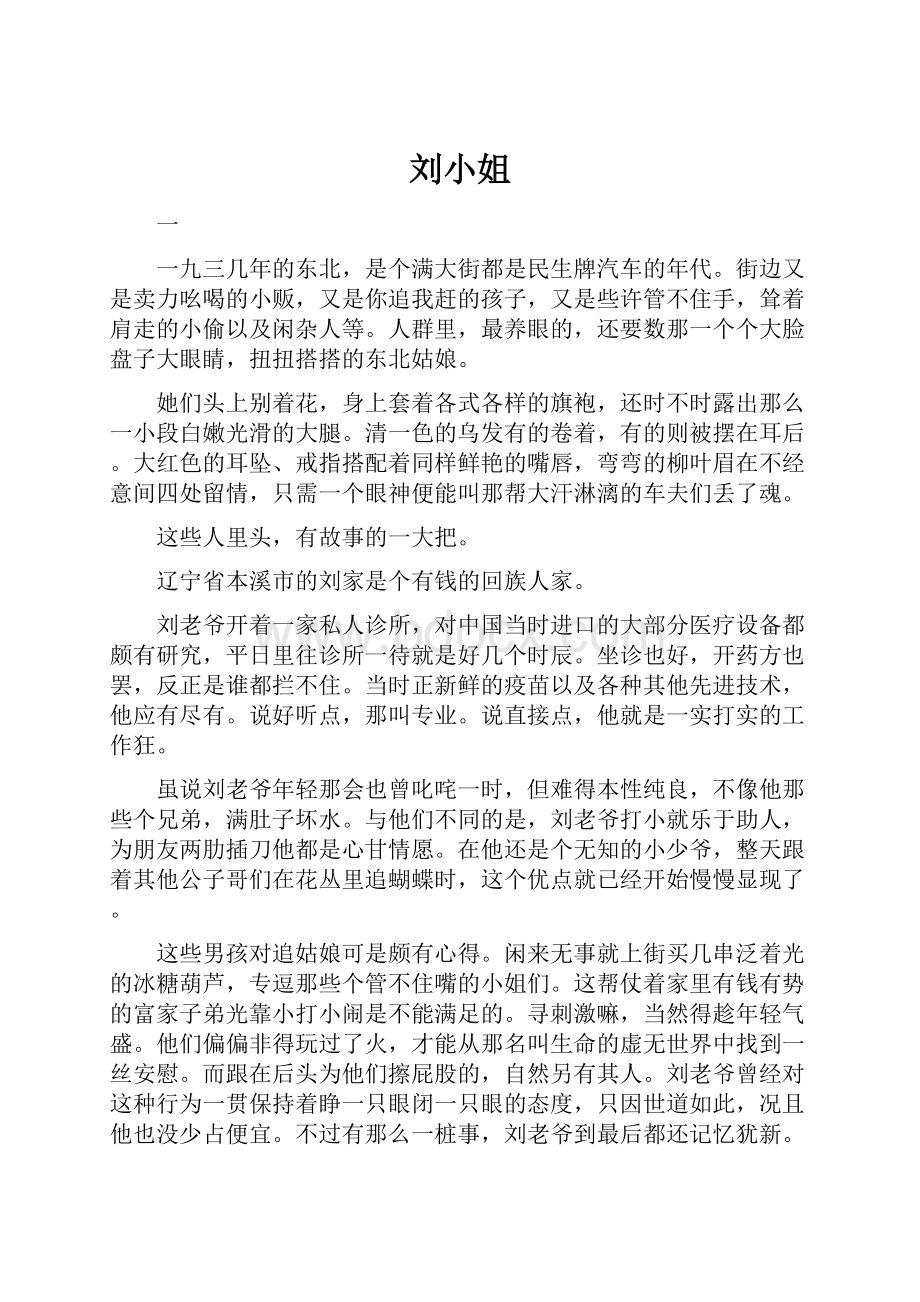
刘小姐
一
一九三几年的东北,是个满大街都是民生牌汽车的年代。
街边又是卖力吆喝的小贩,又是你追我赶的孩子,又是些许管不住手,耸着肩走的小偷以及闲杂人等。
人群里,最养眼的,还要数那一个个大脸盘子大眼睛,扭扭搭搭的东北姑娘。
她们头上别着花,身上套着各式各样的旗袍,还时不时露出那么一小段白嫩光滑的大腿。
清一色的乌发有的卷着,有的则被摆在耳后。
大红色的耳坠、戒指搭配着同样鲜艳的嘴唇,弯弯的柳叶眉在不经意间四处留情,只需一个眼神便能叫那帮大汗淋漓的车夫们丢了魂。
这些人里头,有故事的一大把。
辽宁省本溪市的刘家是个有钱的回族人家。
刘老爷开着一家私人诊所,对中国当时进口的大部分医疗设备都颇有研究,平日里往诊所一待就是好几个时辰。
坐诊也好,开药方也罢,反正是谁都拦不住。
当时正新鲜的疫苗以及各种其他先进技术,他应有尽有。
说好听点,那叫专业。
说直接点,他就是一实打实的工作狂。
虽说刘老爷年轻那会也曾叱咤一时,但难得本性纯良,不像他那些个兄弟,满肚子坏水。
与他们不同的是,刘老爷打小就乐于助人,为朋友两肋插刀他都是心甘情愿。
在他还是个无知的小少爷,整天跟着其他公子哥们在花丛里追蝴蝶时,这个优点就已经开始慢慢显现了。
这些男孩对追姑娘可是颇有心得。
闲来无事就上街买几串泛着光的冰糖葫芦,专逗那些个管不住嘴的小姐们。
这帮仗着家里有钱有势的富家子弟光靠小打小闹是不能满足的。
寻刺激嘛,当然得趁年轻气盛。
他们偏偏非得玩过了火,才能从那名叫生命的虚无世界中找到一丝安慰。
而跟在后头为他们擦屁股的,自然另有其人。
刘老爷曾经对这种行为一贯保持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因世道如此,况且他也没少占便宜。
不过有那么一桩事,刘老爷到最后都还记忆犹新。
他跟他的一发小打俩人都还光着屁股满屋子跑的时候就是邻居了。
这发小同样也是蜜罐子里长大的,却不小心惹错了人。
据说他看上的那姑娘背景可不简单。
别人身后顶多也就有个富家爹爹罩着,可这姑娘竟和当年一唯我独大的黑道人物好上了。
这发小可算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有天夜里俩人正要往家走,却被几个彪形大汉堵了去路。
这大半夜的,再怎么喊也不见得能有人来帮忙,更别说一来就撞见这么几位凶神恶煞的索命无常。
发小眼看情况不妙,不断督促着让刘老爷先走,他殿后。
年纪轻轻的公子哥们就跟大街上那帮毛头小子差不多,都是些没见过什么世面却还要打肿脸充胖子的狗熊。
刘老爷自然是没丢下他,毕竟自己的面子也摆在那呢。
只见那帮恶徒中,有一人摸索着掏出了把刀,刘老爷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这是要玩命啊。
他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见敢对着自己掏家伙的人,也不知道上面沾了多少人的心头血。
他当即做好了殒命于此的准备,却只听那发小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那些人就跑了。
刘老爷当时可是心急如焚,只能使劲摁着发小肚子上呼呼冒血的窟窿,也不敢大声呼救,怕把那些人引回来。
且想想,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少爷满手是血地跪在地上,眼前还躺着副奄奄一息的身子。
这局面,刘老爷怕是想都没想过能被自己摊上。
那发小后来因失血过多死了,刘老爷也抑郁了一段时日。
后来再遇见那些个眼波流转却庸脂俗粉的漂亮姑娘,他也不再动心了。
经这么一折腾,刘老爷也算是领略到了“世事难料”这四个字的精髓。
前一秒还生龙活虎的人,说没就没了。
那阵子过后,他便下定了决心,下半辈子,一定要医人。
丁氏可同刘老爷从前追过的那些莺莺燕燕不一样。
她从小到大就秉持着一个道理,那就是嫁得好不如跳得高。
像她这样的女人,可是花了刘老爷好大功夫才追到手。
丁氏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和哥哥当年都是名声在外的文化人。
家里的女眷虽然没接受过教育,但好歹也对唐诗宋词耳濡目染。
去过她家宅子里的人都说,那地方,就连木头柱子都是香的。
每每听见这种糊弄小孩的胡话,丁氏不过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只当听戏罢了。
除了父亲跟哥哥,丁氏就没怎么跟其他异性来往过,于是对刘老爷的猛烈追求起初无动于衷。
她是偶然听见丫头们议论,说这刘小少爷就跟变了个人似的,竟对自家姑娘如此认真,才动了心的。
那也是她唯一一次,破天荒地从头到尾听完了那些闲话。
当时的刘老爷仍然被归类于不是善茬这一栏下,家里有女孩的都提防着他,怕哪天自己闺女也被他始乱终弃。
他们不知道的是,本来就没有过多少坏心思的刘老爷,早就已经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了。
刘氏夫妇前前后后生了六个男孩、七个女孩,总共十三个孩子。
这么多孩子每天把刘丁氏忙活得够呛,常常恨不得把自己掰成十三瓣,一人分一瓣。
最让她头疼的必须是睡觉这件事了。
又大又宽的炕上一个个全往中间挤,都想挨着自个妈。
最后挨得刘老爷实在受不了,搬到外屋睡去了。
小点的挨不着就哭,大点的挨不着就闹,襁褓里的搞不清状况也得跟着叫唤几声。
因此刘丁氏经常是两边拍着双胞胎姑娘,脚下躺着几个,身上趴着几个,还有几个就那么生着闷气睡过去的。
不知道后来是不是终于想通了,请了位奶妈,这十三块石头,才算是勉强放下了。
要说刘氏夫妇最疼的孩子,那肯定是年龄最小的刘小姐了。
作为家里唯一受过教育的女性,刘小姐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字还写得极其漂亮。
您要是觉得她就是那个年代典型的大家闺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刘小姐可不是个一般的女子。
她不喜欢脂粉,对漂亮衣裳也没多大兴趣。
她更是不信男尊女卑这套不像话的说辞,更不会因此做出任何退让。
她一直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一份既稳定又特别的工作,还有一个任凭雨打风吹却仍旧安如磐石的家。
于是她的少女时期,理所应当地轰轰烈烈,刻骨铭心。
***
本溪市另一边,伴着家喻户晓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和叮叮当当的电车声,黑家那条小狗又开始仰着头汪汪地叫。
您还别说,阿岛可真不是条一般的狗。
别人家的公鸡打个鸣能把一屋子人吵醒,阿岛一张口,左邻右舍都得从炕上爬起来,冲出去朝着黑家房门吼上那么两三句,解解恨。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唾沫星子混着汗珠肆意挥洒,楼下路过的偶尔还会伸出手接一下,紧接着撒腿就跑,赶着回家收衣服。
黑家是个产业工人家庭,家里只有黑山这么一个儿子。
这要搁到别人家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但老黑总说,养一个出息的可比养一百个没出息的强。
这话邻里听了当然不乐意了。
你说得轻巧,那是因为你上辈子不知道积了什么德,落着这么好的孩子。
确实,黑山这小子,从小不哭不闹,还极其懂事。
见人知道打招呼,受了别人恩惠知道推辞,推辞不掉知道说声谢谢。
这些美德虽然现在听起来不算什么,但在那个走路不小心撞着人都能挨一砖的年代里,黑山这样的,着实少见。
一九四六年,本溪保卫战正式打响。
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没有一个不去参军,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一腔热血的黑山。
黑家两口子原本是不愿意送黑山走的,毕竟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而且才十六,捧在手心里疼还来不及。
但老黑眼看着当初怀里牙牙学语的婴孩慢慢长成面前比自己还高半头的年轻人,又顾及到黑山自个的决心,才经过一番心理斗争,艰难地批准了。
为国征战,这是一件多么让人骄傲的事。
尽管如此,彼时黑山也才十六岁,这辈子还没遇见过什么大风大浪,对生离死别能有什么概念?
黑山他娘得知这个消息后跟老黑大吵了一架,盘子碗碎了一地。
她问老黑,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无私?
无私止不了士兵们的鲜血,更换不回他们的命。
可那根本没用。
深居闺中看不清家国大业,女人的眼泪是那个年代最不值钱的东西。
黑山走的那天下着小雨,老黑就坐在窗边的小桌子旁,平时自己喝酒的地方。
临走前他也给黑山倒了一杯,说,虽然有点早,可这画面如果现在看不到,怕以后就没机会了。
父子俩之间显然没什么共同话题,只见那两只杯子一次又一次地被饮尽,填满。
父亲喝得酩酊大醉,儿子却一直清醒着。
送行的时候老黑没去,据说是喝大了,倒屋里起不来了。
黑家的男人不能流眼泪,这是老黑对黑山说的,可他自己却出尔反尔了一回。
略显单薄的少年,身后背着跟自己差不多重的包袱,挥了挥手,就那样云淡风轻地离开了。
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东北解放。
十五岁的刘小姐明眸皓齿,书生意气。
刘小姐是在一个下雪天第一次见到先生的。
他斜顶着军帽,身上披了件墨绿色的呢子大衣,嘴里还叼着支做工精细的红木烟斗。
白皙的皮肤倒是不像久经沙场。
微挑的双眉下,那对黑玉似的瞳仁缓缓扫过路边的行人。
好像如果能有幸被他望见,就是为他挥霍毕生的情爱也不可惜。
这双眼睛,不知道耽误了多少姑娘的青春年华。
刘小姐与先生的第一次对话是烟草味的。
女孩双臂怀抱着一沓书本,冻得有些发红的双手在寒风中略显吃力。
一头短发下那张未施粉黛的小圆脸,迎着似有似无的烟雾,紧紧跟随着男人的一举一动。
听说上好的烟草,初次闻是呛鼻的,再一闻是清雅的,而余味则是温润的。
女孩仔细嗅了嗅,是这味道没错了。
男人与女孩对视的瞬间,雪停了。
军靴踏过的地方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女孩穿着略微潮湿的布鞋静静地立在原地,任凭零零散散的雪花飘落在鞋面上。
她的心情无比紧张,对自己体内突如其来的翻江倒海不知该如何是好。
于是她就那么站着,直到充斥着鼻腔的烟草味越来越放肆。
男人问道,多大了?
男人又问,叫什么名字?
先生的话是寒冬里的一股暖流,却又好生刺耳。
这样温柔的声音,怎么能被卷入那吃人不吐骨头的政治场上呢?
但求先生下辈子是个满肚子墨水的教书人,能用他那副嗓子为莘莘学子朗诵诗文。
但求他不再被牵扯进那没完没了的明争暗斗,能安安稳稳地娶妻生子,过一世平凡的人生。
或许他会有一场盛大的婚礼,又或许两个人的终身会私订在一座隐秘的山林里。
他们大概会生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妹妹被欺负的时候两个哥哥都护着她。
他们又或许会就这样一直过下去,膝下无子,做饭砍柴。
那该是多好的一生啊,刘小姐这样想着。
姓刘,十五。
男人默念了一遍女孩的名字,眼里突如其来的深情让人觉得接下来脱口而出的似乎该是另外几个字。
他呼出一口气,伸出左手在眼前摆了摆,把方才叼着的烟斗夹在了臂下。
取下手套,陶瓷似的手腕,纤长的五根手指,还有发红的指尖,无一不吸引着女孩的视线。
我这样,不妙吧?
***
本溪市税务局,局长办公室。
黑山端坐在办公桌后,有些年头的棕色皮鞋与木质地板融为一体。
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皮肤,杂乱浓郁的眉,粗糙的指节之间来回游走的钢笔,还有它勉强勾勒出的字。
这是阿岛挠的?
惨不忍睹。
面前的姑娘高中毕业,及腰的麻花辫随着她的一举一动左右摇摆,怀表似的看得黑山出了神。
漂亮,真漂亮。
叫什么?
黑山问道。
吾恙。
嗯,好名字。
回族?
是。
字挺好看。
谢谢。
为什么想当秘书?
想来就来了。
黑山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爸,我要结婚。
老黑这边打着哈欠刚从被窝里钻出来,只听屋子对面正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的黑山他娘大喊一句,选日子!
黑山一把扯下斜挎着的帆布包,着急忙慌地拉开椅子坐了下去。
老黑这会儿才逐渐清醒,慢悠悠地也坐了下来。
手里鼓捣着的珠子一刻也没停过,就那么盯着自家儿子。
也是,都二十一了,再不悸动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黑山这块不开窍的木头,作为家里的独苗,老黑还真担心过断后这回事。
这几年给他介绍过的对象也是十根指头都数不过来。
这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黑山这棵铁树,总算是逢春了。
经过一番盘问,老黑也算是大概摸清了对方的底细。
同样是回族,长得又标致,还有文化,怎么想都是自己儿子占了便宜。
于是英明果断的老黑,当下就接下了黑山让自己去提亲这件差事。
吾姑娘她爹比想象中要直接得多,举手投足间不经意流露出的气质风范唬得老黑一愣一愣的。
起初老黑对自己未来亲家的态度完全摸不准,只求别是个自命不凡的主。
这一见面才体会到了真正的文质彬彬,有里有面。
更让老黑庆幸的是,吾姑娘他爹与自己竟有许多同样的爱好。
老黑这人平时对茶道颇有研究,毕竟上了年纪的人没什么事干,都爱鼓捣这些玩意打发时间。
被吾姑娘他爹领着参观茶柜的时候,他一眼就瞧见了自己四处打听都没能讨着的上好龙井。
吾姑娘他爹好歹也是个生意人,整日游走在饭局应酬间,察言观色自然不在话下。
他将这珍品拿了出来,规规矩矩地开始温具,趁着间隙还偶尔抬眼瞅瞅目不转睛的老黑,在自己心里打着算盘。
看眼前这人这么老实,想必儿子也差不到哪去。
再加上黑山在政府工作,俩人要是真成了,闺女的下半生也能安稳。
至于闺女愿意与否,那就得看黑山这小子能不能成功俘获她的芳心了,毕竟自己女儿的主意可大了去了。
几盏茶过后,两位父亲愉快地握住了对方的手,眼角含笑地达成了共识。
三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
刘家隔壁的回民饭店每天乌泱泱挤满了人。
刘家大院里也没闲着。
用人们左一碗汤,右一盘菜地紧着上,光是看着脚步就让人头晕眼花。
刘老爷坐在席中间,一边是刘丁氏,一边是刘小姐,其他子女叽叽喳喳地你一言我一语,好不热闹。
姑娘们聊的都是新衣裳、新布鞋。
刘家大少爷这边才刚开始跟父亲请教做买卖这回事,没一会就被刘老爷“只赔不赚”四个字打发了。
隔壁的老二聚精会神地抱着一本《政治经济学》,还时不时推推鼻梁上不断下滑的眼镜。
坐得最远的老三隔三岔五地敲敲桌面,不用问,铁定又是缺了零花钱。
饭桌上老四、老五和老六的位子都还留着。
刘老爷说了,他们即便是年纪轻轻就不在了,也不能把人家存在过的痕迹抹了去,毕竟曾经都是一家人。
刘小姐本性不喜热闹,更别提唠嗑了。
这不,筷子一撂,站起来就走。
其他人像是见惯了似的,自家老小这脾气,愣是头牛都犟不过她。
刘小姐屋内有个衣柜,上好的沉香木做的,费了刘老爷老大劲才给从云南运过来,据说能把衣物催得飘香。
起初刘小姐对这柜子的意见可大了去了。
占地方不说,还有股奇怪的味,害得她整夜整夜地头疼。
不过后来有那么一天,刘小姐放学回家刚好撞见用人们把这柜子往外搬,竟急得亲自上前抱住了它,死活不让动。
用人们虽然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但也没敢继续搬,于是这柜子就这么留下了。
这柜子里有个上了锁的红木箱子,打送到刘家起就在那了,愣是在里头摆了几个月才被发现。
估计是木匠给买家的一个惊喜,箱子上刻的花纹一看就是功夫活。
刘小姐起初本想把它送给刘丁氏的。
母亲喜欢用红木箱装首饰,显得人精致大方,可后来却是说什么都不肯给了。
要说这里头都装了些什么,那装的,可是款款深情。
亲爱的兰:
今天你好吗?
昨日看见你放学,本想同你说说话,却见你一脸倦容,便没上前打扰。
这段时间没休息好吧?
我知道你学业繁忙,却没想到如此费神。
自那天遇见你之后,我便满脑子都是你。
虽然这样说话有些唐突,可我偏是不可控地想着你。
近来天冷,多喝些热水暖暖胃,可别感冒。
你要是愿意,就上你们学校对面的饭馆里坐坐吧。
要说我没私心那是假的,不过想让你尝尝他们家的糖饼是真的。
我听说小姑娘家都好吃甜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盼安。
亲爱的兰:
今天你好吗?
记得前两天答应过要带你去湖边走走,不知道你何时方便?
你父亲管得严,要是不行也无妨。
只是几日不见,有些想你罢了。
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倒是有些不务正业,整天借着写诗打发时间。
下次见面我想送你几首我新写的,一是请你帮忙品品,二是希望你也能惦记着我。
我等你答复。
盼安。
亲爱的兰:
今天你好吗?
今天早晨路过你家院子,在门口看见了几枝你最喜欢的榆叶梅。
你说它有欣欣向荣的意味,我平时虽然对这些不太了解,不过你说的,想必都是对的。
改天我也在我住处附近种上两棵,随你一起进步。
我还想找个空旷些的地方,种上一大片,等来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同你一起去赏花,你看如何?
盼安。
***
一九五一年冬天。
这一天,黑山难得起得比阿岛还早。
他着急忙慌地跳下了炕,一路小跑着进了外头的公共便所,身后带上的门发出了结结实实的一声响,直接震醒了老黑两口子。
心气不顺的老黑刚要追出去撒撒火,就被老伴一把拉了回来。
他嘟囔了几句只有自己听得见的话,随后又转身倒下了。
只是这么一闹,黑山他娘倒是再也睡不着了。
毕竟今天是个大日子,她可得给自己儿子好好做顿早饭,壮壮士气。
正琢磨着该做些什么好,就听见了平日里同自己还算亲近的邻居张婶洪亮的嗓音。
张婶这人特别热心肠,黑家偶尔有什么需要她都尽可能地照应着。
知道他们家是回民,所以请他们吃饭时,桌上摆的绝对一律清真。
不过这热心肠倒不仅仅是为了友好的邻里关系,而是因为那张婶家里有个还算标致的小侄女,从小就对男子气概十足的黑山万分景仰。
张婶原先无数次找黑山他娘聊天的目的,都是为了能让自己侄女跟黑山处对象,甚至把将来俩人结婚之后到谁家拜年的顺序都构思了一遍。
黑山他娘虽说对张婶没什么意见,对她家那小侄女也还算认可,但她总觉得差了点什么,于是每次都巧妙地避开了这个话题。
日子久了,张婶见自己侄女明显是一厢情愿,倒也没再过多地提起这件事。
只是这天,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让她直接找上了黑家的门。
虽说交谈到最后俩人不欢而散,可黑山他娘却因为把事情挑明了,总算松了口气。
强扭的瓜不甜这道理,她可是再清楚不过了。
想当年自己与老黑,那也是久经坎坷才好不容易修成了正果。
只不过毕竟是做母亲的,她也有些心疼张家那小侄女,一片真心到最后却什么也不是。
后来那小侄女嫁了个官二代,是个整天好吃懒做的主。
那人似乎性格也不怎么样,稍微提高点嗓门跟他争上几句他就动手。
那天黑山出门前这小侄女去找他了。
常听别人说,将死之人都会回光返照,她对黑山的执着好像也是这样。
豆蔻年华的少女,遇到了一个承载着所有美好的人。
如果可以的话,她当然会继续等,只因为他是光,触不可及,又耀眼到让人无法回避。
当所有对爱情的憧憬和幻想都摆在眼前,有谁会掉头再去追求别的东西?
可唯独感情这玩意,能一次又一次地给予伤害,让最执着的人选择离开。
她不擅长说话,动不动就害羞,不是黑山喜欢的类型。
她很清楚这一点,可她不想再懦弱了。
她就是想拼一次,也算是给自己这么多年来偷偷红过的脸一个交代。
她准备了一大段说辞,可真正站到黑山面前的时候她却又害怕了。
她怕被拒绝,更怕被拒绝后自己会从他的生命里消失。
她对黑山最后的印象是一个仓促的微笑。
明明是那么阳光的人,却总对自己疏离得过分。
是啊,他要去追求他喜欢的姑娘了,可千万别把他临走前的礼貌当作救命稻草。
除了祝福,自己好像并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
路上小心,她说。
尽管这最后一个字,连同她最后残存的一丝希望,都被黑山离开时带起的风刮走了。
再怎么怕疼,也得撞一回南墙。
听别人说那小侄女嫁过去没多久就死于非命,而她那官二代丈夫则娶了同他一起长大的青梅,连灵牌都没能摆进夫家的祠堂。
自古红颜多薄命,说得还真没错。
黑山从便所回来以后借过他娘的镜子仔细研究了一番自己的脸。
他的五官绝对不次,眉眼中透露出的英气,少说也能迷倒些初出茅庐的小姑娘,但偏偏今天让他怎么都看不顺眼。
一会觉得黑眼圈太重了,跟只熊猫似的,一会又觉得眼睛里的血丝太明显了,一看就像休息不好,肾虚的症状。
总之,黑山的早晨是伴着阿岛的叫声,他娘的唠叨声,和自己逐渐加快的心跳声一块度过的。
因为今天,是他和吾恙的第一次约会。
黑山听老黑说,姑娘家都喜欢逛街。
对恋爱约会这方面毫无经验的他,虽然对老黑的提议疑心满满,但除了硬着头皮照做,还真是没有更好的法子。
黑山家里有些拮据,坐电车的钱凑了一个星期都没凑齐。
他本来想着在附近溜达溜达,看看景就挺好的了。
至于逛街,应该跟遛弯没什么差别吧?
吾恙主动掏了来回的车票钱,这一大公无私的举动,使她在黑山心里的地位又光辉伟大了许多。
黑山从没见过像她一样,从眉眼到举动都透露着清冷的姑娘,跟自己从前那些只会受人摆布的相亲对象简直是天差地别。
任何物件在她眼里都激不起丝毫水花,反倒是黑山担心那些东西玷污了它们的纯净。
偶尔,当这双眼睛停留在某枝花、某棵树上的时候,黑山仿佛能看见它们的变化,却怎么也想不出这变化的缘由。
每到那个时候,黑山就告诉自己,等他赚够了钱,第一件事就是娶她。
到时候,酒席一定要办得大张旗鼓,让所有人都知道,这吾姑娘,进了他黑家的门。
四
刘小姐十六岁那年学会了抽烟。
她为此被刘丁氏数落了不知道多少回,说她一回族姑娘整天手里拿着支烟斗,一点都不像话。
刘小姐倒是从没把这些放在心上,总趁自己母亲说得口干舌燥到处找茶喝的工夫继续抽,不以为然。
抽烟是她那年冬天学会的。
想必刘小姐与先生的初见在她心里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以至于每回下雪的时候,她都拿着烟斗坐在炕上,朝着窗外小片小片的雪花呼气。
刘小姐抽烟的时候极漂亮。
轻颤着的睫毛和潮红的双颊,都彰显着她时而波涛汹涌,时而静如止水的思绪。
也唯有她才能把烟抽得如此雅致了吧。
都说刘小姐秀外慧中,谁要是娶了她那可真是烧了高香了。
但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却经常会想,如果自己是个男人会是什么样?
“他”该是个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
眉清目秀,但不是个专情的人。
即便片叶不沾身,也不会有人责骂,因为他们都相信“他”会带来改变,带领所有人走向更好的未来。
而被“他”玩弄过的女人,都不过会成为“他”谈笑风生时拿来打趣的话柄。
刘小姐已经有些天没收到过先生的书信了。
自己父亲对先生的态度她看得一清二楚,只不过是不想捅破这层纸,不然就真的连一丝念想都没了。
但热恋中的年轻男女哪顾得上这些啊?
就是三天不见都想得慌,何况这俩人已经几个星期没来往了。
刘老爷绞尽脑汁想出了无数种理由阻止她出门,可刘小姐这刚烈的性子哪受得了这样的束缚?
在又一次出逃失败之后,刘老爷终于发怒了。
刘老爷虽算不上什么严父,却也是个明白人。
刘小姐每天夜里偷偷往外跑这件事他早就知道了。
之所以没草率地做出什么大动作是因为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把自家闺女这般性子冷淡,高高在上的小姑娘迷得神魂颠倒。
人都是护犊的,更别提像刘老爷这般偏心的父亲了。
虽说在那个年代,十六岁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可他就是对这来路不明、神神秘秘的先生喜欢不起来。
再往深了一打听,好家伙,是个汉民!
绝对不行。
先生住所隔壁的小巷子是他们的秘密花园。
虽然跟刘家大院有段距离,可刘小姐却丝毫不在乎。
刘丁氏跟她说过,这世上有两种爱情。
第一种是奋不顾身的,等到哪天你真的爱上了一个人,就是叫你跋山涉水你也心甘情愿。
而第二种是细水长流的,是柴米油盐,是小打小闹,却也是最踏实的。
我想着你大概更向往第一种,因为那样的体验只能有一次,可它不够长久。
姑娘家,要是想落得下半生安稳,还是该选第二种。
刘小姐时常会想起刘丁氏的话,然后剩下的就只有不屑。
打出生起,她就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她是那花丛中开得最美的一朵,却也是刺最多最尖的。
她相信爱情本就该轰轰烈烈,就算不知道接下来要往哪走,起码以后回想起来是与众不同的。
刘小姐跟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最喜欢看先生抽烟。
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别人抽烟让她厌恶,而先生抽烟却让她着迷。
先生偶尔会俯下身来在刘小姐耳边轻轻呼出一口含着些许烟雾的气,不经意的动作磨得人魂牵梦绕。
他会蛊惑人心。
刘小姐说想学抽烟,可想而知地遭到了反对。
她问为什么,先生只用一句对身体不好打发了。
先生又问她怎么净喜欢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于是刘小姐就义正词严地列出了自己不喜欢的所有事物。
她不喜欢的东西真的很多,多到数都数不过来。
那会不会有一天,你连我也不喜欢了?
瞎说,我只喜欢你。
先生说,如果可以,他希望自己能死在战场上,因为那是离他的信仰最近的地方。
他不想一辈子靠头脑过活,时而日复一日,时而无所事事的生活早就把他的耐心磨尽了。
那些明枪暗箭,那些钩心斗角,统统都去一边吧!
他真正想做的,是拿起把枪。
先生死在了一九四九年的秋天。
枯黄的叶子落在他的头上、身上,是他浑身上下最显眼的颜色。
后来先生还是没能种下那片榆叶梅,甚至没能等到来年春夏交替,那花开得最好看的时候。
他没能如自己所希望的那般死在战场上,而他在这世上留下的最后一眼里,有参差不齐的瓦房,有黑压压的头顶,却唯独没有刘小姐的影子。
围观的人群散去后的场景,何其凄凉。
曾经那么爱干净的人,就这样散于秋风中,葬于泥土里。
刘小姐是真心想过嫁给先生,也相信先生是真心想过要娶自己回家。
***
一九五八年,黑山二十八,吾恙二十五。
吾恙她爹已经公私合营了自己的诊所,金圆券全部作废,成了每个月拿着八百块钱的闲人。
他起初还有些舍不得,那诊所可是他倾尽心力做起来的,说放手谈何容易?
可转念一想,这反倒是件好事。
毕竟单凭自己这几十年来积攒的丰厚家底,以及明显不及当年的身子骨,也到了该享享清福的时候了。
本想着能被自己闺女孝敬孝敬,可还没过几年,吾恙跟黑山这对夫妇就搬去了宁夏。
在这之前,吾恙可是位实打实的职业女性。
她嫁给黑山后离开了自己出生的城市,父亲随他搬到了长春。
作为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