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叙事体式与礼之关系考.docx
《《左传》叙事体式与礼之关系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左传》叙事体式与礼之关系考.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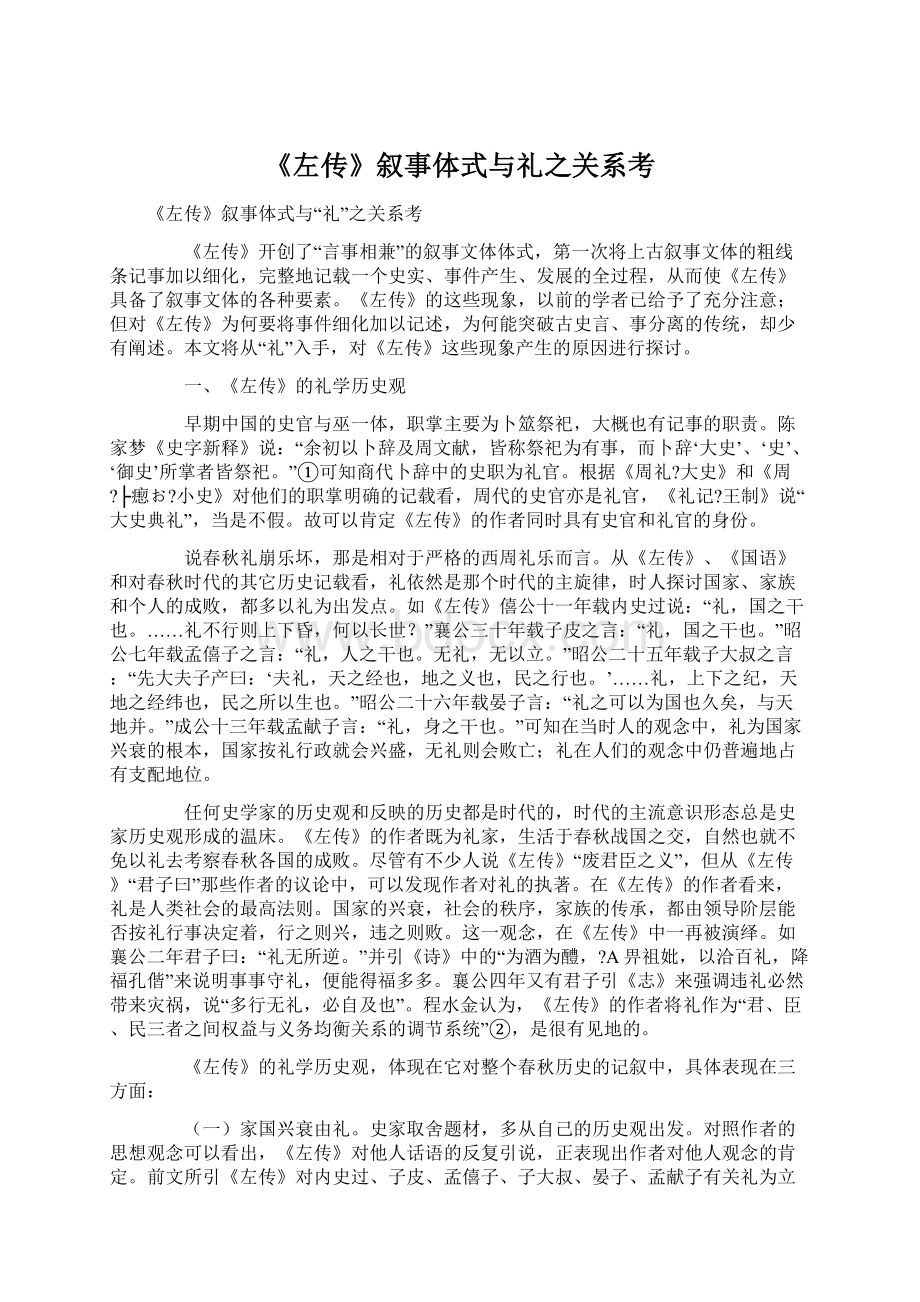
《左传》叙事体式与礼之关系考
《左传》叙事体式与“礼”之关系考
《左传》开创了“言事相兼”的叙事文体体式,第一次将上古叙事文体的粗线条记事加以细化,完整地记载一个史实、事件产生、发展的全过程,从而使《左传》具备了叙事文体的各种要素。
《左传》的这些现象,以前的学者已给予了充分注意;但对《左传》为何要将事件细化加以记述,为何能突破古史言、事分离的传统,却少有阐述。
本文将从“礼”入手,对《左传》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左传》的礼学历史观
早期中国的史官与巫一体,职掌主要为卜筮祭祀,大概也有记事的职责。
陈家梦《史字新释》说:
“余初以卜辞及周文献,皆称祭祀为有事,而卜辞‘大史’、‘史’、‘御史’所掌者皆祭祀。
”①可知商代卜辞中的史职为礼官。
根据《周礼?
大史》和《周?
├瘛お?
小史》对他们的职掌明确的记载看,周代的史官亦是礼官,《礼记?
王制》说“大史典礼”,当是不假。
故可以肯定《左传》的作者同时具有史官和礼官的身份。
说春秋礼崩乐坏,那是相对于严格的西周礼乐而言。
从《左传》、《国语》和对春秋时代的其它历史记载看,礼依然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时人探讨国家、家族和个人的成败,都多以礼为出发点。
如《左传》僖公十一年载内史过说:
“礼,国之干也。
……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襄公三十年载子皮之言:
“礼,国之干也。
”昭公七年载孟僖子之言:
“礼,人之干也。
无礼,无以立。
”昭公二十五年载子大叔之言:
“先大夫子产曰: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
”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言:
“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
”成公十三年载孟献子言:
“礼,身之干也。
”可知在当时人的观念中,礼为国家兴衰的根本,国家按礼行政就会兴盛,无礼则会败亡;礼在人们的观念中仍普遍地占有支配地位。
任何史学家的历史观和反映的历史都是时代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总是史家历史观形成的温床。
《左传》的作者既为礼家,生活于春秋战国之交,自然也就不免以礼去考察春秋各国的成败。
尽管有不少人说《左传》“废君臣之义”,但从《左传》“君子曰”那些作者的议论中,可以发现作者对礼的执著。
在《左传》的作者看来,礼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
国家的兴衰,社会的秩序,家族的传承,都由领导阶层能否按礼行事决定着,行之则兴,违之则败。
这一观念,在《左传》中一再被演绎。
如襄公二年君子曰:
“礼无所逆。
”并引《诗》中的“为酒为醴,?
A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偕”来说明事事守礼,便能得福多多。
襄公四年又有君子引《志》来强调违礼必然带来灾祸,说“多行无礼,必自及也”。
程水金认为,《左传》的作者将礼作为“君、臣、民三者之间权益与义务均衡关系的调节系统”②,是很有见地的。
《左传》的礼学历史观,体现在它对整个春秋历史的记叙中,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一)家国兴衰由礼。
史家取舍题材,多从自己的历史观出发。
对照作者的思想观念可以看出,《左传》对他人话语的反复引说,正表现出作者对他人观念的肯定。
前文所引《左传》对内史过、子皮、孟僖子、子大叔、晏子、孟献子有关礼为立国与立身根本的话语,已可看出《左传》以礼为历史的中心视点。
而《左传》所记各国具体的历史事件中,作者的这一历史观也贯穿始终。
如庄公十年载齐国灭谭,作者总结其原因说:
“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
”故齐师灭谭,过不在齐,而在“谭无礼”。
记宋昭公之败时,作者将所有的原因也都归于昭公无礼。
文公八年载,宋襄夫人借戴氏之族,杀宋昭公之党,作者认为其根源在昭公对宋襄夫人“不礼”。
文公十六年,“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也因为“昭公无道”而“宋公子鲍礼于国人”:
宋发生饥荒时,公子鲍“竭其粟”借给百姓,对老人“无不馈饴”,并“时加羞珍异”,尽事“国之才人”,极尽全力体恤亲属。
襄公七年,郑僖公被臣下弑杀。
作者记述道,郑僖公作太子时与子罕适晋,对子罕“不礼”;与子丰适楚,对子丰“不礼”;至其即位朝于晋时,又对子驷“不礼”,以至将一再进谏的侍者杀死。
作者通过这些记述,表明郑僖公灭亡的原因在于不以礼行事。
僖公十二年载:
“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
管仲辞曰:
‘臣,贱有司也。
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
陪臣敢辞。
’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
”作者认为管仲有礼,“让不忘其上”,因而“管氏之世祀也宜哉”。
谭之灭,宋昭公之败,郑僖公之死,管氏之世祀,其全部原因并非有礼、无礼一言可以尽之,但作者都将其归结于当事人无礼或有礼,这正见出作者守礼则兴、违礼则败的历史观。
(二)邦交和恶由礼。
春秋时代,诸侯相争,外交往来成为各国成败的一个极重要因素。
《左传》在记述各国历史的兴衰时,非常注重考察各国外交。
在记叙外交事件时,作者也将礼作为处理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则。
在隐公三年记载周郑交质后,作者以“君子曰”提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原则:
“明恕而行,要之以礼。
”认为国家之间一切按礼行事,也就不会发生争斗。
作者的这一观念,在《左传》中一再借他人之言表述着。
隐公六年郑伯前往京城朝见周王时,“周王不礼”。
作者记周桓公言于王曰:
“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
D;况不礼焉?
郑不来矣。
”认为即便是天子对于诸侯,也必须以礼相待。
僖公七年,鲁国与齐国盟于甯,商量讨伐郑国。
管仲对齐侯说:
“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
”齐侯于是修礼于诸侯。
郑伯使太子华听命于齐,对齐侯说,违背齐侯命令的是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并表示愿意以郑为内应,攻下三族。
齐侯将许之。
管仲曰:
“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
子父不奸之谓礼,守命共时之谓信。
违此二者,奸莫大焉。
”作者以肯定的态度记述这些,体现的正是他以礼作为邦国纽带的思想。
《左传》中触目可见的对所记事件的直接评说,则更加充分表现着作者的这一历史观。
隐公十一年,鲁与齐、郑伐许,许被占领。
郑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复奉其社稷。
作者赞扬道:
“郑庄公于是乎有礼”;“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隐公八年:
“齐人卒平宋、卫于郑。
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
”文公九年:
“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
`,礼也。
”文公十二年:
“?
J伯卒,?
J人立君。
大子以夫钟与?
J?
来奔,公以诸侯逆之,非礼也。
”宣公四年:
“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非礼也。
”如此等等,无不是作者的这一思想的表述。
(三)战争胜败由礼。
春秋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列国争斗多以战争的形式进行,故《左传》记战争的文字不少。
对战争的成败,作者注意到了双方力量的对比、民心的归向、外交手段和战争策略的运用,但也将礼的实践作为战争胜败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如记晋楚城濮之战,作者在僖公二十七年便交待晋选元帅?
S?
e,是因为?
S?
e“说礼乐而敦诗书”,并以倒叙的手法交待晋文公回国后采纳子犯的建议,教化国民“知义”、“知信”,“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
表扬晋以礼为政,民知礼义。
记楚帅子玉时,作者特借?
l贾之口,交待子玉“刚而无礼”。
僖公二十八年记战争过程,作者又借子犯再次交待“子玉无礼”,并记晋在先轸的“定人之谓礼。
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的劝说下答应子玉的要求,说明晋师有礼。
当曹、卫与楚断绝关系,子玉怒而追晋师,晋师退,军吏认为这是晋军的耻辱时,又记子犯说:
“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报也。
”示晋有礼。
当晋侯登有莘之虚观师时,又通过晋侯的话,交待晋军将士“少长有礼”。
显然,作者反复交待楚之无礼、晋军有礼,在于告诉人们,礼是战争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其它如记秦晋?
ブ?
战,作者一开始就借王孙满之口,交待“秦师轻而无礼”,又记先轸言“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将秦败的原因归于秦之“无礼”;郑宋大棘之战,宋师败绩,郑俘获华元、乐吕等二百五十人及甲车四百六十乘。
作者在寻找宋人失败的原因时,也将其归结于“失礼违命”。
政治、外交、战争与家族之间的争斗构成了春秋社会发展的历史,《左传》将其成败都归结到礼这一点,可知礼是作者考察历史的中心视点。
二、《左传》叙事的细化与礼
《左传》为《春秋》之传,但二者不仅历史观不同,而且记事方式也不同:
《春秋》简洁,《左传》繁细。
对《左传》与《春秋》叙事不同的原因,前人有过讨论。
杜预《春秋左传序》认为,原鲁《春秋》有违周礼,孔子“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曲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删原鲁《春秋》而成《春秋》。
似乎原鲁《春秋》文本繁杂,孔子删繁以寄礼法,故有孔子《春秋》之简洁。
《左传》的作者是史官,身份与孔子不同。
史官记事,必“广记而备言之”,“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故《左传》其文繁细。
杜预从《左传》为史的角度来说明《左传》文繁的原因,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没有涉及根本。
《左传》记事的繁细,主要表现为记事注重事情的过程和细节。
而注重事情的本末和细节,关键的原因还在作者的礼学历史观。
因为历史观是史家考察历史的原则和出发点,决定着史家记述历史的角度和方法。
当《左传》的作者将礼作为历史视点时,便会自觉地将礼作为标杆,以礼为参照去反映历史。
《左传》的礼学历史观,决定了《左传》的“以事明礼”。
据说孔子作《春秋》,是因为他认为礼“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深切著明”③。
故“以事明礼”比空谈礼义更能说明礼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当史家以“事”来为明“礼”服务时,礼也就在史的写作过程中获得了对叙事角度和方式的支配地位。
由于礼借人们的行事(礼仪)而得以表现,故《左传》记事也就自然会在极大的程度上以礼仪为参照;而作者对于礼仪过程的熟悉,也使得他熟练地把礼的礼仪表现形式引入《左传》的叙事。
礼是以细节的过程表现意义的。
礼源于原始宗教礼仪。
在原始宗教中,任何仪式都以一个完整的过程表现着,而这一过程又以众多的礼仪细节连结而成。
由于原始宗教的每一仪式都以表现特定的意义来达到特定的目的,意义与仪式混为一体,目的通过具体仪式而实现,因而,仪式与意义具有严格的对应性。
仪式的一定行为细节过程和物品的形态、数目、位置、色彩、高低等均表现一定的意义;仪式一定的行为细节构成和形态、数目、位置、色彩、高低的改变都会导致其过程的改变,而过程的改变又导致意义的改变。
因而,原始宗教仪式对所用物品、数目、摆放的位置、人的一举一动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
如纳西族祭天,要先念《祭天除秽》等四部经文除秽,然后由专门负责祭天事宜的两人在祭台的左边立天树(一黄栗木),右边立地树(一黄栗木),中间立一胜神之树(柏树)。
三棵树前要放九个“高鲁”(胜神之石),三个为一堆。
天树、地树前各插一根镇鬼的竹刺“勤”,中间的胜神之树前插一杆矛、一根顶灾木,在木石前供上酒饭。
杀猪献牲之前,东巴要端坐不动,前放一浅圆竹筐,内铺青松针,上放一“董鲁”(阳神之后)。
④在这祭天的仪式过程中,每一细节及物品都代表着一定的意义,如果少了任何一个细节或物品的数量等,仪式就不完整,就不能达到祭祀的目的。
因而,行为的细节和过程对原始宗教仪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周礼依据西周以前的宗教礼仪而制订。
所谓“周因于殷礼”,主要是指宗教礼仪。
周之三礼中,《仪礼》与《周礼》、《礼记》互为表里。
《礼记》是《周礼》的制度意义的伦理道德阐述,它们共同的意义为《仪礼》的本质,而《仪礼》则是《周礼》和《礼记》意义的行为实现。
秦蕙田《五礼通考》卷首第三写道,郑玄《礼序》云:
“礼也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
然则《周礼》为体,《仪礼》为履。
”所谓“《仪礼》为履”,即《仪礼》是《周礼》在生活中的细节实施。
尽管周礼与原始宗教礼仪有许多区别,但原始宗教一定的仪式与一定的意义的严格对应性却没有丝毫改变。
《论语?
子罕》载孔子言:
“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
”按礼,臣子朝见君主,应先在堂下磕头,升堂后再磕头;如果只在堂上磕一次头,少了在堂下先磕头这一过程,就不合礼,故孔子说“今拜乎上,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