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党员队伍发展的回顾与思考.docx
《大革命时期党员队伍发展的回顾与思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大革命时期党员队伍发展的回顾与思考.docx(3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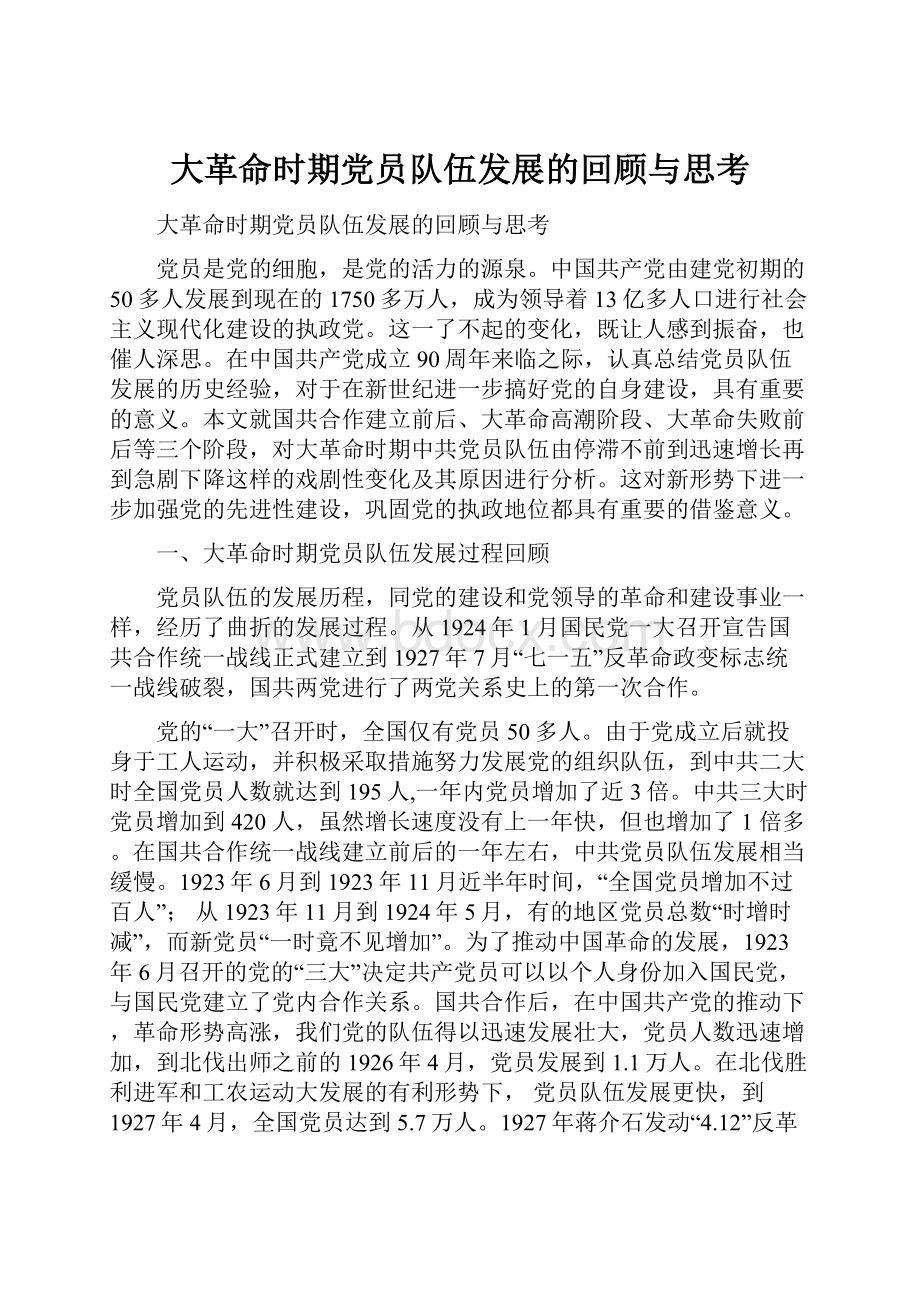
大革命时期党员队伍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大革命时期党员队伍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党员是党的细胞,是党的活力的源泉。
中国共产党由建党初期的5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1750多万人,成为领导着13亿多人口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
这一了不起的变化,既让人感到振奋,也催人深思。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来临之际,认真总结党员队伍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在新世纪进一步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就国共合作建立前后、大革命高潮阶段、大革命失败前后等三个阶段,对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队伍由停滞不前到迅速增长再到急剧下降这样的戏剧性变化及其原因进行分析。
这对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大革命时期党员队伍发展过程回顾
党员队伍的发展历程,同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一样,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从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宣告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到1927年7月“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标志统一战线破裂,国共两党进行了两党关系史上的第一次合作。
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党员50多人。
由于党成立后就投身于工人运动,并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发展党的组织队伍,到中共二大时全国党员人数就达到195人,一年内党员增加了近3倍。
中共三大时党员增加到420人,虽然增长速度没有上一年快,但也增加了1倍多。
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前后的一年左右,中共党员队伍发展相当缓慢。
1923年6月到1923年11月近半年时间,“全国党员增加不过百人”;从1923年11月到1924年5月,有的地区党员总数“时增时减”,而新党员“一时竟不见增加”。
为了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了党内合作关系。
国共合作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革命形势高涨,我们党的队伍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北伐出师之前的1926年4月,党员发展到1.1万人。
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大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党员队伍发展更快,到1927年4月,全国党员达到5.7万人。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7.15”反革命叛变,第一次大革命终于失败,党组织惨遭破坏,党员数量锐减到1万多人,党的组织转入秘密状态。
二、大革命时期党员队伍曲折发展的原因探析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前后中共党员队伍的缓慢发展及其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前后,中共党员队伍的发展速度异常缓慢,但并不是说这个时期中共党员的绝对数没有增加,而是相对于其前面的创建时期和其后面的大革命高潮时期的增长速度而言实在太缓慢了。
为什么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党员队伍的发展速度反而如此缓慢?
原因何在?
依据大量史料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过分看重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忽视中共的组织队伍建设,而这种态度又直接影响到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对发展自身组织队伍的认识。
在指导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过高地估计了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性和力量,根本瞧不起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陈独秀也认为:
“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很幼稚。
”中共三大通过的决议也明确指出:
“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国共合作建立后,为避免惹起国民党的反感,中共中央还进一步强调:
“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
”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错误思想左右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把帮助国民党发展各级组织作为党在当前的一件头等大事。
为了表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诚意,甚至要求全体党员要“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
以致在国共合作建立前后,生怕“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拉走他们的党员”,而不敢放手扩大自己的党员队伍。
第二,广大中共党员致力于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无暇顾及党的自身建设,是导致中共党员队伍发展缓慢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1923年1月,孙中山还邀请陈独秀、林伯渠等中共党人到国民党中央任职。
后来又任命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委员。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后,谭平山、李大钊又分别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由于中共方面的一些重要领导人被邀请到国民党里帮助国民党筹划改组,以致“党的工作”,包括组织队伍的发展工作“实际上做得很少”,甚至“什么也没有做”。
1924年1月,陈独秀、李大钊等23名中共党人参加了国民党一大,经过大会选举,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三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等七人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新成立的“八部一处”中央机构中,除谭平山、林伯渠分别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农民部部长外,还有不少中共党人在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秘书、干事等重要职务。
在国民党的一些地方执行部也有不少共产党人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
在国民党机构中任职的中共党人大部分本来就是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委员会的重要负责人,他们加入国民党尤其是在国民党中担任某种职务以后,就把改组国民党作为一项首要的“主业”,而积极努力地工作。
而他们却把在中共党内担负的重要工作当成了一种“副业”,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中共自身的建设。
比如,中共北京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在国共合作建立前后,他曾四赴上海,两下广州,积极帮助孙中山谋划改组事宜,同时还主持和参加了北京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再如,身为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的谭平山,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更是左右逢源,身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央执委会常委、秘书处成员等数职,日理万机,忙不胜忙。
中共全党上下积极响应党中央“只要有可能全体党员就要在各地帮助国民党的发展”的号召,全力以赴地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这就无形中把中共党员队伍的发展工作抛在脑后。
中共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国民党改组工作的结果,一方
面使国民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完善和扩大。
另一方面,由于广大中共党员忙于国民党改组,“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党内的组织生活极其散漫。
上海、汉口、山东等地的党组织都普遍存在忽视党的小组会议的现象,据1924年5月的上海地方报告称:
“上海以所有党员,划分五组”,“在最近一月来惟第一组开了三次会议,第二三组只开过一次会议;第四五组一次也没有开过。
”在汉口甚至还存在“忽视小组会议,故意不出席,甚至有成年不为党任事”的现象。
不少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只晓得自己是一个国民党员几乎忘了自己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整天忙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中共党内的活动大大减少,党的组织纪律极其涣散。
使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受到严重的影响。
想直接加入共产党的人自然就少了。
第三,全国工人运动处在低潮,党日渐脱离了与工人群众的联系。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全国的工会“大半封闭解散了,其未被封闭的也只得取守势”。
从1923年5月到1924年“五·一”节,全国共发生罢工36次,除湖南水口山工人和湘潭锰矿工人举行的二次罢工规模稍大一点外,其余的都是手工业工人举行的小规模罢工。
]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对革命前途十分悲观,他们对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的态度也都十分冷淡,甚至认为:
“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
”在这种消极思想指导下,就是那些想深入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组织工作的中共党员也失去了往日的热情。
在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汉口、长沙等地很多工会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消灭的被消灭,即没有消灭的也不过名存实亡”。
党的区委领导有的遭到通缉,有的被逮捕,还有不少党员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据统计,仅湖南水口山工人罢工失败后就有20来名党员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下落不明。
随着国民党组织的扩大,需要更多的中共党人去国民党的各级委员会工作,而中共党员又“一时实不见增加”,以至“做群众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忙于委员会工作的同志不可能腾出时间去做群众工作”,所以“我们同工人群众失去了某种直接的联系”。
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工作做得越少,工人运动开展的规模就越小,次数就越少。
工人运动开展得越少,失败的次数越多,工人群众的意志就越消沉,党与工人群众的关系就变得越疏远,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工人积极分子也就越少。
党的组织队伍的发展特别是在工人中的发展自然也就越缓慢。
第四,中共在发展党员时要求过于严格,堵塞了党员队伍发展
的入口。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
早在成立之初就力图按照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高标准来接收党员,认为那些“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
”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发展新党员的时候,提倡注重质量,避免单纯地追求党员数量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下发展党员时严格要求就更有必要。
但是,如果把党员标准定得太高,要求他们在入党前就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较强的组织宣传能力。
其结果,只会把一大批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拒之门外。
因为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相当落后。
而真正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一定工作能力的人并不多,提出这样高的要求实际上就等于关死了党组织的大门。
在国共合作建立前后,中共中央虽然多次强调:
“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于本党组织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
但同时又把党组织大门的门槛立得老高,强调“凡非对于本党主义策略及党之纪律充分明了,并恳切的愿意服务本党者,不必轻率加入。
”甚至错误地认为,只有“先经过民族民主的政党之政治训练,然后才可以加入无产阶级的政党”。
这样,就在中共党人纷纷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也把与他们有联系的工会会员及青年学生大批大批地介绍进了国民党。
使国民党的组织队伍得到迅速壮大,而中共自身
党员队伍的发展却停滞不前。
第五,中共活动经费的严重短缺也是制约党员队伍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一旦共产国际的经费不能按时到位,党的组织工作和其它各项工作就无法顺利开展。
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办公费用、交通费用以及生活开支也随之明显增加,但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活动经费依然只有1000金卢布。
尤其是鲍罗廷来华后,把一切工作的重心都集中在帮助国民党改组上,对中共的财政困难不闻不问。
由于中共“在10月、11月、12月都没有从共产国际执委会那里得到钱,而整整6个月没有从红色工会国际那里得到钱了。
”党的宣传组织工作都几乎陷入停顿状态。
从中共三大到三届一中全会,“《新青年》应出二期,只出一期;《前锋》应出五期只出一期;《向导》应出到四十九期,只出到四十六期”。
要想扩大党的队伍,就必须深入广泛地宣传、发动、组织群众,通过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不断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党的宣传工作一旦玩不转,党的组织发展工作自然就会大打折扣。
同时,由于缺乏经费,党内的一些日常工作也举步维艰,比如,一些专门从事党的工作的同志,本来薪水就不高,一旦连这点钱都不能到位的话,生了病都没钱医治。
再如,因中国地域广阔,从广州派一个人去一趟北京就得花一百块钱,如果拿不出钱的话,事情就办不成。
怪不得“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共产党员既“积极”又“满意”,因为这种工作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而且能够缓解他们经济上的困难。
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国际的经费提供仍旧时常出现延误数月的情况,仅中共中央在1924年1—6月收到的月平均经费数额与1923年11—12月收到的月平均经费数额相比就差不多少了一倍。
[68]由于经费不足,中共“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
进而使党“失去了许多有利的发展机会。
”
(二)、大革命高潮时期中共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加及其原因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高涨,党员人数迅猛增加,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前夕党员人数就由1925年初的不足1000人猛增到57967人,扩大近60倍。
党的组织几乎遍及全国,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区委就有8个,地委有6个。
大革命高潮时期党的组织队伍发展如此迅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共产国际,中共中央逐步认识到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性。
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和指导下,中共先后召开了第一次扩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使党的组织发展走出了停顿徘徊的局面。
经过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考验,全党进一步认识到壮大党的组织队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925年8月,维经斯基建议中共中央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依靠革命工人扩大党的队伍上。
”同年10月,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的中央执委会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提出,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担当起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任,“第一便是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知识阶级中革命分子。
”会议认为:
“共产党假使不能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发展和巩固,那么,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向前发展,简直无从设想。
”北伐战争开始后,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下,中共党员队伍的发展速度明显提高,但仍然远远不能适应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
各地都普遍存在“人材缺乏的饥荒。
”[76]为了迅速缓解党在领导农民群众、发展各级组织过程中存在的党员人数不足,人手不够,人才缺乏的压力,中共中央提出:
“党员数量上的增加,目前我们更应努力,必须是广大群众的党才能担负起这日愈艰巨的革命工作。
”1926年10月,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发出《给各级党部的信》,在信中他提议:
“我们党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党员应发展到四万以上。
”]并给各个地方党组织分配了具体的发展指标。
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
”由于中共中央一改过去的认识,把迅速增加党员数量当作党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来抓,党员队伍得到了迅速地扩大。
其次,群众运动的广泛开展推动了党员队伍的迅速壮大。
早在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就提出:
“在工人群众中吸收党员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
”并要求“赶紧组织工厂铁路等处的共产党支部”,以负责指导工会工作和组织工厂小组的工作。
在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罢工,罢工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这次“罢工工人当中有50多人加入了我们党(其中有3名妇女),并成立了两个支部。
”五卅运动中,中共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深入人心。
不少共产党员深入群众,积极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大大提高了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
这样,上海、广东等地的工人积极分子纷纷加入了党的组织。
到1925年10月止,中共党员人数迅速由四大时的994人增加到3000人。
其中,上海在“五卅”运动前仅有党员290人,“五卅”后即增加到785人,而新增加的工人党员就有679人,占总增加额的86%。
北伐军占领武汉和南昌后,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更是风起云涌,在全国总工会的直接领导下,全国工会会员迅速增加了20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的工会组织发展最快。
工会会员的增加为党的队伍的迅速壮大提供了重要来源。
随着工会会员的不断的增多,工人党员也随之增加。
中共四大时,工人党员人数还只占党员总数的50%多一点,到1926年1月,工人党员人数的比例就上升到70%;到1927年1月,工人党员所占的比例更高,达到75%。
到五大前夕,工人党员所占的比例仍达53.8%,使中共在工人阶级中奠定了自己的组织基础。
在大革命第一次高潮中,农民党员还非常少。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国共两党积极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农民协会会员剧增,从1926年7月到同年9月,短短二个月时间,仅湖南的农协会员就由20万人增加到30—40万人。
[87]到1927年1月,湖南农协会员又猛增到200万人。
其他各省的农协会员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随着农民协会会员的剧增,农民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也不断提高。
1926年5月,全党农民党员仅650人,只占党员总数的5%,2个月后就发展到1200人,占全党党员总数的10%,到1927年4月,农民党员又猛增到10840人,占党员总数的18.7%。
在农民运动中大力发展农民党员,极大地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这是中共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这一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一种尝试,也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
在大革命第一次高潮中,农民党员还非常少。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国共两党积极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农民协会会员剧增,从1926年7月到同年9月,短短二个月时间,仅湖南的农协会员就由20万人增加到30—40万人。
到1927年1月,湖南农协会员又猛增到200万人。
[88]其他各省的农协会员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随着农民协会会员的剧增,农民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也不断提高。
1926年5月,全党农民党员仅650人,只占党员总数的5%,2个月后就发展到1200人,占全党党员总数的10%,到1927年4月,农民党员又猛增到10840人,占党员总数的18.7%。
在农民运动中大力发展农民党员,极大地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这是中共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这一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一种尝试,也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
党在组织、领导青年运动时,也积极领导广大青年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和团组织。
由于大量吸收工人、农民加入党的组织,使知识分子党员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1926年11月,知识分子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下降到15.3%,但到中共五大前夕又有所回升,达到19.1%。
可见知识分子仍然是党的一个重要群众基础。
再次,进一步完善入党手续,放宽入党条件。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吸收更多的工人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中共四大将“三大”党章“有五人至十人以上均得成立一小组”的规定改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
同时改变了一些地方要求新党员在入党前要先入团的做法,规定“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多应该直接加入本党。
”]1925年8月31日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中共通告第五十三号》,重新规定介绍新党员的二个介绍人中只要有一个是正式党员即可,且不要求他一定要有半年以上的党龄。
《通告》还指出,各地的候补党员,凡在“五卅”运动中“能活动且诚实无过者,宜尽量缩短候补期”。
1925年10月,中共第二次扩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式决定缩短“候补期”,将“三大”以来党章规定的“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改为“工人农民候补期一月,知识分子三个月”,并明确提出:
“大产业工人,本是天然的共产党员,只要他们有阶级觉悟及忠于革命,便可加入,不必更有其他条件。
”这就改变了曾经一度过分强调入党条件,认为工人觉悟不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太低而不去积极争取的错误做法。
为了吸收更多的农民积极分子入党,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扩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
“农民加入我们的党,应以是否忠实而勇敢的为农民利益争斗为标准,不必问其有无宗法社会思想及迷信。
”这样就为广大农民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打开了方便之门。
(三)、大革命紧急时期党员人数急剧减少的原因
大革命失败前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及中共中央
无原则的妥协退让,加上中共的党内教育严重滞后,在敌人的进攻
下,党的各级组织纷纷遭到破坏。
党员人数由“五大”前后的近6万
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成为中共历史上党的组织所遭受破坏的程
度最大,党员人数减少最多、下降速度最快的历史时期。
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开始,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
后背叛革命,他们以“清党”为名,到处摧毁各种进步组织和革命团
体,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在这场血雨腥风中,中共的各
级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死在敌人
的屠刀之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下令查封一切工
会组织,逮捕屠杀工人领袖,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惨遭毒手,汪寿
华、赵世炎、张佐臣、杨培生、郭伯和等共产党员先后光荣牺牲。
继“四·一二”屠杀后,李济深在广州也发动了“四·一五”大屠杀。
他们包围、查封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等革命团体和
组织,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000多人,[151]其中被秘密杀害的
不计其数。
肖楚女、刘尔崧、熊雄、邓培、毕磊、李启汉等中共党
员都惨遭毒手。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的党徒还在南京、无锡、
宁厦、福州、厦门、汕头等地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蒋介
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政权后,立即成立“清党委员会”,并发布《通
缉共产党首要令》,开列了193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名单,
四处通令拿办。
这样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东南各省,几乎每天都有共
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的消息。
与蒋介石遥相呼应的北方反动军阀也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
命志士。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包围并袭击了北京东郊民巷苏
联驻北京大使馆,逮捕了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于4月28
日,将李大钊等20人秘密绞杀。
4月10日,张作霖还在天津杀害
革命志士10多人。
随着工农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国民党反动派压力的不断加强,国
民革命军内部一些仇视革命的反动军阀相继叛乱,疯狂屠杀共产党
员和革命群众。
1927年5月9日,四川军阀杨森率部进占宜昌,
强令解散宜昌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并大开杀戒。
随后,反
动军阀夏斗寅也于5月13日发表反共通电,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农协会员,有的被浇上洋油活活烧死,有的被烙铁烫死,有的被一
刀一刀地割死,手段极其残暴。
“在湖北总计这样死的同志在夏逆
叛变后达三四百人以上,连同死难的农民合计三千人以上”。
[152]
继夏斗寅叛变后,5月21日,许克祥又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枪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仅事变当天,就有100多名共产
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长沙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事变后,
许克祥等人又在长沙等地一连屠杀了七、八天。
湖南的湘潭、衡阳、
武冈等十几个地方都相继发生了反革命屠杀事件。
从5月21日到
6月10日,在湖南就有10000多人被杀害。
田波扬、杨昭植、贾
云吉、陈爱元等共产党员相继遇害。
湖南马日事变的枪声未停,朱
培德又开始在江西“礼送共产党”,驱赶甚至活埋共产党员。
1927年6月28日,何键在汉口发布反共宣言,派部队查封工会,并在
街头公然捕杀共产党员。
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进行“清党”,
第二天就在武汉附近的孔垄镇枪杀了20多名共产党员。
8月5日,
九江警备司令金汉鼎又枪杀了彭江等好几位共产党员。
在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以及北方反动军阀的屠杀政策下,
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相继遭到逮捕和屠杀。
据不完全统
计,1927年被逮捕和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国共有68760
人,仅被处决和被反动军队屠杀的就有37706人,其中江苏1836
人、广东7896人、湖南21353人、湖北1271人、江西513人、四
川1200人,其他各省人数不等。
另外还有一些特别记载,如,江
苏被杀的主要革命分子850人、广东被杀的革命领袖200人。
上述
人数还仅仅是报上登载的以及各个地方的济难会掌握而报告给全
国济难总会的数据,至于被秘密处决或被捕后未暴光的,还有在各
地暴动后被反动军队杀死或逃亡而无法统计的都不包括在内。
[153]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从维护自身
利益出发,极力维护统一战线而不惜牺牲中国工农群众的利益,在
其控制下的中共中央只好忠实地执行了妥协退让的方针。
结果一方
面助长了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另一方面使中共失去了工农群众的
大力支持。
这样,中共党组织遭受破坏的程度就越大,党员人数下
降的速度自然就更快。
早在“四·一二”政变前夕,随着江西战场的胜利,蒋介石集团
逐渐右倾,共产党受排挤打击的危险越来越严重。
共产国际及其代
表不去采取措施加强共产党的力量,反而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汪精卫
和唐生智等国民党军事将领身上,幻想以退让求团结。
一方面提出
蒋汪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