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光范墩子.docx
《灵光范墩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灵光范墩子.docx(3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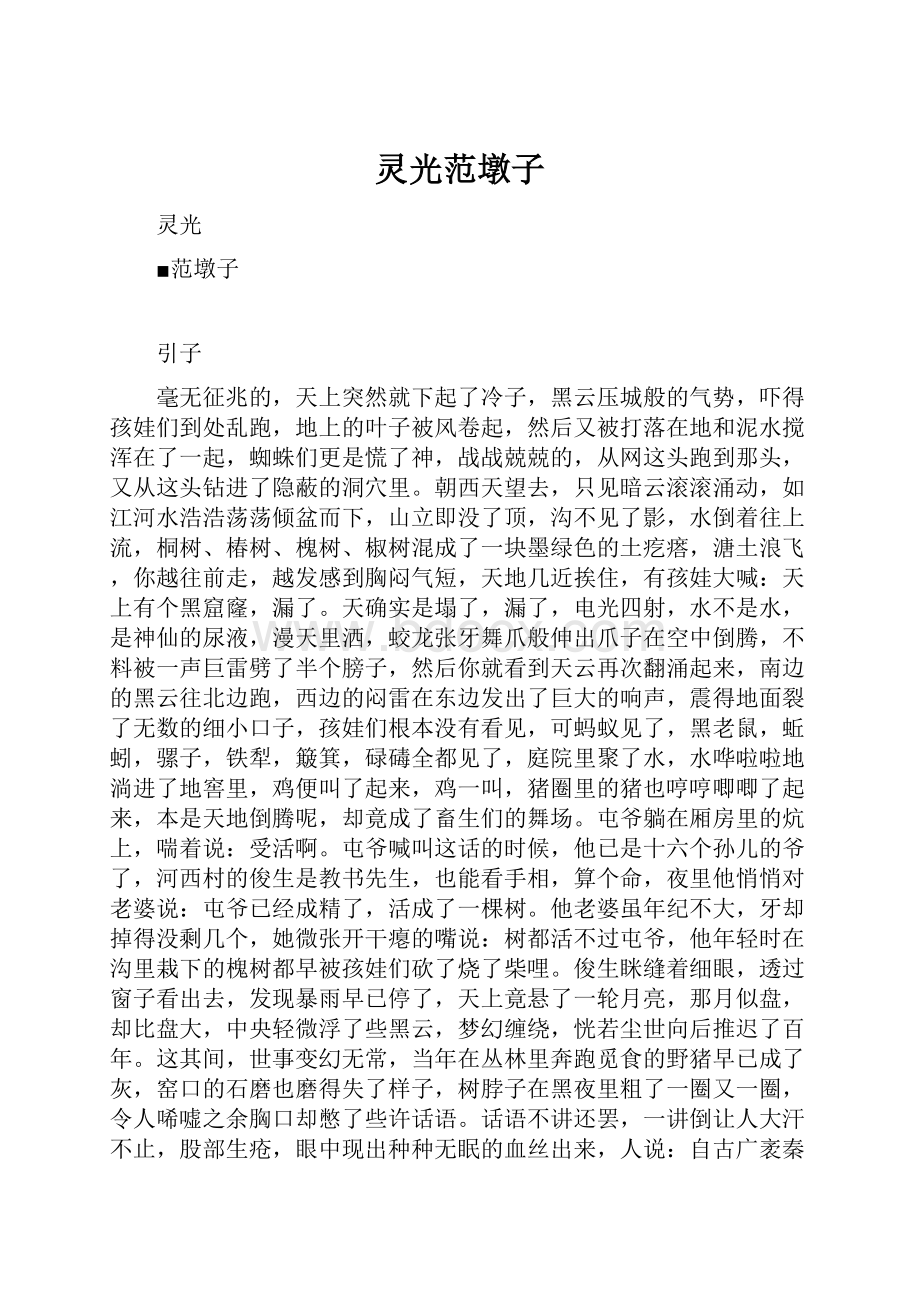
灵光范墩子
灵光
■范墩子
引子
毫无征兆的,天上突然就下起了冷子,黑云压城般的气势,吓得孩娃们到处乱跑,地上的叶子被风卷起,然后又被打落在地和泥水搅浑在了一起,蜘蛛们更是慌了神,战战兢兢的,从网这头跑到那头,又从这头钻进了隐蔽的洞穴里。
朝西天望去,只见暗云滚滚涌动,如江河水浩浩荡荡倾盆而下,山立即没了顶,沟不见了影,水倒着往上流,桐树、椿树、槐树、椒树混成了一块墨绿色的土疙瘩,溏土浪飞,你越往前走,越发感到胸闷气短,天地几近挨住,有孩娃大喊:
天上有个黑窟窿,漏了。
天确实是塌了,漏了,电光四射,水不是水,是神仙的尿液,漫天里洒,蛟龙张牙舞爪般伸出爪子在空中倒腾,不料被一声巨雷劈了半个膀子,然后你就看到天云再次翻涌起来,南边的黑云往北边跑,西边的闷雷在东边发出了巨大的响声,震得地面裂了无数的细小口子,孩娃们根本没有看见,可蚂蚁见了,黑老鼠,蚯蚓,骡子,铁犁,簸箕,碌碡全都见了,庭院里聚了水,水哗啦啦地淌进了地窖里,鸡便叫了起来,鸡一叫,猪圈里的猪也哼哼唧唧了起来,本是天地倒腾呢,却竟成了畜生们的舞场。
屯爷躺在厢房里的炕上,喘着说:
受活啊。
屯爷喊叫这话的时候,他已是十六个孙儿的爷了,河西村的俊生是教书先生,也能看手相,算个命,夜里他悄悄对老婆说:
屯爷已经成精了,活成了一棵树。
他老婆虽年纪不大,牙却掉得没剩几个,她微张开干瘪的嘴说:
树都活不过屯爷,他年轻时在沟里栽下的槐树都早被孩娃们砍了烧了柴哩。
俊生眯缝着细眼,透过窗子看出去,发现暴雨早已停了,天上竟悬了一轮月亮,那月似盘,却比盘大,中央轻微浮了些黑云,梦幻缠绕,恍若尘世向后推迟了百年。
这其间,世事变幻无常,当年在丛林里奔跑觅食的野猪早已成了灰,窑口的石磨也磨得失了样子,树脖子在黑夜里粗了一圈又一圈,令人唏嘘之余胸口却憋了些许话语。
话语不讲还罢,一讲倒让人大汗不止,股部生疮,眼中现出种种无眠的血丝出来,人说:
自古广袤秦川盛出英杰,海碗赛锅口,面比腰带长,但何以轮你胡拉裘乱扯?
言此,屯爷颤着身,拿起炕上的鬃刷,从屋里出来,双腿一弯,坐在了院子里的台阶上,他那右边豁着气的半个耳朵,萎缩成了一团肉疙瘩,显得极为丑陋突兀,但那天屯爷的心情着实不错,他嘴里叼着烟锅,烟锅下面掉着烟袋儿,不时地,烟锅中冒出几丝烟气,那烟抽的不似孩娃们抽的那般急,响亮,而是不响不亮,动作极为缓慢悠长。
人说:
这烟抽的不是烟,是世事,是境界。
屯爷睁开左眼,右眼依旧紧闭,道:
这孙儿倒会说,嘴儿灵哩。
这孙儿见屯爷如此说他,心中不禁大喜,竟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孙儿说,屯爷,我能否讲与旁人听?
屯爷紧抽一口烟锅,片刻后,鼻子里,嘴里皆喷出了形态规则的烟圈,他来回品咂几口,左眼盯住孙儿上下瞅了几眼,接着说:
本来带进墓子呀,你这孩娃却非要讲给旁人听,倒也无所谓了。
孙儿闻此言,立即向屯爷跪了下来,连磕了七七四十九个响头后,面色突然变得土黄,沧桑了几分。
屯爷从嘴里拔出烟锅,攥在手里,然后看天,天上一片蔚蓝,见不到一丝的云朵,朗朗明空,浩瀚无垠,秦朝的天也是唐朝的天,唐朝的天,却也飘过汉朝的云。
屯爷九十有几,心中虽隐隐发颤,面色却静得像村后的庙山,处在缭绕香火中,没有丝毫的波澜。
屯爷说,暴雨后必是岑寂,寂过了,又是暴雨啊。
孙儿说,不懂。
屯爷说,镜子里有青蛙,青蛙的前世就是皇帝啊。
孙儿说,还是不懂。
屯爷笑骂着说,球!
你要懂了,爷就白活了。
孙儿不语,却抓住屯爷的白胡子耍,耍着耍着,就扯断了屯爷的一根白胡子,屯爷盯着孙儿笑,孙儿不解,拿起胡子便问,屯爷,这不是胡子,是银线。
屯爷说,终究是一股烟。
说毕,长嘘了一口气,回到了土屋里。
后来,当那孙儿长大回想这一切的时候,竟发现那一日是屯爷在河西村的最后一天。
孙儿再也无法忍住,抱住门前的桐树失声痛哭了起来。
屯爷离开河西村时,天色尚早,晨露落在草尖儿上打湿了行人的裤腿,屯爷上了一辆锃亮的黑色小车。
门口的桐树哗啦啦地摇响,但却没有一片叶子落下来,暗暗的光影中,能够看见屯爷的双手微微在颤抖,上车时,屯爷并未掉眼泪,却突然迈过步子,绕到那棵桐树跟前摸了一把。
与此同时,那个给屯爷磕了七七四十九个响头的孙儿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见了一条青色的大蟒蛇缠住了他孱弱的身体,大蟒蛇力气很大,他根本无法挣脱开来,他说:
大蟒蛇,你要作甚?
大蟒蛇将头拧了过来,看着他说:
你知道的太多了,却没告诉一个人。
孙儿瞬间被吓得面色如土,表情凝滞,他说:
我正准备写呀。
大蟒蛇却不理会他的话语,而以更大的力气勒他,他吓得一下子端坐在了炕上,大汗淋漓,神色暗淡。
这孙儿冥冥中感到,自己身上担负着某种神圣的使命,他觉得应该把他知道的全写出来,不然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灾难,尽管他明白,其实他知道的很少。
屯爷去了城里,接他去的是他的孩娃们,孩娃们出息了,干了大事,接他去城里享几年福。
然而屯爷万万没有想到,去了城里不久便出了事,那日,他在街上乱走,他那缺了半个的豁耳,引来不少行人的注视,但屯爷丝毫未感到一点不快,他佝偻着腰身,双手背在后面,脑子里不知在想些什么东西,他的眼神迷离,街面上稠密的人流让他有种恐怖的情绪,他隐隐想起,当年能见到这么多的人,还是在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哩,狗日的鬼子啊,屯爷牙齿咬得咯嘣嘣响,他似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走在街上,稍不留神,可能就被鬼子的枪给崩了,那时天气冷,就是夏天他都经常穿着褂子,他试图想起曾经咬掉他半个耳朵的那个日本鬼子的模样,然而任凭他怎么想,都是无法想起来。
是我老了吗?
屯爷在心里自己问自己。
瓦罐,木镰,胡基,马场等等这些东西,他现在就能想得起来,也正是因为他的走神,以至让他忽略了他此刻是走在城市里的大街上,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绣成的肉疙瘩,屯爷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在他眼里,城市可能就是放大了的河西村,隔几步就能看见东河水里的蛤蟆,水蛇,鳖鱼,抬眼就能看见蹲坐西边那体型俊朗巍峨的娄敬山。
很多人在看屯爷,那些热辣的眼睛都藏匿在雾霾深处,细细打量,虽与自身无关,却看了个热闹。
屯爷右边的半个豁耳便是热闹。
当年,云雨比金子还值钱的时候,他常常立在沟岔上,看着面前纵横蜿蜒的沟坎,狼就在里面活动呢,但那时他着实胆大,背着一把弯刀,上坡下沟,爬崖走壁,人比长虫还简麻,半崖上的土裂了几指深的口子,谁家的毛驴儿还在那棵槐树下面安静地窝着,不声不响,然而他胸中郁闷万分,心想着狗日的老天真是不下一滴水了?
他脚下一甩,就将一堆土坷垃踢进了万丈深沟,大喊:
雨云!
不久,沟对面也传来方才的喊音:
雨云!
这一声雨云,叫得猛烈,呛得他喉咙哽咽,眼里竟涌出两股晶莹的眼泪。
屯爷沉浸在记忆中,将他身边的事物忘了个干干净净,似乎时间在他身上,未曾往前流淌,一直停在那个被战火塞严了的年代。
可毕竟现在是在城市里,正因他连绵不断的走神,以致始终没看路,路上是否有汽车,电车,屯爷一概不知,无意识地,他在一个漆黑的下水道跟前突然绊了一脚,这一脚可绊得不轻,躺在地上,瞬间便体无知觉。
街上车水马龙,商人,公务员,环卫工人,打工仔都在人流里混着,人们过过往往,皆往躺在地上的屯爷看,这样一个缺了半个耳朵的白胡子老人,谁能看清他的身世呢,有人说:
一看都是个江湖骗子,老家伙家里说不定盖了五层的小洋楼呢。
人们的眼神恶毒而狡诈,无不发出莹莹的绿光,有人又在地上擤了鼻涕,有人往地上吐痰,虽是光鲜的城市,黑污的地面却暴露了它真实的文明程度。
这时,一位蓬头垢面形似叫花子的汉子瘸着双腿跑了过来,他一跑,身体一高一低,一起一浮,活像只蠢笨的鸭子。
汉子说:
人都摔得没模样了,还没人救?
!
不想他刚说毕此话,更多的眼光朝着他射了过来,射得他全身发痒,一身的不自在,他二话不说,蹲下,再将屯爷扶起,背在了身上,然后一瘸一拐地朝着市医院的方向走了过去,他和屯爷的身影在人们的视野里渐渐变小,直至消失在了街巷的尽头。
几个时辰后,屯爷的孩娃们基本上都到场了,孩娃们脸色都不好看,黄里带黑,像生吃了几斤的生姜。
见屯爷迟迟未醒,过了片刻,医室凝固了的气氛终于被一声响亮的哭声给打破了,再接着,又一个孩娃哭了,两股长泪看得那瘸腿汉子都动了情,掉了眼泪,最后,孩娃们都认为屯爷是死了。
爸啊!
爷啊!
哭声终于在逼仄的空间里散涌了开来,将整个屋子占得严严实实,孩娃们看着屯爷那干瘦的手掌,心里无不动容,惶惶然如被抽走了魂魄。
正在孩娃们恸哭欲绝的时候,屯爷却缓缓睁开了眼睛。
爸!
爷!
老爷!
叫爸的和叫爷的声音响成一片。
那写书的孙儿呢?
屯爷的声音小得几乎没有人能听清。
啥?
孩娃们齐问到。
孙儿……写书……
说毕,屯爷的双眼永远紧紧地闭上了。
彼时,屯爷嘴里所说的那后生正在沟里放羊,他年纪尚小,连加减乘除都算不清楚,他见西天聚了一堆黑沉的云疙瘩,似神毯,又似内部藏了怪兽,来回翻腾。
这孙儿冥冥中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但又猜不出到底是什么,他一屁股蹲坐在了地上,荒草,酸枣树将他围困住,他心间一发潮,一股眼泪竟涌了出来,他并不知道屯爷死了的事。
十五年后,当他第一次听到屯爷的死讯时,屯爷的坟冢上早已被荒草盖实了,两棵长势凶猛的柏树像两位身姿矫健的将军一样站在一旁,这十五年间,他先后走出了镇子,县城,上大学时还出了省,屯爷在他的心里一直活着,比活佛还要俊朗。
求学归来,他才意识到时间竟然一下子向前跨越了十五年,心中淤积的愁苦情绪再也无法控制得住,夜里他孤身一人去了屯爷的荒冢跟前,抱住那棵柏树连哭带嚎,天被哭阴了,月亮被哭残了,树叶被哭落了,哭了三天三夜之后,他终于在某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拿出了一沓白净的纸张,他烧了几张扔在屯爷的坟头上说:
爷,我写呀,好不好你在天上都别骂我。
说毕,两股热泪糊了他的眼,他又想起以前蹲坐在屯爷跟前听他讲故事的场景,那时他虽年纪小,记性却不差,模模糊糊记了一些残缺的片段。
他跪在了屯爷的坟跟前,连磕了三个响头后就走了。
那时,山沟里万籁俱寂,没有一丝生息,月亮悬在半空,似有种神意冥冥在山野里徜徉,不远处,隐隐能够看到一团蓝火,那火不似柴火那般耀眼,也不似灯火那般亮堂,微微弱弱,在沟里晃动。
等这孙儿正要从沟里上来回到村子里时,一颗明亮的流星从空中划过,落在了天的尽头。
这孙儿抬头便喊:
屯爷!
是屯爷!
那时候,屯爷当然不能称为爷,他官名叫万有屯,小名叫屯娃。
屯娃出生后的几年,天下大旱,种下的庄稼还未成熟就已干死在了地里,眼见收成无望,河西村的走川立在东家的地畔上,聋拉着瘦弱的身体,虽心急如焚,却没有一点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即将黄了的麦子渐渐干成了一堆草,数月的暴晒,土地几近成为一块烙铁,将鸡蛋打碎扔在地上,不一会儿就煎成了熟鸡蛋。
隔几日,村里已有人提前割了麦子备下来年当柴火烧,走川便迈着碎步子往家里跑,他刚跑进屋时,看见他的孙子屯娃正和万景义的小女儿朵棉在院子的桐树下面踢鸡毛毽子,他擦了擦额上的黑水,又将手放在被汗浸透了的黑裤子上揉搓了几下,他走上前去,捏着孙儿屯娃的脸蛋说:
你爹呢?
屯娃转过来说:
在后院提水呢。
朵棉突然咯咯笑了,走川说:
大小姐,你笑啥?
朵棉说:
爷,你脸上的黑水都干成条条了。
走川便马马虎虎用袖子擦了擦脸,然后就进了内屋,刚掀开门,见万景义正与其妻蓝氏搂抱在一起,他咳了一声,说:
老爷。
万景义被走川的叫声吓得不轻,他见走川已站在屋里,便立即放开了蓝氏,然后很平静地扯了扯衣裤说:
怎么了?
走川说:
老爷,麦都干死在了地里,别家都去收了,咱收不?
万景义端起桌子上的茶杯喝了口水,说:
现在几月了。
走川说:
六月了。
万景义沉着脸说:
收了烧柴吧,收毕了你跟春连再把地一犁吧,这鬼天真是不让人活了。
走川回到后院里,将镰从墙橛上取下来放在磨石上磨,热辣辣的阳光落在地面上,尘土浪飘,在空中形成一层虚幻的气流,若隐若现。
万家后院宽敞亮堂,挨东墙的地方有口窖,窖边因为长期湿漉漉的缘故而长满了绿色的青苔。
春连正从窖里往出提水,见他爹走川进来磨镰,便说:
爹,老爷让收了?
走川说:
明儿个咱爷俩先把麦收了,后头再把地犁了。
春连将满满一桶水倒进瓦瓮里,水流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犁地那日,太阳比往常还要毒,射出的光线很快就转化成了溽热的气流,打在人身上,比扎针还要难受。
坡地本来就不均匀,都是先人开垦的,野草到处都是,走川和春连拉着家里的驴去了地里,走川带着草帽站在地畔上说:
可惜了一料麦啊。
春连一边给驴套上犁,一边抬起身说:
说不定过几天就下雨呀。
地面上散乱着遗落了不少的麦秸,橙黄的颜色与旷野融成了一体,走川在前面牵着驴,春连则跟在驴后面掌握着铁犁的方向,因为地皮太干、太硬,他的双臂使足了劲儿按住犁,驴走得很吃力,不一会儿,身上便渗出了细密的汗水,春连的衣服也早湿透了。
走川在前面喊:
连,要不停下歇歇吧?
春连闷着头,久没吱声,犁过了一行后说:
再拉几行吧。
但走了几步,中间的地越来越干,驴的步子渐渐慢了下来,见此,春连的心一急,就在驴屁股上狠狠踹了两脚,这两脚下去,驴只是浑身颤了颤,还抖落下来了不少汗滴。
走川说:
驴都累了。
春连双臂使劲将犁往下压,希望能将地下深层的干土给翻上来,但驴却干脆止步不走了,他一怒之下,连将驴踢了四脚,最后一脚竟端端地踢在了那驴掉在裆部的长鞭上,驴一下子就精了,精了的驴挣脱开了走川手里的缰绳,在地头来回跑了几圈后,带着铁犁径直朝着春连跑了过去,那只坚硬的右蹄就踩在了春连的腿上,铁犁砸在了他的脑袋上,脑浆都被砸了出来。
走川一下子就瘫软在了地里,他口里大喊着:
连!
连!
连!
喊着喊着,就喊出了一脸的泪花,片刻,他脑子里一片空白,昏倒在了地里。
几只黑老鸹就从远处的桐树上飞了过来,在地上空盘旋了几圈后,拉下了几滴白花花的屎,旷野大,很快屎就没了臭味道,远看过去,竟成了一道黄白相间的风景,有滴屎落在了春连的额颅上,走川灵醒过来后,刚落下时的稀屎已被太阳光晒干在了春连的脸上。
春连的眼睛睁得很大,圆溜溜的,很显然受了不小的惊吓,走川颤着手扶住春连的脸,又将手指放在春连的鼻子上顿了数秒,他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痛,大声地哭了出来:
连!
连!
我的儿啊!
河西村东头有条沟,沟很深,向南一直延伸了过去,尽头是哪里,村里谁都不清楚,沟底有条不宽的河,河边到处都是泥石头,挪开泥石,会发现不少的虫子,偶尔还能见到蝎子哩。
春连被驴踢死后,其妻兰花,在沟里到处哭喊,屯娃跟在娘的屁股后面,拽住他娘的衣襟说:
娘,你喊啥哩?
他娘转过身看着屯娃水灵的五官,心中更加悲恸了起来,一串晶莹的泪花就从眼眶里刷刷地淌了下来。
屯娃见娘哭了,心里也难受,他哭着鼻子说:
娘,你咋了?
他娘说:
我儿别哭,娘好着哩,好着哩!
说毕,眼泪比之前的还多,还汹涌。
兰花接着往前走,一直走到春连被驴踢死的坡地上,她的喊声拉得更长了,更匀了:
春连……春连却不在了,他的魂儿散落在了沟里,地畔上的那棵槐树上钻了一窝土蜂,嗡嗡叫的声音不绝于耳,兰花于是朝着槐树喊:
春连……娘的声音拉得太长,听得屯娃心里慎得慌,他又抬头问娘:
娘,你喊啥呢?
他娘拧过身子说:
给你爹喊魂呢。
数年过后,当屯娃长成一个健壮的小伙时,他那时才明白了喊魂的意思,然而当娘眼泪汪汪的告诉他给爹喊魂时,他却听得一脸糊涂,完全不知娘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时,虽久未下雨,天干地燥,树木都被太阳抽走了魂儿,到处都是一幅没有气力的病怏怏之态,杂乱的树丛中偶有野猪活动,有砍柴归来的人还说见到了狼哩,村里的高德老汉却说:
这年代,人都皮包骨了,狼早被饿成一堆土了,哪里还能有狼?
可偏偏屯娃就遇到了狼,那是在他爹春连死后的第三年,他和朵棉在沟里的杏树林里玩耍,他俩一会儿藏在塄坎下面,一会儿又躲在杏树背后,蝴蝶在草丛上飞来飞去,他俩就开始追呀追呀,追到林子边缘时,他俩瞬间就愣了,一匹野狼伸着舌头立在了他俩面前,干瘦的身体丝毫没有掩藏住那魁壮的体型,屯娃让朵棉站在他的身后,朵棉吓得腿都软了,嘴唇乌青,眼泪就绷在眼眶边儿上,那匹狼一直立着,屯娃感觉自己几乎听到了野狼呼吸的声音,他心里其实也害怕极了,但那时他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让他愣愣地站在了野狼的面前,野狼的眼睛浑圆,在阳光下面泛出一层闪亮的绿光,那眼神既让他恍恍惚惚,又让他感到熟悉,他心中疑惑万分,好像在哪里见过,是如此熟悉的神光,是爹?
!
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轻轻喊:
爹?
那匹野狼竟微微晃了晃脑袋,然后眼角流下了一滴眼泪。
狼转身走了。
朵棉压住胸脯长叹了一口气,他对着屯娃说:
那狼咋没吃咱俩?
我以为我们就要死了。
屯娃红着眼睛说:
我爹。
朵棉说:
啥?
屯娃摇摇头便下了沟,回去了。
屯娃遇狼的消息被他娘知道后,他娘再也不让屯娃去沟里,她紧紧抱着屯娃说:
你爹死了,你要是出个啥事让娘咋活呀?
屯娃抬起头看着娘说:
娘,我不会有事的。
他娘轻轻捏住屯娃的脸,眼泪却汹涌了出来。
春连被驴踢死后,她就没有睡过好觉,天天夜里总是噩梦连连,梦里总会浮现出春连的背影,在一棵大槐树背后,她隐隐看见春连站在树背后,树影被太阳晃得闪闪烁烁,四周的空气比远山还要绵长,她愣了下神,然后赶紧跑过去,嘴里还边跑边喊:
春连!
春连!
跑到大槐树背后,却发现什么都没有,只有几只蚂蚁在地上慌慌张张地搬运一只死了的苍蝇尸体。
她赶紧坐起来,夜色虽黑漆漆一片,但她那苍白的脸色还是无法被覆盖,从屋顶往下看,似有某种白光在闪烁,那段日子,她神情恍惚,脑子动不动就停止了转动,愣愣地盯着一堵土墙看,墙头上的蒿草在风中微微摆动,若不是屯娃将他遇狼的消息带回来,她可能还会沉浸在过度的悲伤中。
走川敲敲她屋子的门说:
兰花啊,人就是一坨土,念想了,就去沟里看看,屯娃还小,你可别哭伤了身子啊。
说这话时,走川心里更是悲痛万分,他就春连这么一个儿,敦厚勤快,平日里也没个啥坏心眼,年纪轻轻地就走了,他想起、春连小时候拉住他裤腿的样子,一股浊泪便从布满皱纹的眼眶中涌了出来。
从此,每天清早,天刚麻麻亮,就能见到走川扛着镢头去沟里挖地的身影,他一到沟里,站在地头往远处眺望,仿佛远处的那一朵朵的疙瘩云就是春连的魂儿,飘啊飘啊,他的心里一阵阵酸,年轻时,他爹让他多生几个儿,要保住家里的香火,他对爹说,等春连长大了再要吧,可刚过一年多,他的婆娘却在沟崖上挖药时不慎滚落了下来,当场就摔死了,这以后,他一直守着春连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春连成人后,因为家太穷,说不下媳妇,等结婚的时候,已经快三十了,兰花生下屯娃的那天,他躲在灶房里偷偷地抹眼泪,用拳头使劲在胸口上砸,他说:
爹啊,这下好了,香火续上了,你不会恨我了吧?
!
可谁知道,屯娃还没长大,春连却走了,白发人送黑人,一想,他的心里便如刀割一般。
他卯足劲儿,狠狠地,一镢头挖了下去,用力微抬镢把,再提起镢头,狠狠地,又是一下,他边挖边哭,边哭边唱,西边的疙瘩云就散开了,散成了一片一片,一朵一朵,从东边浮过来,又从西边浮过去,而他在沟坡上挖下的每一镢头,猛看过去,如同地皮上裂开了一条一条的伤疤,淌着黑血。
沟里的草很盛,绿得快能拧出水来。
走川一直立在坡上挖,他每挖一镢头,头顶便有鸟雀飞过,留下空灵的鸣音,那鸣音,与他的哭喊声交织一起,便显得空旷了许多,壮烈了几分。
万景义是在春连死后三个月的一个晚上进了兰花的屋。
他是河西村最大的财东,家有良田上百亩,女人当然也不缺,他一共娶了六个老婆,死了四个,人都说他命硬,克女人,女人要是被他上了身,不死掉也得半身残废,当然这话有夸张的成分,要是那个样子,那剩下的两个女人咋还活得好好的呢?
他第四个死了的女人珍珍是被他亲手用鞭子抽死的。
那年他刚三十岁,娶上了第六房的女人,这女人说是女娃可能更合适点,嫁过来的时候才刚满十六岁,她是邻村张贫生的女子,她爹张贫生本是不愿意将女儿嫁到万家的,可家里实在是揭不开了锅,穷得吃了上顿就没了下顿,还欠了东家不少的钱。
万景义还是在后山里屙屎的时候第一次看见了珍珍,当日的天气确实不错,珍珍提着粪笼在麦地里挖荠菜,走到地畔的时候,却发现有人正在塄坎下面屙屎,不禁发出了啊的一声,万景义也被吓了一跳。
但当他看见珍珍的模样时,内心一下就欢喜了起来,他在心里暗暗骂道:
妈个X,娶了五个老婆都长了个猪模样么!
这地方还有这等美人儿呢!
他股子都没擦就将裤子提了起来,说:
你是哪个村的?
珍珍因第一次看见男的屙屎,羞得脸红到了脖子根,她不想回答万景义,准备转身就走,却不想万景义一步跨到珍珍的跟前拉住了她的胳膊,她慌张地说:
你想干啥?
万景义嘴歪向一侧说:
哟,性子蛮烈的嘛!
见别人如此调戏她,珍珍不禁愤怒了起来,猛地将万景义推开骂了句:
流氓!
然后转过身就跑回了家。
谁知她却忘了带粪笼,这样一来,万景义便提着她的粪笼去了她们村,打听了几户就找到了珍珍的家。
张贫生知道万景义的心思后,出于无奈,两周后就将珍珍嫁到了万家。
珍珍嫁给万家的那日,张贫生和他婆娘一直没露面,他婆娘坐在灶房里,边哭边骂,骂她怎么嫁给了这么个窝囊废,骂张贫生是狗日的,把女儿送给狼了,你没看那万景义是啥人?
他都娶了五个老婆了还不知足,他长得是驴球啊!
张贫生赶忙捂住他婆娘的嘴,说:
你声音小点行不行?
被万家听见了,珍珍可就遭罪了!
他婆娘的眼泪却越来越多,她的哭喊声被张贫生捂住了,她就开始咬,一直将张贫生的手咬出了血。
然而张贫生和他婆娘万万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万景义用鞭子竟抽死了珍珍,那日,万景义因为太高兴自己娶了个漂亮的少女,就和村人放开了喝,最后喝了个酩酊大醉,入夜,月亮升起时,前来道喜的街坊才散了去,万景义摇摇晃晃地进了屋,却看见珍珍瑟缩在床的一角,便说:
不高兴?
珍珍没有说话。
万景义又说:
嫁给我万家是你的福。
说着就往床边靠,一把抓住了珍珍的腿,珍珍吓得面色如土,嘴唇乌青,用力将腿往后拽,不想她越拽万景义越是用力,最后竟一下将珍珍的裤子拽了下来,万景义醉得一塌糊涂,见到珍珍白皙的腿,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然后猛兽般扑向了珍珍的身上,将珍珍的衣服全撕扯了开来,他掏出自己裆里那东西就往珍珍身上蹭,珍珍早已吓得昏死了过去,体无知觉了,做毕那事,万景义的怒火一下子就窜了上来。
他知道珍珍只有十六岁,是处女,可珍珍下身竟没流出一滴血,万景义只觉得脑袋发胀,沉默了片刻后,下床找来了吆驴的鞭子,照着珍珍的下身就是一鞭子,珍珍的身上立即就有了一条血红的印子,她醒了过来,只是哭,眼泪如两股小溪往下淌,万景义借着酒劲却抽得越发凶狠,鞭子抽得越来越猛,珍珍的腿上,胸上,脸上,被整整抽了半个钟头,等万景义的胳膊感到酸痛时,他终于扔下了鞭子,这时,珍珍早已没了气息。
他的第六个老婆就这么被活活给抽死了。
张贫生的婆娘听闻女儿被万景义用驴鞭子抽死的消息后,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痛,哭喊着要去杀了万景义。
当时她正端着簸箕择豆子,村里的三朵急匆匆地跑进她屋,她说:
三朵,咋了?
三朵说:
婶,不好了。
她说:
啥不好了?
三朵说:
珍珍被万景义用鞭子抽死了。
张贫生的婆娘当场就晕了过去,片刻后,她一醒来就哭着要去杀了万景义,却被刚挖地回来的张贫生拦住了。
张贫生说:
狗日的!
狗日的啊!
说着他一镢头下去就砸碎了装有柿子的瓦瓮,张贫生的婆娘见张贫生只是哭,就去屋子里提了菜刀撵去了万景义的家。
万景义刚刚睡醒,他记起昨晚的事情后,心中虽觉得难受,但还是装作若无其事,他见张贫生的婆娘怒冲冲地跑了进来,说:
丈母娘来啦,走川!
快上茶!
张贫生的婆娘一口唾沫唾在地上,骂道:
上你娘的X!
你个狗日的,我今天要杀了你!
说着就拿起菜刀向万景义冲了过去,不想万景义早张贫生婆娘一步,一脚踢在了她的腿上,张贫生的婆娘就长躺在了地上,她的哭声又响了起来,那声音,丝丝缕缕,缠缠绕绕,听得人不由得心中感到慎得慌。
张贫生也跑了过来,见他婆娘在地上躺着,他却只看了万景义一眼,一句话都没说,就将他婆娘背了起来,快走到万景义家门口时,蓝氏往出扔了两块银元。
张贫生的婆娘一直用脚踢张贫生,骂张贫生没出息,一句话都不说,骂他是个窝囊废,连个屁都不敢放。
张贫生边走边淌着眼泪说:
谁让咱是穷汉人啊!
老天爷啊!
回家后,他气得直喘,却不敢去找万景义的麻烦,只好提着斧头将院子里的粗桐树砍了,那日,他婆娘几乎砸了家里的所有东西,水瓮,粮囤(空空如也),脸盆,碟子,海碗,能砸的东西都砸了,从始到终,张贫生一声未吭,没有阻拦他婆娘。
一周后,他带着他婆娘南下逃荒去了,因为没有吃的,最终两人都饿死在了半路上,连个坟头都没有。
据说,他俩饿死的那地方,后来长成了一片花海,成了某县区重要的自然公园。
那些野花,常年盛开着,比牡丹还要郁香,比玫瑰还要鲜亮,直到现在,那地方仍然游人如织,四季被人踏足。
谁能料到这白灿灿的花的前世后生呢?
一入冬,下了场大雪,整个沟野都被盖实了,天地白茫茫一片,那些柿树、槐树、桐树突兀在崖坎儿上,羊不再出来,都被圈在窝里,就是出来了,大雪封地,干草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