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与老屋.docx
《少年与老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少年与老屋.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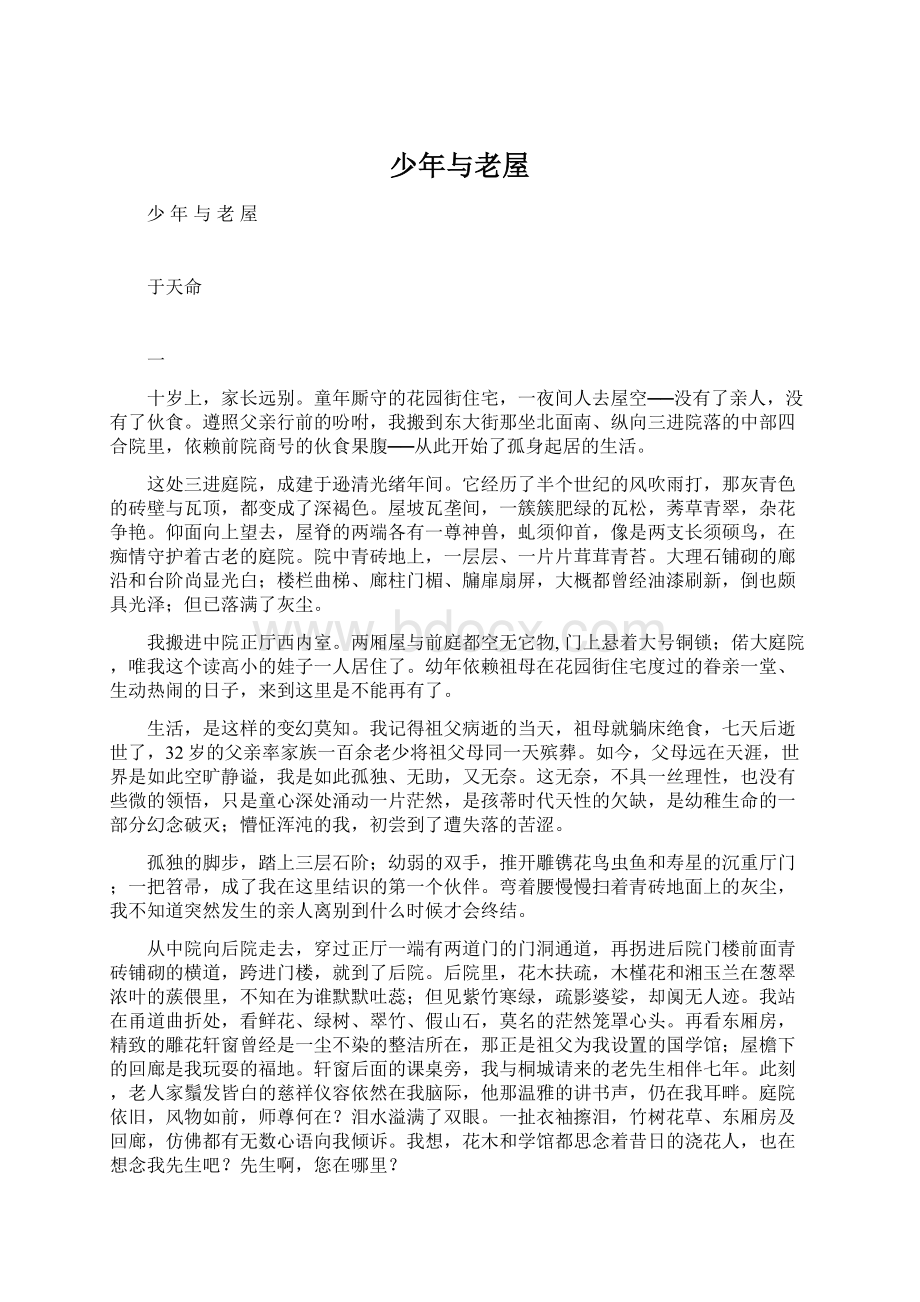
少年与老屋
少年与老屋
于天命
一
十岁上,家长远别。
童年厮守的花园街住宅,一夜间人去屋空──没有了亲人,没有了伙食。
遵照父亲行前的吩咐,我搬到东大街那坐北面南、纵向三进院落的中部四合院里,依赖前院商号的伙食果腹──从此开始了孤身起居的生活。
这处三进庭院,成建于逊清光绪年间。
它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打,那灰青色的砖壁与瓦顶,都变成了深褐色。
屋坡瓦垄间,一簇簇肥绿的瓦松,莠草青翠,杂花争艳。
仰面向上望去,屋脊的两端各有一尊神兽,虬须仰首,像是两支长须硕鸟,在痴情守护着古老的庭院。
院中青砖地上,一层层、一片片茸茸青苔。
大理石铺砌的廊沿和台阶尚显光白;楼栏曲梯、廊柱门楣、牖扉扇屏,大概都曾经油漆刷新,倒也颇具光泽;但已落满了灰尘。
我搬进中院正厅西内室。
两厢屋与前庭都空无它物,门上悬着大号铜锁;偌大庭院,唯我这个读高小的娃子一人居住了。
幼年依赖祖母在花园街住宅度过的眷亲一堂、生动热闹的日子,来到这里是不能再有了。
生活,是这样的变幻莫知。
我记得祖父病逝的当天,祖母就躺床绝食,七天后逝世了,32岁的父亲率家族一百余老少将祖父母同一天殡葬。
如今,父母远在天涯,世界是如此空旷静谥,我是如此孤独、无助,又无奈。
这无奈,不具一丝理性,也没有些微的领悟,只是童心深处涌动一片茫然,是孩蒂时代天性的欠缺,是幼稚生命的一部分幻念破灭;懵怔浑沌的我,初尝到了遭失落的苦涩。
孤独的脚步,踏上三层石阶;幼弱的双手,推开雕镌花鸟虫鱼和寿星的沉重厅门;一把笤帚,成了我在这里结识的第一个伙伴。
弯着腰慢慢扫着青砖地面上的灰尘,我不知道突然发生的亲人离别到什么时候才会终结。
从中院向后院走去,穿过正厅一端有两道门的门洞通道,再拐进后院门楼前面青砖铺砌的横道,跨进门楼,就到了后院。
后院里,花木扶疏,木槿花和湘玉兰在葱翠浓叶的蔟偎里,不知在为谁默默吐蕊;但见紫竹寒绿,疏影婆娑,却阒无人迹。
我站在甬道曲折处,看鲜花、绿树、翠竹、假山石,莫名的茫然笼罩心头。
再看东厢房,精致的雕花轩窗曾经是一尘不染的整洁所在,那正是祖父为我设置的国学馆;屋檐下的回廊是我玩耍的福地。
轩窗后面的课桌旁,我与桐城请来的老先生相伴七年。
此刻,老人家鬚发皆白的慈祥仪容依然在我脑际,他那温雅的讲书声,仍在我耳畔。
庭院依旧,风物如前,师尊何在?
泪水溢满了双眼。
一扯衣袖擦泪,竹树花草、东厢房及回廊,仿佛都有无数心语向我倾诉。
我想,花木和学馆都思念着昔日的浇花人,也在想念我先生吧?
先生啊,您在哪里?
后院正厅东端,有道角门,跨出去,步石阶而下二丈余,便是碧波荡漾的大水塘。
蓝天白云落水中,水面一片片潋滟明丽的白云倒影。
满塘的莲叶,春天浓绿,夏秋荷花盛开,岸上翠柳摇曳。
池对岸有街坊女子们洗衣濯巾,环肥燕瘦,靓臂裸膝,棒槌上下,起落之声阵阵;槌衣声伴着一派莺声燕语,自亭亭玉立的荷花丛中款拂漪澜,飘荡而来。
我有时走出后角门,去水塘边洗鞋洗袜;有时就在塘边柳荫下坐一会儿,稍解寂寞,歇歇脑筋。
碧水里,游鱼浮戏,蜻蜓们展翅翘尾,自由自在滑翔着,不时地向着飘浮于水波的香菱花朵间飞去。
高天的鸟儿在白云间翱翔,洗衣妇们身后有娃娃们追逐嘻戏;而池塘的这一边,惟我一个少年孤独的来去,寂无人语。
我暗暗羡慕飞鸟、游鱼、蜻蜓们自由结伴的乐趣。
同处一塘水,彼岸乐,此岸苦,我多么羡慕彼岸娃子们在亲人身边玩耍的幸运。
有时候,我拿了钓具,溜出后角门,走下塘边去垂钓;或者索性脱掉衣裤,踩入浅水,抠捉蚌蟹,自得其乐,兴致阵阵;可又隐隐感到,这旖旎如画的碧水荷花,鹅浮鸭游、鱼戏蜓飞的种种情趣,终究都不是我的课业和书本。
每天四次,我都要从寂静的中院向人声喧杂的前院里走过。
前院堆放一捆捆、一包包货物,议质论价、过秤、打捆、装箱,一片繁忙。
许伯、李伯、贾叔、阙叔、郭叔、马叔、赵叔、庞叔、小王叔、老仝伯等,都是跟随祖父多年的得力员工;他们不因我祖父逝世、父亲从外地回来把全家带走,就也散伙各奔前程。
他们不动生色,一如既往地劳作着,营业着,在许伯指挥下,团结一心,维护生意买卖正常进行,好像我家中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
每天,他们看着我上学走了,下学回来了,就问长问短,逗逗玩笑。
我知道他们淳朴和蔼的善意,往往应答几句,或立正站好,背一二段诗词,唱支歌,给他们助兴。
他们摸摸我的头,掂掂我的耳朵,拍拍我的肩,拉正我的书包。
我从他们温热的大手上,感觉到诚恳关爱和阵阵力量的鼓舞。
我知道,父亲相信他们,行前把祖父的商铺和监护我的责任都交给了他们。
我怀着被员工们关怀的欣快,穿过商号,走上大街──走向学校。
但是,如此生活,少小独居──没有家人温存,没有家人抚慰,没有家人凭依,没有家人教训,没有我倾诉和撒骄之所。
这样的少年时光,颇似一株无人修剪、无人嫁接的荒山上的酸枣树苗,任天风天雨自然吹打,虽生机勃勃,却枝杈芜蔓,怕要疯长成七歪八斜的灌木丛,而不能长成参天大树了。
下学归来,思亲之情时常袭我心头。
眼前赭黄的楼板,尘封的牖扉、扇屏和窗棂,屋檐下的燕巢和一团团灰蒙蒙的蜘蛛网,无不在我心上激起阵阵凄凉。
自感是一支断了线的风筝,无依无靠,却落不到地上,飘浮云中,不得厚土。
无论怎样的遥想眷亲一堂的日子,此时却除了偶尔有书信寄来,父母与我,依然是关山遥隔,白云横亘。
大雁南飞,一字形、人字形雁队,不时飞过老院上空,越飞越远,没入缥渺,望不见了。
“雁飞高兮邈难寻,空断肠兮思愔愔”,梧桐树的片片黄叶,在深秋的寒风里悄然飘落地面;这深褐的院子里,草木都变得萧瑟而淡黄,更失去生气。
母亲带走了我二弟三弟,还要照顾外婆,本就繁忙,而我的衣鞋,原是伯母所做,但在离别后之今日,母亲也为我做鞋两双,一并托人带回。
我双手捧着二位老人一针针一线线衲底缝帮做成的新鞋,我酸憷的心上即刻泪涌满腔,潸潸滴落鞋面。
泪影里,依稀看见,远在天涯的伯母和母亲二老啊,她们,还在为我筹划冬季的棉衣。
我曾热切盼望,能有谁来到这座幽静庭院,同我一道起居、同进同出呢──然而,没有。
谁人的家长都不会允许自己孩子居住别家;何况,起早贪黑忙忙碌碌为衣食而操劳的家长们,谁也不曾注意到,这人去屋空的宅院里,只剩下一个十岁娃子茕茕独存。
黑夜降临的时候,芭蕉树和海棠树的密枝浓叶,遮挡了天际尚存的微稀月色,黑暗笼罩了树下的一切。
昏暗模糊的院子,仿佛变成一艘古老航船,自天海云霾中沉落了下来,沉向了乌黑大海的最深处,端然是与世隔绝了。
在寂静得可怕的黑暗中,老鼠和蛇们活跃起来。
唧唧、嗤嗤、噗噗之声时骤时稀。
我从学校上完两堂夜自习归来,跨过门厅那道高厚门槛,摸出一支火柴擦亮,慢慢走进西内室,点燃书案上的香油铜灯,拔亮那绺棉线灯芯。
这时候,油灯特别明亮,简直是光芒四射!
它跳跃着欢快的火焰,好象是欢叫终于等到我归来;它像是天穹抛落一团火球,刹那间,就把空旷大屋的黑暗和冷寂一下子赶出了门外。
这时候,我的身影与我心情为伴,同我身我影相依为命的,只是西内室,这间西内室令我崇敬无限。
它原是祖父生前的书房,存藏一撂撂线装古书,还有民国年间许多“洋版”书刊,以及《申报》、《大公报》、《新民报》、《南阳报》、《秦风工商报》等;这些存藏,足以装载两马车,自然已成了祖父留给我的遗产。
我已受儒塾训教六年十个月,对祖父藏书中比较易懂的部份是能够阅读一些了,忍不住就在祖父的书橱间拣来翻去。
也正是拣来翻去的长了些见识,才在数年后,于县中学存放的抗日战争时河南大学留下尚未运走的图书中,识别出了河大的《楚辞集注》、《文心雕龙》、《四部丛刊》、《柳河东集》等,均与我祖父所藏版本不同。
由此,引发我悟得一丝新知:
古代著作与典籍历经朝代更替,多有不同时期的文人点评校勘,因而版本各异。
后人针对某项欲焯真知,非广览版本,博识众论,而不能勃发灼见。
每当耳畔升起启蒙之初所读《三字经》文“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时,便伏案铜灯的光亮下,不想稍息,越发汇神专注于课本作业了。
“漏尽金风冷,堂虚玉露清,穷经谁氏子,独坐对寒檠”,恰应上了此刻的生活,这正是祖父提倡的少年们应有的经历。
我心上升起一股朦胧的神圣。
父亲行前吩咐说“你十岁了,应该学会自己照料自己。
你是长子,受些苦好,去县高小把你没学过的算术混合四则学会,考中学吧。
不要哭,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忘了么?
”我没有忘,可不知父亲长年在外地为何突然归来?
又为何匆匆离去?
更不懂他为什么要把全家人都带走,而只留下我?
我深感凄凉,但不晓这情绪正是惆怅。
二
也许是,院子里白天总是无人的缘故,自大人们走后,鼠和蛇就多了起来,它们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儿;无论是鼠是蛇,都公然与我举目对望。
我跺脚喊叫,投掷东西击打,冀图镇慑它们;有个伢鼠被我击中,从门额上摔落下来,我大出了一口怨气。
可是,鼠们高超的繁殖能力生生不息,越发肆虐起来。
它们成群结队,梁上床下案头椅边,追逐信步;好象是向我示威。
我方知自己奈何不得这个兴旺发达的族类,而它们却有能力随时伤我,至少害我夜夜不得安宁。
如今,我孤单无助,既知不可为,而为之,岂不徒费光阴?
何况,换种想法,鼠类之间没完没了的争斗,在它们也许认为是与我无关,可我却伤害了它们的同类。
这样想来,显然是我的不是。
于是我任其表现,听之任之了。
但是,鼠子们还是让我饱尝了人人都厌恶这个族类的原因。
它们作害甚多,把书籍、衣服都一再咬烂,到处都有它们作孽留下的碎渣。
它们居然智慧地把书案上的铜灯掀倒,把铜灯里的香油吃喝净尽,还屙下黑虫似的一粒粒粪便撒布桌面,不管我回来怎么办。
睡梦里,鼠子们心安理得地从我脸上爬过,还不时把一片片尿渍留到我的枕巾、被子上面;还要在我看书的时候悍然从脊背上追逐而去,好象就应当似的……鼠子们生性狡猾,自持灵动,虽然不具备与人争斗的勇气,却善于出没无常的,反反复复的,发起令我防不胜防的扰乱。
鼠子们的龌龊行径,让我想到一个危险:
人类中若活动着具有鼠性者,那真是这世界一个大不幸。
他们不直接吃人,也不以凶相吓人,只是执着地、运用形形色色的龌龊行径,给别人制造不安,让你过着烦心的日子。
它们永远不是故意,却本能地以充沛的精力,给人制造麻烦、制造损失、制造愤怒、制造伤感,它们从危害善良、戏弄弱者的过程中获得快感!
我长大了若遇上鼠性人物,该怎么办呢?
是果断抵抗呢,还是逆来顺受?
蛇们,同鼠子的作为大相径庭。
看那蛇族滚圆柔长的身子从梁上檩间爬过,是那样的无视旁类,它们不肯轻易改变独来独往、洁身自好的姿态,常常将身子一圈圈盘绕一团,稳伏一处,比起鼠子们,多了些睡眠,多了点儿安详。
蛇们不事喧嚣,俨然斯文儒雅、道貌岸然,很有点儿胸有成竹、高深莫测的样子;但有时高扬挺挺的头颈,傲然四顾,扁嘴张开,飞箭般吐出利刃似的尖细长舌。
在我眼里,那么一种强者独尊的霸主姿态,明明是一种狰狞,尤显丑恶,实属滑稽。
不知蛇们是习惯于目空一切的摆谱儿,还是作恶行凶之前的最后思索,当我一瞥之下,看见它们狰狞的尊容,本能地就望而却步。
可怜我两腿骤软,心里怦怦急跳,似觉末日降临。
还算侥幸,六年过去了,直到我离开老屋,蛇们总算没顾得上伤我。
兴许是,我没有防碍它们的出没,也不曾怀疑它们的桀傲和能力,在它们眼里认为微不足道的我还算知趣,所以也就尚能容忍我的存在,坦然地不屑与我计较了。
蛇们如此大度,终于让我发现自己心上已经对它们产生了莫名的“敬意”。
事实上,屋檐下的燕巢,墙洞中的麻雀,树杈上喜鹊窝里,那吞不完的雏鸟和鸟蛋,已经足够大小蛇们日日饱餐而眠了。
也许是禽鸟们前赴后继的无辜牺牲,恰恰保障了我的安全。
这样,蛇们悠悠然与我保持相安无事,宽宏大量地容忍我在老屋里暂住了六年。
后来,当我离开老屋的时候,竟对蛇们怀有一丝恋念:
他们能屈能伸,不计世人过错,恐怕正是向我昭示一种处世的境界吧。
那些翔鸟飞禽们,则是我唯恐离别,而刻意挽留的同度时光者。
日常,我给它们扫除掉落在院子里的漓漓粪便,把地面打扫干净,洒上一些水,让它们感到清凉;还不时去前院厨房,拿来剩饭剩菜饲奉它们。
我在殷勤之中却未料到,竟引起更多的鸟儿纷纷飞来,它们在屋檐下,在树枝上,筑起大大小小的窝巢;甚至飞落到我肩上头上,伶俐地贴近和亲妮。
我先是惊异,尔后是油然骄傲和忘却一切的快乐。
前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