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颜面上.docx
《现代性的颜面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现代性的颜面上.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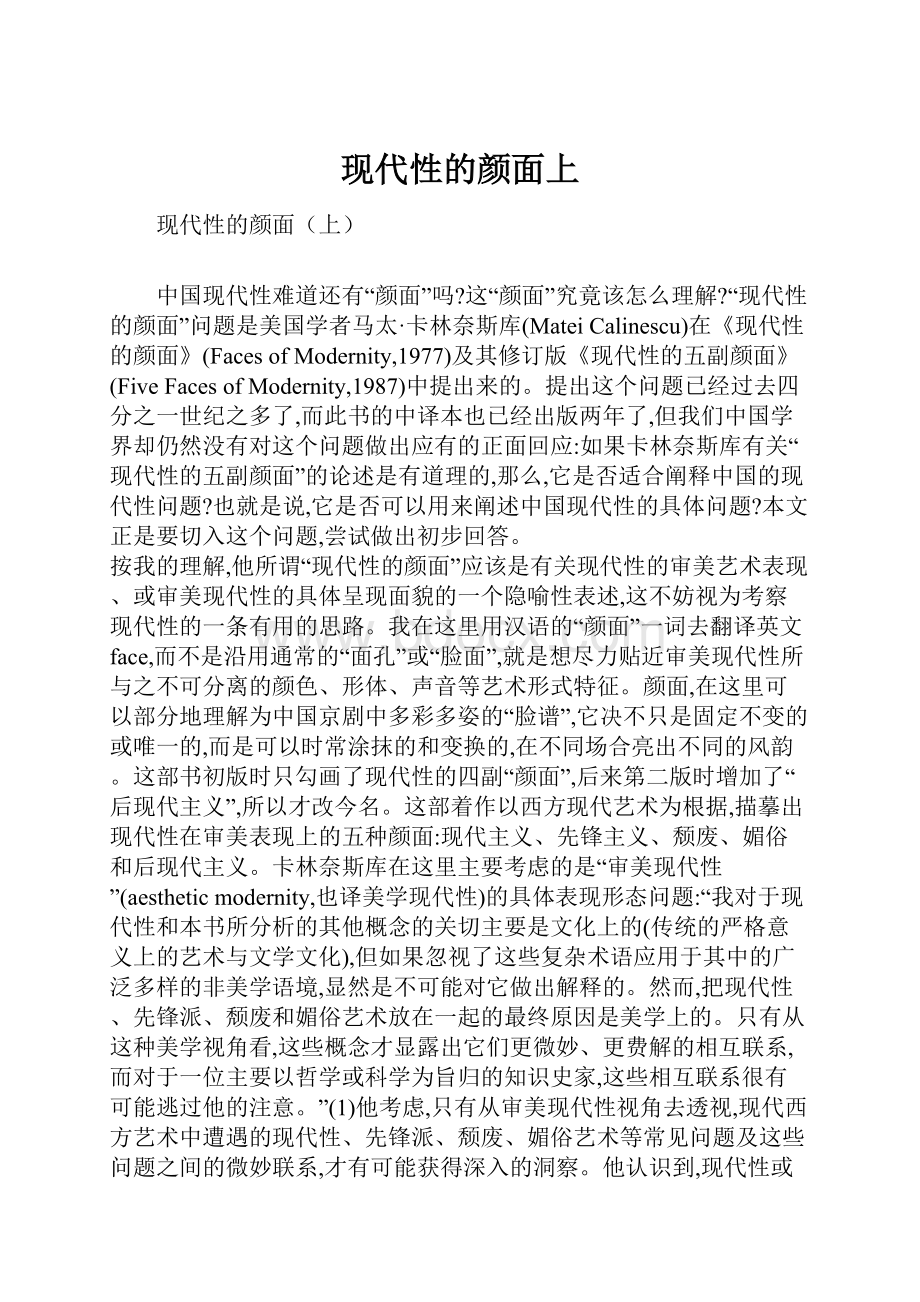
现代性的颜面上
现代性的颜面(上)
中国现代性难道还有“颜面”吗?
这“颜面”究竟该怎么理解?
“现代性的颜面”问题是美国学者马太·卡林奈斯库(MateiCalinescu)在《现代性的颜面》(FacesofModernity,1977)及其修订版《现代性的五副颜面》(FiveFacesofModernity,1987)中提出来的。
提出这个问题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之多了,而此书的中译本也已经出版两年了,但我们中国学界却仍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应有的正面回应:
如果卡林奈斯库有关“现代性的五副颜面”的论述是有道理的,那么,它是否适合阐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也就是说,它是否可以用来阐述中国现代性的具体问题?
本文正是要切入这个问题,尝试做出初步回答。
按我的理解,他所谓“现代性的颜面”应该是有关现代性的审美艺术表现、或审美现代性的具体呈现面貌的一个隐喻性表述,这不妨视为考察现代性的一条有用的思路。
我在这里用汉语的“颜面”一词去翻译英文face,而不是沿用通常的“面孔”或“脸面”,就是想尽力贴近审美现代性所与之不可分离的颜色、形体、声音等艺术形式特征。
颜面,在这里可以部分地理解为中国京剧中多彩多姿的“脸谱”,它决不只是固定不变的或唯一的,而是可以时常涂抹的和变换的,在不同场合亮出不同的风韵。
这部书初版时只勾画了现代性的四副“颜面”,后来第二版时增加了“后现代主义”,所以才改今名。
这部着作以西方现代艺术为根据,描摹出现代性在审美表现上的五种颜面:
现代主义、先锋主义、颓废、媚俗和后现代主义。
卡林奈斯库在这里主要考虑的是“审美现代性”(aestheticmodernity,也译美学现代性)的具体表现形态问题:
“我对于现代性和本书所分析的其他概念的关切主要是文化上的(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艺术与文学文化),但如果忽视了这些复杂术语应用于其中的广泛多样的非美学语境,显然是不可能对它做出解释的。
然而,把现代性、先锋派、颓废和媚俗艺术放在一起的最终原因是美学上的。
只有从这种美学视角看,这些概念才显露出它们更微妙、更费解的相互联系,而对于一位主要以哲学或科学为旨归的知识史家,这些相互联系很有可能逃过他的注意。
”
(1)他考虑,只有从审美现代性视角去透视,现代西方艺术中遭遇的现代性、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等常见问题及这些问题之间的微妙联系,才有可能获得深入的洞察。
他认识到,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变,即从一种由来已久的永恒性美学转变到一种瞬时性与内在性美学,前者是基于对不变的、超验的美的理想的信念,后者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变化和新奇”
(2)。
卡林奈斯库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性的颜面问题:
从审美现代性的视角看,中国现代艺术中哪些因素可以获得其必要的或重要的意义?
困难不在于是否能从中国现代艺术中找出与卡林奈斯库所论述的“五副颜面”相对应的现象,这一点是容易做到的。
因为,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都已经和正在发生种种实实在在的影响,或者说出现了种种相似的回应。
但真正的困难在于,找到这些对应物后如何加以甄别:
中国的这些相似现象或相通物与西方的原生物是一回事吗?
如果不是而只是部分相似或相通,那么,两者间的具体异同及其原因究竟何在?
显然,真正研究起来就会感到问题相当复杂。
我想我只能这样做:
不直接套用卡林奈斯库的“五副颜面”说,因为直接套用难免忽略中国自身的问题所在,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具体性帮助不大;而是在沿用“现代性的颜面”说并参照“五副颜面”的同时,主要从中国现代性语境出发,着力寻找那些能够呈现中国现代性的具体状况及其微妙方面的审美现代性因素。
也就是说,在现代性的颜面这一名义下,我将集中寻觅并展示现代艺术中专属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那些特定因素。
历数中国现代性的诸种颜面,既可采用共时态并列的方式,即暂时不考虑历时演变因素而仅仅将所有颜面挤压到同一个横截面中,让它们显得仿佛是多元共生;也可以从在时间上轮流占据主流地位的角度,将这些颜面作历时的逐一展示。
我的做法是将这两种方式大致地拼贴起来:
既寻找到属于中国现代性的那些特有的颜面,又大致按照它们的主流地位的历时演变线索而加以排列。
这样,我的脑海里渐次浮现出这样几副颜面:
首先是革命主义,接着有审美主义、文化主义、先锋派以及拿来主义。
当然还可以列出若干副颜面,但我想这“五副颜面”应是必不可少和不应忽略的。
一、现代性的颜面之一:
革命主义
“革命”或“革命主义”称得上中国现代性的一副颜面吗?
(3)对中国人来说,现代性在变化强度和烈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文化转型。
它决不仅仅意味着吉登斯意义上的“时空分离”,而代表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深刻而又最富于动荡性的巨变。
古往今来的中国艺术曾经发生过林林总总的变化,但是,没有任何一次能像20世纪这样变化迅捷、日新月异!
要表达这样一种特殊的巨变情形,除了“革命”这个词外,还能找出任何其他更恰当的词吗?
在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看来,19世纪是“革命的年代”(AgeofRevolution),而20世纪是“极端的年代”(AgeofExtremes)(4)。
其实,在中国,20世纪无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年代”。
不过,这个“革命的年代”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景:
它同时既是“革命”的又是“极端”的,是“革命的年代”与“极端的年代”的奇特的叠加形态,因而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革命的年代”。
正是在这样一个“极端的革命的年代”里,“革命”曾给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带来过无限的希望、激发过无尽的浪漫激情。
不妨听听蒋光慈的热烈礼赞:
“在现在的时代,有什么东西能比革命还活泼些,光彩些?
有什么能比革命还有趣些,还罗曼谛克些?
”(5)在蒋光慈看来,“革命”直接关系到艺术的“生命”、“生气”和“活力”:
“而革命这件东西能给文学,宽泛地说的艺术以发展的生命;倘若你是诗人,你欢迎它,你的力量就要富足些,你的诗的源泉就要活动而波流些,你的创造就要有生气些。
否则,无论你是如何夸张自己呵,你终要被革命的浪潮淹没,你要失去一切的创作活力。
”(6)出于对革命的神奇力量的无穷想象,这种带有“极端”特色的革命主义无疑成为中国审美现代性在20世纪的一副最激动人心而又最引发争议的标志性颜面。
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作为崇尚激进的美学变革及其社会动员效果的艺术观念、思潮或运动,革命主义曾长时间地扮演过主角,产生过至今仍余响不绝的深远影响,因而不妨多谈几句。
在20世纪中国,到底出现过多少种“革命”术语?
不得而知。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从1899年起率先打出了“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等多种“革命”旗号(7),在自己担任主笔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大力倡导。
蒋智由则作《卢骚》加以响应,以诗的浪漫语言呼唤文学的“全球革命”:
“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
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
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8)而在清末产生过最大的社会影响力的“革命”话语当数“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1885-1905)的《革命军》(1903)了。
在这部当时发行上百万册的小书中,他用诗意的语言赞美说:
“巍巍哉!
革命也。
皇皇哉!
革命也。
”(9)这部洋溢着浪漫的革命主义激情的书很快风行海内,被章炳麟称之为“义师先声”、章士钊主笔的《苏报》誉之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1912年2月,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签署命令,追赠邹容为“大将军”。
鲁迅说:
“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10)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审美现代性一开始就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方面,审美现代性常常以革命的名义在社会中推演自身,把自己的形式魅力播撒向社会公众,从而使得审美形式变革产生出更深厚的文化变革力量,例如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另一方面,社会的文化变革也往往借助审美革命的形式、披上诗意的外衣,例如邹容的《革命军》。
“革命”确实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字眼。
诚然,上述含义当然是它题中应有之义,但却并非仅仅只有此义。
较早从日本引进并推广这一术语的梁启超,担心它被应用于鲜血和暴力的变革义,从而专门作《释革》(1902)加以澄清:
“‘革’也者,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
Reform者,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如英国国会1832年之Revolution是也。
日本人译之曰改革、曰革新。
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革命。
‘革命’二字,非确译也。
”他还回溯汉语词源,指出“‘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其在《书》曰:
‘革殷受命。
’皆指王朝易姓而言”,因而与Revolution的变革意不同。
他坚持革命仅仅是指“人群中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的“变革”,这是社会进步之常道,不必惊骇。
他列举当时中国出现的“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指出它们的“本义”就是“变革”。
“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
革命可骇,则变革其亦可骇耶?
”在两年后他又写《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904),更明确地指出,革命具有三层不同含义:
“革命之义有广狭:
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
”第一层为革命的最广义,是指社会上一切事物的大变动;第二层为其次广义,是指由和平或暴力方式导致的以新时代取代旧时代的社会大变迁;第三层为其狭义,是专指推翻中央政府的军事行动。
相比而言,他竭力将革命局限于头两义,而恐惧和担忧第三义:
“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唯心醉狭义的革命。
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11)梁启超的小心考辩意在张扬非暴力的头两义而抑制暴力的第三义,用心良苦。
但从中国现代性的实际进程来看,他的革命三义论毕竟还是公允之论,较为全面地梳理了现代革命概念的多层内涵,为理解审美现代性中的革命主义奠定了基础。
(12)
这样,如果从梁启超的“革命”三义论来考察,审美现代性中的革命主义具有三层含义或形态:
第一层为最广义的革命主义,往往涉及那些旨在推进社会事物的局部或总体变化的新思潮,有黄遵宪的“新派诗”、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主张等,这通常被视为温和的“改良主义”或“渐进主义”。
第二层为广义的革命主义,是指那些有组织有目的的社会变革运动,最典型的就有陈独秀和胡适等的以“文学革命”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就体现了现代革命论特有的依赖大众媒介和新的语言实施有组织的社会动员的含义,可以视为现代革命主义的最基本含义。
如果说第一层主要体现社会变革“思潮”,那么,第二层的显着标志就是社会变革“运动”。
其具体代表作有:
《尝试集》、《呐喊》、《彷徨》、《女神》、《雷雨》等。
第三层为狭义的革命主义,是指直接听从于现代政党号令、首先做革命者再以艺术服务于革命斗争的观念体系,如“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等,这常常被称为“革命文学”、“革命文艺”。
郭沫若较早认识到这种革命文学的“无产阶级”性质:
“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赤裸裸的人性。
”(13)恽代英则规定了这种狭义的革命主义的基本原则:
“自然是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的文学的。
”(14)这里提出了后来风行中国的狭义革命主义美学原则:
要想做革命艺术家,先要做“革命家”;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的文艺。
“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
”(15)这种狭义革命主义的直接成果有20世纪20年代后期“革命+恋爱”小说、茅盾小说、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
而在“文革”时期,这种狭义革命主义原理结出了江青提出并由姚文元修正的“三突出”畸果。
当然,革命主义的这三层含义之间不存在天然鸿沟,而实际上彼此关系含混而又相互滑动。
例如,梁启超的思想就常常徘徊于第一、二层之间;胡适则从开初的第一层进展到第二层,而对陈独秀和李大钊后来向往的第三层持批评态度;陈独秀则尤其独特:
依次经历了第一、二、三层的演变,即从改良主义思潮(“五四”前)到革命主义运动(“五四”期间)再到共产主义政党活动(创建中国共产党)。
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演变看,“五四”前的革命主义大致体现了这个词的最广义,“五四”文学革命则集中了它的广义,而后“五四”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等则凸现了它的狭义。
说到中国“革命”及“革命主义”的含义与形态,还不能不提到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中提出的“双轮革命”概念:
19世纪欧洲的革命是一种“双轮革命”(Dualrevolution),即是法国政治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的结合。
“革命”(Revolution)在英文中最初就是“旋转”的意思,而“双轮革命”显然可以形象地理解为一种双轮驱动的旋转。
至于中国革命主义中的“革命”一词,我想可能不只有双轮含义,还需要增加来自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启示义:
被压迫阶级与民族也可以成功地领导美学革命。
就中国审美现代性而言,法国式的政治革命在这里主要涉及根本的政体制度及相应的文化观念的变革,如西方美学观、艺术观、教育观、文化观等;英国式的工业革命主要体现为传媒技术和文化产业的变革,如机械印刷媒介取代传统雕版印刷技术、摄影与电影等新媒介的运用、艺术的机械复制等;苏俄式社会主义革命则为以专政手段推翻旧趣味而推行新趣味提供了合法性。
这样,中国审美现代性中的革命主义应当是一种由政体—文化革命、传媒革命和阶级趣味革命合力驱动的“三轮革命”。
只有同时从这全部“三轮”去作完整的理解,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主义的最广义、广义和狭义三层含义的共存情形及其复杂关联,例如狭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和“三突出”的出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而也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中国革命主义的独特特色。
单从今天的眼光看,审美现代性自然应当与诗意、愉悦、自由、解放等联系在一起。
诗情画意、浪漫潇洒似乎应是它的代名词。
这似乎不言而喻、甚至天经地义。
然而,只要冷静而全面地考察,就不得不承认,在几乎整个20世纪长河里,审美现代性航船却总是必须悬挂着鲜艳的革命旗帜,在它的映照下乘风破浪或逆水行进。
这究竟是为什么?
原因并不复杂:
这种革命主义得以发生的缘由,其实主要地并非来自艺术领域的内在审美要求本身(当然也不能不与此相关),而是来自外在的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现代性变革需要。
这是因为,梁启超等现代人文知识分子一次次痛感中国现代性进程的艰难性和曲折性,并深知这种艰难和曲折的症结就在于广大普通民众的愚昧,认识到如果不首先唤起他们的理性觉悟,就无法真正推动越来越沉重的现代性车轮。
当然,还应当看到,在广大普通民众的愚昧后面,还有更深厚的文化无意识原因:
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和自我中心幻觉。
正是这种传统重负阻碍着中国人轻松地弃旧图新。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看到这一点:
中国在现代的“落后”,“事实上并非由于中国人在技术或教育方面无能,寻根究底,正出在传统中国文明的自足感与自信心”。
所以“中国人迟疑不愿动手,不肯像当年日本在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一样,一下子跳入全面欧化的‘现代化’大海之中”。
只有等到局势变得不可收拾了,即古典文化传统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时,中国人才能猛醒过来;但这时,渐进的改良道路已经断绝,只剩下激进的革命道路了。
“因为这一切,只有在那古文明的扞卫者古老的中华帝国成为废墟之上才能实现;只有经由社会革命,在同时也是打倒孔老夫子系统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开。
”(16)甚至连知识分子们要唤醒愚昧的民众,也不得不运用艺术革命的激进手段。
如何唤起民众呢?
处于困境中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上下求索、“别求新声于异邦”,从西方和日本的现代性经验中获得启示,回头激活中国的“诗教”传统,发现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具有任何其他形式都无法比拟的特殊的审美感染力,可以有力地和有效地完成现代性的社会动员任务。
而当旧的艺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时,打碎旧艺术、创造新艺术、实行彻底的艺术革命,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了。
所以,革命主义的生成,首要地来自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特殊的社会动员需要。
为了圆满地完成社会动员任务,艺术就必须实行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这样,诗歌革命、小说革命、戏剧革命、美术革命等,就在20世纪初的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兴起了。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忍不住要质问:
审美现代性真的必须长出一副“革命”的颜面吗?
今天一些人在总结五四文学革命的经验时,就常常难以抑制住对“革命”颜面的厌恶与痛惜之情:
这场文学革命简直就是野蛮地糟蹋中国文化传统的闹剧,竟导致中华文化的传统血脉在现代断绝;现在只有改弦更张而回归古典,才是唯一生路。
在纪念“五四”八十周年之际,着名作家、加州大学白先勇教授就毫不掩饰他对五四文学革命的严厉质疑:
“《儒林外史》、《红楼梦》,那不是一流的白话文,最好、最漂亮的白话文么?
还需要什么运动呢?
就连晚清的小说,像《儿女英雄传》,那鲜活的口语,一口京片子,漂亮得不得了;它的文学价值或许不高,可是文字非常漂亮。
我们却觉得从鲁迅、新文学运动起才开始写白话文,以前的是旧小说、传统小说。
其实这方面也得再检讨,我们的白话文在小说方面有多大成就?
”他还认为由于这场文学革命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使五四运动后的教育和文学都缺乏传统文化的继承,制造出“文化的怪胎”。
他归纳说: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17)这样的全盘否定性认识来自今天的文学视角,确实有些道理,因为单纯的文学内部变化完全可以在传统本身的弹性框架内有序地和渐进地进行,而不必一定采用“革命”的激进方式。
例如,以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进程,完全可以用更冷静的筹划和更长的时间渐次进行,而不必在“五四”这短暂时间内一举断裂而成。
这种迅猛的断裂方式导致现代文学与古典传统截然脱轨。
但是,如果按当时的现代性语境设身处地地想想,就不难见出这种革命性断裂所包含的文化合理性了。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慧眼中,陷入困境的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只有仰仗艺术革命才能转危为安啊!
1916年8月,李大钊在创办《晨钟报》时就有意掀起一场“新文艺”革命运动: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18)如果现代性意味着一种“新文明”,那么,它就必须依赖“新文艺为之先声”。
“新文艺”的作用不在于一般地娱乐读者,而在于通过表现崭新的“理想”、振奋“自我之权威”、呼唤“自我觉醒”,去“惊破”蒙昧的广大民众的“沉梦”。
显然,文学革命的动机直接地并非文学的,而是来自文学之外即是文化的。
让文学去革命,为的就是文化现代性本身。
那么,文学革命与整个文化革命之间有什么具体联系、前者对后者有什么实际作用呢?
这一点可从陈独秀对“三种文学”的“排斥”中见出:
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的“公同之缺点”在于将“宇宙”、“人生”和“社会”排斥在“构思”之外。
而正是这样的文学“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相互走向沉沦。
所以,要改造“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就必须首先改造与它“互为因果”的旧文学。
(19)可见,文学革命实在是要服务于改造“国民性”的任务。
革命主义在现代中国之所以成为人们竞相拥戴的“显学”,实在是由于中国现代性的“非常”局势。
这种“非常”在于:
由于中国人的固有的宇宙模式和中优外劣心态等的束缚,中国现代性一再处于低于理想水平或者成理想的反面的缓慢变革的或危机的状态。
而这种非常局势在现代竟实际上充当了中国现代性变革的常态。
这属于非常性常态。
对这种非常性常态的痛切体验煎熬着现代知识分子的心,逼迫他们采取激进的革命姿态,从而不无道理地导致现代性长出一副革命主义的激进变革颜面。
这样,革命主义在现代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所以,轻易否定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革命主义原则是不足取的。
不过,应当冷静地看到,革命主义不大可能在任何时候都成为现代性的主旋律。
作为这种主旋律,革命主义往往是在动荡不已的现代一时段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因为摇晃不已的现代性车轮需要革命主义的非常态的强势推力、甚至多种力量的合力推举。
而到了相对和平的现代二时段,革命主义的现实需要可能会大大减退,从而从“主旋律”降低为“次旋律”。
尽管如此,我确信,革命主义在中国现代性时段决不肯轻易退场。
每当中国现代性处于动荡状态或危机情势时,革命主义总会适时地登场亮相,推演出革命的种种激进场面,无论你是否乐意观赏。
二、现代性的颜面之二:
审美主义
审美主义能称得上中国现代性的一副颜面吗?
审美主义,是英文词aestheticism的汉译,在长时间里曾被译作“唯美主义”。
而一谈到“唯美主义”,稍有历史记忆的人都会知道,这向来是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崇尚“为艺术而艺术”的颓废思潮加以否定和清算的。
现在改译为“审美主义”,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越出以往意识形态偏见而加以冷静反思的理智立场。
(20)审美主义是19世纪后期在英法等国曾一度兴盛的艺术思潮之一,它的主要代表有英国的王尔德(OscarWilder)和佩特(WalterPater)、法国的戈蒂耶(TheophileGautier)等。
从20世纪初年起,审美主义及“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就介绍到中国,引发持续不断的争论,产生过这样那样的深远影响。
(21)据研究,“周作人是第一个把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介绍到中国来的,他也是最早推崇佩特‘刹那主义’的人之一。
周作人1909年翻译出版王尔德的《安乐王子》(收入《域外小说集》),1922年在《晨报副镌》上开辟‘自己的园地’专栏宣扬‘独立的艺术美’,最终在小品文中实践其唯美主义理想。
”同时,“周作人不仅把唯美主义当作艺术理想,更把它付诸生活实践,使之贯穿于自己生命力中的方方面,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生活之艺术’。
”(22)其实,不仅周作人,甚至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们,也都曾不同程度地心仪过王尔德及其审美主义信条。
在1915年11月出刊的《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前身)第1卷第3号封面上,就赫然登载王尔德的肖像。
(23)激进的革命的文化启蒙刊物竟然以审美主义者王尔德为供师法之偶像,这不能不使人产生联想:
五四新文化或多或少与审美主义相关。
在“五四”青年对艺术的社会动员力量的想象中,似乎不无道理地会回荡着审美主义的以艺术改造人生与社会的幽灵。
确实,审美主义是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副颜面。
审美现代性中的革命主义原理其实就内含着审美主义的前提:
由于美的艺术可以改造生活丑、成为生活的美的典范,因而艺术革命才是合理的。
然而,应当看到,审美主义在欧洲其实可以有更为宽泛的内涵:
它不仅狭义地指以王尔德为代表的19世纪后期英法审美主义思潮,已如上述;而且也可以广义地涉及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期德国古典美学思潮。
这样,审美主义有广狭两义。
广义的德国式审美主义,可以称思辨式审美主义,注重从思辨角度高扬审美旗帜,主张审美与艺术是文化的最高原则、以审美去改造现有的衰败的文化。
其代表主要是一批哲学家,如康德、席勒、黑格尔、谢林等。
席勒认为,在“审美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称之为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东西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
”(24)“惟独美的沟通能使社会统一,因为它是同所有成员的共同点发生关系的。
”(25)而狭义的审美主义,在中国常被称为“唯美主义”,可以称日常式审美主义,在承认德国思辨式审美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进而着重让这种原则从思辨王国沉落为现实生活行为:
突出艺术本身的自为性,提出“为艺术而艺术”原则,并且身体力行地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艺术化。
其代表人物王尔德、佩特和戈蒂耶等都是艺术家,并在艺术创造追求美化和在日常行为上都追求艺术化。
无论是广义的思辨式审美主义、还是狭义的日常式审美主义,其共同点是把审美当做文化的最高原则和解决文化问题的绝对中介,幻想以审美与艺术去改造现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