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与交流戏曲与祭祀仪式剧异同论.docx
《分别与交流戏曲与祭祀仪式剧异同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分别与交流戏曲与祭祀仪式剧异同论.docx(3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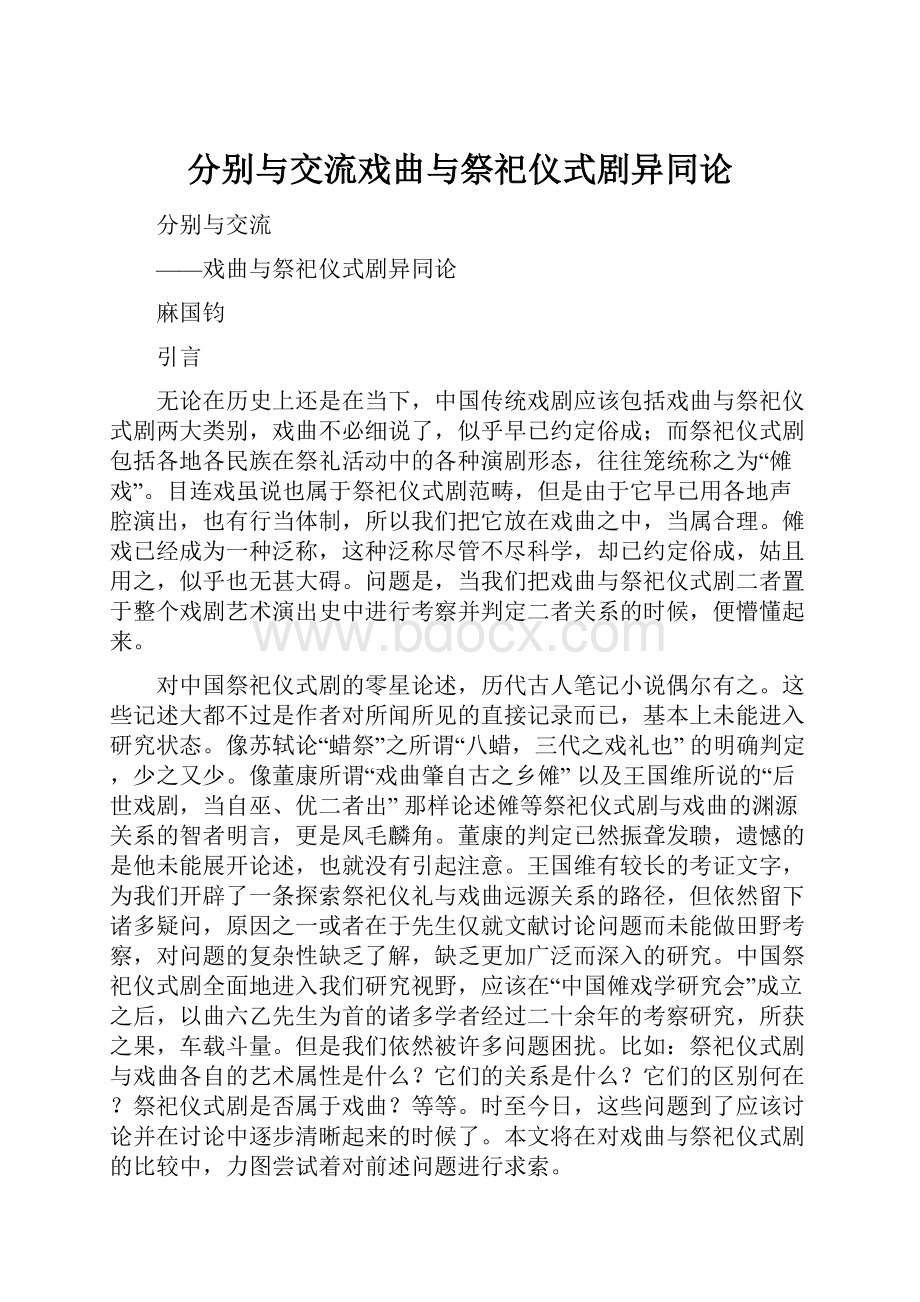
分别与交流戏曲与祭祀仪式剧异同论
分别与交流
——戏曲与祭祀仪式剧异同论
麻国钧
引言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中国传统戏剧应该包括戏曲与祭祀仪式剧两大类别,戏曲不必细说了,似乎早已约定俗成;而祭祀仪式剧包括各地各民族在祭礼活动中的各种演剧形态,往往笼统称之为“傩戏”。
目连戏虽说也属于祭祀仪式剧范畴,但是由于它早已用各地声腔演出,也有行当体制,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戏曲之中,当属合理。
傩戏已经成为一种泛称,这种泛称尽管不尽科学,却已约定俗成,姑且用之,似乎也无甚大碍。
问题是,当我们把戏曲与祭祀仪式剧二者置于整个戏剧艺术演出史中进行考察并判定二者关系的时候,便懵懂起来。
对中国祭祀仪式剧的零星论述,历代古人笔记小说偶尔有之。
这些记述大都不过是作者对所闻所见的直接记录而已,基本上未能进入研究状态。
像苏轼论“蜡祭”之所谓“八蜡,三代之戏礼也”的明确判定,少之又少。
像董康所谓“戏曲肇自古之乡傩”以及王国维所说的“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那样论述傩等祭祀仪式剧与戏曲的渊源关系的智者明言,更是凤毛麟角。
董康的判定已然振聋发聩,遗憾的是他未能展开论述,也就没有引起注意。
王国维有较长的考证文字,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探索祭祀仪礼与戏曲远源关系的路径,但依然留下诸多疑问,原因之一或者在于先生仅就文献讨论问题而未能做田野考察,对问题的复杂性缺乏了解,缺乏更加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中国祭祀仪式剧全面地进入我们研究视野,应该在“中国傩戏学研究会”成立之后,以曲六乙先生为首的诸多学者经过二十余年的考察研究,所获之果,车载斗量。
但是我们依然被许多问题困扰。
比如:
祭祀仪式剧与戏曲各自的艺术属性是什么?
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它们的区别何在?
祭祀仪式剧是否属于戏曲?
等等。
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到了应该讨论并在讨论中逐步清晰起来的时候了。
本文将在对戏曲与祭祀仪式剧的比较中,力图尝试着对前述问题进行求索。
一、最初的分野:
巫优分化
当优从古巫中分离而出之时,就是祭祀仪式与戏剧最初分野之际。
尽管在那个遥远的时代,无论是祭祀仪式剧还是戏曲都远远没有成立,但是恰恰在那个时候,构成戏剧最核心的成分之一的演员就已经分道扬镳,走向与巫不同的发展道路,巫抑或各种与巫师同质者,伴随着祭祀仪式剧一路同行,而从巫分离而出的优则以歌舞娱人,进而在实践中演化出脚色行当,最终成为戏剧的构成因素。
尽管在各自行进的漫长道路上,他们有交流,有借鉴,探亲访友,勾肩搭背,但却常分而短合。
它们像两个人那样,谈婚论嫁,生出了后代,但是这两个人依然是两个个体。
迄今为止,戏曲与祭祀仪式剧依然独自存在,甲不是乙,乙也不是甲。
今日如此,在古代,虽说巫、优分道扬镳,却的确未能彻底分开,也是事实。
而巫与优的未能彻底分开,同祭祀仪式剧与戏曲未能彻底分开,是一件事的两种表现。
这样的比喻似乎不尽科学,所以还得进一步论证。
继董康、王国维之后,冯沅君先生在她的《古优解》中展开了详细的论考,那是20世纪30年代末叶的事了。
她说:
“古优的远祖,导师、瞽、医、史的先路者不是别种人,就是巫。
在迷信的氛围极度浓厚的原始社会里,巫觋是有最大威权的,群巫之长往往就是王。
这类人所以能总揽一族大权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有时别人也认为)是神的化身,为神所凭依或神、人间的媒介;他们有神秘超人的法术、技能,以此法术、技能来满足一族人的为生存而发生的欲求。
因此远古巫者,大都用卜筮的方法(甚或不用)预测未来的祸福休咎,能为人疗治疾病,能观测天象,通习音乐,能歌舞娱神。
随着社会的演进,巫者技艺渐分化为各种专业,而由师、瞽、医、史一类人来分别担任,倡优则承继它们的娱神的部分而变之为娱人的。
”后世称谓戏曲演员为优伶、优人,便发端于此。
在此之后,巫的职责为娱神,而优则以娱人为其主业。
就整体而言,祭祀仪式剧与戏曲双双基本上恪守着原始的分野,一路长行。
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没有变通的存在,在巫的娱神中,也包含娱人,而优人也在娱神活动中,时而显露其身影。
二、演出形态的异同
细心的观众一定会发现戏曲与祭祀仪式剧在演出形态上的巨大不同。
我们常说,戏曲艺术是唱、做、念、打综合一体的。
我以为,这四个字应该有两种解读,一则唱、做、念、打被综合在每出戏中;二则唱、做、念、打被综合在一个剧中人物身上。
换言之,戏曲演员需要用此“四功”去完成戏剧人物塑造。
一般而言,需要具备以上两点才算满足戏曲的演出要求。
虽然事情并非如此绝对,有些戏并非唱、做、念、打齐备,如京剧《三岔口》突出的是“打”,基本没有“唱”,“念”也很少,但它仍然是戏曲。
又如申凤梅演出的越调《诸葛亮吊孝》,大段的“唱”与“做”却很少“念”,根本没有“打”,也依然是戏曲。
等等,例证很多。
个中的原因是什么?
本标题下暂不讨论。
这里,我们暂时关注一般性规律,个例或少量的剧目演出形态,不能撼动整体性特征,中国戏曲无疑是综合性戏剧艺术。
祭祀仪式剧则不尽相同,而且所呈现出的是比较复杂的局面,如祭祀仪式剧中重要的种类——傩戏,便比较纷纭复杂。
首先,我们把“傩戏”归类在祭祀仪式剧之中,可能有点儿不尽合理。
因为在傩的肇始阶段,虽入于礼,但还不属于严格的祭祀礼仪。
《周礼》记载傩礼在“夏官·司马·方相氏”。
周代设置六官,以司马为夏官,掌军政和军赋。
将驱傩的主帅“方相氏”置于执掌军政的官员“司马”之下,首先可以肯定“方相氏”属军中且官位不高,重要的还在于,“方相氏”不是巫。
《周礼》在男巫、女巫中,未列入方相氏,后世历代史书大都将驱傩置于军礼。
所以,当时的傩入于礼仪而不属于祭祀,何以如此?
关键的是没有巫的参与。
后来,驱傩主神告别了单打独斗的历史。
早在汉代,方相氏的麾下便增加了帮手,即所谓“十二兽”,十二兽的影响之深远,可在大唐宫廷驱傩中发现其遗响,《新唐书》描绘大傩仪所谓“十二神”以及今天山西曲沃《扇鼓神谱》中所谓“十二神家”,便与汉代的“十二神”遥遥相接。
可以想象,驱傩主神的变化与驱傩队伍的扩充,势必导致古傩形态的变化。
大约在隋、唐以后,巫与方相氏共同出现在宫廷大傩仪,分别执掌不同的仪礼程序,巫与方相氏依然没有合流。
大约在明清时代吧,民间的傩事活动渐渐不见了方相氏,而由巫师替代原本是方相氏的职能,成为驱傩者。
而一些道教以及民间信仰宗教中的神灵如白泽、钟馗、关羽、险道神等等,介入傩礼并一跃而为驱傩主神,甚至某些外来神灵如佛教保护神金刚力士、古波斯祆教(拜火教)的善神阿胡拉也在西域、荆楚一带的驱傩中闪亮登场。
而在西域,这些外来神灵与中国古老的白泽、钟馗等组成国际联军,共同讨伐魑魅魍魉。
隋唐以降,由于巫的加盟,使得傩礼与祭礼的界限模糊起来,到了明清时代,傩礼与祭礼最终合流,尤其在民间,执掌傩礼仪式以及傩戏演出的是巫师。
可见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古傩也在变化中延续。
在延续过程中,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不变体现在渐进式性质上,即在某个特定朝代,不会发生大变,因为大傩仪毕竟入于宫廷礼制,一个朝代的礼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但是在中国古代全史之中,傩礼傩仪的确在变中存在,在变中延续,而变才是它生命延续的条件、保障与必然。
汉代的傩与周代不同之处,还有其他方面。
这里我们特别关注的是驱傩词的引入。
至于为什么在变化的多种因素中,单单提出“驱傩词”,容待下述。
《后汉书·礼仪志》记述东汉宫廷大傩仪有这样一段:
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
曰:
“甲作食(歹凶),(月弗)胃食虎,雄伯食魅,
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
断食巨,穷奇、滕根共食蛊。
”凡使十二神追恶凶。
“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
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
”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
”
如何解读这段文字呢?
笔者认为,这是一段舞台脚本,它的排列应当如下:
[ 中黄门倡,侲子和。
中黄门 (倡)甲作食(歹凶),(月弗)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
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
错断食巨,穷奇、滕根共食蛊。
!
[ 凡使十二神追恶凶。
侲 子 (和)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
粮!
[ 作方相与十二兽舞。
如果我们认可以上解读与重新组织起文字的话,那么自然会读出更加重要一些的信息。
请注意“中黄门倡”一句,黄门为皇宫宫禁,也是官名,汉代的中黄门由宦官任职。
倡,在这里当作“唱”或“领唱”解。
“和”为唱、和之“和”。
这段文字把“中黄门倡,侲子和”提前,而把他们唱和的两段唱词后置,从而造成我们阅读与理解上的误差。
中黄门所唱,是分配某神制服某鬼的战斗任务;而侲子所唱则是对众鬼魅的告知与恫吓。
“中黄门倡,侲子和”、“凡使十二神追恶凶”、“作方相与十二兽舞”三句,相当于“舞台提示”。
综合看来,这是一段历史最早的大傩仪演出本,是汉代大傩仪的核心部分,而且具有恒定性。
恒定性表现在600年后的唐代,宫廷大傩仪的中心情节与唱词依然维持汉代原状而未作改变。
不过,正如前面说的,变是绝对的,而不变是相对的。
在整体不变的情况下,唐代大傩仪对汉傩进行了改革。
我们注意到,唱、和者做了部分调整,把汉代“中黄门”与“侲子”的对唱,置换为“方相氏”与“侲子”的对唱。
我们绝对不能无视这种变革,在笔者看来,方相氏与侲子唱、和这种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读罢上面引文,我们已经知道,汉代的方相氏是只舞不唱的。
到了唐代,宫廷大傩仪的方相氏又舞又唱。
舞与唱合于同一人物,是戏曲演出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进而言之,歌、舞、白的合流,即唱、舞、白三大表演手段合于场上同一个人物,是戏曲从古代祭祀礼仪衍生出来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古代祭祀礼仪一个明显特征,是祭祀程序的各个环节都有专门执掌者。
王国维先生指出:
“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与乐神人者也。
”还说:
“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
”进而言之,虽然统称为巫,但是巫有大巫、小巫之别。
祭祀时,小巫是大巫的助手;歌舞时,在通常情况下,大巫、小巫有分工,大巫舞则小巫歌,小巫舞而大巫歌。
正如清代毛西河所谓:
“古歌舞不相合,歌者不舞,舞者不歌。
”毛西河的这句话很重要,但却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毛西河这句话与史实基本相合,宋·陆游《秋赛》诗云:
“小巫屡舞大巫歌,士女拜祝肩相摩。
”宋·舒岳祥《乐神曲》:
“枫林沉沉谁打鼓?
农家报本兼祈禳。
打鼓打鼓急打鼓,大巫邀神小巫舞。
”诗歌描绘的是民间赛神娱神的情况,即便在祭祀活动相对松散的民间,也还有大巫、小巫的分工合作。
民间祭礼中大巫、小巫的分工合作制,无疑来自官方祭祀礼仪制度。
古代祭礼不但歌与舞分离,诵诗、乐手以及被祭祀的对象,也无不有专人专司其职。
其中“祝”负责颂辞与嘏辞的念诵。
《礼记·礼运》:
“修其祝嘏,以降上神。
”郑玄注:
“祝,祝为主人飨神辞也;嘏,祝为尸致福于主人之辞也。
”孔颖达疏:
“祝,祝为主人飨神辞也;嘏,祝为尸致福于主人之辞也。
”明·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卷六:
“祝者,陈其词于鬼神,又致鬼神之辞于主人之称也。
”颂辞,即颂扬祝福之词,祝是古代用语言(诗)沟通神、人的祭祀官员。
可见,在古代宫廷祭祀中,歌、舞、诗分别由三人执掌,互不相杂。
歌、舞、诗三者分离这一古代祭祀礼仪的规制,长期制约着、捆缚着祭祀礼仪中表演艺术的手脚,使之不能轻易地和三为一。
恰恰这一点造成了祭祀仪式剧不能充分地戏剧化,也造成戏曲艺术生成之期大大地延迟。
于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国戏剧艺术过长的怀胎过程。
在怀胎过程中,歌、舞、诗分别发展,虽然日臻完美,却迟迟未能合一。
一旦条件成熟,一朝落草,便很完美并迅速地攀升艺术的高峰,它虽然是初生的婴儿,却是个早熟的婴儿,甚至一跃而至成年,元人北曲杂剧便是例证之一。
我们一直不十分清楚,元人北曲杂剧何以在不知不觉中诞生,并迅速地攀登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高峰,原因可能正在于此。
前人曾对此做过各种探索,很多结论颇为有理,但是所找到的大都是客观因素,却忽视了歌、舞、白长期分离这一内在的艺术因素。
在元人北曲成就之前,我们看到诸多艺术形态,它们以歌、以舞,以滑稽性语言为主的队舞、队戏、宋杂剧等形态分头发展演进的事例。
我们还看到,在歌、舞、诗三者中,歌与舞率先合流在一起,因为歌与舞最易于合流,继之才是诗(语言)的部分加入。
唐宋时代的队舞,歌者、舞者尚处于分离状态,即便发展为可以敷衍故事的队戏,歌、舞、诗依然没有完全融合为一,去塑造人物。
这种分离状况的队舞、队戏,古今实例很多。
王国维先生早已关注的宋代大曲《剑舞》,它已经初步具备了故事情节以及人物,但是歌、舞、诗,仍有分离现象存在。
我们据《鄮峰真隐漫录》转录如下:
《剑舞》
二舞者对厅立禋上。
竹竿子勾。
念:
伏以玳席欢浓,,金樽兴逸。
听歌声之溶曳,思舞态之飘颻。
爰有仙童,
能开宝匣。
干将莫邪之利器,擅龙泉秋水之嘉名。
鼓三尺之荧荧,云间
电闪;横七星之凛凛,掌上生风。
宜到芳筵,同翻雅戏。
[二舞者自念:
伏以五行擢秀,百炼呈功。
炭炽红炉,光喷星日。
研新雪刃,气贯虹霓。
斗牛间,紫气浮游;波涛里,苍龙缔合。
久因佩服,粗习徊翔。
兹闻阆
苑之群仙来会,瑶池之重客,辄持薄枝。
上侑清欢,未敢自专,伏候处
分。
[竹竿子问:
既有清歌妙舞,何不献呈?
(二舞者答。
笔者案:
此处,似未记述答词。
旧乐何在?
(竹竿子再问。
一部俨然。
(二舞者答。
[二舞者答:
再韵前来。
[乐部唱【剑器曲破】。
乐作,舞一段。
[二舞者同唱【霜天晓角】:
荧荧巨阙,左右凝霜雪。
且向玉阶掀舞,终当有用时节。
唱彻,人尽説。
宝此制无折。
内使奸雄落胆,外须遣财狼灭。
[乐部唱曲子。
作舞【剑曲器破】一段。
[舞罢,二人分立两边。
别两人汉装者出,对坐。
桌上设酒果。
[竹竿子念:
伏以断蛇大泽,逐鹿中原。
佩赤帝之真符,接苍姬之正统。
黄威既振,天命
有归。
势虽盛于重瞳,德难胜于隆准。
鸿门设会,亚父输谋。
徒于起舞之雄
姿,厥有解纷之壮士。
想当时之贾勇,激烈飞飏;宜后世之效颦,回旋婉转。
双鸾奏技,四座腾欢。
[乐部唱曲子,舞【剑曲器破】一段。
[一人左立者上舞裀,有欲刺右坐客之势。
又一人舞进前,翼蔽之。
舞
罢,两人舞者并退。
汉装者亦退。
复有两人唐装者出,对坐。
桌上设笔砚纸。
一人换妇人装,独立裀上。
[竹竿子念:
伏以云鬟耸苍壁,雾榖罩香肌。
袖翻素霓以连轩,手握青蛇而的砾。
花影下
游龙自躍,锦裀上蹌凤来仪,轶态横生,瑰姿谲起。
倾此入神之技,诚为骇
目之观。
巴女心惊,燕姬色沮。
岂为张长史草书大进,抑亦杜工部丽句新成,
称妙一时,流芳万古。
宜呈雅态,以洽浓欢。
[乐部唱曲子,舞【剑曲器破】一段。
[作龙蛇蜿蜒曼舞之势。
两人唐装者起,二舞者一男一女对舞。
结【剑
器曲破】彻。
这个《剑舞》可以视为歌舞小戏,是一出“队戏”。
它由前后两段构成,前一段表现“鸿门宴”故事,是节目的中心,后面一小段则是一男一女对张旭草书的舞蹈化。
从内容上说,前后不搭,没有任何联系,联系二者的仅仅是【剑器曲破】,乃截取大曲中之【破】多次演奏,是一种音乐上的联系。
王国维先生说:
“由此观之,其乐有声无词,且于舞踏之中,寓以故事,颇与唐歌舞戏相似。
而其曲中有‘破’有‘彻’,盖截大曲入破以后用之。
”而定为“队舞”。
我们之所以认定其为队戏,是其已经有故事情节,也有人物,也在用曲、舞、白来表现故事,称之为“戏”,不为过也。
然而,它并未成熟为“戏曲”。
因为它在中心部分的“鸿门宴”中,虽有曲,却无歌唱,虽有诗,这诗却由竹竿子而非场上人物念诵,场上人物依然是“哑”的,不说也不唱。
所以,尽管已经敷衍故事,也有人物,却依然不够成熟,可以说,它是一种“准戏剧”形态,去戏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事实证明,举凡被称为“队戏”的戏剧形态,大体如此。
这出《剑舞》歌舞小戏演出还有另外一点值得关注,即乐部参与演唱。
文本中多次出现“乐部唱【剑器曲破】”、“乐部唱曲子”等舞台提示。
笔者认为,中国古剧发展到队戏阶段,虽然去戏曲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剑舞》既然有故事情节,就需要叙事,既然有人物,就需要表达人物的主张与情感、行为,那么“唱”就不再可有可无。
谁来演唱呢?
受古制的约束,“两人汉装者”不能唱,“诗”的部分被竹竿子分担了;同样受古制的约束,说与唱不能由一人承担,于是“乐部”便担当起演唱的大任。
实际上,这里的“乐部”与“竹竿子”类同,本质上都属于场上场下的脚色,从“竹竿子念”、“乐部唱”的角度说,他们是“场上”人;而从二者均未塑造人物的角度看,二者又属于“场下”人。
或者,这是中国古剧向高度综合性的戏曲过渡的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
历史推进到宋、金、元三代,在此前长时期的酝酿,不断地打破旧规,歌、舞、白努力汇集,终于诞生了南曲戏文及北曲杂剧。
而北曲杂剧的一脚色主唱的音乐演唱规制,或者可以遥遥地接续古老的祭祀礼仪有人专司演唱的陈规吧。
也就是说,北曲杂剧中的“一人主唱”是古代祭祀礼仪歌、舞、诗分离的一种延续。
与《剑舞》大同小异的队戏,在今天的山西、河北等地依然存在着,有些队戏的戏剧化进程甚至不如宋代的《剑舞》,有白,无歌,亦无舞的演出形态依然照旧。
四年前,我去武安东通乐村考察,亲眼看到数出队戏演出。
队戏《度柳翠》是学界人人皆知的剧目。
武安东通乐村的《度柳翠》与固义村的《度柳翠》不尽相同,该剧共三个人物:
和尚、柳翠、柳翠的用人。
三人在场上只有肢体语言而无歌、无白,简单的七言四句诗由站立一侧的竹竿子诵念,谓之“开”。
所以,剧名也叫《开度柳翠》。
竹竿子念道:
“回回吃酒回回醉,回回抱着旗杆睡。
若问对戏名和姓,月明和尚度柳翠。
”这四句顺口溜报告了三个信息:
剧名、酒后的和尚以及和尚与柳翠的尴尬故事。
严格地说这四句顺口溜不算道白,而是“开”,即“开呵”的省略语。
其它队戏《激张飞》《赵公明抓虎》《小国称》《大国称》《探神》《大耗小耗》等的演出形式与《度柳翠》别无两样。
河北固义村的“打黄鬼”大型赛社中演出的队戏《吊鬼兵》《吊劣马》《吊玄坛》等,场上人物有舞而无歌、无白,而故事情节与人物,也由立于舞台一侧的“竹竿子”诵念而出。
山西赛社有称之为“哑队戏”者,即为队戏中场上人物无歌无白的准戏剧品种。
不但中国,印度的传统舞剧“卡塔卡利”大都取材于《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演出时场上人物也是哑的,无歌无白,歌与白的任务由坐在旁侧的乐队担当,而丰富的肢体语言由场上演员担当。
日本号称“哑狂言”的京都壬生寺的“壬生狂言”,演出时偶有极少量说白,也由击鼓者或吹笛者分担。
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全国多地的傩礼之中,所以才有傩舞、傩戏之别。
所谓闭口傩,就是场上人物只能舞而不能开口歌唱,也没有道白;所谓开口傩,顾名思义,在人物歌、舞的同时,也可以道白。
所以,开口傩是相对成熟的傩戏,即便是这种看起来似乎很像戏的演出形态,仍不能与戏曲同日而语,其原因在后面将予以解说。
由此可见,古老祭祀礼仪的规制——各司其职的制约力量多么强大!
在歌、舞、诗三者合流的问题上,以娱人为主旨的戏剧形态率先突破重围,因为它必须完成娱人的需求,需要完美的演出呈现。
而作为祭祀礼仪的各种民间傩等,更多地恪守、也更易于保留古老的祭祀礼仪传统,从而延误了其向戏剧转化的速度。
一则,尽可能地恪守祭祀礼仪的旧规,是历代祭祀礼仪的法则,它依照这些法则而代代相传;二则,被祭祀的神灵不会像人类观众那样站出来表示对演出不够完美的不满,于是祭祀礼仪中的演剧进化程度,远不如以娱人为主要目的的戏剧形态来得迅速。
这或许是戏曲早就以其美轮美奂的身姿炫耀于世人面前,而祭祀仪式剧却依然端着古老的身段、踱着方步而蹒跚在各种祭祀空间的原因之一吧。
应该说明的是,在讨论演出形态的时候,应该涉及人物造型如面具、服饰等,也应该谈到声腔等演唱部分等等,但是限于篇幅,这里暂时不谈,而只就笔者认为重要的、不大为人关注的歌、舞、白的分合问题略陈己见。
三、展演空间异同
刚刚,我们提到“祭祀空间”,下面索性对戏曲与祭祀仪式剧的演出空间进行讨论。
戏曲与祭祀仪式剧的展演空间不尽相同,说“不尽相同”便意味着二者有相同或相似的展演空间。
而相同是相对的,不同则是绝对的。
虽然,戏曲与祭祀仪式剧都发端于古老的祭坛,但是这两个从同一摇篮中站起来的婴孩,却在不同的空间中展示身姿。
戏曲当其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也就逐渐地走出祭坛,迈进戏场。
虽然在走出祭坛的过程中时而徘徊,时而踟蹰,但目标却是明确的。
祭祀仪式剧不同,其演出空间几乎一直没有离开各式各样的坛场。
我们用极其粗略的形式表示不同历史时期戏剧演出及祭祀仪式剧的演出空间,大约是这样的:
戏 剧:
坛场——神庙剧场—→勾栏—→多种形式的剧场
祭祀仪式剧:
坛场———————————————→坛场
任何图标只能反映一个事物的大概,上图也一样。
戏曲与祭祀戏剧的展演空间原本不像这个图表那样简单。
戏曲在萌芽阶段便力图摆脱祭祀坛场的束缚,经由漫长的神庙剧场的展演,转身融入城镇,进入勾栏,成为向观众献艺的商品。
既然是商品,她就必然要满足五方杂处的城镇人群的需求,变着法地改进、变革而日新月异。
根据史料可知,北魏时期的寺庙演出,开后世长期寺院、神庙演出戏剧的先河。
这种戏剧乃至戏曲在寺院、神庙做场的习俗绵延日久,迄今依旧。
从宋代起始,与寺院、神庙做场并行不悖的是勾栏以及各种演出剧场迅速展开,再变为后世厅堂、会馆、市井剧场、宫廷剧场等等五花八门的展演空间。
而在这些展演空间中,我们时而会发现祭坛的痕迹,宋元勾栏式剧场,保留着“神楼”,那应该是神庙中供奉主神的正殿之微缩版,在北京老戏园子二楼后面,偶有神龛之设,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古老祭坛的遗痕。
同时,成熟后的戏曲也没有完全抛弃养育它的摇篮——祭祀坛场以及它曾经献艺的寺院、神庙剧场,时而走进去向神灵献艺。
不过,在戏曲返回祭礼空间的时候,情况不尽一样,如果在庙中戏台演出,则照本宣科,不做改变;若进入民间坛场,往往被简化、变为坛场风格的演出形态。
在山西曲沃《扇鼓神谱》中,有《采桑》一出戏,它的故事、主要人物、情节与元人北曲杂剧《汉钟离智勇定齐》的核心情节基本一致,我们怀疑《采桑》是对《汉钟离智勇定齐》杂剧的剪裁版。
在安徽池州傩坛上,也看到南曲戏文剧目。
此种现象比较普遍,绝不限于上述两例。
这些“坛外之戏”进入祭坛的时候,往往仅取其故事与人物等,而改变其演出形态,一般来说,需要一个去程式化的处理。
这里也有不同情况,当戏曲进入祭祀空间演出的时候,按照原本演出而不做改编,那么演出者大约是外请的戏曲戏班,这种演出带有助兴或凑凑热闹的性质,姑且把它叫做“外外坛戏”吧。
笔者估计,这种情况可能在晚近时期出现,不是傩戏等祭祀仪式剧的传统。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傩坛等祭祀坛场很少有纯观赏性的戏曲演出。
傩戏等祭祀仪式剧,它的根本属性是神灵的供品,它必须依附于祭祀仪式,必须在祭祀坛场中演出。
在本质上,傩戏等祭祀戏与奉献给神灵的绢帛、牺牲等没有区别,只是形态、形式不同而已。
这种根本属性受制于严格的祭祀规制而长期延续,至今未能彻底打破。
换言之,傩戏等祭祀仪式剧不过是祭祀礼仪的构成部分,它的存在价值也只有在祭祀礼仪中方能显现,离开祭祀礼仪,祭祀仪式剧的价值必将丧失或者大为减损。
正因为祭祀仪式剧的这种属性,使得它不便甚至不能进入戏曲的演出空间之中去展演。
何况,严格地讲,祭祀仪式剧不属于观赏性戏剧,不具备审美价值。
研究傩戏等祭祀仪式剧的人士,大约没有人抱着艺术鉴赏的心态去观摩,人们关注于傩戏等民间祭祀仪式剧的,几乎完全在于它珍贵的文化价值以及不可多得的历史价值。
身处村村寨寨的民众,同样不以艺术鉴赏为诉求,充其量是年节时的游乐,而根本的目的是连同祭祀者一起,完成对神灵的奉祀,人们或多或少的依然相信,经过这样的系列祭祀程序,一定会得到神灵的好感而应允他们的诉求——合村安稳、百姓无灾、骡马无病、收获满满。
这样的情况至今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更不必说古代。
说到底,民间祭祀礼仪的空间,是民众与神灵对话的空间,而不是艺术鉴赏的空间。
当然,普通百姓作为观众,也会或多或少地获得愉悦,到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仅凭这一点还不能撼动其祭礼空间的性质。
那么,在戏曲展演的空间中,几乎见不到傩戏等民间祭祀仪式剧演出,便是一种必然。
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