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书生.docx
《远去的书生.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远去的书生.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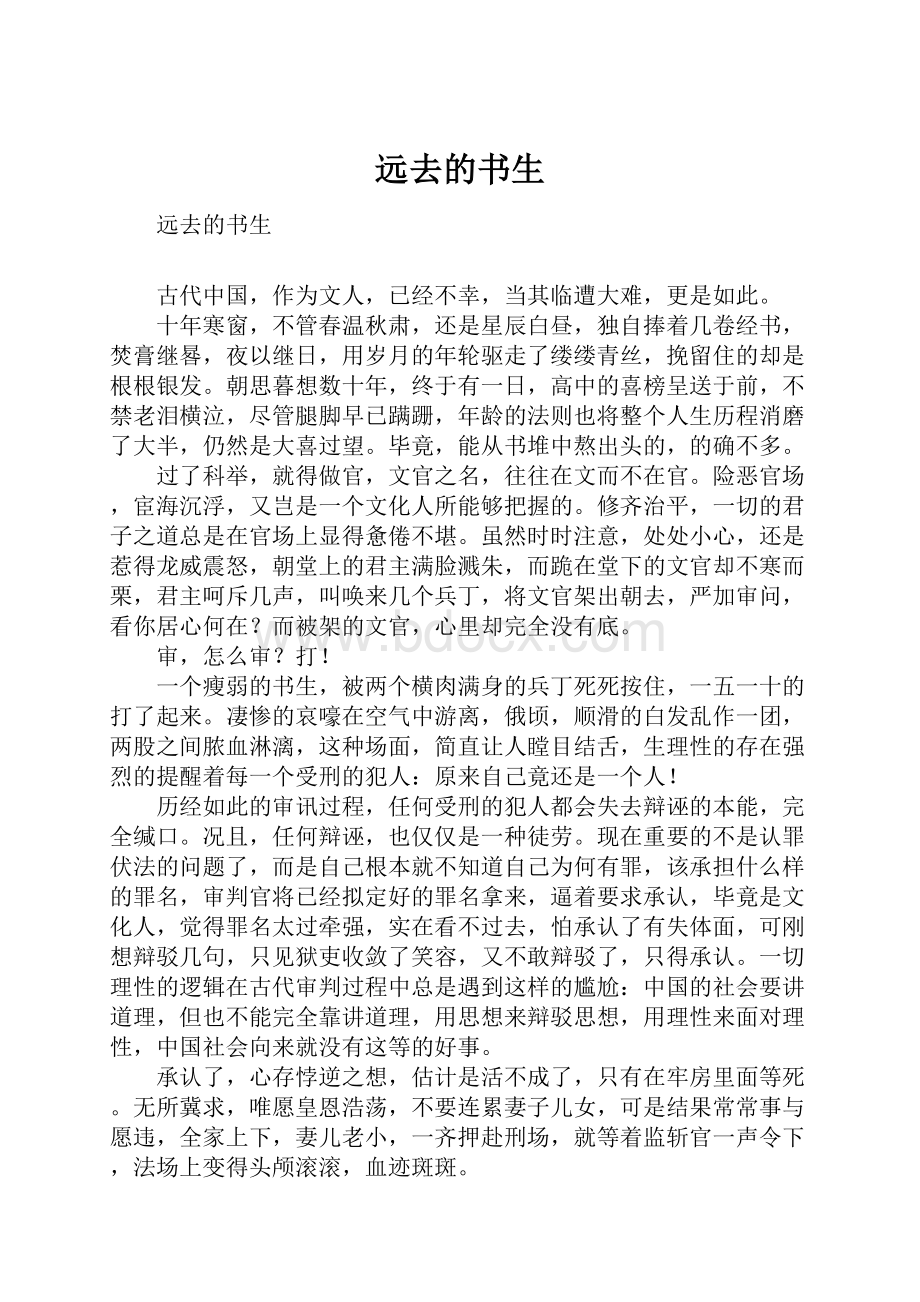
远去的书生
远去的书生
古代中国,作为文人,已经不幸,当其临遭大难,更是如此。
十年寒窗,不管春温秋肃,还是星辰白昼,独自捧着几卷经书,焚膏继晷,夜以继日,用岁月的年轮驱走了缕缕青丝,挽留住的却是根根银发。
朝思暮想数十年,终于有一日,高中的喜榜呈送于前,不禁老泪横泣,尽管腿脚早已蹒跚,年龄的法则也将整个人生历程消磨了大半,仍然是大喜过望。
毕竟,能从书堆中熬出头的,的确不多。
过了科举,就得做官,文官之名,往往在文而不在官。
险恶官场,宦海沉浮,又岂是一个文化人所能够把握的。
修齐治平,一切的君子之道总是在官场上显得惫倦不堪。
虽然时时注意,处处小心,还是惹得龙威震怒,朝堂上的君主满脸溅朱,而跪在堂下的文官却不寒而栗,君主呵斥几声,叫唤来几个兵丁,将文官架出朝去,严加审问,看你居心何在?
而被架的文官,心里却完全没有底。
审,怎么审?
打!
一个瘦弱的书生,被两个横肉满身的兵丁死死按住,一五一十的打了起来。
凄惨的哀嚎在空气中游离,俄顷,顺滑的白发乱作一团,两股之间脓血淋漓,这种场面,简直让人瞠目结舌,生理性的存在强烈的提醒着每一个受刑的犯人:
原来自己竟还是一个人!
历经如此的审讯过程,任何受刑的犯人都会失去辩诬的本能,完全缄口。
况且,任何辩诬,也仅仅是一种徒劳。
现在重要的不是认罪伏法的问题了,而是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何有罪,该承担什么样的罪名,审判官将已经拟定好的罪名拿来,逼着要求承认,毕竟是文化人,觉得罪名太过牵强,实在看不过去,怕承认了有失体面,可刚想辩驳几句,只见狱吏收敛了笑容,又不敢辩驳了,只得承认。
一切理性的逻辑在古代审判过程中总是遇到这样的尴尬:
中国的社会要讲道理,但也不能完全靠讲道理,用思想来辩驳思想,用理性来面对理性,中国社会向来就没有这等的好事。
承认了,心存悖逆之想,估计是活不成了,只有在牢房里面等死。
无所冀求,唯愿皇恩浩荡,不要连累妻子儿女,可是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全家上下,妻儿老小,一齐押赴刑场,就等着监斩官一声令下,法场上变得头颅滚滚,血迹斑斑。
当然,也有几个受刑者,或者因为是学富五车,亦或是功勋卓著。
皇帝会网开一面,选择轻一点的刑罚。
皇帝的恩赐呈送于前,双膝不禁又自然曲下,痛哭流涕,大叫皇上仁慈。
遭受惩罚还引得受惩罚人感恩戴德,天下也仅有中国有这样的道理。
但是,一个在文化上并不太差的文化人毕竟因此而躲过了一次人生浩劫,这就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书生的幸运了,有时就是整个文化史,也会跟着增色不少。
二
贬谪似乎是中国政治上的常用的惩罚手段了。
任何有违政治规则的政治家们,先是被皇帝以及其矫情的方式褒佳一番,然后调离京城,居赋闲置,中国政治之开明大抵也在这里。
数年后,当我们重新检阅这些卷宗后不禁发现,这里面居然还有不少才华横溢又人品出众的大学者,唐代的柳宗元就算一个。
唐顺宗永贞元年,王叔文政治改革失败,柳宗元先是被贬谪到了永州,后又改迁到了柳州。
任何历史的大豪迈或大悲壮之后总是潜藏着不少历史个体的喜怒辛酸,这本也算不了什么,但是,一旦历史的大线条与文化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就值得后世之人震撼几分了。
柳宗元的贬谪行程是从长安到永州的,两千多里的行程,都得由这位大学者一步又一步的走出来。
倘若是普通人,承受一下生理上的劳累也就罢了,而关键是柳宗元是一个书生,是一个文化人,他得想得更多,想得更远。
就这样一路想、一路走,想了许多,有对君王的哀叹,有对奸佞的愤恨,有对亲朋的牵挂,也有自己的反躬自省,想得多,就痛苦;想得远,就更痛苦。
就这样,即使到了永州,
跌荡的心绪仍然无法平静,索性放浪形骸,寄情于山水,但刚刚触摸到自然的淳朴,又不免对文化人的尊称产生了怀疑,恨不能让自己愚笨一点:
“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为愚’睿而为愚者也。
皆不得为真愚。
今予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
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予得而专名”(《全唐文》卷五百七十八)
但是,这是官话,是气话,也是文人的迂腐气。
毕竟,心绪还是眷念着朝廷,只是有心无力。
面对着时乖命蹇的窘态,也只有任岁月蹉跎,空叹怀才不遇:
“今弃是州也,农夫渔夫过而陋之。
价四百,连岁不能售。
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遇乎?
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朝也。
”(《柳河东集》卷三十)
显然,作者心有怨气,极不平静。
而这样的文章,后人读之,感受至深,无不拍案称绝。
想不到,文化的精神即使在穷乡辟壤也能复苏,当大师的文化结构超越灾难时,则灾难,亦是一种福音了。
但是,好景不长,柳宗元在永州做了十年的司马,终于于元和十年被贬到了更为荒凉的柳州,做柳州刺史,而这一次,柳宗元彻底绝望了。
“假令病尽身复壮,幽幽人世,不过三十年客尔。
前过三十七年与瞬息无异,后所得者,不足把玩,亦已审矣。
”(《柳河全东集》卷三十)
从对生的执著到对死的惊觉,柳宗元的人生彻底哲学化了。
Albert Camus说:
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自杀问题。
但是,从一个文学家蜕变为一个哲学家,对文化本身来说,并没有因此而遭受丝毫的损失。
而真正不幸的是:
四年之后,年仅四十六岁的柳宗元客死于柳州。
三
解读了一个柳宗元,已经让我们对这位远去的书生无所适从了,似乎人类的情感本身就是一个两难,这也难,那也难,只有静下心来,然后大哭一场。
与文化人受刑相比,柳宗元倒也是幸运了。
向来,政治犯是不用受刑的,而在中华法系中,政治犯连如此微薄的权利,竟也被无情的褫夺了。
“笞、杖、徒、流、死”,行刑的伎俩万千,花样百出,而行刑的时候,又远不及文本上写得文明,人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可能成为苦痛的由头,整个行刑的过程,变成了一场可供细细品味的精彩大戏,这些方法,也只有那些充满了想像,又完全泯灭了人性的法律家们才想得出来。
太史元年,一位史学大师在遭受了如此残酷的摧残后,拖着疲惫的脚步,缓缓的走出了大狱,他就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
司马迁是因李陵案的牵涉而下狱的,下狱时,司马迁万万没有想到事端竟然会变得如此严重,还对自己的罪行不以为然。
直到行刑时,司马迁才对他受的刑罚感到惊惧了,他竟要受宫刑,这会让一个名誉卓著的血性汉子名誉扫地,永远低头。
司马迁不得不痛苦了,他的心绪烦乱,一切可以他后来的书信作为佐证: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侮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
虽累百世,诟弥甚耳!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
每念于斯,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昭明文选》卷四十一)
受刑后,他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死,他一次次的想了却余生,但文化的责任感和文化人的使命感却一次次的阻止了他,他终于忍辱负重的活了下来了。
“仆窃不幸,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纪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
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昭明文选》卷四十一)
上述大著就是廿五史中的首部——《史记》。
当然,没有这场灾难,司马迁同样也写得出来,但是,可能远不如此发人深省,感人肺腑。
更难能可贵的是:
就是对汉武帝的功过得失,司马迁也作了公允的评述,而这一点,是以后许多的史学家自愧不如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史记》就成了廿五史中成就最高的一本著作了,连挑剔如鲁迅,对其也是啧啧称赞。
四
想不到最后,笔墨竟会点落在流放的刑种上了。
不管是贬谪还是受刑,毕竟还只是个体性的文化灾难,文化的伤害还是会轻许多,而流放刑种则不然了,往往是一个书香门第,上下老小,被一群兵丁驱赶着,一步步的向荒凉迈进,因为是书香门第,每个人的学问自然都不会太差,因此,流放反而转化成了一种群体性的文化大灾难了。
一大群人,有的早就不相往来了,想不到一场灾难,又从新将血缘关系扭结起来了。
而在这时,任何因连累而有怨气的文化人却将怨气完全收敛了,回去的希望既然已经渺茫了,心灵憧憬的心理防线也就自然脆折了大半,而情感,也就成了心理存在的唯一支撑了。
“嗟呼!
此札南飞,此身北滞,夜阑秉烛,恐遂无期,唯愿尺素时通,以当把背,唱酬万里,敢坠斯言。
”
(《寄顾舍人书》)
此人就是清朝的著名学者吴兆骞。
顺治十四年,吴兆骞卷进了南闱科场案,顺治帝震怒,于顺治十五二月在中南海亲自考试此次中榜的正副举子,每个举子都带上刑具,由护军营的军校持刀监视。
吴兆骞一看,自己是江南名士,怎么会因区区一个举人而行贿考官,引得如此考试,范得着吗?
一向文章“惊才绝艳”的他,这次竟交了白卷。
本来这也算不了什么,书生的木讷与迂腐,忍一忍也就算了,想不到年方二十的顺治帝对此却大动肝火,对其惩罚之严,已完全达到了离谱的程度:
“方章钺、吴兆骞等十八名考生,具著责四十大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流徙宁古塔。
”(《清世祖实录》卷十八)
吴兆骞来到了宁古塔,这里自然条件之恶劣已完全超出了他的想像,他到了宁古塔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赶快回去,闲暇时间,他就写诗,他后来送给纳兰容若的两首《金缕曲》,写得悲愤慷慨,感人至深,当纳兰容若看到这首词时,竟被催得声泪俱下,甘心帮着赎回吴兆骞。
除了劳作,吴兆骞还写诗。
宁古塔是荒凉野蛮之地,想不到文化的热度最终温暖了人心,融化了愚昧,一个个粗壮彪悍的东北汉子,也能静静地聆听君子之道、圣人之言,我不知道当吴兆骞面对如此的情景时作如何感想,反正我是被这种对文化的虔诚深深的打动了。
本来,文化就不应该对任何人类群落吝啬,而应该去惠及众生,当二十三年后,吴兆骞离开宁古塔的时候,不说桃李天下,也是学生满堂了,对于东北的开化,吴兆骞的确是有贡献的。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直到康熙二十年,吴兆骞终于奉诏赐还,而这时候,早年的英姿不见了,只留得满头银发,连他在东北生的儿子,也足足有了十七岁。
而尽管这样,重新回来仍然使得这位老者泪眼盈眶,感慨万端:
“与亲友相聚,执手痛哭,真如再生也。
流人复归本土,玉门之关既入,才子之名大振。
(吴振臣《宁古塔记略》)
吴兆骞回来的时候,纳兰容若也赋诗一首:
“星沉渤海无人见,枫落吴江有梦还。
”
纳兰容若的评价无疑是中肯的,吴兆骞二十三年的流人史,除了留下一个凄冷的故事外,也仅剩下几卷动人的诗稿了。
显然,我仅仅是撷取了流放刑种中的一例,来说明了文化灾难之残酷,当政治强权引得一个文化整体走向灾难时,那么一个王朝的政权,也要因此而覆灭了,清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五
眼睁睁的看着伤痕累累的书生离我们而远去了,我恨不能拔腿追赶上去,但是,面对他们因此而留下的文化经典,我又只能将指点方向的手指垂放下来,停驻行进的脚步,浩叹一声。
灾难在造就书生痛苦的同时,又彻底把他们从书生的学究气和迂腐气中剥离出来了,在灾难的旋涡中,他们渐渐明白,什么是鲜活的人情世故?
什么是实在的事态人情?
什么又是真正的人生大义?
这一点,当然不是能在冰凉的书本中入木三分、洞若观火的。
由此而对比整个中华文明的脆弱点,也正是在于如此实证的功夫下得太少,因此,在近代,我们的文明就必然要衰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的文化大灾难就必然伴随着文化大兴盛,而事实上,大灾难仅仅引领着个体性的文化人格的辉煌,而与此同时,又必须以整体性的文化委顿为代价,个体的文化人需要吃苦,但整体上脆弱的文化往往又经不起吃苦,常常在灾难过去数年后,整体性的文化才能缓缓复苏。
或许,真正的文化浩劫还远不在这里,而是错误的将愚昧当成了文明。
四十年前,当一场文化的浩劫被革命的外衣包裹时,一个个文化人被强行的驱出了文化的现场,一本本文化经典被搬到了操场,然后堂而皇之的付之一炬,孰不知,人类的一切愚昧,往往要从烧书开始。
面对一次次的文化灾难,我只有祷告,祈求上苍不要再给文化人制造灾难了。
假如还有,救救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