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闲适与道德解读周作人的谈鬼.docx
《从闲适与道德解读周作人的谈鬼.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闲适与道德解读周作人的谈鬼.docx(2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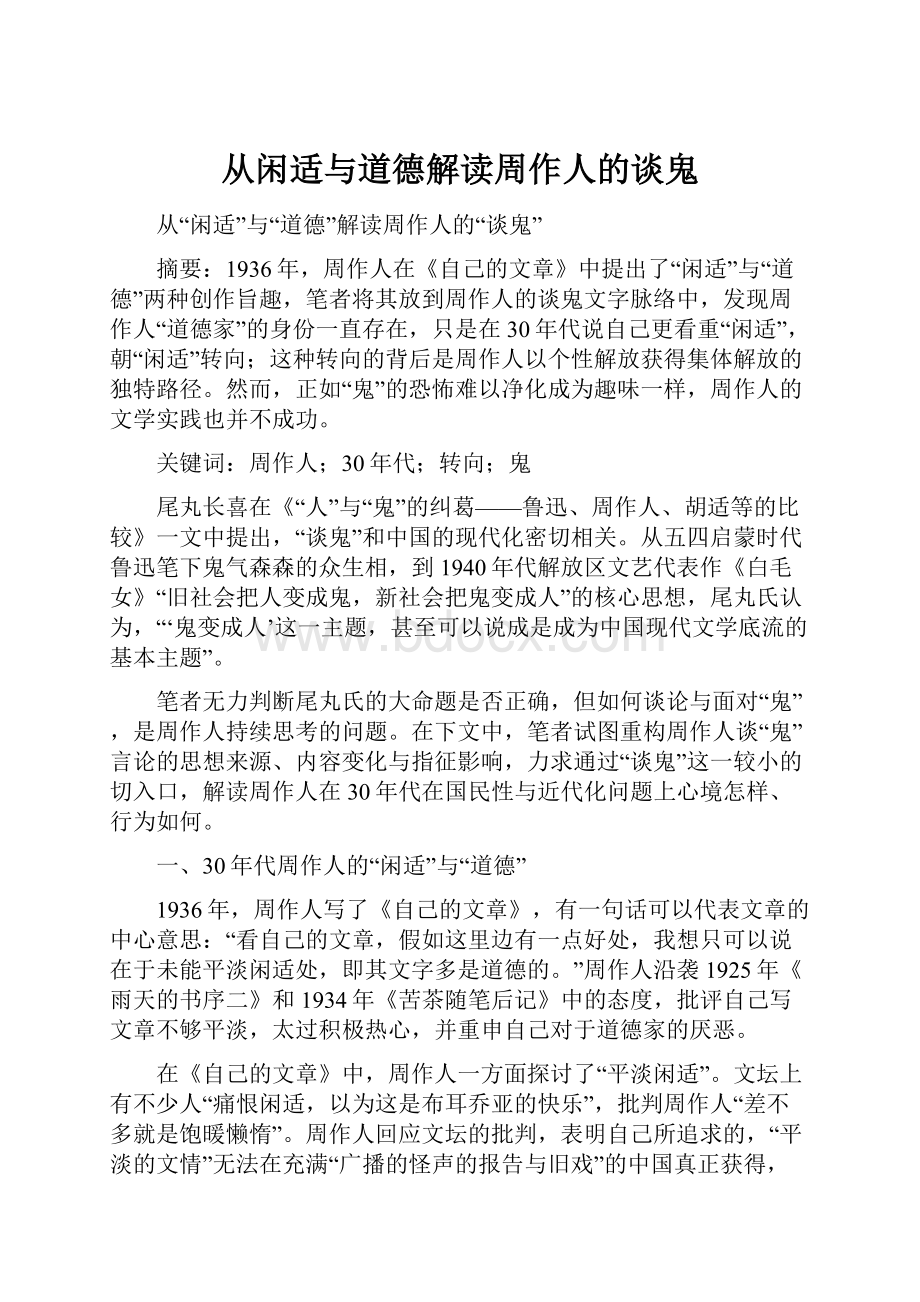
从闲适与道德解读周作人的谈鬼
从“闲适”与“道德”解读周作人的“谈鬼”
摘要:
1936年,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了“闲适”与“道德”两种创作旨趣,笔者将其放到周作人的谈鬼文字脉络中,发现周作人“道德家”的身份一直存在,只是在30年代说自己更看重“闲适”,朝“闲适”转向;这种转向的背后是周作人以个性解放获得集体解放的独特路径。
然而,正如“鬼”的恐怖难以净化成为趣味一样,周作人的文学实践也并不成功。
关键词:
周作人;30年代;转向;鬼
尾丸长喜在《“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周作人、胡适等的比较》一文中提出,“谈鬼”和中国的现代化密切相关。
从五四启蒙时代鲁迅笔下鬼气森森的众生相,到1940年代解放区文艺代表作《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核心思想,尾丸氏认为,“‘鬼变成人’这一主题,甚至可以说成是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底流的基本主题”。
笔者无力判断尾丸氏的大命题是否正确,但如何谈论与面对“鬼”,是周作人持续思考的问题。
在下文中,笔者试图重构周作人谈“鬼”言论的思想来源、内容变化与指征影响,力求通过“谈鬼”这一较小的切入口,解读周作人在30年代在国民性与近代化问题上心境怎样、行为如何。
一、30年代周作人的“闲适”与“道德”
1936年,周作人写了《自己的文章》,有一句话可以代表文章的中心意思:
“看自己的文章,假如这里边有一点好处,我想只可以说在于未能平淡闲适处,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
”周作人沿袭1925年《雨天的书序二》和1934年《苦茶随笔后记》中的态度,批评自己写文章不够平淡,太过积极热心,并重申自己对于道德家的厌恶。
在《自己的文章》中,周作人一方面探讨了“平淡闲适”。
文坛上有不少人“痛恨闲适,以为这是布耳乔亚的快乐”,批判周作人“差不多就是饱暖懒惰”。
周作人回应文坛的批判,表明自己所追求的,“平淡的文情”无法在充满“广播的怪声的报告与旧戏”的中国真正获得,只是心向往之。
他实际上是积极的,因为“歌于斯哭于斯的地方”“眼见得那么不成样子”,“令人怒从心上起”,“平淡乃是跛者之不忘履也”。
然而,周作人的潜台词,始终把“平淡”当成最高理想,试图说服大众认可“平淡”。
“平淡”不同于“闲适”,前者是周作人一贯推崇的,后者却是文坛诸公“改换名目称之日闲适”,重命名后加以批判的对象。
《自己的文章》里,两者的区别被周作人自己消弭,他确认“平淡闲适”是自己追求、却未能实际达到的境界。
他进一步将“平淡闲适”分为农人驻足观水式的“小闲适”,和“以婉而有趣的态度”面对生死问题的“大幽默”、“大闲适”。
另一方面,周作人探讨了“道德”问题。
他重申自己在《雨天的书序二》中提出的“最讨厌道学家”的立场,反省这种厌恶乃由于“自己是一个道德家”,厌恶对方的“伪道德不道德”,恰是“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道德来”。
他重申了自己的“道”:
“我的道德观恐怕还当说是儒家的,但左右的道与法两家也都掺合在内,外面又加了些现代科学常识,如生物学人类学以及性的心理,而这末一点在我较为重要。
”
《自己的文章》是周作人有关创作的内心剖白,他多次征引前作并进一步阐释,可见其30年代的文学思路的变化是非常坚定的。
我们可以参考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传》中对周作人30年代转变内核的解释,加深对“闲适”和“道德”的理解。
当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抛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的集体主义的时候,周作人高举起了“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
谈鬼画蛇的闲适,是个性解放与自由的体现;盼望社会进步、所有人都好的道德家心态,却又是集体主义的体现。
周作人努力建构起一条从个性解放推及集体革命之路,试图将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事业相调和,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也是他的不足之处。
通过研究周作人笔下的“鬼”,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具体的实践中的不成功。
二、周作人在创作中如何谈“鬼”
“鬼”是周作人写作的重要话题。
《五十自寿诗》中有“街头终日听谈鬼”;1926年,周作人在《两个鬼》中说,“在我的心头住着DuDaimone,可以说是两个——鬼。
……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
”这两个鬼是周作人灵魂中绅士风度与臭架子、流氓胆量质朴和市侩恶俗的化身,周作人终身受这两个鬼的牵扯。
周作人动辄讲鬼,还拿鬼来代指自己灵魂中的两个相面,谈“鬼”贯穿了周作人的创作生涯。
“谈鬼”很好地体现了周作人30年代从“道德”到“闲适”的转向,以及他在试图调和二者的状态。
笔者认为,周作人谈“鬼”可分为两种,其一是文学或者生物学上的某种神秘生物,其二是人世间鬼鬼祟祟的思想和行为;前者乃接近“闲适”的“鬼味与谐趣”(《谈鬼论》),后者则为接近“道德”的借鬼讽世;前者因谈鬼有趣味所以爱谈,后者则乃鬼可见人心讽世事而谈。
这两种鬼紧密联系在一起,难以断言某一处具体的谈鬼到底是出于“兴趣”还是“世道人心”。
附录中笔者摘取了周作人1918-1936年间的“谈鬼”文字,制成表格,附在最后。
学界有人说周作人“谈鬼”是逃避现实人生、不负社会责任是不对的。
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所谈的两种鬼常常在一篇文章中同时出现,而周作人想要极力压抑的谈“道德”,实际上从未绝迹。
我们至多可以讲,1928年及之前,周作人多为借鬼讽人,少见单纯谈鬼本身的文字;1929年之后,从文艺或生物学出发单纯讲鬼的文字变多了。
1928年及之前,周作人的“谈鬼”方式与鲁迅相似,拿“鬼”来指国民精神的劣根性,他在《济南道中》(1924)声明自己“大体上赞成”“打‘玄学鬼’与‘直脚鬼’”,在《茶话·永乐的圣旨》(1925)里写“朱棣的鬼还是活在人间,所以煞是可怕。
不但是讲礼教风化的大人先生们如此,便是‘引车卖浆’的老百姓也都一样,只要听他平常相骂的话便足以证明他们的心是还为邪鬼所占据。
”在《爆竹》(1925)中写“中国人的生活里充满着迷信,利己,麻木,在北京市民彻夜燃放那惊人而赶鬼的爆竹的一件事上可以看出,而且这力量又这样大,连军警当局都禁止不住。
”仅举三例,周作人直面国民劣根性的地方还有很多。
在这一时期,周作人出于兴趣写了《花煞》(1925)一篇介绍绍兴人结婚时捉弄人的小鬼花煞,未有什么批判之意;这种单纯谈“鬼”的文字在这一阶段仅此一篇。
总体来讲,周作人这一阶段的战斗性还是很强的,可仔细体会他的文字,相较于尖锐锋利的“投枪”要温和迂回许多。
到了1930年,周作人的谈“鬼”发生了转变。
他在《艺术与生活序二》中写道:
“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不过以前还凭了少年的客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亦无非是自骗自罢了,近几年来却有了进步,知道自己的真相,由信仰而归于怀疑,这是我的‘转变方向’了。
不过我并不倚老卖老地消极,我还是很虚心地想多知道一点事情,无论这是关于生活或艺术以至微末到如‘河水鬼’这类东西。
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宣传,我只要听要知道。
”周作人认为,自己以前的高谈阔论是由于少年的客气,可以弃之不取,他转向“河水鬼”,是为了“知道一点东西”。
1929-1930年《伟大的捕风》《水里的东西》两篇,均是这种“转向”的标识。
周作人仍旧讽刺性地描述国民精神中的“遗传神君”——小鬼,骂二十四史是鬼画符,也开始认真地介绍死鬼——幽灵、活鬼——僵尸、河水鬼和日本的河童等。
更能体现其转向的是,他建议大家把“守护天使,三尸神”作为“很有趣味的笔记材料”“稍能反省”,大力提倡“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这一角落的明灯”,以“河水鬼”作为先锋,期待更多人通过这条路径,去“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
1929年之后,周作人的“谈鬼”,是他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的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俗与神话》《希腊神话》与《金枝上的叶子》介绍了古希腊古埃及的英雄及神鬼观念,《鬼的生长》《刘青园常谈》《洗斋病学草》《文字的趣味》《游山日记》《关于雷公》等介绍了古书中的鬼,《谈油炸鬼》《儿时的回忆》《再谈油炸鬼》从民俗入手论鬼,《说鬼》《谈鬼论》则是说“谈鬼”,应对外界的批判、澄清自己的立场,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谈鬼。
《谈鬼论》集中体现了周作人的转向。
周作人从理论的角度,将“说鬼”分为文艺与历史两途,提醒后继者将“鬼”的文本用作文学作品与民俗两种学科的研究。
第一类乃“文艺”上“写得好,简洁而有力”的“好故事”,鬼故事是故事的一种,“以志怪为目的”,生动活泼,很有趣味;第二类乃“历史的,再明了的说即是民俗学上的兴味”,不信鬼但喜谈鬼,通过鬼看到人的“喜惧愿望”。
周作人喜欢谈鬼,谈“鬼”时常常怀抱现世关怀,他从鬼的故事中看出人情,也借鬼讽人;读文艺、看民俗,谈鬼以识人,是周作人提倡的了解人的根本途径。
这一途径强调国民通过自我反省和学术研究,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从而振奋精神,发愤图强。
他不再振臂高呼,尽力停止以“鬼”骂人,尽量避免直接指出国民性如何糟糕,而是为后来者指出“自我启蒙”的路——去研究古今中外文艺中的鬼,思考“鬼故事”背后的人;去探究乡村野地里的鬼神信仰,看看中国人精神最原始是什么样子、什么东西会“遗传”、以及我们如何看待和面对这些东西。
不再是振臂高呼的“道德家”,而转变成态度平和的“闲适人”。
周作人写诸多文章,实际上是在做研究范例,他研究文艺和民俗,且寻求同路人和他一道。
他只是换了一个关心社会的方式,却从未放弃他对于自己心中独特的“道德”追求。
三、谈鬼中“闲适”与“道德”两种语境之贯通
强调每一个人的发展和幸福,这实际上是周作人的思想底色。
早在1918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将“人兽鬼”三道并举,都是人行于世的方式。
社会上许多人“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旁皇了多年,才得出来”。
1924年《我们的敌人》沿用这种说法,“我们的敌人……不是活人,乃是野兽与死鬼,附在许多活人身上的野兽与死鬼。
”一些人身上没有人性,反而有残忍的兽性和阴阳怪气的鬼性。
1935年《日本管窥之三》中说“残忍的恶风与怕鬼的迷信也只是人类所有,在动物里不能发见”,但却都是“动物以下的变态”,不能和“人情之美”相提并论。
周作人的“人兽鬼”三道,是人之三种状态的表现。
人道仁恕有情,兽道残忍暴虐,鬼道阴恻玄乎。
1935年《刘青园常谈》中摘刘青园说纪晓岚“鬼道设教”,虽然能补“王法所不及者”,却终究解释鬼神,落人口实。
刘青园觉得以鬼故事宣传人道,终究不合适。
周作人这样评价刘青园的看法:
以鬼道设教,既有益于人心世道,儒者宜赞许之,但他终致不满,这也是他的长处,至少总是一个不夹杂道士气的儒家,其纯粹处可取也。
从周作人的语气读者能够看出,他不赞同刘青园的意见,也不以纯粹的儒者自况。
寄道于鬼神,是周作人常用的一种手段。
周作人在1936年的《谈鬼论》中征引1934年所写《鬼的生长》,可以看做“道”隐于“谈鬼”写作方式之纲领:
“我不信鬼,而喜欢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
虽然,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当不谬也”
张载《正蒙·太和》载:
“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张载将鬼神解释为阴阳二气的屈伸;周作人说自己不懂,实际是不屑于古人强释鬼神。
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上,他不信有鬼,但他认同鬼乃中国人关于死亡之后的讨论,蕴藏了人的种种情态。
周作人似乎找到了一条以人道主义结合个人与集体的大道。
当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了理智和人道主义精神,意识到了鬼神之谈背后的国民劣根性,了解了人生的喜惧愿望,那么健全理智的社会才有可能出现。
人在没有思考清楚自己之前去批判社会,以周作人的视角看,无疑有些幼稚。
然而,虽然周作人提出了自己的救国道路,确定了自己文学实践的方向,却没有获得成功的实践结果。
四、“闲适”与“道德”两种语境之难以调和
刘皓明在《从“小野蛮”到“神人合一”》中说,周作人的思想底色有相当一部分18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内容,浪漫主义把人类看做超越意义的神性整体,而人类个体价值的实现,便在于发明个人内在神性,并看到他人身上的神性。
如此,个人就可以存在于人类神性的整体之中,达到最终的超越。
周作人提出从谈鬼中得知人性、从个人澄明到集体澄明的道路,大概也有浪漫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另一个方面,便是浪漫主义中对于“恐怖”和“癫狂”的独特嗜好。
谈鬼的“趣味”,距离恐怖与冷漠只有很短的距离,而谈鬼的“兴趣”很容易迷失于“为谈鬼而谈鬼”的歧路。
考察周作人30年代的文学创作,有不少和国民劣根性等现实指向完全无关,在人兽鬼三道之外单独拎出“鬼”来谈论。
例如《文字的趣味一》,全篇考证日语中“饿鬼”“山神”“阿魔”等词汇的读音;《儿时的回忆》闲笔叙述儿时的“反案鬼”,还“查《越谚》卷中鬼怪类虽有大头鬼独脚魈等十几种”……周作人似乎并不热络于想虫鱼神鬼能否带来及时的社会效益,我们很难完全分辨清楚,他的文字何种程度上出于兴趣,何种程度上出于为后来者指路、开拓新的学科方法、从而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感。
笔者认为,周作人最感兴趣的一直是社会中的文艺问题,而非政治问题。
1925年《黑背心》一篇中提出,他“对于什么民有民享,什么集会言论自由,都没有多大兴趣”,而关心“文字狱信仰狱等思想不自由的现实”。
在文艺问题中,“谈鬼”对周作人而言是很有意思的题目,做起来颇有趣味,不觉厌烦;1932年《杂拌儿之二序》中有:
“但是话虽如此,我们固然也要听野老的话桑麻,市侩的说行市,然而友朋间气味相投的闲话,上自生死兴衰,下至虫鱼神鬼,无不可谈,无不可听,则其乐益大,而以此例彼,人境又复不能无所偏向耳。
”
如此孜孜不倦地谈鬼,很难让人相信周作人没有丝毫个人的“恐怖趣味”。
付丹宁在《“谈鬼”的正与变——1930年代周作人的神话学历史观及其文学实践》一文中,深入剖析了30年代周作人谈鬼的文学实践的紧张结构,作者从希腊神话将“恐怖”变为“崇高”开始叙述,找到了周作人《缢女图考释》和《鬼的叫卖》两篇未收入自编文集的文章为例,论证周作人没有成功地将“恐怖”洗脱出惨烈现实,在发言描写恐怖的同时已经消解了现实的严肃性。
笔者认为,这篇文章很好地揭示了周作人“谈鬼”难以获得其期待的社会效应之原因。
谈鬼的“闲适”和“恐怖”或“猎奇”只有一墙之隔,但通过“谈鬼”获得个人的澄明、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却是长路漫漫。
救国压倒一切的语境下,周作人这种先救出“一个人”的逻辑,被集体携笔从戎、以笔为枪的逻辑打败,是正常的。
而其中纠结,周作人只能在苦雨斋中吃苦茶来消化与和挣扎,无人能解。
附录1
以“闲适”与“恐怖”分类周作人之谈鬼文字
题目
创作时间
文学或者生物学上的某种神秘生物
人世间鬼鬼祟祟的思想和行为
人的文学
1918
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
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
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旁皇了多年,才得出来。
文艺上的异物
1922
古今的传奇文学中,多有异物——怪异精灵的出现。
……现在姑取异物中的最可怕的东西——僵尸——作为一例。
民间的习俗大抵本于精灵信仰(Animism),在事实上于文化发展颇有障害,但从艺术上平心静气地看去,我们能够于怪异的传说里面瞥见人类共通的悲哀或恐怖,不是无意义的事情。
科学思想可以加入文艺里去,使他发生若干变化,却决不能完全占有他,因为科学与艺术的领域是迥异的。
文艺批评杂话
1923
我们常听见人拿了科学常识来反驳文艺上的鬼神等字样,或者用数学方程来表示文章的结构,这些办法或者都是不错的,但用在文艺批评上总是太科学的了。
茶话·永乐的圣旨
1926
我相信像上边所录的圣旨是以后不会再有的了,但我又觉得朱棣的鬼还是活在人间,所以煞是可怕。
不但是讲礼教风化的大人先生们如此,便是“引车卖浆”的老百姓也都一样,只要听他平常相骂的话便足以证明他们的心是还为邪鬼所占据。
——赶走这些邪鬼是知识阶级的职务,我希望他们多做这一步工夫,这实在要比别的事情更为根本的。
花煞附结婚与生死
1926.3.9
花煞是一种在人们结婚时候捉弄人的凶鬼。
至于绍兴的风俗是什么意思我还不能领会,我看他不是同希腊那样的拿新娘的花冠去给死人戴,大约是颠倒地由活人去学死装束的。
中国人的心里觉得婚姻是一件“大事”,这当然也是有的,但未必会发生生与死相联属的深刻的心理;独断地说一句,恐怕不外是一种辟邪的法术作用吧。
爆竹
1924.12
我们的敌人是什么?
不是活人,乃是野兽与死鬼,附在许多活人身上的野兽与死鬼。
济南道中
1924.5.31
中国近来新起一种“打鬼”——便是打“玄学鬼”与“直脚鬼”——的倾向,我大体上也觉得赞成,只是对于他们的态度有点不能附和。
我们要把一切的鬼或神全数打出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更无论他们只是拍令牌,念退鬼咒,当然毫无功效,只足以表明中国人术士气之十足,或者更留下一点恶因。
我们所能做,所要做的,是如何使玄学鬼或直脚鬼不能为害。
我相信,一切的鬼都是为害的,倘若被放纵着,便是我们自己“曲脚鬼”也何尝不如此。
济南道中之三
1924.6.10
中国现在有相信鬼神托梦魂魄入梦的人,有求梦占梦的人,有说梦是妖妄的人,但没有人去从梦里寻出他情绪的或感觉的分子,若是“满愿的梦”则更求其隐密的动机,为学术的探讨者;说及神话,非信受则排斥,其态度正是一样。
读京华碧血录
1924.4
我不相信中国会起第二次的义和拳,如帝国主义的狂徒所说;但我觉得精神上的义和拳是可以有的,如没有具体的办法,只在纸上写些“杀妖杀妖”或“赶走直脚鬼”等语聊以快意,即是“口中念念有词”的变相;
黑背心
1925.6
我不知怎的觉得是生在黑暗时代,森林中虺蜴虎狼之害总算是没有了,无形的鬼魅却仍在周围窥伺,想吞吃活人的灵魂。
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
1925.6.1
如吕滂(GustaveLeBon)所说,人世的事都是死鬼作主,结果几乎令人要相信幽冥判官——或是毗骞国王手中的账簿,中国人是命里注定的奴才,这又使我对于一切提唱不免有点冷淡了。
我的微小的愿望,现在只在能够多了解一分,不在能成功一厘,所以这倒也还无妨无妨。
两个鬼
1926
在我的心头住着DuDaimone,可以说是两个——鬼。
我踌躇着说鬼,因为他们并不是人死所化的鬼,也不是宗教上的魔,善神与恶神,善天使与恶天使。
他们或者应该说是一种神,但这似乎太尊严一点了,所以还是委屈他们一点称之曰鬼。
这两个鬼是什么呢?
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
古朴的名字
1926.11.20
鬼怪似乎都是很笨,而且容易被骗的,我们只要看那很通行的,给小孩起一个污糟讨厌的名字的习惯,便可明白了。
这会引起鬼怪的嫌恶,觉得这样的小孩是不值得去麻烦的。
聊斋鼓词六种序
1928.11.21
他写狐鬼和人一个样子。
除了说明他们本相的地方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妖气,我想在青年读者羡慕之余,以为狐鬼亦佳者当复不少,所以他这实在是狐鬼的人化,俗传此书本名“狐鬼传”,专以讽刺人间者,未免是齐东野人之语(荒唐而没有根据的话)了。
我又记得题词中有这两句: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我很喜欢这种态度,这是一种文学的心情,不汲汲于功利,但也不是对于人事完全冷淡,只是适中地冷静处之罢了。
闭户读书论
1928.11
通历史的人如太乙真人目能见鬼,无论自称为什么,他都能知道这是谁的化身,在古卷上找得他的元形,自盘庚时代以降一一具在,其一再降凡之迹若示诸掌焉。
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
历史
1928
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
“僵尸,僵尸!
”我完全同感于阿尔文夫人的话。
世上如没有还魂夺舍的事,我想投胎总是真的,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时代的戏,不必请戏子去扮,许多脚色都可以从社会里去请来,叫他们自己演。
我恐怕也是明末什么社里的一个人,不过有这一点,自己知道有鬼附在身上,自己谨慎了,像癞病患者一样摇着铃铛叫人避开,比起那吃人不餍的老同类来或者是较好一点了吧。
伟大的捕风
1929.5.13
普通鬼有两类。
一是死鬼,即有人所谓幽灵也,人死之后所化,又可投生为人,轮回不息。
二是活鬼,实在应称僵尸,从坟墓里再走到人间,《聊斋》里有好些他的故事。
此二者以前都已知道,新近又有人发见一种,即梭罗古勃(Sologub)所说的“小鬼”,俗称当云遗传神君,比别的更是可怕了。
只要稍能反省的朋友,对于世事略加省察,便会明白,现代中国上下的言行,都一行行地写在二十四史鬼簿面画符,念咒,这岂不是上古的巫师,蛮荒的“药师”的勾当?
但是他的生命实在是天壤无穷,在无论那一时代,还不是一样地在青年老年,公子女公子,诸色人等的口上指上乎?
即如我胡乱写这篇东西,也何尝不是一种鬼画符之变相?
只此一例足矣!
水里的东西
1930.5
我们乡间称它作Ghosychiü,写出字来就是“河水鬼”。
它是溺死的人的鬼魂。
……河水鬼的法门也就差不多是这一类,它每幻化为种种物件,浮在岸边,人如伸手想去捞取,便会被拉下去,虽然看来似乎是他自己钻下去的。
假如吊死鬼是以色迷,那么河水鬼可以说是以利诱了。
河水鬼大可不谈,但是河水鬼的信仰以及有这信仰的人确实值得注意的。
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域,但总部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是这一角落的明灯,不过在中国自然还不发达,也还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发达。
我愿意使河水鬼来做个先锋,引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之兴趣。
我想恐怕喜欢顿铜钱的小鬼没有这样力量。
艺术与生活序二
1930.10.13
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不过以前还凭了少年的客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亦无非是自骗自罢了,近几年来却有了进步,知道自己的真相,由信仰而归于怀疑,这是我的“转变方向”了。
不过我并不倚老卖老地消极,我还是很虚心地想多知道一点事情,无论这是关于生活或艺术以至微末到如“河水鬼”这类东西。
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宣传,我只要听要知道。
但是,以前这么主张过,却也未始不可让人家知道,反正是随便看看,说的对不对也没有多大关系罢。
杂拌儿之二序
1932.11.25
但是话虽如此,我们固然也要听野老的话桑麻,市侩的说行市,然而友朋间气味相投的闲话,上自生死兴衰,下至虫鱼神鬼,无不可谈,无不可听,则其乐益大,而以此例彼,人境又复不能无所偏向耳。
习俗与神话
1933.12.11
《世界欲》是一部半埃及半希腊的神怪小说,神怪固然是哈葛德的拿手好戏,其神话及古典文学一方面有了朗氏做顾问,当然很可凭信,因此便决定了我的选择了。
“哈氏丛书”以后我渐渐地疏远了,朗氏的著作却还是放在座右,虽然并不是全属于神话的。
希腊神话一
1934.3
简·哈里森笔下,希腊的英雄与亡魂。
金枝上的叶子
1934.2
弗雷泽夫人著作中的魔鬼、恶鬼、鬼。
鬼的生长
1934.4
关于鬼的事情我平常很想知道。
知道了有什么好处呢?
那也未必有,大约实在也只是好奇罢了。
古人云,唯圣人能知鬼神之情状,那么这件事可见不是容易办到的,自悔少不弄道学,此路已不同,只好发挥一点考据癖,从古今人的记录里去找寻材料,或者能够间接的窥见百一亦未可知。
虽然,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当不谬也。
自己不信有鬼,却喜谈鬼,对于旧生活里的迷信且大有同情焉,此可见不佞之老矣,盖老朽者有些渐亦苛刻,有的亦渐益宽容也。
刘青园常谈
1935.7.18
中国人虽说是历来受儒家的薰陶,可是实在不能达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一面固然还是“未知生”,一面对于所谓腊月二十八的问题却又很关心,于是就参照了眼前的君主专制制度建设起一个冥司来,以寄托其一切的希望与喜惧。
谈油炸鬼
1935.10.7
麻花摊所制各物殆多系寒具之遗,在今亦是最平民化的食物,因为到处皆有的缘故,不见得会令人引起乡思,我只感慨为什么为著述家所舍弃,那样地不见经传。
刘在园范啸风二君之记及油炸鬼真可以说是豪杰之士,我还想费些功夫翻阅近代笔记,看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