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期在解决国家与法问题中的思想展开.docx
《马克思早期在解决国家与法问题中的思想展开.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马克思早期在解决国家与法问题中的思想展开.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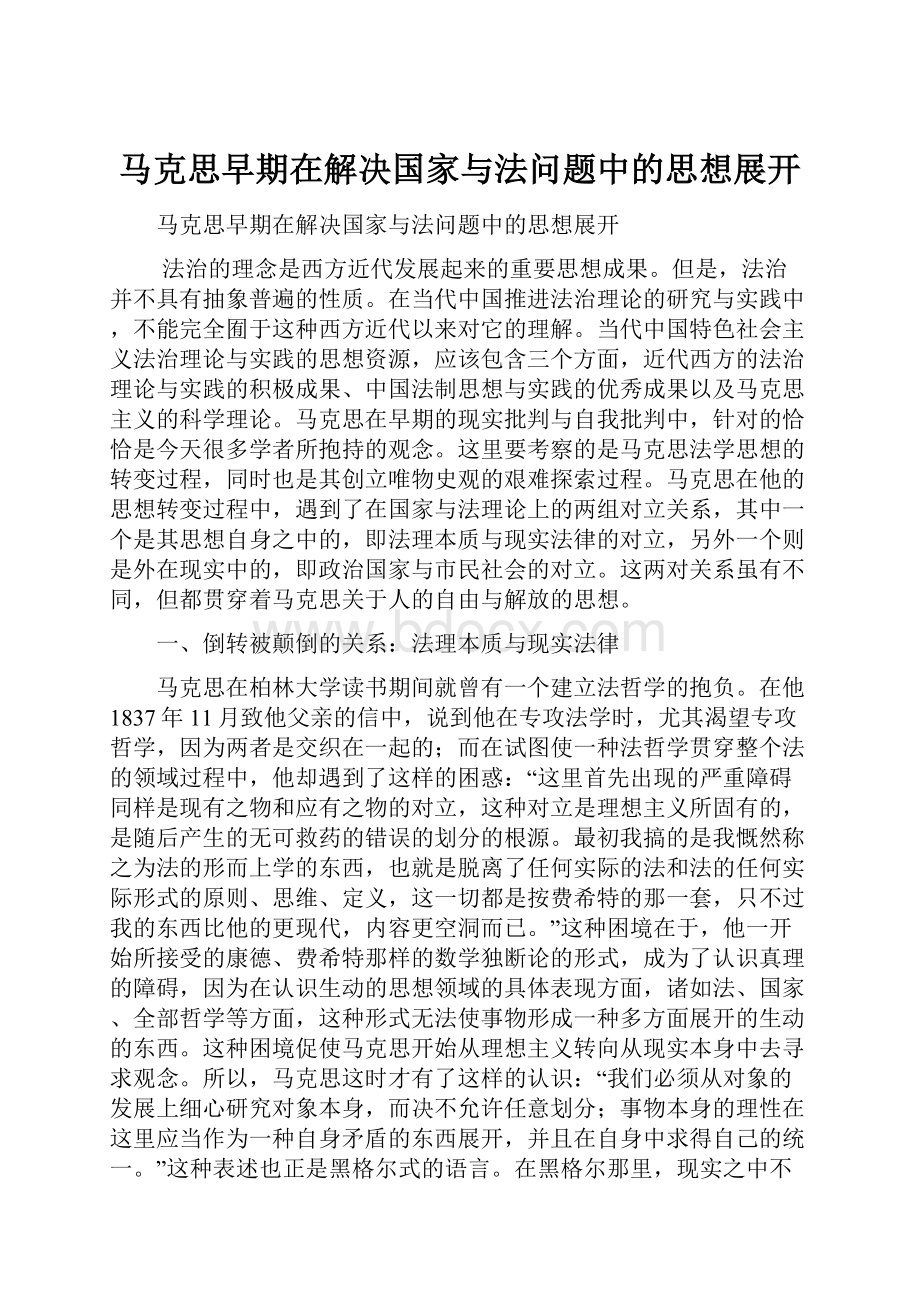
马克思早期在解决国家与法问题中的思想展开
马克思早期在解决国家与法问题中的思想展开
法治的理念是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重要思想成果。
但是,法治并不具有抽象普遍的性质。
在当代中国推进法治理论的研究与实践中,不能完全囿于这种西方近代以来对它的理解。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思想资源,应该包含三个方面,近代西方的法治理论与实践的积极成果、中国法制思想与实践的优秀成果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在早期的现实批判与自我批判中,针对的恰恰是今天很多学者所抱持的观念。
这里要考察的是马克思法学思想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其创立唯物史观的艰难探索过程。
马克思在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中,遇到了在国家与法理论上的两组对立关系,其中一个是其思想自身之中的,即法理本质与现实法律的对立,另外一个则是外在现实中的,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
这两对关系虽有不同,但都贯穿着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思想。
一、倒转被颠倒的关系:
法理本质与现实法律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读书期间就曾有一个建立法哲学的抱负。
在他1837年11月致他父亲的信中,说到他在专攻法学时,尤其渴望专攻哲学,因为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而在试图使一种法哲学贯穿整个法的领域过程中,他却遇到了这样的困惑:
“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同样是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这种对立是理想主义所固有的,是随后产生的无可救药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
最初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之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内容更空洞而已。
”这种困境在于,他一开始所接受的康德、费希特那样的数学独断论的形式,成为了认识真理的障碍,因为在认识生动的思想领域的具体表现方面,诸如法、国家、全部哲学等方面,这种形式无法使事物形成一种多方面展开的生动的东西。
这种困境促使马克思开始从理想主义转向从现实本身中去寻求观念。
所以,马克思这时才有了这样的认识:
“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而决不允许任意划分;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统一。
”这种表述也正是黑格尔式的语言。
在黑格尔那里,现实之中不仅包含着观念,而且观念必将在现实中实现自身。
所以,麦克莱伦才这样指明了马克思转向黑格尔的必然性:
“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这种巨大差距,使马克思后来考虑用黑格尔哲学来克服。
”
马克思这时很快开始倾心于黑格尔的哲学,开始“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
”黑格尔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克思也把理念或理性视为最为真实的内容,而且也认为理念必定在现实之中实现自身。
黑格尔就曾这样坚决反对应然与实然的对立,坚持认为“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理念,而理念并不会软弱无力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而不是真实如此的程度。
”马克思在写于1839年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象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
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
”这里,马克思仍然是把应然与实然进行了二分,但并不把二者视为对立的,而是要用“应然”去统摄“实然”。
马克思在其后的《莱茵报》时期,在他写的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的论文(1842年3—4月)中,对于法律的性质与作用有这样的看法:
“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
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把法律视为自由的体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马克思所受到的黑格尔的影响。
所以,马克思当时的辩护必然要诉诸法律本身。
马克思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1842年7—8月)中,也继黑格尔之后,对历史学法学派的创始人物古斯塔夫·胡果进行了批判。
在1842年初,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接受普鲁士国王的使命对普鲁士的法律进行修订,而这一派在当时反对法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典。
马克思参与了这次法律修订的讨论,并为《莱茵报》撰写了该文,其后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历史法学派的面目进行了揭露。
针对胡果宣称康德是自己的老师,马克思明确指出:
胡果完全曲解了康德,只是一个否认事物的必然本质的怀疑主义者,“他根本不想证明,实证的事物是合乎理性的;相反,他力图证明,实证的事物是不合理性的。
”胡果与康德的理论实质区别在于:
“如果说有理由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那么,就应当把胡果的自然法看成是法国旧制度的德国理论。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胡果的批判也是从“理性”出发的。
对于历史法学派的理论实质,马克思指出,他们把研究起源变成自己的口号,但这种研究无疑是以历史来为现实进行辩护,正如一年之后马克思所揭露的那样:
“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有个学派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鞭子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的鞭子——的每一声呐喊都宣布为叛乱……因此,这个历史法学派本身如果不是德国历史的杜撰,那就是它杜撰了德国历史。
”这对于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马克思来说,是不能忍受的,因而也是必须清算的。
在其后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论文(1842年10月)中,涉及具体的物质利益之时,虽然马克思还肯定“人类的法是自由的体现”,强调法律应该是“事物的法理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但已明确地认识到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法律观念是不一样的,“‘维护林木所有者利益的法理感和公平感’是一项公认的原则,而这种法理感和公平感同维护另外一些人的利益的法理感和公平感正相对立;这些人的财产只是生命、自由、人性以及除自身以外一无所有的公民的称号。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10—12月)中,对现代国家的法律本质已有了明确的认识:
“在这个自私自利的世界,人的最高关系也是法定的关系,是人对法律的关系,这些法律之所以对人有效,并非因为它们是体现人本身的意志和本质的法律,而是因为它们起统治作用,因为违反它们就会受到惩罚。
”对于这时的马克思,法律不再是自由本质的体现。
但马克思并没有放弃人类自由解放的理想,他最终放弃的只是这种自由观念的抽象普遍的理解。
对于应该怀抱一个什么样的自由观念,虽然马克思没有给出答案,但就如何由“实然”通达“应然”,他已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方法上的路径。
他在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中,虽然还有黑格尔哲学的印迹,如他说到“理性向来就存在,只是不总具有理性的形式”,但总体来说,他已开始接近唯物主义。
他这样指出:
“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
”对于马克思来说,不再是预先设定“应然”并最后落实于“实然”,而是要从“实然”之中揭示“应然”,从现存的现实的特有形式之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真正现实。
这也预示了他即将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马克思一直被法国革命所鼓舞,但他从未认为,法国革命就是他的“理想”,从不认为德国就应走法国的道路。
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12月)中明确提出:
“在法国,全部自由必须由逐步解放的现实性产生;而在德国,却必须由这种逐步解放的不可能性产生。
”马克思的分析是,在法国,从事普遍解放的角色分别由法国人民的各个不同阶级担任,但他们并不感到自己是一个特殊的阶级,而自认为是整个社会需要的代表;但是,在德国,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除非是由于自己的锁链本身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
马克思宣称,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恰恰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即无产阶级。
二、揭露被歪曲的关系: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
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后,很快因卷入现实政治问题,尤其是“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发现不仅 “应然”与“实然”并未统一起来,而且“实然”自身也发生着分裂,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马克思由此产生了对黑格尔的批评,而这种批判的第一部著作就是他在1843年着手的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主要是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第260—313节的全面分析与批判,而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分析与批判则构成了中心的问题。
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只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两个环节,但又被视为相互对立的:
市民社会追逐个人私利,而政治国家关注普遍事务。
黑格尔力图解决两者的对立的方式则是以政治国家来统摄和吞食市民社会。
马克思一方面这样高度评价了黑格尔:
“黑格尔觉得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是一种矛盾,这是他的著作中比较深刻的地方。
”但另一方面也深刻揭露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性质,明确肯定了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前提;同时明确批评了黑格尔满足于解决两者对立的表面现象,指出了这种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正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这种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导致了人权与公民权的分离。
这里所谓的“人权”,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是与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权利,因此,《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中的自由,不过是“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
而自由这一人权的运用,实际上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
“这就是说,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
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应用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
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
”所谓的公民权,就是一种政治权利,是在政治共同体即国家中与别人共同行使的权利。
在现代社会之中,不是身为公民的人,而是身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
让马克思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一个刚刚开始解放自己、扫除自己各种成员之间的一切障碍、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民族,竟郑重宣布同他人以及同共同体分隔开来的利己的人是有权利的(1791年《宣言》)。
”尤其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公民身份、政治共同体甚至都被那些谋求政治解放的人贬低为维护这些所谓人权的一种手段”。
马克思的这种“困惑不解”正是通过“讽喻”的方式指出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非完全对立,恰恰相反,通过政治革命解放出了人,但这个人是利己的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构成了政治国家的基础;同时,政治共同体被那些谋求政治解放的人贬低为维护这些所谓的人权的一种手段。
因此,马克思提出:
“政治国家的建立和市民社会分解为独立的个体——这些个体的关系通过法制表现出来,正像等级制度中和行帮制度中的人的关系通过特权表现出来一样——是通过同一种行为实现的。
” 马克思这时更多的是揭露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及其所导致的人们不仅在思想中而且在现实中的二重化,即过着天国的生活与尘世的生活这样的双重生活。
前一种生活,是在政治国家中的生活,人把自己作为社会存在物,把自己视为共同体的一员,而后一种生活,是在市民社会中的生活,人是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并把自己视为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中的重大思想进展,一是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做了更为具体的说明,二是明确指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一方面,市民社会决定了政治国家。
在市民社会中,那种利己主义的个人在他们的抽象之中把自己理解为原子,但市民社会的成员绝不是原子,因为原子是自满自足的,它身外只是绝对的虚空。
作为现实的个人,“他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他身外的世界和个人的意义,甚至他那世俗的胃也每天都在提醒他:
身外的世界并不是空虚的,而是真正使人充实的东西。
”因此,在一个追逐身外的事物以满足其需要的个人同在他之外并拥有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的个人之间,就必须建立起联系。
可以说,正是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联合起来了。
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还会妄想,市民生活必须由国家来维系,其实恰恰相反,国家是由市民生活来维系的。
”马克思再次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
另一方面,政治国家只是对其特殊利益的一种保护:
1830年的自由资产阶级,不再把立宪的代议制国家看成追求的理想,“而是把它看做自己的独占权力的正式表现,看做对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承认。
”马克思认为拿破仑已懂得了现代国家是以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为基础的,但仍然以国家为目的本身,以致在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与他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就弃这些物质利益而不顾,这也就成了拿破仑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的成员,屈从于利益的追逐,成为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现代国家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本身。
”近代确立起来的法治原则,其实就是原子似的个人追求法律上的自由与平等。
但是,“这种市民社会的奴隶制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因为这种奴隶制看上去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个人独立,这种个人把自己的异化的生命要素如财产、工业、宗教等的既不再受普遍纽带束缚也不再受人束缚的不可遏止的运动,当做自己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运动实际上是个人的十足的屈从性和非人性。
在这里,法代替了特权。
”法代替了特权,这为近代以来的法治观念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法代替特权,是历史的进步,但却是以人的异化为代价的。
以法代替特权,有两个重要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表面上的分离,也就形成了公法与私法这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故而,对于“法治”才有了这样一个经典的表述:
“私域自治、公权受限”。
其实,这个表述不过是市民生活与政治国家之间、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相互对立、相互博弈结果的自由主义的表达,国家仅成为个人权利的捍卫者、自由市场的守夜人:
“个人和团体通过市场来进行交易,追求自身的利益天经地义,其前提是不妨害他人同样追求自身利益的努力,国家只是这种自身交易的公平裁判者,而不必卷入社会福利的追求本身。
这个基本信念成了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基本信条,并且反映在其对政府合法性的论证方面。
”这种对立有其现实的根据,那就是出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的目的。
但这种对立只是经验层面上的现象,本质上却具有内在一致性,对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已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两者的内在一致做了深刻的揭示。
把权利与权力对立起来的这种法治理念绝非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一种构想。
第二个后果是,恩格斯后来明确指明的是“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这也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的:
“在这个自私自利的世界,人的最高关系也是法定的关系,是人对法律的关系。
”近代的法治观念,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法律之治、规则之治,要求法律在形式上的普遍性,并且能够平等地对待所有人。
但这种形式上的平等,虽然在一定的意义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依然改变不了不平等的实质,包含着“实际上是个人的十足的屈从性和非人性”。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艾伦·伍德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形式上的不平等,被移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实质上的不平等。
而这种资本主义政治领域中的形式上的平等,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的实质上的不平等。
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和政治的分离,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功能本身的分化,将分化出来的功能分别分配到私人的经济领域和国家的公共领域。
这种分配将直接与榨取和占有剩余劳动相联系的政治功能,与那些更具普遍性和公共性目的的政治功能分离开来。
经济的分离实际上是政治领域的分化,这种概括从某些方面来说更适于解释西方发展的独特过程和资本主义的特性。
”
马克思这个时期,对于资本主义的利己的、原子的个人的批评,也预示着他把“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在他看来,这种构想必然会消除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阐述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深刻关系。
在他看来,政治解放有其局限性,那就是人自身的二重化:
“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
马克思接着指出: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为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导致了人自身的二重化,表现为人的异化,因而,克服这种异化即实现人的完全复归,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
马克思在这里将人类解放寄希望于一个新的阶级:
无产阶级。
这也就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第二篇文章,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重要结论。
三、国家与法的思想主题:
人的自由与解放
马克思在早期有关国家与法的理论的批判中所遇到的这两对关系是相互关联的,因为法与国家是一体的。
他在分析两对关系之中贯穿着一个同样的思想主题,那就是人的自由与解放。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提出了“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这就让人想起黑格尔的命题:
“法是自由的定在”。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国家就是具体自由的实现,是“伦理理念的现实”,虽然他也承认现存的国家并不完全符合国家的理念。
马克思早期也是这样来看待国家的。
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2年2月)中,马克思对于国家与法的观点并没有脱离黑格尔的印记,如他说:
“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
……即使公民起来反对国家机构,反对政府,道德的国家还是认为他们具有国家的思想。
”马克思这里的“国家的思想”无疑还是黑格尔式的国家理念,而法律所体现的自由也只是一种抽象的自由。
马克思还明确肯定法律应该保护私有财产,主要是因为当时德国还面临着如何从封建专制中解放出来的政治任务。
马克思的思想在随后的一年多的时间中有了重大的推进。
这个时候,他已发现现实中人的不自由,而这种“不自由”就表现为一种人的“异化”。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也是随着他的思想发展越来越丰富起来的。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虽然肯定了政治解放的意义,但认为它远不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完成。
马克思的看法是,政治解放可以说是市民社会的革命,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解放出来,但在这个解放了的市民社会中,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构成了它的首要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
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
金钱成了统治一切的力量,剥夺了整个世界包括人的价值。
但金钱不过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
在随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明确提出了私有制导致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被奴役,直接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对私有财产的否定。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深入地讨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与结构,但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考察,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概念,强调这种异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工人与他的人的类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相异化。
马克思指出,只有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才能最终消灭人的异化。
马克思对于自由的理解,与自由主义的理解大异其趣。
自由主义对于私有财产这一人权的理解就是“任意地、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
”借用当代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对两种自由的区分,可以说,自由主义一直倡导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消极自由。
而马克思所倡导的则是一种积极的自由。
在《神圣家族》中,他对法国的唯物主义做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们的思想汇入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他这样指出:
“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人不是由于具有避免某种事物发生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具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产生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温床”。
在马克思这里,自由就是“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力量的自由”。
马克思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他要从法国唯物主义的环境造就人的结论中引出一个革命的结论,那就是要以合乎人性的方式造就环境。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自由的看法,最初是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把自由视为抽象的、普遍的,而后则是逐渐抛开了这种看法,开始关注现实的人的自由问题,得出了自由受制于社会的条件并通过改变这种条件来获取自由这样的结论。
马克思关于国家与法的思想也随着他向唯物主义的推进而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时,在国家与法这一法治理论的核心问题上,马克思早期的自我批判和思想探索也是一项重要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