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3.docx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3.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任继愈《中国佛教史》3.docx(3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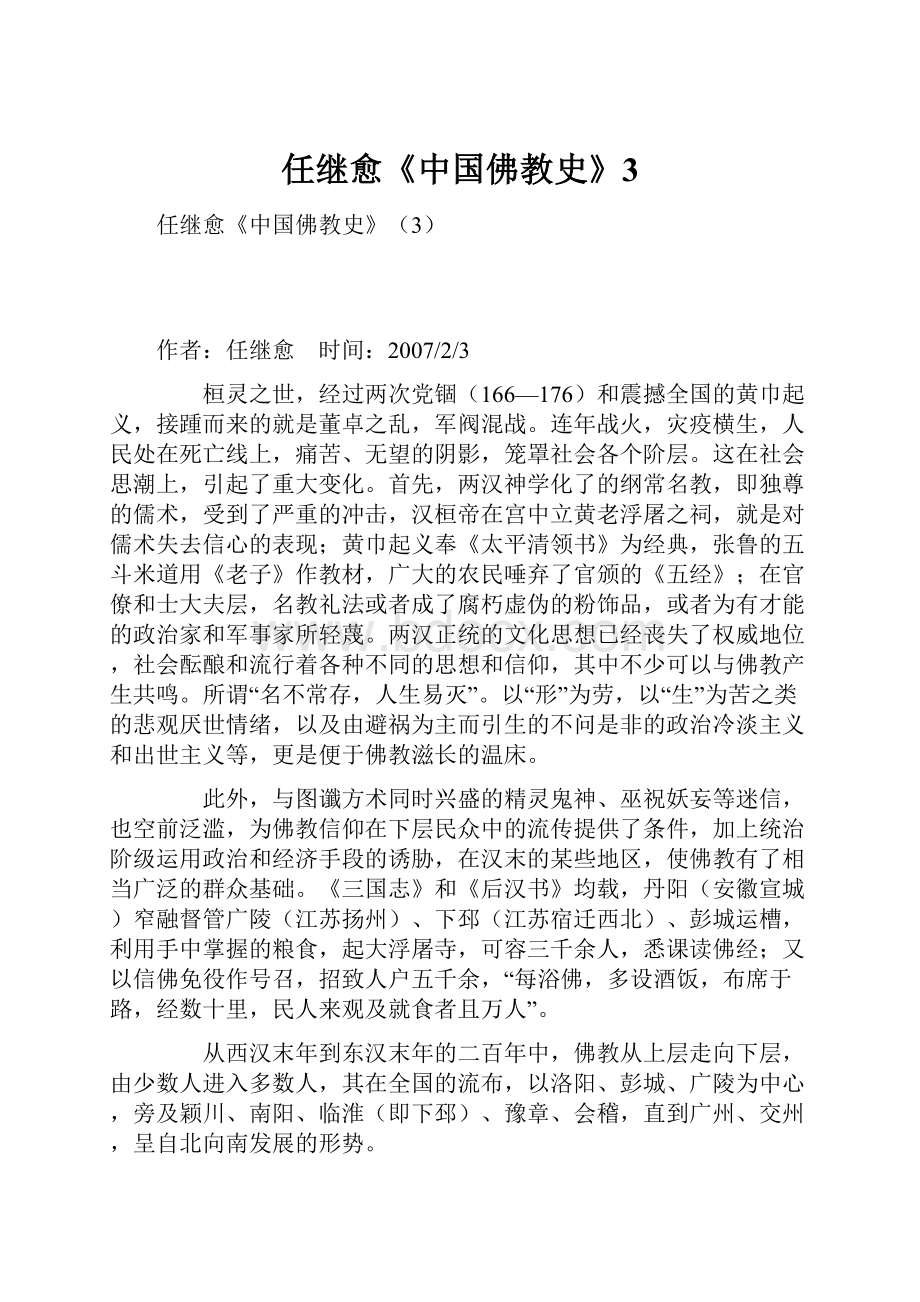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3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3)
作者:
任继愈 时间:
2007/2/3
桓灵之世,经过两次党锢(166—176)和震撼全国的黄巾起义,接踵而来的就是董卓之乱,军阀混战。
连年战火,灾疫横生,人民处在死亡线上,痛苦、无望的阴影,笼罩社会各个阶层。
这在社会思潮上,引起了重大变化。
首先,两汉神学化了的纲常名教,即独尊的儒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就是对儒术失去信心的表现;黄巾起义奉《太平清领书》为经典,张鲁的五斗米道用《老子》作教材,广大的农民唾弃了官颁的《五经》;在官僚和士大夫层,名教礼法或者成了腐朽虚伪的粉饰品,或者为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轻蔑。
两汉正统的文化思想已经丧失了权威地位,社会酝酿和流行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其中不少可以与佛教产生共鸣。
所谓“名不常存,人生易灭”。
以“形”为劳,以“生”为苦之类的悲观厌世情绪,以及由避祸为主而引生的不问是非的政治冷淡主义和出世主义等,更是便于佛教滋长的温床。
此外,与图谶方术同时兴盛的精灵鬼神、巫祝妖妄等迷信,也空前泛滥,为佛教信仰在下层民众中的流传提供了条件,加上统治阶级运用政治和经济手段的诱胁,在汉末的某些地区,使佛教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国志》和《后汉书》均载,丹阳(安徽宣城)窄融督管广陵(江苏扬州)、下邳(江苏宿迁西北)、彭城运槽,利用手中掌握的粮食,起大浮屠寺,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又以信佛免役作号召,招致人户五千余,“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的二百年中,佛教从上层走向下层,由少数人进入多数人,其在全国的流布,以洛阳、彭城、广陵为中心,旁及颖川、南阳、临淮(即下邳)、豫章、会稽,直到广州、交州,呈自北向南发展的形势。
二、佛教向交州的传播
交州,汉魏亦称交趾(今越南河内),也是中国早期佛教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汉末士燮(137—226)任交趾太守(同时领有广州),在郡40余年,相对安宁,中原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一时学术荟萃,思想文化十分活跃。
士燮本人倡导儒学,尤精《左传》《尚书》;佛教和道教方面的“异人”也集中不少。
与士燮同为苍梧人的牟子,就是佛教的代表人物。
牟子与笮融同时,将母避乱至交趾,从其所著《理惑论》看,这里的佛教义学已相当成熟,与儒家五经和道家《老子》相调和,全力排斥道教神仙辟谷之术,为佛教的发展开路。
据此可见,交趾的佛教最初是来自内地北方,但也有材料说明,交州佛教原是由海路南来,并由此北上中原,成为佛教传入内地的另一渠道。
三国吴赤乌十年(247)抵达建邺的康僧会,原籍康居,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居交趾,可以说,他自幼受到家传天竺文化的影响。
但康僧会又是生长在交趾儒学绍隆之区,使他的佛教思想中充满着儒家精神,同当时已经流传于大江南北的玄学和般若学,大异其趣。
《高僧传》本传称他“初达建邺,营立茅茨,设像行道”,为舍利建塔,成为江左建寺之始,这是典型的天竺风气。
他编译的《六度集经》有关菩萨“本生”的故事,在天竺大都能找到相应的遗迹。
其中太子须大拏的传说,亦见《理惑论》。
据《大南禅苑传灯录》记:
“交州一方道通天竺,佛法初来,江东未被,而赢又重创兴宝刹二十余所,度僧五百余人,译经一十五卷……于时有比丘尼摩罗、耆域、康僧会、支疆梁、牟博(即牟子)之属在焉”。
因此,说康僧会所传佛教是经海路迁入交趾,然后又北上南京,不是没有根据的。
此外,三国吴时在交州译经的还有西域僧人支疆梁,泽出《法华三昧经》。
晋惠末年(306),天竺耆域经扶南至洛阳,取道交、广。
晋隆安(397—401)中,闹宾高僧昙摩耶舍达广州,交州刺史女张普明咨受佛法,耶舍为其说佛生缘起,并译出《差摩经》。
他的弟子法度,专学小乘,禁读方等,独传律法,在江南女尼中有甚深影响。
求那跋摩在跋婆国弘教对,宋文帝曾敕交州刺史泛舶延清。
南朝齐梁之际,有释慧胜,交州人,住仙洲山寺,从外国禅师达摩提婆学诸观行;诵《法华》日计一遍。
与慧胜同时的还有交趾人道禅,亦于仙洲山寺出家,以传《十诵律》著称。
他们后来都进入南朝京都,声播内地。
交州自汉末以来,就是佛教沿海路传入中原的重要门户。
早期的交州佛教,大小乘都有,此后信奉《法华经》则比较突出。
《法华·药王品》把焚身供佛作为最上供,影响很久。
《弘赞法华传》载,交州陆平某信士,“因诵《法华》”,仰药王之迹,自焚之后,出现奇迹。
5世纪上叶,黄龙昙弘适交趾之仙洲山寺,亦于山上聚薪自焚。
三、初传期的佛教译著
汉末的社会历史状况,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合宜的温床。
据现存最早的经录《出三藏记集》记载,从汉桓帝到献帝(189—220)的40余年中,译介为汉文的佛教经典54部,74卷,知名的译者6人;唐《开元释教录》勘定为192部,395卷,译者12人。
达标志着中国佛教开始了大规模的发展。
译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
安世高,本名清,原为安息国太子。
父死,“让国于叔,驰避本土”,游历西域各国。
汉桓帝(147—167)初年,进入中国内地,在洛阳从事译经。
至汉灵帝建宁年(168—172),20余年间,共译出沸经34部,40卷(《开元录》订正为95部,115卷),主要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修行道地经》等。
灵帝末年,关河扰乱,安世高避难江南,经庐山、南昌至广州,死于会稽。
他行走的这条路线,大体反映着当时佛教传播的路线。
据僧传记载,安世高善“七曜五行,医方异术”,并懂“鸟兽之声”,带有浓厚的方士色彩。
他在佛教上的贡献,是首次系统地译介了早期的小乘思想。
其中一些译典属于四《阿含》中的单行本,另有一些是自成体系,大致相当于上座部中说一切有部之说。
晋释道安评论说,安世高“博学稽古,特专阿毗昙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他用“禅数”之学来概括安世高的佛学特点。
所谓“禅数”的禅,即是禅定;所谓“数”,指用四谛、五阴、十二因缘等解释佛教基本教义的“事数”,从佛典的文体上说,属于“阿毗昙”,以其能使人懂得佛教的道理,亦称为“慧”。
因此,“禅数”也就是后来中国佛教常说的“定慧”、“止观”。
安世高所传禅法,影响最大的是“安般守意”,后称“数息观”。
它要求用自一至十反复数念气息出入的方法,守持意念,专心一境,从而达到安谧宁静的境界。
他们相信,这种禅法最后可以导致“制天地、住寿命”,“存亡自由”。
这种修禅的方法与古代中国神仙方术家的呼吸吐纳、食气守一等养生之术相似,很容易为人们接受。
作为一种气功,安般禅至今还在流行。
安世高的“数”学,即佛教教理,集中反映在《阴持入经》上,“阴持入”,新泽作蕴、处、界,亦称佛教“三科”,是着重说明人生和世界之所以存在及其本质的。
此经的中心,在于把人的世俗观念,特别是通过感官的感受和观念说成是苦的远因,而人的爱欲,主要是食与性,则是苦的近因。
人生在世必然是苦。
据此,它要求通过禁欲主义途径,达到出世的目的。
安世高所译佛经“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比较通顺,他所介绍的教理,在汉魏两晋都有影响。
当时临淮(安徽泗县东南)人严佛调撰《沙弥十慧章句》,开始发挥安世高学说;三国吴康僧会曾从安世高弟子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随学,并与陈慧共注《安般守意经》;晋僧道安,为大小《十二门经》、《安般守意》、《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等经作序作注;东晋名士谢敷也曾为《安般》作序。
可见安世高的译籍,不但流传时间长,影响亦广。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月支人,桓帝末年游于洛阳,在灵帝光和、中平之间(178—189)译出佛经14部,27卷,影响最大的是《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
《道行般若经》亦称《般若道行品》,与三国吴支谦译《大明度无极经》,姚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属同本异译,相当于唐玄奘所译《大般若经》第四会。
此经是大乘般若学介绍进中国内地之始,它的怀疑论倾向和否定一切权威的批判精神,在分崩离析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支谶在翻译中,把“真如”译作“本无”、“自然”、“璞”等,很容易与《老子》的概念相混。
《道行般若经》在陈述“缘起性空”时,强调相对主义的方法,既把“性空”视作终极真理,又把“缘起”当作“性空”的表现,从而导向折衷主义的双重真理观,这又与《庄子》的某些思想相通。
魏晋玄学盛行时,般若学在佛教中得到突出的发展,此经起了不小的作用。
《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都是讲大乘禅法的。
“首楞严”意译“健相”、“勇伏”等,“三昧”即是禅定的另一种梵音。
这种禅定,在于用幻想示现种种境界,种种行事,证明行者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力量,从而激励勇猛精进,修习佛教,超度众生。
所谓“般舟”,意为“佛立”、“佛现前”。
修此“三昧”,在于使“十方诸佛”在虚幻想像中出现于行者面前。
此经中还特别宣扬,只要专心思念西方阿弥陀沸,并在禅定中得见,死后即可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
这为中国的净土信仰奠定了基础。
但这种禅定也提供证明,“佛”不过是“心”的自我创造,本质也属空无,所以在理论上,与般若经类相互补充。
以上二经自支谶译出至于姚秦,二百余年中,先后有多种译本,说明这种用大神通游戏世间的思想,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这个时期,除了译经之外,也开始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写的佛教著述。
像《安般守意经》就保存有多家注解。
上述《沙弥十慧章句》已佚,《四十二章经》也可能是汉末人所辑。
比较完整反映汉魏之际的中国佛教思恩的,是《牟子理惑论》。
牟子本人“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
又“翫《五经》为琴簧”,熟悉中国的正统思想。
他的立论就是用“儒典”和《老子》,证成佛家学说,为佛教义理的发展斩荆披棘。
其中反映当时攻难佛教的言论,主要有,佛经非儒典所载,乃“夷狄之术”;“出家毁容,不合孝道”;“妄说生死鬼神,非圣贤之语”等。
对此,《理惑论》一一作了辩解。
它说:
“君子博取众善”,子贡亦曰“夫子何常师之有乎?
”所以“书不必孔丘之言”。
至于华夷的界限本是相对的,何况“禹出西羌”,“由余产狄国”,“昔孔子欲居九夷”,对佛教“尊而学之”,决不意味着“舍尧舜周孔之道”。
沙门“捐家财、弃妻子”,剃头毁容,属权变小节,重要的是,“修道德”、“崇仁义”,与圣人无异。
“至于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更是大孝大仁。
佛教讲“人死复当更生”的因果报应,最为当时所惑,《牟子》则以招魂的习俗和《孝经》所言“为之宗庙,以鬼享之”等证明这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事。
总之,“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二者虽有出世和处世的差别,但都属“君子之迫”,不可使之对立。
佛教作为外来的一种宗教,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曾长期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特别是儒家观念的挑战,引起多次争论,虽历两晋南北朝而至隋唐,未曾停止。
而就其涉及的根本内容言,大体不出《理惑论》的范围;从佛教立场解决中外两种宗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基本上采取《理惑论》这种既保持佛教的一定独特性,又依附或适应中国某些传统思想的路子。
假若说,两汉之际佛教是依附于儒学方士,到桓灵之世又成为道教方术的补充物,那么《理惑论》则同《老子》的五千文站在一起,依附儒典七经,重点转向抨击道教的神仙长生术。
佛教在汉魏之间,已经与道教明确分家。
《理惑论》中提到“今沙门剃头发,被赤布”,又记问者言:
“今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说明在汉人中间,出家为僧者已不是个别现象,骨干则是落魄的士大夫,像临淮的严佛调,是早期的译家之一,广陵(扬州)、彭城(徐州)二相,则是佛经讲座的最早创立者。
第三章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第一节印度的笈多王朝和佛教的发展
一、印度社会与文化概况
公元320年,旃多罗·笈多一世创建笈多王朝,在华氏城建都,以恒河与宋河、朱木那河流域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张,经过沙摩陀罗·笈多和旃陀罗·笈多二世(超日王,380—413年)的武功与联姻,使原处于分裂的印度达到了近乎孔雀王朝那样的统一,经济和文化更加昌盛。
笈多王朝在西北部,臣服了贵霜人(大月氏人)和塞人的许多小国,但不久又受到了白匈奴的入侵。
西方史学家称作白匈奴的,中国史称嚈哒,5世纪分布在阿姆河以南,建都巴底延城(阿富汗伐济纳巴德),势力大规模南下。
笈多王朝虽然作了抵抗,但效果甚微;到5世纪末和6世纪初,他们已经稳固地占领了锡亚尔科特地区和东马尔瓦,中国的疏勒、于闻也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笈多王朝退缩到摩揭陀,延续到7世纪中叶,史称后笈多王朝。
519—520年,北魏宋云在犍陀罗谒见嚈哒王,就是白匈奴的戈拉斯,也就是入侵的主要统帅米希拉古拉。
6世纪中叶,嚈哒国势衰退,破突厥与波斯所灭。
笈多王朝强大期,声威远及隔海相皇的斯里兰卡岛,但始终没有在德干高地建立起真正的政权。
这个广大地区,由很多不同的种族建立的许多小国分别统治。
5世纪上半叶,在建志(马德拉斯附近)建都的帕拉瓦王朝兴起,6世纪下半叶统一了南方诸国,征服了斯里兰卡。
这个王朝在发展南印的政治文化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建志城成了婆罗门教和佛教的重要学术中心。
从总体上说,笈多王朝着力支持印度教的发展,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婆罗门教复兴的时期。
其中对于毗湿奴(遍净天)和湿婆(大自在天)的崇拜尤其盛行。
由此形成的两大教派,也得到北方嚈哒等外来统治者和南方帕拉瓦等王室的赞助。
不过所有这些王国,大都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允许各种信仰并存,自由辩论和竞争。
在这样的气氛下,佛教依然遍及全印,持续高涨。
这个时期,印度的对外交通继续扩大。
北部经波斯,沿里海抵达地中海,与西方罗马帝国有商业和文化交往。
东逾帕米尔进入我新疆和河西地区,往来日益频繁。
南部沿海形成许多海上贸易的港口,西经亚历山大港驶入红海,也是沟通罗马帝国的重要渠道;向东则通向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等地,与中国大陆的水上联系也紧密起来。
二、北印佛教
公元399年,东晋高僧法显发自长安,渡流沙,越葱岭,横穿印度,抵斯里兰卡,411年搭商船回国,经苏门答腊(或爪哇)的耶婆堤国,于412年飘回山东半岛,从崂山登陆,次年回到建康。
从陆路到海路,完成了交通印度的旅行。
著有《佛国记》。
法显在印度接触的是以商人为主体的中下层民众和僧侣,他在《佛国记》中的记载反映了当时民间的习俗和信仰。
大致说,北印佛教依然以犍陀罗为中心,包括陀历(巴基斯坦奇特拉尔以南)、乌苌(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地区)、宿呵多(巴基斯坦境喀布尔河支流斯瓦特河流域)、刹尸罗(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西北)、弗楼沙(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北)、那竭(阿富汗贾拉勒阿巴德)、跋那(巴基斯坦班努)等国,伽兰众多,僧徒聚居,除个别大小乘兼学者外,多属小乘学者。
有关佛的遗物,如佛遗足迹、佛齿、佛骨顶、佛剃发剪爪、佛钵、佛锡杖、佛影等,散布诸地,建塔供养,亦有僧众居止。
其中佛本生故事,如菩萨割肉贸鸽、以眼施人、投身喂虎等,也有遗迹存留,所建四大宝塔,金银校饰,诸国王臣民竞兴供养。
弗楼沙原是犍陀罗首都,传说迦腻色迦王曾在此处建大塔,高40余丈,众宝校饰,壮丽威严,“阎浮提塔,唯此为上”。
亦即宋云所记之“雀离浮图”。
此地的佛钵,被视作佛法兴衰的象征,建塔及伽兰供养,有僧七百余。
建塔已成普遍风气,那竭国城更有诸罗汉、辟支佛塔千数。
其醯罗城的佛顶骨精舍,成为全民的崇拜中心,国王每早先诣精含礼拜,后听国政;居士长者,亦先供养,乃修家事。
公元480年,哒灭大月氏,据有犍陀罗,势力远及康居、安息、于阗、沙勒和三十余小国。
518年,即法显自天竺回国百年后,北魏宋云、惠生,也游历了乌苌、犍陀罗等地。
据他的记录,当时哒国王“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杀生血食”。
犍陀罗由哒贵族子弟为王,治国二世,“多行杀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
但国中婆罗门种崇奉佛法,好读经典,当是大乘信仰者,与犍陀罗王矛盾甚深。
该王又与罽宾连续进行了三年战争,不得人心。
罽宾历来是小乘有部的活动基地,没有发现因战争遭到严重破坏的迹象。
所以嚈哒统治者的非佛态度,对佛教的发展影响或许不大。
乌苌国亦在嚈哒势力范围,那里的佛迹崇拜依然兴旺,具有新的发展。
国王笃信佛教,蔬食长斋,晨夜礼拜,日中以后始治国事。
此等行事,显然是法显所记那竭国王奉佛的延续。
该国寺院亦多,僧徒自50人至300人不等,戒行精苦。
乌苌国的佛教带有国教性质,国王奉佛列为每日三时的必修课;民众也把礼沸组织在日常生活之中,这种情况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公元556年,进入北魏邺都的那连提黎耶舍说,他游历诸国,北背雪山,南穷师子,自所经见,唯马苌国主乃真大士。
他描述的乌苌国处理政教关系的情况,与宋云所见大体相同。
在6世纪下半叶,游方来到中土的马苌国学僧,除那连提黎耶舍,还有毗尼多流支等,译出《月藏》、《日藏》等多属大乘经典,突出地表现了佛教吸收原始宗教,从咒术星象到天龙鬼神,向多神多信仰转化,其特点,集中强调诸神在护法、护国、护民中的作用。
此类经典后被编入《大集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喀什米尔和我国新疆西部地区佛教信仰的状况。
三、中印和东印佛教
法显渡印度河,进入以朱穆纳河为中心的佛教发源地:
包括毗荼国、摩偷罗国(马土腊)、僧伽施国(卡脑季西北)、罽饶夷城(卡脑季)、沙祗大国(卡脑季东南阿约底)、拘萨罗国舍卫城(北方邦拉普提河南之塞特马赫特)、迦维罗卫(尼泊尔境)、兰莫国拘夷那竭城(卡西亚或加德满都东)、毗舍寓(木札法普尔)、摩揭提国(巴特那与加雅地区)、巴连弗邑(即华氏城,今巴特那)、王舍新城(比哈尔西南之拉杰吉尔)、伽耶城(伽雅)和迦尸国波罗捺城(瓦腊那西)、拘弥国(阿拉巴德之西南)、达嚫国(德干高原中部)、瞻波(巴加尔普尔地区)、多摩梨帝国(加尔各答西南)等。
这些国家和城市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以摩偷罗和摩揭提等为代表的中天竺诸国,这里的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文化宗教发达,佛法转盛,寺院众多,规模宏大,有的可住僧6、7百人。
据说,“天竺诸国国王皆笃信佛法,供养众僧”,包括居士在内。
为众僧起精舍,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
“铁卷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众僧住止房舍,衣食无缺。
看来寺院经济已经普遍发展,僧侣生活方式有了根本性变化。
众僧聚居和崇拜对象,按其信奉教条而有区分,所以其住处所作诸塔,亦有差别。
阿难曾请世尊听女人出家,所以比丘尼多供养阿难塔,而诸沙弥多供养罗云塔,阿毗昙师供养“阿毗昙”,律师供养“律”,而摩诃衍人则供养“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观世音等。
他们每年各有自己供养的节日。
这样,必然形成大小乘多种教派杂居的状况。
摩揭提国的华氏城,为中天竺最大的都城,其宫殿建筑神工鬼斧,雕文刻镂,被疑为非世所造。
“民人富盛,竞行仁义”。
时有大乘婆罗门子名罗汰私婆迷的,为国王师,举国瞻仰。
僧众造摩诃衍伽兰,四方高德沙门及问学人,欲求义理,皆诣此寺。
法显于此寺得《摩诃僧祇律》、《萨娑多部众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祇阿毗昙》等。
可见大乘寺也是容纳小乘经典的。
婆罗门子之师曰文殊师利,即住此寺,成为大乘比丘所宗。
每年建2月8日行像,彩画诸天,上悬幡盖,四边作龛,皆有坐佛,菩萨侍立,可有20车,庄严各异。
境内道俗皆集,作倡伎乐,华香供养。
婆罗门子请佛入城,通夜燃灯。
长者居士各于城中立福德医药舍,凡贫穷孤独残破疾病等人,皆可诣此舍取得医药饮食供给。
摩揭提国华氏城成了当时大乘学的重镇,也是以大乘理国的样板,不过小乘寺僧依然并存。
5世纪上半叶,智猛西游至华氏城,“有大智婆罗门,举族弘法,王所钦重”,猛于其家得《大泥洹》、《僧祇律》等,仍是法显所见的情形。
另一类地方可以拘萨罗国舍卫城与迦毗罗卫国为代表。
后者是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土地空荒,人民稀疏,道路怖畏,野兽横行。
城中亦无王民,只有僧众民户数十家。
但几乎处处都有释迹圣迹,从白净王故宫、太子入胎,到佛陀得道,父王说法等,迹址一一可指。
释迦牟尼是当地人民的骄傲,人们给他创造的神话和指定的遗迹,饱含着对他的怀念。
伽耶城的情况类似,佛得道处有三伽兰,仍有僧住,由民户供给。
拘萨罗国有96种外道,各有徒众,于旷路侧立“福德舍”,供给行路人及出家人,以求福祐。
佛陀布道重地舍卫城,人烟稀旷;尤可注意者,迦叶、拘楼秦、拘那含牟尼所谓过去三佛的生处,也都在舍卫城周围,有调达僧众住处,他们是供养过去三佛,而不供养释迦文佛,可见释迦佛徒在这个地区实质上已经失势,佛教也不甚兴盛。
对于佛陀佈道的另一个重要据点毗舍离,法显只记载了若干佛教遗迹,而未提及僧众情况,或许佛教也比较冷落。
多摩梨帝国,地处西孟加拉邦入海处,那里有二十四僧伽兰,尽有僧住,佛法兴盛。
从法显在这里用两年时间写经、画像看,佛教文化相当发达。
它东渡缅甸,南航斯里兰卡,当是佛教走出印度的重要口岸。
四、斯里兰卡佛教
斯里兰卡佛教在大乘思潮的不断冲击下,促使无畏山寺内部发生了分化。
公元4世纪初,哥塔巴耶王即位(309年)后,一个叫乌西利那帝沙的长老率领300僧人离开了无畏山寺,到南山寺另辟据点。
其中的萨伽利(意译为“海”)长老,后来主持了大军王(334—362年在位)赐予的祇陀林寺,倡导大乘中观派主张,被称作祇陀林寺派。
这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第二次分裂,由此形成了与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三足鼎立的局面。
佛教大乘思潮并不都受到国王们的欢迎。
据《大史》记,哥塔巴耶王就曾对无畏山寺的方广部采取严厉的制裁,将该部60名僧人驱逐到南天竺的注辇(朱罗)国。
此后诸王对大乘佛教也多半实行限制政策,到12世纪,正式取缔了祇陀林寺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乘思想对斯里兰卡佛教没有深广的影响,就在大军王统治期,斯里兰卡的史籍提到了第一尊大乘菩萨像的出现。
汉译《六度集经》中的菩萨行故事,在南传三藏中也有保存。
继承大军王位的是室利·弥伽婆拉(362—409年在位),从印度羯陵伽国(哥达瓦里河以北,孟加拉湾沿岸)迎来了佛牙和部分舍利,并由国王亲自安置在宫中,无畏山寺的长老主持了盛大的奉祀典礼。
这是斯里兰卡佛教史上的大事,也是文化史上有意义的事件。
此后每年一度,都要将佛牙从王宫迎往无畏山寺供养。
佛牙成了斯里兰卡的国宝,佛牙出行成了举国欢庆的节日。
据说,以后在楞伽岛上只有真正拥有佛牙的人,才能够成为国主。
如今,佛牙保存在康提的佛牙寺中,被视作文化传统的一种象征。
公元410年,法显抵达师子国。
时国王笃信佛法,净修梵行,佛教大为兴旺;城内四衡道头都有“说法堂”,每月三次铺施高座,道俗四众皆集听法。
共有僧众5、6万人,由国王于城内供养者约5、6千人。
无畏山寺有僧5千人;寺东40里,有支提精舍,可有2千僧;城南有摩诃毗可罗精舍(大寺),有3千僧住。
王为众僧每造新寺,乃选好上牛一双,令其自耕四边,然后割给民户和田宅,书以铁券。
众寺建有僧库,多储珍宝、无价摩尼,王者为之生贪。
法显目睹了每年8月佛齿出行的壮观场面。
出行的前10天,饰王者骑象击鼓,演唱菩萨为众生苦行成佛的种种故事,道路两边作菩萨500身以来的种种变现,然后佛齿出中道而行,随路供养到无畏山寺佛堂。
道俗云集,烧香燃灯,种种法事,昼夜不息,满90日始还归城内。
如果说无畏山寺是法事的中心,而支提寺则有大德达摩瞿谛,大寺亦有高德沙门,并为国人和王者所宗仰。
法显在这里两年,更求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和《杂藏》等。
据此可见当时的斯里兰卡尚非上座部一系的世界,化地部就相当流行。
到法显的时代,师子国已成为南方佛教的重要圣地。
公元412年,其国律师僧伽跋尼在东晋庐山传律,译出《弥沙塞律抄》一卷。
429和433年,先后两批师子国尼众共19人来到宋都,在转道师子国来华的求那跋摩的主持下,为宋境尼众3百余人重新次第受戒。
为供养师子国尼众而建造的寺院名铁萨罗寺。
铁萨罗是她们的领袖。
488年,师子国觉音所注忧波离集的律藏,即《善见律毗婆沙》传来南齐,由僧伽跋陀罗在广州译出。
其中载有“众圣点记”,是确定佛灭时代的重要依据。
与肠宾南北相望,师子国也是向外传播戒律的一大基地。
撰写《善见律毗婆沙》的觉音(亦译佛音),是南传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学者,5世纪生于印度菩提伽耶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