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读书笔记.docx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读书笔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读书笔记.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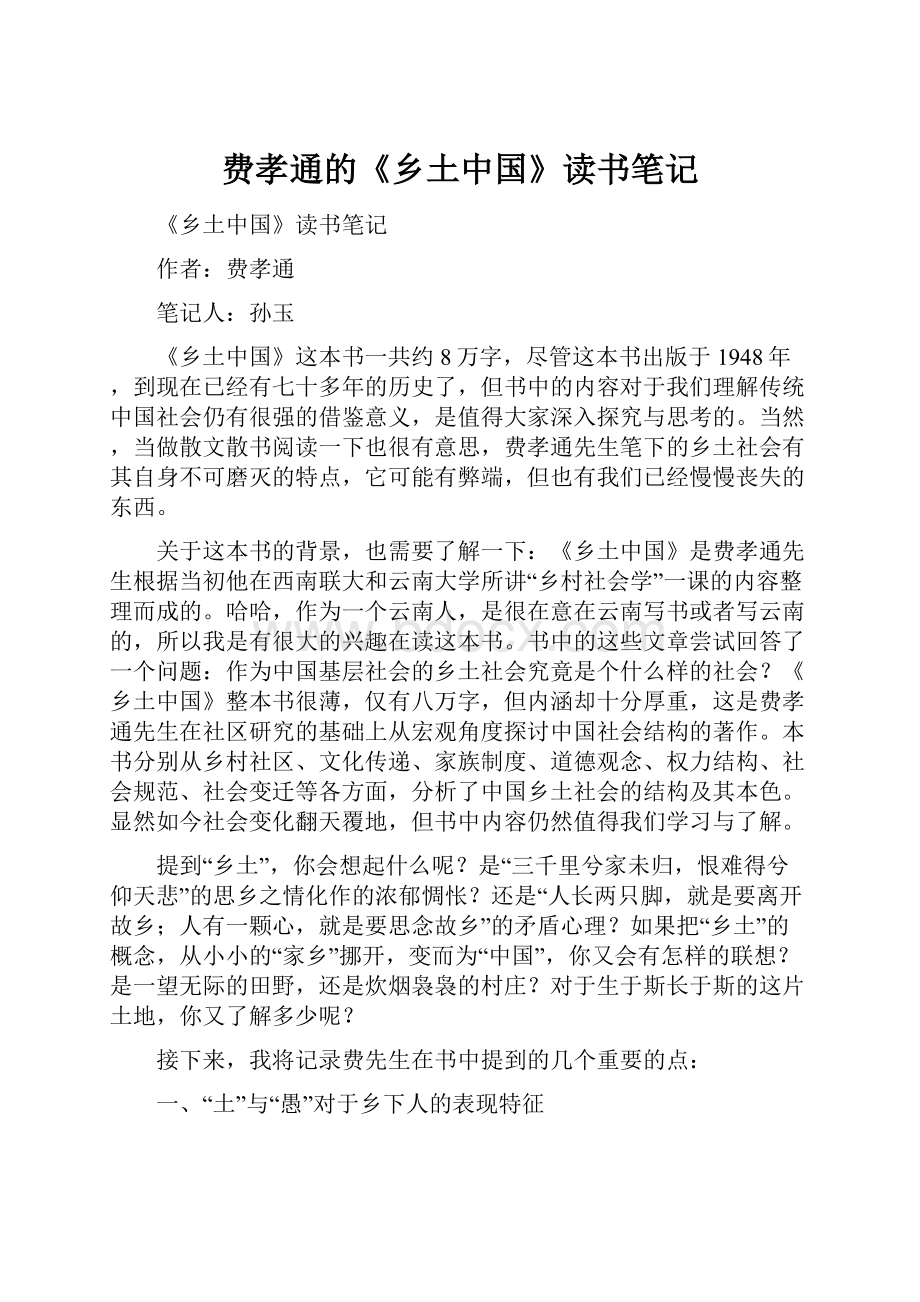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作者:
费孝通
笔记人:
孙玉
《乡土中国》这本书一共约8万字,尽管这本书出版于1948年,到现在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但书中的内容对于我们理解传统中国社会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是值得大家深入探究与思考的。
当然,当做散文散书阅读一下也很有意思,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社会有其自身不可磨灭的特点,它可能有弊端,但也有我们已经慢慢丧失的东西。
关于这本书的背景,也需要了解一下: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根据当初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整理而成的。
哈哈,作为一个云南人,是很在意在云南写书或者写云南的,所以我是有很大的兴趣在读这本书。
书中的这些文章尝试回答了一个问题:
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乡土中国》整本书很薄,仅有八万字,但内涵却十分厚重,这是费孝通先生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
本书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方面,分析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
显然如今社会变化翻天覆地,但书中内容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与了解。
提到“乡土”,你会想起什么呢?
是“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的思乡之情化作的浓郁惆怅?
还是“人长两只脚,就是要离开故乡;人有一颗心,就是要思念故乡”的矛盾心理?
如果把“乡土”的概念,从小小的“家乡”挪开,变而为“中国”,你又会有怎样的联想?
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还是炊烟袅袅的村庄?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你又了解多少呢?
接下来,我将记录费先生在书中提到的几个重要的点:
一、“土”与“愚”对于乡下人的表现特征
在这本书的一开始,费孝通先生就写到: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他建议我们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因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到: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
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
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
”
在乡下,“土”是人们的命根。
中国自古以来,在数量上站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
“土地”是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
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习惯在远离故土的时候,将一抔故土带入行囊。
由此情景,足以见得“土”在我们的这种文化里所占的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中国是依靠农业发展起来的国度,这个民族注定和土地分不开,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
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可以择地面而居,迁移无碍;但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地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半身插在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而这,便是乡村社会的特性之一。
除去“土”,在很多城里人的眼里,乡下人或许还是“愚”的。
有人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
“病”和“贫”是有客观的判断标准的,但是说乡下人“愚”,又是依据什么呢?
费孝通为我们解释了这一现象:
有的人说乡下人愚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为“文盲”,但这只是知识不足,并不是“愚”,因为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乡土社会的本质所造成的。
比如,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的汽车连续摁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
这是愚吗?
如果说这是愚的话,那么当一位城里来的小姐看着田里长的苞谷,却冒充着内行说:
“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这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一种愚的表现呢?
所以说,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这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我们并不应该将其定义为“愚”,这就好像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
文字也是一个道理,乡村孩子在生活中没有机会接触太多的文字,乡村部落的生活也不需要太多的文字,因而乡下人往往不善于识字。
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总是移动的。
因此,相对于城市,乡下的流动性会更小,这样就会产生一个结果:
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
在这样的社会中,经验的获取更多来源于传递或传承,正如书中写道:
“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
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板子里演员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
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时代的经验。
经验无需不断积累,只需老是保存。
”
对于这种传承性的经验来说,语言的作用远远大于文字。
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而这种询问往往是通过面对面的亲密接触,通过口口相传来完成的。
所以说,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必要。
因此,我们并不能仅仅因为乡土社会中乡下人拥有的知识量少,就判定其为“愚”。
当然,费孝通先生所写到的是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
如今,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基层已经发生了变化,文字也下乡了。
在今天,无论是乡下还是城市,人们的平均知识水平都直线上升,但是当年先生所说的道理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学习:
“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而且这种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
”
二、“公家的”与“私家的”
除去“土”、“愚”,费孝通提到,在当时的乡村工作者看来,乡村还有一个问题是“私”。
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句俗语。
其实抱有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是乡下人,就是所谓的城里人,何尝不是如此?
普通人家把垃圾往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
什么东西都可以向出路本来不太畅通的小河沟里一倒,明知有人家在这河里洗衣洗菜,却毫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自制的地方。
如果你问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么他们多半会回答——这种小河是公家的。
在很多人眼里,公家的就意味着可以占便宜,意味着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
两三家合住的院子,公共的走廊上尘灰堆积,满院生了荒草,谁也不想去拔拔清楚。
没有一家愿意去管“闲事”,因为谁看不惯,谁就得白侍候人,到最后反而连半声谢意都得不到。
于是像坏钱驱逐好钱一般,公德心就在这里被自私心驱走。
但是,我们一直在说私,那什么是私,什么又是公呢?
我们常常说的“自家的”和“公家的”又是怎样划分的呢?
费孝通通过中西社会的不同例子,为我们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
假设有一个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你知道要和他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吗?
如果是在西方,这是很明确的。
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
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
但是在中国,这句话是含糊的,因为在我们的用字中,这个“家”字可以说是最能伸缩自如了。
“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
由此看来,自家人的范围在我们的语言环境中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方的格局是不相同的。
如果说,西方的格局是一捆一捆的柴,那我们的格局更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著名的“差序格局”。
三、可伸缩的差序格局
与西方社会的格局相比,我们的社会格局如同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可能是圈子的中心,而每个人也可能是被波及的部分。
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中国人的亲属关系网络,可以广袤无垠,一直连接着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
而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
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是完全相同的。
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
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
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便是“街坊”。
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
同样,这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
这一范围的大小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
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布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贾家鼎盛的时候,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甚至宝琴,岫云,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
可是势力一变,便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
可见,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
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家庭便可以大到像个小国。
正是因此,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
西方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费孝通先生将这种格局与儒家常常讲到的“人伦”联系在了一起。
儒家在关系中讲究“人伦”,费孝通先生把这个“伦”解释为:
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
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
伦是有差等的次序。
所谓“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意思是这个社会结构的架格是不能变的,变的只是利用这架格所做的事。
这种差序格局在中国社会中有多么根深蒂固,我们以儒家的孔子和基督教的耶稣对比来看看。
耶稣普爱天下,甚至爱他的仇敌,还要为杀死他的人请求上帝的饶赦。
但是孔子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论语》里面的一段对话。
或曰:
“以德报怨,何如?
”意思是说,用善行回报恶行,怎么样?
子曰:
“何以报德?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孔子说,用什么回报善行?
用适当的代价回报恶行,用善行回报善行。
这是孔子所强调的差序层次,他把这道德范围依着需要而推广或缩小。
回到我们上次谈到的“私”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差序格局中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就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私”的问题了。
因为这种差序的推浪形式将群、己的界限变得模糊,所以对于公私的看法,对于权利和义务的分别也难以清清楚楚。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学》中说:
“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
当一个人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
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
因为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
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道德体系与道德观念的出发点,是“克己复礼”(指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你可以发现,在差序格局中我们很难甚至无法找到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
以儒家为例,其所提倡的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
或许,有人可能会说,那仁呢?
孔子常常提到的“仁”难道不是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吗?
那我们不妨来想一想,在孔子眼中何所谓“仁”。
孔子常常提起“仁”字,《论语》中对于“仁”字的解释最多,但是也最难捉摸。
孔子不少次认为很多人“不够说是仁”,但是当他积极地说明仁字是什么时,他却说“克己复礼为仁”。
克己复礼,你看,最终还是退回到了这一套私人间的道德要素了。
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
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
中国的道德和法律,也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为我们举了这样的例子:
“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讳隐。
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
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
”这看上去似乎很矛盾,但实际则不然。
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让我们判断拿出什么标准来的,往往是对象的身份,以及他和自己的关系。
那么,在乡土社会中,有没有基本的社群关系呢?
当然有,这种社群被称为“大家庭”,也就是费孝通先生在另外一本著作《江村经济》中所提到的“扩大了的家庭”。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大并不是取决于人数,而是取决于结构。
也就是说,一个有十多个孩子的家并不构成“大家庭”的条件,但一个只有公婆儿媳四个人的家却可以被称为“大家庭”。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家庭是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
“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
这社群的结合是为了子女的“生”和“育”。
但是生育的功能,就每个个别的家庭说,是短期的,孩子们长成了也就脱离父母的抚育,去经营他们自己的生育儿女的事务。
因此,家庭这个社群是暂时性的。
家庭既以生育为它的功能,在开始时就得准备结束。
抚育孩子的目的就在于结束抚育。
但是在乡土社会中,家庭关系并没有随着结束抚育而终止,而是沿着亲属差序向外扩大,进而形成家族。
费孝通认为,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的了。
这样一来,一代一代,一圈一圈,家便绵延不断,不因个人的成长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
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
不过,这样形成的团体社群与西方是不同的。
在西方的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子女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
但是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却并非如此。
我们的家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
如此一来,夫妇便成了配轴。
同时,配轴虽然和主轴一样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
所以,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成为了日常可见的现象。
我们会发现,乡下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话的”,“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更别说有什么亲热与亲昵的举动。
在乡下有说有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龄的集团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用他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叫“男女有别”。
四、关于男女有别
在乡土社会中,我们似乎很少看到夫妻之间耳鬓厮磨,你侬我侬,多半是一早便各人忙各人的事,出了门,也是各做各的。
妇人家如果不下田,便留在家里带孩子。
男人们工做完了也不常留在家里,有事在外,没事也在外。
茶馆,烟铺,甚至街头巷口,都是男子们寻找感情上安慰的消遣场所。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要想探究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男女分化开始说起。
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但生育却又规定了男女的结合。
这一种结合基于异,并非基于同。
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是困难的,是阻碍重重的,是需要不断地在创造中求统一的,但最后的统一是永远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
不但这样,男女的共同生活,愈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序也愈是深,求同的阻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这阻碍的创造力也更需强大,不过也有人认为,正是因为这样,生命力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
但是,在乡土社会中这种精神是不容存在的。
因为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它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的。
比起不需要创新,乡土社会更害怕的是社会关系的破坏,因此,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
这便是男女有别的原则。
“男女有别”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因此需要在生活上加以隔离。
这隔离非但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发生在心理上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便是如此,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
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秩序破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
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
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五、关于礼治秩序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更多的时候讲究的不是“法”,而是“礼”。
所以,我们要提到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礼治秩序。
如果说,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那么在乡土社会中,礼则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
那么,法和礼的差别在哪里呢?
如果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说,礼本和法律无异,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礼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
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
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那么,传统是怎么维持礼的呢?
我们不妨回到问题的源头来思考。
究其实质,我们规范行为的目的是什么?
是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而社会的任务是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所以归根究底,我们规范行为是为了尽可能地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
而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
这个时候便需要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
上一代所试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
这样一代一代地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
而在乡土社会中,这一点就更加明显。
因为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在这样的环境中,父辈们的经验更加可靠和有效,到最后,生活在这样社会里的人,对于很多传统,不必知晓为何,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
于是人们对于传统就渐渐有了敬畏之感。
这种敬畏感不断地加深,而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所谓的“仪式”。
因此,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
但是,礼治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
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个前提,所以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
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
不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的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
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方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个人了。
这其实就是法律。
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
乡土社会可以说是“无法”的社会,但作为礼治社会,其秩序并非是由个人的好恶来维持的,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
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人们已经把外在的规矩化成了内在的习惯。
因此,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
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
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
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
比如,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偷偷地越出规矩。
不过,在乡土社会中,一个人做出这样的事,首先可能会被谴责没有规矩,而不是不遵循法律,那么解决的理想手段也往往是教化而不是折狱。
这种教化手段,在乡村往往被称作调解。
所谓调解,便是一场教育的过程。
那么,在乡村什么人会充当调解者呢?
往往有两类,一类是村里读书知礼的人,这类人往往被认为是权威。
再有一类便是村里的长老。
归结起来,便是德高望重之人。
而调解的过程,也大同小异。
这一过程,在我们看来是调解,在矛盾双方看来,则是评理。
所以,在乡村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局面:
两个争执得不可开交的人吵到最后总会说一句,我们去找谁评评理去。
于是便推推攘攘地来到调解人的家里。
而充当调解者的人总是把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
训斥的语言也大同小异,比如说:
“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
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
”教训之后,他依着他认为“应当”的告诉他们。
这在乡土社会里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
从中也可以看出,法和礼的区别在于:
一个法官并不考虑教化人,刑罚的用意也不再是立规矩,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
但是,在乡土社会中,长老或者调解人不是这样,他们往往更多考虑的是道德问题、伦理问题,是希望不丢这个村子的脸,不破坏现有的规矩。
但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使得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
在中国传统的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
普通老百姓弄不明白这一套,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样利用。
因此,其实在当下中国,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
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了。
这就使得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
这是一个二元悖论,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但从事实上看,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的“败类”的人物。
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
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
因此,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
六、血缘与地缘
血浓于水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也是中国人非常重视的一点。
而这种血缘关系,在越缺乏变动的文化里就越被看重。
什么是血缘社会呢?
血缘社会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
血缘社会的基础是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
血缘社会是稳定的;变动得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
我们所说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而非个人的静止。
这种结构的静止表现在:
虽然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受着生命的限制,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但是通过生育依旧可以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
比如,职业的血缘继替是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身份的血缘继替是贵人之子依旧贵;财富的血缘继替是富人之子依旧富。
也就是说,在很多时候,血缘社会中,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
而这个地位往往取决于谁是你的父母。
血缘如此,那地缘又是什么?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
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地缘是社会契约的基础。
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规定。
因此在订立契约时,个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
契约的完成是权力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定的单位,可靠的媒介。
因此,在地缘关系中,我们有的是冷静的考虑,是理性而不是感情支配着人们的活动。
但是,这在乡土社会中是缺少的。
因为乡土社会的稳定性使得地缘关系也成为了血缘关系的投影。
“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
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
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
就像儿谣里唱的那样:
“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里,“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
而血缘和地缘的合一便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所以,在乡土社会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些生活在这个村子很久的外乡人,一些寄居在社区边缘上的人物往往并不觉得自己已经成为村子中的一员,也并不能说已插入这个村落社群中,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
而这些都是因为乡土社会是个亲密的社会,这些人却是“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
那这种亲密的血缘社会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首先,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着若干社会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冲突和竞争。
亲属是自己人,是从一个根本上长出来的枝条。
所以,在乡土社会中,原则上面对亲属应当痛痒相关,有无相通的。
况且在这样一个流动性很低的社会中,亲密的共同生活就意味着人和人相互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这样一来,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地清算往回。
或者说,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在一定程度上就依赖于人和人之间都相互拖欠着未了的人情。
所以也才会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说法,在这种社会中,亲兄弟明算账是很难的。
在我们的朋友圈子中,也很容易看出这一点。
朋友之间抢着回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
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
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合作。
所以,亲密社群中很难甚至无法不互欠人情,而且也最怕“算账”。
因为“算账”这个词在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