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docx
《《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docx(2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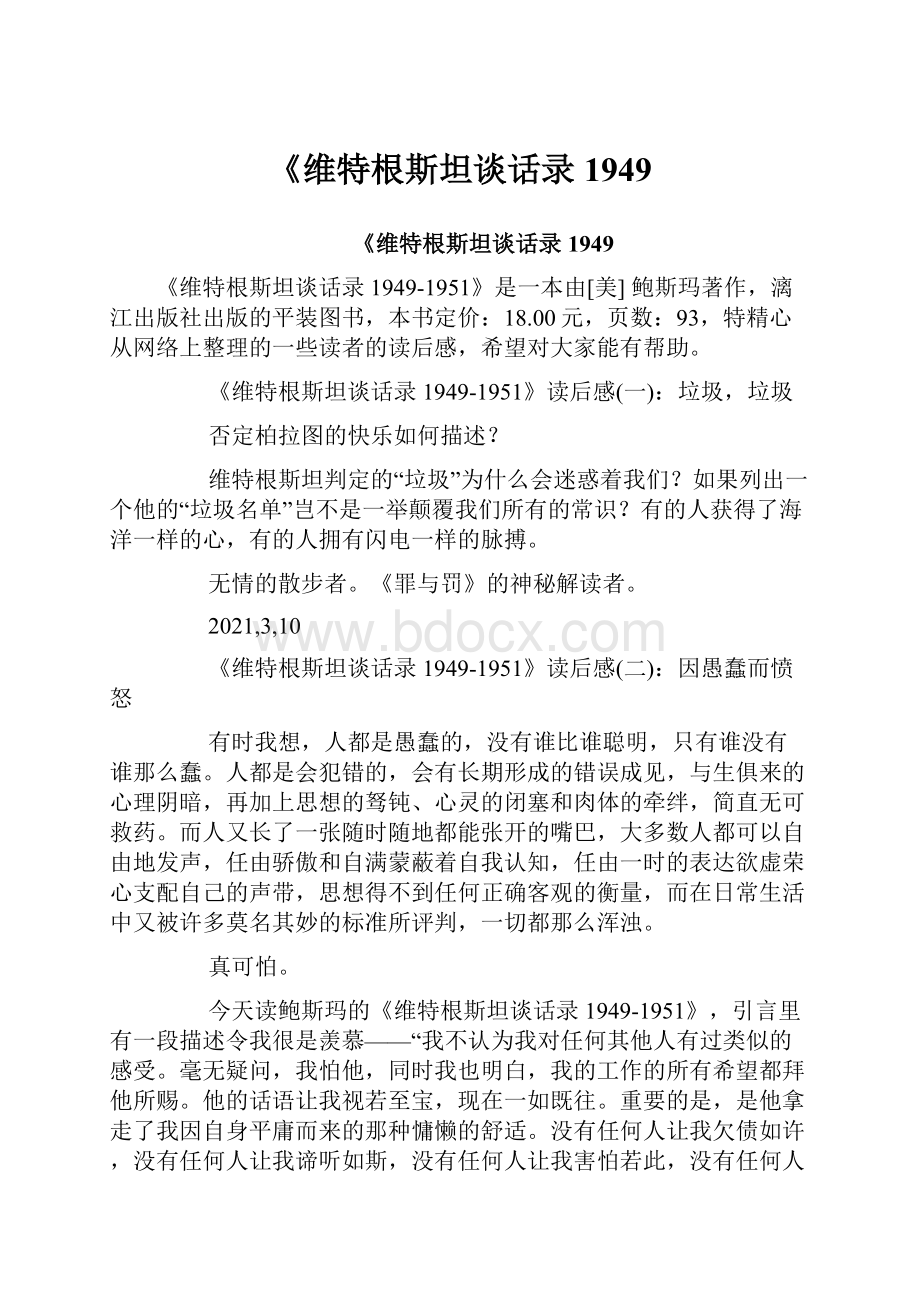
《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
《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
《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是一本由[美]鲍斯玛著作,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
18.00元,页数:
9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读后感
(一):
垃圾,垃圾
否定柏拉图的快乐如何描述?
维特根斯坦判定的“垃圾”为什么会迷惑着我们?
如果列出一个他的“垃圾名单”岂不是一举颠覆我们所有的常识?
有的人获得了海洋一样的心,有的人拥有闪电一样的脉搏。
无情的散步者。
《罪与罚》的神秘解读者。
2021,3,10
《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读后感
(二):
因愚蠢而愤怒
有时我想,人都是愚蠢的,没有谁比谁聪明,只有谁没有谁那么蠢。
人都是会犯错的,会有长期形成的错误成见,与生俱来的心理阴暗,再加上思想的驽钝、心灵的闭塞和肉体的牵绊,简直无可救药。
而人又长了一张随时随地都能张开的嘴巴,大多数人都可以自由地发声,任由骄傲和自满蒙蔽着自我认知,任由一时的表达欲虚荣心支配自己的声带,思想得不到任何正确客观的衡量,而在日常生活中又被许多莫名其妙的标准所评判,一切都那么浑浊。
真可怕。
今天读鲍斯玛的《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引言里有一段描述令我很是羡慕——“我不认为我对任何其他人有过类似的感受。
毫无疑问,我怕他,同时我也明白,我的工作的所有希望都拜他所赐。
他的话语让我视若至宝,现在一如既往。
重要的是,是他拿走了我因自身平庸而来的那种慵懒的舒适。
没有任何人让我欠债如许,没有任何人让我谛听如斯,没有任何人让我害怕若此,没有任何人让我如此相形见绌。
我没有目睹也没有听闻任何人能与他相提并论。
”
看来,维特根斯坦于鲍斯玛,是神一般的存在。
这种虔诚,这种感激,这种谦卑,似乎带有某些宗教性质。
身边的神。
我想,绝大多数人的生命中,都不曾遇见一个这样的对象。
当我心里有一个想法,当我对某个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当我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我要怎样能知道我是对的。
我知道,即使我错了,也并不至于在听者和读者的心里产生多大的不良影响,毕竟人们了解信息的渠道远不止于此。
但是,抛开别人不谈,自己的思想若能有一个坚实的依靠,该是一件多么有安全感的事。
我想遇见一个人,能够为我的愚蠢愤怒,并让我信服,我会怕,也许会哭,但也会感激。
让我在某一个人面前保持永久的谦卑,让我不论是当时顿悟或者过后思考,都会发现他是对的,没有一点不平、委屈、无言以对。
要注意的是——指出别人的愚蠢是很困难的,而对别人下一个愚蠢的判断却简单。
我非常讨厌有些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用“你还小”之类的话来堵我,因为比我多吃几十年的饭并不是他比我正确的充分条件。
我需要被说服,需要明白我为什么错了。
如果有人能在说服我的同时,为我的愚蠢而愤怒,那更是应该感激的——为我的思想有错而生气,大动肝火地要我改正,还有比这更慷慨无私的事么……
但是,遇见自己的神不容易。
我有和睦的家庭,家里每一个人都与我有着永不割舍的联系,给我最好的祝福;我有相交几年的朋友,见或不见都会牵挂,会惦念;也许以后我还会有一个忠诚的爱人,许下爱我一生的承诺,并矢志不渝……但现在没有,以后大概也不会有的,大概就是一个随时指出我的愚蠢并为之愤怒的人。
也许终其一生,也只能在漆黑的道路上自行摸索。
然而,至此,我发现,指出我的错误最多的人,是我;为我的愚蠢大为恼火的人,是我;能够用一种观点推翻我的原有观点的人,是我。
我简直无法想象没有自我审视和纠正的人生是多么可怕。
蒙昧的浊物啊,竟做了自己的神。
《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读后感(三):
行走的图景
这当然算不得是一篇书评,但是也绝非为一页笔记,那究竟是什么?
一种现象一度令我感到不可思议:
人们在描述某人将死之前的情形总是能达到一种近乎极端的清晰。
显然,对于缺乏死亡提示的平常的每个瞬间,我们总不会记得太牢靠:
试着描述一下早上10点15分时你的每一个动作。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鲍斯玛的记录当然没有细微到如此程度,但即便仅仅是最后短暂的18个月里的只光片影的记录,文本也意在提示着什么。
那些东西于维氏而言,近乎生命的根本,但也恰是为人所不理解的部分,这一点,作者以某种略带戏剧性的意味展示了出来。
在借助命题述谓结构的言说和哲学言说之间,维氏究竟看见了什么以致于被深深刺痛的他终究选择“沉默”?
引号又将含有哪些重要的提示?
可以看到,这里维氏正在遭遇和1935年前后的海德格尔同样的困顿:
如何开启一种有意义的“说”?
海氏在艺术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为“诗”的艺术言说所表征的某种非述谓性的“思”。
他选择了Denken,抛弃了Philosophie。
而对于维氏,Verschwiegenheit展示着什么呢?
这一类困惑一开始便纠结于阅读当中,这里期待一种清晰,显然,这无关乎海氏在艺术问题上所言说的“澄明”,以及在诗歌语言中获致的那种“显明”。
毋宁说,在维氏的言说里,向Denken身份的转换还远未触及那些至关重要的差异。
读者必须直面类似的困惑:
这里究竟需要什么意义上的清晰?
很明显的一点是,作为文字记录者的鲍斯玛在如下一点上与维氏在《哲学研究》以来的文本写作中所力图展示的一种思考相吻合:
叙事(如很多记录者所以为的那样)将不再是重要的展示手段,重要之处在于如何通过图像的勾画使得一种差异和联系凸显出来,虽则在维氏看来,人们对图像的后续使用通常总是在一种错误的观念引导下展开的。
不同于Monk等作家,鲍斯玛并未通过一些既得信息来构建一个饱满圆融的故事框架来展示一种真实的场景,而是极力将行动以及思考的精微细节真实地刻画出来,而不置入任何有待填充的叙事架构。
这一点对维氏而言显得至关重要,它与维氏思考哲学的某种方法密切相联:
看清一种“面相”。
看清一种面相亦即获得一种差异,而一种差异则意味着一种行止。
既然,思考的某种力度将真切地体现在一种“看”上,那么通过细致入微地对细节和局部的查验而力图在一种混乱中获得一种面相将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训练。
鲍斯玛或许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许没有。
但在其提及维氏时的一些只言片语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对后者的某种“敬畏”使得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进行叙事编排的狂妄勇气,而宁愿(正如布鲁姆所揭示的)以一个“矮子”的形象示人。
实际上的确如此。
对作者所能亲历的18个月以来维氏行动细节的详细描画恰从深处紧扣读者的心弦。
从见面的一开始,维氏就以其急促的思考力度和令人不安的严肃深沉使得鲍斯玛时刻绷紧神经面临某种“挑战”,恰如他所说,“当他离开的时候,我感到自由”。
这是一幅极富宗教张力的画面,面对维氏的严肃和暴躁就如同体验着耶稣式的热忱与庄严,但也恰如译者所指出的,“宗教是一种‘隐喻’,除非重新定义宗教”。
在面对维氏时,人们将一次次被扯进一些极为平常的生活图景里,在那里,维氏正奋力地展开一项讨论、细心地观察着一片叶子、小心地识别一只不知名的生物、不断地撕扯自己的头发咒骂着自己的“愚蠢”......似乎没有丝毫的停歇与倦怠。
但,那些说了的和正在说着的,或许已经不在重要,而在生活深处那紧皱的双眉间,维氏却以某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正言说着一些极为深刻的洞见。
鲍斯玛察觉到了一种深刻和力量,但是正如所有人正在做的那样,我们并不理解那是什么。
在一种行动细节的细微展示里,我们看清了一种联系或者差异,于是形成一幅图景,那么清晰自然,以至于一度曾使我们误以为已经理解了一种哲学。
但正是在迈开那显示行动意味的第一步时,一切又变得如此混乱不堪,我们将不得不跟随这颗伟大的心灵,并期待下一刻某种行走图景的生成。
在一种宗教意义上,这里展示着一种教化与一种践行,而在花园、吊桥、地下室、瀑布、以及林间,维氏和鲍斯玛各自进入了各自的生活。
有一种“清晰”,获取它则需要我们一度的“混乱”。
《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读后感(四):
【刘云卿】:
维特根斯坦的捕蝇瓶---兼论《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
维特根斯坦的捕蝇瓶
——兼论《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
刘云卿
虽然几经起伏,维特根斯坦让人困惑的影响力持续至今。
他过目难忘的头像就像旧时的门神秦琼和尉迟恭,不时地会出现在年轻读者的床头或者桌边。
笛卡尔与福柯暧昧的面相让人一眼就能看出那是一副面具,尽管其深度无从测度,与他们不同,维特根斯坦的那张有着非凡穿透力的脸好像与面具无涉,他的读者认定它是透明的。
一般来说,像笛卡尔那样“戴着面具出场”未必是维特根斯坦的意图,但其人格与哲学的复杂性强化了这种感觉。
试想一下与维特根斯坦相连的那些界定,诸如“逻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哲学”之类在今天看来有多么离谱就可以对此类困惑略知一二。
在这种意义上,从斯坦利?
卡维尔(StanleyCavell)到斯蒂芬?
马霍(StephenMulhall)的“新维特根斯坦主义”只能算是一种矫枉。
维特根斯坦特有的悖论在于,作为“学院哲学”最炙手可热的论题(一如海德格尔,背后是庞大的学术工业),其意图旨在颠覆哲学作为一种学科的合法性。
这可以部分解释他在英美学院哲学中起伏不定的声誉。
另外,除了不多的几个例外,比如布尔迪厄和米歇尔?
德?
塞都,所思对象的“特定性”使他成为英语世界以外的“放逐者”。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复杂性源自诸多因素,譬如这种哲学置身其中的环境、维特根斯坦的意图和他的哲学策略。
《逻辑哲学论》写于战壕之中,《哲学研究》跨越了二战。
“黑暗时代”的说法并不像说出来这么轻描淡写,寄身其后的一切构成维特根斯坦伦理企图的一部分。
他试图摧毁的“沙滩建筑”覆盖了希腊已降的传统,不过,那并不意味着他必定侧身“犹太哲学”的谱系。
维特根斯坦没有置身事外,但仍然与自迈蒙尼德直至罗森茨威格的犹太哲学判然有别,尽管有一次他说自己是百分之百希伯来化的;维特根斯坦是“犹太哲学家”,同时又不是“犹太哲学家”。
这个悖论多少有些类似他贯穿始终的信仰问题。
很难想象维特根斯坦会隶属于某种特定的宗教,那是他“一个人的宗教。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信仰与恶的问题紧密相关。
他绝非偶然地成为克尔恺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并对斯塔夫罗金、伊凡?
卡拉马佐夫、斯麦尔佳科夫表达了耐人寻味的同情。
同样道理,纵然对恶的想象力异乎寻常,维特根斯坦的纯真始终如一:
艰苦卓绝地祛除恶的努力构成其人格的一部分。
先知现身在朝向先知的努力之中。
小心地规避任何诱惑,拒绝被指派给任何流派,也不会委身于任何宗教构成这种努力最为可见的一部分。
正因为如此,将维特根斯坦还原到与之相关的语境(《Wittgenstein’sVienna》)、将其植入一种语境(《LanguageandSolitude》),抑或将其“风格”的根源追溯到里希滕贝格均于事无补。
生命的难以规范一如哲学的难以规范。
在某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算得上是一位“古人”。
他完全可能是帕斯卡尔和莱布尼茨的同时代人,或者侧身列奥纳多身旁,甚至更为久远,比如普罗提诺或斯多葛学派,直至苏格拉底;哲学与人的一致性可溯至历久弥新的传统:
视哲学为一种“生活方式”。
这注定了他的哲学外观,“哲学著作”的意义,以及人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不可能轻易地被收编为意识形态的元素,也不是某种类似于女红或收集蝴蝶标本之类的无关痛痒的嗜好,同样不可能只是一种“学说”,从而与人无关。
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哲学乃是荡涤灵魂的力量,是一种战斗和行动,并影响着具体的行动。
德?
塞都说的没错,他是二十世纪的“赫勒克勒斯”;维特根斯坦试图去撬动那条经久甬道的每一块石板。
对《哲学研究》莫衷一是的解释正是这种复杂性的体现,对“职业哲学家”和剑桥“学院生活”的憎恶,一如对“牛津哲学”的轻蔑,构成最外在的证词。
《哲学研究》的“公案”自罗素伊始就始终相随。
克里普克甚至认定维特根斯坦无力写出前后一贯的著作。
这种荒谬的判断竟然出自一个有声望的学者之口多少让人有些惊讶。
在某种意义上,印行了近六十年的《哲学研究》仍然是一本尘封的书,学者们似乎只是徒然地扬起尘土。
《哲学研究》第一部分1947年业已完成,并准备交付出版,但维特根斯坦最终放弃了生前出版它的愿望。
或许他所怀抱着卡夫卡式的想法:
就其自身而言,所“写下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完美无缺的”,但面对上帝,它们微不足道。
面对自身著作的含混其辞堪称题中应有之议。
此类担心从他意味深含的前言中可见一斑。
只有傻子才会完全相信或全然不信他在“前言”中写下的话,诸如“风景相册”之类的说法;它的似是而非意味着一种选择。
在《逻辑哲学论》的前言中维特根斯坦选定了他的读者,这种遴选在《哲学研究》中更其隐蔽。
被排除在外的人可以试着去阅读他的“传记”。
哲学以外没有传记,他隐秘的传记写满了他的言行。
于是,二十世纪最动人心魄的哲学著作纵然由“断片”组成,其“结构”依然完整无缺。
《哲学研究》是德语中的“杰作”,是那种刷新了“杰作”含义的杰作,它的独一无二只有散文中的晚期卡夫卡或诗歌中的晚期策兰尚可比拟。
如果说在被迻译成英语时,它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优秀著作”,那么罪不在安斯康(G?
E?
M?
Anscombe):
《哲学研究》激发出德语的潜能,换句话说,它使自身变成了“外语”,而当它被落实为一种实在的外语时,它毫无选择地堕入平庸。
听完乐队演奏的《李尔王》的序曲后,柏辽兹回答说:
差不多正确,“差不多正确”的意思就是完全错了。
这里不是考虑“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关系的地方,但翻译几成隐喻:
独一无二的存在伴随着对它的特定“使用”。
使用是必然性的一部分。
这里涉及到那种被称为“哲学风格”的东西。
表面看去,这种风格寄存在一种语言特有的措辞、节奏和韵律之中,比如汉娜?
阿伦特所说的“感叹词”或埃里希?
海勒(ErichHeller)所说的“分号”之类。
两位出身德语的思想家辨识出了《哲学研究》的特异之处丝毫不会让人感到惊讶,同样顺理成章的是,比起那些“学院学者”,伯恩哈德和巴赫曼似乎更能够领悟它的深邃和微妙。
《哲学研究》不止如此。
维特根斯坦拒绝出版的另外一个原因或许来自作为“作品”的《哲学研究》所具备的强制性。
在《逻辑哲学论》中,“沉默”比言说更为重要,与这种沉默同样重要的,是他在奥地利乡村长达六年的沉默。
与之相比,《哲学研究》的自我消解毫不逊色,但挑战更其巨大。
拒斥理论的意图注定了方法上的描述性,然后是例证的选择和剪辑。
维特根斯坦切换的方式乃是一位伟大导演的方式,间或出现的沉默不啻对话的猝然中断,它们左右着运行的节奏。
跳接和错位的剪辑随处可见。
《哲学研究》中的例证像是对日常生活的“移植”,看似漫不经心,俯拾皆是,另一方面,它们的刻意和精湛就像取自《格林童话》或者《哈希德故事集》。
它们高度肖似但却无以重合,既不能还原又无法“使用”。
不仅如此,《哲学研究》无异于“精神操练”的记录,从而并置着记忆和启示。
那段细小的距离可以忽略不计,可一旦付诸丈量,你却无从跨越。
《哲学研究》中充斥有着难以预期的跳跃。
如果《哲学研究》是一部作品,它的背叛就难以规避;如果它不是作品,“语法的”或“逻辑的”描述,或者伴随着每一次具体的“看”而来的“先验性”是无法理解的。
无限的可能性取代了对可能的启示。
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提供某种“非哲学”或阿兰?
巴丢所说的“反哲学”,他只是拓宽了哲学的疆域,在这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超越了所有的哲学家,包括尼采。
整体看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神秘的,尽管晚期的论题从不涉及神秘。
维特根斯坦是平衡的大师,就像“走钢丝的表演者”:
一如生命为死亡包围,健康的理智为疯狂包围。
这种平衡在《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被打破,换句话说,它以另外一种方式被建立了起来。
存于维特根斯坦及其哲学中的平行性借助一个亲证者的手得以交汇;并置被连接取代。
尽管“死亡不是生命的事件,”但死亡或许是通向永生的门户。
那些看似无心的记录变成了从不朽背后实施的刻画。
经验的重复在死亡的背景下变成了事件,它们的清晰难以言传,似乎每一个动作、眼神和姿态都是独一无二的。
博尔赫斯有一次说,从这一扇门走到另一扇门就完成了一次宇宙旅行。
当一个哲学家的行动转变为更新经验的材料时,悲凉与慰藉拥有同等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意在为苍蝇指明逃出捕蝇瓶的线路,结果招引了更多的苍蝇朝着捕蝇瓶飞去。
但维特根斯坦不是叔本华,后者对其身后之事很是担心,非常害怕那些“教授们”会吞噬他的著作,就像蛆虫吞噬他的尸身。
维特根斯坦完全没有这种担心,因为教授们无从找到他的尸身,他们只是对着空空的墓穴张开了嘴巴。
被追捧而不是被理解未必是他的愿望,他也未必喜欢,但这一切都没有超出他的预料。
当有人说起舒伯特的崇拜者疯抢这位音乐家被扯碎的乐谱时,维特根斯坦表示了理解。
就像一颗孤独的星辰,维特根斯坦独自在夜空中闪耀。
按:
本文的编辑版被载于3月25日的《光明日报》。
《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读后感(五):
:
可惜说这些都晚了高山杉发表于2021-06-1001:
35
《维特根斯坦谈话录:
1949-1951》
[美]鲍斯玛著
[美]克拉夫特哈斯特维特编
刘云卿译
漓江出版社
2021年2月第一版
93页,18.00元
艾耶尔1954年访问中国时惊讶地发现,在这个哲学的鸟从不生蛋的国家,居然还住着像洪谦这样的逻辑实证主义者。
其实这也没啥好奇怪的,如果他往美国中西部内布拉斯加州跑一趟的话,就会发现在这个荒草多于文化的地方,顽强地生存着一个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阐释者——鲍斯玛(NetsKolkBouwsma,1898-1978)。
要知道就算在当时的英国,也没几人能说清楚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到底是什么东西。
鲍斯玛是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的名字看上去有点儿怪,因为那是荷兰语,他是荷兰移民的后代。
鲍斯玛原是黑格尔哲学的拥趸,后来因为读到摩尔(G.E.Moore)的著作,就和唯心论说再见了。
他不仅自己刻苦钻研摩尔的思想,还把学生送到剑桥跟摩老深造。
这些学生里面有个叫马尔康姆(NormanMalcolm,1911-1990)的,一到剑桥反倒被维特根斯坦给迷住了,他就是《回忆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AMemoir)的作者。
在此前后,鲍斯玛也读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笔记《蓝皮书》,这书当时在私底下流传,还是油印本。
通过阅读,他意识到摩尔只是个鸣锣开道的,而维特根斯坦才是“那将要到来的”先知。
1949年7月,已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马尔康姆促成维特根斯坦访美,在大学和自己家中举办各种讨论班,参加者有纳尔逊(JohnNelson)、多尼(WillisDoney)、布莱克(MaxBlake)、布朗(NormanBrown)以及专门从内大跑来的鲍斯玛。
鲍斯玛比维特根斯坦约小十岁,为人严肃踏实。
初见面时,鲍斯玛非常紧张,也有些害怕,但没想到先知非常看重他,多次邀他一起外出散步,讨论问题。
鲍斯玛很快意识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少见的天才,他不喜欢闲聊和扯淡,对别人所提的问题,不分大小,都以狮子搏兔的方式思考,能听他讲话,实在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遇。
在康奈尔度过夏天后,鲍斯玛来到麻省北安普敦的史密斯女子学院担任秋季学期公休学术假期的替补教师。
维特根斯坦回英国前,又于10月中旬到史密斯学院拜访鲍斯玛,待了大概三天,两人继续散步、讨论。
回到英国后,牛津方面请维特根斯坦担任“洛克讲座”,他谢绝了,却推荐了鲍斯玛,于是两人又在英国重逢,重新开始散步、讨论,直到维特根斯坦1951年4月在剑桥去世。
鲍斯玛后来回忆说,想起要给维特根斯坦汇报洛克讲座的事儿,他心里就害怕。
还好,老维什么也没问。
鲍斯玛是个有心人,维特根斯坦每次讲什么,他都记在脑子里,回来就做笔记。
这些笔记一直在学生和朋友间流传,但鲍斯玛从未有出版的打算。
原因之一是维特根斯坦骂了一些人,而这些人当时大多数还在世。
老维骂人的导火线,是席尔普(PaulArthurSchilpp)主编的《在世哲学家文库》。
这套书出版时,张大哲学家申府曾作热情洋溢的推介,说它是“大战的几年里边,最出色的一部哲学书”。
但维特根斯坦和老张显然意见不一致。
关于杜威卷,他很不屑:
“杜威还活着呐?
”鲍斯玛贡献过文章的摩尔卷,有篇摩老的自传,里面描述了自己的童年。
老维却哪壶不开提哪壶:
“但鞋匠也有童年呀。
”
最毒舌的评语,献给了老维早年的两个师傅,罗素和怀特海。
张申府在《罗素——现代生存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中肉麻地说过:
现在罗素在浪迹差不多三十年之后又复回到原来治学讲学的剑桥三一学院去了。
据说也已白发满头(从照像上也看得出)、老态龙钟(?
)了。
这是人生的无常。
可是罗素的学问、罗素的思想、罗素的著作、罗素的风趣、罗素的同情(仁),却正如日月在天,定同日月之常。
对于重回剑桥吃粉笔末的罗素,老维的评语与张大哲学家正好相反:
“罗素一度挺好的,做过一些扎实的工作。
他好的时候,剑桥让他走人了。
他不好的时候,又把他请回来。
”从这里看不出什么“日月在天”的样子。
张申府的《罗素》发表在1946年4月12日的《新闻评论》上,请看前一年老维所见的罗素:
“罗素1945年办过讲座——三个听众席挤满了女人和美国兵。
最后一讲是罗素论罗素自己。
什么呀,难看死了。
”不过老张有一点倒说对了,“恨他的纵有,爱他的更多,特别在女人群里”。
怀特海如何?
老维一个都不饶:
以前还不错,后来呢,骗子一个。
鲍斯玛说,维特根斯坦不明白这些人到底是肿么了。
某些人本来有天赋,特别是罗素,可后来就好像他们觉得“我干得可以了”,就松懈下来。
科学家中好些人也这样,他们停下来,吃着老本儿。
维特根斯坦特别提到赫兹(Hertz),说这人从不松懈。
赫兹就是德国那个大物理学家HeinrichRudolfHertz(1857-1894),他影响了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属于老维一辈子都佩服的特殊人类。
科普“双子星”金斯(SirJamesHopwoodJeans)和爱丁顿(SirArthurStanleyEddington),当时红透半边天。
张申府是他们在中国的吹鼓手,金斯的《流转的星辰》还有金克木译本。
但是,老维对他们俩评价极低,认为都是骗人的主儿。
他心目中好的科普作品是法拉第(MichaelFaraday,1791-1867)的《蜡烛的故事》(TheChemicalHistoryofaCandle)。
以老维的标准衡量,金克木和张申府的趣味可能大有问题。
直到鲍斯玛去世八年后,挨骂者中年纪最小的赖尔(GilbertRyle,1900-1976)也死了十年,这些笔记才由克拉夫特(J.L.Craft)和哈斯特维特(RonaldE.Hustwit)编辑出版,题为《维特根斯坦谈话录》(Weitgenstein:
Conversations1949-1951,Indianapolis:
HackettPublishingCompany,1986)。
两位编者还合撰长篇导言,交代笔记编刊的前因后果。
全书依照维特根斯坦和鲍斯玛会面的不同时间和地点,分为《康奈尔篇》、《史密斯学院篇》和《牛津篇》,每一篇又按年月日分为若干节。
我说得热闹,但原文才78页,够薄的了。
今年,《谈话录》终于出了汉译本,译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刘云卿副教授。
不过,这个译本同李步楼与贺绍甲合译的《回忆维特根斯坦》(商务印书馆,1984年7月第一版)一样,只能说是不成功。
我这不是危言耸听,我有我的理由。
先说最简单的词义错误,比方说把“Texas”(得克萨斯)译成“坦萨斯”(序,页2),“手稿复制”(manuscriptreproductions)译成“文稿再版”(页2),“practice”(开业)译成“治疗”(页5),“unintelligibility”(晦涩难解)译成“不智”(页25),“tonic”(补药)译成“清醒剂”(页30),“pleasantries”(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