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节选》文本细读.docx
《《雷雨节选》文本细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雷雨节选》文本细读.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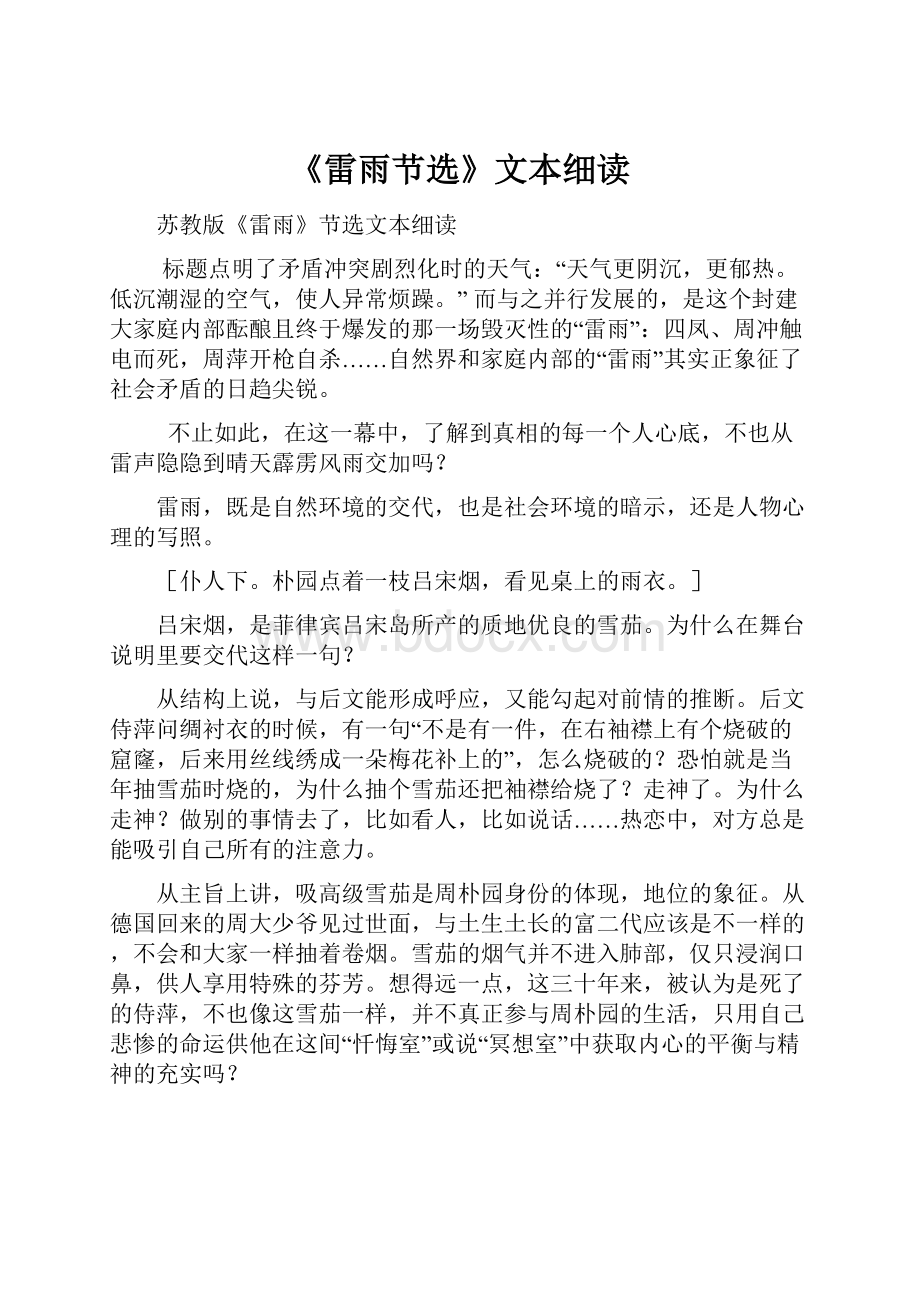
《雷雨节选》文本细读
苏教版《雷雨》节选文本细读
标题点明了矛盾冲突剧烈化时的天气:
“天气更阴沉,更郁热。
低沉潮湿的空气,使人异常烦躁。
”而与之并行发展的,是这个封建大家庭内部酝酿且终于爆发的那一场毁灭性的“雷雨”:
四凤、周冲触电而死,周萍开枪自杀……自然界和家庭内部的“雷雨”其实正象征了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
不止如此,在这一幕中,了解到真相的每一个人心底,不也从雷声隐隐到晴天霹雳风雨交加吗?
雷雨,既是自然环境的交代,也是社会环境的暗示,还是人物心理的写照。
[仆人下。
朴园点着一枝吕宋烟,看见桌上的雨衣。
]
吕宋烟,是菲律宾吕宋岛所产的质地优良的雪茄。
为什么在舞台说明里要交代这样一句?
从结构上说,与后文能形成呼应,又能勾起对前情的推断。
后文侍萍问绸衬衣的时候,有一句“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怎么烧破的?
恐怕就是当年抽雪茄时烧的,为什么抽个雪茄还把袖襟给烧了?
走神了。
为什么走神?
做别的事情去了,比如看人,比如说话……热恋中,对方总是能吸引自己所有的注意力。
从主旨上讲,吸高级雪茄是周朴园身份的体现,地位的象征。
从德国回来的周大少爷见过世面,与土生土长的富二代应该是不一样的,不会和大家一样抽着卷烟。
雪茄的烟气并不进入肺部,仅只浸润口鼻,供人享用特殊的芬芳。
想得远一点,这三十年来,被认为是死了的侍萍,不也像这雪茄一样,并不真正参与周朴园的生活,只用自己悲惨的命运供他在这间“忏悔室”或说“冥想室”中获取内心的平衡与精神的充实吗?
当然,这种解读更类似于“过度解读”,但能够从作品的细节中生发出这些联想,也不失为对自己思维能力的一种训练,这样的解读若说不上正确,恐怕也不能算是错误。
朴(向鲁妈)这是太太找出来的雨衣吗?
没有认出侍萍,也没有发现这个人之前没有在这个家庭中出现过。
从周朴园的角度来思考,很正常:
这个家里的人都是被自己管理着的人,不是妻子、孩子就是下人。
鲁(看着他)大概是的。
怎样看?
眼神没有躲闪,在想什么?
朴(拿起看看)不对,不对,这都是新的。
我要我的旧雨衣,你回头跟太太说。
家具陈设是旧的,布局习惯也是旧的,连要穿的雨衣这种小物件,也是旧的。
只能说,周朴园入戏很深。
鲁嗯。
朴(看她不走)你不知道这间房子底下人不准随便进来么?
为什么不走?
一方面三十年不见,今天突然见到,想起当年的无情无义,另一方面也想知道今天的周朴园到底对当年的鲁侍萍是什么态度。
为什么底下人不准进来?
因为这里是他留给自己一个人的世界,正如朱自清的荷塘。
他要在这里面对那个三十年来已经很立体丰满、很多情而又高贵的自己,当然不允许他人的乱入。
若这些年的习惯只是做做样子给外人看,倒是应该多让人进来看看才对。
鲁(看着他)不知道,老爷。
一直在看。
既不想被认出来,也想被认出来。
既想逃避,又想质问。
朴你是新来的下人?
鲁不是的,我找我的女儿来的。
我是原来的下人,被你们赶出了家门,没想到三十年来兜兜转转,我的女儿又做了你们家的下人,实在是造化弄人。
朴你的女儿?
鲁四凤是我的女儿。
朴那你走错屋子了。
这间房子下人都不准随便进来,何况是下人的亲戚?
你快走吧,不要打扰我了。
鲁哦。
--老爷没有事了?
你没有认出我来吗?
你把这间房子的陈设保持得这么好,若说是对我念念不忘,为什么真人当面却茫然如盲?
朴(指窗)窗户谁叫打开的?
当年侍萍生周萍后怕风,从此这扇窗户就常关着。
鲁哦。
(很自然地走到窗户,关上窗户,慢慢地走向中门。
)
仿佛回到当年,这些动作做起来轻车熟路,从而为下文周朴园觉得这动作眼熟所以发问、进而引出对过去生活的不同表述埋下伏笔。
朴(看她关好窗门,忽然觉得她很奇怪)你站一站,(鲁妈停)你--你贵姓?
破折号表示声音的延长,同时也意味着思路的变化。
本来要说的可能是“你这举止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你对这间房子怎么这么熟悉”“你是不是之前在我家里做过事”……话到嘴边,觉得太突兀太直接,换了个问题,旁敲侧击。
鲁我姓鲁。
奇怪,你明明姓梅,什么时候变成姓鲁了?
不奇怪,跟祥林嫂不管丈夫还是不是祥林都被人叫做祥林嫂不一样的是,侍萍嫁给鲁贵,就用了夫姓。
两种不同的称谓,一种不变的思维——夫为妻纲。
之前为什么姓梅而不是姓别的?
因为母亲是姓梅的。
奇怪,怎么不跟着父亲姓却要随母亲的姓呢?
不奇怪,或许侍萍的母亲在生下她之后也“失去”了她的父亲,为着跟过去一刀两断,让女儿随自己姓了——这样想来,就不是两代人的悲剧,竟然是三代人的悲剧了!
作为戏剧,在集中地表现社会矛盾、叙写人物命运方面,《雷雨》明里暗里的安排,不可谓不精彩了。
朴姓鲁。
你的口音不像北方人。
鲁对了,我不是,我是江苏的。
朴你好像有点无锡口音。
鲁我自小就在无锡长大的。
自觉不自觉地牵引着话题继续深入。
朴(沉思)无锡?
嗯,无锡(忽而)你在无锡是什么时候?
鲁光绪二十年,离现在有三十多年了。
朴哦,三十年前你在无锡?
对周朴园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个小惊喜了。
有时候我们漂泊江湖,偶尔会遇到生命的轨迹与自己有交集的人,说起那些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知道的同样的事情,往往勾起对过往的温暖回忆,仿佛是找到了一个自己生命中某一片段的见证者。
三十年前也在无锡的侍萍,对周朴园而言就是一个生命历程的见证者,而且是一个不知情的见证者,这实在是太好了!
当年侍萍投水这件事说不定她也知道,这样一来既可能有共同的回忆,对当年自己做下的那些事情又不会很清楚,实在再合适不过。
鲁是的,三十多年前呢,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没有用洋火呢。
为什么要点出这一个小细节?
二雯说,好的作品没有一句话是废笔,也没有一个道具是多余,一切都是隐喻。
深以为然。
洋火,也就是火柴。
为什么要用这个物件来串起三十年前与三十年后?
是什么细节促使侍萍有这样的感慨?
就是那支吕宋烟。
朴园用什么点烟?
洋火。
由《雷雨》其他部分的描写可知,朴园是习惯了别人伺候着给他点烟的。
三十年前,想来侍萍为朴园也点了不少次烟吧?
爱情的火花,雪茄的烟雾,氤氲一片。
三十年后,还是那个人,还是那种烟,点烟的法子却不一样了,好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三十年前真的没有用洋火吗?
侍萍之于朴园,不也像燃起、点过、烧尽就扔掉的洋火?
朴(沉思)三十多年前,是的,很远啦,我想想,我大概是二十多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无锡呢。
鲁老爷是那个地方的人?
朴嗯,(沉吟)无锡是个好地方。
上等人的语气。
无锡好在哪里?
是山美水美还是人美生活美?
实话说来无锡对于周朴园并不是个好地方,他虽然在那里找到了美好的初恋享受了幸福的爱情,却也是在那里痛失了最初的爱人别离了第二个孩子。
二十来岁的周朴园,对爱情是认真的,对侍萍是认真的,但资产阶级富二代的身份是他的硬伤——他的一切收入都依靠家庭供给,经济的无法独立必然导致爱情的不能自主,所以他没办法和侍萍私奔,只能无奈地接受家庭的安排。
当年滚滚的河水吞噬掉的,不仅是他的侍萍和他的第二个孩子,也是他对真爱的向往,对自由生活的想象。
此后的婚姻生活中,他再也没有感受到过真实的爱情;此后的社会生活中,尔虞我诈的争夺让他的心狠起来了。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周朴园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他也有情感的需要。
所以在这三十年间,他不断用自己编织的故事来消解负罪感,不断用虚假的怀念来弥补空虚感。
在这种怀念中,他觉得自己虽有罪于前,却仍能补过于后,仍不失为多情而高贵,从而卸掉了良心和道义上的重负,心理趋于平衡和充实。
从他的主观来看,这种怀念之情是真实的,否则精神空虚无法填补;但这种怀念也有做作的成分,特别是他发现此举能教育子女、稳定家庭、在社会上博取好名声后,他越做越认真,也越做越虚假,越自欺欺人。
因此,无锡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回忆里的天堂——这回忆中的故事是凄美动人的,回忆中的主角是多情高贵的,这样的无锡,当然是一个“好地方”。
鲁哦,好地方。
你怎么会认为是个好地方?
要我说,那是个地狱,是我一辈子不想再去不想再想的伤心地。
朴你三十年前在无锡么?
鲁是,老爷。
朴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
出名?
难道这件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大少爷跟家里的下人私通,还生下了两个孩子,而家里为了让大少爷和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完婚,在年三十的晚上逼着这个刚生下第二个孩子三天的丫环带着这快死了的孩子离开周家去投了河,这件事太不光彩了,周家自己不可能大肆宣扬,反而会尽力遮掩,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那为什么周朴园又要说这事很出名呢?
因为当年刻意被隐瞒的这件事,三十年来被周朴园不断包装不断渲染得面目全非,反而变得光彩照人了。
“出名”的是“贤惠”“规矩”的“梅家小姐”本来与周家大少两情相悦却忽然投水的故事,是周家老爷多年以来不忘旧爱重情重义的故事。
这个故事,已经与侍萍无关了。
所以,在这里周朴园故意只说时间不说事件,试探下侍萍是否知道当年旧事。
鲁哦。
朴你知道么?
鲁也许记得,不知道老爷说的是哪一件?
当然记得,一件件都记得,你要说哪一件呢?
朴哦,很远的,提起来大家都忘了。
大家都忘了,那么谁还老是提起来?
“我”还老是提起来的。
大家都忘了,我是一直不忘的。
你们看看,我痴不痴情,动不动人?
鲁说不定,也许记得的。
朴我问过许多那个时候到过无锡的人,我想打听打听。
可是那个时候在无锡的人,到现在不是老了就是死了,活着的多半是不知道的,或者忘了。
鲁如若老爷想打听的话,无论什么事,无锡那边我还有认识的人,虽然许久不通音信,托他们打听点事情总还可以的。
问一件事,找一个人,只要你有心用心,总能想到办法。
只叹无心人太多,无情人太多。
朴我派人到无锡打听过。
--不过也许凑巧你会知道。
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家姓梅的。
是的确有行动,不是嘴上说说。
“到无锡”,说明派人的时候已经搬到了济南。
时间过去较久了,住处也不在原地了,当年的少爷变成老爷了,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了,能够想点办法来弥补了。
鲁姓梅的?
朴梅家的一个年轻小姐,很贤慧,也很规矩,有一天夜里,忽然地投水死了,后来,后来,--你知道么?
梅家的年轻小姐当得起周家的海归少爷,贤慧的女子遇上潇洒的男子,两个人都是规规矩矩的——换言之,就是合乎礼法顺乎人情的,那段爱情故事是正当的美丽的,所以忽然地投水才是凄婉的感伤的,令人扼腕叹息的。
为什么在朴园的讲述中要省去侍萍投水的原因而代之以“忽然地”?
从朴园的角度看,侍萍的投水是一个意外,是一个他也不愿见到的悲剧,是他的家庭拆散他们的结果。
当年的他也是非常无奈的:
一个没有经济基础的富二代,在家里类似婚丧嫁娶的这种大事情上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他能做些什么呢?
他当年的处境类似现在的周萍,不,连周萍都不如——周萍还有勇气和四凤私奔,勇敢地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当年的朴园却只能在家庭驱逐侍萍时怯懦地畏缩在房间里哭泣。
也不全对,他当年还是做了点什么的,后面他说到“我看见她河边上的衣服,里面有她的绝命书”,说明他去找过,或者听别人说有人投河之后去现场看过,可惜再也看不到他的侍萍了,只有衣服和绝命书,从那一刻起,侍萍在这个世界上就死掉了,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侍萍开始以崭新的方式活在了朴园的心里。
所以,在后来一遍遍的反思和回忆中,这一段知情人“不是老了就算是死了”“活着的人多半是不知道的,或者忘了”的痛苦经历,他不愿再想起、当然要省去,在对外人叙述的版本中就变成“忽然”投水了,这样一来无辜的“我”就很不解很惶惑,就一直想不通一直放不下了。
而从侍萍的角度来看,周朴园作为凶手当然要隐瞒自己的罪行,因为正是周朴园与周家的人一起逼她投水的。
后文有说到,是“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人称有变化!
前面是“你”要娶,后面是“你们”逼着我离开。
这个细微的不同,或许是当初周朴园主观上无意逼走逼死侍萍的一个旁证。
到底当年娶那位小姐是不是周朴园的主动要求?
恐怕不是周朴园移情别恋了喜新厌旧了,但不管怎么说,周朴园当年并没有反对家庭的做法,也没有做点什么来阻止侍萍被赶出门外,那么对于侍萍而言朴园就是帮凶。
甚至再想得深一点远一点多一点,当年侍萍的母亲梅妈为什么没有在自己女儿的身边帮帮她?
后文侍萍说到“自从我被你们家赶出来以后,我没有死成,我把我的母亲可给气死了”,这里其实是有bug的。
梅妈的死不该是在侍萍被赶出周家之后:
没道理自己女儿带着一个快夭折的孩子被赶出周家,母亲还能安心在周家做事而袖手旁观;而如果梅妈跟着女儿一起离开周家,也不会眼睁睁看着她抱着孩子投水自尽。
那么梅妈之死应该是在侍萍还在周家的时候。
什么时候?
很可能是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后——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冥顽不灵一厢情愿地又走上了自己当年的老路而自己无可奈何,这个女儿还为周家的少爷生下了一个孩子断绝了以后正常婚嫁的后路,梅妈怎能不气?
两代人的悲剧反复上演,气急而死才说得通。
由于《雷雨》剧本的反复修改,文中其实还有很多不能自洽的地方,我们不深究了。
话说回来,既然三十年前梅妈已死,那么侍萍在周家就只有朴园这样一个依靠,她把一切都给了朴园,而朴园在那样关键的时刻什么也给不了她——我是为了你才落到这个地步的,你的不作为就是你的罪!
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才是主犯!
一个“忽然”,说者有意,听者有心。
鲁不敢说。
你倒是真敢说……
朴哦。
鲁我倒认识一个年轻的姑娘姓梅的。
不过跟你说的那个小姐可不一样。
你愿意听的话,我就说下去。
朴哦?
你说说看。
鲁可是她不是小姐,她也不贤慧,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
听到周朴园的谎言,想起自己这些年的遭遇,满怀悲愤,所以语带讽刺,表达了内心的痛苦和对周的不满。
朴也许,也许你弄错了,不过你不妨说说看。
有点尴尬,这个人恐怕真的知道点什么,也清楚自己在说谎,不过倒是提供了一个了解后事的渠道,不妨听听。
鲁这个梅姑娘倒是有一天晚上跳的河,可是不是一个,她手里抱着一个刚生下三天的男孩。
听人说她生前是不规矩的。
朴(苦痛)哦!
本不愿揭开与面对的伤疤被撕裂,忽然一下要直面多年来有意忘却的痛苦。
鲁这是个下等人,不很守本分的。
听说她跟那时周公馆的少爷有点不清白,生了两个儿子。
生了第二个,才过三天,忽然周少爷不要了她,大孩子就放在周公馆,刚生的孩子抱在怀里,在年三十夜里投河死的。
是个下等人而不是小姐,所以跟周大少门不当户不对;不守本分不规矩,所以才被规矩给抹杀掉了。
你跟别人不清白,人家要跟你算得一清二白。
针对前面周朴园说“忽然地投水”,侍萍此刻一语道破没有说出的真相——那当然是因为周少爷“忽然”不要了她。
朴(汗涔涔地)哦。
皇帝的新装被观众给叫破,痴情人的遮羞布被一把扯了下来。
热啊,天气闷热,内心燥热,怎能不大汗淋漓。
鲁她不是小姐,她是无锡周公馆梅妈的女儿,她叫侍萍。
周朴园煞费苦心一层层包装起来的故事又被一点点撕开,我觉得此处如果有BGM响起,应该是杨宗纬的《洋葱》:
偷偷地看着你 偷偷地隐藏着自己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
你会发现 你会讶异
你是我最压抑 最深处的秘密
朴(抬起头来)你姓什么?
意外、吃惊于居然点出了人物的姓名和身份,于是直截了当地问。
言外之意,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你到底是谁?
鲁我姓鲁,老爷。
我不是你想的那个人,我只是鲁贵的老婆,这儿四凤的妈,我只是一个下人而已。
朴(喘出一口气,沉思地)侍萍,侍萍,对了。
这个女孩子的尸首,说是有一个穷人见着埋了。
你可以打听得她的坟在哪儿么?
按照上文问答的惯性,这里应该轮到周朴园判断鲁妈所说的人是否就是自己故事里的那位梅家的小姐了。
很明显,面前这个人对当年的事情一清二楚,那么自己这么多年一厢情愿自说自话的角色扮演在她面前就像一个笑话,无比尴尬的周朴园只好转移了话题——你知道坟在哪儿吗?
要注意到,“梅家的小姐”变成了“这个女孩子”,周朴园在知情者面前默认了二者所说的是同一个人。
“说是有一个穷人见着埋了”一句,呼应上文派人去打听的举动,也正是由于当年打听之后知道侍萍是真的死了,所以周朴园此后可以按照自己心愿美化侍萍、美化当年的一切。
或许,我们不能用“谎言”来把周朴园的故事一概否定。
因为说不定在他的心中,如果当年侍萍真的是一个“某家”的小姐,他们之间的爱情就会开出美丽的花、结出甜蜜的果。
造化弄人,在年轻的时候、可以纵情去爱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无法自主;成熟了以后能自立了以后他们又已经永失所爱。
此后这两个人对这段感情的处理也非常值得品味。
一直命很苦一直不如意的侍萍为生计所迫漂泊江湖辗转求生,在繁忙的生活和工作中没时间也不愿意再想起这段伤心过往,所以她选择了遗忘。
一直很受伤一直放不下的朴园生意亨通财源广进之余精神生活却极端空虚,他这样一个中年男人,在婚后的无爱生活中有的是时间,也有的是心情一遍遍回忆当年的初恋,一次次舔舐自己的伤口,一层层涂抹朦胧的色彩,他选择了铭记。
说到底,周朴园也是个受害者。
他好像一只珍珠蚌啊!
鲁老爷问这些闲事干什么?
所谓“闲事”,就是无关紧要的事,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
你之前既然装成一个旁观者无辜者,你现在问这么多有什么用?
朴这个人跟我们有点亲戚。
鲁亲戚?
内亲外戚,请问这个投河的女孩子跟你是什么亲戚呢?
她当初和你在一起无名无分,被你赶走后无依无靠,有这样的亲戚吗?
朴嗯,--我们想把她的坟墓修一修。
给死人修坟,并不能让逝者睡得更舒服一点,修坟是修给活人看的。
扫墓也好修坟也罢,都只不过用这种方式给生者以慰藉,予缺憾以弥补而已。
周朴园想给鲁侍萍修坟,和后文写支票一样,都是为了用这种手段来赎罪,使自己得到内心的安宁。
鲁哦--那用不着了。
朴怎么?
鲁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朴(惊愕)什么?
几十年的思维定势一朝打破,茫然失措,惶然失态。
鲁她没有死。
朴她还在?
不会吧?
我看见她河边上的衣服,里面有她的绝命书。
那你到底是希望她还活着呢还是希望她死了呢?
如果你是希望她还活着,这时候难道不该说“那太好了,她在哪儿?
”
鲁不过她被一个慈善的人救活了。
她差点被一个无良的人害死了。
朴哦,救活啦?
鲁以后无锡的人是没见着她,以为她那夜晚死了。
朴那么,她呢?
鲁一个人在外乡活着。
这里的“一个人”,窃以为对应前文的周家的“你们”那一群人,一家人。
朴那个小孩呢?
鲁也活着。
知道侍萍还活着,接下来没有问在什么地方做什么,过得怎么样,而是马上追问孩子的下落。
朴(忽然立起)你是谁?
更加惊疑不定,甚至有种大难临头债主上门的感觉。
鲁我是这儿四凤的妈,老爷。
朴哦。
鲁她现在老了,嫁给一个下等人,又生了个女孩,境况很不好。
不是你想象中那个小姐,也不再是当年那个青春单纯的侍萍了。
朴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不是“我的爱人在哪里”的热切追问,而是“那个杀手来了吗”式的惊惶询问。
鲁我前几天还见着她!
朴什么?
她就在这儿?
此地?
是喜是悲?
是惊是惧?
从“你是唯一的神话”变成了“你是电,你是风”,你是颠覆一切的恐怖。
鲁嗯,就在此地。
朴哦!
强作镇定。
鲁老爷,你想见一见她么?
朴不,不,谢谢你。
想要就此打住,已经不再沉浸于自己臆想的痴情传说。
鲁她的命很苦。
离开了周家,周家少爷就娶了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
她一个单身人,无亲无故,带着一个孩子在外乡什么事都做,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在学校里伺候人。
你怕麻烦不想见,你怕戳穿不敢见,我却偏要说!
欲说还休,欲休还说。
三十年的苦水,被高度概括。
朴她为什么不再找到周家?
既有“她既然这么苦,为什么不来周家寻求帮助”的疑惑,也有“她被周家害成这个样子,走投无路了为什么没有找周家算账”的试探,然而侍萍只听出了前一层意思。
鲁大概她是不愿意吧?
为着她自己的孩子,她嫁过两次。
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出卖尊严。
朴嗯,以后她又嫁过两次。
她怎么可以再嫁两次呢?
当初初恋时那个笑靥如花痴情如诗温婉如梦的女子,怎么可以投入别人的怀抱呢?
枉我这些年来一刻也不忘她,一直留着这间房子,我对她如此专情,她却变得如此无情……但侍萍依然没有听出朴园的言外之意,以为他同情着她的不幸遭遇。
鲁嗯,都是很下等的人。
她遇人都很不如意,老爷想帮一帮她么?
你现在知道侍萍的下落了,也知道了她这些年的不如意,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呢?
当年无情负心的你,现在可有愧疚悔过之意?
朴好,你先下去。
让我想一想。
此时的周朴园已经乱了方寸,需要一个独处的空间来调整心态,面对突如其来的真相。
鲁老爷,没有事了?
(望着朴园,眼泪要涌出)老爷,您那雨衣,我怎么说?
你问了这么多,我说了这么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在看到房间的陈设、听到朴园的讲述之后,侍萍对朴园或许还抱有一点点幻想——这个人当初虽然没有行动,但内心还是痛苦不安的,以至于这么多年不曾忘怀过往的时光,所以这时候眼泪还没有流出来;当幻想再次被打碎,内心的痛楚终于无法遏制了。
朴你去告诉四凤,叫她把我樟木箱子里那件旧雨衣拿出来,顺便把那箱子里的几件旧衬衣也捡出来。
鲁旧衬衣?
朴你告诉她在我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没有领子的。
鲁老爷那种纺绸衬衣不是一共有五件?
您要哪一件?
朴要哪一件?
还没回过神,茫然。
鲁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
还有一件,--
朴(惊愕)梅花?
从这个绣梅花补窟窿的细节,可见当年感情生活的真实和谐。
看到袖襟上的梅花,就当然会想起绣花的梅侍萍。
这个女孩不仅当年给了周少爷甜蜜的初恋,也在后来的三十年间用另一种方式填补着周少爷感情的窟窿。
为什么姓梅?
梅花高洁,梅花顶风冒雪,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梅——没,春天到了,梅也就没了。
年三十的晚上,新春前夕,她随水而逝了。
鲁还有一件绸衬衣,左袖襟也绣着一朵梅花,旁边还绣着一个萍字。
还有一件,--
朴(徐徐立起)哦,你,你,你是--
几可肯定,手足无措。
鲁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朴哦,侍萍!
(低声)怎么,是你?
不敢相信,无法接受。
鲁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
朴你--侍萍?
(不觉地望望柜上的相片,又望鲁妈。
)
心中高贵优雅、贤慧温顺的情人形象在这个老妈子的面前瞬间消解,平生唯一的寄托轰然崩塌。
鲁朴园,你找侍萍么?
侍萍在这儿。
你不是要找我么?
你不是要给我修坟么?
我现在就在你面前,你想说什么?
你想做什么呢?
朴(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
恼羞成怒的朴园从梦想回到现实,利益的考量浮上心头。
你是想来认儿子,还是想来敲一笔?
前面说过,侍萍死了,所以她活着;而现在侍萍还活着,所以她就真的死了。
鲁不是我要来的。
是你们周家的太太让我来的,我要是知道这是你的家,我才不会来!
这句话意义的重点在“我不是为了当年的事情而来,不是为了见你而来”。
朴谁指使你来的?
周朴园理解的重点却变成了“来这里不是我的主意,鼓动者另有其人”。
就像《桥边的老人》里那位士兵和老人的交流一样,周朴园和鲁侍萍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去理解对方的语言,从而使双方话语的指向产生了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