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架构.docx
《从论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架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论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架构.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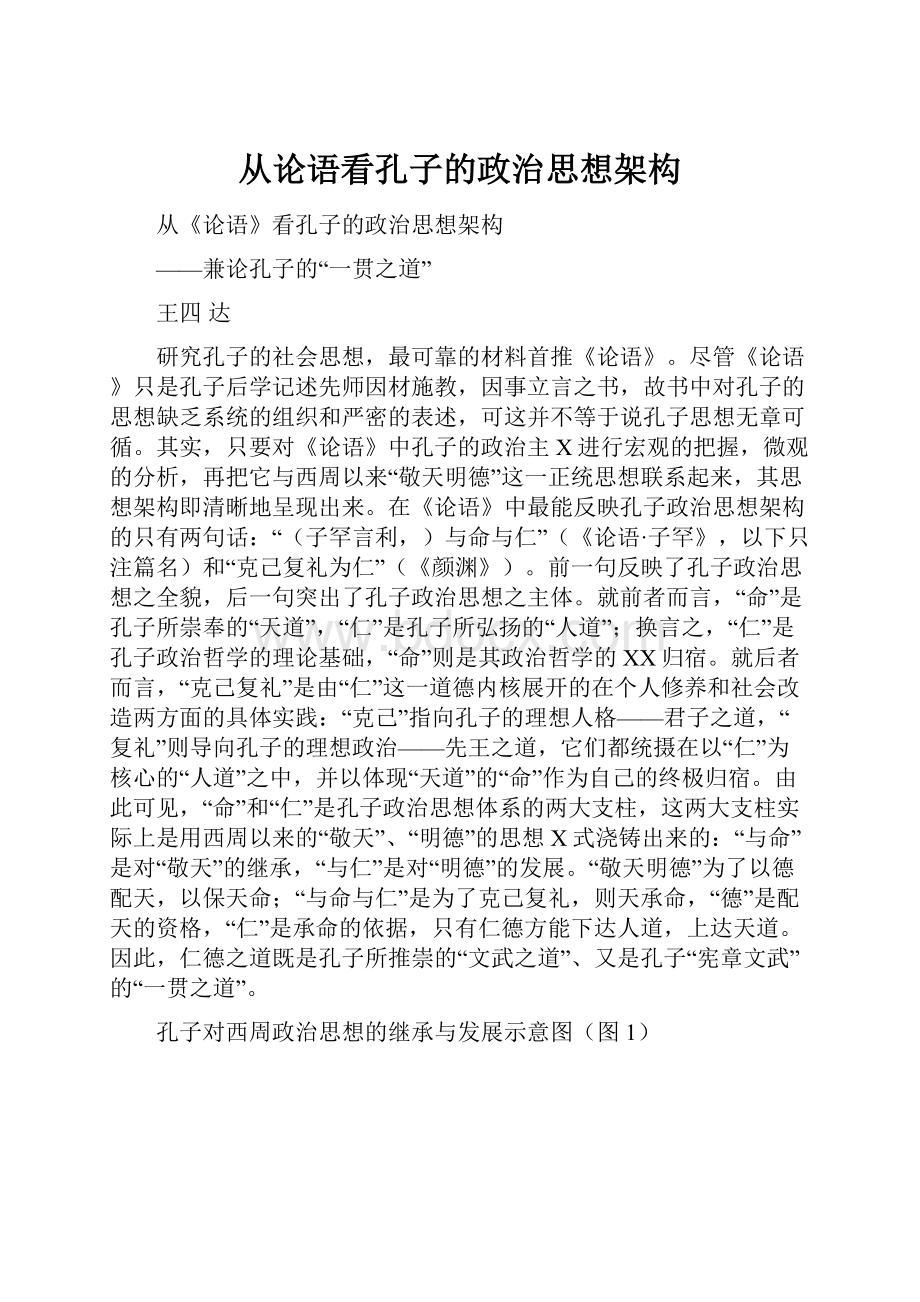
从论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架构
从《论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架构
——兼论孔子的“一贯之道”
王四达
研究孔子的社会思想,最可靠的材料首推《论语》。
尽管《论语》只是孔子后学记述先师因材施教,因事立言之书,故书中对孔子的思想缺乏系统的组织和严密的表述,可这并不等于说孔子思想无章可循。
其实,只要对《论语》中孔子的政治主X进行宏观的把握,微观的分析,再把它与西周以来“敬天明德”这一正统思想联系起来,其思想架构即清晰地呈现出来。
在《论语》中最能反映孔子政治思想架构的只有两句话: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和“克己复礼为仁”(《颜渊》)。
前一句反映了孔子政治思想之全貌,后一句突出了孔子政治思想之主体。
就前者而言,“命”是孔子所崇奉的“天道”,“仁”是孔子所弘扬的“人道”;换言之,“仁”是孔子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命”则是其政治哲学的XX归宿。
就后者而言,“克己复礼”是由“仁”这一道德内核展开的在个人修养和社会改造两方面的具体实践:
“克己”指向孔子的理想人格——君子之道,“复礼”则导向孔子的理想政治——先王之道,它们都统摄在以“仁”为核心的“人道”之中,并以体现“天道”的“命”作为自己的终极归宿。
由此可见,“命”和“仁”是孔子政治思想体系的两大支柱,这两大支柱实际上是用西周以来的“敬天”、“明德”的思想X式浇铸出来的:
“与命”是对“敬天”的继承,“与仁”是对“明德”的发展。
“敬天明德”为了以德配天,以保天命;“与命与仁”是为了克己复礼,则天承命,“德”是配天的资格,“仁”是承命的依据,只有仁德方能下达人道,上达天道。
因此,仁德之道既是孔子所推崇的“文武之道”、又是孔子“宪章文武”的“一贯之道”。
孔子对西周政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示意图(图1)
则天承命
配天敬天与命天道上达
知天达命
克己君子之道
以德明德与仁人道下学
复礼先王之道
西周思想孔子思想
图1
一、“克己复礼”的政治观和伦理观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架构,是“仁”为中心而展开的。
“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对“仁”的诸多诠释中既全面又扼要的表述:
“克己”集中体现了孔子的伦理观;“复礼”高度概括了孔子的社会观。
孔子政治思想的主体架构基本上就是由这两大板块构成的。
“克己”从消极的方面说,是克制约束自己(非礼的思想言行),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从积极的方面说,则是培养自己符合礼的道德,并把这种道德用来对待他人(“仁”字从人丛二,原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思想准则)。
因此,当子路问君子时,孔子答道: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宪问》)。
孔子心目当中的君子之道就是由“修己”与“安人”这两方面构成的。
在《论语》中,孔子对“修己”的论述是极丰富的,既作出了总体性的设计,又提出了具体的行为准则和修养目标,其总体性设计概括起来有七项内容,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它包括道德修养与才学培养两个方面。
“道”是君子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和终极目标,而“志于道”则是君子“修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夫子曰: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这个“道”对自身修养而言,它表现为君子之道;对政治理想来说,它又是先王之道。
实现君子之道是恢复先王之道的先决条件,而恢复先王之道又是追求君子之道的终极目的。
君子的志向就是追求这种一分为二又合而为一的“道”。
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士志于道”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
君子既立志于道,则必须“据于德”,因为“道”与“德”不可须臾离也,故夫子曰:
“君子怀德”(《里仁》)。
对于君子之德,孔子一方面赞扬“主忠信,徙义”,“先事而后得”的“崇德”行为(《颜渊》),强调“中庸”这种“至德”;另一方面又反对“道听而途说”,及“巧言”,“乡原”这些“乱德”,“贼德”行为。
他对这些不道德,不徙义,不从善的现象深为忧虑,曰: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
然而,“德”又是以“仁”为依旧的。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通常是“德”的抽象实体,“德”大多是“仁”的具体体现。
例如,忠、信、义、直这些具体的德行就是“依于仁”表现;而“巧言令色”,“乡原”这些“乱德”,“贼德”行为,则是“鲜于仁”“违于仁”的结果。
故夫子曰:
“苟至于仁,无恶也”(《里仁》),“观过,斯知仁矣”(《里仁》)。
正因为摒恶,改过,修德都必须“志于仁”,“依于仁”,故夫子又说: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席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仁”与“德”作为君子“修己”的内在依据,还必须与“礼”联系起来。
“礼”是“仁”、“德”、“道”的集中体现和表现形式,先王之道就是“周礼”(当然亦可包括夏礼与殷礼)。
一方面,礼的实行要以仁为先决条件,故夫子曰:
“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
另一方面,恭、慎、直这些仁德又必须“约之以礼”,因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礼成了君子安身立命的基础,故曰“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礼”又必须与“乐”相配合:
一方面,“礼”和“乐”均是先王之道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即所谓“礼乐”是也;另一方面,“礼乐”对王道社会中等级名分的维护和君子思想感情的培养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孔子曾反问: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意思是说,礼乐难道只是玉帛,钟鼓这些外在形式吗?
言下之意是,比形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它们的精神实质,这个精神实质当然又“仁”,故夫子曰:
“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对于“乐”,夫子最推崇的是《韶》《武》,他对《韶》入迷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
由于《韶》乐是“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故君子“立于礼”而“成于乐”。
在致力于仁、徳礼、乐的基础上,孔子又提出“兴于诗”的主X。
在孔子看来,由于《诗》“思无邪”,故可用来陶冶人的性情,抒发人的思想感情和增长知识。
他对弟子们的说: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他对“二南”推崇备至,曰: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而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
因此,“不学《诗》,无以言”(《季氏》)。
“游于艺”是孔子对君子“修己”在才学方面的一项总体要求,“艺”即六艺,据朱子对“游于艺”作注,“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但孔子还主X弟子应先做到“孝弟”,“爱众”,“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对此,朱子又谓“文”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
按孔子之言“艺”,可能二者皆有:
在“志道”,“依仁”、“据德”的基础上,“艺”指礼乐等六艺;在“孝弟”,“爱众”,“亲仁”的基础上,“文”(艺)又指《诗》《书》等六艺,但不管哪一种六艺,对追求君子之道和实现先王之道来说的来说目的一样,殊途同归,故孔子曰:
“六艺于治一也”(《史记·滑稽列传》)。
然而,除了这个总体性的设计外,孔子对君子“修己”还提出来一些明确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概括起来主要有“道三”、“绝四”、“行五”、“思九”和“三畏”、“四教”、“三戒”、“三友”等等。
所谓“道三”,即孔子提出的“君子有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
在论及子产时,孔子又说:
“有君子之道四焉: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
所谓“绝四”,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这虽是夫子在自身修养方面做出的表率,亦可视为君子“修己”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所谓“行五”,为“恭、宽、信、敏、惠”,夫子曰: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阳货》)。
至于“思九”者,乃孔子所说的“君子有九思: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
此外,孔子又提出: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有“三戒”:
戒色,戒斗,戒得(《季氏》);“益者三友”:
友直、有谅、友多闻(《季氏》);“益者三乐”:
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季氏》),以及“周而不比”(《为政》);“和而不同”(《子路》);“泰而不骄”(《子路》),“矜而不争”(《卫灵公》)、“见贤思齐”(《里仁》)、“见利思义”(《宪问》)、“讷言敏行”(《里仁》)等等,这些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孔子关于君子“修己”的理论。
“修己”的另一方面是“安人”,也就是使他人安乐。
其总的精神是“爱人”,因“爱人”故能“安人”、而使他人安乐,按不同的关系(对象)可以分为“孝弟”、“忠”、“恕”、“爱众”四个方面:
“孝弟”是待亲的行为准则,即对父母孝,对兄长弟。
夫子曰: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而》),其弟子有若更进一步地把孝弟说成是“仁之本”(《学而》)。
“忠”是把“孝弟”的原则推广于事君。
夫子曰:
“孝慈、则忠”(《为政》),“臣事君以忠”(《八佾》),“忠”表现为“事君,能致其身”(《学而》),“毋欺也,而犯之”(《宪问》)等等。
“恕”是待人待友的准则,其基本精神是“能近取譬”:
一方面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另一方面还应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对于亲、君、友之外的众人,孔子提出“泛爱众”的主X。
“众”非专指“小人”,因为孔子说“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可见“众”里含有“仁者”;但孔子又说: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可见“众”既可包括君子,亦可以包括小人。
此外,孔子还把“修己以安人”进一步阐释为“修己以安百姓”,朱子注曰:
“百姓则尽乎人矣”(《论语集注》)。
笔者以为这与孔子的“泛爱众”主X是相吻合的。
上述这四方面就构成了孔子的“安人”之道。
然而,孔子“修己以安人”的君子之道并不仅仅是一种伦理道德学说,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伦理观是从属于政治观的,“克己”只是“复礼”的道德前提,“复礼”则是“克己”的政治归宿。
如前所述,“复礼”是“仁”的另一方面内容,是仁的精神在社会政治领域的贯彻。
孔子对“复礼”的论述,综合起来大致包括“弘道”、“复古”、“礼治”三个方面。
“弘道”就是弘扬先王之道,由于先王之道即“礼”,故“复礼”必先致力于“弘道”;“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朱熹论语集注》),故夫子曰: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弘道”大体上包括四个环节:
“学道”、“谋道”、“行道”、“达道”。
夫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卫灵公》),故君子“弘道”必先“学道”。
夫子本人对先王之道非常神往,曾感慨道:
“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又自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学”即学道。
弟子子夏亦云:
“君子学以致其道”(《子X》)。
由于学道的目的是为了“致其道”,故君子应抱有“谋道”之志,“忧道”之心。
夫子曰: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
一旦形势许可,君子应替天行道。
他多次强调: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如果“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公冶长》)。
夫子的崇拜者也把他看作是替天行道的圣人,仪封人说:
“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
而夫子有时也以替天行道者自居,晚年他曾自叹: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
尽管如此,他仍然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努力弘扬先王之道。
他极力宣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守死善道”,“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卫灵公》),在形势不利时,“隐居以求其志”;在时机成熟时,“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王道达致之日,即周礼恢复之时。
“弘道”具体落实到对当时的社会社会改造上去,则必须“复古”。
因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对尧舜文武等先王之道,只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即只能相信并传述先王之道,不要加以主观发挥。
对于春秋这个社会变革时代出现的新事物,孔子十分反感,他曾针对当时把酒器觚的形体由原来的四棱改为圆筒一事质问道:
“觚不觚,觚哉?
觚哉”(《雍也》)!
在他看来,觚就应该恢复古时的形状才能算作觚:
“天下无道”的春秋社会也应该恢复到“直道而行”的三代社会才算实现礼,所以要“好古”、“述古”。
“述古”大致可分为“从周”、“变鲁”、“为邦”、“归心”四部分。
他最崇拜西周的典章制度,曰:
“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又曰: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
在孔子看来,齐鲁是保存周礼最好的诸侯国,因此他主X通过“变齐”、“变鲁”来实现王道,他说: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由于孔子主X“述古”,“从周”,故颜渊问“为邦”时,孔子答道: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卫灵公》)。
对于如何恢复被破坏的旧秩序,孔子公开主X: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如此,则“天下之民归心焉”(《尧曰》)。
当然,孔子并非为“好古”而“述古”,他之所以“述古”,是希望通过“复古”来匡正当时“礼崩乐坏”的春秋社会,故“复古”的实质是“复礼”,他说:
“为国以礼”(《先进》),意即以礼治国。
“礼治”也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正名”。
正名是礼治的前提。
子路问孔: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
“必也正名乎”!
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子路》)。
针对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乱状况,孔子对“正名”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明确要求,务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守名分。
二是“尊王”。
孔子认为,春秋以来出现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等僭越现象,是“天下无道”的表现,也是对周王的不尊;因此,只有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的旧秩序,才是“尊王”和“天下有道”的表现。
在评价管仲时,孔子本来对管仲的一些违礼行为是指责的,但他仍称赞管仲相桓公,“尊王攘夷”,“一匡天下”的功劳,故而给他“如其仁”的评价。
显然,“尊王”正是孔子肯定管仲的根本原因。
三是“齐礼”。
夫子曰: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
故治国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
在孔子看来,“齐礼”是治国最重要最可取的手段,“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
四是“德政”。
夫子曰: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
对于如何实行“德政”,夫子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他说: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子贡问政,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
对内,应“先之劳之,富之教之”(《子路》);对外,“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季氏》)。
孔子上述这些德政主X就奠定了后来儒家仁政学说的基础。
总之,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是以“仁”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然后分别向“克己”与“复礼”两个方向进发,最后分别导向“君子之道”和“先王之道”。
而“克己”、“复礼”这两个目标一旦实现,最终又回到“仁”这个思想的境界中去,故夫子曰: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前面作为出发点的“仁”只是抽象的政治理念;后面到达目的地的“仁”,已转化为具体的社会成果。
复克
达成
道
礼行立于己
道
归学据于
道于
变从德礼乐
仁
心鲁周孝
先正弟忠爱君
名
齐
王礼恕子
德
之政众之
道道
“克己复礼”的政治伦理构架示意图(图2)
二、则天知命的天命观
《论语·子罕》称: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朱子断句作:
“子罕言:
利,与命,与仁”。
并引程子之语:
“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论语章句集注》)。
在这里,程朱把“与”字做连词解,有些现代学者亦沿袭此说。
但这种解释并不符合《论语》的实际情况,因为在《论语》中夫子罕言的是“利”,“命”与“仁”并不罕言,而且言得最多的是就是“仁”;此外,这一解释也不符合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因为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恰恰就是“命”、“仁”并举,“仁”“命”互参。
其实,“与”之古义,有作“许”、“从”之解,即赞许,信从之意。
从孔子的众多言论来看,这一解释更符合他的实际主X。
只要我们对孔子的政治思想体系进行结构性分析即可发现,“命”与“仁”正是这个思想体系的主体架构:
“仁学”奠定了孔子政治哲学的伦理基础,“命学”构筑了孔子政治哲学的XX殿堂;“仁”是人道的核心,“命”是天道的体现,孔子的“与命与仁”就是对西周“敬天明德”的天人之学的继承与发展。
有的学者认为,孔子是无神论者,不信鬼神,亦不信有人格有意志的“天”,并引用《阳货》中“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句话来证明孔子所说的天是自然之天,对此我们不敢苟同。
孔子对鬼神持存疑态度虽凿凿有据,但他继承西周以来的天命学说,并把天道与人道联系起来构筑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更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在孔子说”天何言哉“之前,他已先说:
“予欲无言”,子贡曰:
“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于是孔子反问道:
”天何言哉……”其意是说,我虽不言但你们应知道我的意思;就像天虽不言,但四时行,百物生都是天的意志的表现,又何必言呢?
所以孟子说:
“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孟子·万章上》)。
孟子这句话正式对孔子“天何言哉”的权威注脚。
天既然是有人格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其意志所在就是“命”。
“命”既可以表现为上天对社稷命运的支配,亦可以表现为对个人命运的主宰。
在天命观方面,孔子一方面继承了西周以来关于天子奉天命的思想,作为先王之道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发展了君子知天命的思想,作为君子之道的一项重要内容。
前者包含三个层次:
则天、成命、顺命;后者亦包括三个层次:
畏天、知命、达命。
层次之间既有纵向的发展,两部之间又有横向的联系。
对君子修身来说,“天”既然是决定“四时行”,“百物生”的最高主宰,君子对“天”和“天命”就不能不敬畏。
在孔子所说的“君子有三畏”中,“畏天命”乃“三畏”之首。
而“畏天命”又是与“知天命”联系的,因为“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所以孔子说: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可见知天命是作为君子的一个必要条件。
孔子也曾自称他“五十而知天命”(《为政》)。
然而,仅仅“畏天”、“知命”还不够,还应做到“达命”,即对“天命”的安排达观,超然。
孔子晚年对天命不兴周已有所认知,但他仍然称自己“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对圣王治国来说,天既然是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故圣王必须敬天,则天。
圣王“则天”就是君子“畏天”在治国方面的反映。
孔子称赞尧曰: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为尧则之”(《尧曰》)!
因为圣王之有天下乃天命所归,王位的继承亦天命所授。
所以尧在把王位传给舜时说:
“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尧曰》)!
由此可见,舜继王位就是“承天命”。
而圣王“承命”亦可视为君子“知命”的必然结果,因为既知天明则不能不承天命,圣王治国如此,君子行道亦应如此。
孔子在努力复兴周道时也以奉天承命自居,在匡受困时他说: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在一生复礼无望的情况下,他曾叹到:
“吾道穷矣”!
并把这归之于天命,曰:
“道之行将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既然天命不可违,因此只能“顺天命”。
“顺命”亦是君子“达命”的必然延伸。
上述孔子天命观的各个部分,就是这样横向现纵向地联系在一起的。
三、贵和执中的中庸之道(方法论)
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中,无论是追求“内圣”的君子之道,还是导向“外王”的先王之道,都很强调“中”的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
“中”即“中庸”,程子曰: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转引自《论语章句集注》)。
其基本原则是无过无不及,准确地把握理想的节度,故又称为“中和”。
“中”的思想由来已久,《尚书·大禹谟》中有“允执厥中”之语;《盘庚中》说:
“各设中于乃心”;《酒诰》说:
“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金文《叔夷钟》:
“眘(慎)中厥罚”。
这些“中”的含义基本相同,都是强调思想行为要符合节度之意,可见在孔子之前,“中”已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贯穿在君子修身和圣王治国的理论中:
“设中于乃心”和“作稽中德”是对君子修身的要求,“允执厥中”和“慎中厥罚”,则是对圣王治国原则的规X。
孔子的“中庸之道”就是从这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先人的“中道”思想的。
由于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社会变革时代,旧制度日趋崩溃,旧道德日益沦丧,背中道走极端的现象非常严重,有感于此,孔子认为有必要把“民鲜久矣”的中庸之道作为一种最高道德来加以提倡,并把它贯彻到“克己复礼”之中。
对君子修己说,要避免过与不及两种极端。
孔子在评论弟子颛孙师和卜商时说,“师也过,商也不及”,“过犹不及”(《先进》),故君子要注意掌握中和的原则,他说:
“质胜则文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在待人处世方面,君子应“和而不同”,“无适无莫”(《里仁》);与人交往要“中行而与之”(《子路》)。
对君王治国来说,同样要避免过与不及两种极端,《中庸》引述孔子的话说:
“舜其大知也……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孔子是否说过这句话虽难以确证,但它符合其思想方法则无可怀疑,因为,执两用中正是孔子善用的方法,孔子自道:
“吾有知乎哉?
无知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
《论语》中亦借尧之口告诫舜治国要“允执其中”,否则“四海穷困,天禄永终”(《尧曰》)。
对于用礼来说,同样要处理好“礼”与“和”的关系;一方面要把“中和”的原则贯彻到礼中去,因为“礼之用,和为贵”(《学而》);另一方面又要用礼节和,因为“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行也”(《学而》)。
可见“执中贵和”也是治国的根本原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庸之道亦是孔子政治哲学的组成部分。
上下
敬克学
达
己
天
受复
配
天礼
以
天命
德
“与命与仁”的政治思想构架示意图(图3)
四、孔子思想体系的一贯之道
夫子曰:
“吾道一以贯之”(《里仁》)。
究竟什么是夫子的“一贯之道”,他本人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
曾子则说: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后人大多以此作为孔子的“一贯之道”的权威解释。
但是,曾子的解释未必符合其师的原意,更不符合夫子政治思想体系的实际情况,因为,宏观地审视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夫子之道”绝非“忠恕而已”。
其实,“忠恕”只是孔子所宣扬的社会伦理关系中“事君”与“待人”的二种准则而已,它们本身是建立在“孝弟”与“爱人”的基础上的:
“孝弟”是“仁之本”,“忠”则是“孝弟”的必然延伸。
有子说: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已;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
孝弟者必不犯上作乱,这就发展为“忠”,故夫子曰:
“孝慈,则忠”。
同样,“爱人”是仁的基本精神,“仁者爱人”,其具体方法是“能近取譬”,把这种“仁之方”推广开来,就是“不欲”、“勿施”和“立人”、“达人”的“恕道”。
既然“孝弟”与“爱人”是“仁之本”,“仁之方”,故只能说“恕忠”是“孝弟”与“爱人”的逻辑发展,而不能本末倒置的说“孝弟”与“爱人”都是“忠恕”的体现。
“忠恕”不但不能统摄“孝弟”与“爱人”,同样亦无法统摄“修己”的全部内容,孔子对君子“修己”提出的“志于道……成于乐”等七项总体性设计,以及前述的“道三”、“绝四”、“行五”、“思九”、“三畏”、“三戒”等具体修养目标,绝不能“忠恕”二字所能概括的。
至于孔子的“复礼”思想及对先王之道的论述,亦比“忠恕”的内涵丰富得多。
此外,孔子的“天命观”和“和中庸之道”,更非“忠恕”二字所能包含,因此我们认为,“忠恕”只是孔子所赞许的两种社会伦理规X,在孔子的整个政治思想体系中并不能占据统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