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研究报告.docx
《当代散文研究报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当代散文研究报告.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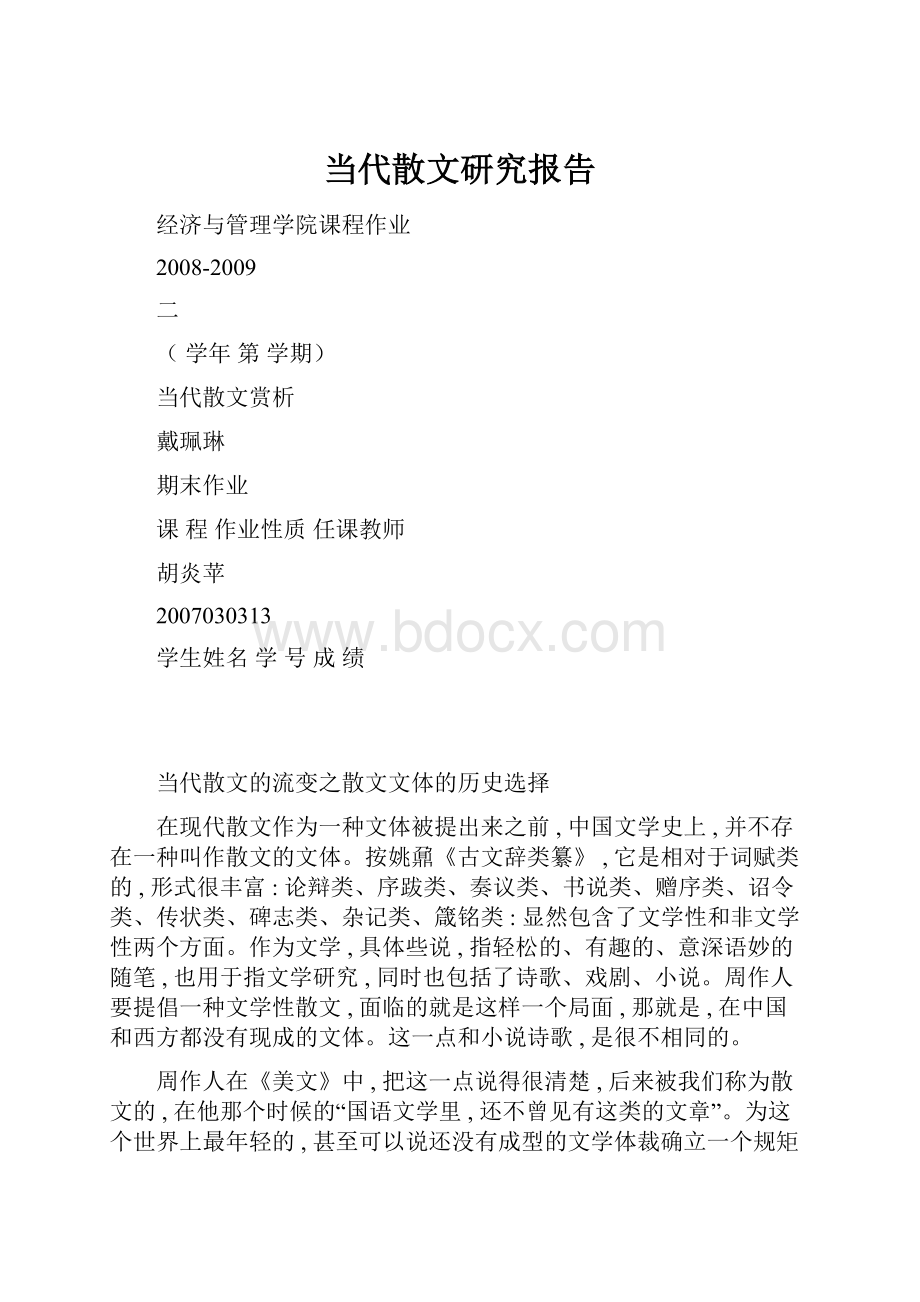
当代散文研究报告
经济与管理学院课程作业
2008-2009
二
(学年第学期)
当代散文赏析
戴珮琳
期末作业
课程作业性质任课教师
胡炎苹
2007030313
学生姓名学号成绩
当代散文的流变之散文文体的历史选择
在现代散文作为一种文体被提出来之前,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种叫作散文的文体。
按姚鼐《古文辞类纂》,它是相对于词赋类的,形式很丰富:
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
显然包含了文学性和非文学性两个方面。
作为文学,具体些说,指轻松的、有趣的、意深语妙的随笔,也用于指文学研究,同时也包括了诗歌、戏剧、小说。
周作人要提倡一种文学性散文,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那就是,在中国和西方都没有现成的文体。
这一点和小说诗歌,是很不相同的。
周作人在《美文》中,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后来被我们称为散文的,在他那个时候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的文章”。
为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甚至可以说还没有成型的文学体裁确立一个规矩(或者规范),气魄是很大的,也是很冒险的,留下偏颇甚至混乱,也许不可避免。
他给这类文章,规定了“叙事与抒情”的特征,相当于今天审美性的散文。
正因为当时新文学中,还没有这种文体,所以他主张应该去“试试”。
这个“试试”,可能是从胡适的《尝试集》得到的启示。
孰不知新诗的尝试,不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是有稳定的诗体可藉的,而散文却是中西都没有。
“叙事与抒情”的规定,说明周氏倾向于美文,但是,他又把它归入“论文”一类,说“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
这说明,他有点动摇,觉得应该把主智的论文囊括进来。
可是他的题目又是“美文”。
显然,在理论上一直摇摆在主智的论文和主情的美文之间。
只是在具体行文中,他又明显倾向于主情的美文。
虽然他的主张号称来自西方,但是,西方的文论并不足以支持他作出主情的决策。
推动他作出如此坚定的论断的,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他的艺术趣味,具体表现在他对晚明公安派性灵小品的执著。
“叙事与抒情”和“真实简明”都不是西方论文和美文的特点,而是他所热爱的公安派的风格。
一九二八年,他在《燕知草·跋》中明确宣言晚明的“公安派”是“现在中国新散文的源流”。
其实,在他心目中,那就是现代散文的楷模。
促使他作出这样的论断的还有一个具体原因,那就是对《新青年》的“随感录”文体的不满足,(虽然他自己也是这个栏目的重要作者),从一九一八年四月栏目成立之时起,到周作人为文之时,已经三年,这种文体以笔锋犀利,议论风生为特点。
不要说其他五四先驱的文章,就是鲁迅收到《热风》里的二十七篇随感录,也完全符合西方的随笔(论文)的标准。
如果真的师承西方的散文观念,完全可以把这一类分析、思索、解释、评论,又有感性的文章,列入散文正宗。
但是,他在对五四初期的杂感进行反思时,却称之为“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他提出了一个与论文不同的文体的“美文”美文s。
把“叙事与抒情”作为根本的准则,只能说明他为中国散文作出了严格意义上审美价值的选择。
他当然不可能不知道,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广义的散文都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抒情的、审美的、诗化的,特点是从感觉、知觉到情感的抒发;一个就是主智的,越过感情,从感觉直接到个人化的智慧深化。
从理性上说,周作人感到了两者的矛盾,又有些偏向于情,说“好的论文”,也就是好的论文,就是“散文诗”,可是又不敢废了智,因而不免又吞吞吐吐地说“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
其实,“记”和“叙”固然是感性的美文文体,而“说”,包括先秦纵横家的游说和后世文人讨论政治和道德性质问题的书答(如韩愈的《师说》、《上宰相书》)是智性文体,笼统归入美文是勉强的。
历史发展总是带着某种“片面的深刻”的。
周作人凭着有限的西方文学阅读经验,又从明人性灵小品中,抽了两者之间最大公约数,首先把散文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文体,和理性的“论文”分开;其次,在文学中,又和诗歌和小说分立起来;再次,在智性与情感的矛盾中,选择了抒情。
后来王统照提出“纯散文的口号,也是沿着这条思路。
接着胡梦华提倡“絮语散文”,强调的是“不同凡响的美的文学”、“抒情诗人的缠绵的情感”、“人格动静的描画”、“人格色彩的渲染”、“个人的主观”、“非正式的”。
这里的关键词是“美的文学”、“抒情诗人的缠绵的情感”。
其次是“非正式的”,相对于正式的而言。
一九二八年,周作人为俞平伯的散文集《杂拌儿》作跋,就用“絮语散文”的观念来阐释“论文”,认为其特点是“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
在他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时还明确宣布:
“议论文照例不选。
”的确他所选的几乎全是抒情性质的散文。
这里有两点不可忽略:
第一,这不是周作人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在重大历史关头,抒情审美价值取向,独具民族和时代特色。
中国现代主情的审美散文和欧美多少主智倾向的“论文”就这样走上了不尽相同的道路。
第二,这仅仅是理论上的选择,与实践有相通的一面,又有错位的一面,但长期以来,没有引起注意,理论性的反思只能在实践经验饱和之后,和现代新诗中理论往往走在实践前面不同,散文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
抒情审美的取向,符合草创时期的散文发展要求,大大解放了散文的生产力,在短短十年间,五四散文居然被鲁迅认定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小说和诗歌。
先驱们的选择是:
建构一种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散文文体。
一九三五年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对人们把中国的现代散文和法国蒙田的“essais”,和英国培根的“论文”相联系,不以为然。
他说:
“其实,这一种翻译名义的苦心,都是白费心思,中国所有的东西,又何必和西洋一样?
西洋所独有的物质文化,又哪里能完全翻译到中国来?
所以我们的散文,只能约略地说,是prose的译名,和论文有点相像,系除小说、戏剧之外的一种文体,至于要想以一语来道破内容,或以一个名字来说尽特点,却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
”①想来郁达夫并不是不知道,在英国文学体裁中,并没有具体的“prose”这样一种文体,他不过是借此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历史选择辩护。
到此为止,就不是五四时期的理论预设,而是近二十年的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
这样的选择和总结,只能是理论上的自圆其说,在实践上,却留下了三个不大不小的漏洞:
第一,就是鲁迅的杂感式散文,充满了议论,好像在审美抒情美文里无处存身,究竟算不算散文呢?
如果按西方的论文准则,是天经地义的论文。
但,作为抒情叙事的散文,却难以自圆其说,以致长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②。
为了成全散文的抒情的叙事特性观念,不得已而求其次,硬把鲁迅式的杂感从散文中分离出来,命名为“杂文”。
作为一种文体,迅速得到广泛的认可。
但是,留下一个悖论:
鲁迅式的杂文算不算文学?
算不算散文呢?
如果算,则另立这样的文体,实属多余;如果不属文学,为何又写进现代文学史?
第二,就是在五四散文中(如鲁迅的《朝花夕拾》),也并不是只有抒情和叙事,还有幽默,而幽默是无法归入抒情之中的。
这一点要等到十多年后,郁达夫在《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来弥补。
这种片面的理论建构,造成的后遗症,直到八十年代林非的“真情实感论”,仍然阴魂未散。
这一命名的第三个漏洞,那就是掩盖了历史和传承的跛脚。
周作人只认定明人性灵小品为现代散文的源头,排斥了唐宋八大家和先秦诸子,事实上就是排挤了智性在散文中的合法地位。
这个漏洞,在并不很久以后,就引起了反思。
钟敬文在《试谈小品文》中,就提出了散文“有两个主要的元素,便是情绪与智慧”,情绪是“湛醇的情绪”,而智慧则是“超越的智慧”。
也许当时的钟敬文的权威性不够,似乎并没有引起重视。
一九三三年,郁达夫接着提出,“散文是偏重在智的方面的”,同样也没有得到重视。
这么宝贵的理性感悟,居然石沉大海,充分说明中国散文意识的不清醒。
等到七八十年后又有人加以反思。
余光中说:
“认定散文的正宗是晚明小品,却忘却了中国散文的至境还有韩潮澎湃,苏海茫茫,忘了更早,还有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
”在余光中看来,周作人所确定的现代散文规范,其实就是抒情“小品”,而大海似的中国古典散文则是智性的“大品”。
这主要是从思想容量的宏大和精神品位的高贵讲的。
其实,就是西方的随笔,不管是蒙田的,还是培根的,都不仅仅是小品,而且有相当多的“大品”。
梭罗的《瓦尔登湖》,不但是篇幅上,而且在情思和哲理的恢宏上,是小家子气的小品所望尘莫及的。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智性(审智)话语失去了合法性,其消极后果就是五四散文的小品化,除极个别作品(如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外,思想容量博大,气势恢宏的散文绝无仅有。
这当然造成散文舒舒服服的“内伤”,最明显的就是,鲁迅杂文在现当代文学史上长达五十多年,危峰孤悬,追随者队伍零落,至今只剩下邵燕祥、周国平等。
散文的这种偏废,除了社会政治原因以外,其文体的原因,要等八十多年后,才从文体观念上,开始做历史的和逻辑的清算。
回过头来看,中国现代散文的这种背离智性,单纯强调审美抒情的取向,显然是一个片面的选择,注定中国现当代散文在文体自觉上的极度不清醒。
一方面,迷信抒情,一度甚至把散文当作诗,走向极端,产生滥情、矫情;另一方面,又一度轻浮地放弃抒情,把散文弄成通讯报告。
在这样盲目的情况下,流派的不自觉就是必然的了。
和诗歌、小说追随世界文学流派的更迭形成对照,散文落伍于诗歌小说的审智潮流长达数十年,甚至在新时期还徘徊十年以上才做出调整,追赶上了从审美到审智的历史潮流。
二、散文文体意识的失落
三十年前,举国认同的散文旗帜,就是杨朔、刘白羽和秦牧。
他们的作品所凝聚的成就,带着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色彩,充满已经为历史所否决的政治观念(如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图解。
今天的读者看来,难免有不堪卒读的篇章,这主要是历史的局限,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
值得分析的倒是,杨朔在散文艺术上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观念,那就是他在《东风第一枝》的《跋》中所总结出来的:
把散文都当作诗来写。
这个说法一出,迅速风行天下,成为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散文的艺术纲领。
在那颂歌和战歌的刚性情调一统天下的局面中,杨朔散文多少追求某种个人的软性情调,口语、俗语和文雅的书面语言结合,情致随着语气的曲折,做微妙的变化,对于当时的散文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他的语言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倒是他反复运用从具体事物、人物升华为普遍的政治、道德象征的构思,成为一时的模式。
在今天看来,这实在是散文的枷锁,比之周作人的叙事抒情论更加狭隘;可是,在当时可是一种令人兴奋的艺术解放。
这是因为,在杨朔散文模式出现之前,中国散文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
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文学可以说有点朝气蓬勃的气象。
小说界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登记》等;诗歌界有崭露头角的闻捷的《天山牧歌》、公刘的组诗《在北方》已经脍炙人口;散文领域,却是颇为寂寞。
钱锺书、王了一(王力)搁笔,张爱玲远去香港,巴金等老作家正尝试着和新的政治意识形态适应,新人却并未产生。
到了一九五四年,中国作家协会总结五年成就,出版了《短篇小说选》、《诗选》,甚至《独幕剧选》,可就选不出一本散文选,只勉强出了一本《散文特写选》。
这就暴露了散文对于“特写”的依附。
特写,其实就是通讯报告,从性质上来说,是新闻文体,属于实用理性,并不是一种审美的艺术形式。
当时被认为最优秀的散文,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一系列“朝鲜通讯”之一。
巴金的《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其实也属于朝鲜通讯范畴。
诗人冯至的《东欧杂记》虽然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制约,但是其浓烈的抒情意味却保持了散文的文体感,然而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这说明,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其危机是如何严峻。
这种危机并非偶然出现,而是其来有自的。
早在四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就存在着两种散文潮流:
一个在国统区,以梁实秋、林语堂、钱锺书和王了一(还有张爱玲)为代表,以个人话语作自我表现,其最高成就,已经突破了审美诗化,以学者风范深邃内审,议论纵横,渗透着幽默的审“丑”,散文的文体自觉空前高涨,散文的谐趣和情趣一样,得到普遍的重视。
涉笔成趣的议论与抒情和小说的叙事相比,自成别开生面的艺术格局。
而在解放区,特别是一九四二年以后,由于自我表现受到批判,诗歌已经以“时代精神的号角”为务,散文岂能成为自我表现的避风港。
丁玲、周立波、吴伯箫、刘白羽等的散文向表现新人新事的新闻性质的通讯报告方面转移。
流风所及,散文遂为新闻性的通讯报告的附庸。
新闻、通讯、报告,得到行政方面的高度重视
以近乎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形成空前的热潮。
胡乔木甚至为文曰《人人要学会写新闻》。
这当然是战争环境,强化实用宣传功利所致,但是,在胜利进军的热潮中,狭隘政治功利对于散文的伤害却被忽略。
甚至到了只能出版《散文特写选》的时候,也还没有引发反思。
直到一九五六年“百花”时期,才稍稍有所改观,一些老作家乃有迥异于时代精神的带着个人色彩的散文。
但是,毕竟是自发的,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特殊性,要达到自觉,尚需积以时日。
真正的文体自觉,可能要等到五十年代末,一九五九年以降,六十年代初,“散文笔谈”之类广泛见诸报端。
秦牧提出“一个中心”说和“一线串珠”论②。
《人民日报》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开辟“笔谈散文”专栏,肖云儒的“形散而神不散”论,应运而生③,其实,就是秦牧的“一个中心”说和“一线串珠”论的发展。
这一说法后来风靡神州大地,意味着散文文体自觉意识的萌动。
但是,这种远远落后于五四散文理论的、先天不足的“理论”,还不足以引发文体真正的自觉。
理论的自觉,还要等待创作实绩的积累,主要是杨朔、刘白羽和秦牧有更多的作品,有更大的影响。
三、诗化散文模式和“说真话”背后的危机
杨朔最大的功勋,乃是以他超越当时水平的语言魅力,推动了散文文体意识的复苏。
把散文当作诗来写,不言而喻的就是不再依附新闻、通讯、报告,不再以狭隘社会功利为务,散文的诗化,实际上隐含着某种审美独立的意味。
在《荔枝蜜》、《雪浪花》中,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夹缝中,杨朔式的诗意流露出人情宽松的美,而不是斗争的、剑拔弩张的美。
正是因为提供了这样一点并不十分宽广的空间,杨朔散文才不是偶然地风靡一时,席卷华夏文坛。
当然,杨朔有其幼稚的一面。
散文中固然可以有诗,但是,散文和诗,在文体上,不管从西方文论还是中国古典文论看都有不可混淆的特性。
从这一点上来说,杨朔是矛盾的:
刚刚勇敢地把散文从通讯报告中解放出来,又匆匆忙忙把散文纳入了诗的牢笼。
文体意识的麻木,推动了杨朔散文风靡一时,模仿者络绎不绝,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散文的想象天地仅在杨朔模式之中,这在当时居然没有任何异议。
谁也没有反思一下,把散文当诗来写,在实际上,并不是全部诗意,而是诗中的颂歌、战歌和牧歌,比之五四时期周作人并不绝对排斥智性的抒情“美文”,比之郁达夫的“幽默”的天地不知狭隘了多少。
等到十年浩劫过去,思想获得空前解放,凌驾于散文上空沉重的政治乌云得以驱散,然而,颇为吊诡的是,邵华的《我爱韶山红杜鹃》影响巨大,甚至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仍然未脱事-情-政治象征的杨朔模式,虽然杨朔已经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
在当时影响较大的回忆浩劫的散文中,几乎毫无例外的是激情的倾泻,观念直白,散文的形式感荡然无存。
就是影响较大的陶斯亮怀念陶铸的《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也未能免俗。
这时影响最大的是巴金的《随想录》,把政治控诉转化为真诚的自我反思和解剖,提出了自我忏悔的命题,显示了老作家的心灵的纯洁和人格的崇高,获得一片赞扬。
比他的散文影响更大的是他提出的散文观念“说真话”但也并没有带来散文文体意识的觉醒。
从理论上来说,比之把散文当作诗来写,“说真话”更加不属于散文,不但不属于散文,而且很难说属于文学。
比之钱玄同在五四当年为胡适的《尝试集》作序,痛斥“毫无真情实感”的“文妖”,提出“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并没有什么发展。
虽然,其积极意义不可抹煞,但是,其中隐含着三个误区:
第一,在政治高压下,敢不敢说真话,是道德和人格的准则,并不完全是文学创作的准则;第二,在文学中“说真话”,不仅仅需要道德勇气,真话,并不是现成的,只要有勇气就脱口而出,真话是被假话、套话窒息着的,遮蔽着的,说真话就意味着从假话、套话的霸权中突围,这是需要高度才情和睿智的。
在思想解冻的初期,真实的情志,往往存在于潜意识的深层,可意会而不可言传,需要话语颠覆的才能;第三,就是把潜在的、深邃的真话顺利地讲了出来,还有一个散文文体的特殊性问题。
真话不等于诗和小说,真话也不等于散文。
同样的真话,在不同的文体中,会发生不同的变异。
一味用诗的话语去写散文,正等于用散文的话语写诗。
巴金的说真话一时被奉为金科玉律,正说明了散文文体意识仍然麻木。
在说真话的神圣道德大旗下,巴金可能也有点自误,虽然他的《随想录》中,《怀念萧珊》、《小狗包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是,长达几十万字的多卷散文中,精品如此有限,绝大多数作品写得都太随意,从构思到语言,都比较粗糙。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年的溢美之词,正是散文文体意识沉睡的证据。
与风起云涌的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引发文坛“地震”的艺术革新相比,散文显得呆板而且僵化。
当小说和诗歌的青年作者纷纷“崛起”,给老一辈作家以巨大冲击之时,散文领域里却如哈姆莱特所说,“丹麦王国平安无事”。
将近三年以后,在这近乎一潭死水的领域中,最初激起波澜的,并不是一批青年,而是资深的老作家。
孙犁短小的散文,出现在《光明日报》,引人注目的是,并不以诗性的抒情为务,他发挥了他小说家老到的功力,他的叙述在平实中见深沉,从容淡定。
就是怀念遭受迫害而牺牲的战友,也不夸张其高尚,不渲染其苦难,不追求廉价的、幼稚的、感情升华的效果,不以诗意的营造来美化自我;相反,不时表露出对自我的不满甚至调侃。
这当然引起了许多赞叹,然而真正要引起文体的反思,还需要更多更重的分量。
一九八一年,杨绛以一种非常朴素的形式发表了《干校六记》。
一般散文作家,都是先把文章在报刊上分别发表,引起关注,然后收集成册。
而杨绛却一下子把六篇文章,以一个薄得不能再薄,一共才六十七页的小册子,在三联书店出版。
这种不事张扬的做法和她不事张扬的文风不谋而合,然而,却在内行人之间,触发了对散文文体的反思。
杨绛的文风显得比孙犁更加从容,更加坚定地反杨朔之道而行之,不把散文当成诗来写,就是把散文当作散文来写,就是在非诗的领域里追求散文的情趣和谐趣,哪怕写“文革”的灾难,甚至生离死别,屡遭横逆,她也节约着形容和渲染以平静的叙述为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比之孙犁,当然,有时也有所强调,甚至有些夸张,但那往往不是抒情,不是美化,有时,恰恰是在强调某种“丑化”,这一点在《“小趋”记情》中表现很是突出。
我在《文学性讲演录》中这样说:
杨绛在《干校六记》里讲过:
她女儿住在老乡家,小娃子拉了一大泡屎在炕席上,她急得用手纸去擦,大娘跑来责备她糟蹋了手纸,也糟蹋了屎,大娘呜噜噜一声喊,就跑来一只狗,上炕一阵子舔吃,把炕席连同娃娃的屁股都舔得干干净净。
她说,下了乡才知道为什么猪是不洁的动物,因为猪和狗是同嗜,不过,猪不如狗,只顾贪嘴,会把蹲着(拉屎)的人撞倒,狗则坐在一旁耐心等待,到了时候,才摇着尾巴过去享受。
一方面是很脏的事,另一方面是老大娘很淳朴的感情。
她比较节约,比较坦然,并不觉得这是寒碜的事。
狗和猪相比,狗比较文雅地等,猪等不及就把人拱倒了,表面上都是很丑的,不存在“礼让”和“同嗜”这样文雅的问题,吃人的大便,也不存在“享受”的问题,这是语言和情感的错位。
这是幽默,是“软幽默”,是调侃,不是讽刺,没有进攻性。
这里表现了人与人间的一种沟通,她对大娘并没有厌弃,对狗也没有表现出愤怒。
这显然是幽默的谐趣,这是五四散文的另一个传统,长期被忽略,其特点可以说是“以丑为美”,从这一意义上说杨绛把五四散文的两个传统,审美的抒情和审丑的幽默,一下了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不是过誉。
一大批文坛宿将在散文界的贡献,远远超过了青年散文作者,这在当时很是奇特。
以至于有人提出:
诗是青年的艺术,小说是中年的艺术,而散文是老年的艺术。
这当然只是现象,实质是五四散文传统对极度狭隘模式的冲击,但是,冲击仍然是自发的,杨绛并没有引发散文文体反思的雄心。
杨绛没有舒婷们幸运,一来,她在创作上反杨朔模式,肯定瞧不起杨朔,作为学者的她,也许觉得作品更雄辩,懒得作理论宣言;二来,散文界不像诗歌界那样为官方所重视,没有近水楼台的行政压力,也就没有强烈的反抗;三来,散文没有严密理论,是世界性的现象,因而也就没有对峙,也没有任何“地震”,更没有全国性的“围剿”。
等到汪曾祺的散文有了影响,已经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了,他在《〈蒲桥集〉自序》中说:
“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
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
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
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他针对的也许不是杨朔,但是,的确是五四散文风格对类似杨朔的文风的批判。
散文理论界,缺乏历史感,未能意识到杨绛和汪曾祺回归五四散文传统的价值,没有接过话头,眼睁睁看着诗歌和小说中,理论战线大叫大喊,战云密布,遍山旗帜,而散文理论界,偃旗息鼓,一片沉寂。
恢复活力的散文,对理论的兴趣,甚至不如美术界。
四、“真情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