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读后感.docx
《铁皮鼓读后感.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铁皮鼓读后感.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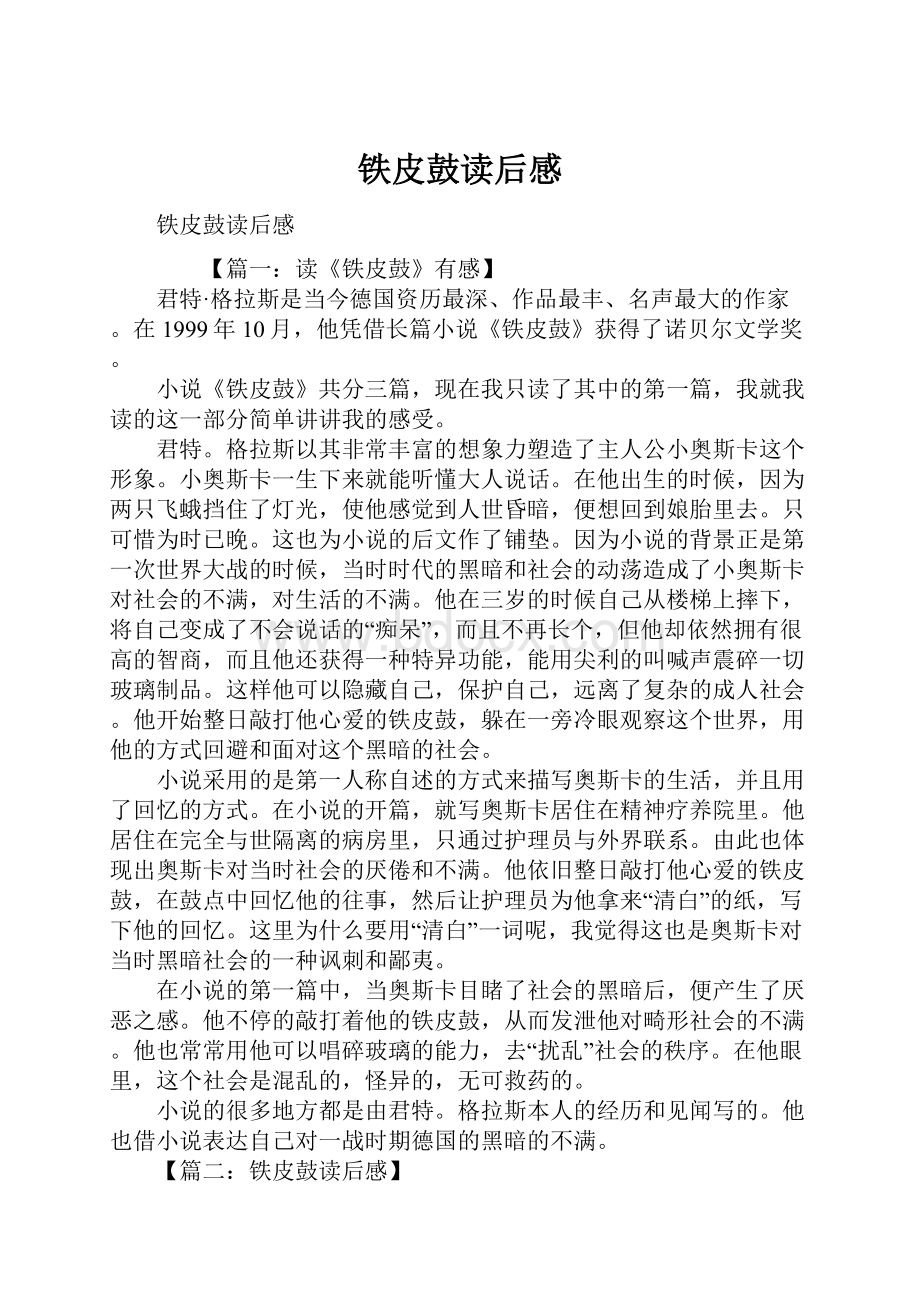
铁皮鼓读后感
铁皮鼓读后感
【篇一:
读《铁皮鼓》有感】
君特·格拉斯是当今德国资历最深、作品最丰、名声最大的作家。
在1999年10月,他凭借长篇小说《铁皮鼓》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铁皮鼓》共分三篇,现在我只读了其中的第一篇,我就我读的这一部分简单讲讲我的感受。
君特。
格拉斯以其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主人公小奥斯卡这个形象。
小奥斯卡一生下来就能听懂大人说话。
在他出生的时候,因为两只飞蛾挡住了灯光,使他感觉到人世昏暗,便想回到娘胎里去。
只可惜为时已晚。
这也为小说的后文作了铺垫。
因为小说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时代的黑暗和社会的动荡造成了小奥斯卡对社会的不满,对生活的不满。
他在三岁的时候自己从楼梯上摔下,将自己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痴呆”,而且不再长个,但他却依然拥有很高的智商,而且他还获得一种特异功能,能用尖利的叫喊声震碎一切玻璃制品。
这样他可以隐藏自己,保护自己,远离了复杂的成人社会。
他开始整日敲打他心爱的铁皮鼓,躲在一旁冷眼观察这个世界,用他的方式回避和面对这个黑暗的社会。
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来描写奥斯卡的生活,并且用了回忆的方式。
在小说的开篇,就写奥斯卡居住在精神疗养院里。
他居住在完全与世隔离的病房里,只通过护理员与外界联系。
由此也体现出奥斯卡对当时社会的厌倦和不满。
他依旧整日敲打他心爱的铁皮鼓,在鼓点中回忆他的往事,然后让护理员为他拿来“清白”的纸,写下他的回忆。
这里为什么要用“清白”一词呢,我觉得这也是奥斯卡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一种讽刺和鄙夷。
在小说的第一篇中,当奥斯卡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后,便产生了厌恶之感。
他不停的敲打着他的铁皮鼓,从而发泄他对畸形社会的不满。
他也常常用他可以唱碎玻璃的能力,去“扰乱”社会的秩序。
在他眼里,这个社会是混乱的,怪异的,无可救药的。
小说的很多地方都是由君特。
格拉斯本人的经历和见闻写的。
他也借小说表达自己对一战时期德国的黑暗的不满。
【篇二:
铁皮鼓读后感】
三岁的奥斯卡无意中发现母亲和表舅布朗斯基偷情,又目睹纳粹势力的猖獗,便决定不再长个儿,宁愿成为侏儒。
从此在他的视角里,社会和周围的人都是怪异和疯狂的。
他整天敲打一只铁皮鼓,以发泄对畸形的社会和人世间的愤慨。
父亲或老师惹了他,他会大声尖叫,震得窗玻璃和老师的镜片稀里哗啦地变成碎片;他还以此来“扰乱”社会秩序,给纳粹分子集会造成麻烦。
尽管他个子不高,但智力超常,聪明过人。
面对他的洞察力,母亲羞愧忧郁去世,父亲成了纳粹军官,表舅在战乱中毙命。
邻居女孩玛丽亚来照顾他,两人发生了性爱,怀孕后她却嫁给了父亲,生下了库尔特。
奥斯卡随侏儒杂技团赴前线慰问德军,三年后回到家中,苏军攻占了柏林,父亲吞下纳粹党徽身亡。
埋葬父亲时奥斯卡丢掉了铁皮鼓,同时亲生儿子库尔特用石子击中了他的后脑勺,使他倒在坟坑中,流血不止;不过他就此开始长个儿,尖叫使玻璃破碎的特异功能也随此消失……
这是整本书的故事情节,离奇而透着古怪。
扭曲的人性在其中很明显的表现了出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穿插讲述了但泽的多灾多难的历史。
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时,这个海港城市划归普鲁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但泽成为自由市,由国际联盟代管。
希特勒以但泽走廊问题为借口,入侵波兰,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战后但泽划归波兰。
这是作家对希特勒统治的强烈不满,也是对当时德国的现状的感慨与悲痛。
此书分为三个章节,其中第一章可以看出故事发生地点是但泽,时间从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三九年,主要以一九三三年纳粹党魁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纳粹势力在但泽抬头为背景。
在第二章中,故事发生地点仍是但泽,时间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军事行动,纳粹党的安乐死计划(把精神病患者、痴呆儿童等病人作为“不值得活的生命”予以消灭),集中营煤气室屠杀犹太人,一九四四年军官暗杀希特勒的“七。
二”事件,反抗运动,以及战后划归他国的原德国领土上的德国人被驱逐。
而在第三章中,故事地点位于杜塞尔多夫,背景是战后美、英、法占领区即西德的物资匮乏时期,老百姓的黑市交易,帝国马克贬值和以美军香烟为商品交换计值单位,西德货币改革,通过基本法和联邦德国成立后的经济复苏,时间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四年。
这些是小说发表时三十岁以上的德国人都亲身经历过的、想忘也忘不了的往事,而作者偏要勾起人们对这些往事、尤其是个人在这段既往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回忆。
而以但泽为故事发生地本身,就涉及到当时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铁皮鼓用几个关键词来分析就是疯狂,绝望,无奈以及残酷。
现实的情形反映到了作品之中,这是作家的反思,也是人民的反思,更是对当权者的讽刺,这是一本很有现实意义的小说。
【篇三:
铁皮鼓读后感作文】
在王小波的书中不知一次提到了这本书,所以是仰慕已久。
然而这本书的阅读时间也实在拖的太久了,都感觉有点对不起格拉斯。
俗务在身加心多旁骛,无法好好的阅读这部精彩的小说实在是一大遗憾。
今天阅毕,就算是对自己对格拉斯对王小波的一个交代了。
本书充满了太多的隐喻,如果深挖,会有不少乐趣的。
逃避成人世界奥斯卡是一种消极反抗的象征。
可以随心所欲的达到停留在3岁小孩的效果,我猜想这是大多数成年人的梦想。
然而小孩是盼望早早长大的,除了早熟的奥斯卡。
然而身体停留在3岁的状态,却不能使心灵也停留在3岁的状态,而成长的心灵使奥斯卡倍受欲望和邪恶的折磨的痛苦——终于有一天他要长大,虽然只是一点。
还好,有神奇的铁皮鼓,这件孩童的玩具无疑是童真的外化。
拥有铁皮鼓的奥斯卡或者说奥斯卡拥有的铁皮鼓具有神奇的耶稣般的魔力,这种力量正是童真的力量,他(它)能让成年人舞蹈哭泣——回到远离的童年时代。
还有一件奇迹是奥斯卡孩童时的尖叫——随意雕刻玻璃的工具,这是无力的孩童的唯一武器,它有神奇的力量同时也不具备丝毫真正的威力。
在现实的磨练中,这件武器渐渐的失效了。
有一幕场景让我很感动——在“洋葱地窖”中借着洋葱哭泣。
以上只是在这里写下来时的零碎感想,如果有时间要好好的将本书分析分析。
【篇四:
《铁皮鼓》之观后感】
首先声明电影中意象的内涵是多重的,其意义指向也是外延式的,它所讨论的层面是多元、丰富的,涉及了包括种族、性爱、爱情、人性的弱点在内的诸多话题。
我仅就战争对个人的影响这一个话题来谈谈自己对《铁皮鼓》的理解。
我认为《铁皮鼓》的主题在于着力表现战争对个体的异化和个体对这种异化的抗争。
异化首先是从个人意愿服从于集体意志开始的。
这种服从是强制性的,它从军队逐渐蔓延到家庭当中,让每一个公民都成为一个战士,只听从上级领导的命令,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选择,从而形成一种社会战备总动员。
电影中奥斯卡的爸爸强迫他妈妈阿格妮斯吃鳗鱼的情节旨在表现家庭关系中的强制性,而他的叔叔扬被强迫参战则是强制性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
阿格妮斯和扬这两个相互爱恋却无法在一起人的悲剧结局又向我们表明,战争的残酷会压抑人对美好和自由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泯灭人性中最纯真的一面,让人陷入一股痛苦的精神折磨中,甚至能够毁灭人的一生。
而当个人意志完全服从与集体意志之后,个人的判断能力便随之丧失,人将自觉地按照一种上下级关系来建立起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战争本身是需要热情和斗志的,但是当社会中的每一成员都充满着极度的热情去对待战争时,这场战争将变得极为可怕。
最令人担忧的不仅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是对战争本身的崇拜:
一旦所有人的双眼被蒙蔽,他们就看不到战争罪恶的一面,无法分清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差别,更不会承认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侵略行为。
就像二战时期日本侵略者打着解放东三省、拯救全亚洲的借口一样,把侵略视为正当行为,借口也就正大光明地被当作口号,即便在战后多年也不能深刻地反省错误的严重性,导致现在右翼势力抬头。
战争非正义的性质被掩盖,取而代之的却是其合理存在的因素,战争本身甚至会演变成为一种人的精神寄托和对未来的希望。
而一旦战败,这种狂热的信仰便瞬间瓦解,人们将再一次陷入无助的绝望感和深深的幻灭感中,奥斯卡父亲的死亡结局便象征了狂热分子精神世界支柱的崩溃,也宣示了战争所引发的双重悲剧。
个体的差异性被完全消除,社会将逐步走向一致性,最终达到高度的同一,公民作为个体的身份也就丧失,成千上万的个人便完全沦为了国家的机器,而且还是成分不同等级的复制品——这就是异化的结果。
不过异化也并不是每个人的宿命,也不是所有人都逃不出异化的魔掌,至少在电影中有三类人似乎摆脱了外在环境的束缚:
一类是以奥斯卡祖母为代表的旁观者,她将自己完全抽离于尘世纷争当中,宛若时间的化身,作为第三只眼静静地看着一切缘起缘落;第二类以马戏团的侏儒演员们为代表的空想主义者,表面上他们为军队提供服务置身于战争之中,但实际上却有着自己的独立主张,发挥其自身优势得以生存,甚至得到军队的尊敬,对世界也充满了关爱和悲悯之情。
然而当活生生的暴力冲击到其周围或自身时,他们既无力阻止(沙滩上圣母在他们面前被杀害)也无法抗拒命运(罗丝维塔的意外死亡),悲剧在他们身上依旧上演;第三类则是以奥斯卡为代表的斗士,由于跌倒而导致无法生长,他首先便作为一个异质而存在,每当他面对外部的施压时他便敲击自己的铁皮鼓并且大声尖叫以示反抗,当他发现自己拥有一副可以击碎玻璃的特殊嗓音时,他又不断利用自己的本领尝试去改变在他看来极不合理的世界。
在我看来,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摸过于奥斯卡利用自己的鼓声搅乱了欢迎仪式上军官走在红地毯的配乐的情节,乐队停止演奏严肃的进行曲而改奏起优美的舞曲,最后现场除奥斯卡父亲之外的所有人都随着旋律翩翩起舞,这无疑是奥斯卡拿起自己的武器奋力一搏、向这个荒谬的世界进行的最有力的回击。
也就是说,个体是有能力拒绝被异化的,奥斯卡最后坐上火车离开旧地预示了抗争的胜利和新的开始。
战争本身持续的时间相对短暂,然而它所带来的影响却是长久而深刻的。
尽管在客观上战争对科学技术、社会变革、历史发展等宏观世界能够产生一些催化作用,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它对个人的生活状态、性格的健全发展、人格的完整性等个体层面的巨大伤害是不可否认的。
作为人类的一大共同灾难,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地抹杀掉战争给人造成的难以愈合的心灵伤害。
表现德国新纳粹主义的电影《浪潮》与《铁皮鼓》交相辉映,前者向我们表明个人很容易受到集体力量感染,因而社会随时都潜在着利用大众的反动势力的可能,后者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每个人都需要携带一架铁皮鼓,在面对扭曲自身的外部压力时,随时奏响反抗的鼓声。
【篇五:
《铁皮鼓》读后感】
这本书写什么?
写一个傻子。
《尘埃落定》也写傻子,那是个傻子加先知;莎士比亚写了若干傻子,统统是傻子加智者;《喧哗与骚动》也有个赫赫有名的傻子,傻到没个性,读者很难“角色代入”;《狂人日记》的傻子,则完全是作者的传声筒。
《铁皮鼓》的傻子怎么样呢?
那是个非常合我心意的傻子,几乎和《尘埃落定》的傻子一般钟爱。
奥斯卡,侏儒,铁皮鼓手,是个傻子加撒旦。
君特·格拉斯长于大战期间,同期涌现的文学大师非常多。
奇怪的是,《铁皮鼓》没有历史的“现场感”。
最近也在读埃利亚斯·卡内蒂的三卷本自传,有所比较。
这位用德语写作的欧洲作家,同样生于20世纪初。
大战开始时,卡内蒂还是孩子,有个强大的保护者——母亲。
他回忆中的战争,没有战火,没有死亡。
卡内蒂只关注自我,精妙而不厌其烦地将自己层层剥开(这才是真正的“剥洋葱”)。
然而,这个紧紧围绕“自我”的小世界,不断吸附周围事物,不断扩大,使一切随之旋转。
这种磁力和能力,给所有喋喋不休的私密叙述,赋予了宏大意义。
有人说卡内蒂的自传,虚构多多,那又如何,至少战争爆发时,他那厢勾勒几位身边的平常人,我这厢立即闻到了销烟。
《铁皮鼓》的奥斯卡也经历战争,君特·格拉斯替他枚举数据史料,描述死人、伤人、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的人,甚至让奥斯卡亲历波兰邮局保卫战。
但作为读者的我,仍没有“现场感”。
我——作为读者,被禁锢在奥斯卡3岁的身体里了。
这不是叙述方式的问题,《尘埃落定》也傻子视角,但有历史现场感;《大师与玛格丽特》也夸张荒诞,也有历史现场感——甚至有着作者布尔加科夫的血与肉。
相比之下,俄国人写作像在掏心掏肺,想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想想帕尔捷斯纳克。
读《日瓦戈医生》时,我不仅看见战争,还在亲历战争。
而德国人君特·格拉斯——擅于运用匠心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君特·格拉斯,却是那么不动声色。
我看不到血,听不到炮火,感知不到奥斯卡的身外在发生什么,只有那个声音——平静、冷酷、乖戾的,是奥斯卡也是格拉斯的声音,顺着一条平缓的甬道上升。
这种写作风格,正是我想象的制造“纳粹事件”的君特·格拉斯可能的风格。
但在《铁皮鼓》面前,“纳粹事件”一点不重要。
因为君特·格拉斯本人如何,一点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塑造了小奥斯卡!
这部作品中,战争不是主角,而是背景。
真正的主题是人类灵魂的一次漫游。
像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写作那样,这部层次丰富的作品,离不开希腊和希伯来两大传统,有神话原型如弑父,也有上帝与撒旦。
事实上,撒旦是奥斯卡的一部分,奥斯卡是撒旦的一部分。
格拉斯帮助我们理解撒旦。
在此意义上,这部作品比绝大多数战争写实小说来得伟大,它接近了战争的本质——恶。
作家需要发现、探索、理解恶。
他首先要看到自己的恶。
恶应该是文学的重要主题,但长久以来它不是。
恶是有罪的,不该的。
所以被忽略,摒弃。
文学史出现萨德这号人物,完全是压抑过久的大爆发。
只有正视恶,才能更好地理解善。
我想,这是《铁皮鼓》的伟大。
君特·格拉斯是我迄今最喜爱的知识分子作家。
我对那帮“新寓言”的知识分子,没有太大感觉。
法国人,喜欢玩精妙。
可惜无论法国人的精妙,还是日本人的暧昧,我都感觉不强烈。
我需要的是当头一棒,让我震撼与晕眩。
力量感,是我个人评价作家的重要标准。
俄国作家、美国作家,总体而言力量感强。
前者的力量来源偏重于精神,后者偏重于现实。
中国作家中,北方作家的力量感比南方的强(想想莫言和余华的作品差别)。
回到“知识分子写作”,几年前,《玫瑰之名》让我对这个词倒尽胃口(依据上述,该作品力量感为零)。
我一边阅读一边疑惑:
《玫瑰之名》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意义何在?
不能带给我任何感动、震撼和启迪。
如若一些捧臭脚的知道分子说的那样,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我真想把书中的大段理论以及更为大段的注释剪下来,叠起来,戳到他们面前,让他们摸着心口说说,这么一堆聱牙诘屈的东西,是否真对“引人入胜”一词没有致命杀伤。
如果知道分子们捧起另一只臭脚,说该书阐释了某种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因此它比只知夺人眼球的侦探小说深刻许多。
那我倒想问:
为何不直接读论文,岂不更深刻清晰、节约时间?
最终,我意识到了,《玫瑰之名》——以及其他可以想见的艾科制造——被写出来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展示作者风采:
这位学者小说家拥有相当的知识,掌握相当的写作技巧。
至少,他比侦探小说作家深刻,比哲学论文作者会写小说。
这种穷凶极恶的知识炫耀,让我想起北京话的一个词:
提人。
指提及各路要人,并作熟稔状。
事实上,提人不能使提人者本身成为要人,就像炫耀知识的小说家,不能使作品本身具备知识或者成为好小说。
我曾被迷惑过,但越来越认识到:
知识不是用来炫耀,而是用来帮助认清世界的。
最后,扯一下另一位知识分子作家米兰·昆德拉。
我曾将他贬至一无是处。
但这有感情色彩。
就像初恋,开始期望得完美,结束未免失望得惨烈。
米兰·昆德拉,就是我的文学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