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文学观与文学三元论.docx
《历史的文学观与文学三元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历史的文学观与文学三元论.docx(2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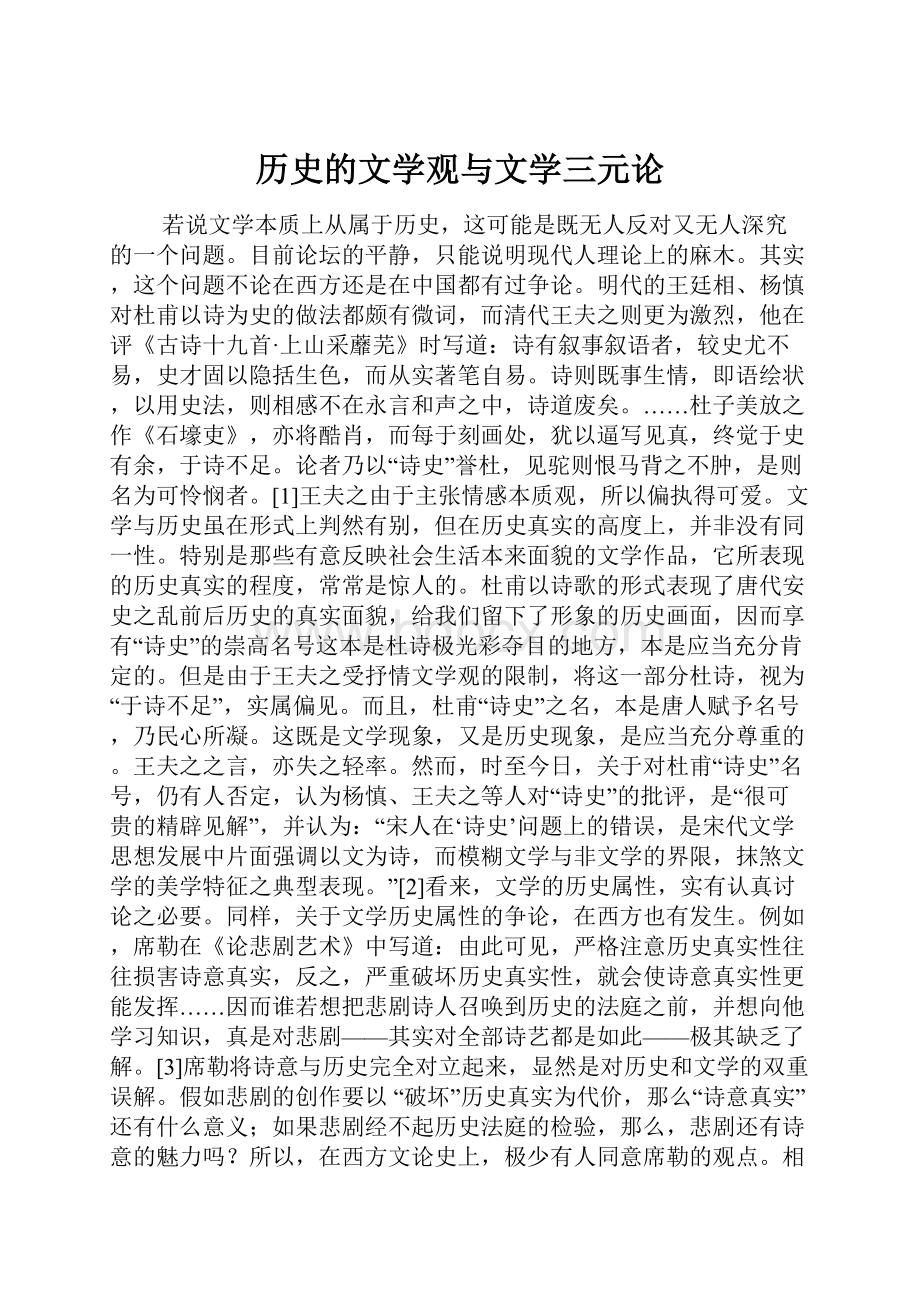
历史的文学观与文学三元论
若说文学本质上从属于历史,这可能是既无人反对又无人深究的一个问题。
目前论坛的平静,只能说明现代人理论上的麻木。
其实,这个问题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过争论。
明代的王廷相、杨慎对杜甫以诗为史的做法都颇有微词,而清代王夫之则更为激烈,他在评《古诗十九首·上山采蘼芜》时写道:
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隐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
诗则既事生情,即语绘状,以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
……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
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
[1]王夫之由于主张情感本质观,所以偏执得可爱。
文学与历史虽在形式上判然有别,但在历史真实的高度上,并非没有同一性。
特别是那些有意反映社会生活本来面貌的文学作品,它所表现的历史真实的程度,常常是惊人的。
杜甫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历史的真实面貌,给我们留下了形象的历史画面,因而享有“诗史”的崇高名号这本是杜诗极光彩夺目的地方,本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但是由于王夫之受抒情文学观的限制,将这一部分杜诗,视为“于诗不足”,实属偏见。
而且,杜甫“诗史”之名,本是唐人赋予名号,乃民心所凝。
这既是文学现象,又是历史现象,是应当充分尊重的。
王夫之之言,亦失之轻率。
然而,时至今日,关于对杜甫“诗史”名号,仍有人否定,认为杨慎、王夫之等人对“诗史”的批评,是“很可贵的精辟见解”,并认为:
“宋人在‘诗史’问题上的错误,是宋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片面强调以文为诗,而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抹煞文学的美学特征之典型表现。
”[2]看来,文学的历史属性,实有认真讨论之必要。
同样,关于文学历史属性的争论,在西方也有发生。
例如,席勒在《论悲剧艺术》中写道:
由此可见,严格注意历史真实性往往损害诗意真实,反之,严重破坏历史真实性,就会使诗意真实性更能发挥……因而谁若想把悲剧诗人召唤到历史的法庭之前,并想向他学习知识,真是对悲剧——其实对全部诗艺都是如此——极其缺乏了解。
[3]席勒将诗意与历史完全对立起来,显然是对历史和文学的双重误解。
假如悲剧的创作要以“破坏”历史真实为代价,那么“诗意真实”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悲剧经不起历史法庭的检验,那么,悲剧还有诗意的魅力吗?
所以,在西方文论史上,极少有人同意席勒的观点。
相反,文学的历史属性,却得到了较充分的讨论。
但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无论中西都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和讨论。
一、中国古代对文学历史属性的讨论中国最早的历史的文学观,一般表现为诗、史混同论。
这可能与中国上古的杂文学观念有关,既然诉诸竹帛者都是文学,那么,诗与史自然为一家了。
关于诗与史的关系,敏泽先生在他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中,有比较醒目的勾勒,现在,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作比较详细地梳理和研究。
最早将文学与历史等而视之并诉诸文字的是孟轲(前372-289)。
《孟子·离娄(下)》有云: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在孟子看来,《春秋》等史书的出现,乃是《诗经》延续和补充,诗于史几乎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
由此开创了中国诗、史不分的文艺观。
其实,这种思想并非孟轲首创,很可能是他对上古诗学传统的总结。
请看,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中的“观”的意思,不就包含着历史的文学观的内核吗?
所谓“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注),所谓“考见得失”(朱熹注),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诗歌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而这就是文学历史属性的表现。
孔子这样看待诗歌,也非凭空产生,而是从当时官方对待民间诗歌的态度和做法中自然而然地归纳出来的。
孔子之前,许多文献记载了宫廷和贵族“观乐”的活动。
这些都是孟子点破诗与史关系的基础。
在汉代,司马迁作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却以《诗经》为楷模,为自己制定写作原则,他写道: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4]显然,司马迁是继承了孟子的观点,按《诗》的原则去写历史,《史记》成了他的发愤之作。
这样,《史记》中充满了浓郁的诗情,具有鲜明的文学性便不足为怪了。
同时,司马迁写《史记》还秉承了《春秋》以来的史学传统。
他说:
“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5]这样他又把“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精神,带进了史传文学,开启了中国文学的写实传统。
这种思想与先秦诗学的“美刺讽谏”说合流,形成了《诗大序》的文学观,它对《诗经》作了新的诠释。
其云: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这里将《诗经》之风、雅、颂全都系之于社会生活,称为“四始”,认为它是《诗经》达到艺术至境的原因,明显是一种历史的观察视角。
这种视角在扬雄、班固那里也有表现。
扬雄(前53-公元18)虽提出“心声”、“心画”说,但却同时承认文学与生活(历史)的联系,他说:
“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昏昏,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
[6]总之,文章虽为心声,而实际上,它却是历史时空中的客观世界在心灵上的反映。
班固(32-92)首先肯定了司马迁的史学传统。
他说:
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7]班固对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既树立了史学原则,又树立了一条文学原则,而影响深远,几乎贯穿中国文学史。
他在《汉书·艺文志》中,除重申了古代“采诗”、“观风”之说外,还以历史的眼光,论述了“诗”亡而“赋”作的社会原因。
如云:
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
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8]这里揭示了诗亡而赋作的社会原因,肯定了诗、赋产生的社会根源的一致性,也是对文学历史属性一种发现。
之后,何林在《公羊传解诂》中对诗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本质性概括,王充《论衡》中对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再次肯定,都可以看出《汉书》的影响。
魏晋六朝之际,玄理与缘情文学观并起,先后成为主流文学倾向。
而文学的历史本质观,呼声甚微。
惟有葛洪(283-363)尚有某些实录的文艺思想。
他对王充的《论衡》很推崇,又十分佩服司马迁的历史眼光。
其《抱朴子·名本篇》有云:
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
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
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
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
葛洪不仅佩服司马迁那种历史学家的勇气,还推崇王充厚今薄古的反传统眼光,他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敢说今诗胜于古诗、汉赋高于《诗经》的评论家。
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刘勰由于主张“原道”、“宗经”,其历史的文学观并不明显。
唯在《文心雕龙·时序》中,亦显示了对文学历史属性的尊重。
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是随时代(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必然表现为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
因而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著名观点。
这其中就包含着对文学的历史属性的领悟。
其云:
[!
--empirenews.page--][1][2][3][4][5][6][7][8][9]下一页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
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
尽其美者何?
乃心乐而声泰也。
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
成汤圣敬,“猗欤”作颂。
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
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
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
这里叙述了不同的时代便会产生不同的作品,是想说明一个道理:
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便会产生什么样的文艺,因此,文学的历史属性在这里是映衬得是很分明的,只是刘勰没有言明而已。
唐代,应当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的历史本质观生成的时期。
唐初,撰史成风,因此,出现了著名历史理论家刘知己(661-721)。
他对中国古代诗、史混同论的大力张扬,对唐代文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认为文学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提出“则文之将史”的观点。
其云: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
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
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
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
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
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9]刘知己这段论述大有深意:
其一,他将“不虚美,不隐恶”不仅视为史学传统,而是首先视为诗学传统,这可能是唐人以诗为史的理论根据;其二,他所列举文学作品和作家,在内容上是忠于生活,体现历史真实的典范,在人格上是不谄、不谤的忠良正直的典范,这就为唐代作家树立了理想的艺术范本和人格范本;其三,在传统观念中,对历史家充满着尊敬,他们可“以口诛笔伐”使“乱臣贼子惧”,是民族精神的正义的象征,而文学艺术直到汉代还被有些人视为“雕虫小技”,文学之士被视为“弄臣”,刘知己能一反传统观念,认为文学与历史具有同样的价值,文学家与历史家一样,都是民族的忠良正直之士,这对历史学家触动也许不会太大,但对文学家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振奋;其四,“则文之将史”的提出,等于为文学树立了一个严格的历史批评标准,这样,我国文学史上许多作品,如《国风》、《楚辞》,如贾谊、赵壹、晁错等的作品,都有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10]的历史借鉴作用。
这已是相当自觉的文学的历史本质观。
显然他在在当时是影响巨大的,就连狂放不羁的李白都受了这种文学观的影响,他在《古风》二首中写道: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我志在删述,重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这里,李白以《诗》亡而作《春秋》的孔子自况,以“志在删述”,重辉“春秋”为己任,承担起书写历史的任务,恢复古道的光辉,俨然是一位历史学家,而其实他讲的是怎样作诗。
这种将写诗和写史混为一谈的做法,看似天真,它却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学观,一种以表现历史真实为目的文学观。
只是由于李白的创作个性不合辙,他说得到而做不到而已。
但是,比他小十二岁的杜甫,却认真地向着这一新的方向走去。
杜甫(712-770)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史上,最自觉地以诗为史的诗人。
他不仅写下了像《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等高度写实的名篇,还明确地在诗文中反复申述了自己以诗为史的文学观。
他写道:
直笔在史臣,将来洗筐箧。
(《八哀诗·故司徒李光弼》)留滞一老翁,书时记朝夕。
(《雨》二首之二)采诗倦跋涉,载笔尚可记。
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坠。
(《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杜甫的创作态度,显然是受司马迁以来的诗、史混同论的影响,他胸怀黎民,肩担社稷,秉笔直书,以诗为史,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无疑是个创举。
杜甫不仅用历史的文学观从事创作,同时他还用这种眼光去评价同时代的诗人。
例如,他将元结(719-772)誉为“俊哲”、“国桢”,并高度评价了他的作品。
他在《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中写道:
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
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
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
杜甫认为,元结其人为天下邦伯、乱世忠臣,有汉官良吏之风;其诗有知民疾苦“直举胸臆,用为鉴戒”的作用,它有“彰善而不党,指恶而不诬”[11]的“春秋”笔法和实录精神。
所以,杜甫将元结视为同调,他写道:
“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
[12]又说“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诗”。
看来,杜甫在当时并不孤立,写“规风”之诗,呈“鉴戒”之章,以诗为史,正是杜甫与元结文学观的中心思想,在中唐之后影响巨大,发展为白居易、元稹为首的新乐府诗歌运动。
白居易(772-846)是一位更为自觉的以诗为史者,他在著名的《与元九书》中写道:
自登朝来,年齿见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这便是著名的新乐府运动的创作原则。
所谓的“合时”、“合事”而作,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必须符合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尊重历史真实。
这种作品必然具有鲜明的历史属性,所以这种文学观,实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文学本质观。
而这些正是他从前人的书、史中悟出的道理。
这使白居易和元稹都成了十分自觉的历史主义者,他在写给樊宗师的诗中说:
阳城为谏议,以正事其君……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君为著作郎,职废志空存。
虽有良史才,直笔无所申。
何不自著书,实录彼善人,编为一家言,以备史阙文。
[13]白居易对元稹人格的称赞,对樊宗师的建议,都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气魄要求于文学家的。
由司马迁、刘知己、杜甫以来所提倡的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正面的阐述和发扬。
他在这里提出的诗人为“良史才”,视诗歌为“史”之“阙文”的观点,在当时是有相当影响的。
例如,唐宪宗时代的李肇(生卒不详),曾著《国史补》一书。
这一书名是大有深意的,说明他已将文学视为历史的、或者说是正史的补充,标志着我国文学的历史本质观的深化。
书中将《庄子》的寓言、沈既济的《枕中记》、韩愈的《毛颖传》等志怪、幻想型作品,统统视为“史”,也许认为文学有补察时政的作用吧,将它们称为国史之“补”,盛赞这些作品的作者为“良史之才”,他所使用的理论范畴,可能是从白居易那里化出,但是,他的文学观,已与白居易那种走写实路子达到历史真实的有所不同。
李肇的文学观,分明是想将整个文学都纳入历史的范畴,而白居易的文学观还仅仅是想将直书时事的文学作品,视为历史。
对历史范畴理解上的含义的广狭之分是很明显的,而李肇的眼光更高远。
由于以较明确的历史的文学观作指导,白居易领导的新乐府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比杜甫元结时,具有更大规模,和更强烈的社会反响。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人们更认识到了杜甫价值,理解了他的情怀,赠予他“诗史”的光辉的名号,本是水到渠成的事,所以孟棨说“当时号为‘诗史’”。
孟棨的记录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这种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说明,唐代是我国文学的历史本质观自觉的时代,杜甫和元结的实录事实,白居易等的新乐府运动,可以说是文学的历史本质观在我国文学史上掀起的第一个高潮。
宋代是一个主理的时代,以议论为诗、以哲理为诗是其主潮,所以,文学的历史属性常被忽略。
但是,还是有不少人认为文学与历史有关。
首先,宋祁(998-1061)在他代表官方撰写的《新唐书》中,再次肯定了杜甫“诗史”的地位。
他说:
(杜)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
--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5][6][7][8][9]下一页这种肯定意义重大:
一是说明唐代的这一文学现象得到了宋代官方的承认,也是得到了历史的肯定;二是说明文学的历史属性通过“诗史”的形式已升华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形态,必然能对后世产生更大的影响;三是说明,在北宋前期,文学的历史本质观还是相当流行的。
例如,被刘克庄称为宋代诗歌“开山祖师”的梅尧臣(1002-1060),他一方面主张“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另一方面又希望诗人们恪守古道,像孔子作《春秋》那样秉笔直书,不著空文。
他在《寄滁州欧阳永叔》一诗中写道:
君才比江海,浩浩观无涯。
······有才苟如此,但恨不勇为。
仲尼著《春秋》,贬骨常苦笞。
后世各有史,善恶亦不遗。
君能切体类,镜照嫫与施。
直词鬼胆惧,微文奸魄悲。
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
唯存先王法,好丑无使疑。
安求一时誉,当期千载知。
梅尧臣的文学主张,说到底,还是儒家的秉笔直书的言史精神。
其中既有孔子、司马迁和杜甫的实录精神,又有白居易不谈“风月”的理论,表现了对传统的文学历史本质观的一脉相承。
再如,作为理学领袖的邵雍(1011-1077),在主张“文以载道”的同时,也提倡“诗史”说。
他在“史笔”与“诗史”之间,更倾向于“诗史”。
他在《诗史吟》一诗中写道:
史笔善记事,长于炫其文;文胜则实丧,徒憎口云云。
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
邵雍发现,以诗为史(即以杜甫创造的“诗史”的形式)可以通过艺术真实达到历史真实,从而留下真实而形象的历史画面,常能比历史书更能反映出历史的本真状态,而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
所以,他赞成“诗史”,并且还将它与绘画相比较,认为:
“诗史善记意,诗画善状情,状情与记意,二者皆能精。
……形容出造化,想象成天地。
体用自此分,鬼神无敢异。
诗者岂于此,史画而已矣。
”[14]从这里透露出,邵雍还有相当高明的理论眼光。
“诗史”的观念之外,他又造出“诗画”的名词,可能专指艺术性的绘画,并认为它和“诗史”一样,都能达到极精极真的境地,与诗史一样,可以描写历史画面,故称“史画”。
这种将文学的历史本质观泛化为艺术观的现象,是极有见地的。
它说明宋人历史的文学观所达到的深度,已非简单的“补察时政”的水平了,而是在写实的领域,对艺术的真实性、典型性有所领悟了。
此外,北宋黄庭坚(1045-1105)也对文学的历史本质观有所领悟。
他首先对杜甫有极精辟的见解。
认为:
由杜子美以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未有升子美之堂者。
……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
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入其门耶?
故使后辈人自求之,则得之深矣。
[15]这段话,自然不能当作纯粹的历史文学观来看,其中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应是其强调的主要方面;但是不管怎样,忠于生活,关心现实的历史主义态度,也必然是这“无意之意”的主要内容。
每当宋人肯定杜甫时,也包括着对杜甫“诗史”地位的肯定。
这里自然也包含着黄庭坚对杜甫“诗史”荣誉的肯定。
我们这样的揣测并非没有根据,黄庭坚不仅像元好问那样认为自己“最知子美”,而且,还对文学的历史本质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他在《廖袁州次韵见答》一诗中,称廖氏之诗为“史笔纵横窥宝铉”,并自注道:
“干宝作《搜神记》,徐铉作《稽神录》,用意亦同。
”他的意思是说,像干宝《搜神记》和徐铉《稽神录》那样的作家和作品,都是具有史家气魄和历史价值的作品。
那么,这样的历史文学观,显然又与杜甫所表现的有着忧国忧民现实情结的历史观有所不同;而却与唐人李肇《国史补》的历史文学观极为相似了,因此也可以说,黄庭坚是在更广义历史文学观的意义上肯定杜甫的,同样表现了宋人理论思考的深入。
南宋时期,文论家仍然喜欢围绕杜甫谈文学的历史属性。
如陈岩肖的《唐溪诗话》,姚宽的《西溪丛话》,黄彻的《鞏溪诗话》,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和洪迈的《容斋续笔》卷二等,都对杜甫“诗史”的地位和成因,进行了评论,说明南宋人对文学历史属性的关注,还是相当普遍的。
而最有代表性的还是诗人陆游(1125-1210)的见解,他强调了社会生活对文学艺术的决定关系,他写道:
必有是实,乃有是文。
……爝火不能为日月之明,瓦釜不能为金石之声,潢污不能为江海之涛澜,犬羊不能为虎豹之炳蔚;而或谓庸人能以浮文眩世,乌有此理也哉?
[16]在这里,陆游已经看出,决定文学有无的是来自社会生活(即历史)的两个方面:
一是其实,二是其人。
前者决定文学的基本内容和形式,后者决定作品的质量和境界。
总之,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都逃不出他们的历史的(即社会生活的)规定性。
而这正是文学总体上具有历史属性的根本原因。
陆游能看到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
陆游对杜甫非常的崇拜,他吟咏道:
“天未丧斯文,杜老乃独出”。
[17]他认为:
“今日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此,且如《岳阳楼》诗……此岂可以出处求哉?
……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亦远矣。
盖后人原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
[18]他批评江西诗派,只知字句,不知杜甫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功夫在诗外”。
他写道:
少陵,天下士也。
早遇明皇、肃宗,官爵虽不尊显,而见知实深,盖尝慨然以稷莴自许。
及落魄巴蜀,感汉昭烈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
顿挫悲壮,反复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
[19]杜诗之所以“顿挫悲壮、反复动人”,在陆游看来原因有三:
一是志意高远,有“不胜爱君忧国之心”;二是见多知广,亲历落魄和离乱之苦;三是悲愤积于中而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和发愤著书的史迁精神。
这三者才是杜甫成功的原因,才是后人应当向杜甫学习的地方。
显然,陆游对杜甫的理解是深刻的,对文学的历史属性的理解也是深刻的。
宋元时期,也是我国小说戏剧形成的时代,人们开始发现小说戏剧与历史的联系。
如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
“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
当时小说又称“讲史”,多取材历史故事。
许多讲者都能“诸史俱通”,“谈论古今,如水之流。
”宋元间人罗烨在《醉翁谈录》也记录了当时人们关于小说的见解。
他在《小说开辟》中说: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
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
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
显然,小说以历史为根基;然而,它又是文学,“论词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文章”;同时它还是表演艺术,“烟粉传奇,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只凭三寸舌”,“自然使席上生风,不枉教座间星拱”。
但是,小说终归是属于历史,它要“讲历代年载废兴,记岁月英雄文武”,形象、生动、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
同时,宋末元初的理学家胡祗遹([!
--empirenews.page--]1227-1293)也在戏剧的领域,探索了戏剧与现实生活(历史)的关系。
他在《赠宋氏序》一文说:
乐者与政通,而伎艺亦随时所尚而变。
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变而为杂剧。
既谓之“杂”,上则朝廷君臣政治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理,殊方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
[20]这里不仅对杂剧之“杂”作了阐释,而且将杂剧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历史属性讲得十分透彻。
胡祗遹对杂剧的论述,绝不是泛泛而谈,他是对杂剧很有研究的理论家。
说明中国戏剧虽然形成较晚,但起点是很高的。
进入明清之后,文学的历史本质观一方面遭到主理派的非议,如明代王廷相说杜甫的言史诗是“骚坛之旁轨”,不算文学正宗;[21]另一方面又受到主情派的攻击,如清人王夫之就嘲笑杜甫以诗为史的作品不是诗。
然而文学的历史本质观却随着小说戏剧的发展而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小说戏剧理论家的核心观点。
而就小说戏剧怎样表现历史真实而言,明清人大致有三派:
第一派认为应当“羽翼信史而不违”。
此见是修髯子(张尚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提出来的。
他写道:
上一页[1][2][3][4][5][6][7][8][9]下一页史氏所志,事鲜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
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櫽栝成编。
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
……是可谓羽翼信史而不违者矣。
这种观点,秉承太史公和杜甫的实录精神,主张一种较狭隘的诗(文学)史混同论,认为小说的题材,必须严格尊重历史事实,不允许有任何虚构。
正如《隋炀帝艳史·凡例》的作者所说:
“虽云小说,然引用故实,悉遵正史,并不巧借一事,妄设一语,以滋世人之惑,故有源有委,可征可据,不独脍炙一时,允足传信千古。
”持类似观点的并非一人,亦非一书,如林瀚(1434-1519)的“正史之补”说,余邵鱼、余象斗等的评论,都大致属于一类。
当然,也有认为可以稍有虚构的人,如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认为,历史小说可以“留心损益”,只要“庶几乎史”就行了,是可以有所虚构的。
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少,有可观道人、陈继儒、甄伟等等,显然,后者较为合理。
第二派认为“劈空捏造”亦能达到高度历史真实。
相传为李贽(1527-1602)所写的《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中说:
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
罗贯中借笔墨粘出。
若夫姓某、明某,不过劈空捏造以实其事耳。
如世上先有淫妇人,然后以杨雄之妻、武松之嫂实之;世上先有马泊六,然后以王婆实之……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亦何能至此哉!
此《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也。
[22]这一观点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