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权力支配下的小农一.docx
《专制权力支配下的小农一.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专制权力支配下的小农一.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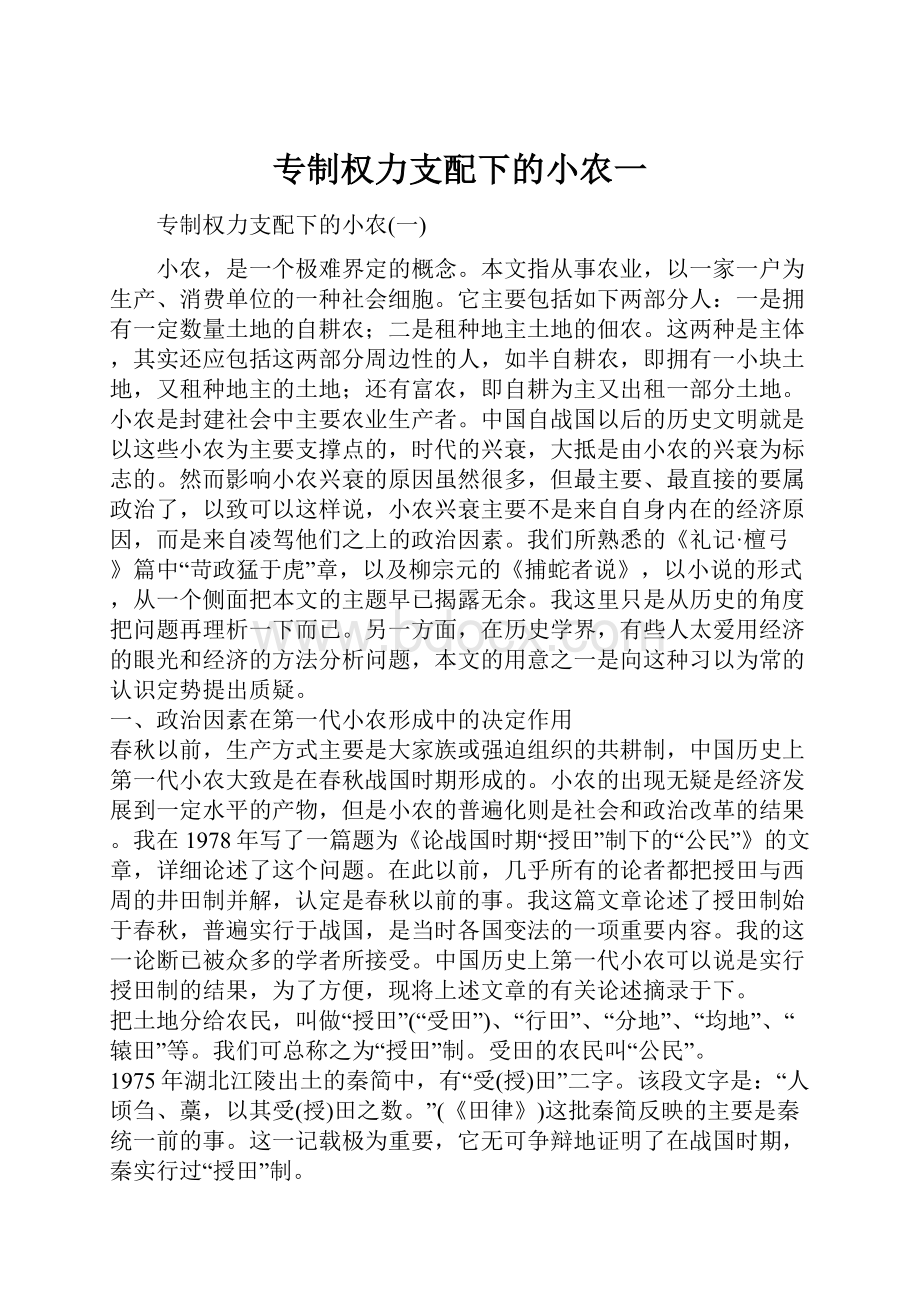
专制权力支配下的小农一
专制权力支配下的小农
(一)
小农,是一个极难界定的概念。
本文指从事农业,以一家一户为生产、消费单位的一种社会细胞。
它主要包括如下两部分人:
一是拥有一定数量土地的自耕农;二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
这两种是主体,其实还应包括这两部分周边性的人,如半自耕农,即拥有一小块土地,又租种地主的土地;还有富农,即自耕为主又出租一部分土地。
小农是封建社会中主要农业生产者。
中国自战国以后的历史文明就是以这些小农为主要支撑点的,时代的兴衰,大抵是由小农的兴衰为标志的。
然而影响小农兴衰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最主要、最直接的要属政治了,以致可以这样说,小农兴衰主要不是来自自身内在的经济原因,而是来自凌驾他们之上的政治因素。
我们所熟悉的《礼记·檀弓》篇中“苛政猛于虎”章,以及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以小说的形式,从一个侧面把本文的主题早已揭露无余。
我这里只是从历史的角度把问题再理析一下而已。
另一方面,在历史学界,有些人太爱用经济的眼光和经济的方法分析问题,本文的用意之一是向这种习以为常的认识定势提出质疑。
一、政治因素在第一代小农形成中的决定作用
春秋以前,生产方式主要是大家族或强迫组织的共耕制,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小农大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
小农的出现无疑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但是小农的普遍化则是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结果。
我在1978年写了一篇题为《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的文章,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
在此以前,几乎所有的论者都把授田与西周的井田制并解,认定是春秋以前的事。
我这篇文章论述了授田制始于春秋,普遍实行于战国,是当时各国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的这一论断已被众多的学者所接受。
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小农可以说是实行授田制的结果,为了方便,现将上述文章的有关论述摘录于下。
把土地分给农民,叫做“授田”(“受田”)、“行田”、“分地”、“均地”、“辕田”等。
我们可总称之为“授田”制。
受田的农民叫“公民”。
197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秦简中,有“受(授)田”二字。
该段文字是:
“人顷刍、藁,以其受(授)田之数。
”(《田律》)这批秦简反映的主要是秦统一前的事。
这一记载极为重要,它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在战国时期,秦实行过“授田”制。
魏国的“行田”也是“授田”。
《吕氏春秋·乐成》引魏襄王的名臣史起的话:
“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
”“行田”就是分给土地的意思。
《汉书·高帝纪》:
“法以有功劳行田宅。
”苏林注:
“行,……犹付与也。
”根据《乐成》的记载,魏国是普遍实行过“行田”的。
它应是李悝“尽地力之教”的主要内容。
如果把“行田”同梁惠王关于凶年移民之事一并加以考察,我认为,说梁惠王(即魏惠王)的移民以“行田”为基础不是勉强的。
孟轲到齐国,对齐宣王讲的关于“制民之产”一段话也很耐人寻味。
“制”即制定、规定之意。
“产”指什幺?
即文中所讲的“恒产”一“五亩之宅”、“百亩之田”。
“制”的主体是谁呢?
文中已点清楚,是君主。
民产由君主规定,那幺把它解释为类似秦的“授田”、魏的“行田”,我想是可以说得通的1]。
《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秦商鞅变法有一项是“制辕田”。
再早,晋在春秋时曾“作爰田”2]。
辕与爰通用。
关于“爰田”历来有不同释解。
孟康的注是,把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授给农民。
上田每产百亩,中田二百亩,下田三百亩。
根据孟康的注,“制辕田”也就是“授田”,同秦简中,“受(授)田”是吻合的。
另外《管子·国蓄》中讲的“分地”,《臣乘马》中讲的“均地”,《商君书·算地》中讲的“分田”,我认为都是“授田”,的别称。
关于战国存在“授田”制的事实,还可从许行到滕受廛一事得到旁证。
农家学派的许行自楚到滕,对滕文公说“愿受一廛而为氓”3]。
滕文公给了他“廛”。
廛是住宅,属封建国家。
许行受没受田,种不种地呢?
文中没有明讲,但在孟轲与陈相的对话中,谈到了许行之徒是从事耕种的。
许行等耕种的土地从哪里来的?
同廛一样,一定也是从滕文公那里领受的。
一个农民授与多少土地呢?
大体是一百亩(约合今三十一亩多)。
在当时,这同一个农民的劳动力是适应的。
《管子·臣乘马》说:
“一农之量,壤百亩也”。
《山权数》说:
“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
先秦文献中关于一夫百亩的记载很多:
“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4]。
“百亩之田,勿夺其食,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
“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
”6]
《汉书·食货志》记述魏李悝变法,实行尽地力之教,也是按一夫治田百亩计算。
授田百亩是当时的惯例,所以又有“分地若一”之说7]。
先秦文献普遍讲一夫百亩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实行“授田”制的反映。
“百亩”是指针准地。
土地有好有坏,具体实行时会五花八门。
如前引的,魏一般分给百亩,邺这个地方土质不好便分配二百亩。
另外,各地亩大小也不一致,《商君书·算地》记载:
“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
江陵出土秦简中的“受(授)田”,则是按顷计算。
受田的农民有没有土地所有权,能不能私自转送或买卖呢?
关于这一点无明文记载。
但以下材料从侧面说明没有土地所有权。
1.“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举”8]。
这襄对田用的是“弃”,对宅圃(宅旁园地)用的是“卖”。
从侧面说明土地不能卖。
2.《管子·小称》记载,民恶其上,“捐其地而走”。
“捐”是放弃的意思,与前一条材料意思相同。
3.“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9]”照理土地比农具更为重要。
如果土地属农夫,决不会不卖土地,扛上农具就到他国去。
显然,农具属农夫所有,土地不属农夫。
4.战国文献有多处讲到民无法生活时嫁妻卖子。
但没有一条言及卖土地。
这同汉以后多把卖田同嫁妻鬻子连在一起,有明显的不同。
如果拥有土地所有权,通常总是先卖土地而后卖子女。
战国时材料只讲民嫁妻卖子,说明民卖土地的现象还不多见。
5.《庄子·徐无鬼》篇讲:
“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恶则散。
”这段文字形容民之来去未免太自由了。
但在当时民逃来逃去的现象的确很普遍,这些逃亡之民被称之为“氓”。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我认为,民无土地所有权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些逃亡之民只要不被原主人捉住,便可在新主人那襄领受一小块土地。
民大量的逃亡,使统治者很头痛。
为了把民固着于土地,一些统治阶级代表人物,除提出加强行政管理外,在经济上还提出了种种方案。
孟轲提出要使民有“恒产”,有了恒产“才能有”“恒心”。
《吕氏春秋·上农》篇提出:
“民农则其产复(即富),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
”大约到了战国后期,农民对所受之田有了较稳定的占有权。
大约也是在此时期出现了土地的买卖。
秦始皇推行“令民自实田”之后,土地的私有成份增加了,原来受田的农民变为拥有一部分土地的自耕农。
由于第一代农民大部分是由国家“授田”而形成的,加之以后又有多次用权力调整、重新分配土地政策(也可称之为“制度”)出台,在法权上从来没规定土地私有权是不可侵犯的,尽管土地可以买卖,在观念上和事实(一定时期)上,土地最高、最后所有权属于国家,属于君主。
我之所以把第一代农民的形成单列出来,一方面它具有原型的意义;另一方面,在社会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它的性格具有遗传的意义。
其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大改说来是承袭了战国、秦汉历史的模式。
二、专制权力支配人身中的小农
从解剖生产关系入手,可以洞察资本主义的全部秘密。
但是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却是不能完全达到这一目的的。
因为,前者是经济关系制约的社会,后者则是暴力(政治权力)支配着社会的生产和生活。
几千年来的中国专制统治者都把控制人民和占有土地视为同等重要的事情。
《诗经》上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10]可见早自周天子开始,就明确宣布了国家对全国范围内的土地、人民有无可争议的最高所有权和支配权,孟子说:
“诸侯之宝三一土地,人民,政事。
”11]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了中央集权时代以后,仍然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12]。
与周天子口号完全一致。
在土地和生产者两项中,封建国家尤其注重对生产者的支配。
他们说,“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
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
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
”13]就是说,能够控制天下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了他的百姓的人。
能够战胜强敌的人,一定是首先战胜了他的人民的人。
因此战胜人民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制服民众,就象冶炼工人随心所欲地将金属熔之于炉、煅之于砧,制陶工人任意地揉搓泥土,以造出符合他们任何意志需要的器具来一样。
“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14]控制了人民,自然就控制了土地,就会生出各种财富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为了强化对生产者人身的控制,历代王朝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严密的政治统治系统和庞大的常备军。
而在基屑社会直接施诸人身的措施,则是加强户籍管理,严密什伍里甲制度,控制社会谋生途径,运用政治组织措施迫使整个社会生活的政治化以及在法制上实行连坐制度等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统计并制定和执行一套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
由于上交到中央的户籍簿册一律都规定用黄色的封面,所以户籍又称黄籍或黄册。
“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
”15]加强户籍管理从来都是历代统治者管理国家和控制人身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作为“编户齐民”的户籍制度,是同“授田制”的实行,小农的普遍化同时发展起来的。
战国时的户籍大致可以勾勒如下:
“户籍”对各户人口、劳力状况、财产,均有详细登记: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着,死者削。
”16]
“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
其不为用者辄免之,有锢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
并行以定甲士,当被兵之数,上其都。
”17]
“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君实乡卅藏焉。
”18]
“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
”19]
地方官吏的一项主要任务便是核查核对户籍。
《管子·立政》中提出要“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着。
”农民不准自由迁徙,《商君书·垦令》中提出“民不得擅徙”。
《管子·禁藏》中提出“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
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
”逃亡者被捉住要给以严厉的惩处,“逃徙者刑”20]魏设有《奔命律》,便是专门惩治逃亡的法律。
江陵出土的秦律中有一条规定:
“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
”21]这条的大意:
秦国原来的人(以别外来户)逃亡被捉住,上造(军爵中的第二级)以上罚服三年砍柴苦役,公士(第一级,最低的)及以无爵之民,要罚服四至五年筑城的苦役。
民出入邑里,都有有司、里正、伍老之类的小吏监督。
《管子·立政》有如下的描述:
邑里“筑障塞匿,一道路,专出入。
审闾开,慎管键,管藏于里尉。
置闾有司,以时开闭。
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间有司见之,复无时。
”看,多幺严紧啊!
对农民的生产劳动也有严格的监督。
文献中多有记述,择其要者抄录于下:
“贤者之治邑也,早出暮入,耕稼树艺聚菽粟……”22]
“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均修焉。
劝勉而姓,使力作勿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
”23]
“相高下,视肥硗,序五种,省农功,谨蓄藏,以时修顺,使农夫朴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
”24]
《吕氏春秋》和《礼记·月令》按季、按月提出对农民生产进行监督。
《吕氏春秋》中还具体地提出,春天令“耕者少舍”,夏天“命农勉作,无伏于都”,即一律搬到田野庐舍中去住。
秦律中规定:
“百姓居田舍毋敢醢(酤)酉(酒)。
田啬夫、部佐谨御之,有不从者(罪)”25]监督是何等的严啊!
为了保证国家税收有源头,农民必须有收成。
《吕氏春秋·孟春》中主张,开舂要“先定准直”,即规定产量,李悝实行“尽地力之教”,也规定了每亩的标准产量。
各国还有专门法律规定惩罚不勤力耕种者。
《管子·大匡》中提出耕者“用力不农(义为勉)”,“有罪无赦。
”《吕氏春秋·上农》中说:
“民不力田,墨(没收)乃家畜。
”更有甚者,商鞅变法中规定“怠而贫者,举以为孥。
”26]国家控制的“公民”还常常作为君主的赏品,赐给功臣权贵宠幸。
逭中又可分为几种不同情况:
一是连同土地和部分行政权一同赏赐,这叫“赐邑”。
二是把“公民”向国家交纳的租税赐给受赏者,这叫“赐税”。
三是作为受赏者的“隶家”。
秦规定军士斩敌“五甲首而隶五家。
”27]这种“隶家”并不是奴隶,而类似《商君书·境内》篇中讲的庶子。
庶子每月无偿地服役六天。
总之,“公民”没有人身自由,完全依附于封建国家。
秦汉以后的户籍,比战国更严密、完善。
汉代法定每年八月,县都要案产比民。
案比之时,境中所有民产,不分男女老幼,都要整家地前往县府,聚集庭中,由主管官吏将每一个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身材的高矮、胖瘦和长相,以及有无特殊的生理标志等等,一一查验明白,然后重新造册,在年终时由乡县上报所属郡国,郡国再上报朝廷。
这种案户比民的做法当时称为“算民”。
这种户口簿籍当时称为“名数”。
这种户口的按时上报制度和垦田、钱谷出入的按时上报制度一起,称为“上计”。
隋唐时期的“貌阅”、“团貌”,是汉代案比制度的继续和发展。
主管官吏在案比、貌阅中如果发生作弊情事,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隋文帝开皇五年(公元585)下令州县大索貌阅,凡是查出产口不实的,乡正、里长都要发配到边远地方。
户籍制是一套严密控制人身的组织系统,将每一个村邑、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毫无遗漏地织人国家行政网络之内。
它远远超出了一般行政管理的范围,而成为君主国家控制生产者、奴役生产者的重要工具。
君主国家的一切赋税和徭役,都要根据地籍和户籍摊派下去和征发上来。
周秦以至隋唐,国家计丁授田,按产、按床征发租、庸、调,显然完全是以人丁作为主要依据28]杨炎推行两税法以后,虽然开始把土地因素考虑进来,但也只是根据人丁、土地两项标准定赋,所谓“产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29]人丁仍然是国家制订赋役的主要依据之一。
直到明代,情况还是:
以鱼鳞册为经来登载人们的土地占有,以黄册为纬来确定人们的赋役负担30]。
清代在其立国之初,就承袭明制编篡《赋役全书》,立鱼鳞册和黄册与之相表裹。
可见,集权国家的赋役之征从来也不曾脱离过人身,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主要是通过人身控制的政治途径来实现的。
户籍同时又是控制谋生之路的机构。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满足自身的剥削贪欲和巩固既得的特权地位,总是竭力运用政治统治力量控扼经济趋势,障塞通往工商的大门,把人民都驱迫到务农这条路上来。
他们认为,“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
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上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买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可以糊口也,则以避农。
避农,则民轻其居。
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31]要使民俯首听命于君,就要牢握予夺之柄,控制人民的生存命脉,做到“利出一孔”32]。
“私利塞于外,则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
”33]“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养,隘其利途。
故予之在君之,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
故人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34]正是出于这一动机,历代无不奉行“崇本抑末”之策,在很多朝代里都有国家“下令禁民二业”35]的情形,凡是国家分予土地令其务农的人,就不再允许他们从事捕鱼、打猎等等副业活动。
宋代的石介说,“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茗皆有禁,布绵丝枲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36]这是历代同共的现象。
贾谊曾经建议汉文帝,欲使国家富强,根本措施在于“殴民而归之农,皆着于本”37]“殴民归农”一语,就充分地表现出了政治支配形态下农民与土地结合的很大程度的强制性和被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