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洪托夫上古汉语的唇化元音.docx
《雅洪托夫上古汉语的唇化元音.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雅洪托夫上古汉语的唇化元音.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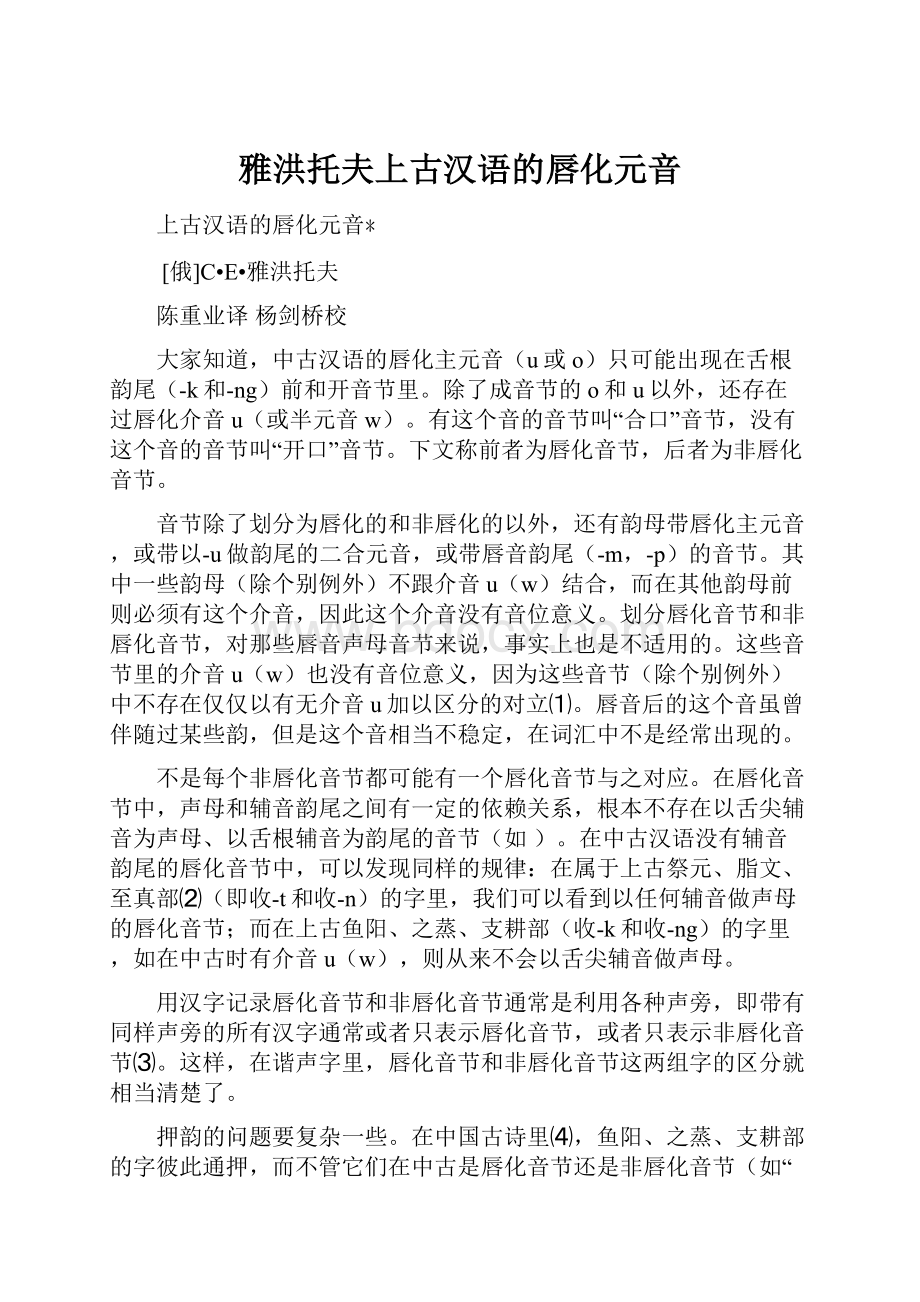
雅洪托夫上古汉语的唇化元音
上古汉语的唇化元音﹡
[俄]C•E•雅洪托夫
陈重业译杨剑桥校
大家知道,中古汉语的唇化主元音(u或o)只可能出现在舌根韵尾(‐k和‐ng)前和开音节里。
除了成音节的o和u以外,还存在过唇化介音u(或半元音w)。
有这个音的音节叫“合口”音节,没有这个音的音节叫“开口”音节。
下文称前者为唇化音节,后者为非唇化音节。
音节除了划分为唇化的和非唇化的以外,还有韵母带唇化主元音,或带以‐u做韵尾的二合元音,或带唇音韵尾(‐m,‐p)的音节。
其中一些韵母(除个别例外)不跟介音u(w)结合,而在其他韵母前则必须有这个介音,因此这个介音没有音位意义。
划分唇化音节和非唇化音节,对那些唇音声母音节来说,事实上也是不适用的。
这些音节里的介音u(w)也没有音位意义,因为这些音节(除个别例外)中不存在仅仅以有无介音u加以区分的对立⑴。
唇音后的这个音虽曾伴随过某些韵,但是这个音相当不稳定,在词汇中不是经常出现的。
不是每个非唇化音节都可能有一个唇化音节与之对应。
在唇化音节中,声母和辅音韵尾之间有一定的依赖关系,根本不存在以舌尖辅音为声母、以舌根辅音为韵尾的音节(如)。
在中古汉语没有辅音韵尾的唇化音节中,可以发现同样的规律:
在属于上古祭元、脂文、至真部⑵(即收‐t和收‐n)的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以任何辅音做声母的唇化音节;而在上古鱼阳、之蒸、支耕部(收‐k和收‐ng)的字里,如在中古时有介音u(w),则从来不会以舌尖辅音做声母。
用汉字记录唇化音节和非唇化音节通常是利用各种声旁,即带有同样声旁的所有汉字通常或者只表示唇化音节,或者只表示非唇化音节⑶。
这样,在谐声字里,唇化音节和非唇化音节这两组字的区分就相当清楚了。
押韵的问题要复杂一些。
在中国古诗里⑷,鱼阳、之蒸、支耕部的字彼此通押,而不管它们在中古是唇化音节还是非唇化音节(如“冈”与“黄”通押等等)。
在上述韵部里,很难找到带介音u(w)的字彼此押韵而不跟不带这个介音的字相押的例子。
相反,在祭元、脂文、至真部,唇化音节多半只能跟同是唇化音节的字相押,例如:
出律滑拙(《荀子•成相》五十五节);
川焚熏闻遁(《大雅•云汉》五章);
轮唇沦囷鹑飧(《魏风•伐檀》三章);
娈婉选贯反乱(《齐风•猗嗟》三章)
在祭元、脂文、至真部里,几乎所有以舌尖辅音做声母的唇化音节都跟其他唇化音节相押;但那些以舌根辅音或唇辅音做声母的唇化音节,则部分跟唇化音节相押,部分跟非唇化音节相押。
上古汉语里在同韵部、同声调的条件下下列类型的音节相互押韵⑸:
(a)TONG,KONG,PONG;
(b)TENG,KENG,KWENG,P(W)ENG;
(c)TWEN,KWEN(部分音节),P(W)EN(部分音节);
(d)TEN,KEN,KWEN(部分音节),P(W)EN(部分音节)。
c组通常不跟d组押韵,即使同韵部同声调也不行。
大家知道,上古汉语的介音﹡i、,无论对押韵还是对谐声都没有产生过任何影响。
那么,为什么那些通常认为以介音﹡w跟非唇化音节相区别的唇化音节,几乎从来不跟那些非唇化音节谐声,甚至常常不跟非唇化音节押韵呢?
为什么半元音﹡w有跟介音﹡i和﹡i不同的特性呢?
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
上古汉语里实际上不存在这一假设的介音﹡w。
c组字里跟韵有关的唇化成分不是介音,而是主元音。
在唇化音节跟非唇化音节可以通押的b组和d组里,唇化只影响到谐声,唇的动作是声母发音动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两组的唇化音节里不是舌根声母带介音,而是圆唇舌根声母kw、gw、xw等等⑹。
的确,声母的区别并不影响押韵,但可能成为使用不同声旁的原因。
主元音的区别则跟押韵有关,也跟声旁的使用有关。
由此可见,上古汉语的c组字有过唇化主元音,这些音构成TON型、KON型、PON型,而不是前面所列出的TWEN型、KWEN型、P(W)EN型。
这里还要指出,b组和d组完全对应,其区别仅在于辅音韵尾(b组是舌根韵尾或没有辅音韵尾,而d组是舌尖韵尾)。
按照人们迄今所采用的构拟,a组和c组之间很少有共同之处;但是如果c组确实有过唇化元音,那么这两组之间的对应关系就会跟b组和d组之间的对应关系完全一样,于是所有四组音节便会构成一个相当整齐的系统。
只有一种情况破坏了这一整齐的系统:
圆唇舌根声母只出现在b组和d组,即它们不可能跟唇化元音相结合。
现在让我们来具体说明,祭元、脂文、至真部里有哪些字进入了c组,哪些字进入了d组。
换句话说,到底哪些字的主元音是唇化音,哪些字的主元音是非唇化音。
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字的上古音可以根据下面一些规律按其中古音来确定:
1.中古汉语的非唇化音节无疑来源于上古带某种非唇化元音的音节。
只是对以唇音做声母的音节不能绝对地作出这种结论,因为如我们所知,唇音声母后的唇化介音成分是不稳定的。
因此,以唇音做声母的音节在中古一般很难分为唇化音节和非唇化音节这两种类型。
2.以舌尖音做声母的音节,通常只在上古有唇化元音的音节里出现唇化。
3.零声母(即“喻”母)的唇化音节有两个来源,这取决于它们是三等字还是四等字。
多数研究者认为,零声母来源于上古的浊辅音(擦音或不送气塞音)。
零声母的三等字(有个别例外)含唇化元音或唇化半元音,它们可以跟中古以舌根音做声母的唇化音节有相同的声旁。
三等字的零声母从来不出现在侯东、幽中和宵部(即明显带有唇化主元音的音节)里。
显然,三等字的零声母来源于上古的圆唇舌根音﹡gw或﹡γw,并且由于圆唇舌根音不可能跟唇化主元音相结合,所以这些音节在上古有过非唇化主元音。
根据高本汉的见解,四等字的零声母来源于上古的﹡d-或﹡z-。
看来,在有些地方四等字的零声母实际上也来源于﹡g-(即舌根音,而不是圆唇舌根音)。
不管怎样,四等字的唇化不可能是在声母的影响下产生的,它们在上古应该有过唇化主元音。
这三条普遍规律有几个例外。
第一,有这样的情况:
中古以舌根辅音(通常是x-和γ-)做声母的唇化主元音,同以s-或z-做声母的唇化音节谐声。
如:
歲:
噦
旬,询:
绚
血:
恤
咺:
狟
惠:
穗
還:
(一字两读)
在中国古诗中,声旁是“歲、旬、血、亘、惠、睘”的字,不管它们在中古是什么声母,总是跟上古有非唇化元音的音节相押⑺。
因此,在这些音节里首先唇化的不是元音,而是声母。
也许,在这些情况下中古的s-和z-来源于﹡sxw-和﹡zgw-之类的复辅音(不过也可能有其他较复杂的解释方法)。
总之,这些音节在上古曾经有过非唇化主元音,而不是唇化主元音。
第二,在两个字——“泉”、“存”里,唇化产生较晚,这是不规则的语音变化。
这两个字在上古只跟有非唇化元音的音节相押。
此外,“泉”是“線”的声旁,“存”是“荐”和几个有同样读音的字的声旁;而“存”本身最初的声旁是“才”。
由此可见,无论是押韵,还是形声字都表明,“泉”和“存”在上古有过非唇化主元音(读音分别为和)。
最后,“维wi”和“惟wi”这两个字不知为什么会跟非唇化音节押韵⑻,虽然这些字属于四等字(而且,根据其声旁判断,在上古它们的声母应为舌尖音)。
我们不清楚这两个字在上古究竟怎么念。
至于祭元、脂文、至真部中的那些曾以唇音做声母的字,由于这些字中的唇化介音成分不稳定,所以不可能根据这些字的中古音来探明其上古音。
中古以舌根音做声母的唇化音节字也是这样,这些字中的唇化可能有两种来源———或来源于唇化主元音,或是在圆唇舌根声母的影响下产生的。
以唇音、舌根音做声母的两组字中,只有个别字根据其声旁能够比较容易地确定其上古音。
例如,假使同一个声旁既用来表示那些根据我们的构拟上古曾以﹡gw-做声母的字,又用来表示那些中古以舌根音做声母的字,那么自然可以假定,所有这些字在上古都曾以圆唇舌根音做声母,因而也曾有过非唇化元音。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声旁是“韦、军、爰、亘”的字。
其次,如果一组谐声字既有声母为舌尖音的字,又有声母为舌根音或唇音的字,那么这组字的元音应该是一样的(如果这组字不仅声母各异,而且元音也不同,那么这组字根本不会谐声)。
如“邁”,照《说文》可写作带声母“蠆”⑼;也就是说,“邁”字应该跟“蠆”字一样,曾经有过非唇化主元音。
“蛮”、“变”跟“娈”字有同一声旁,因此它们都曾有过唇化主元音。
声旁为“出”的“屈”中也曾有过唇化元音。
最后,还要谈一下“貴”这个声旁。
它主要用在以舌根音做声母的字中,但我发现,看来它也是“隤”字的声旁。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声旁为“貴”的那些字在上古也应该有过唇化主元音。
分析形声字后得出的所有这些结论,在《诗经》和《易经》的运用中都得到了证实⑽。
要确定其他那些中古声母为舌根音(在唇化音节里)和唇音的字的上古音,根据任何一条普遍的规律都是行不通的。
我不得不根据古诗用韵逐个确定每个字的读音。
但在这样做以前,我想对我已确定其上古音的一些字作一些概括性说明。
根据中古音或声旁,我发现上古有唇化主元音的所有字都在祭元部和脂文部,而不在至真部。
至真部中以舌尖辅音,并且只以s-或z-作声母的唇化音节很少。
这些字有声旁“血”和“旬”。
因此,正如上文已经说过的,这些字在上古有过非唇化主元音。
至真部里其它类型的唇化音节也不多,而且能够跟非唇化音节通押。
看来,上古至真部里根本没有含唇化主元音的音节,因此下文将只研究祭元部和脂文部。
祭元部和脂文部中那些上文已得出结论、在上古有过唇化音的字有规律地跟其他有唇化音的字相押。
在本文所查考过的上古文献资料里可以找到五十多个例子,其中那些明显有过唇化主元音的字彼此相押⑾,如:
《国风》的《周南•卷耳》二章,《周南•樛木》首章,《周南•芣苢》二章,《召南•草虫》二章,《召南•野有死麕》三章,《邶风•柏舟》三章,《邶风•日月》四章,《邶风•北门》三章,《齐风•南山》首章,《齐风•敝笱》三章,《齐风•猗嗟》三章,《魏风•伐檀》三章,《陈风•墓门》二章,《檜风•素冠》首章,《曹风•蜉蝣》三章;
《小雅》的《南有嘉鱼》三章,《采芑》四章,《沔水》首章,《雨无正》四章、五章,《谷风》二章,《蓼莪》五章,《鸳鸯》四章,《都人士》二章,《渐渐之石》二章;
《大雅》的《緜》八章,《既醉》五章,《公刘》六章,《荡》三章,《桑柔》十三章,《云汉》三章、五章,《瞻卬》二章、五章;
《周颂》的《有客》三章;
《鲁颂》的《閟宫》三章⑿;
《易经》中《蒙》、《颂》、《颐》、《家人》、《蹇》、《萃》、《渐》诸篇里的韵文;
《庄子》中《齐物论》的“为其吻合,置其滑涽,以隶相尊。
众人役役,圣人愚芚,参万岁而一成纯。
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人间世》的“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
来世不可待,往事不可追也”,《大宗师》的“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
《荀子•成相》的九、十一、五十五、五十六节;
《老子》的五、四十一、四十五、五十四、五十六章。
根据上面分析过的特征,上古具有非唇化音节的字彼此间更是经常相押(仅《诗经》中就可以找到一百多个例子⒀)。
祭元部和脂文部里唇化音节跟唇化音节相押(非唇化音节也相应地跟非唇化音节相押)的例子,在我没有全面查考的其他古籍中也常常遇到。
譬如,我发现《孟子•公孙丑上》中“类萃”相押(“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礼记•檀弓下》中“緌衰”
相押(“范则冠而蝉有緌,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
在《诗经》里只能找到为数不多的例外,即上古曾明显带唇化主元音的字跟无疑曾带非唇化主元音的字相押。
下面三个例子(都是脂部上声字)就属于这种例外:
藟弟(《王风•葛藟》首章至三章);
水弟(《郑风•扬之水》首章及二章);
水隼弟乱(《小雅•沔水》首章)⒁。
脂部带唇化元音的上声字,除了三四个例外,都很少使用,因此很难从中找到相押而又合适的字。
它们通常或跟其他声调的字相押(如《小雅•巧言》首章),或跟别的韵部的字相押(如《小雅•沔水》首章),或跟声调和韵部都相同、但带非唇化主元音的使用极广的“弟”字相押(如上引例)⒂。
它们只在一处彼此相押,而不是跟别的韵部的字相押(见《齐风•敝笱》三章)⒃。
还有三个例外(其中第一个例子前面已提到过了):
穗醉(《王风•黍离》二章);
棣檖醉(《秦风•晨风》三章);
愆孙(《小雅•楚茨》四章)
此外,有几个例子似乎是例外,实际上大概不是。
例如,人们通常认为,《邶风•谷风》六章“溃肄墍”彼此相押。
这里“溃”字按照其声旁在上古应带唇化元音,故应跟另外两个字有区别,因此该例似乎是例外。
但该诗中无论哪一章都不是这样三句相押,多数地方奇数句既不跟偶数句押韵,奇数句本身也互不押韵。
既然“溃”是该章第五句的末字,而另外两个字是第六句和第八句的末字,那么很可能“溃”不跟另外两个字押韵。
段玉裁所指出的《周南•螽斯》首章、《邶风•雄雉》二章、《周颂•有客》三章押韵的地方也是这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例外(可跟高本汉对这些诗句的解释比较)。
《齐风•甫田》三章里可能不是四句为韵,而是每两句单独为韵,那么这也不是例外。
最后,有个迥非寻常的例子:
瀌消遗骄(《小雅•角弓》七章)。
这里脂文部的唇化音节跟宵部音节(带唇化音节,但上古没有辅音韵尾)相押。
《大雅•桑柔》八章的韵“君犹顺”也许跟这类似(该诗每章都有八句,奇数句彼此相押。
第八章中“君”、“犹”、“顺”分别是一、三、五句的末字,尽管并没有一贯到底地与第七句的末字“肠”押韵)。
这里也是同属脂文部的两个字跟幽中部的一个字相押。
《易经》里我们也遇到几处(见《临》、《明夷》、《解》诸篇的韵文)唇化音节(属于前面谈到过的那些音节)跟非唇化音节相押。
但总的说来,《易经》中有很多押韵不准确的地方⒄。
《老子》中这样的地方还要多(十五、十八、六十二、六十四、七十章)。
不过我们已经知道,这一著作是不完全可靠的。
由此可见,在我们所查考过的公元前一千年的韵文中,以舌尖音(一部分以其他辅音)为声母的带唇化元音的音节跟带非唇化元音的音节是区分得十分清楚的。
诚然,在其他某些古籍中看不到这一现象。
在《楚辞》、《庄子•外篇》和《庄子•杂篇》,也许还在《左传》和《论语》的某些篇章中,唇化音节和非唇化音节彼此间可以任意通押。
这一点是否可以用方言的差别来解释,或者是由上述各部著作的写作时间所决定,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这个问题还有待研究。
现在来研究一下祭元部和脂文部里中古有舌根声母和唇化介音、或者有唇音声母的那些字的上古音。
应该指出,在这些字中,上古带唇化元音的音节跟带非唇化元音的音节之间的差别远不是那么清楚的。
跟上古带非唇化主元音的字相押的字,有一些与之对应的声旁,这些声旁是可以相当清楚地分出的(下面在每个声旁后先指出我所查考过的古籍中含有这些声旁的字的数字⒅,接着指出这些字跟带非唇化主元音的字押韵的次数,最后是例外,也就是这些字跟带唇化主元音的字押韵的情况⒆):
发(3,12);伐(2,3);烕(2,3);半(2,3);番(4,5);
反(3,11,例外:
《齐风•猗嗟》三章);非(5,15);微(2,6);
匕、比(6,8,例外:
《大雅•皇矣》四章);畀(2,3);米(2,3);
眉(3,3);分(5,7);舌(4,5,例外:
《邶风•击鼓》四章⒇);
厥(3,6,例外:
《召南•草虫》二章);肙(3,3)〔21〕;
官(2,4,例外:
《邶风•静女》二章及《大雅•公刘》六章);
卷(3,3,例外:
《邶风•柏舟》三章);癸(3,7)。
下列字也跟曾带非唇化主元音的字押韵:
败(7);蔽
(1);闭
(1);飞(6);樊
(1);繁
(1);弁
(1);辩
(1);
翩
(1);枚(4);尾(4);美
(1);瀰
(1);火(3);燬
(1);忽
(1);
亹
(1);文
(2);快
(1);外(10);月(5);宽
(1);涣
(2);丸
(1);
冋(4);归(23,例外:
《齐风•南山》首章,《大雅•泂酌》二章及《荀子•成相》“世
之衰,谗人归”);嘒
(2);壶
(1);鳏
(1)。
这其中一部分不是形声字,另一部分字属形声字,但是在我查考过的文献中没有其他字带这些声旁。
带唇化主元音型的音节的声旁较少见到(下面列出带这些声旁的字跟曾带唇化主元音的字押韵的次数,在例外中则指出这些字跟曾带非唇化主元音的字押韵的地方):
夗、宛(3,4,例外:
《卫风·氓》六章);元、完(2,2);褱(2,9);季(2,3,例外:
《魏风·陟岵》二章);昷(2,2);囷(2,2);君(2,7)〔22〕。
所有这些字的声母都不是唇音,而是舌根音(或者是喉塞音)。
下列不多的几个字属于这一类:
喙
(1);贯
(2);畏(4);威(3,例外:
《周颂·有客》三章)〔23〕;萎
(1);蔚
(2);嵬
(2);滑
(1);昆
(1);训
(1)。
这两组字中大部分极少作韵脚,但这些字里元音的唇化性质在好些场合可由其他材料得到证实,如下述叠韵字:
婉娈〔24〕;畏隹(?
)(《庄子·齐物论》:
“山林之畏隹。
”);崔嵬;陮隗(《说文》);昆仑。
这些叠韵词里各有一个字声母为舌尖音,因此在上古有唇化主元音;而另一个字则同这个字叠韵,因此有相同的元音。
又如:
“委”在“緌”这个声母为舌尖音的唇化音节字中作声旁。
此外,我发现“完”是“寇”字(侯东部)的声旁,“昷”是“媪”字(幽中部)的声旁〔25〕,而侯东部和幽中部的字是有唇化元音的。
所有这些事实也证明,声旁为“畏委鬼昷昆夗元”的字里的确有过唇化主元音〔26〕。
有几个声母为唇音的字也只跟有过唇化元音的字相押:
吠
(1);悖(4,但只有《易经·解》一处:
“公用射隼,以鲜悖也”,40——这个字同时跟有过非唇化主元音的字押韵);拜
(1);浼
(1);没
(1);焚
(2);璊
(1)。
韵脚里只出现一次的字一般都属于这一类。
至于其他那些声母曾为唇音的字,情况要复杂一些。
如果这些字跟那些曾有过唇化主元音的音节相押,那么总可以找到它们跟那些曾有过非唇化主元音的音节相押的例子,或者至少可以找到与这些字并存的另一些字,它们有同样的声旁,但跟那些曾带非唇化主元音的音节相押。
中古声母为舌根音的字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例如,跟上古曾带唇化元音的音节押韵的字有:
拔
(2);髮
(1);旆
(2);芾
(1);末
(1);弗
(1);寐
(2);缦
(1);奔
(2);问
(2);闻
(2);緡
(1);
(1);愿(6);熏
(1)。
跟上古曾带非唇化元音的音节押韵的字有:
茇
(1);軷
(1);旆
(1);肺
(1);秣
(1);拂、茀
(1);妹
(1);寐
(2);慢
(1);本
(1);門(6);痻
(1);關
(1);原(6);嫄
(1);熏
(1)〔27〕。
此外,“寐”在一个地方同时跟KEN型音节和KON型音节押韵(《魏风·陟岵》二章)。
因此,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声旁为“市末弗曼本門昏原熏”的字里有过什么元音。
可能在《诗经》时代,PON型音节里(以及个别的KON型音节里)唇化元音可由非唇化元音代替〔28〕。
因此这些字有时跟带唇化元音的字相押,有时则跟带非唇化元音的字相押。
唇音和舌根音后面的唇化元音跟非唇化元音的混用,有时也可在其他韵部看到。
例如“裘”跟(有非唇化元音的)之蒸部字相押,而带同一声旁的另一些字却跟(有唇化元音的)幽中部字相押。
大家知道,所有学者都将祭元部和脂文部的字(至少将这些韵部的大多数字)分别构拟为元音﹡a(或﹡α)和﹡。
但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
这些字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在上古曾有过某种别的元音,即唇化元音,而这些唇化元音在中古被唇化介音跟非唇化主元音的复合形式所取代。
脂文部〔29〕里的唇化元音无疑曾经是*u。
我们从近代汉语史里可以见到闭音节中u→
或u→的变化(如北京话“翁”〔30〕来自中古汉语的,北京话“蒙”来自中古汉语的mung)。
祭元部的唇化元音应该多少接近于a,可能是开口较大的*o〔31〕。
此外,祭元部的唇化元音跟侯东部的元音曾经是相同的。
这两个韵部的字有时有相同的声旁。
例如:
“短tuαn2(*tơn2)”的声旁是“豆”;“蕞”〔32〕和“最tsuαi3(*tsot-s)”的声旁是“取”;“畽thuαn2(*thơn2)”〔33〕的声旁是“重”;“寇”的声旁是“完γuαn(ghon*)”。
既然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同声旁的字辅音韵尾不同(上面四组字里在三组字中各有一字,即“豆”、“取”、“寇”从来没有辅音韵尾),那么其中的元音应该吻合,不然这些字未必能使用相同的声旁。
由此可见,侯东部的字里曾有元音*o(这是王力的构拟)。
这个元音跟祭元部的元音一样,较接近于a(α):
《诗经》里带*-o的音节几次跟带*的音押韵(如《大雅·皇矣》八章),一次跟带*-a的音节押韵(《大雅·桑柔》十六章)。
脂文部的唇化元音跟幽中部、宵部的元音区别也很小。
前面已引了一些例子,说明脂文部的字跟幽中部的字相押(《大雅·桑柔》八章),脂文部的字跟宵部的字相押(《小雅·角弓》七章)。
前面还提到“昷”是“媪?
au2”的声旁〔34〕。
我们还要指出,“敦”字可假借作“彫tieu”和“帱dhαu3”(这两个字属幽中部)〔35〕;“谁źwi(*)”〔36〕跟“孰”(属幽中部)则为同源词。
看来,幽中部跟宵部的元音都接近于u。
幽中部的元音*u在汉语和藏语的比较中可以得到证实:
汉语数字“六”和“九”都属幽中部,跟藏语的drug和d-gu对应。
在联绵词中,幽中部的元音常跟*和*α交替,宵部的元音则跟*e交替。
例如:
戮力,螳蜩dhαngdhieu,徭役,颠倒tientαu2。
“戮力”是幽中部字跟之蒸部字交替,“螳蜩”是鱼阳部字跟幽中部字交替,“徭役”是宵部字跟支耕部字交替,“颠倒”是至真部字跟宵部字交替。
此外,幽部字有时跟之部字相押(如《大雅·思齐》五章),宵部字有一次跟支部字相押(《鄘风·君子偕老》二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上古汉语*u的两个变体间的关系同元音、a跟e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
幽中部字有过舌位偏后的*u,而宵部字则有过舌位偏前的*ü〔37〕。
由此可见,在幽中部和宵部的问题上,无论是高本汉和董同龢的理论,还是王力的理论,在我们看来都没有得到证实。
王力否认中部的存在,把它归到侵部(其中的字都带-m韵尾)。
的确,侵部和中部的字在《诗经》里常常相押(《秦风·小戎》二章,《豳风·七月》八章,《大雅》的《思齐》三章,《公刘》四章,《荡》首章,《云汉》二章)。
但侵部字也跟蒸部字相押(《秦风·小戎》三章,《大雅·大明》七章,《鲁颂·閟宫》五章),而中部字也跟东部字相押(《邶风·旄丘》三章,《郑风·山有扶苏》二章,《小雅·蓼萧》四章,《大雅·文王有声》二章)。
《易经》里中部常跟侵部、东部混用;此外,在一个地方侵部字跟有*-un韵的字相押:
阴顺:
()(《易·泰》:
“内阳而外阴,内柔而外顺”)。
总之,这里的情况相当复杂,把某两个韵部合而为一未必就能排除所有困难。
看来侵部字有过*um韵。
由此就可解释,为什么它们有时跟带*ung(中部)的字相押,而有一处又跟带*un的字相押。
此外,在中部字里,就像前面谈到的PON型音节一样,元音*u由于异化而能被元音*替换。
因此它们有时也跟带*-(蒸部)的字相押。
中部(即带*ung的音节)字有可能有时跟带*-um的字,有时又跟带*-ong的字误押。
能跟带元音u的字相押的不仅有侵部字,而且还有缉部字;谇答退swi3:
tαp:
thuαi3(《小雅·雨无正》四章——脂文部);犹集咎道:
:
:
dhαu2(《小雅·小旻》三章——幽中部)。
此外,跟缉部字同源而在中古念去声的字,语音上几乎总是唇化音节(并跟带*-ut-s的字相押而不跟带*的字相押),如:
答tαp——对tuαi3;入——内nuαi3;集——萃dzhwi3。
由此可见,侵部字和缉部字在上古都曾有过元音*u(它曾可以被
*替换)。
这些字中的元音*u在跟藏语的比较中可得到证实,汉语数字“三(*sum)”(上古侵部字)和“十(*)”(上古缉部字),跟藏语的g-sum和b-tsu对应。
另一个有唇音韵尾的韵部(即叶谈部)明显地带有非唇化元音。
但很难断定这个音是*α还是*a;根据不准确的押韵和声旁都可以追溯出叶谈部和鱼阳部,叶谈部跟歌部、祭元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