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的精神.docx
《论法的精神.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法的精神.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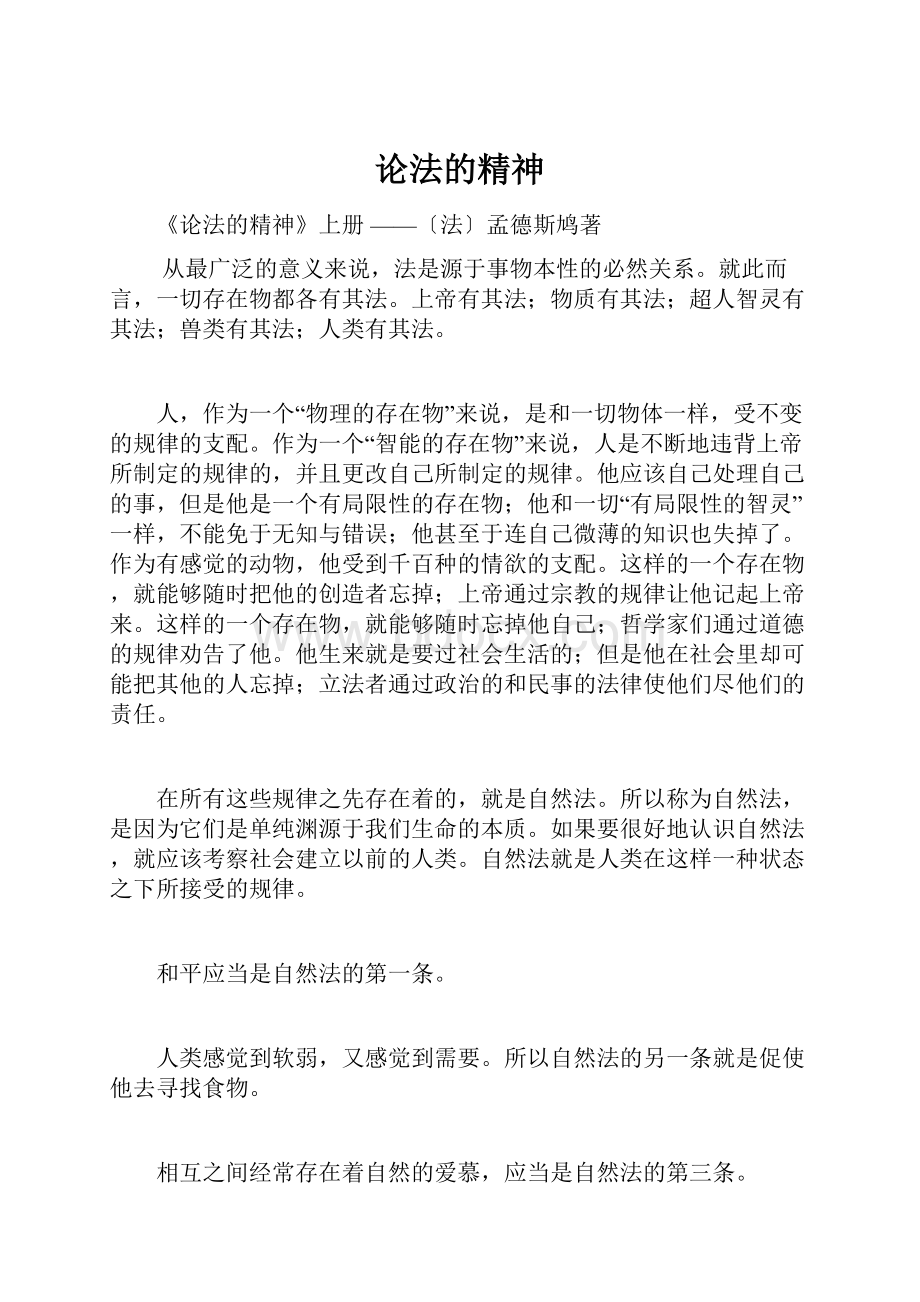
论法的精神
《论法的精神》上册 ——〔法〕孟德斯鸠著
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源于事物本性的必然关系。
就此而言,一切存在物都各有其法。
上帝有其法;物质有其法;超人智灵有其法;兽类有其法;人类有其法。
人,作为一个“物理的存在物”来说,是和一切物体一样,受不变的规律的支配。
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来说,人是不断地违背上帝所制定的规律的,并且更改自己所制定的规律。
他应该自己处理自己的事,但是他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他和一切“有局限性的智灵”一样,不能免于无知与错误;他甚至于连自己微薄的知识也失掉了。
作为有感觉的动物,他受到千百种的情欲的支配。
这样的一个存在物,就能够随时把他的创造者忘掉;上帝通过宗教的规律让他记起上帝来。
这样的一个存在物,就能够随时忘掉他自己;哲学家们通过道德的规律劝告了他。
他生来就是要过社会生活的;但是他在社会里却可能把其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
在所有这些规律之先存在着的,就是自然法。
所以称为自然法,是因为它们是单纯渊源于我们生命的本质。
如果要很好地认识自然法,就应该考察社会建立以前的人类。
自然法就是人类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所接受的规律。
和平应当是自然法的第一条。
人类感觉到软弱,又感觉到需要。
所以自然法的另一条就是促使他去寻找食物。
相互之间经常存在着自然的爱慕,应当是自然法的第三条。
希望过社会生活,这就是自然法的第四条。
作为这个大行星上的居民,人类在不同人民之间的关系上是有法律的,这就是国际法。
社会是应该加以维持的;作为社会的生活者,人类在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上是有法律的,这就是政治法。
此外,人类在一切公民间的关系上也有法律,这就是民法。
国际法是自然地建立在这个原则上的,就是:
各国在和平的时候应当尽量谋求彼此福利的增进;在战争的时候应在不损害自己真正利益的范围内,尽量减少破坏。
战争的目的是胜利。
胜利的目的是征服。
征服的目的是保全。
应该从这条和前一条原则推出一切构成国际法的准则。
政体的原则对法律有最大的影响。
政体有三种:
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
用最无学识的人的观念就足以发现它们的性质。
我假定了三个定义,或毋宁说是三个事实:
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
共和国的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贵族政治。
只有通过选举,人民才能当君主,因为选举表现了人民的意志。
主权者的意志,就是主权者本身。
因此,在这种政治之下,建立投票权利的法律,就是基本法律。
民主政治在法律上规定应怎样、应由谁、应为谁、应在什么事情上投票,这在事实上和君主政体要知道君主是什么君主,应如何治理国家,是一样的重要。
如果那些代理人不是由人民指派的话,便不是人民的代理人。
所以这种政体有一个基本准则,就是人民指派自己的代理人——官吏。
在人民完全不参与政府的国家里,人民将为一出戏剧的演员而狂热,俨然像为国事而狂热一样。
民主政治还有一条基本规律,就是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
一切官职,如果权力大,任期就应该短,以资补救。
当品德消逝的时候,野心便进入那些能够接受野心的人们的心里,而贪婪则进入一切人们的心里。
欲望改变了目标:
过去人们所喜爱的,现在不再喜爱了;过去人们因有法律而获得自由,现在要求自由,好去反抗法律;每一个公民都好像是从主人家里逃跑出来的奴隶;人们把过去的准则说成严厉,把过去的规矩说成拘束,把过去的谨慎叫做畏缩。
在那里,节俭被看作贪婪;而占有欲却不是贪婪。
从前,私人的财产是公共的财宝;但是现在,公共的财宝变成了私人的家业,共和国就成了巧取豪夺的对象。
它的力量就只是几个公民的权力和全体的放肆而已。
在一个国家里,首脑人物多半是不诚实的人,而要求在下的人全都是善人;首脑人物是骗子,而要求在下的人同意只做受骗的呆子;这是极难能的事。
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怖。
在君主国里,教育的法律的目的应该是荣誉;在共和国里,应该是品德;在专制国里,应该是恐怖。
品德,应该高尚些;处世,应该坦率些;举止,应该礼貌些。
对妇女献殷勤,如果是同爱情的思想或征服的思想相结合的话,是可以容许的。
施用权谋术数,如果是同胸襟的伟大或事业的伟大的思想相结合的话,是可以容许的,例如在政治上施用狡诈是无损于荣誉的。
为了求取富贵而去阿谀奉承,这是荣誉所不禁止的。
但是如果不是为求富贵,而是在感情上认为自己卑贱,因而去阿谀奉承的话,那就是荣誉所不许的。
人们所以要真实,是因为一个习惯于说真实话的人,总显得大胆而自由。
实在说,这样的一个人便显得他是专以事物为根据,而不是随和别人对事物的看法。
那些不遵守礼节的人,会得罪一切共同生活的人们,便将失掉社会的尊重,以致不能有所成就。
我们有礼貌是因为自尊。
我们用一些仪表来证明我们不是卑贱,来证明我们从未同各世代所不齿的人们生活在一起过,这就使我们自己感到得意。
当我们一旦获得某种地位的时候,任何事情,倘使足以使我们显得同那种地位不相称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做,也不应该容忍别人去做。
法律所不禁止而为荣誉所禁止的东西,则其禁止更为严格;法律所不要求而为荣誉所要求的东西,则其要求更为坚决。
专制国家的教育所寻求的是降低人们的心志。
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甚至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须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愿就够了。
在专制的国家里,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个别的帝国。
那里的教育主要是教人怎样相处,所以范围是很窄狭的;它只是把恐怖置于人们的心里,把一些极简单的宗教原则的知识置于人们的精神里而已。
在那里,知识招致危险,竞争足以惹祸。
今天我们所受的是三种不同或矛盾的教育,即父亲的教育、师长的教育和社会的教育。
社会教育对我们所说的,把父亲和师长所教育的思想全部推翻。
从来没听说过国王不爱君主政体,也没听说过暴君憎恨专制政体。
变坏的绝不是新生的一代,只有在年长的人已经腐化之后,他们才会败坏下去。
身体的锻炼使人冷酷;推理的科学使人孤僻。
在所有感官娱乐之中,音乐是最不会败坏人的心灵的。
腐败往往不是由人民开始。
在民主政治之下,爱共和国就是爱民主政治;爱民主政治就是爱平等。
在君主和专制的国家里,没有人渴慕平等。
平等的观念根本就不进入人们的头脑里去。
大家都希望出类拔萃。
就是出身最卑微的人们也希望脱离他原来的境地,而成为别人的主人。
在法律没有预防的地方,不平等便会乘隙而入,而共和国也就完了。
贵族政治的国家有两个主要的致乱之源,一个是治者与被治者之间存在着过度的不平等,一个是统治团体成员之间也有同样的不平等。
这两种不平等产生怨恨和嫉妒。
这二者都是法律应该预防或压制的。
第一种不平等的主要情况是:
显要人物的特权的光荣恰恰就是平民的耻辱。
如果不把国库的收入分散给人民的话,就应该让人民知道这些收入的管理是很好的。
把这些财富让人民看一看就多少等于让人民享受了。
法律也应该禁止贵族经营商业。
因为这种有资财的商人,将会垄断一切贸易。
贸易是一些平等的人们之间的职业。
所以专制国家中最不幸的,就是那些君主自己从事买卖的国家。
法律应该使用最有效的手段,使贵族以公道对待人民。
如果法律尚未建立护民官的话,法律自己就应该是护民官。
对犯罪行为进行各种庇护,以致连法律也不能执行,这就使贵族政治趋于毁灭,而接近了暴政的边缘。
荣誉可以说就是贵族的产儿,又是贵族的生父。
.君主政体比共和政体有一个显著的优点。
事务由单独一个人指挥,执行起来,较为迅速。
但是这种迅速就可能流于轻率。
红衣主教李索留劝告君主国要避免由于准许人们集会结社而发生的麻烦;集会结社将在一切事情上造成困难。
如果这个人不是心里有专制主义,就是脑子里有专制主义的思想。
路易斯安纳的野蛮人要果子的时候,便把树从根柢砍倒,采摘果实。
这就是专制政体。
在专制政体之下,一切事物的运转只取决于两三个概念,所以并不需要什么新的概念。
我们训练野兽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改变它的主人,不改变所教的东西和所教的步法。
这样,只通过两三个动作,把印象灌入脑子里就够了。
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
但是这种平静不是太平。
要形成一个宽和的政体,就必须联合各种权力,加以规范与调节,并使它们行动起来,就像是给一种权力添加重量,使它能够和另一种权力相抗衡。
一个政府,如果没有做不正义的事情的爪牙,便不致成为一个不正义的政府。
但要这些爪牙不给自己捞一把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专制的国家里,贪污便是当然的现象。
在这种政体之下,贪污是一种普通的犯罪。
专制的国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物,就是对君王也不能例外。
在共和国里,礼物是可厌的东西,因为品德不需要它们。
在君主国里,荣誉是比礼物更强有力的鼓舞力量。
但是专制的国家,既没有荣誉又没有品德,人们所以有所作为,只是因为希望获得生活上的好处而已。
柏拉图主张,履行职务而收受礼物的人要处以死刑。
这是属于共和国的思想。
他说:
“不管是为着好事或坏事,都不应当接受礼物。
”
.罗马有一项坏法律,就是准许官吏接受小礼物,假使这些礼物一年不超过一百埃巨的话。
没有接受过别人任何东西的人,并不期望任何东西。
接受过别人一点儿东西的人,马上就想要再多一点儿,接着就想要得更多。
不但如此,对一个不应该接受礼物而接受了的人,要使他服罪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对一个可以接受少量礼物却接受多了的人,要使他服罪就不那么容易;他常常可以找到一些借口、一些托辞、一些原因和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来为这种行为辩解。
严峻的刑罚比较适宜于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政体,而不适宜于以荣誉和品德为动力的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
在政治宽和的国家,爱国、知耻、畏惧责难,都是约束的力量,能够防止许多犯罪。
对恶劣行为最大的惩罚就是被认定为有罪。
因此,民事上的法律可以比较容易地纠正这种行为,不需要许多大的强力。
在这些国家里,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罚犯罪,注意激励良好的风俗,多于施用刑罚。
刑罚的增减和人民距离自由的远近成正比例。
治理人类不要用极端的方法;我们对于自然所给与我们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
如果我们研究人类所以腐败的一切原因的话,我们便会看到,这是因为对犯罪不加处罚,而不是因为刑罚的宽和。
让我们顺从自然吧!
它给人类以羞耻之心,使从羞耻受到鞭责。
让我们把不名誉作为刑罚最重的部分吧!
如果一个国家,刑罚并不能使人产生羞耻之心的话,那就是由于暴政的结果,暴政对恶棍和正直的人使用相同的刑罚。
如果有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所以不敢犯法纯粹是因为惧怕残酷的刑罚的话,我们也可以肯定,这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暴戾,对轻微的过错使用了残酷的刑罚。
有两种腐化,一种是由于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人民被法律腐化了。
被法律腐化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弊端,因为这个弊端就存在于矫正方法本身中。
愿意毁灭自由的人们是害怕那些可能复活自由精神的著作的。
拷问可能适合专制国家,因为凡是能够引起恐怖的任何东西都是专制政体最好的动力。
一个好的立法者是不偏不倚的。
平等的真精神和极端平等的精神的距离,就像天和地一样。
平等的真精神的含义并不是每个人都当指挥或是都不受指挥;而是我们服从或指挥同我们平等的人们。
克里特人使用一种极奇怪的方法,使重要官吏必须守法。
这个方法就是叛变。
一部分公民可以揭竿而起,赶走官吏,强迫他们恢复平民的身分。
人们认为这种做法是有法律根据的。
这样的一种制度,准许用叛乱去制止权力的滥用,看来似乎可以颠覆任何一个共和国。
但是这个制度并没有毁坏克里特共和国。
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呢。
被征服的国家通常都是法制废弛的。
腐化已经产生;法律已停止执行;政府变成了压迫者。
如果征服不是毁灭性的征服的话,这样一个国家,正可以因被征服获取一些好处,谁会怀疑这一点呢?
一个政府如果已经到了自己不能进行改革的地步,人家把它改造一下,于它有何损失呢?
如果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的情况是,富人通过千种诡计,万种技巧,在不知不觉间使用无数手段进行掠夺,而不幸的人们受着压迫,嘘吁叹息,看到他们一向认为弊害的东西已经成为法律,并连感到压迫都被认为犯了错误,如果情况如此,我认为征服者就应该把该国的一切都推翻掉,而首先以暴力对待那里暗无天日的暴政。
征服可能消除有害的偏见,并且把一个国家——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放置到更为英明的人的统治之下。
一个民族对自己的风俗总是比对自己的法律更熟悉、更喜爱、更拥护。
命运中的偶然事故是易于补救的;而从事物的本性中不断产生出来的事件,则是防不胜防的。
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
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
这种心境的平安是从人人都认为他本身是安全的这个看法产生的。
要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
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
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
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试看这些共和国的公民是处在何等境遇中!
同一个机关,既是法律执行者,又享有立法者的全部权力。
它可以用它的“一般的意志”去蹂躏全国;因为它还有司法权,它又可以用它的“个别的意志”去毁灭每一个公民。
在那里,一切权力合而为一,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们却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
探究一个题目不应穷源尽委到了不留任何事情给读者做。
问题不应该是让人去阅读,而应该是让人去思考。
哲学上的自由,是要能够行使自己的意志,或者,至少如果应从所有的体系来说的话自己相信是在行使自己的意志。
政治的自由是要有安全,或是至少自己相信有安全。
这种安全从来没有比在公的或私的控告时受到的威胁更大的了。
因此公民的自由主要依靠良好的刑法。
单凭一个证人作证,就可把一个人处死的法律,对自由的危害是极大的。
依据理性的要求,就应该有两个证人,因为一个证人肯定犯罪,被告加以否认,双方各执一词,所以需要一个第三者出来解决。
如果刑法的每一种刑罚都是依据犯罪的特殊性质去规定的话,便是自由的胜利。
一切专断停止了,刑罚不是依据立法者一时的意念,而是依据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
一个公民应该处死,是因为他侵犯他人的安全到了使人丧失生命的程度,或是因为企图剥夺别人的生命。
死刑就像是病态社会的药剂。
侵犯财产的安全也可以有理由处以极刑,但是对危害财产安全的犯罪以丧失财产作为刑罚不但好些,而且也较适合于犯罪的性质。
如果大家的财产是公共的或是平等的,就更应当如此。
但是,由于侵犯财产的人常常是那些自己什么财产也没有的人,因此就不能不用体刑作为罚金的补充。
有一条重要的准则,就是:
对“邪术”和“异端”的追诉,要非常慎重。
这两种犯罪的控告可以极端地危害自由,可以成为无穷尽的暴政的泉源,如果立法者不知对这种控告加以限制的话。
因为这种控告不是直接指控一个公民的行为,而多半是以人们对这个公民的性格的看法作根据,提出控告,所以人民越无知,这种控告便越危险。
因此,一个公民便无时不在危险之中了,因为世界上最好的行为,最纯洁的道德,尽一切的本分,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不受到犯这些罪的嫌疑。
英格兰在亨利八世时通过一项法律,宣布凡预言国王死亡的人犯叛逆罪。
这项法律是很含糊不明的。
专制主义已经可怕到连施行专制主义的人也受到害处。
在这位国王末后一次患病时,医生们怎样也不敢说他已病危。
马尔西亚斯做梦他割断了狄欧尼西乌斯的咽喉。
狄欧尼西乌斯因此把他处死,说他如果白天不这样想夜里就不会做这样的梦。
这是大暴政,因为即使他曾经这样想,他并没有实际行动过。
法律的责任只是惩罚外部的行动。
在专制的国家里,人们几乎不懂得什么叫讽刺文字。
在这种国家里,一面由于软弱,一面由于无知,人们既无才能也不愿意去写讽刺文字。
民主的国家不禁止讽刺文字,这和一君统治的政体禁止讽刺文字,理由正是相同的。
讽刺文字通常是写来反对有权势的人的,这在民主国家正好宣泄作为统治者的人民的怨愤。
在君主国,讽刺文字亦被禁止,然而把它当作行政的问题,而不是犯罪的问题。
讽刺文字能够使一般人的怨愤转为嬉娱,使不满的人得到安慰,减少人们对官职的嫉妒,增加人民对痛苦的忍耐,使他们对所受的痛苦,一笑置之。
问题不是要摧毁掌握政权的人,而是摧毁权势本身。
君主国需要密探么?
好的君主通常不用密探。
一个人遵守法律,他就已经尽了对君主的义务。
至少,他的住宅应该是他的庇护所,而他的其他行为也应该得到安全保障。
君主对于戏言应该极端谨慎。
戏言适中可以取悦于人,因为它是与人亲近熟识的途径;但是尖刻的玩笑出自君主之口,较出自臣民中最微小者之口,远为不可,因为惟有君主能够随时给人致命的伤害。
君主更不应当对他的臣民进行明显的侮辱。
设立君主,为的是进行赦免,进行刑罚;绝对不是为了进行侮辱。
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
要把国家的收入规定得好,就应该兼顾国家和国民两方面的需要。
当取之于民时,绝对不应该因为国家想象上的需要而排除国民实际上的需要。
.想象上的需要,是从执政者的情欲和弱点,从一种离奇的计划的诱惑力,从对一种虚荣的病态羡慕,从在某种程度上对幻想的无力抗拒等等,而产生出来的东西。
那些心神不定,在君主手下主持国事的人们,常常把他们渺小的灵魂的需要当作是国家的需要。
没有任何东西比规定臣民应缴纳若干财产,应保留若干财产,更需要智慧与谨慎了。
计算国家收入的尺度,绝不是老百姓能够缴付多少,而是他们应当缴付多少。
如果用老百姓能够缴付多少去计算的话,那末至少也应当用他们经常的缴付能力作标尺。
专制国家是不能够增加赋税的,因为奴役已经到了极点,无法再增加了。
伊斯兰教徒所以能够征服他国,易如反掌,就是因为他国征收过分的赋税。
[希腊]诸帝王的贪婪是狡巧的,他们想出各种苛捐杂税,困扰各族人民,终无了日。
而在伊斯兰教国的治下,各族人民则只负担简单的一种赋税,既易于缴纳,又易于征收。
各族人民感到,服从一个野蛮的外国,比服从一个腐败的政府,还要快乐幸福。
在这种腐败政府治下,自由已不存在,各族人民要忍受由此所产生的各种弊害,以及当前奴役的悲惨境遇。
疼痛是一种局部地方的痛苦,我们只希望把它消灭掉;对生存所感到的重担却是一种没有固定地方的痛苦,它使我们愿意看到这个生命的终结。
不耐烦的性格本身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但是当它和勇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就不得了啦。
它和轻率不同,轻率使人们无缘无故地从事或放弃一个计划。
它和顽固比较接近,因为它来自对苦难极敏锐的一种感觉,所以它甚至不因经常忍受苦难而减弱。
暴政开始时常常是缓慢而软弱的,最后却是迅速而猛烈;它起初只伸出一只手来援助人,后来却用无数只胳膊来压迫人。
奴役总是由梦寐状态开始。
但是一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安息,时时刻刻都在思考,并且处处都感觉到痛楚的人民,是几乎不可能睡得着的。
政治是一把磨钝了的锉刀;它锉着锉着,慢慢地达到它的目的。
.正确地说,所谓奴隶制,就是建立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支配权利,使他成为后者的生命与财产的绝对主人。
在专制的国家,人民已经生活在“政治奴隶制”之下,所以“民事奴隶制”比在别的国家易为人们所容忍。
在那些国家里,每个人有得吃,能够活着,就应该很满足了。
因此,一个奴隶的生活条件几乎不比一个国民艰难。
知识使人温柔,理性使人倾向于人道,只有偏见使人抛弃温柔和人道。
如果支配劳动的是理性而不是贪婪的话,则任何劳动都不会太艰苦,以致达到和从事那种劳动的人的体力完全不相称的程度。
在别的地方强迫奴隶去做的劳动,是可以通过技术所发明或所应用的机器的便利来代替。
妇女们的“理性”和“容色”永远不能同时存在。
当她们的“容色”正要称霸天下的时候,“理性”却加以拒绝。
当“理性”可以取得霸权的时候,“容色”已不复存在。
大自然所给男子的特点,就是体力和理性。
它把魅力给予女子。
利益越是分歧,法律便越应该引导这些分歧的利益走向统一。
大自然规定了防卫,也规定了进攻。
它把情欲种植在两性双方,给男性勇敢,给女性娇羞。
觉察缺点是“智灵的存在物”的本性。
因此,大自然使我们有羞耻之心,这就是对我们的缺点觉得羞耻。
女性妙龄时期的娇艳的可贵,就是到了衰暮之年,还能使丈夫回忆过去的欢乐;因而心满意足,恩爱不渝。
亚洲的这些帝国的人民,是用短棒统治的。
鞑靼的人民是用长鞭统治的。
欧洲的精神同这种习气永远是水火不相容的。
在一切时代里,亚洲人民叫做刑罚的,欧洲人民则叫做暴行。
骁勇的民族在欧洲的北方形成;他们走出自己的国家,去摧毁暴君与奴隶制度,教育人类,使他们知道大自然所造的人是平等的;除非是为着他们的利益,理性不得使他们依赖屈从。
法治和保国不是格格不相入的;不,法治是很有利于保国的。
所以没有法治,国家便将腐化堕落,而和一切邻邦都不能相比。
一种奴隶的思想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
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
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而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
机器常常有许多磨擦,使理论上的效果发生变化或迟延;政治也是一样。
迷信的偏见强于其他一切偏见,迷信的理论强于其他一切理论。
暴政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暴政,是以暴力统治人民;另一种是见解上的暴政,即当统治者建立的一些设施和人民的想法相抵触时让人感觉到的那种暴政。
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
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风俗、习惯。
结果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一般的精神。
在每一个国家里,这些因素中如果有一种起了强烈的作用,则其他因素的作用便将在同一程度上被削弱。
我们是怎样,就让我们怎样吧!
一切政治上的邪恶并不都是道德上的邪恶,一切道德上的邪恶并不都是政治上的邪恶。
一般来说,各族人民对于自己原有的习惯总是恋恋不舍的。
用暴力取消这些习惯,对他们是悲惨的。
因此,不要去改变这些习惯,而要引导他们自己去改变。
一切不是由于必要而施用的刑罚都是暴虐的。
法律不是一种纯粹的“权力作用”;在性质上无关紧要的东西就不属于法律的范围。
法律和风俗有一个区别,就是法律主要规定“公民”的行为,风俗主要规定“人”的行为。
风俗和礼仪有一个区别,就是风俗主要是关系内心的动作,礼仪主要是关系外表的动作。
一个自由的国家可能得到一个救主;一个被奴役的国家就只能再来一个压迫者。
因为谁有足够力量,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