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亳邑新探.docx
《甲骨文亳邑新探.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甲骨文亳邑新探.docx(3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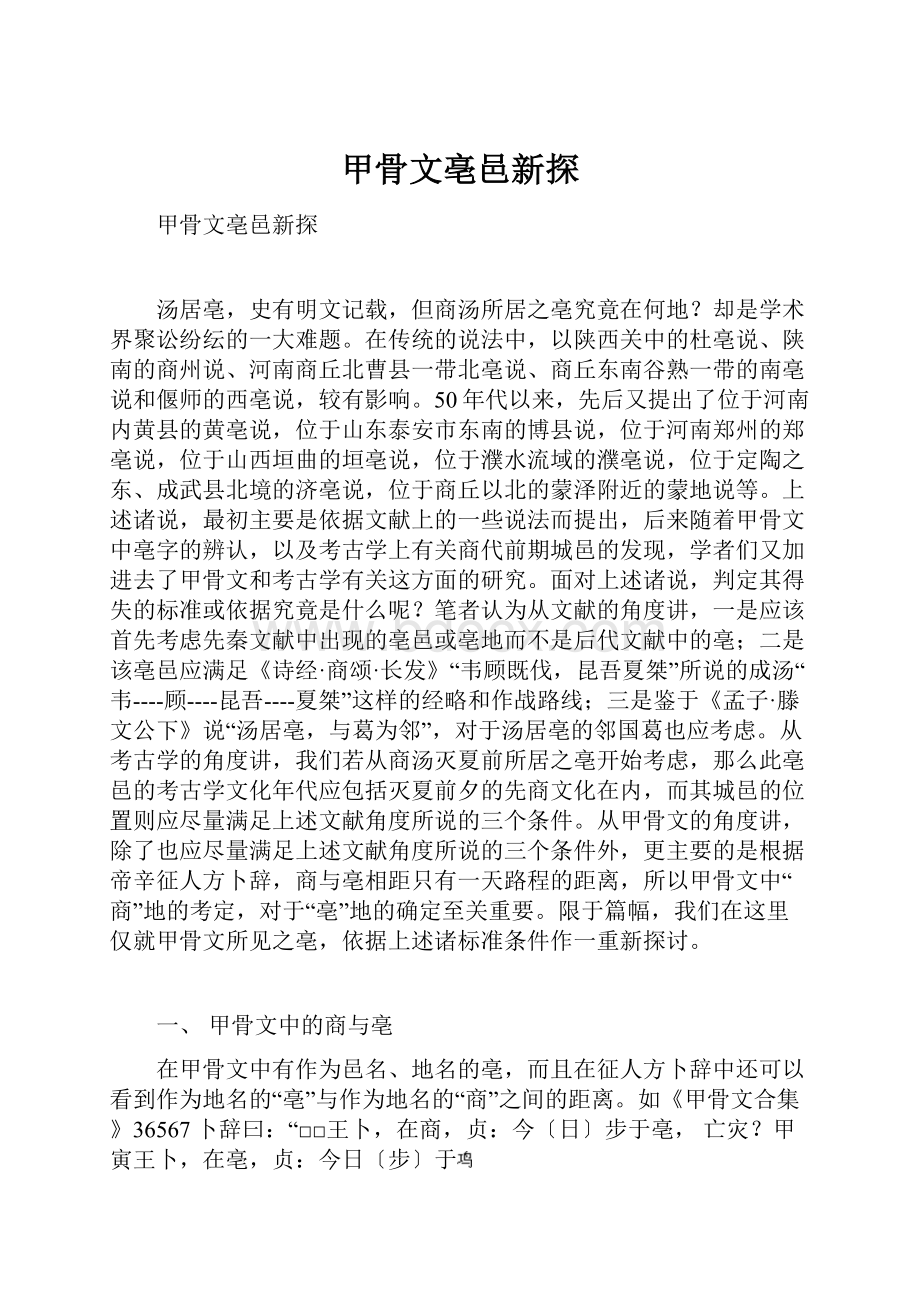
甲骨文亳邑新探
甲骨文亳邑新探
汤居亳,史有明文记载,但商汤所居之亳究竟在何地?
却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一大难题。
在传统的说法中,以陕西关中的杜亳说、陕南的商州说、河南商丘北曹县一带北亳说、商丘东南谷熟一带的南亳说和偃师的西亳说,较有影响。
50年代以来,先后又提出了位于河南内黄县的黄亳说,位于山东泰安市东南的博县说,位于河南郑州的郑亳说,位于山西垣曲的垣亳说,位于濮水流域的濮亳说,位于定陶之东、成武县北境的济亳说,位于商丘以北的蒙泽附近的蒙地说等。
上述诸说,最初主要是依据文献上的一些说法而提出,后来随着甲骨文中亳字的辨认,以及考古学上有关商代前期城邑的发现,学者们又加进去了甲骨文和考古学有关这方面的研究。
面对上述诸说,判定其得失的标准或依据究竟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从文献的角度讲,一是应该首先考虑先秦文献中出现的亳邑或亳地而不是后代文献中的亳;二是该亳邑应满足《诗经·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所说的成汤“韦----顾----昆吾----夏桀”这样的经略和作战路线;三是鉴于《孟子·滕文公下》说“汤居亳,与葛为邻”,对于汤居亳的邻国葛也应考虑。
从考古学的角度讲,我们若从商汤灭夏前所居之亳开始考虑,那么此亳邑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应包括灭夏前夕的先商文化在内,而其城邑的位置则应尽量满足上述文献角度所说的三个条件。
从甲骨文的角度讲,除了也应尽量满足上述文献角度所说的三个条件外,更主要的是根据帝辛征人方卜辞,商与亳相距只有一天路程的距离,所以甲骨文中“商”地的考定,对于“亳”地的确定至关重要。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仅就甲骨文所见之亳,依据上述诸标准条件作一重新探讨。
一、甲骨文中的商与亳
在甲骨文中有作为邑名、地名的亳,而且在征人方卜辞中还可以看到作为地名的“亳”与作为地名的“商”之间的距离。
如《甲骨文合集》36567卜辞曰:
“□□王卜,在商,贞:
今〔日〕步于亳,亡灾?
甲寅王卜,在亳,贞:
今日〔步〕于
,亡灾?
乙卯王卜,在
,贞:
今日步于
,亡灾”。
这版卜辞,虽然第一条卜辞“□□王卜,在商贞:
今〔日〕步于亳,亡灾”缺少占卜天干,但由于它与后两条卜辞辞例格式完全相同,后两条的占卜天干是前后连接的,第一条的天干也应与第二条相连。
此外,由后两条可知,甲寅在亳地占卜贞问“今日步于
”,到第二天乙卯果然是已经到达了
地,又在
地占卜“今日步于
”有无灾祸,这说明这版卜辞中所占卜的“今日步于某地”有无灾祸,在行程上当日是能到达某地的,并形成了一种占卜格式,从而可以确定,第一条卜辞“在商贞,今日步于亳,无灾”所反映的由“商”到“亳”的距离,只是一天的路程。
也就是说,只要确定了这些卜辞中的“商”在何地,“亳”也可以随即确定。
为此,主张郑亳说者,把该卜辞中的“商”放在了今河南武陟县东南的商村或淇县的朝歌;主张北亳或南亳说者,把这个“商”地放在了今河南商丘。
当然,也有把该条卜辞中的“商”放在山东泰安的。
可见问题的关键是,必须首先确定卜辞中的“商”究竟在何地。
在卜辞中,“商”地的问题,又是与“中商”、“大邑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为了能说清楚卜辞中的“亳”地何在,我们还需对卜辞中的“商”、“中商”、“大邑商”的问题,作一系统地分析和讨论。
在卜辞中,关于“商”、“中商”、“大邑商”等典型性的卜辞有:
(1)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
(《屯南》1126))
(2)己巳王卜,贞:
□岁商受〔年〕?
王占曰:
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
吉。
西土受年?
吉。
北土受年?
吉。
(《合集》36975)
(3)辛卯卜,殻贞:
王入于商?
辛卯卜,殻贞:
王勿入于商?
(《合集》10344)
(4)乙卯卜,殻贞:
今夕王入商?
(《合集》39990)
(5)丙戌卜,争贞:
在商亡祸?
(《合集》7814)
(6)贞:
不至于商?
五月。
(《合集》7818)
(7)贞:
勿归于商?
(《合集》7820)
(8)辛酉卜,尹贞:
王步自商亡灾?
(《合集》24228)
(9)己巳贞:
示先入于商?
(《合集》28099)
(10)丙辰卜,于庚申
用?
在商。
(《合集》33127)
(11)癸卯卜,在商贞:
王今夕亡祸?
(《合集》36550)
(12)癸卯王卜,贞:
旬亡祸。
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在商。
癸丑王卜,贞:
旬亡祸。
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在亳。
癸亥王卜,贞:
旬亡祸。
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在
。
〔癸〕酉王卜,在□,贞:
旬亡祸?
〔在〕十月又二,〔王〕征人方。
(《英藏》2524)
(13)□□王卜,在商,贞:
今〔日〕步于亳,亡灾?
甲寅王卜,在亳,贞:
今日〔步〕于
,亡灾?
乙卯王卜,在
,贞:
今日步于
,亡灾?
(《合集》36567)
(14)……勿于中商。
(《合集》7837)
(15)□巳卜,王贞:
于中商乎……方。
(《合集》20453)
(16)戊寅卜,王贞:
受中商年……十月。
……卜,王……不既……于侯,侯……有祐。
(《合集》20650)
(17)己丑卜,殻贞:
于丘商?
四月。
贞:
勿
于丘商?
……
壬寅卜,殻贞:
不雨?
隹兹商有作祸?
贞:
不雨?
不隹兹商有作祸?
”(《合集》776)
(18)甲午卜,燎于丘商?
(《合集》7838)
(19)辛丑卜,殻贞:
妇妌乎黍丘商受……(《合集》9530)
(20)甲午王卜,贞:
作余
朕禾。
余步从侯喜征人方,上下
示,受余有祐?
不
灾祸,告于大邑商,亡
在
?
王占曰:
吉,在九月,遘上甲
,隹十
祀。
(《合集》36482)
(21)丁卯王卜,贞:
巫九
,余其从多田于多伯征盂方伯炎,
衣翌日步,〔亡〕
左,自上下于
示,受余有祐?
不
灾〔祸〕,〔告〕于兹大邑商,亡
在
?
〔王占曰〕:
弘吉,在十月,遘大丁翌。
(《合集》36511)
(22)己酉王卜,贞:
余征三邦方,
令邑弗悔,不……亡……,在大邑商,王占曰:
大吉。
在九月,遘上甲□五牛。
(《合集》36530)
(23)甲午卜,贞:
在
,天邑商皿宫衣,〔兹夕〕亡祸。
宁。
(《合集》36541)
乙丑卜,贞:
在
,天邑商公宫衣,兹夕亡祸。
宁。
在九月。
(《合集》36543)
(24)壬戌卜,贞:
在
,天邑商公宫衣,兹夕亡祸。
宁。
(《英藏》2529)
对于卜辞中“商”的地望,最初作出研究的是罗振玉先生和王国维先生。
罗振玉在《殷虚书契考释》中指出,安阳殷墟乃是武乙、文丁、帝乙三朝之都,卜辞中的商与大邑商、天邑商并皆殷都(即安阳)之称。
王国维赞同罗说,与罗振玉不同的是,他认为安阳殷墟作为殷都始自盘庚终于帝辛,并说商是“始以地名为国号,继以为有天下之号,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商。
讫于失天下而不改”。
他以《多士》之天邑商为殷末周初之事,所以也引《多士》而谓“是帝辛、武庚之居,犹称商也”。
林泰辅及胡厚宣亦从罗、王之说。
胡厚宣先生根据前举卜辞
(2)、(15)、(16)条之内容指出:
以“商”与东南西北并贞,可知殷代已有中东南西北五方之观念;“商”既位于四方之中,“商”即“中商”也,亦即后世“中国”称谓之起源。
古之“中国”之义,本指京师。
他辞之大邑商,即“国之中央,王都之所在,今河南安阳其地也”。
然而,随着材料的增加,卜辞地名所显示的情况愈来愈错综复杂,故而新说也就迭出纷呈。
第一位对罗、王之说提出异议的是董作宾先生。
他通过排列征人方卜辞,特别是上举第(13)条之辞,看到商与亳相近,认为亳是谷熟之南亳,推定商为河南之商丘。
但又以“商”、“大邑商”、“中商”为一地,并承认卜辞“大邑商”“中商”含有“中央”的意思,只是说这是“殷人以其故都”所在地为中央。
其后,陈梦家先生也因卜辞有“在商贞今日步于亳”之语,而认为董作宾推定商为商丘是正确的,但他对天邑商、大邑商、商、中商加以分别,说“凡称天邑商的记衣(殷)祭之事,凡称大邑商的记征伐之事并兼及田游,两者未必一地。
”“天邑商”在今河南淇县东北之古朝歌,“大邑商”疑在沁阳田猎区,“商”与“丘商”在今商丘县一带,“中商”指的是安阳。
岛邦男先生也认为卜辞中的“商”、“中商”、“丘商”、“大邑商”是同一地方,其地在今商丘县,而提出小屯殷墟,卜辞另有称谓称之,即卜辞中称为“兹邑”的地方。
钟柏生先生则提出第一期卜辞中的“商”“丘商”、第二期的“商”、第三、四期的“商”“大邑”、第五期的“大邑商”“天邑商”和一部分“商”在今河南商丘;而第一期的“兹邑”“中商”、第三、四期的“中商”、第五期中的一部分“商”在安阳小屯之殷墟。
他说“‘商’的称谓,在卜辞中是代表二个地望:
一是安阳殷都,一是河南商丘。
这两者之所以相混,完全是卜辞本身暧昧不明,并没有其他的特殊原因”。
近年,郑杰祥先生在《商代地理概论》一书中提出:
卜辞中与四方、四土相对的“商”指的是王畿,而对于卜辞中一般的“商”,即诸如“王入于商”、“在商”之类的“商”,认为指的是一个具体的地名、具体的居邑,他称之为“商邑”,说是位于王畿之内的王都,即今日安阳殷墟。
但又认为第五期卜辞中的“天邑商”和“大邑商”指的是安阳王都,故第五期卜辞中的“商”,“不再指为安阳王都,而应指为后世所称作的朝歌城”,也就是说,郑先生因把征人方卜辞中的“大邑商”看作是安阳殷都,不得不把征人方中出现的“商”放在了淇县的朝歌,至于其他具体的“商”地则仍然指的是作为王都的安阳殷墟。
对于“中商”一地,则说“不能确指其所在”,“当指为王都附近,可能在今河南省安阳市一带”。
此外,还有一些做法是:
有的以征人方卜辞中的“大邑商”为朝歌,而对于其中的“商”,则认为是河南商丘;有的则说“大邑商”即安阳殷都,而把“商”放在山东泰安道朗龙门口水库一带。
分析上述诸家的说法,笔者以为,董作宾先生以“商”、“大邑商”、“中商”为一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他把它们安置在今河南商丘县则是错误的。
董先生之所以把“商”、“大邑商”、“中商”安放在河南商丘,最主要的是依据征人方卜辞中“商”与“亳”很近,他认为人方是南淮夷,征人方是向东南方向进军,他既把“亳”定为商丘县南的亳县附近,则“商”也只能在商丘。
其次,他受王国维《说商》和《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的影响,王国维认为宋地商丘自商先公以来就称作“商”,“宋”、“商”、“商丘”三者为一。
其实,董先生的论述虽说考虑了卜辞中“亳”与“商”很近这一情况,但以亳县之“亳”来证商丘之“商”和他以商丘之“商”来证亳县之“亳”,陷入了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
至于宋地商丘为“商”地问题,主要是相传商先公相土曾居于商丘。
但相土所居之商丘,历来有两说,一说为今河南之商丘,一说为今河南之濮阳,并无定论。
甲骨文中即有“丘商”一地,有学者认为它就是文献中的商丘,并依据卜辞记载商王多次贞问要在这里举行大祭,而且商的王妇妇妌还在这里主持过农业生产,认为这个丘商距王都不会很远,应在濮阳。
应该说,这一论述是有道理的。
退一步说,即使承认相土所居之商丘即为今河南商丘,那也不能解释在商族“前八后五”的多次迁徙中,为何只有相土所居之地一直到殷墟卜辞时代还被称为“商”,而其他先公先王所居之地却都不被称作“商”?
《诗·商颂·玄鸟》说: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诗·商颂·长发》说:
“有
方将,帝立子生商”。
这里的“商”是一个国族名。
也有注释说这里的“商”指的是商的始祖契,契是因其母有
氏简狄吞玄鸟卵而生的。
总之,商族称作“商”,在时间上是以其始祖的诞生、商族的形成为开始的。
而《史记·殷本纪》说契“封于商”,《世本》说“契居蕃”,是商与蕃为一地两名。
依据笔者的研究,“蕃”即战国时的“番吾”,其地在漳水流域的河北南部磁县境。
即使按照王国维的说法,契所居之蕃为鲁国之蕃县,那也不在商丘。
在商族的历史上,与“商”这一名号最早发生关系的是商族的始祖契和昭明,并非相土。
如果再考虑到相土所居之商丘,有可能就是卜辞中的丘商,也就是帝丘濮阳,而今河南商丘与商的关系,却是由于周人推翻商王朝后,商的后人微子启被封于宋亦即封于今日商丘的缘故的话,那么,董作宾等先生独取所谓相土所居之地为“商”,而对于契和昭明等其他先公所居之地亦曾名“商”却置之不理,特别是对于商的时王所居之国都,却不作为“商”来对待,都是说不通的。
还有,董先生看到“商”、“大邑商”、“中商”有天下“中央”之含义,但他又认为这是“殷人以其故都大邑商所在地为中央”。
笔者不禁要问,从武丁到帝辛,殷人为何不以时王的王都即时王的国都为天下之中央,而却要以灭夏之前某一位先公所居之地即所谓“故都”来作为商国后期的天下之中央?
这种思维方式是当时殷人的实际思维吗?
这在历代王朝中都不曾有过。
所以,董先生认为“商”、“大邑商”、“中商”在宋地商丘的说法,问题甚多,不足为据。
岛邦男先生承认“从武丁时至于殷末,殷首都在今之安阳”,但他根据“贞:
洹弗作兹邑〔祸〕?
”(《续》4·284)、“殻贞:
洹其作兹邑祸”(《
》2·476)等卜辞,认为临于洹水的殷都安阳,其称谓是“兹邑”。
“兹邑”之外,“殷都又被称作什么,不得而知”。
关于卜辞中的“商”、“大邑商”、“中商”,他依据征人方卜辞中的“商”与“亳”等地的关系,信从董作宾的说法,认为“商”在河南商丘,从而“大邑商”、“中商”也都在商丘。
笔者以为,“洹其作兹邑祸”之类卜问,只能证明在卜辞中安阳有时又被称作“兹邑”,但它并不能证明“大邑商”、“中商”和“商”所指的就不是殷都安阳,也就是说,“洹其作兹邑祸”一语,不能作为“大邑商”、“中商”和“商”不是安阳的证据。
至于他依存董说,以为“商”、“大邑商”、“中商”在河南商丘,由于董说已不可靠,自然也难以立足。
陈梦家先生以“商”为商丘,以“天邑商”为朝歌,以“大邑商”为沁阳。
前一说法即以“商”为商丘,是遵从董说,这里不再赘述。
后两说法,属于新创。
但陈先生区分“大邑商”与“天邑商”为两地的证据,颇有片面性,不能说明问题;二者本来为一,已为多位甲骨学者所指出。
笔者以为作为王畿的“大邑商”应包括朝歌在内,但并非仅仅指朝歌,它依然以安阳殷都为核心。
对此,我们后面再相加论述。
此外,陈梦家、岛邦男等学者还以“商”又被称作“兹商”,并根据前举(17)卜辞中,“丘商”与“兹商”为同版所卜,便认为“兹商”就是“丘商”,亦即今河南商丘。
这一说法,表面上看起来有些道理,但仔细考察原片是有问题的。
据张秉权等先生的考释,这一版一共刻了十二组对贞的卜辞,其内容各不相同,前举(17)之卜辞只不过是其中的两组而已,这两组卜辞是否有必然的联系,难以确定,从而说卜辞中的“兹商”即“丘商”,至少是依据不足,何况此“丘商”也不一定就在河南商丘,如前所述,它更有可能在河南濮阳。
钟柏生先生认为从武丁到帝辛的卜辞中,有的“商”是安阳殷都,有的“商”是河南商丘。
钟先生所说有些“商”在商丘,除了受董先生等人的影响外,主要是考虑到卜辞中被称作“方”的国族与“商”的关系。
他认为“方”在卜辞中代表两支居住地不同的民族,一支是武丁、文武丁时期分布于殷之北方、西北方或西方的民族;一支是文武丁时期分布于殷之东方或南方的民族。
关于后者,钟先生认为诸如卜辞:
“甲戌卜,扶贞:
方其盪于东,九月”(《粹》1172)和“戊申卜,方
自南,其
?
戊申卜,方
自南,不其
”(《乙》151),辞中的“方”,即可作为“方”在殷之东方及南方的证据。
这个在殷之东方及南方的“方”,钟先生说就是《后汉书·东夷传》和《竹书纪年》中的“方夷”。
他根据卜辞“壬午卜,
贞:
乎
方
商?
壬午卜,
贞:
王令多
方于〔商〕?
”(曾毅公《甲骨
存》39;《后》下41·16加《后》下42·9)以及卜辞“□巳卜,王贞:
于中商乎
方”(《佚》348),认为既然位于东方和南方的“方”族能威胁到商邑,那么这个“商”,“应当是指殷都南方的‘丘商’”。
他还根据“戊午卜,贞:
不丧,在南土祸,告史?
戊午卜,
克贝、
南丰方?
己未卜,隹
方其克贝,
在南?
己未卜,贞:
多
亡祸,在南土?
己未卜,贞:
多
亡祸,在南土?
”(《甲》2902)等卜辞,认为“
”地在南方、在南土,而在他的有关征人方卜辞的排谱中,“
”地与“商”地相距甚近,并与“亳”地相联,因此,与“
”地有关的“商”乃至“天邑商”,也都在南方,而且都是“丘商”的代称,其地就在今河南商丘县。
钟先生的上述说法,值得商榷的有四:
其一,即使卜辞中的被称为“方”的国族可分为两支,其中一支就是文献“东夷”中“方夷”;而且这个“方”的国族,还“启自南,其
”;商王曾令多
抵御“方”族于“商”(《甲骨
存》39);或在“中商”来抵御“方”族(《佚》348),但这也不能说明这里的“商”和“中商”就不是商都安阳而要位于南方或东南方。
换言之,东方或东南方的“方”也罢,方夷也罢,若威胁商邑,为何只能威胁到今河南商丘而不能威胁到安阳?
与商丘相比,安阳固然距离方夷要远一点,但若威胁不到商都安阳,还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威胁吗?
。
其二,“多
亡祸,在南土”的卜问,并不能说明“商”在河南商丘。
《甲编》2902卜辞“己未卜,贞:
多
亡祸,在南土”中的“在南土”,也可以理解为“在南土占卜”。
更主要的是,把《甲编》2902卜辞与《甲编》2907卜辞联系起来考虑,可以看出这两版卜辞占卜的是雀和多
在南土征战时是否安全无祸,以及商王要不要亲征,卜辞本身既不能说明多
居住在南方,更不能说明商都在河南商丘。
其三,除了有人依据前举(17)卜辞因“兹商”与“丘商”同版的关系而被认为“兹商”即“丘商”外,在卜辞中并没有什么材料能证明“商”即“丘商”。
至于(17)卜辞辞例的问题,如前所述,钟先生自己也认为,(17)辞例中,“兹商”与“丘商”的两组卜辞是否有必然联系,是难以确定的。
所以,钟先生所说的《甲骨
存》39卜辞中的“商”和《佚》348卜辞中的“中商”,“应当是指殷都南方的‘丘商’”,以及“天邑商”是“丘商”的代称的说法,也是没什么依据的。
仅以现在的材料而论,应该说卜辞中带“商”字的地名与“丘商”,是不同的地方,不应混用。
其四,单就卜辞“丘商”而言,虽说这个“丘商”有可能就是文献中的“商丘”,但因文献中相土所居之商丘,究竟在今河南商丘还是在濮阳,历来两说并存,并无定论。
所以,无法证明卜辞之“丘商”一定是今河南商丘而不是濮阳。
根据以上四个方面,钟先生把卜辞中的“商”分配在安阳与商丘两个不同的地方,其证据尚嫌不足,其说也是可商的。
以上诸说,凡是把卜辞中作为地名的“商”说成是在商都安阳之外者,其最根本的一点主要是依据征人方卜辞的排谱。
虽说诸家的排谱各有差异,但其共同点是:
第一,把凡能排入帝辛征人方谱的材料尽可能地都排入了帝辛十祀时的征人方谱中,而不深究其是否真的全是十祀时的卜辞;第二,几乎所有的论者都把十祀九月甲午日“告于大邑商”作为十祀征人方的起点,而把十又一月癸卯日“王征人方在商”、□□日“在商贞今步于亳”、十又一月癸丑“王征人方在亳”、甲寅日“在亳贞今日步于
”、乙卯日“在
贞今日步于
”之类与“商”地有关的卜辞,排在出发二个月之后的途中。
依据这样的排谱,在十祀征人方中,作为出发地的“大邑商”与作为中途的“商”,就必然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在这样的排谱中,就出现了有的学者以沁阳为“大邑商”,以商丘为“商”;有的学者以安阳殷墟为“大邑商”,以淇县朝歌为“商”;有的学者以朝歌为“大邑商”,以商丘为“商”;有的学者以安阳殷都为“大邑商”,以山东泰安道朗龙门口水库一带为“商”;等等。
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排谱很值得怀疑。
首先,“征人方……告于大邑商”的卜辞,记有“隹十祀”的纪年,而上引“在商”、“在亳”之类的卜辞,有的虽记有“征人方”、记有月和干支日或仅记干支日,但恰恰都没有“十祀”的纪年。
也就是说,自董作宾先生以来,是研究者自己主观上认为这些“在商”“在亳”的征人方卜辞,应该和有“十祀”纪年的“告于大邑商”的卜辞一样,都是商王十祀时征人方卜辞,因而把它们排列在了十祀征人方卜辞之中,而这些卜辞本身却并未告诉我们它们是十祀时的卜辞。
卜辞自身并没有“十祀”纪年,那它就有属于“十祀”之外征人方卜辞的可能。
其次,那些只是记有“在某地贞:
今日步于某地,无灾?
”而并无“征人方”字样的卜辞,是否一定是征人方卜辞,也很值得怀疑,因而也就不一定非要排入征人方谱中不可。
在征人方卜辞中,那些无“十祀”纪年却写有“在商”“在亳”之类的卜辞,有可能属于“十祀”之外,而根据出土材料,帝乙帝辛时期征人方也并非仅仅是“十祀”一次,至少还有“十五祀”征人方的记录。
如商代《小臣艅犀尊》铭文:
丁巳,王省夔京。
王赐小臣艅夔贝。
唯王来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
日。
此铜器被认为是十五祀征人方归途所铸。
“唯王来征人方”用语,与卜辞“二月癸巳,唯王来征人方,在齐
”(《合集》36493)和“五月癸卯,唯王来征人方,在
”(《合集》36495)中的“唯王来征人方”,完全相同。
铭文中的“唯王十祀又五,
日”属于时间署辞,其中“唯王十祀又五”是纪年,“
日”是以周祭祭祀作时间署辞,是配合前面的干支日使用的,据研究,在商代末期盛行这种用干支加周祭祭祀纪日的制度。
乙辛时期,既有十祀时的征人方战役,也有十五祀时的征人方战役,也可能还有其他时间的征人方事件,但排谱者们几乎把绝大多数材料都排入十祀征人方谱中,留给十五祀的寥寥无几,这种情况固然有研究中的无奈。
但值得指出的是,正是由于把上举那些记有“在商”的卜辞排入十祀征人方谱中,才使得同样都是第五期卜辞中的“商”,却呈现出不同的地理方位概念这样的矛盾现象。
例如,前举
(1)
(2)卜辞材料就属于第五期卜辞,辞中“商”与四方四土并贞,使得“商”有天下之中的含义。
不论这个“商”指的是国族(商王国)还是商的王畿,作为天下之中,总是以国都为依托、为中心的,所以,此处“商”的地理方位的中心点在商都安阳是不言而喻的。
而诸如前举(12)(13)条记有“在商”一语的卜辞也是第五期卜辞,只因被排入十祀征人方的谱中,其卜辞中的“商”,也就被视为远离商都安阳,被认为是从殷都出发二个月之后的地点。
这样,与四方四土并贞的“商”和征人方中的“商”之间的矛盾之处,就突显了出来。
然而,我们若把(12)(13)卜辞之类的材料从十祀征人方谱中拿出去,把它视为十五祀征人方卜辞或其他时间的卜辞,并把这些记有“在商”卜辞中的“商”作为十五祀征人方的出发地点,那么,上述矛盾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所以,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十祀时的贞人把出征时的告庙之地亦即出发地写作了“大邑商”,而十五祀或其他时间的贞人把出发地写作了“商”,因为都是商王亲自统兵征伐,所以作为出发地“大邑商”和“商”都应该是商都安阳。
有了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商”、“中商”、“大邑商”作一概括。
笔者认为,在“商”、“中商”、“大邑商”诸概念中,“商”是最基本、最核心的。
在卜辞中,“商”字有二个层面的含义或用法。
其一是作为一个大的区域范围来使用的“商”,如作为商的王畿或国族名来使用;其二是作为一个地名王都、国都来使用的“商”。
关于前者,可以举出《小屯南地》1126号卜辞:
“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
”以及《甲骨文合集》36975号卜辞:
“己巳卜,贞:
□岁商受〔年〕?
王占曰:
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
吉。
西土受年?
吉。
北土受年?
吉。
”在这里,若把与“商”并贞的“四方四土”理解为是在商的疆域内、受商王所控制或统辖的四土与四方的话,那么,这个“商”可以理解为商的王畿或王畿内的商都;而若把“四方四土”理解为商的诸侯国之地域,尽管其中相当多的诸侯国和商王国有着从属、半从属或时服时叛的关系,而这个“商”却可以理解为商国、商王国。
总之,不论把这里的“商”理解为商的王畿还是整个商国,它都是作为一个大的区域范围使用的。
又由于与“四方四土”并贞的“商”,含有中央的意思,所以,此“商”之中包含有时王的王都,而且还以王都为其依托。
关于后者,诸如卜辞中“王入于商”、“今夕王入商”、“王步自商”王“在商”、“在商贞”等等,都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地名来使用的,这个地方就是时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