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阳明心学.docx
《张居正与阳明心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张居正与阳明心学.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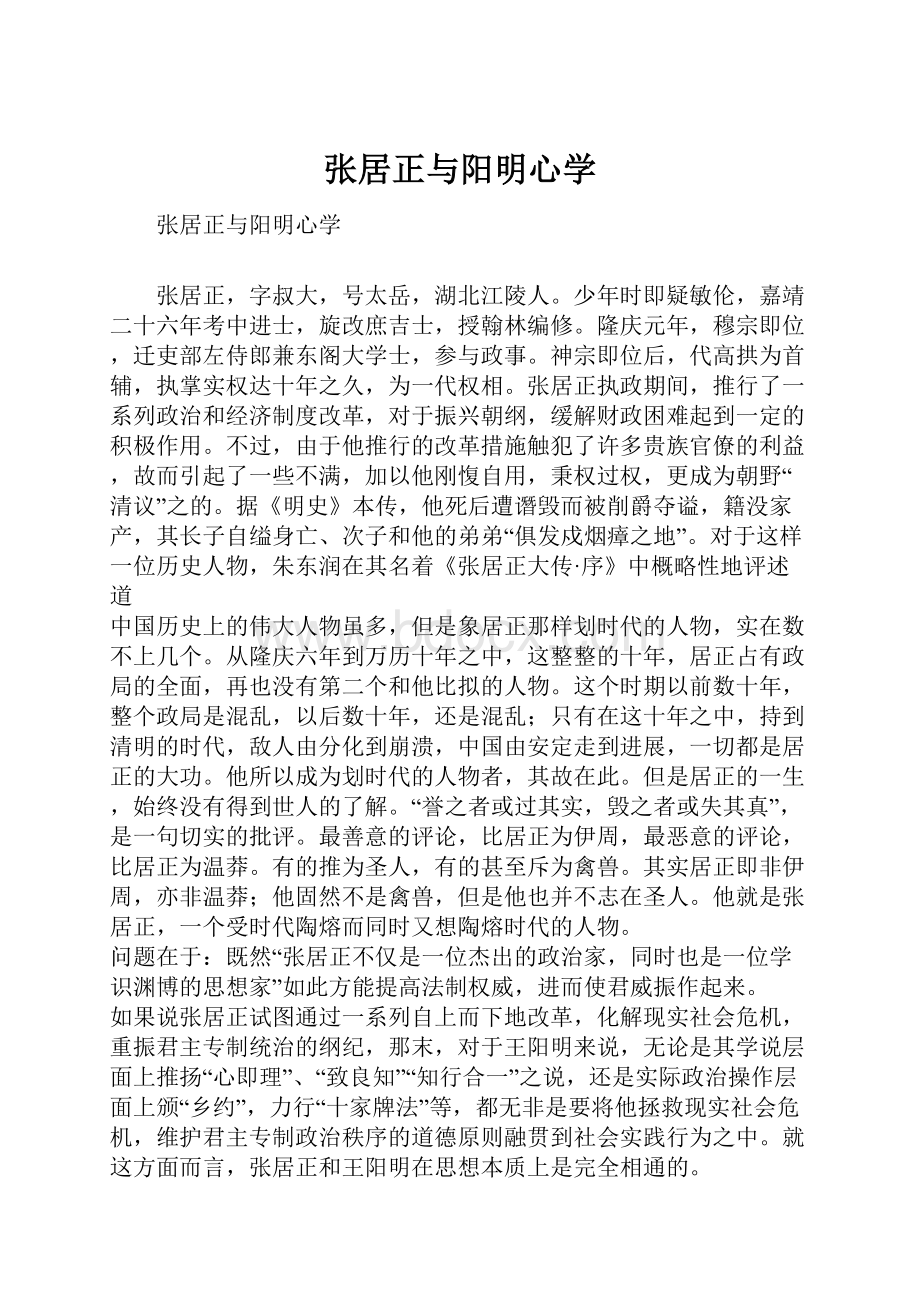
张居正与阳明心学
张居正与阳明心学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
少年时即疑敏伦,嘉靖二十六年考中进士,旋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
隆庆元年,穆宗即位,迁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政事。
神宗即位后,代高拱为首辅,执掌实权达十年之久,为一代权相。
张居正执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对于振兴朝纲,缓解财政困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不过,由于他推行的改革措施触犯了许多贵族官僚的利益,故而引起了一些不满,加以他刚愎自用,秉权过权,更成为朝野“清议”之的。
据《明史》本传,他死后遭谮毁而被削爵夺谥,籍没家产,其长子自缢身亡、次子和他的弟弟“俱发戍烟瘴之地”。
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朱东润在其名着《张居正大传·序》中概略性地评述道
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象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
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也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
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持到清明的时代,敌人由分化到崩溃,中国由安定走到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
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
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
“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
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
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
其实居正即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
他就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
问题在于:
既然“张居正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如此方能提高法制权威,进而使君威振作起来。
如果说张居正试图通过一系列自上而下地改革,化解现实社会危机,重振君主专制统治的纲纪,那末,对于王阳明来说,无论是其学说层面上推扬“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说,还是实际政治操作层面上颁“乡约”,力行“十家牌法”等,都无非是要将他拯救现实社会危机,维护君主专制政治秩序的道德原则融贯到社会实践行为之中。
就这方面而言,张居正和王阳明在思想本质上是完全相通的。
二
张居正不仅在应对社会实际问题上与王阳明有着完全一致的积极用世的态度,并与阳明一样,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秩序为最终目的,而且,他更从纯学术的角度对阳明心学有高度评价,尝谓:
“自孔子没,微言中绝,学者溺于见闻,支离糟粕,人持异见,各信其说,天下于是修身正心、真切笃实之学废,而训诂词章之习兴。
有宋诸儒力诋其弊,然议论乃日益滋甚,虽号大儒宿学,至于白首犹不殚其业,而独行之士往往反为世所姗笑。
呜呼!
学不本诸心而假诸外以自益,只见其愈劳愈弊也矣。
故宫室之弊必改而新之,而后可观也;学术之弊必改而新这,而后可久也。
”[22]可见他是在纵观学术发展大势,对汉唐诸儒以至程朱陆王之学作了认真比较以后,才选择、认同阳明心学的。
阳明心学对张居正影响最大者,乃是其所提倡的“狂者胸次”。
按:
关于“狂狷”精神,孔子曾曰: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23]孟子对此有进一步讨论,据《孟子·尽心下》记载:
“万章问曰:
‘孔子在陈曰:
盍归乎来!
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
孔子在陈,向思鲁之狂士!
’孟子曰:
‘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孔子岂不中道哉?
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问何如斯可谓之狂矣’’曰:
’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
’‘何以谓之狂也?
曰:
‘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汉唐诸儒似未留意于此一问题,而宋儒中二程对“狂”的论述最有影响,其言有曰:
“曾皙言志,而夫子与之,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谓狂也。
”[24]至于王阳明,“良知”的信念与实践使其在百死千难的危机中从容应对,并终于化解危机,经受住了人生严峻的考验,这自然更坚定了他对“良知”学说的自信。
他在与门人回顾江西平藩后那一段险恶的经历时曾说
……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乡意思在,我今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
[25]
他自谓“在南都以前”还有些“乡愿”的意思,而此后则具备了“狂者的胸次”。
这“狂者的胸次”如其所说,就是“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或如其弟子王畿所说是“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的熟化之境。
他后来在回答弟子们提出的“乡愿狂者之辨”时对这“狂者”境界有更进一步的诠释,曰
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
然究其心力,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坏矣,故不可以与入尧舜之道。
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
惟不克念,故洞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行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哉。
[26]
尽管他并不认为“狂者”就是“圣人”,“狂者的胸次”亦非最高理想人格境界,但他指出“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千仞之意”,这远远超胜常人,距“圣人”境界已不远,故而“一克念即圣矣”。
阳明所点示的这“狂者胸次”对其门下弟子影响甚深,正如他所说:
“予自鸿胪以前,学者用功尚多格局;自吾揭示良知头脑渐觉见得此意者多,可与裁哉。
”[27]阳明门下弟子多认得“狂者胸次”这个意思,故而呈露出浴沂舞雩的气象,这在理学家中是很罕见的。
而且受阳明心学影响,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出现了讲求自尊自信自立之狂者境界的思潮。
[28]
受时代思潮激荡、尤其是阳明心学影响,张居正颇具“狂者胸次”。
他在嘉靖后期短暂家居时有诗句云:
“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
百年有贵适,贵贱宁足论。
”[29]“作赋耻学相如工,干时实有杨云拙。
一朝肮脏不得意,翩翩归卧泛江月。
”[30]从中可以看出其有见于官场黑暗、政治混乱而生发出的归隐求适的情调。
但他又不象一般士大夫那样消极地追求归隐以获一己之自适,而对归隐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借评析魏晋竹林七贤的人格心态而申述己见道
……夫幽兰之生空谷,非历遐绝累者莫得而采之,而幽兰不以无采而减其臭;和璞之蕴玄岩,非独鉴冥搜者谁得而宝之,而和璞不以无识而掩其光。
盖贤者之所为,众人固不测也,况识有修短、迹有明晦,何可尽喻哉?
今之论七贤者,徒观其沉酣恣放、哺啜糟漓,便谓有累名教,贻祸晋室。
此年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独持绳墨之末议不知良工之独苦者也。
……余观七子皆履冲素之怀,体醇和之质,假令才际清明,遇适其位,上可以亮工弘化,赞兴王之业;下可以流藻垂芬,树不朽之声,岂欲沉沦泽秽无所短长者哉?
……自以道高才隽,深虑不免,政放言以晦贞,沉湎以毁质,或吏隐于廓庙,或泊浮于财利,纵诞任率,使世不得而羁焉。
然其泥蟠渊默,内明外秽,澄之不清,深不可识,岂与世俗之蒙蒙者比乎?
蝉蜕于粪溷之中,爝然涅而不缁者也。
……[31]
他认为,貌似放荡不羁的“竹林七贤”,并非自甘堕落,而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耽心自己因“道高才隽”而难免于害,这才晦贞毁质,纵诞任率,究其实尽皆“内明外秽”、出污呢而不染的耿介之士。
由此当可知道张居正何以会以嘉靖后期产生出归隐求适的念头。
至于上引文中以“幽兰”、“和璞”自喻其孤高自珍的心态,则既体现了心学高视自我的“狂者胸次”,又透露出居正本人待时而动的人生自信。
因此,嘉靖末年的张居正绝不是一位心灰意冷的隐士,而是尚未遇时的潜龙、匣中待试的宝剑,据行状载:
“太师体故孱弱,又倦游,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请告,艰苦得请归,则卜筑小湖山中,家僮锸土编第,筑一室三五椽,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扫煮茶洗药。
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反观,久之,即神气日益壮,遂下帷益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
”[32]从其当是生活内容看,与其说是厌倦仕途,倒不如说是为今后的进取积蓄能量,并期待着大用于世时机的到来。
他曾对耿定向说:
值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之时,“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弥天下之患。
顾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为慨叹也。
中怀郁郁,无所发舒,聊为知己一叹,不足为他人道也。
”[33]
尽管在万历朝的最初十年间,张居正出任首辅,实际掌握朝政,但他位高权重本就招来许多忌恨,而他所试图矫正嘉靖中期以来形成的因循疲软之风的考成法,事事立限、处处较真,使官员们感不便,有的还产生严重的危机心理,至于清丈田地、推选“一条鞭法“更触犯了一般士绅的既得利益。
这样,朝野上下就潜伏着一股伺机涌动的抵制新政的潮流。
如万历四年御史刘台即以门生身份上疏弹劾座主张居正,指责他“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
[34]五年,张居正遭父丧,神宗帝下诏“夺情”而不准其丁忧守制,这更成为官员们向张居正发起攻势的机会。
客观上,皇帝、皇太后的支持,司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使张居正抵制住了反抗潮流,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并取得了相当成效。
主观上,面对前所未有的阻力,张居正对于他所推行的表政坚执着义无反顾的信念。
这种信念,首先来源于他对自己所具有的大公至诚的自信。
他曾说
仆一念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诚专一,其作用处或有不合于流俗者,要之,欲成吾为国家士大夫之心耳。
仆尝有言:
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
又一偈云:
高岗虎方恐,深林蟒正嗔。
世无迷路客,终是不伤人。
[35]
既然自己坚信于心无愧,所作所为尽皆出于公心,也就不在乎别人物议了。
其次,这种信念来源于他不顾身家性命的献身精神和甘于做祭坛牺牲的烈士心态。
他自谓“二十年前曾有一弘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
……有欲害虫取吾耳鼻,我亦欢善施与,况诋毁而已乎?
”[36]又云
不谷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欲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
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
[37]
其三,这种信念又与其忧国忧民的情怀起超然的胸襟密切相关。
一方面,张居正一直以一身而系天下安危自任,多次向人表白“苟利社稷,死生利之”,如在《答藩伯吴小江》中说:
“今赖天地宗社之灵,中外颇称宁谧。
惟是黎元穷困,赋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在念。
”[38]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是他敢于去克服重重阻力、推行新政的强大精神支柱。
另一方面,他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圣贤之学有举世不见知而无悔者”,“则虽不见知于世而无闷也”,[39]故其谓
吾平生学在师心,不蕲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
[40]
不谷生于学未有闻,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则诚自信而不疑者。
[41]
这种受阳明所倡狂者精神影响形成起来的高傲自得的思想境界,“不见知于世而无闷”的超然胸襟,无疑是他笑对不时扑面而来的反张潮流的内在精神支柱。
张居正虽然不是王学传人,但确实具备了阳明心学修养。
正是这修养,使他形成起超越制度、超越世俗毁誉的独行的人格,并获得了内在与外在的两重自由。
而若无这修养,他在灸手可热的权力面前终将会成为严嵩或魏忠贤式的人。
从此一角度讲,张居正的出现应该是阳明心学的一大积极成果。
三
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张居正与王阳明本人似乎并无什么直接接触,但在他交往的朋友中有很多心学人物,其中如聂豹、胡直、罗洪先、罗汝芳、赵贞吉、耿定向、周友山等还是知名的心学学者。
这就使张居正与阳明后学的关系很值得予以分析。
阳明殁后,门下弟子裂变,出现了诸多心学流派。
张居正在与各种心学广泛接触中,对聂豹、罗洪先一派最感兴趣。
聂豹,字文蔚,江西永丰人,后因徙家双溪,故自号双江。
其学“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说,与辩难,心益服”,[42]认为“良知之学”“是王门相传指诀”;[43]后巡按应天,继续与阳明讲论良知之学,“锐然以圣人为必可至者”,[44]并重刻《传习录》、《大学古本》等阳明着作,服膺阳明“致良知”说之志益坚;乃至阳明既殁,又“以弟子自处”[45]故后世学者谓之“出于姚江”,[46]不无道理。
聂豹之学的特点在于提倡“良知本寂”说,而此说颇遭“同门”学者非难,《明儒学案》卷十七《江右王门学案·聂豹传》对之记载甚详。
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
他虽曾服膺“守宋人之途辙”[47]的罗伦之为人,又曾师事以“朱子之学”为“圣人之学”[48]的李中,但他年十五,闻阳明于赣州开府讲学,心即向往;比《传习录》出,手抄玩读,竟至废寝忘食,欲往受业,父不可而止。
年二十五,师事同郡江右王门学者黄宏纲、何廷仁,自是日究阳明“致知”旨。
其后,访晤王畿、王艮、唐顺之、赵时春、邹守益、欧阳德诸王门学者,心学修养日深。
年三十九,始闻聂豹的“良知本寂”说发展为“良知本静”说,谓:
“此心中虚无物,旁通无穷,无内外可指、动静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今来,浑然一片,而吾身乃其发窍,非形质所能限也。
”[49]王门诸子多承认他学宗阳明,且以之为师。
[50]
张居正认同聂豹、罗洪先归寂求虚的心学理路,说:
“窃谓学欲信心冥解,叵但从人歌哭,直释氏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已非分耳。
昨者伏承高明指未发之中,退而思之,此心有跃如者。
往时薛君采先生亦有此段议论,先生复推明之,乃知人心有妙万物者,为天下之大本,无事安排晨,此先天无极之旨也。
夫虚者道之所居也,涵养于不睹不闻,所以致此虚也。
虚则寂,感而遂通,故明镜不屡照,其体寂也。
虚谷不疲于传响,其中壳也。
今不于其居无事者求之,而欲事事物物求其当然之则,愈劳愈疲也矣。
”[51]这里,他除了强调心学的自信自悟外,更对归寂以致虚、致虚以通感的心学思路有着深切体悟。
不过,张居正接受心学思想影响,并非为了追求个体愉悦,而是为解决人生进取中的自我心理障碍,从而更好地实现其经邦济国的现实目的。
他在《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辨》中说
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食哉;周公《立政》,其克诘尔戎兵:
何尝不欲国之富且强哉!
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之辨、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
[52]
这样一种基本思想精神,使他一方面把那些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心学家引为“同志”,时常与他们相互切磋砥砺,另方面对那些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心学末流深恶痛绝,斥之为“腐儒”、“俗儒”。
在致周友山的尺牍中,他反复申述了这种爱憎分明的态度,如说:
“今人妄谓:
孤不善讲学者,实为大诬。
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事背于尧、舜、周、孔之道?
但孤所为,皆欲身体力行,以是虚谈者无容耳!
”[53]“吾所恶者,恶紫之夺朱也、莠之乱苗也、郑声之乱雅也、作伪之乱也。
夫学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须臾离者。
言喜道学者,妄也;言不喜道学之为学,不若离是非、绝取舍,而直认本真之为学也。
……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实好学者矣。
”[54]所谓“真认本真”,亦即阳明之“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就是要真切体认自家虚灵静寂的心体,以之为天下大本,并据之行事。
这使他与聂豹、罗洪先等阳明后学息息相通。
但是,张居正特别强调结合实际,要求身体力行,反对以虚见为默证。
他尽管在心学上几无创造性理论,但也绝非只会拾人牙慧,而是从现实的改革事业和富国强兵的需要出发,对儒学史上分化出来的内圣与外王两派取长补短,致力于二者的结合,以自成一定之言。
他在《答楚学道胡庐山论学》中说
承教虚寂之说,大而无当,诚为可厌。
然仆以为近时学者皆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故其说屡变而愈淆。
夫虚故能应,寂故能感。
《易》曰君子以虚受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诚虚诚寂,何不可者?
惟不务实得于己,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异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谓寂然者,宜其大而无当、窒而不通矣。
审如此,岂惟虚寂之为病?
苟不务实得于己,而于言语名色中求中,则曰致曲、曰求仁,亦岂得为无弊哉!
[55]
在《答西夏直指耿楚侗》中云
辱喻谓比来涉事日深,知虚见空谈之无益,具见丈近精实处。
区区所欲献于高明者,下在于此。
但此中灵明,虽缘涉事而见,不因涉事而有。
倘能含摄寂照之根,融通内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于外得矣。
[56
在《答胡剑西太史》中亦曰
弟甚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
窃以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
自起居言动动之微、至经纶天下之大,无一事不有微权妙用,无一事不可至命穷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弹也,即圣人不能尽也,诚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
兄固深于《易》者,暇时更取一观这,脱去训诂之习,独观昭旷之原,独复有得力处也。
[57]
他把“虚”与“实”看作是种体用相即的关系。
所谓“昭旷之原”、“寂照之根”、“此中灵明”,指的就是作为天下之大本的心体;这种心体的本来状态是“诚虚诚寂”的。
但体不离用、用不离体,只有努力从事“实得于己”的工夫,“融通内外之境”,把“虚”于“实”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经纶天下”,“成变化而行鬼神”。
如果“不务实得于己”,离用以求体,必然流为“虚见空谈”,“窒而不通”。
当然,如果离体以求用,不去认真领会“致曲”、“求仁”的精神实质,也将化为虚文,产生很大的流弊。
张居正的这种思想显然同聂豹、罗洪先的归寂说有很大差别。
张居正同阳明后学思想上的差异,在其《答罗近溪宛陵尹》中也有所体现。
他说:
“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
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纷纠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
仆每自恨优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妄本觉可以照了,然比利时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
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辨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
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
孔子云’道不远人’;今之以虚见为默证者,仆不信也。
”[58]而他所以与聂豹、罗洪先、耿定向、胡庐山、罗汝芳等反复论学,除了共同的心学旨趣外,还有因见于阳明后学“以虚见为默证”之弊,而欲以实用救之的意图。
但学说思想上的重大差异,又使得这种改造阳明后学的意图往往落空。
这从张居正与泰州后学耿定向、罗汝芳的关系可略见一斑。
耿定向,字在伦,号天台,湖北黄安人。
黄宗羲曾对其学术主旨评论道:
“先生之学,不尚玄远,谓’道之不可与愚夫愚妇知能,不可以对造化通民物者,不可以为道,故费之即隐也,常之即妙也,粗浅即精微也’。
其说未尝不是,而不见本体,不名打也世情队中。
”[59]由于“不见本体”而“不尚玄远”,所以耿定向特别强调人伦日用。
并且,他还反对一味虚见空谈,提倡静以应感、虚以求实,如谓:
“只此无声无臭,是为真常,凡涉色象名号者,卒归消灭;只此不为不欲,是为本心,凡务阔大放散者,终堕堑坑;只此不学不虑,是为天德,凡由意识安排者,便是人为;只此庸言庸行,是为妙道,凡务高玄奇诡者,即是虚妄。
”[60]这使张居正不仅把他引为思想上的“同志”,而且更希望他成为学以致用的榜样。
张居正不仅令其以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具体负责清田之事,欲借此“验其学之分际,不知能否副所期否?
”[61]而且还曾向耿定向许以辛勤供职成功以后的酬报:
“借重闽中已及三载,拟将简置内台,觊以助仆之浅薄”。
只是因耿定向遭父丧而回家丁忧守制,张氏才不得不很遗憾地说:
“忽闻令先公之计,无任忉怛。
且二三年间,仆将复有明农之请,不能为国家早进贤俊,置之周行,即死有余憾矣。
”[62]但就耿定向这一方面来说,尽管在福建也很努力,但不仅他本人无意照张居正的设想去发展,而且对张氏作风亦颇有看法,还曾“苦言”相劝,如据焦竑《澹园集》卷三三《耿天台先生行状》载:
“自今上临御,江陵励精求治,提衡宇内,宴然如一。
后浸为苟急,不类初政。
先生以桑梓之谊,又雅为所推午,屡进苦言,江陵卒其规不以受,而先生自此疏矣。
”正因为这“疏”,使得耿定向在张居正病逝后未被倒张者列为张党,从而才有可能在万历十二年被重新启用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罗汝芳,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
他是泰州学派着名平民儒者颜山农的弟子,以讲求“赤子之学”为学术主旨,认为道在此身,身是赤子,良知良能,不学不虑,并在嘉靖、万历年间以善于讲学而闻名于士林。
张居正与罗汝芳义往甚早,且引为“知己”,但又深知与罗氏学术主张有差别,故而一方面承认为罗汝芳在太湖“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此固罗近溪本来面目然”,另方面仍以“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纷纠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63]相劝。
及至嘉靖三十九年罗汝芳升任宁国知府时,张居正作《赠罗惟德擢守宁国叙》以送之,仍在强调其学以致用的见解,谓:
“断蛟龙,刳犀革,遇磐错而无厚,干将诚利矣。
匣而弗试,利无从见也。
是故士不徒学,而惟适用之贵,裕内征外,懋德利躬,此励己之符而亦镜物之轨也。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惟德其念也!
”[64]但罗汝芳始终有着他自己的思想,他不仅要学以为仕,而且更要以仕为学,即令其治下皆兴好学之心、皆能知忠知孝,故而“殆守宁国,教化益行,郡堂无鞭朴声,且惟讲学西水、志学二处,以崇学育才为功课”。
[65]据传他做宁国知府时,“集诸生会文讲学,令讼者跏跌公庭,敛目观心,用库藏充馈赠,归者如市。
”[66]会文讲学的场所竟是讼者纷纭的公庭,讼者的呶呶乃易为跏跌静坐的冥默,封建政府的公库居然成为馈赠“罪犯”的财源;这样的知府,不执行封建政府律令,以“罪犯”为良善,可谓绝无仅有。
时任通政的杨时指责他“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逾闭荡检,反道乱德,莫此为甚。
”[67]更重要的是,罗汝芳热心于讲学,积极组织讲学的集会活动,这自然要激起张居正的不满。
万历元年,张居正当国,罗汝芳恰丁忧起复,二人相见,张氏“问山中功课,先生曰:
‘读《大学》、《论语》,视昔差有昧耳’。
江陵默然。
”张居正先将其补为山东东昌知府,三年任期满后即令其升任云南副使,再三年转为云南参政,看来是想将罗汝芳置于云南西陲教化那些未开化的山民,以发挥其讲学才能,同时又不会对新政推展有任何阻碍。
但罗汝芳却并不满足于在云南讲学,或从事兴修水利的实务,而更乐意在京师开讲,张居正也就只好将之永远清除出官场了:
“万历五年,进表,讲学于广慧寺,朝士多从之者。
江陵恶焉。
给事中周良寅劾其事毕不行,潜往京师,前勒令致仕。
”[68]
尽管曾经深受阳明心学影响,又与阳明后学有着广泛的私人交往,但政治家而兼学问家的张居正,主要是以政治眼光看待、裁量学术思想的。
在《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中,他具体指出当时一批讲论心学的“同志”在学术、政治两方面存在的流弊,并较详尽地阐述了他的思想主张和对应之策,说
夫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
然窥其微处,则皆以聚党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庄子所谒其嗌言若哇,佛氏所谓虾蟆禅耳!
而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惑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
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救者所深忧也。
《记》曰:
凡学,官先事,士先志。
士君子未遇时,则相与讲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所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一门以为学者也。
……假令孔子生今之时,为国子司成,则必遵奉圣祖学规以教胄,而不敢失堕;为提学宪臣,则必遵奉皇上敕谕以造士,而不敢失堕:
必不舍其本业而别开一门,以自反古之罪也。
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之立教者,而甘蹈于反古之罪,是尚谓能学孔矣乎?
明兴二百余年,名卿硕辅勋业恒赫者,大抵皆直躬劲节、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讲学者每诋之曰:
彼虽有所建立,然不知学,皆气质用事耳。
而近时所谓知学,为世所宗者,考其所树立,又远出于所诋之下;将令后生小子何所师法耶?
此仆所未解也。
仆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
……毋以前不足学而轻事诋毁,毋相与造为虚谈,逞其胸臆,以挠上之法也。
[69]
为了达到“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的目的,就必须统一思想,使学术严格地绝对从属于政治。
这就难怪要发生《明儒学案》卷三二所记之事:
“江陵秉政,东溟上疏条九事以,以讥切时政,无非欲夺其威福,归之人主。
其中有宪纲一第,则言两司与巡方抗礼,国初制也,今之所行,非是。
江陵即出之为广东佥事以难之,使之为法自敝也。
”而且,张居正更大力整饬学政,严禁聚徒讲学,诏毁天下书院,规定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不许别标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