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的嬗变.docx
《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的嬗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的嬗变.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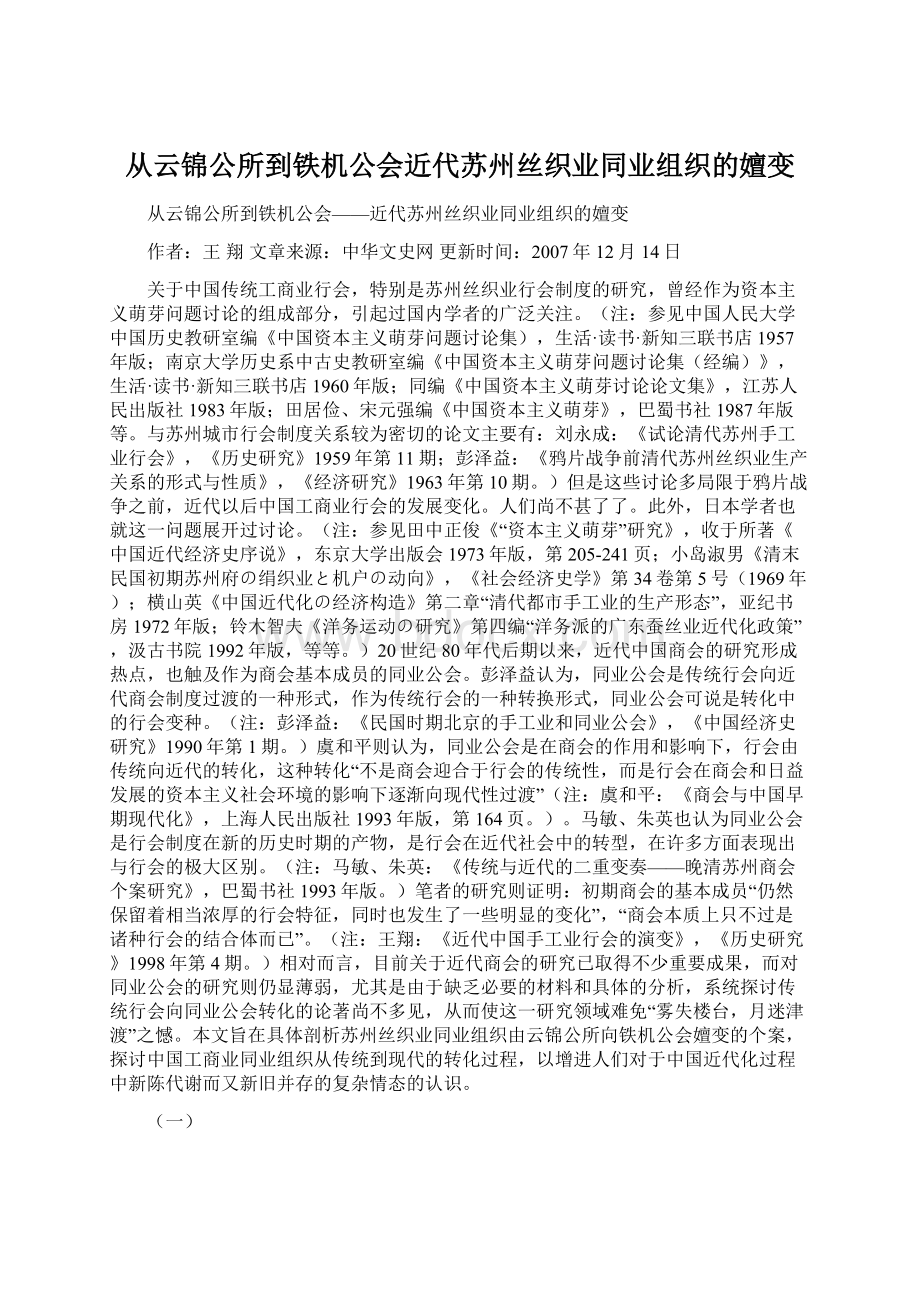
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的嬗变
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的嬗变
作者:
王翔文章来源:
中华文史网更新时间:
2007年12月14日
关于中国传统工商业行会,特别是苏州丝织业行会制度的研究,曾经作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组成部分,引起过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注: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古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经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同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巴蜀书社1987年版等。
与苏州城市行会制度关系较为密切的论文主要有:
刘永成:
《试论清代苏州手工业行会》,《历史研究》1959年第11期;彭泽益:
《鸦片战争前清代苏州丝织业生产关系的形式与性质》,《经济研究》1963年第10期。
)但是这些讨论多局限于鸦片战争之前,近代以后中国工商业行会的发展变化。
人们尚不甚了了。
此外,日本学者也就这一问题展开过讨论。
(注:
参见田中正俊《“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收于所著《中国近代经济史序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版,第205-241页;小岛淑男《清末民国初期苏州府の绢织业と机户の动向》,《社会经济史学》第34卷第5号(1969年);横山英《中国近代化の经济构造》第二章“清代都市手工业的生产形态”,亚纪书房1972年版;铃木智夫《洋务运动の研究》第四编“洋务派的广东蚕丝业近代化政策”,汲古书院1992年版,等等。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近代中国商会的研究形成热点,也触及作为商会基本成员的同业公会。
彭泽益认为,同业公会是传统行会向近代商会制度过渡的一种形式,作为传统行会的一种转换形式,同业公会可说是转化中的行会变种。
(注:
彭泽益:
《民国时期北京的手工业和同业公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虞和平则认为,同业公会是在商会的作用和影响下,行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这种转化“不是商会迎合于行会的传统性,而是行会在商会和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向现代性过渡”(注:
虞和平: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
马敏、朱英也认为同业公会是行会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是行会在近代社会中的转型,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行会的极大区别。
(注:
马敏、朱英:
《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
)笔者的研究则证明:
初期商会的基本成员“仍然保留着相当浓厚的行会特征,同时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商会本质上只不过是诸种行会的结合体而已”。
(注:
王翔:
《近代中国手工业行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相对而言,目前关于近代商会的研究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而对同业公会的研究则仍显薄弱,尤其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材料和具体的分析,系统探讨传统行会向同业公会转化的论著尚不多见,从而使这一研究领域难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之憾。
本文旨在具体剖析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由云锦公所向铁机公会嬗变的个案,探讨中国工商业同业组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过程,以增进人们对于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新陈代谢而又新旧并存的复杂情态的认识。
(一)
行会制度是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同时又是商品生产发展不够充分,社会分工不够发达,商品市场不够广阔的产物。
它由同一城镇中的同业者或相关职业者所组成,主要功能一是联结同业,以与不利于己的人事相抗衡;二是避免竞争,维持本行业共存共荣的垄断地位。
在中国,苏州是行会制度发展得较为成熟的一座城市,其中尤以丝织手工业行会的历史最为悠久,特点最为鲜明,作用最为显著。
早在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苏州丝织业同行就曾建立过“机圣庙”(注:
顾翰:
《重建苏城机神庙碑记》(乾隆五十七年),转引自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其具体情形不得而知,大致可以说是行会组织的雏形。
元贞元元年(1295年),苏州丝织业同行在元妙观内设立吴郡机业公所,明万历年间改建机房殿,以为行会会所,并“立有行头名色”(注:
孙珮:
《苏州织造局志》卷11,“祠庙”,转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84页。
)。
清道光二年(1822年),在祥符寺巷成立了云锦公所,据称由“丝织、宋锦、纱缎业合建”(注:
苏州市工商联编:
《苏州清代会馆公所资料摘记》,见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苏州工商经济史料》第1辑,第227页。
)。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行会曾经对手工业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明末清初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品市场的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商业资本向生产过程的渗透,行会组织越来越成为丝织手工业发展的桎梏。
苏州丝织业行会极力维护小生产的方式,竭力用严格的行规来限制竞争,从产品规格、数量、价码、市场到生产技术,以及开设铺坊的规模和招收徒工的数目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实行硬性规定。
道光二年的《元和县严禁机匠借端生事倡众停工碑》规定:
“自示之后,各乡匠揽织机只,概向机房殿书立承揽,交户收执。
揽机之后,务宜安分工作,克勤克俭,计工受值,不得将货具经纬私行侵蚀,以及硬摄工钱,借词倡众停工。
”(注: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4-25页。
)这显示出劳动契约的订立受到行会的强制。
缔约地点必须在机业行会所在地的“机房殿”,契约条文必须由机业行会制定,而该契约书也必须交给机业行会“收执”。
这样一来,如契约内容有违反行规之处,就无法得到行会的认可,无法完成缔约的手续。
南京丝织业中也有相同规定。
《江宁县缎机业行规碑》规定:
“一议各号无论生意好歹,如有机范出来,有无‘承管’连环互保者,统归一律开账,不准自行搭找料户。
如不遵议,察出照规究罚。
”(注:
江苏省博物院编: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66页。
)此处所谓“承管”的角色,颇类似于一般所说的“行头”。
两地资料相互印证,可见在资本与劳动力之间,有行会强行楔入,竭力阻挠两者的自由结合。
行会还以同乡同行的地缘关系和宗法关系为纽带,固结团体,排斥竞争,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
碑刻资料记载:
“苏城花素缎机生业,向分京、苏两帮,各有成规,不相搀越。
惟以上机经纬,造成缎匹,向非机匠一手一足之力,尚有手艺数项,赖此以生。
如机张之须用泛头也,有结综掏泛一业;如丝之须练也,有槌丝一业;如经之须接也,有牵经接头一业;如织花缎也,有上花一业。
以上四业,均系世代相传,是以各归主顾,不得紊乱搀夺。
”据说这种“成规”,“数十年来,向章如此”。
各行业的操作技术,“均系世代相传”,行业成员“靠此养象糊口,别无生计”,倘若“群起效尤,占无底止”,势必使其丧失垄断地位,甚至会被排挤出市场,“情同绝命”。
(注:
《元长吴三县为花素缎机四业各归主顾不得任意搀夺碑》(光绪二十四年),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46页。
此碑虽立于光绪年间,但从碑文中所谓“数十年来,向章如此”来看,用以说明清前期情况,似无不妥。
)
行会把“兴办善举”,周济贫困,养生送死作为“第一要务”,对于年老孤贫、病残无依者,生贴养赡,死助殓葬,规定“捐厘助济绸业中失业贫苦,身后无备,以及异籍不能回乡,捐资助棺,酌给盘费,置地设家等善事,自当永远恪遵”。
(注:
《苏州府为绸缎业设局捐济同业给示立案碑》(道光二十三年),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6页。
)行会的“兴办善举”,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手工业者身受的苦难,但同时也具有阻滞手工业者分化,遏制新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的负面社会效果。
在师傅与徒弟之间,则表现为一种拟制的血缘关系。
“置徒授业,皆有先例”。
“凡置徒弟,教养待遇总与自己子弟相同。
徒弟不得随意行动,成业之后,须终身敬师,无负师恩。
”(注:
《支那经济全书》卷12,东京1908年刊印,第319页。
按,此为日本人调查记录的杭州丝织业行会的规约,苏州丝织业行会的情况同样如此。
见同书卷12,第259页。
)这体现出行会内部的家族宗法制原则。
在行会的重要事务中,迎神赛会、祭神祀天占有突出的位置。
行会的会馆、公所既是成员集会议事的场所,又是同业祭祀神道的地点。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据《吴门表隐》记载,苏州丝织业祀奉的神道,从黄帝、先蚕圣母到染色仙师、黄道仙婆,多达26位。
(注:
顾震涛:
《吴门表隐》“寺观”,苏州市博物馆藏。
)遇到神祖诞辰,便要举行迎神赛会,祭祀祝福,以此加强同行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可借中国民间对神祖的景仰和敬畏,加强对行会成员的监督和控制。
丝织工匠若有违反行规行为,除了进行赔偿之外,“须进一步将该料户之姓名揭示于祖庙(机神庙)、会所……令公众人等皆知该料户之不仁系其自身之罪戾”,以防“酿成纷议,损害行会之信用”。
(注:
《支那经济全书》卷12,第318页。
)
凡此种种,凸显出旧式行会组织上的封闭性、业务上的垄断性和技术上的保守性。
行会与官府相互为用,将行会力量与政治权威结合起来,防范资本的渗入,限制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墨守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工具,以过时的陈规陋习妨碍丝织生产过程中技术分工的发展,力图遏制同业竞争的加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也就阻滞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与行会制度是不相容的,“工场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注:
恩格斯: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87页。
)。
原因就在于行会制度用超经济的强制方法使手工业生产踏步不前,严重地限制和阻碍着小生产者的分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然而,明清时代,商品经济毕竟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市场相对扩大,竞争也随之越发激烈,行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日趋尖锐,破坏行规的现象与日俱增,行会内部的分化也不断加剧。
苏州丝织业行会对于阻挠同业间的竞争,防范资本的渗透,限制劳动力的自由买卖,消除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从前述道光二年元和县重申行规,要求揽织机匠“概向机房殿书立承揽”,“严禁机匠借端生事俱众停工”的事例可见,虽然行会企图依靠官府,用政治权力来“重整”、“重申”行规,把已经逾越范围的丝织手工业重新纳入传统行规的轨道,但是在商业资本渗入生产过程的情况下,行会制度已经开始动摇,因为行会行规的强制职能是“向章如此”,天经地义的,需要重申则表明已经不为人们信守,表明当时已经存在不去机房殿承揽,而由资方与劳方自由组合的情况。
事实上,所谓“倡众歇作,另投别户”(注:
《元和县严禁机匠借端生事俱众停工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4页。
)的情况,确已时有发生,显露出行会的功能日渐削弱,行会制度渐趋式微的征兆。
(二)
同治初年,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清政府重新在苏州恢复了统治秩序,工商业生产逐渐复苏,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瘫痪的云锦公所再度成立。
以往论者,多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后苏州工商业会馆公所的恢复,视为旧式行会的卷土重来,把会馆公所的“重建”与行会组织的“重演”混为一谈,认为“行会的重建体现着封建统治秩序在城市里的恢复,对城市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造成极其严重的障碍”,“资本主义萌芽向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道路几乎完全被堵塞”。
(注:
茅家琦主编:
《太平天国通史》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331页。
该节内容为段本洛等所撰。
其实,彭泽益于60年代即已提出类似看法。
参见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如前所述,成立于道光二年的云锦公所,原本确是苏州丝织业的行会组织。
不过,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苏州丝织业中的“帐房”势力急剧扩展,阶级关系日渐明朗,阶级对立日益加剧,行会组织越来越无法把各个不同阶级的人们包容在一起,越来越难以以全行业最高代表的面目出现。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激荡风云,更加速了传统统治秩序和旧式行会组织的瓦解。
行规无形中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