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有生之年遇见你.docx
《美文有生之年遇见你.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美文有生之年遇见你.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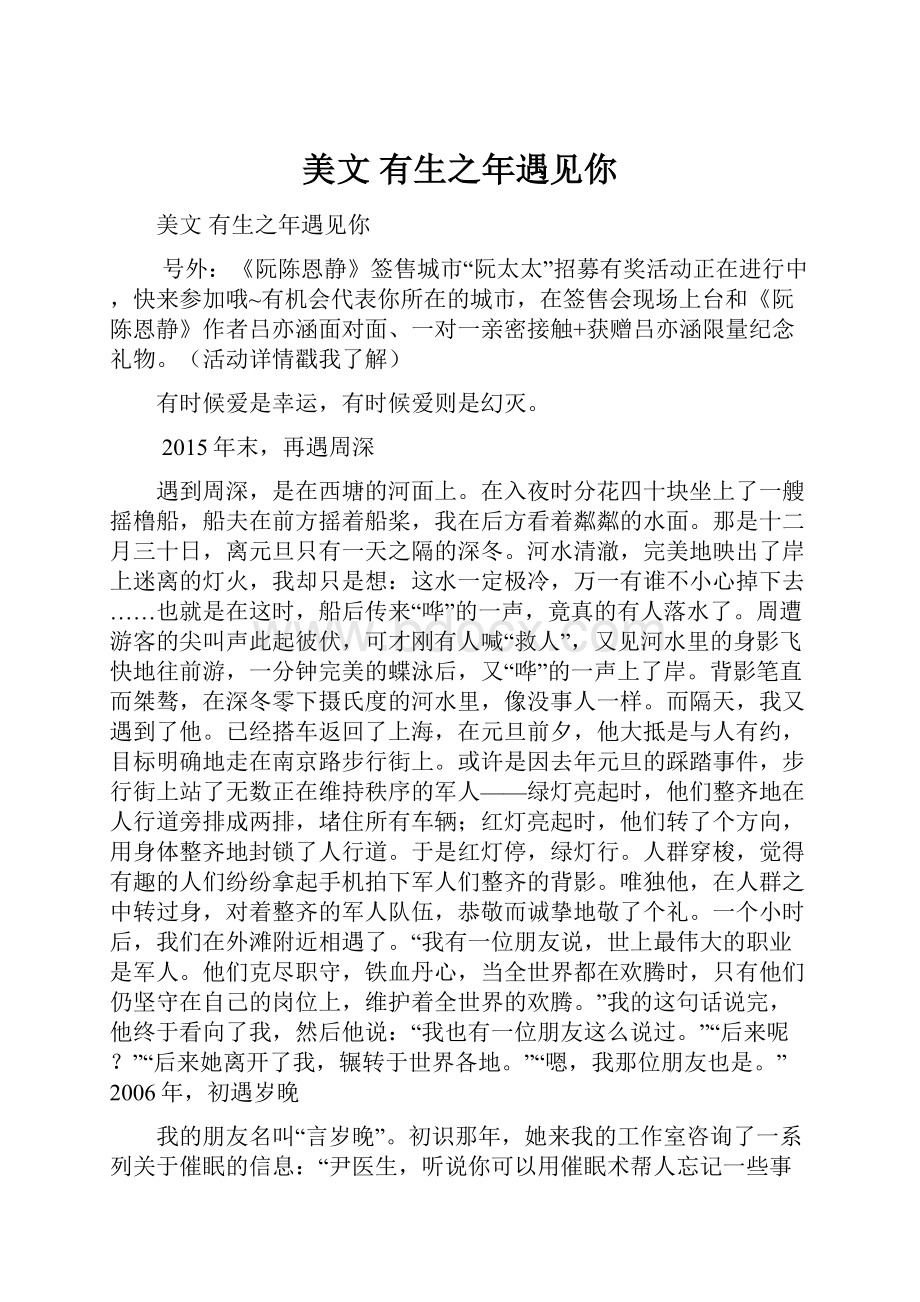
美文有生之年遇见你
美文有生之年遇见你
号外:
《阮陈恩静》签售城市“阮太太”招募有奖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参加哦~有机会代表你所在的城市,在签售会现场上台和《阮陈恩静》作者吕亦涵面对面、一对一亲密接触+获赠吕亦涵限量纪念礼物。
(活动详情戳我了解)
有时候爱是幸运,有时候爱则是幻灭。
2015年末,再遇周深
遇到周深,是在西塘的河面上。
在入夜时分花四十块坐上了一艘摇橹船,船夫在前方摇着船桨,我在后方看着粼粼的水面。
那是十二月三十日,离元旦只有一天之隔的深冬。
河水清澈,完美地映出了岸上迷离的灯火,我却只是想:
这水一定极冷,万一有谁不小心掉下去……也就是在这时,船后传来“哗”的一声,竟真的有人落水了。
周遭游客的尖叫声此起彼伏,可才刚有人喊“救人”,又见河水里的身影飞快地往前游,一分钟完美的蝶泳后,又“哗”的一声上了岸。
背影笔直而桀骜,在深冬零下摄氏度的河水里,像没事人一样。
而隔天,我又遇到了他。
已经搭车返回了上海,在元旦前夕,他大抵是与人有约,目标明确地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
或许是因去年元旦的踩踏事件,步行街上站了无数正在维持秩序的军人——绿灯亮起时,他们整齐地在人行道旁排成两排,堵住所有车辆;红灯亮起时,他们转了个方向,用身体整齐地封锁了人行道。
于是红灯停,绿灯行。
人群穿梭,觉得有趣的人们纷纷拿起手机拍下军人们整齐的背影。
唯独他,在人群之中转过身,对着整齐的军人队伍,恭敬而诚挚地敬了个礼。
一个小时后,我们在外滩附近相遇了。
“我有一位朋友说,世上最伟大的职业是军人。
他们克尽职守,铁血丹心,当全世界都在欢腾时,只有他们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维护着全世界的欢腾。
”我的这句话说完,他终于看向了我,然后他说:
“我也有一位朋友这么说过。
”“后来呢?
”“后来她离开了我,辗转于世界各地。
”“嗯,我那位朋友也是。
”2006年,初遇岁晚
我的朋友名叫“言岁晚”。
初识那年,她来我的工作室咨询了一系列关于催眠的信息:
“尹医生,听说你可以用催眠术帮人忘记一些事?
”我点头,然后看她点了一支烟,开始讲一段陈年旧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周深与言岁晚。
初识那年,两人就读于A大的商贸系。
五月鸣蝈,六月精阳,极炽热的教室里,选修课教授正对着一系列描绘军人的画作侃侃而谈:
“军人一旦披上了铠甲,那就是为战争、为活着了……”坐在角落的女生突然举起手,还不等教授回应,就径自站起身:
“老师,我觉得您的话是有误的。
军人和常人一样,有血、有泪、有家庭,怎么能说他仅因战争而活呢?
有国才有家,他们为之而活的,是国这个大家和自己的小家!
”话音落下,偌大的教室里鸦雀无声,只坐在后排的周深嘴角弯了弯,对身旁的同学说:
“这丫头是叛逆期还没过完吧?
竟连张教授的话也敢反驳。
”可同学却像是见到了新大陆,在周深莫名其妙的目光下,瞪大眼睛:
“同班近一年,第一次听到她开口说话呢!
”周深挑了挑眉。
“真的!
不信你问问别人,大家都在背地里说,这言岁晚不是哑巴就是自闭呢!
”他这才往那个叫“言岁晚”的女生身上多瞧了两眼——的确,要不是在今日的课堂上见识了这一幕,恐怕他永远也不知同班还有这么一个女生。
就像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的人,每天都在不知不觉中擦肩而过。
可若有一天你记住了她,便会奇怪地发觉,其实你们常常会不期而遇。
比如几天后,他又遇到了她——在兼职的奶茶铺外,岁晚闷声不响地调配着饮料,沉默得如同在班级里。
原本有序的队伍却突然有人插队,一名看上去很嚣张的女生突然插到了第一位。
女生在这一带大概是臭名昭著,所以后面的人也没敢说什么。
倒是一直闷不吭声的岁晚在女生点了珍珠奶茶后,将手上的珍珠奶茶包好,然后递给了女生身后的人。
“喂!
你眼瞎了啊?
没看到老娘排第一个吗?
”谁知岁晚竟没理她,只是平静地看向下一名排队者:
“你要什么?
”“哎,老娘说……”这下子,面色淡然的女子终于将视线移到了她的身上:
“我没眼瞎,倒是你可能脑残了,连排队的常识都不懂。
”人群里突然暴发出一阵大笑,谁也没想到这沉默的女生竟有这样好的口才——嗯,还有这样好的胆识。
那时周深就在排队的人群里,清楚地看着嚣张的女生气红了脸,还有临走时恶毒地投到岁晚身上的警告的目光。
就像是觉得很有趣一样,他含笑的眼在言岁晚身上定了许久。
然后,他转头问身后的人:
“这奶茶铺什么时候关门?
”“晚上六点吧。
”“好。
”很奇怪,从这天起,奶茶铺收摊之后,在岁晚匆匆赴往下一份兼职之时,总会在途中遇到这个传说中的“商贸系男神”。
一连六天,周深都若有似无地跟着她。
有趣的是,岁晚一开始还以为是巧合,后来就像是有所怀疑。
第N次见到他时,有些疑惑地蹙了一下眉头;可第N+1次见到他时,还是疑惑地蹙一下眉头,那表情就像是在说:
“应该是巧合吧?
他怎么可能跟着我?
”呵,这家伙,反应是不是慢了点啊?
一直到第七天,言岁晚的表情才终于有所改变——是的,上回那个嚣张的女生竟带着一帮人朝她围过来,面上带着欲破表的狠毒神色:
“这下堵到你了吧?
让你再嚣张!
”言岁晚慌了,那么多人全堵在她面前……可那群人还没做什么呢,后边又传来一把凑热闹的声音:
“干什么呢?
”是周深。
“周深?
”就连嚣张的女生也认识他,“干嘛?
我堵人关你什么事?
”“是不关我的事,可问题是你堵到我想追的人了。
”他的笑容里颇有点骜傲的味道,伸手在女生肩上拍了拍,“卖我个人情怎么样?
下回你要真出了事,哥一定让人给你帮忙。
”A大里有两拔特殊的人群:
一拔成绩低端家世却高端,利用各种关系踏进了A大的校门;一拔家世平平成绩却顶尖,被A大用免除学杂费用等各种方法请进来——他属于前者,而她属于后者,而刚好,皆处在金字塔顶端。
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周深说出这种话,自然是有说服力的。
于是人群没多久便一哄而散了,余下他和她,在入了夜的公交车站牌前,一个依旧双目含笑,一个渐渐又恢复到一贯的面无表情。
这是岁晚第一次跟他说话:
“你知道她们要堵我?
”“不知道。
”她垂下头,正不知该说些什么时,又听到他说:
“但猜到了。
”岁晚这才想起这男子几天里若有似无的“跟踪”——莫非是那天看到了她和那个女生发生争执,怕她出事才跟在她身边的?
可事实上,围堵事件过去后,周深也还是常常出现在她身边。
那天她正赶着到市中心去当家教,同样是在公交车站牌前,头一转,又看到了他——不,不是跟踪,那厮对她简直称得上是光明正大地跟随了:
每次下课,她前脚踏出教室,他后脚便跟上;在奶茶铺时,他总在她身旁晃;赴下一份兼职时,他就跟在后方,踩着她的身影。
而她这个反应永远慢半拍的家伙,这次终于走到他面前,疑惑地问他:
“为什么还跟着我?
”“不是‘跟’,是‘追’。
”周深的眼中含着倜傥的微笑。
“啊?
”“还看不出来吗?
我是在追你啊。
”言岁晚愣住。
公交车站上的移动传媒正播放着广告,鲜活的色彩衬着逐渐笼罩的黑夜。
周深对着那个广告上指了指:
“你是不是想去看这场画展?
”是的,移动传媒上播放的,正是近期将举办的波兰艺术家画展。
她每次在这里等车时,总会在那片绚丽的色彩前伫立良久。
而他说:
“我有票。
”“为什么?
”商学院的男生怎么会对这些感兴趣?
“因为我想追你啊。
”他还是那么倜傥地笑着,“然后,你同意吗?
”怎么可能同意?
对于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陌生的男子。
可男子说:
“不同意没关系啊,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追求,可你得誓死捍卫我追求你的权力。
”“为什么?
”“因为我帮过你啊。
”其实彼此心里都明白,言岁晚没拒绝周深并不是因为上一回的帮忙,而是——对,她实在是太想看那一场画展了!
班上不久后便开始有“周深看上了言岁晚”的流言传出——他向来都是风云人物,长得帅,又会做人,再加上一个据说挺传奇的背景,在这学校里的风评简直是NO.1,怎么会看上那么个……呃,“普通”的女生?
就连岁晚自己也不相信。
只是周深这人自来熟的功夫一流,没多久,岁晚竟也习惯了这个“商贸系男神”的存在。
就连他大周末开着跑车来接她去看展,众人目光惊愕时,她也能安之若素地坐进车里。
其实周深不懂画,也没兴趣看画,在看画展的一整个下午,言岁晚始终在认真地看画,而他,则在认真地看她。
直到来到一幅油画前,周深才终于将目光移开:
“爱有两张脸?
”那是一幅印象派画作,长发妖娆的西方女子长了两张脸,一张红色,一张黑色,画名就叫“爱有两张脸”。
周深觉得挺奇怪:
“这是什么意思?
”岁晚看上去却挺喜欢:
“爱有两张脸,一张红脸,一张黑脸。
”回头看他似乎听得更蒙了,又耐心解释道,“因为有时候爱是幸运,有时候爱则是幻灭。
”说完她顿了一下,看着画的眼神突然有点空。
直到周深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小小年纪,讲得好像自己很懂爱情似的。
”岁晚蹙眉,本不想再理他,谁知他又接下去,“谈过几次恋爱了?
十次?
”语气里不知不觉便有了淡淡的取笑。
岁晚没理他。
“五次?
”“……”“三次?
”“……”“好吧,两次?
”眼看她眉间已开始腾起羞恼的神色,他故意更夸张地道,“天哪,不会一次都没有吧?
”“周深!
”可抬头却看到他笑意盎然的眼,带着明显逗弄的神色:
“没关系,我就喜欢没谈过恋爱的你。
”他的声音低低的,目光深深的,好看的桃花眼中似漾着三月的春水。
她一直是反应慢半拍的女子,可这一瞬,却迅速想起那句“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
走神的当口,只恍惚听到他说:
“不问我为什么?
”她便不知不觉地跟着问:
“为什么?
”“因为,那样的你好骗啊。
”“……”2008,他追她的第三年
可事实证明,周深真的是想太多了,她不好骗,更不好追。
因为整整一学年过去了,周深还是没有追到言岁晚。
那年学校外的奶茶铺收了摊,岁晚顿失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
周深虽没问过她家里的情况,却也知必是不好的。
所以那次他将她推荐到他爸的公司里当兼职的文员,想着能近水楼台先得月。
可事实上,第二学年亦即将过去之时,他还是没有追上她。
他对她那么好,他追她还那么勤,他又长得那么帅,他……呃,他爸的公司那么大,可岁晚的回应却是:
“就因为你爸的公司那么大,你和我怎么会有可能呢?
”就连周妈妈都耳闻过自家儿子的疯狂事迹,那天来公司时,特意往岁晚这边绕过来,笑容看上去似乎挺和蔼:
“我们家阿深哪,小时候什么小猫小狗都往家里带,长大后更是不得了,什么人都往公司里带。
”那时岁晚就站在一排看热闹的同事中间,第一次恨不得自己的反应能慢半拍。
也就是在那天之后,周深说为她物色到了另一份“堪称惊喜的新工作”。
那是在市中心的一家画廊里,周深说:
“我堂哥正好缺一个销售员。
”对了,他的堂哥周文正是这家画廊的老板。
而言岁晚的命运,大抵就是在这家画廊发生转折的吧。
新工作并不是特别有趣,可她却喜欢得紧。
没人知道岁晚对色彩、构图、创作有多么原始的兴趣,她以为周深也不知,直到那一天——言岁晚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在画廊的某个拐角处工作时,周深的声音从拐角的另一端传来:
“我说你这当人老板的,有空多鼓励鼓励她呀!
”“鼓励她什么?
”“当然是鼓励她自己创作啦!
看不出我们家岁晚其实很想画画吗?
”拐角这端的她的手一顿。
第二天,老板果然对她说:
“我看你这孩子挺有天赋的,画廊没顾客时,就试着画画吧。
”平淡的语气,一点也不像是特别照顾她的表情。
坐在一旁刷美剧的周深也状似无意地附和:
“就是,没准画好了,还能给我哥增加点收入呢。
”话听上去像是在帮他哥,可言下之意,在场的谁又不知呢?
那天岁晚下班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周深没开车,却坚持要送她回学校。
上海已经入冬,离开画廊后,周深就看岁晚不断地搓着手——这城市的冬夜有多阴冷她不是不知道,可这家伙竟勇敢得连手套都没戴。
周深皱眉看了她通红的手好久,才突然有点气急败坏地说:
“话说本公子追你多久了,发点福利、小手让我牵一下吧?
”“啊?
”岁晚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这土霸王将一只手套脱下来,强行给她戴上,而那只已经没有手套戴的手握住了她同样赤裸的手,然后——放入自己的大衣口袋里:
“这是追你N年该享受的福利,敢不给?
”陡然间,掌心那么暖,传递到她反射弧太长的大脑时,又慢了半拍。
而周深已经更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那晚他难得安静,只是一路牵着她,表情挺享受。
直到岁晚先开口:
“周深,你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
”那时两人刚出地铁站,狂风再一次不客气地吹过来时,周深低下头看她:
“言岁晚,你说你笨不笨?
”看她果然挺笨地蹙起眉,又心满意足地笑开,“讲那么多次都记不住!
对你好当然是因为想追你啊。
”“认真的吗?
”“认真的啊。
”“很认真很认真吗?
”“很认真很认真!
”“认真到,确定将来可以和我结婚吗?
”他顿住了——结婚?
可岁晚已经别过了头:
“随便说说的。
”其实她不知,那一瞬间,在盛大的欣喜涌入他的心头时,周爸周妈的话也同时入侵了周深的脑海:
“还真打算把那丫头追回家吗?
闹一闹就算了,还想带回来?
没门!
”就像他不知道,那是她第一次对人产生白头偕老的冲动——对,不是“在一起”,不是简单肤浅不负责任的“在一起”。
而是……永远在一起,到老。
结婚能让最亲的亲人安心祝福,和心爱的人一起白头则是所有女孩梦寐以求的事。
可他却没有给她最好的回答。
岁晚第二次产生这样的冲动,是在毕业那年。
那年她已经开始作画了,令人吃惊的是,她一提笔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力,就连周文都忍不住赞叹:
“看这平时默不作声的,原来潜力都藏在笔下了啊!
”可不是?
商学院出身的女子,不过是修过一门美学课、看过几幅画而已,竟能在提笔之时表现出那么强大的创造力。
那日画廊里寂寂无人,岁晚原本正窝在画室里创作,却被周深一口气拉回到学校——“你怎么了?
要带我去哪儿?
”“到了你就知道了。
”他的语速很快,声音很急,一路拉着她来到A大艺术学院的画廊里——然后,岁晚瞪大眼,震惊地瞪大眼,看着学校橱窗里“历年优秀作品展”中,自己从没想过要裱出来的那一幅写实画。
“这是……”“你的《老军人》。
”是,画的名字叫“老军人”,只是——“这幅画怎么会在这里?
”“是我从你宿舍里偷出来的。
”不,不,她的意思是——她的画怎么可能被裱在这里?
怎么能有这样的资格?
“别怀疑自己的能力,我哥和艺术学院的教授都说,这幅画真的非常有水平。
”是的,他不懂画,可他有心,让懂画的周文暗地里挑出她最好的作品,悄悄送到学校里来。
岁晚的心突然暖了暖,就像骤然穿越到了春水初生时,周遭温暖,而她眼底满是潮湿的情绪。
那日从学校再返回画廊时,周深一边开着车一边问她:
“怎么觉得你对军人特别有感情呢?
”“因为我的外公是一名退了伍的军人,从十岁开始,我就跟着他一起生活。
”“哦?
你爸妈呢?
”“没了。
”他握着方向盘的手一僵,怎么也没料到会是这种回答。
可岁晚只是口吻淡淡:
“我妈在我十岁那年被我爸扔下一纸离婚协议书,原因是他爱上别人了,甚至马上就要组建新家庭。
他曾经那么爱她,给她家、给她温暖、给她希望,却在我十岁那年,全部抽离。
”周深的眉头突然皱起,就像预料到她接下来要说什么一般。
果然——“所以办完离婚手续后,她把我交付给了外公,然后……就去自杀了。
”“岁晚……”“你知道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
她说晚晚,从一而终的才叫爱情。
”说到这里,她的目光终于缓缓移到他身上,“周深,能结婚、能厮守、能白头的,才叫‘爱情’。
”所以那一年,她问他:
“认真到确定将来可以和我结婚吗?
”所以这些年,她一直不肯接受他。
他有那样的家庭、那样的父母——如果她接受了,却最终因为父母之命而不能相守;如果他给了她希望,却最终又给她绝望。
那他与她之间,白头之时,还能像现在这样退而求其次地当朋友吗?
车窗外的街道异常拥挤,大抵是前方发生了车祸,所以整条街上的车全都停止了前进。
漫长而沉默的寂静中,周深无数次张口又闭口,想说什么,却最终什么也没说。
2009,他追她的第四年
2009年,他和她都毕业了。
一贯秉承“男人先成家再立业”的周爸周妈开始替周深安排起了相亲。
有很长一段时间,言岁晚并不知他有这样的困扰。
直到那日周深将一名女子带到画廊来买画,岁晚才从老板口中得知,那是周家爸妈塞给他的相亲对象,姓王。
那位王小姐一口气买了她的三幅素描,原因无他,只因那三幅素描里的模特都是周深。
这样明显的占有欲想必是冲着岁晚来的,可这个当事人却只是表情淡淡,就连王小姐主动提出请“阿深和堂哥一起去吃饭”,她也没皱一下眉头。
而那厢,周深一顿饭吃到大半夜,再返回画廊时,顾客和店员早已经走光了,只岁晚一人留在工作室里。
他挟着浑身的酒气在她旁边看了很久,看着画笔在宣纸上勾勒出新作品的轮廓,一笔一画。
他许久才开口:
“她怎么样?
”岁晚的笔顿了一下,然后又继续:
“挺好的。
”“怎么个好法?
”“漂亮,有涵养,和你门当户对。
”他沉默了。
其实他为什么会沉默,言岁晚是知道的,只是她又该说些什么呢?
许久过后,还是周深先开口:
“我怎么觉得,自己并不是很想听到你这样的回答?
”背对着自己的女子似乎僵了僵。
看不到表情,他干脆走到她面前,俯身用高大的身躯挡住了白炽灯的光线:
“言岁晚,你说你笨不笨?
”带着酒气的手指轻勾起她的下巴,口吻温存得就像那年甫出地铁站之时,他说“言岁晚你笨不笨?
连忌妒、吃醋、生气该怎么表现都不懂吗”。
岁晚僵硬的表情又恢复到一贯的素淡:
“周深,很晚了……”“是的,很晚了,”他点了点头,带着温和的醉意重新站起身,“该回家了。
”就连口气也这么温和。
只是踉踉跄跄地往门外走了两步后,那温和的背影又停下了——突然之间,只是电光石火的一瞬间,他突然又转过身朝她走来。
在岁晚错愕的目光下,一脚踹掉了她身边的作画工具:
“哼!
”缤纷的涂料染了一地,衬着男子突来的凶狠表情:
“这就是你的回答!
我爱了你四年!
这就是你的回答!
”狂暴的怒气无边无际,逼红了他醉酒后的眼,也逼红了她永远隐忍的眼眶。
那是周深第一次对她发火,从前不管她再笨、再迟钝、再冷淡、再没反应,他都不会生气,他见鬼地一看到她就连气长什么样都不知了道。
他只想护她、爱她、怜惜她,他想把所有她在乎的美好都捧给她。
可四年了,这女子竟能无动于衷到这种地步!
“言岁晚,你的心呢?
是石头做的吗?
啊?
”他在极盛的怒气中狠狠地摇着她的肩膀。
只是,一个人的心怎么会是石头做的呢?
他一步一步走出工作室,步履蹒跚,背影孤寂得就像是永远也不会再回来。
而那颗被他以为是石头做成的心却缩得死紧,泪水一颗颗掉落,最终迅速滚下来。
泪眼朦胧中,那个孤寂的背影转了个弯,然后消失了。
她突然那么慌,慌得就像是再这么下去自己将再也看不到那个背影一般:
“周深……周深!
”外头的走廊里突然响起周深熟悉的手机铃声,在午夜的空气里寂寞地回荡。
许久许久,铃声停下,他的电话被接通时,岁晚才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
“我想外公了,好想好想……如果你愿意陪我去看他老人家的话,回到画室来好吗?
马上回到画室来,好吗?
!
”周深简直无比欣喜。
第二天一早,这厮竟然又神采奕奕地打电话过来,就像是怕她反悔似的:
“快,身份证号码报过来,我要订机票了!
”口气愉快得和昨晚的醉酒男判若两人。
岁晚的外公住在北方的乡下,从上海过去,必须转一趟飞机再换乘一班汽车,但周深一点也不介意。
飞机上的他还是那副龙心大悦的样子:
“说吧,是不是想着带我回去,让外公帮忙做个鉴定啊?
”岁晚闭着嘴,故意不理他。
“不是鉴定难道是见家长的意思?
”某人继续天马行空,心情好得很。
可你知,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乐极生悲。
就在两人下了飞机之后,周深发现自己的钱包被偷了。
身份证在包里,信用卡在包里,护照什么的全扔在家里,现在就算是想办临时身份证来转下一趟飞机都不可能了。
两人只好在机场附近先找了一家旅馆——对,旅馆,他连身份证都没有,正规的酒店哪能办入住?
可也就因为选了这么一家旅馆,霉运接二连三地降临了。
这一晚,不习惯北方气候的周深突然发起了高烧。
凌晨一点多,岁晚被他难受的呻吟声惊醒——他身上没一分钱,她钱包里的现金也有限,为了省钱,两人选了个双床房。
可这破旅馆里竟然没有药!
大半夜的,意兴阑珊的前台人员懒懒地对她说:
“附近有24小时药店,穿过巷子就到了。
”他不肯让她去,说太晚了。
可现在都什么情况了,哪还能顾得上晚不晚?
“你等等,就一条巷子的距离,我马上就回来。
”她信誓旦旦地在他神志不清的耳边说。
可那晚,她最终没有回来。
2012,岁晚与尹医生
“没有回来?
你去哪儿了?
”故事听到这里,我心中突然腾起一种很不好的预感,可言岁晚并没有回答。
于是我只好换了个问题:
“那周深呢?
最终见到你的外公了吗?
”“见到了。
”外公喜欢周深,很喜欢——“这孩子啊,正气,善良,关键是对你好!
错不了的小晚,错不了啊!
”外公牵着她的手,笑眯眯地将她的手放到周深的掌心里,就像每一场婚礼上父亲将女儿交给新郎时那样,放心而郑重的。
而周深呢?
也郑重地、信誓旦旦地说:
“外公,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可最后,”言岁晚跟我说,“我们还是分开了。
”那是2010年年初,两人告别了外公回到上海的两个月后——他依旧对她那么好,恨不得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耗在她身上。
她一有点不顺心或是一点风吹草动他就紧张得好像要惊动全世界,有时她被他缠烦了不让他跟在身边,他就去游冬泳,在冬天冰冷的河水里一遍遍地告诫自己:
要增强体质,不准再感冒!
不准再发烧!
不准再出现那夜的惨况……可如斯努力许久后,她最终还是说:
“周深,我们分手吧。
”连原因都没有。
2010年,本该是她最忙碌的年份,因为周深说要为她办一场画展,让全上海的人都认识她这颗冉冉升起的艺术新星。
可新星的作品还准备不到一半,就连人带作品一起消失了。
周深发了疯似的将整个上海翻找过一遍后才收到她的短信:
别找我了,我到外面找一些灵感,新作品没完成前,就不回去了。
淡淡的、任性的口吻,不负责任得如同之前的每一年。
而后来,这成了他们之间的常态——每年总有那么些时间,他留在上海,而她游走各地。
好久之后再回来时,带着她的新作品:
“周深,我回来了,你还好吗?
”和那群所谓的“艺术鉴赏家”不同,其实言岁晚的作品我并不怎么欣赏——太压抑,也太绝望。
可不得不承认,未见其人之时,我对她已经充满了兴趣。
真正的接触是在2012年,在那场轰动全上海的印象派画展上,我看到了这个名唤“言岁晚”的女艺术家:
年轻,淡漠,平静的表面下隐藏着丰盛的感情,可只消看一眼我便知,终有一天,她会来找我。
而果然,一个多星期以后,她就出现在了我的工作室里。
却不是独自一人——对,是周深,他带着她一同来找我:
“尹医生,听说你可以用催眠术帮人忘记一些事?
”彼时她就坐在他身旁,明明连情侣都称不上,可他说话时,她安静信任得如同这个男子就是她的丈夫。
直到周深说:
“我想请尹医生帮我们俩同时催眠掉一段记忆。
”岁晚的目光才凝了凝,然后,有浓得化不开的哀伤渐渐流露。
我分别跟他们俩进行了一场深入的交谈,先是周深,而后是言岁晚。
与周深沟通完毕后,我已经知道这两人想被催眠掉的是哪一段记忆了。
可在周深面前始终不曾提出抗议的女子,却在独自面对我时问我:
“尹医生,阿深他不懂画,可我懂——我所有痛苦的回忆都在自己的画里,所以你觉得催眠对我有意义吗?
”“言小姐的意思是?
”“拜托你,好好地帮他吧——帮他一个人就好,这些年,我们家阿深……实在是太痛苦了。
”咨询室外的男子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一刻,有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
迅速,毫不迟疑,在这间安静的咨询室里。
没听过那场回忆的人一定不知道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那么努力地想弥补我,可他越努力我就越痛苦,他也越痛苦……”可我是知道的,刚刚周深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结束交流时,有一瞬间我几乎发不出声音,为这男子数年如一日的执着。
终于,在他要走出咨询室时,我开口道:
“周先生,冒昧地问一句,你究竟爱她什么?
”一个是翩翩公子哥,全上海无数适龄女子的梦想结婚对象,一个是数年如一日沉默冷淡的女子。
可他却回答得毫不犹豫:
“初见时的固执,再见时的善良,以及后来每一天所表现出来的努力。
你知道,我是个二世祖,这辈子恐怕永远也不会有这种努力。
”“不,其实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很努力地爱着她。
”“不,尹医生,”他淡淡地笑了,孤寂的眼底似囊括了所有前程往事。
他说,“尹医生,爱是本能,不需要努力。
”2016年,元旦画展
再见到周深,是2015年的年末。
我看到他在西塘的河里冬泳,看到他对着站岗的军人行礼。
交谈于外滩时,这男子已经将我忘了。
可当他得知我亦是岁晚的朋友时,还是热情地招呼我:
“明天有岁晚的新作品展,尹小姐也一起来吧。
”我点头,“自然是要去的。
”三年多了啊,时间一不留神又晃了过去。
三年后的言岁晚比起三年前,知名度和地位都提高了不少。
一场展览看下来,作品不多,可观赏者却是那么多。
慕名而来的除了画迷外,还有中外无数的评论家……这么一场画展办下来,没有足够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恐怕不可能吧?
所以在周深带着我行走于画廊各处时,我忍不住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这画展的幕后投资人,其实是你吧?
”他啜着香槟的动作一顿。
而我已从这一顿中得到了答案。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爱情。
我看着这双曾经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