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哲学与程朱理学比较及现实意义.docx
《戴震哲学与程朱理学比较及现实意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戴震哲学与程朱理学比较及现实意义.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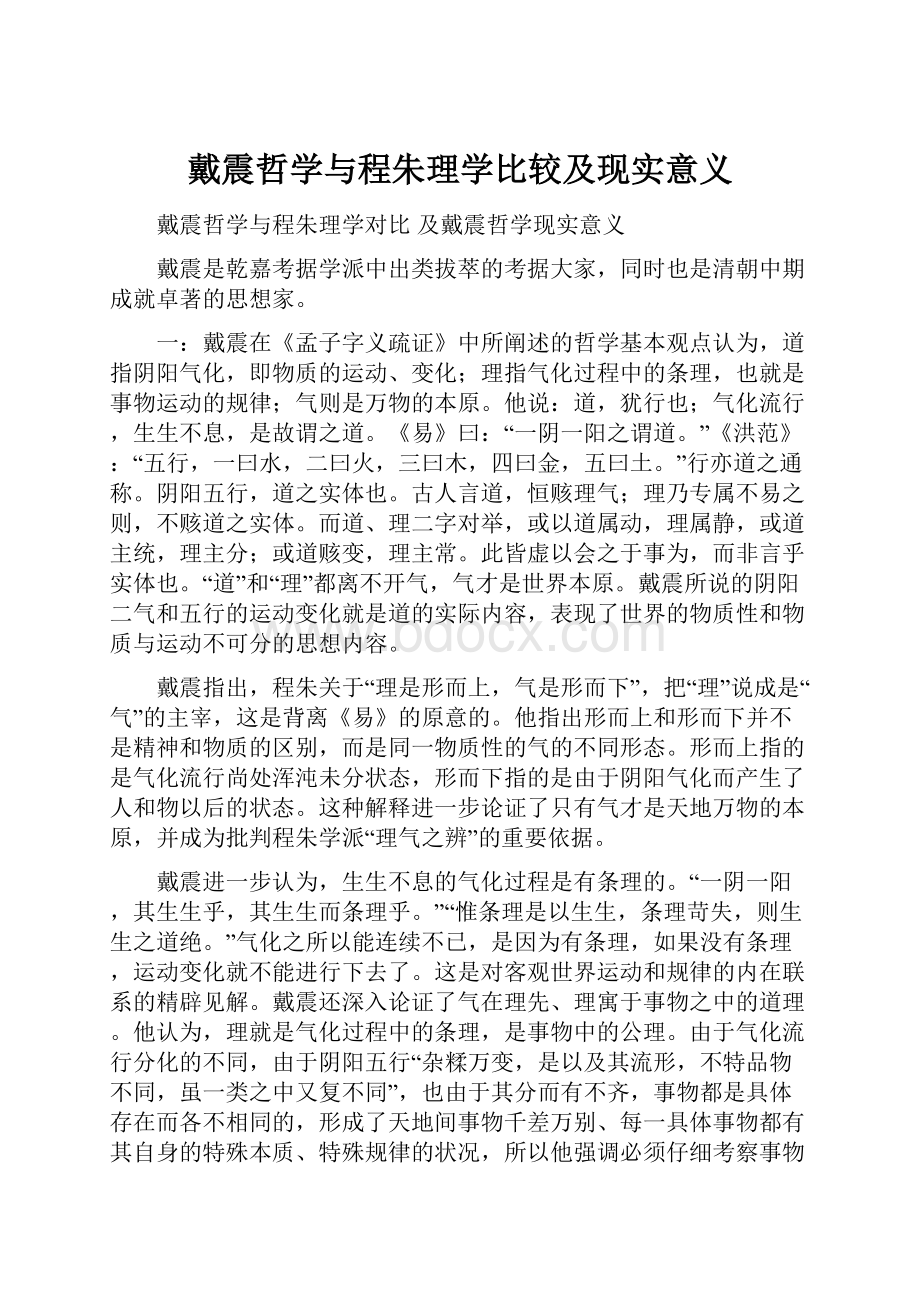
戴震哲学与程朱理学比较及现实意义
戴震哲学与程朱理学对比及戴震哲学现实意义
戴震是乾嘉考据学派中出类拔萃的考据大家,同时也是清朝中期成就卓著的思想家。
一: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所阐述的哲学基本观点认为,道指阴阳气化,即物质的运动、变化;理指气化过程中的条理,也就是事物运动的规律;气则是万物的本原。
他说:
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
《易》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
”《洪范》: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行亦道之通称。
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
古人言道,恒赅理气;理乃专属不易之则,不赅道之实体。
而道、理二字对举,或以道属动,理属静,或道主统,理主分;或道赅变,理主常。
此皆虚以会之于事为,而非言乎实体也。
“道”和“理”都离不开气,气才是世界本原。
戴震所说的阴阳二气和五行的运动变化就是道的实际内容,表现了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与运动不可分的思想内容。
戴震指出,程朱关于“理是形而上,气是形而下”,把“理”说成是“气”的主宰,这是背离《易》的原意的。
他指出形而上和形而下并不是精神和物质的区别,而是同一物质性的气的不同形态。
形而上指的是气化流行尚处浑沌未分状态,形而下指的是由于阴阳气化而产生了人和物以后的状态。
这种解释进一步论证了只有气才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并成为批判程朱学派“理气之辨”的重要依据。
戴震进一步认为,生生不息的气化过程是有条理的。
“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
”“惟条理是以生生,条理苛失,则生生之道绝。
”气化之所以能连续不已,是因为有条理,如果没有条理,运动变化就不能进行下去了。
这是对客观世界运动和规律的内在联系的精辟见解。
戴震还深入论证了气在理先、理寓于事物之中的道理。
他认为,理就是气化过程中的条理,是事物中的公理。
由于气化流行分化的不同,由于阴阳五行“杂糅万变,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虽一类之中又复不同”,也由于其分而有不齐,事物都是具体存在而各不相同的,形成了天地间事物千差万别、每一具体事物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本质、特殊规律的状况,所以他强调必须仔细考察事物的具体规律——分理。
他说:
“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
”又说:
“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
”“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
”总之,理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特殊规律,具体事物的规律就是理。
戴震强调理是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直接与程朱学派所谓“万物一理”相对立。
“分理”理论的提出,是批判程朱理学的“理”在理论上的突破。
戴震深刻揭露了程朱理学的思想渊源和神学本质。
他比较了程朱理学和老庄、佛教的本体论,指出《庄子》用“真宰”,佛教用“真空”、“神识”作为万物的本质和宇宙的本体,程朱学派的理,正是由此转化而来。
二:
朱理学从“理在气先”的观点出发,在认识论上,主张“得于天而具于心”,意思是,上天本来已经把真理放置在人们的心里,只是有些人不能自觉地认识它,这是因为“为私欲所蔽”而不能显露出来,人们只要“冥心求理,”就会“复其初”,认识到上天早已给予的真理。
戴震在认识论上的观点与程朱学派的观点相反,他提出了“血气心知”的认识论。
戴震认为,人具有认识能力,人的血气心知来自于阴阳五行。
人从阴阳五行的“气化流行”中分得一份,是物质的形体“血气”,敌人的认识作用是以人的生理机能为基础的。
他指出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能够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而动物只能适应自然。
“人之异于禽兽者,虽同有精爽,而人能进于神明也”;“夫人之异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各遂其自然也。
”人是如何去认识客观事物的呢?
戴震认为是通过人的感官产生感觉,进而“心通其则”,通过思考和分析,进而认识事物的规律。
声、色、臭、味都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
“盈天地之间,有声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举声色臭味则盈天地之间者无或遗矣。
外内相通,其开窍也,是为耳目鼻口。
”人的感官的形成,是为了适应客观世界这众多的客观现象,而人的感觉是外界客观事物直接作用的结果:
“耳之能听也,目之能视也,鼻之能臭也,口之能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
”感官之外的心是主宰感官的,心可起到神明的作用,是感官的主宰者。
味、声、色和理义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在感觉和心中,却能为人的感觉和心所辨别。
从而说明了人的认识不是“得于天而具于心”,批判了朱熹的“理得于天而具于心”和陆王“心即理”的先验论。
戴震又进一步批判了程朱的“无欲则无蔽”、心中的真理是“为私欲所蔽”而不能显露出来的观点。
程朱此说,以为只要去尽人欲,“冥心求理”,便可以“复其初”,不用学便可得理。
戴震认为“无欲则无蔽”之说,同老子的“常使民无知无欲”、释氏的“常惺惺”,在实质上是一样的。
他说:
“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
欲之失为私,不为蔽。
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而不明。
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
”因此,不能“因私而咎欲”,也不能“因蔽而咎知”。
“私”和“蔽”是两回事,“私”属于伦理道德范畴,“蔽”属于认识论范畴。
道德上的“不善”,不是由于有情欲,而是因为情欲有私;知识的不正确,是因为“心知”有蔽隔,因此才未能把握事物的本质。
他由此认为,人不可能无蔽,有的只是蔽深与蔽浅的问题;有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蔽而自智,视自己的意见为理去害斯民。
所以,“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如学”。
戴震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素质虽有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大,“智愚之甚远者盖鲜”,只要努力学习,就能使人由不知到知,由知不多到知更多。
人的认识既是一个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化过程,也是一个由蒙昧到圣智的扩充过程。
他说:
“人与人较,其材质等差凡几?
古贤圣知人之材质有等差,是以重问学,贵扩充。
”经过问学、慎思、明辨、笃行,不断理解和消化所学到的知识,就可以“极而至乎圣人之神明”。
戴震的认识论存在着缺陷,这主要表现在是一种直观的、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论。
他把人的认识能力比作一种火光,人对事物的认识,仿佛火光照物,光有大小明暗的区别,对事物的认识也就有深浅粗精的不同,由此神化“圣人”,以为只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的圣人才能没有错误地察照万物,“愚者”光小,资质愚昧,方需要学习。
他还贬低知行关系中行的意义,说“重行不重知,非圣学也”。
他以人们的主观认识的一致作为真理标准,即把“心之所同然”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也是错误的。
人性的善恶问题、理欲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长期有争论的问题。
戴震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是,性是善的,“理”、“欲”是统一的。
他对程朱的“理欲之辨”进行了猛烈抨击,无情鞭挞。
戴震是当时反对程朱理学和统治者“以理杀人”本质的最激进的代表。
戴震明确地指出:
“宋以来儒者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
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
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绝?
”他由此认为,人都有喜怒哀乐、怀生畏死之情,都有对饮食男女的需要,都有求生存、平等的欲望。
这些都是人的自然的情欲,是人的本性,是血气心知反映在人性方面的实在内容。
人类“有欲而后有为”,人欲对人类的存在有重要意义。
戴震对于人性情欲的肯定,是与其“血气心知”的认识论一致的。
他总结说:
“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
”“欲”是人对声色臭味的要求,“情”是人的喜怒哀乐的表现,“知”是人辨别是非美丑的能力。
“欲出于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所同欲也,故曰‘性之欲’。
”欲是性之欲,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本性,是人所共有的。
如果没有这些欲望和要求,人也就不存在了。
戴震论证的“欲”是人的本性,是饮食男女和生养之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也就证明了所谓“气质之性”并不是产生罪恶的渊薮,是合理的和至善的,从而批判了程朱理学把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并把“气质之性”说成是产生人欲、产生罪恶根源的谬论。
关于理与欲的关系,戴震认为是则与物的关系,是自然与必然的关系。
“自然”指的是本来的情况、情欲,“必然”是指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
人的感情欲望是“血气心知之自然”,理是必然。
自然与必然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必然是自然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理是欲的适应满足和调整,自然的目标是归于必然,是自然的完成。
他所讲的天理是存人欲的天理,是对程朱理欲观的否定。
戴震进而尖锐地批判了理学的社会作用。
他提出: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
人死于法,犹有怜之死,死于理,其谁怜之?
”对于“理”所造成的巨大而无形的危害提出了控诉和抗议。
程朱理学中的“理”,在本质上“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理学家是以理杀人,其后果比以法杀人更为严重。
戴震所生活的时代是乾嘉时期,清朝统治者正极力促使理学的复兴以加强统治,戴震却直言控诉了程朱理学的危害,深刻揭露了程朱理学的社会本质,这是具有重大意义,并且是难能可贵的。
从其种意义上说,自明代以来特别提倡的理学,已经被明中叶以至清初的有识之士所揭露和批判,戴震揭示了“以理杀人”的哲学根源,是对理学的终结,其深度是前无古人的。
戴震还同时提出了“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的观点。
他说要使天下太平,就必须“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以情絜情”、“情得其平”,要“施仁政于民”。
这样,才能“与民同乐”,“民富国强”。
戴震的哲学思想尽管并不完善,并且在当时也不被人所重视,但由于他没有株守博物考订、训诂名物,而是勇敢地继承了王夫之等人的观点,指名道姓地批判程朱理学,使他的思想独具自己的特点并超越了前人以及同时代人,取得了比同时代学者更为丰富的学术成就。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派,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与心学相对。
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他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上帝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
所以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人(儒家最高修为者,人皆可达之),还可能会迷失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後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灭人欲,不是无欲,而是理欲合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从“毋”变成“无”),则无论做什麼都不会偏离天道了。
他还认为,由於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
三:
戴震是十八世纪清代考据学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把考据学的方法与对义理的阐释结合起来,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解读:
他以“血气心知之自然”言性,性无不善,然不免有“失”,所以必须通过对理义的学习以使同样是出乎自然的“心知”进于神明,如此方能使心之“反躬”在情欲之流行中把握到理。
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他对宋明儒的心性之学,对他所以为的程朱理学身上的老、释、陆、王的成份进行了批判。
然而这种批判却是基于对性、情、理、欲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及宋明儒所谈论的问题的误读,这种误读使戴震在贯彻其思路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为了解决这种困难,戴震最后对“心”的理解超出了传统儒家的立场,而使人心带上一种知性甚至理性的色彩,从而预示着近代哲学的发端,其思想的时代意义也正于此。
明季以降,学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士人们有感于家国之痛,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经世致用之学于是大兴。
对宋明新儒学之“空疏无用”的批判导致了重新建构儒学传统的努力,即通过运用一种极具实证精神的训诂考据的方法来恢复儒家经典的本来面貌,清除佛道教义对经典的污损。
这样一种传统对十八世纪的考据学派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经典的方法。
这样一种方法最终导致了对儒学经典的道德特征的忽视,在他们看来,自然科学(指他们对天文、历算、算术和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兴趣)和文献考证等技术手段对于经典的解读才是本质重要的。
然而,他们对宋明新儒学的批判显然是基于一种误读,这一方面是由于批判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所运用的以考证为特征的儒学话语使他们无法读懂宋明儒所讨论的那些问题,这些有关道德践履、心性修养的问题对于他们的努力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然而这种误读却是必然的。
晚明以来,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开始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领会他们所处的世界,人心开展出另一种向度。
基于这样一种变化,人们是以自己领会世界的方式去面对古人生活中所特有的问题,如此,误读就不可避免了。
不过,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误读。
因为他们在这种误读中阐明了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的内在意蕴。
而所有这一切,都在戴震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戴震在其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把考据学的方法与对义理的阐释结合起来,他从对经典中理、气、性、情等基本概念的考释入手,认为只要通过运用考证的方法,清除其中佛道的成分,就可以经纠正朱熹及其他新儒家学者对这些概念的错误理解,从而得以把握《六经》、孔、孟之真精神。
但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实证的方法对于本不属于认识领域中的真理的把握是否是同样有效的。
对戴震哲学的分析,不仅要考察晚明以来学术史的变迁及社会生活的变化对学术的影响,这自然是一个极重要的方面,但我们在此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其思想,即直接从概念本身入手,分析戴震和宋明儒在一系列基本概念上的不同用法,来说明人心的变化,进而说明社会生活的变化。
在我们看来,有此理,必有此心;无此心,必无此理。
一切学术最终都是对心的研究,或者说,一切学术研究必然都是对心之某种存在的显明。
心由于所面对的事物本身及其所处的条件(中国人称之为“时”)的不同,因而有种种不同道理的把握,然统而言之,不过是同一个心的不同妙用。
因此,我们解读戴震哲学的方法与戴震解读儒家经典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既然学术是对心的阐明,因而一种学术被了解为一个体系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正是出乎把戴震哲学从一种体系来解读的目的,我们的做法难免会引起那种实证研究的不满,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意味着把某种东西强加给戴震,我们仅仅是把戴震本人说得不清楚的东西说清楚,把他想说而又未能表达出来的东西给他说出来。
因此,我们分析戴震哲学的目的所在,便是要把握戴震是如何阐述心的某种不同于传统中国人的运用,即阐述心之知性乃至理性运用的方面。
并且我们把戴震的这种误读看作是对心之某种运用的执着,而未在一种更深的基础上把这些不同运用协调起来。
如此看来,具有实证精神的考据学运动的意义并不在于对宋明心性之学的批判,也不在于对儒家经典本来面貌的或多或少的把握,而是在于这种考据的方法阐明了心之不同于良知运用的一面,他们所阐述的道理不过是这种运用的结果。
而这正体现了明季以来社会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思想的时代意义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