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宋之争及其演进.docx
《汉宋之争及其演进.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汉宋之争及其演进.docx(3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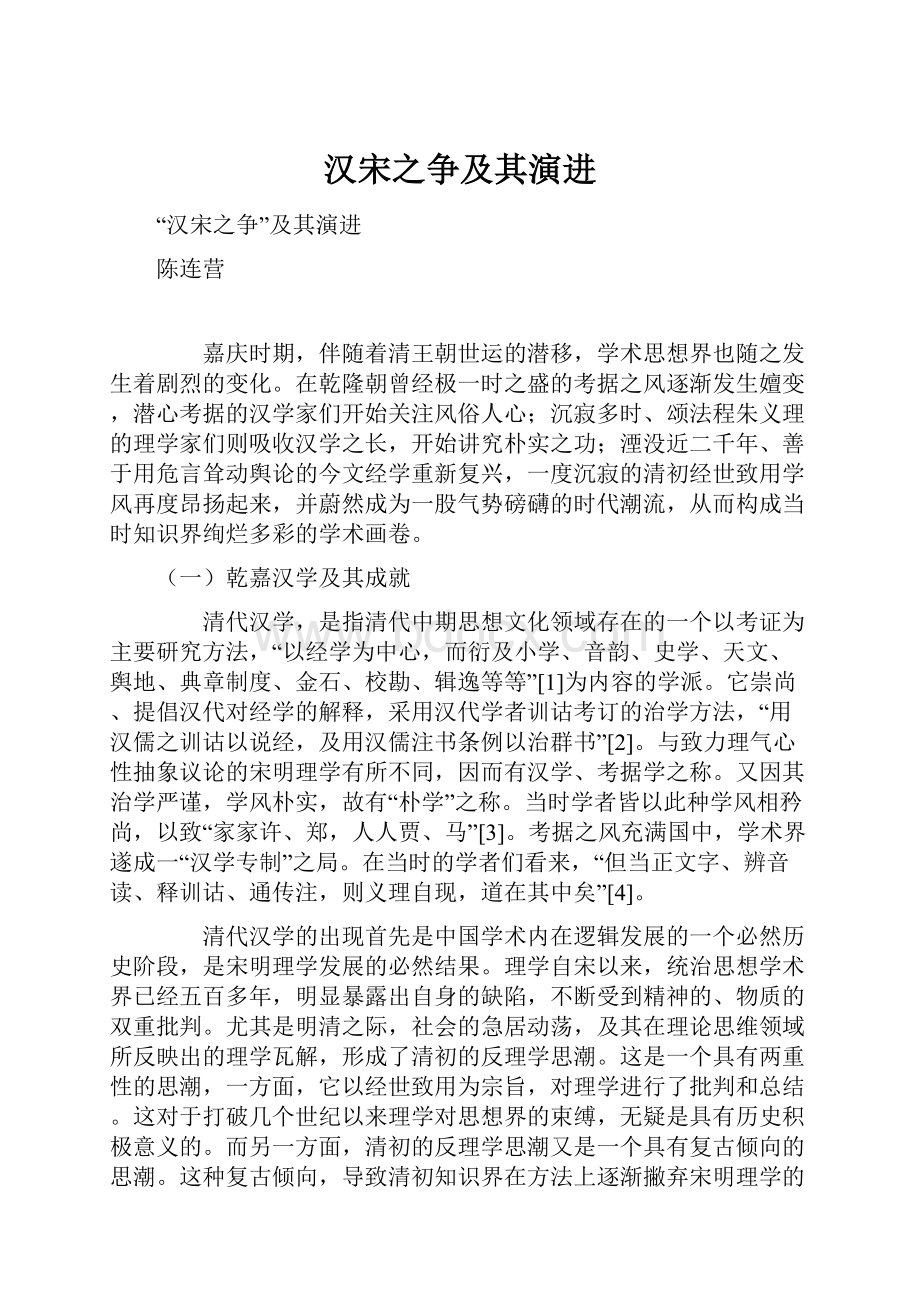
汉宋之争及其演进
“汉宋之争”及其演进
陈连营
嘉庆时期,伴随着清王朝世运的潜移,学术思想界也随之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在乾隆朝曾经极一时之盛的考据之风逐渐发生嬗变,潜心考据的汉学家们开始关注风俗人心;沉寂多时、颂法程朱义理的理学家们则吸收汉学之长,开始讲究朴实之功;湮没近二千年、善于用危言耸动舆论的今文经学重新复兴,一度沉寂的清初经世致用学风再度昂扬起来,并蔚然成为一股气势磅礴的时代潮流,从而构成当时知识界绚烂多彩的学术画卷。
(一)乾嘉汉学及其成就
清代汉学,是指清代中期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一个以考证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文、舆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1]为内容的学派。
它崇尚、提倡汉代对经学的解释,采用汉代学者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条例以治群书”[2]。
与致力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因而有汉学、考据学之称。
又因其治学严谨,学风朴实,故有“朴学”之称。
当时学者皆以此种学风相矜尚,以致“家家许、郑,人人贾、马”[3]。
考据之风充满国中,学术界遂成一“汉学专制”之局。
在当时的学者们看来,“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现,道在其中矣”[4]。
清代汉学的出现首先是中国学术内在逻辑发展的一个必然历史阶段,是宋明理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理学自宋以来,统治思想学术界已经五百多年,明显暴露出自身的缺陷,不断受到精神的、物质的双重批判。
尤其是明清之际,社会的急居动荡,及其在理论思维领域所反映出的理学瓦解,形成了清初的反理学思潮。
这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思潮,一方面,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对理学进行了批判和总结。
这对于打破几个世纪以来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无疑是具有历史积极意义的。
而另一方面,清初的反理学思潮又是一个具有复古倾向的思潮。
这种复古倾向,导致清初知识界在方法上逐渐撇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走向了朴实考经证史的途径。
从而,为尔后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的逻辑依据。
可以说,清中期汉学的形成,是清初反理学思潮蜕变的直接结果。
如果没有清初诸儒在学术领域、学术方法上的开拓,也就没有汉学家们在学术方法上的系统成熟。
至于汉学为什么能在乾隆年间走上取代理学的独尊地位,这确实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个是当时统治阶级对经学的的提倡,另一个则是社会的相对安定,封建国家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为知识界的经籍整理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环境[5]。
对此,当时的知识界是有充分认识的。
对于清中期汉学与清初经世学派的继承关系,当时汉学家们也是普遍认可的。
如乾隆年间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书目提要》时就说:
“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
古义彬彬,于斯为盛”[6]。
其实这种说法实际为当时学者的共识。
洪亮吉就曾说过:
“我国家之兴,而朴学辈始出,顾处士炎武、阎征君若璩首为之倡”[7]。
王鸣盛为清初学者臧琳所著《经义杂记》作序也说当时信实学风的形成源于清初诸家,“溯厥首庸,实维先生与顾、阎诸公为之导夫先路”[8]。
汪中更明确地说:
“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
《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易》者,惠氏也。
凡此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9]。
嘉庆时人臧庸也说过:
“虽小学训诂为今日为极盛,然国初诸老已启其端”[10]。
也正是基于对考据方法是传统学术之一、清代汉学是传统学术发展必然阶段的认识,当时学者甚至把考订方法的根源推及两汉。
如纪昀就说:
“自郑玄淹贯六经,参互钩稽,旁及纬书,亦多采摭,言考证之学者,自是始。
”[11]阎若璩也曾说考订校勘之学始于秦汉:
“圣门之校订之学何如哉?
秦汉大儒,精专斯业,如毛公、伏生、董仲舒、韩婴、司马迁、孔安国、司马相如、扬雄、刘向、刘歆、贾逵、许慎、马融、蔡邕、郑康成、卢植、服虔、应劭等,学有纯驳,行有邪正,然并先儒之领袖,后学之模范也。
”[12]由此可见,在当时汉雪家看来,考经征史的方法以东汉为最精,所以他们才遵循汉儒的治学方法,而其最近源头则在清初诸儒。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在论述乾嘉考据学的内在逻辑成因时,漆永祥注意到两千年来儒学发展史上考据与义理并存问题,是很有道理的,自从有了文化典籍,自然就有了不同的理解方式:
考据训诂与推阐义理,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正确理解先贤遗留下来的修齐治平的道理。
同时,也应该承认,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社会的相对安定,封建国家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为知识界的经籍整理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环境。
此中道理自不必说,但有一点,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文物的不断出土,确实给学术研究带来诸多便利,以致孙星衍曾不无得意地说过:
“国家统一车书,拓地万里,山陬海澨,吉金贞石之所出世比之器车马图,表瑞清时,旷古未有,前哲所未纪也。
”[13]近世学者陈登原则强调了印刷业兴盛与学术发展的关系,说:
“欲明清学之所以盛者,虽知其由多端,要不能与藏书之盛漠无所关”[14]。
需要说明的是,在清代汉学奏向鼎盛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对经学的提倡也起了相当作用。
早在康熙年间,康熙帝就认为,“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15],因而在考试重视经说的同时,还举行了博学鸿词科,对于博通经术之士,颇为重用。
以经术受知康熙的何焯,就曾很感激地说:
“天下后世闻风兴起,为人之祖、父者,孰不思以一经教其子孙,孰不思以朴学显其祖、父?
”[16]
乾隆即位之初,即举行博学鸿词科,并颁发《十三经》、《二十一史》,倡导研经读史。
乾隆六年更要求各地督抚、学政采访研究六经、明心见性的著述进呈,八年颁发《十三经注疏》。
昭梿就此评价说:
“上初即位时,一时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经术者。
上特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课其学之醇疵。
特拜顾栋高为祭酒,陈祖范、吴鼎等皆授司业。
又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命方侍郎苞、任宗臣启运等裒集《三礼》,故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于大著,龌龊之儒,自蹍足而退矣”[17]。
惠栋曾于乾隆十七年以“博通经史,学有渊源”受到两江总督尹继善举荐,他颇为感动地说:
“国家两举制科,尤是词章之选,近乃专及经术,此汉、魏、六朝、唐、宋以来所未行之旷典。
”[18]乾隆十九年,饱学之士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纪昀等同中进士,他们对皇上提倡实学颇为感激,王鸣盛就说:
“今天子金声玉振,以实学为海内倡,更定取士令式。
丁丑,礼部试贡士,首以‘循名责实’发题,盖欲学者削繁除滥,崇雅黜浮,由记由词章而徐进于研经穷理之地,皇极之敷言垂训,深切如此。
”[19]钱大昕称赞说:
“夫皇上慎重科场,厘定成宪,除去表、判雷同剿袭之陋,首场试《四书》文,乃性理论,二场试经文,增五言排律,复谕礼臣申严磨勘墨卷之例,将使士皆通经学古,淹长者无不收录,浅陋者不得幸售,远近闻风,争自奋厉”[20]。
特别是《四库全书》的编纂,对朝野影响甚巨。
卢文弨曾论及四库开馆及戴震入馆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说:
“天子开四库馆以网罗放矢,雠校之司,必得如刘向、扬雄者方足以称上指。
东原用荐者,以乡贡士起家,入馆充校理。
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廷对,洊升翰林,天下闻之,咸喜以为得发抒所学矣”[21]。
洪亮吉就注意到社会稳定局面、四库全书编纂对学术昌盛的影响,他说:
“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余年,鸿伟瑰特之儒接踵而见,惠徵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
及四库馆之开,君与戴君又首膺其选,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内之士知向学者,于惠君则读其书,于君与戴君则亲闻其绪论,向之空谈性命及从事帖括者,始骎骎然趋实学矣。
夫伏而在下,则虽以惠君之学识,不过门徒数十人止矣;及达而在上,其单词只义即足以歆动一世之士。
则今之经学昌明,上之自圣天子启之,下之即谓出于君与戴君讲明切究之力,无不可也。
”[22]所以《清史稿》称赞说:
“清兴,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
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23]。
值得说明的是,清代“文化专制”政策与汉学的形成没有直接关系。
理由是清代文字狱政策偏重的是明清之际的历史,并没有对所有的研究领域进行控制,学者的研究也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所有才有钱大昕等人影射史学的出现。
钱大昕讥刺时政的倾向非常明显,如《洛闽党争论》影射文字狱政策说:
“夫摭拾语言文字之失陷人于罪,纵幸而得逞,如吴处厚之于蔡碓,犹为士论所薄”[24]。
论宋初徐铉增《说文解字》一事,有“处猜忌之朝,不敢引古义以力争,而间于注中微见其旨,千载之下,当原其不得已之苦心也”[25]。
论君权与君臣关系时说:
“古之治天下国家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者也,身之不治而求治于民,所谓‘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者也,非忠恕之道也”。
“《大学》论平天下,至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帝王之能事毕矣”[26]。
《晁错论》中说:
“古之人君于其臣也,尊之信之,礼貌以待之,故臣不挟术以干君,君亦不忍徇利而弃臣”,“礼有议贵议能之例,而法家绌之,恶其法不立也。
法在必行,错所受申、商之学如是,庸讵知适以自祸也。
是故任刑之君常至于乱国,任法之臣常至于杀身”[27]。
他还说:
“唐虞三代,皆封建之世,其土地人民,天子与诸侯共之,天子不甚尊,诸侯不甚卑”,天子诸侯皆“以匹夫匹妇之饥溺为己患”,不求个人安乐,然而“自秦人废封建为郡县,遂以天下为天子私有,竭四海以奉一人,尽改古昔淳朴之俗,欲为子孙万世之利。
迨其后嗣不肖,天怒人怨,豪杰之士,桀其乱而攘取之。
”[28]他因而提出了“君诚有道,何至于弑,遇弑者,皆无道之君”[29]的认识。
所有这些,无疑是对清代君主专制极端强化、奴使臣民的声讨。
如果说,当时的文字狱真的非常严密,钱氏又如何敢如此放肆呢?
第二,汉学家们并非不讲义理、不讲躬行。
惠栋、江永无不继承顾炎武宗仰朱熹的传统,惠栋父亲惠士奇有名联:
“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30]。
江永既为《近思录》作注,又继承朱熹之志撰《礼书纲目》88卷。
自称作此目的是:
“欲卒朱子之志,成礼乐之完书,虽僭妄有不辞也。
”他在自序中盛推宋学说:
“道在天下,亘古长存。
自孟子一线弗坠,有宋诸大儒起而昌之,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功伟矣。
其书广大精微,学者所当博观而约取,玩索而服膺者也。
……晚学幸生朱子之乡,取其遗编,辑而释之,或亦儒先之志”。
惠栋虽讲“理”不满宋人将天理、人欲对立的做法,强调其现实的人事内容,但对宋人正心诚意、立身制行之学极力推崇,称:
“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
此先自治而后治人者也。
以《大学》言之,诚意正心,修身规矩准绳,所谓先自治也;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先自治而后治人也。
由本达末,原始反终,一以贯之之道也。
”[31]他曾说:
“自古理学之儒,滞于禀而文不倡;经术之士,汩于利而行不笃”[32],因此“汉人经术,宋人理学,兼之者乃为大儒。
”[33]此为后起之戴震、焦循等人所继承和发展,如凌廷堪的提倡复兴“礼学”,阮元的“仁学”等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卢文弨强调要学以明理,躬行实践:
“夫杂学不如学经,而穷经之道,又在于言理。
理何以明?
要在身体而力行之,时时省察,处处体验,即米盐之琐,寝席之亵,何在非道,即何在非学,正不待沾沾于讲说议论之功也。
”[34]洪亮吉也说:
“夫人之知力有限,今世之所谓名士,或悬心于权贵,或役志于高名。
在人者未来,在己者已失,又或放情于博弈之趣,毕命于花鸟之妍。
劳瘁既同,岁月共尽,若此皆巧者之失也”[35]。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从清代汉学出现的原因可以看出,汉学对清代学术的贡献,首先表现为它彻底结束了宋明理学在学术领域中的独尊地位,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比较彻底地摆脱了元明以来学术研究的空泛之风,开始以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方法,对数千年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考订和整理。
其次则是对古代典籍的研究整理,而且所涉猎的范围异常广泛,包括经学、史学、天文、历算、地理、农学、医学等方方面面,从比较宽广的范围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象惠栋潜心研究《周易》三十年,数易其稿,“专宗虞仲翔、参以荀(爽)、郑(玄)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百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36]。
戴震学识宏博,“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已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圣人遗经,发明独多”[37]。
他所著《考工记图》一书,对《考工记》本文及郑康成之注多有订正。
此外,他还从《永乐大典》中整理出失传已久的《海岛算经》、《周髀算经》等古典算学专著,自此之后,校勘、注释古代天算著作便成为学术界一大时尚。
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众所周知的《四库全书》。
如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征书时算起,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七部《四库全书》全部缮写完毕为止,前后历时18个年头。
《四库全书》内容浩瀚,包罗万千,共收书3503种,79337卷,另有存目6793种,93551卷,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总汇。
尤其是由纪昀等人在此基础上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考古必衷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反映了18世纪中国学术的最高水平[①][38]。
尽管清廷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存在着删改、销毁“违碍”、“悖逆”书籍的一面,但毕竟第一次系统整理了中国古代的典籍和社会思想,正因为如此,《四库全书》的编纂一直被清代学术界誉为“会诸家之大成,光稽古之圣治”,乃“文治之极隆而儒士之殊荣”,“盖自列史《艺文》、《经籍志》及《七略》、《七录》、《崇文总目》诸书以来,未有宏博精审若此者”[39]。
值得充分重视的是,《四库全书》的编纂进一步推动了清朝学术的全面发展,时“海内从风,人文炳蔚,学术昌盛,方架汉唐”,各省督抚纷纷“礼聘儒雅,广修方志,群邑典章,灿然大备”[40],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专制文治至此臻于极盛境界。
与此相对应,史学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由清廷经数十年完成的《明史》,“议论平允,考稽详该,前代诸史莫能及也”,属于比较成功的正史著作[41]。
对《尚书》、“三礼”等著名经典的分析与考订,为人们准确了解古代社会,尤其是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创造了重要前提。
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则有力推动了通史研究的发展。
在正史研究趋于深入的同时,方志学也获得较大发展。
一是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的成熟,一在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随着统一事业的不断前进,知识界对边疆问题日益重视,有关清朝边疆的研究也逐渐获得加强。
早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起,清廷就对全国进行实地测量,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绘制成《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第一幅用近代方法测量绘制的全国地图,它不但对中原,而且对边疆地区进行了详尽的测绘,“关门塞口,海泛江防,村堡戍台,驿亭津镇,其间扼险,环卫交通,荒远不遗,纤细毕载”,“核亿万里之山河,收寰宇于尺寸之中,画形胜于几席之上”,为“从来舆图所未有也”。
到乾隆中叶,清廷统一新疆,又对伊犁和南疆进行测量。
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清廷对《皇舆全览图》进行修订增补,将新绘新疆地图增入,称《乾隆内府舆图》,这幅地图可以说是国家统一的科学见证。
成书于乾隆前期的《西域同文志》,对青海、西藏和新疆地区的地名、部落首领名称等用满、汉、蒙、藏、维、托忒等六种文字进行记载,并以汉语述其语源、含义、人物世系等,为深入研究西北地区历史地理准备了良好的资料基础。
乾隆二十七年(1762),《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编成,这是清朝官方研究新疆史地的重要成果,该书图文并茂,对新疆地理、官制、兵防、音乐、学校、物产、民情、风俗等方方面面都有详细记载,为乾隆《大清一统志》新疆部分打下了良好基础。
除官方研究外,学者个人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
赵翼对蒙古地区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风情的关注,纪昀、洪亮吉等对新疆地区的研究,钱大昕对蒙古历史的深入研究,松筠所著《新疆识略》、《西藏巡边记》、鄂尔多斯喇嘛罗卜藏丹津所著《蒙古黄金史》等史地专著都有效地增强了人们对边疆问题的重视与了解。
而且,乾嘉学派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它既是对清初学术的发展,也对近代学术起到了推动作用。
清中后期今文经学的兴起就发源于经学的深入,无论庄存与、刘逢禄,还是龚自珍、魏源,其治学方法及治学内容,都与汉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提倡西汉今文经学的春秋学,正是继承汉学弃宋复汉的疑古传统,再次突破其局限向前延伸。
清后期的诸子学研究,更是肇始于乾嘉学者的研究,如钱大昕、汪中、刘台拱、凌廷堪、臧庸、郝懿行等人对《荀子》的表彰,汪中对《墨子》即贾谊《新书》的肯定,孔广森等对《曾子》的考订,臧庸等对《管子》的发挥,卢文弨、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顾广圻等人对子部书籍的校理,都为后来学者开拓了领域。
在文字训诂的研究方面,段玉裁、朱骏声、桂馥、王筠等对《说文解字》的研究,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引之《经传释词》,以及郝懿行、邵晋涵对《尔雅》的研究,也为其后文字训诂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乾嘉学派良好的学风和客观的归纳演绎方法,更为近现代学者所吸收,此不需多言。
乾嘉学者中,如戴震、程瑶田、焦循、凌廷堪、阮元等,“以复古为解放”,对义理学的重新阐释方式,也为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继承和借鉴,如康有为、章炳麟、刘师培等人,无不是从古典中发掘其思想根源,吸取营养的。
总之,乾嘉汉学的兴起,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学术思潮,乾嘉学者以自己信实的学风、宽阔的学术视野,巨大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学术史上打下了自己深深的烙印,他们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不可动摇的。
(二)“汉、宋”之争局面的出现
在嘉庆时期有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就是“汉、宋”学术之争,而且这种局面早在汉学走向鼎盛时即开始出现,成为汉学独尊局面下的重要不协音。
如当汉学初起,江南文人袁枚即唱为别调,致书惠栋加以商榷,指出:
“足下与吴门诸士厌宋儒空虚,故倡汉学以矫之,意良是也。
第不知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
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
”[42]尔后,面对汉学风靡,一味复古,宋学营垒中人目击其弊,亦不乏起而抨击者。
如《四库》馆臣程晋芳,指斥一时学风之弊说:
“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
古之学者由音释训佑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广大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琐琐章句,至老死不休。
”因此他喟叹:
“海内儒家,昌言汉学者几四十年矣。
其大旨谓,唐以前书皆尺珠寸壁,无一不可贵。
由唐以推之汉,由汉以溯之周秦,而《九经》、《史》、《汉》,注疏为之根本,宋以后可置勿论也。
呜呼!
为宋学者未尝弃汉唐也,为汉学者独可弃宋元以降乎!
”[43]
《四库》馆臣姚鼐、翁方纲皆主张分学问为义理、考订、词章三途,力倡以义理为依归,反对专走考据一路。
翁方纲指出:
“墨守宋儒,一步不敢他驰,而竟致有束汉唐注疏于高阁,叩以名物器数而不能究者,其弊也陋。
若其知考证矣,而骋异闻,侈异说,渐致自外于程朱而恬然不觉者,其弊又将不可究极矣。
”[44]姚鼐则更诋汉学为“异道”,他说:
“近时阳明之焰熄,而异道又兴。
学者稍有志于勤学法古之美,则相率而竟于考证训佑之途,自名汉学,穿凿琐屑,驳难狠杂。
其行曾不能望见象山、阳明之伦,其识解更卑于永嘉,而辄敢上低程朱,岂非今日之患哉!
”[45]为捍卫自己的学术主张,姚鼐甚至毅然辞去四库之职,甘愿过着著述讲学的清贫生活。
清初著名汉学家臧琳的孙子臧庸,也给姚鼐写信表示自己的担心:
“文教日昌,诸先正提倡于前,后起之士,精诣独到者间有其人,而浮薄之徒,逞其臆说,轻诋前辈,入室操戈,更有剽窃肤浅之流,亦肆口雌黄,谩骂一切,甚至诃朱子为不值几文钱者,掩耳弗忍闻。
此等风气开自近日,不值伊于胡底!
二三十年前,讲学者虽不及今日之盛,而浇薄之风亦不至是。
殆盛极必衰,不可不为人心世道忧”[46]。
即使汉学中人如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指出,汉学家的考证论辩虽然“征实不诬”,但往往“嗜博”中“失之拘执”[47],“一字音训动辩数百言”,恰似“散钱满屋”,“未及排贯”[48]。
因此,主张兼采汉、宋,以救正其弊端。
主张“六经皆史”的章学诚,对宋学空疏之风曾大事挞伐:
“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意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
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然而对当时“汉学专制”之局也深表忧虑:
“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49]。
“近日考订之学,正患不求其义,而执形迹之末,铢黍较量,小有同异即嚣然纷争,而不知古人之真不在是也”[50]。
他明确地把考证之学称之谓“功力”,而非真知灼见,他说:
“记诵名数,搜剃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辄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误执功力为学问者,但趋风气,本无心得,直谓舍彼区区辍拾,即无所谓学,亦夏虫之见矣”[51]。
汉宋学术之争为什么会在汉学鼎盛时出现?
其原因就在于汉学本身存在有局限性。
从汉学本身的因素来看,汉学家们强调“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的治学方法确有一定的科学性,但说“非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52]将训诂、考证看成是探求义理的唯一路径,而忽视了“义理有时实在语言文字之外”[53],其片面性显而易见。
汉学家们本来的目的想“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54],所以汉学的学术内容,在吴派固然重在追寻三代制度,而皖派更是精于三礼的考证。
然而绝大多数汉学家一生都疲精惫神于文字,而终无所归,一字之证动辄数千言,以致“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55]。
正如颜元所说:
“书之文字固载道,但文字不是道;犹车载人,车且是人?
”因此,汉学家往往抱小遗大流于琐碎。
研究经学本是为了应对现实的需要,过分强调研究方法,忽视研究的目的,忽视经学中包含的核心思想内容,仅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它就颠倒了思想与方法的主次关系,很自然地,当它发展到极端时,就必然要回归到研究目的的探讨上,纠正其颠倒了的主次关系。
另外,汉学家们的研究中也确实存在授人口实的不足。
其一是轻易改经之弊。
卢文弨就曾说:
“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
况未有雕板以前,一书而有所传各异者,殆不可偏举。
今或但据注书家所引之文,便以为是,疑未可也”[56]。
他对王念孙改《大戴礼》指出不少错误。
嘉庆时人王聘珍曾受聘翁方纲校订古籍,对王念孙改《大戴礼》指责颇多:
“近代以来,人事校雠往往不知家法。
王肃本点窜此经,私定《孔子家语》,今反据肃本改易经文,是犹听信盗贼,研审事主,有是理乎?
又或据唐宋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之流,增删字句,或云据《永乐大典》改某字作某,是犹折狱者舍当官案牍、两造辞证,而求情实于风闻道路,得其平乎?
是非无正,人用其私。
甚者且云:
某字据某本作某。
岂知某本云者,皆近代坊贾所为,其人并无依据,是直向聋者而审音,与盲人而辨色。
凡此数端,大率以今义绳古义,以今音证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孔壁古奥之经,变而文从字顺,洵有以悦俗学者之目。
然而经文变矣,经义当由兹而亡,可不惧哉!
”[57]洪亮吉也曾批评研究经学不求甚解、牵强附会的错误说:
“近世六书几成习尚,甚至江总词客,亦讽《说文》;郭公画史,并研字学。
实则明三隅而昧一,知二五而忘十,必推其故,亦可言焉。
其下者则芟除音声,惟讲意义,中心为忠,如心为恕,得其一端,欲杜千口。
其次者则不明假借,不辨声转。
说要之义,则久假不归。
举背之形,则古文未悟。
草修成羽,叶纣为鲖。
此则书登梵箧,口必加旁;字入道书,雨常建首。
曾儒衣冠,而膜拜禹步之同量矣。
又或本非义类,强为牵合,稽省旨而加山,贡合章而成水。
小言破道,似是实非。
若不严两观之条,恐无救六书之失者乎?
”[58]
另一极端则是拘泥经籍,强为之解释。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钱大昕和王鸣盛。
钱大昕就说过:
“六经定于至圣,舍经则无以为学”[59]。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也说:
“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贬之,此其异也。
抑治经岂特不敢驳经而已,经文艰奥难通,若于古经注凭己意择取融贯,犹未免于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