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中关于生产劳动的动作描写.docx
《当代文学中关于生产劳动的动作描写.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当代文学中关于生产劳动的动作描写.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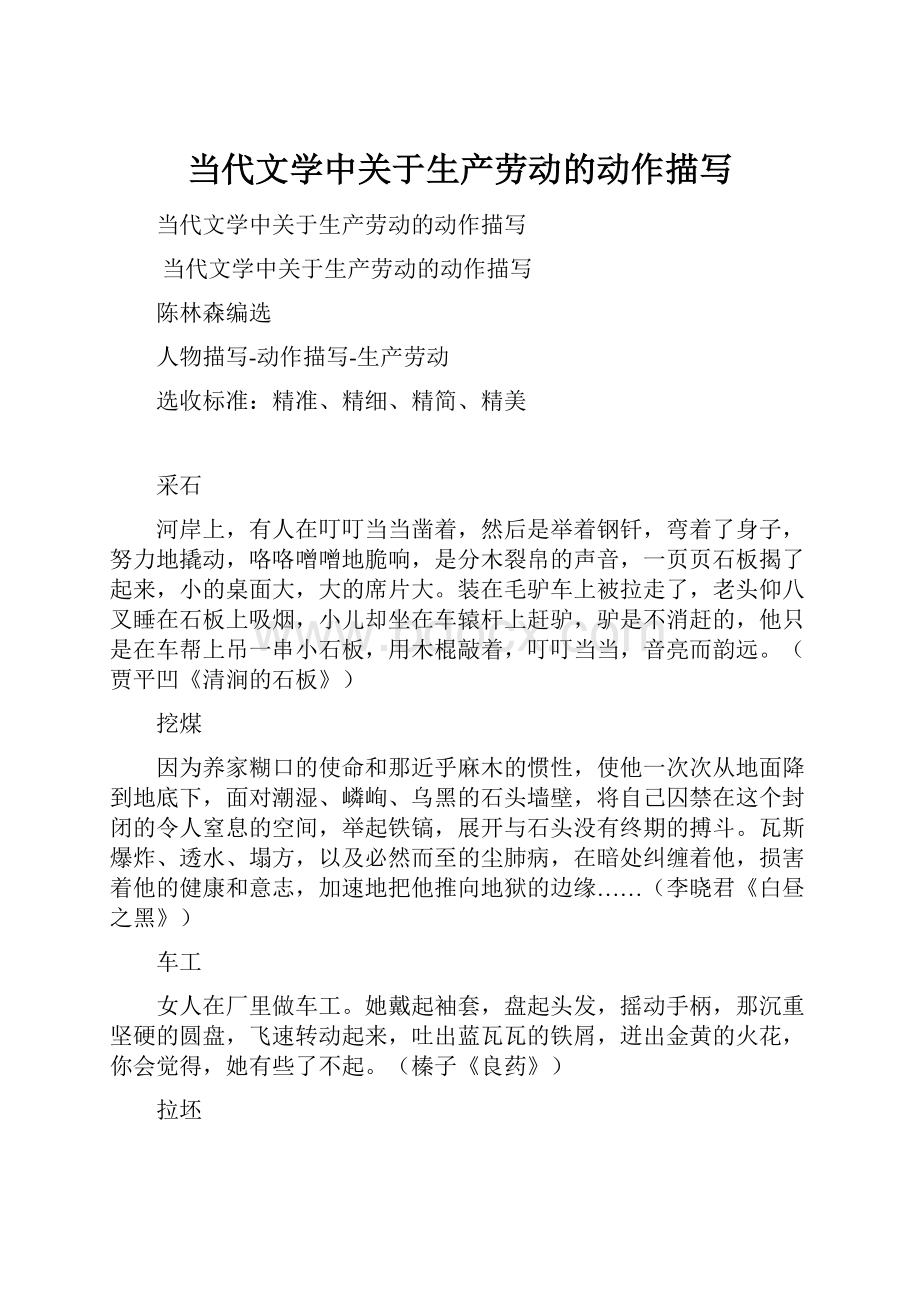
当代文学中关于生产劳动的动作描写
当代文学中关于生产劳动的动作描写
当代文学中关于生产劳动的动作描写
陈林森编选
人物描写-动作描写-生产劳动
选收标准:
精准、精细、精简、精美
采石
河岸上,有人在叮叮当当凿着,然后是举着钢钎,弯着了身子,努力地撬动,咯咯噌噌地脆响,是分木裂帛的声音,一页页石板揭了起来,小的桌面大,大的席片大。
装在毛驴车上被拉走了,老头仰八叉睡在石板上吸烟,小儿却坐在车辕杆上赶驴,驴是不消赶的,他只是在车帮上吊一串小石板,用木棍敲着,叮叮当当,音亮而韵远。
(贾平凹《清涧的石板》)
挖煤
因为养家糊口的使命和那近乎麻木的惯性,使他一次次从地面降到地底下,面对潮湿、嶙峋、乌黑的石头墙壁,将自己囚禁在这个封闭的令人窒息的空间,举起铁镐,展开与石头没有终期的搏斗。
瓦斯爆炸、透水、塌方,以及必然而至的尘肺病,在暗处纠缠着他,损害着他的健康和意志,加速地把他推向地狱的边缘……(李晓君《白昼之黑》)
车工
女人在厂里做车工。
她戴起袖套,盘起头发,摇动手柄,那沉重坚硬的圆盘,飞速转动起来,吐出蓝瓦瓦的铁屑,迸出金黄的火花,你会觉得,她有些了不起。
(榛子《良药》)
拉坯
……制瓷的第一道工序——拉坯。
雪白如面的瓷泥,在年近七旬的老师傅手中被揉成圆形的半成品。
他的脚下是一个用木棒拨动的木圆盘,没有电力,盘子只靠惯性飞速运转。
瓷泥放在盘中央。
随着盘的转动,老师傅揉捏着,用双手完成简单的造型。
一块块瓷泥在他的手中鬼使神差般变成了泥碗、泥瓶。
做好的泥坯放在院落中间的木架上阴干。
(张映勤《雨中的古窑》)
烧缸
冯大举知道这是一次发大财的机会,就挑出了上好的黄泥,在这泥里要搅拌进去石粉、鸡蛋清和糯米汤。
这大缸烧出来就不是那种泥缸了,也叫泥瓷或粗泥瓷。
秦汉久定制的是十只,进窑的至少也得十五只,出窑的时候冯大举要用柞木棒子挨个去敲,声音好的才能算数。
敲完以后还要往这缸里放满水,要用棉布把缸外擦净,然后再看看是不是渗漏,不漏的话这缸才能算合格。
(白天光《木香镇的匠人》)
制瓦
一只手将一些泥巴摔打在模子上,另一只手轻轻地转动模子,慢慢地抹匀,从模子上取下的竟然是一个筒状的泥圈圈。
老人用工具将这泥圈圈画出均匀的四个条纹,差不多快晾干后,用手一一掰开,瓦的外形就产生了。
(王剑冰《周庄事物》)
打夯
夯的重量大约200来斤,“打夯”一般是八个人一组,所以也叫“八人抬”。
一人掌握把手,七人牵抻拉绳将“夯”抛向空中,那石夯随着夯歌节奏转换重重的落地,砸出一个凹陷。
再随着夯歌升空,在掌夯人的控制下移动着位置。
“一层灰土三遍夯”,待整个地基夯实找平后,就开始挖底槽,拌入白灰土,再一层层的夯实。
(马士明《故乡夯歌》)
筑路
就在公路停止的地方,山坡上有一排低矮的木板房。
而在山坡下,一群赤膊的山民,挥着大锤,扶着钢钎,拉着板车,锤着碎石,叮当之声扬起,又在深山里悄悄消失。
那背部、那胳膊是黝黑黝黑的,汗粒在上面闪着晶莹的光泽。
(刘益善《神农架短章》)
拆墙
第一天去了两个装修工,他们都是彪形大汉。
他们先用电钻在墙上打眼。
钻头找准砖缝,在刺耳的声音中不依不饶地掘进。
担心损坏工具,他们在墙眼里喷了水,类似于血浆的浓稠液体在电钻的旋转中喷涌出来,血道子在下边的墙面上挂成了血帘。
然后他们用锤子敲,不停地敲,一块破损的砖飞到我的脚下。
然后他们换了锤子。
他们使用的锤子像春晚小品里黄宏使用的锤子那么大。
咚的一声,墙在颤,整幢楼,整个世界都在颤。
咚的一声,豁口处有砖头和水泥的碎粒掉下来,晃动的墙面上泛起一片白光。
(杨凤喜《玄关》)
挑担
雾渐渐散去,山道上过来一位挑夫,竹制的扁担横在右肩,一根差不多长的木棍搁在左肩,压在扁担下,向前伸出,与扁担成丁字状,左小臂搭在木棍上——想必是用来平衡双肩重量的吧。
……走近了,走近了,是一位30来岁的壮汉,有着岩石一般的崚嶒骨架,挑的是粮食、水果、青菜,蓝布的坎肩为汗浸透,低着头鼓着劲,额角、脖颈、胳膊皆毕露着青筋。
挑夫把担子放下,抽出木棍,一头杵在地上,一头顶着扁担,那高度,正好供他可以半站着歇息,不用大幅度弯腰。
(卞毓方《山中天籁》)
拉纤
每遇到河道狭窄处,哗哗白浪一排排自天而下,船靠岸略停,不用吩咐,这时候自有一些船客挽起裤脚下船,依次搭上一条纤索,拉着船体逆水而上,就算是给船家交钱。
纤索悠悠弯弯地悬垂,似乎并未吃上力,却不知纤夫们何以拉得一个个都四肢伏地,一颗颗屁股高高翘起被太阳烧烤。
他们胀得脸红脖子粗,额上青筋暴出,大口喘气的嘴巴几乎就要啃着地,啃着河岸上粉红色的野花,啃着岩鹰偶尔投撒过来的影子。
本地人把行船叫作爬船,我开始以为是对划船的误读,后来才觉得叫爬船也很切——纤夫们一路上确实就像狗一样爬着。
(韩少功《北门口预言》)
司炉
无法判断出年龄的司炉躬着腰身,用大锹铲着煤,不断地投向喷吐着火焰的炉膛,炉口上的挡板不断地像折扇一样打开,里面的火光一下子喷吐出来,将他的面庞及浑身照彻,司炉的整个人形就像铁匠从火焰中抽取出来的铁件,红到接近透明。
(张锐锋《火车》)
洗瓶
小萼的工作是清洗玻璃瓶,她手持一柄小刷子伸迸瓶口,沿着瓶壁旋转一圈,然后把里面的水倒掉,再来一遍,一只绿色的或者深棕色的玻璃瓶就变得光亮干净了。
小萼总是懒懒地重复她的劳动,一方面她觉得非常无聊,另一方面她也清醒地知道世界上不会有比这更轻松省力的工作了。
(苏童《红粉》)
农业劳动
在缺少金属机械和柴油的情况下,两头不见天,摸黑出工和摸黑收工是这里的常态。
垦荒、耕耘、除草、下肥、收割、排渍、焚烧秸秆等,都靠肢体完成,都意味一个体力透支的过程。
烈日当空之际,人们都是烧烤状态,半灼伤状态,汗流滚滚越过眉毛直刺眼球,很快就淹没黑溜溜的全身,在裤角和衣角那些地方下泄如注,在风吹和日晒之下凝成一层层盐粉,给衣服绘出里三圈外三圈的各种白色图案。
(韩少功《日夜书》)
双抢
炎天暑热,乡下人照样要到田里去劳作,勾头晒背,起头晒面。
尤其是七月流火的双抢,就不光是太阳晒得难过,还特别累,男女老少天天都是从天光做到摸暗,容不得有半点喘息,实在是季节不等人。
割稻子、打谷,是干地里的功夫,多少要好一点。
栽二晚就无异于人在蒸笼,上面太阳晒,下面热水煮,身体再强健的人,从田里回来,也会头昏脑胀,腰酸背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拉黄尿。
这不是一般的黄,就像是用陈年的茶叶泡出来的酽茶。
现在的农民倒是极少有这样的体验,收割机和抛秧技术以及除草剂等等已经将他们进行了第二次解放。
(杨喜平《赣北蔬菜录》)
点籽
这天播种小麦,三叔耕地,二叔跟在小宝(驴)后面点籽并撒粪。
二叔左肩挎着用棘条编制的粪斗,右肩挎着种子袋。
一手点籽,一手撒粪,籽点下去后再踩上一脚。
这一踩很重要,它让种子与土壤紧密结合,以保证种子的发芽率。
(刘凤梅《三婶》)
种菜
那时,每年一出正月,娘就开始收拾她的“宝贝”菜园。
姐弟们帮着娘先把自家猪圈里的猪粪和房前屋后堆积的土杂肥一挑一担地运到园子里,然后一锹一锨地将这些肥料撒匀,把冬耕的坷垃地耧碎耙平。
待麦苗返青、小草拱芽、山野里呈现出“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景象时,娘带上全家人将已粉化的墒地调成大小不等的块块畦田。
谷雨时节,菜地里早已种满了嫩绿的瓜菜幼苗。
(王友卓《娘的菜园》)
起菜苗子
起菜苗子看着简单,学问却不小。
菜苗子很小,很嫩,是没筋骨的,稍不注意碰到了就断了,还有不能硬拔,把根须断在土里一样不行,最稳当的起法是带着姥娘土,就是把菜苗子连同土一起起下来。
做到这一点单凭手段是不够的,还要给菜苗子浇些水,不能太湿也不能太干,太湿姥娘土起不成块,太干姥娘土容易散掉,必须干湿适中才好。
(王子群《临时夫妻》)
移栽小白菜
在秋天有小白菜可栽的人,是有福的,他们默不作声,把小白菜秧移栽下去,用拇指、食指压紧根部,然后浇灌。
过几日,也不闲着,用水把粪稀释,去描一下——我们乡下人就是这么说的:
我去“大暮凹”描一下小菜秧去。
(钱红丽《万物美好,我在其中》)
种瓜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一场春雨飘过,我娘觉得时机成熟,她把头上包了一块毛巾,把放在窗台上已经出芽的瓜种子碗,小心地放到挎篮里,去了西河滩。
……她把发芽的黑色的种子红色的种子,小心地从碗里捏出来,用手挖一个小坑,把芽儿朝上放好姿势,小心地埋上土。
这时候不能用脚踩,怕把芽儿踩回到壳里去。
(璎宁《月光下的田园》)
犁田
他看过六富叔犁田,一手扶犁把,一手挥竹鞭,轻轻吆一声,牛就缓缓走动起来,湿黑的泥土就像书页一样给犁刀抄翻上来,整齐地晾晒在太阳底下。
(肖建国《乡下一年》)
栽秧
栽秧是一个体力活,妇女们叉开双腿,弯腰在水中,一只手分拣着秧苗,另一只手迅速地取过来栽插到水田里。
手里在忙,两只脚在水田里交替着向后拖着。
因此插秧的辛苦就是在短时间内“面朝浊水背朝天”地超强劳动,长时间弯着腰把秧苗插入水田,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缪新华《栽秧号子》)
杀虫
那真是一场虫口夺粮的紧张战斗。
那时候社员们都回家歇憇了,连狗都吐着舌头躲在阴凉地方睡着了,大保却要穿上长袖衣裤,戴起草帽,捂紧口鼻罩,脖子里围一条毛巾,把全身包得严严实实,下到田里,一边摇动喷雾器,一边大步往前走。
淡黄色的“六六六”粉末喷射而出,像一条条黄龙掠过稻田,铺洒开来,一些药粉粘附在了稻禾上,也有一些粉末扬上天去,在空中凝结不动,把太阳都遮暗了。
田水滚烫,空气刺鼻。
(肖建国《乡下一年》)
插薯
春上,取窖里红薯种,植一炕桌大的土圃,待红薯发芽、长藤,细藤长若辫,便可剪插了。
雨日,大清早,我娘割来一背篮,剪刀剪,剪若咫许,一根藤蔓,可剪三五根,趁雾蒙蒙,趁雨蒙蒙(晴日,是不行的,其时红薯生命脆弱,会晒死——红薯就这点要求),无根,藤便是根,将根一行行插进土里,行了,“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本草纲目》)。
不用再浇水,也不用再施肥,噌噌噌,红薯长起了。
(刘诚龙《红薯叶》)
割麦
庄稼人一手薅住麦子,一手拿着镰刀,他们的动作从右往左,一把,一把,又一把。
等你把这个动作重复了十几遍,你才能向前挪动一小步。
人们常用一步一个脚印来夸奖一个人的踏实,对于割麦子的庄稼人来说,跨出去一步不知道要留下多少个脚印。
这其实不要紧,庄稼人有的是耐心。
但是,光有耐心没有用,最要紧的,是你必须弯下你的腰。
这一来就要了命了。
用不了一个上午,你的腰就直不起来了。
(毕飞宇《平原》)
采花
下午,何峻把我带到了采摘场地。
十几个工人散布在花丛里采摘,卡车旁的几个工人则负责整理包装工作。
他们把采下来的花按颜色分类,在剪口处蘸上保鲜液,大束大束地捆扎好,包上保鲜纸,装进一个个大纸箱里,再搬上卡车码好。
(夏岚馨《紫灯区》)
割草
我学着别人的样子,找一处茅草密集成片的地方,站好架势,左手拢住茅草,右手便扬起磨亮的弯刀连续不断地割。
由于草茎坚韧,草丛中还夹有刺条,往往要用力砍,才能使它们断绝与土地的联系。
茅草虽已枯萎。
它的锯齿状的边缘却依然锋利,待我割得一小担茅草,我的手心手背上也割出了许多细长的小口子,渗出条条血丝。
(少鸿《红薯的故乡》)
锄地
终于,西山的阴影落进了河谷,被太阳晒了一天的六安爷,立刻感觉到了肩背上升起的一丝凉意。
他缓缓地直起腰来,把捏锄把的两只手一先一后举到嘴前,轻轻地啐上几点唾沫,而后,又深深地埋下腰,举起了锄头。
随着两只臂膀有力的拉拽,锋利的锄刃闷在黄土里咯嘣咯嘣地割断了草根,间开了密集的幼苗,新鲜的黄土一股一股地翻起来。
(李锐《锄》)
锹地
他夺过一把铁锹,往地上一插,脚踩着锹的肩膀,摇晃着身体,扎下去。
他吃力地把一团盘生着密密草根的泥土掘起来,双手平端着锹柄,身体先往左转了九十度,然后猛地往右转了一百八十度,刺啦一声响,那团泥土像死公鸡一样翻滚着飞出去,落在一片盛开着淡黄色的小花的蒲公英上。
(莫言《丰乳肥臀》)
锹土
他先后退一步,使身子和取土的地方保持一定距离,拿锹的双臂向后缩,锹头对准目标,然后向前猛跨一步,一猫腰,只听嗤溜一声,连锹头带锹把,差不多把铁锹的三分之一斜插进土里。
接着,收腿直腰,顺势把锹把轻轻一提,泥土发出一声吸吮的声响,一块半米长一尺厚、象钢锭一样的坷垃,随着铁锹切割下来。
老魏趁这时换了一口气,然后一蹬腿,一扭腰,把锹向后一扬,这团五六十斤重的泥块,越过好几个人的头顶,在空中翻了个跟斗以后,摔落在一人多高的渠岸上。
(汪浙成、温小钰《土壤》)
刨草皮
山岗上处处草皮丰厚,我们耐心地,一锄一锄地刨……枯萎的草根被锋利的锄头平行切断,发出明脆的声响,像小石子与小石子的碰撞,在秋风里荡来荡去。
无须几小时光景,被锄起的草皮堆在那里相当可观(钱红丽《万物美好,我在其中》)
烧火粪
火粪,是农家肥的一种。
颇费周折。
随便找一块空地,用铁锹翻土,把土坷旯一一敲碎,垒成锥型的堆,再从中间扒开,垫一层稻草,这样的基础工夫完成后,就在稻草上陆续铺上干牛屎片、干树枝、碎木屑等,然后再在上面铺一层稻草,最后将事先扒开的土覆盖上,依然是一个锥型的土堆,两边露出稻草,以便引火用。
擦一根火柴,稻草被点燃,经风一吹,烧得呼啦啦的,紧接着,就到了土的里层,火遇到了阻拦,势头刹那间小起来,青烟适时起来了……人可不管了,挑着两只稻箩回家。
土堆里的干牛屎片、干树枝、碎木屑等什物,就那么被土蒙着,一般要独自烧上三两天才熄灭。
三两天后,人又来了,这时除了两只稻箩、一捆稻草外,还扛过来一把锄,要把土堆盘一盘,原本褐黄色的土变成黄黑色,看上去尚不够肥,再依照第一次的程序,把土烧一遍。
这样地烧过三四遍后,整个的土就彻底乌黑一片了,是瓜豆们最好的肥料。
(钱红丽《万物美好,我在其中》)
打谷
他们打谷子都是在下午,太阳开始往山那边斜了,清早割倒的稻子已经在田里晒得酥蓬蓬的,这时候抓起一把稻子,用力甩起来,稻穗打在桶壁上,砰地一声,谷子便全落进了桶里。
(熊正良《美手》)
晒谷
晒谷是乡间最轻松的活,多数由老人和妇女担任。
主要是看场,防止鸡、鸭、猪、牛等畜牲来糟蹋。
到了半中午,也要翻翻谷子。
翻谷子是有讲究的,掀起席子的一角,连同谷子一起折过半,然后,对角折过来,隆起的谷子就幻出一个精美的菱形,再用木耙把谷子摊开。
于是,谷席上便清晰地展现出一道道柔美匀称的金色纹路,如细浪,如农家古朴俚歌的旋律。
(沈世豪《晒谷》)
摘棉花
在地头,表姐为我在腰里系了个蓝白格子的包袱皮儿,贴腰的那面勒得紧,外面则松松地张了口,以便往里面装棉花。
表姐腰里也系个同样的包袱皮儿,边摘棉花边为我讲解摘棉花的要领——下手要准,抠得要净,棉花碗儿里不能丢“棉花根儿”。
……表姐看我摘得拙,笑死了,跑过来为我示范——眼到手到,左右开弓,同时摘两朵棉花,指尖带了钩儿一样,轻轻一抠,棉花碗儿就溜光地见了底儿……不一会儿,表姐的包袱就鼓起来了,怀孕一般,拿手托着包袱底,腆着肚子回到地头,把一包袱棉花倒在一个大包袱皮儿里,轻了身回来继续摘。
(张丽钧《摘棉花》)
种烟叶
前几年种过烟叶,挣钱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
后来就不种了,可能是嫌太麻烦。
烟叶很油,粘在身上黏糊糊的,采了烟叶还要编成杠,然后在烟叶楼子里炕。
的确很麻烦。
烟叶别人家不种,一家半户的想种也种不起来,难就难在烟叶楼子上。
叶子长成个儿了就得采,采了就不能等,不然就会烂掉,一次采的烟叶根本不够一炕,硬要炕很划不来。
(王子群《临时夫妻》)
刨花生
刨花生是一项喜人的劳动,同学们刨花生的兴致都很高。
他们瞅准一棵花生的根部,用小抓钩把根部的土掘松,揪住花生棵子往上一提,一嘟噜白白胖胖的花生就从土里出来了。
花生刚从土里出来是很美气的,美气得颤颤悠悠,像在风里荡秋千一样。
(刘庆邦《乡村女教师》)
刨红芋
割过麦子收春红芋了。
李小琴很会刨红芋,双手一前一后握住抓钩,轻轻提起,重重落下,落到一半即收起劲慢慢、慢慢地一拉,一嘟噜红芋便拉了出来,够那姓杨的学生拾半天。
(王安忆《岗上的世纪》)
打芝麻
初秋时,将熟的芝麻就被砍下来,捆成个子拉回家,戳在房顶上晒。
矗立着的芝麻个子顶着头,看上去像一间小屋子,又像头顶着头的一排人。
芝麻粒长在芝麻梭子里,当芝麻梭子一伐又一伐地被太陽晒开,芝麻粒暴露出来时,主人就把矗立着的芝麻个子提起来,头朝下地用棒捶“投”。
棒捶打在芝麻个子上,成熟的芝麻溅落在铺好的大包皮袱里。
被捶打的芝麻个子再被戳起来,待晒开了芝麻梭子再投。
(铁凝《笨花》)
摘柿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里的多数农民盖起了新房子,但收入仍然很低。
主要一笔是深秋对于柿子的收获。
一般是家庭的一男一女上阵,男子爬到树上,女子拿着一个布单,两侧绷上木棍,手持木棍将布单抻平,等在树下,男人从树上摘下柿子,投下来,女人用布单迎上去,乒的一声,柿子完好无损地收下来了。
(王蒙《山中有历日》)
车水
夏天他还在枫杨树乡村的稻田里打稗草,洪水还没有从山上冲下来,所有人都在稻田里无望地奔忙。
有时候在正午时分踩水车,听着风车叶片吱呀呀地枯燥地转动,水从壕沟里慢慢升高,流进稻田。
(苏童《米》)
拉架子车
母亲借来了架子车,我们一车车地运。
土地被刨翻得虚松不平,轮子陷进土里拉不出来,母亲往手心啐一口吐沫,搓一下,拉紧车把,咬住牙、屏住气,像一头发狠的牛。
车轮终于从土坑出来。
我和弟弟拍着手在路边欢呼。
下坡路,母亲被重车推赶着一溜儿小跑,我牵着弟弟在后面追。
我看见鸟雀从田野飞过,如果我再大几岁,或许我知道那是一只只鸟妈妈,它们在觅食、衔草,搭建过冬的巢,哺育幼雏。
(贾志红《北邙往事》)
锯树
那天,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把小钢锯,搭在了树身上。
他个子不高,锯搭在了相当于他身高的三分之一处,他攥着锯,锯很锋利,一下一下地来回扯着,密集的锯齿咬中了树,一点一点地往里挺进,白如泡沫的碎屑漾了出来。
(简默《三棵树》)
打猪草
小时候,我常跟着村里的小孩一起出门割猪草,特别是在缺草的冬季,几乎每家的小孩都有割猪草的任务。
我们每人肩上挎个篮子,一群人在旷野上走走停停,像冬天一群觅食的麻雀。
……
没草时,大家漫散着步子,东瞧西望;找到草时,大家就争先恐后,镰刀嚯嚯。
别看大家都差不多大小,又都在一起割草,可就是有敏捷和笨拙之分,有的孩子用猪草把篮子灌得满满的了,可有的孩子的篮子才刚刚及半。
(谢宗玉《四季农事》)
吆鸭子
秦三老汉是秦村人,曾经是有名的吆鸭子的竿儿匠。
每年一过芒种,秦三老汉就会从孵房里逮上五百小鸭儿,担着他的鸭儿棚子,带着他老婆一块儿,赶着鸭群出了村。
鸭子在闲田里自由觅食,他就跟他老婆手持长竹竿站在高处,一个这头,一个那头,不时相互吆喝一声,通报鸭子的去向。
到了夜间,两口子就搁下鸭儿棚子,一个烧火做饭,一个圈鸭子。
等到天亮,继续赶着鸭群走,走过土镇、走过爱城、走过竹城……一路上走走停停,等走到成都已是中秋,鸭子也肥了。
(安昌河《冬至》)
喂牛
其实,喂牛没什么难的,用破老汉的话说,只要勤谨,肯操心就行。
喂牛,苦不重⑨,就是熬人,夜里得起来好几趟,一年到头睡不成个囫囵觉。
冬天,半夜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
尤其五更天给牛拌料,牛埋下头吃得香,我坐在牛槽边的青石板上能睡好几觉。
(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套马
马倌套马是一项优美、高难的艺术,也可变为套狼杀狼的高超武艺。
马倌为了给己给人换马、给马打鬃、打药,还要阉马、验马、驯生马,几乎天天离不开套马。
从古至今,草原民族的马倌练就了一身套马绝技,使用一根长长的套马杆,在飞奔的马背上,看准机会,探身抖杆,抛投出一个空心索套,准确地套住马脖子。
好马倌一套便中,很少落空。
此技用来套狼,只要马快,与狼的距离短,或有猎狗帮忙,同样能套住狼。
(姜戎《狼图腾》)
养蜂
村里有几户养蜂的。
一排排的蜂箱放置在村外的油菜地里,每天有人戴着网罩的帽子在蜂箱前忙碌。
有时从蜂箱里抽出木格子,上面爬满了蜜蜂;有时拿一只镊子在木格子上面点着什么;有时则把木格子放进一只桶里转动,停止后下面是透明而闪着光泽的液体。
那是蜜糖。
很甜很甜。
(干亚群《小物三题》)
采茶
杭一中的初一年级那个春天,曾全班集体去梅家坞采茶半个月。
湿漉漉的青山绿水,漫遍野都是绿油油的茶园。
无数娇嫩的叶芽,从蓬勃的茶树上一片片翘首探头,用一双双小手轻轻采摘下来,小心地置于竹篓中,拇指与食指都被茶叶染得绿了。
细雨蒙蒙中采茶归来,全身的衣裤都沾着茶叶的香气。
(张抗抗《说绿茶》)
割苇
他挥汗如雨,弯刀在触及苇杆的瞬间传来一种细碎而清脆的断裂声,那声音坚韧地深入到他的灵魂中去,痛苦并且快乐。
他一直以俯冲的姿势朝苇荡弯着身子,苇杆密不透风,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弯刀带着风穿行在错综交集的苇丛,他把气力都汇聚到腰部和右手腕上。
一天过去,他感到腰开始发胀发酸,手腕开始麻木。
身后已经小山一样堆垛着他割下的芦苇,在湖边晓霞的映照下,芦苇垛闪烁着金子般的光,华丽得有点晃眼,这是他一天辛苦的成果。
(刘鸿伏《割苇的少年》)
编席
就从剥苇、破篾儿、碾篾儿、编席这一整套活儿下来,她第一张席(当然是丈席了)用了七天,第二张席用了四天,第三张席仅用了两天一夜(这是村里女人最快的速度了),第四张席仅用了一天一夜!
这时候,那手已经不是手了,那手血乎乎的,一处一处都缠着破布条子;那腰是弹弓做的么,弯下去的时候,就成响成晌地贴在席面上……以后就好了,游刃有余了。
那手,快得就像是游在水里的鱼儿,长长的篾条儿在她的手下成了翻动着的浪花,一赶一赶的,哗哗哗哗,就“浪”出一片来,女人们说,那真叫好看。
这时,她竟一天编一领席,老天,还不耽误做饭、喂猪!
(李佩甫《城的灯》)
织布
向喜每逢看见眼前这套四蓬缯被褥,便想起同艾,想起她从纺线、染线、浆线、掏箸递缯到上机织布的情景。
他尤其愿意看同艾坐在织布机前那副前仰后合的模样,她身子弯下去,胳膊飘起来;身子直起来,胳膊又摆下去。
她微晃着头,一副银耳环在昏暗的机房里闪闪烁烁。
(铁凝《笨花》)
打油
打油时,油匠们都光着上身,穿着短裤,打着赤脚,野性的肌腱如铁打的砧板,刀枪难入。
随着号子,油匠们先是扶住油锤边跑边退,把油锤高高举起。
又边跑边进,把油锤低低放下。
油锤和油楔子猛然一撞,沉闷、响亮而又旷远的声音,就从油坊里飘出来,飞得很高,跑得很远。
楔子被油锤越撞越进到油槽里面,油枯被楔子越插越紧缩一团。
油,就亮闪闪地被挤压出来,丝丝,线线,漉漉滴淌。
浓浓的油香,立时弥漫,飘入肺腑。
(彭学明《流年》)
切药
华公公在药铺里属于哪份摊子,我们始终搞不清。
全体人员到齐时,他便一个人去药铺后面那间阴暗的刀房切药。
他能将大大小小圆圆方方结结实实的各种药块统统切得薄如纸片,匀匀称称。
在旁边站上片刻,听着“嚓嚓嚓”的落刀声,看看飘飘洒洒的药片儿,是一件极快活的事。
(吕锦华《五味糖》)
打面
卞玉春在村口的路边开了一个打面机房,打面机是用一台柴油机带动的。
无人打面时,打面机房的门是锁着的。
卞玉春就在附近的地里干活儿。
见有人扛着粮食或用架子车拉着粮食往打面机房那里走,卞玉春跑着就过去了。
他用一根铁制摇把,把柴油机摇得嗵嗵地动起来,传动皮带往打面机的轮子上一挂,打面就开始了。
(刘庆邦《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