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 乐黛云未名湖畔学界双璧.docx
《汤一介 乐黛云未名湖畔学界双璧.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汤一介 乐黛云未名湖畔学界双璧.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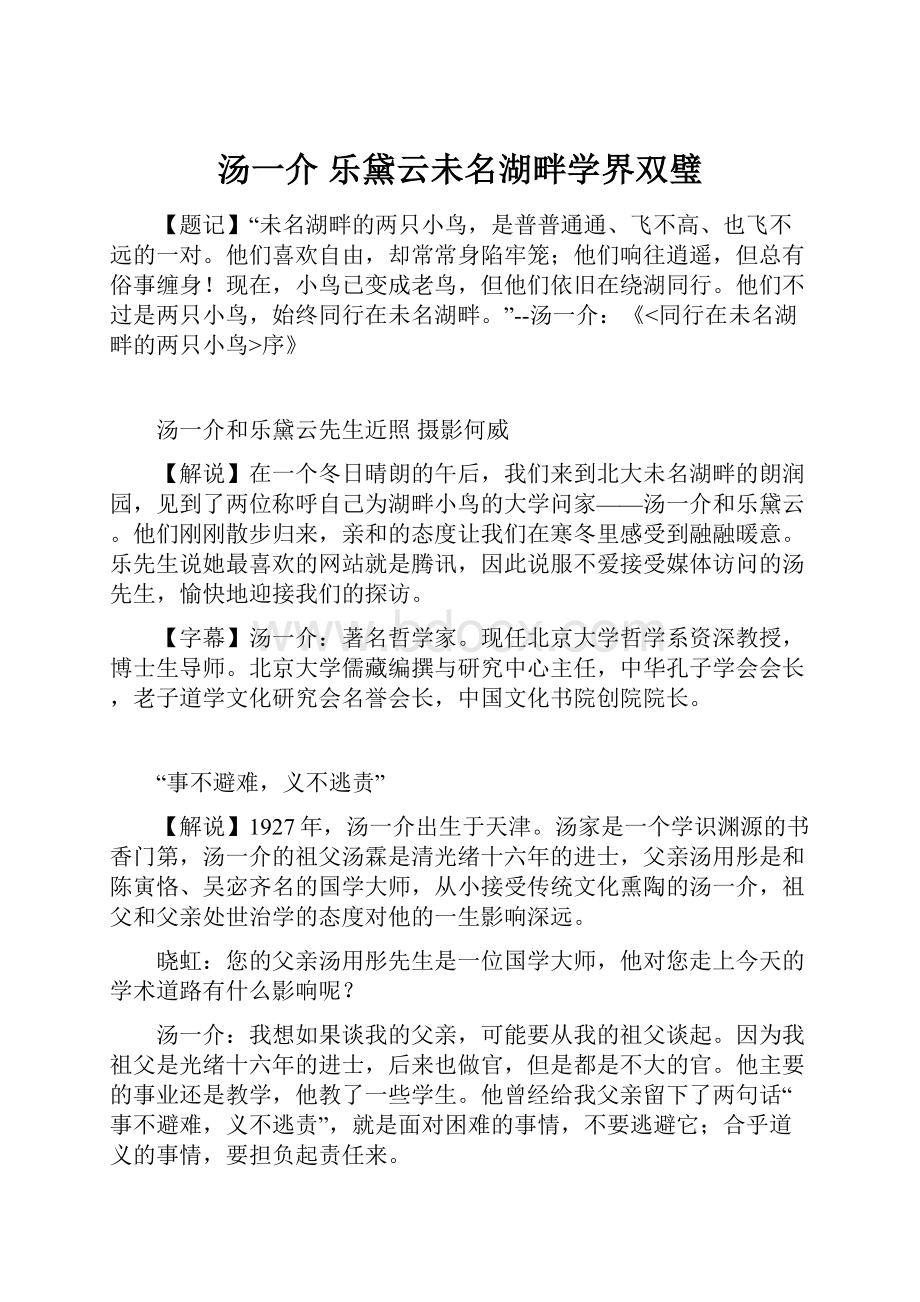
汤一介乐黛云未名湖畔学界双璧
【题记】“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
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响往逍遥,但总有俗事缠身!
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
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
”--汤一介:
《<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序》
汤一介和乐黛云先生近照摄影何威
【解说】在一个冬日晴朗的午后,我们来到北大未名湖畔的朗润园,见到了两位称呼自己为湖畔小鸟的大学问家——汤一介和乐黛云。
他们刚刚散步归来,亲和的态度让我们在寒冬里感受到融融暖意。
乐先生说她最喜欢的网站就是腾讯,因此说服不爱接受媒体访问的汤先生,愉快地迎接我们的探访。
【字幕】汤一介:
著名哲学家。
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儒藏编撰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解说】1927年,汤一介出生于天津。
汤家是一个学识渊源的书香门第,汤一介的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和陈寅恪、吴宓齐名的国学大师,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汤一介,祖父和父亲处世治学的态度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
晓虹:
您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是一位国学大师,他对您走上今天的学术道路有什么影响呢?
汤一介:
我想如果谈我的父亲,可能要从我的祖父谈起。
因为我祖父是光绪十六年的进士,后来也做官,但是都是不大的官。
他主要的事业还是教学,他教了一些学生。
他曾经给我父亲留下了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就是面对困难的事情,不要逃避它;合乎道义的事情,要担负起责任来。
我父亲在这个方面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是我祖父留给我父亲的话,所以我父亲也把这样的要求留给我。
我想举一点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方说“事不避难”。
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来看,佛教传入中国,在其他写中国哲学史(的书)里,这个方面都没有打通,都遇到了一个难关。
到底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有什么影响?
起了什么作用?
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他把这个问题基本上应该说是打通了,所以其他的学者都认为他是使中国哲学史可以比较完整写下来(的人)。
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佛教到底有什么影响,这是他的贡献。
他的贡献可以说是把这段中国哲学史的空白基本上填补了。
这本来是一个难题,他花了15年的时间写《中国佛教史》,但是没有写完,只写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而《隋唐佛教史》只是一个史本,这个史稿是我帮他整理和出版的。
另外他的一大贡献就是,西方学者(包括某些中国学者,如张东荪)常常认为中国没有本体论哲学,但是他专门研究魏晋玄学,提出来有一种中国式的本体论,跟西方的本体论哲学是不同的本体论。
所以现在的魏晋玄学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种学问,而且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大的进步。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事不避难”的精神影响了我。
“义不逃责”,北京大学从昆明搬到北京来的时候,是跟清华、南开分别搬迁的。
当时胡适在美国,傅斯年作为代理校长在重庆,可是学校本身是在昆明。
谁管的昆明这一摊子呢?
当时傅斯年就清我父亲来帮他管这一摊子,怎么样(把学校)从昆明搬到北平来。
那时他虽然刚50多岁,但身体不好(高血压),可是他担当起这个任务。
主要的工作是聘任教授……因为他没有做过这种行政工作,他做的都是学术工作,即使是担任系主任、文学院长(的时候),也是学术工作,行政工作他没有做过。
解放后他原来是校委员会主席,(那时候)没有校长,他就做校委员会主席。
后来,派马寅初先生来做校长,我父亲就做了副校长。
到1952年,学校从沙滩搬到燕园来,分工让他做什么呢?
管基建和财务。
他完全不懂基建和财务,但是也一直管了两年,直到他生病为止。
他这种“义不逃责”的精神对我也有些影响。
筑建魏晋玄学的理论构想
【解说】汤一介子承父业,和父亲汤用彤共同筑建了魏晋玄学的理论构想,这被看做是汤一介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
汤一介先生近照摄影晓虹
汤一介:
在80年代以前,在北大我也教哲学,教的是中国哲学。
那个时候我们几乎完全是用苏联的模式来进行教学的,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模式,完全没有创造性、没有个性。
80年代开始,我就考虑自己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不同的路子来研究学问。
当时我就想我要从什么方面来突破呢?
我认为可以从魏晋玄学这个方面来突破。
我的突破可以说对我父亲的魏晋玄学有一点补充。
因为他没有写完这本书,我的突破就是从这些方面突破。
魏晋玄学家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每一个玄学家都会留下来一些他没有解决的问题,因而,下面的一个哲学家来解决(之前)的问题。
(但是)他又留下来新的问题,又要后面的人帮他解决,所以这样哲学才有前进,我们才可以找出魏晋玄学的内在逻辑,发展理路,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魏晋玄学的发展。
对魏晋玄学的研究,在1949年后,我可以说是最早的,1981年讲这门课,1983年出版《郭象与魏晋玄学》,这是最早的研究魏晋玄学的一本书。
现在写的人就更多了,所以这门学问就越来越在中国受到重视。
我对西方文化并不排斥
【解说】受传统家庭氛围的影响,汤一介性格儒雅平和,内敛沉静,但这似乎和他开放自由的治学心态并不矛盾,他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却又对西方文学和哲学以及西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
汤一介:
虽然很多人说我是儒家,实际上我是很喜欢西方哲学的,特别是西方文学。
我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应该讲比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俄国的托尔斯泰这些(作家)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在年轻的时候就定型了,还有法国的纪德(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汤一介先生在未名湖畔季羡林先生栽种荷花前留影资料图
我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现代的我不喜欢听,但是我也并不喜欢京戏,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欣赏。
我最喜欢西方古典音乐。
我也很喜欢西方的建筑,欧洲大部分的国家我都去过。
有时候我也喜欢旅游,我刚从武夷山回来。
国外的我也去了很多地方……有的时候在欧洲去旅游,有的时候到北欧、有的时候到北美、澳洲去看看各个地方。
因此,我对国外的东西并不排斥,而且有的我还是很爱好的。
我不是一个杰出的哲学家
【解说】或许正是这种开放的心态和兼收并蓄的治学思路,让汤一介不断提出“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问题,从而推动了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
晓虹:
在我们访谈的开始时,您说到了一段话,您说因为完成不了那种构建一个完美的哲学体系的愿望(转而去编撰《儒藏》),在您的心目中,一个完美的哲学体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汤一介:
用“完美的哲学体系”这个词本身就有点问题。
我认为任何哲学体系它都只能是相对地完美,不可能有绝对地完美,它都会留下一些它没有解决的问题。
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很想成为一个哲学家,可是解放后有一个说法,只有马克思、列宁、恩格斯和毛泽东才能叫做哲学“家”我们这些做哲学的人只能叫“哲学工作者”。
为什么我们只能叫“哲学工作者”呢?
因为我们的工作是解释那些领袖的思想,是用那些领袖的思想来解释历史和现实社会的。
在1949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么长时间,我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哲学工作者,我的任务就是解释这些领袖的思想。
我要用他们的思想来解释历史,来解释社会生活。
这样的一个思想已经影响了我30年,要从这个思想全盘解放出来是相当困难的……
虽然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哲学家,但是我还可以提出一些哲学的问题来,让大家来讨论,来考虑。
首先,我提出了美学、哲学范畴的问题,接着,1983年我提出“真、善、美”的问题,我认为可以用能不能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来说明中国对真、善、美的看法。
后来我受到美国余英时的影响,他提出了一个“内在超越”的问题,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内在超越”的哲学。
西方哲学是外在超越的哲学。
我受他影响,我就研究“内在超越”的问题,因为他开了一个头,后来我就研究儒家“内在超越”的问题,道家“内在超越”的问题,还有中国佛教禅宗的“内在超越”问题。
此后,我不断地提出一些问题来。
后来到90年代,主要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我就想到“和而不同”的问题,是不是孔子的这一思想可以为“文明共存”,为多元文化提供某些思想资源?
“再后来我是讲“新轴心时代”的问题,再后来我就讲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就是说对哲学不能“照着讲”必须“接着讲”。
第一个是怎么样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第二个是怎么样接着西方哲学来讲;第三个是怎么样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
必须“接着讲”,不能照着他们来讲。
完全照着他们讲,一是不一定适合当今中国的社会,另外一个,这个学术就不能得到发展。
讲“新轴心时代”三个“接着讲”。
现在我考虑的是文化中的“普遍价值”的问题。
所以,我虽然不能成为一个很杰出的哲学家,但是我多少可以提出一些哲学问题,让大家来考虑。
自由是一种创造力
【解说】汤一介提出哲学问题,同时也在生活中实践着自己的研究,“和而不同”是他的思考,也是他的处世之道。
在他看来,自由是一种创造力。
汤一介:
当然我这个人是比较平和的,不大在乎名利,也并不想做官赚钱,这些欲望都没有。
而且我也很少去批评别人,当然,对我的学生有一些问题,我会跟他们讨论,给他们建议。
有一个问题可以说明我的情况,1984年建立中国文化书院,中国文化书院在当时可以说是第一个建立的民间学术团体……当时在初建的时候,有冯友兰先生、有张岱年先生,他们都是支持办中国文化书院的。
1984年我从美国开会回到中国,要正式成立中国文化书院,大家就希望我做院长。
我的想法是如果建立这样一个学术团体,一定应该像蔡元培先生一样,是“兼容并包”的。
所以我找的参加的学者是各种各样的学者,有像梁漱溟先生这样的学者,当然冯友兰先生他们都参与了。
也有李泽厚、庞朴这样的学者还有“全盘反传统”的,如包遵信等,我都请他们来参加。
为什么呢?
我觉得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你只有是兼容并包的,能够有很自由的讨论环境的学术团体,这样才真正能够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
因此,我和所有这些学者相处都很好。
我当然我有的看法,看法不一样,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例如我跟李泽厚、庞朴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也不一样。
而且像杜维明先生也是我们文化书院的导师,我们也请他来,因为我对现代新儒家也有我的看法,但我们都是好朋友。
可能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所有这些人的长处就可以补足我的一些缺陷。
不可能有一个学者什么问题都比别人强,绝不可能,我从来不认为我自己的学问是比别人有多强的,所以我现在非常反对说“大师”。
我不是大师
【解说】汤一介很反感被称作大师。
在他看来,这个时代缺乏产生大师的条件。
他曾经感慨上个世纪后半叶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大师。
在他看来,只有两个人是自己非常欣赏的。
晓虹:
您对“大师”这个称呼这么反感,所以说您绝对是把自己和这两个字分清楚的?
汤一介:
对,我自己从来不说我是大师,而且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当大师,而且自上个世纪后半叶到现在为止,我也没看到一个真正可以称得起“大师”的学者。
我所比较欣赏的,在1949年以后有两个学者,一个是费孝通,特别是费孝通晚年,他并不高调,他比较低调。
但是他提出的三个思想:
多元一体、文化自觉、文明共存,我觉得对中国讲应该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我比较佩服的学者是华东师大的,也是已经去世的教授叫冯契。
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这个马克思主义是有他非常鲜明的特点。
他希望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中国儒家思想,还有西方所谓的“分析哲学”,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他认为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性与天道”的问题。
晓虹:
大师是必须得要时代才能创造的吗?
汤一介:
对,因为你的思想要定于一尊的话(旧指思想、学术、道德等以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做唯一的标准。
),很难产生大师。
必须有自由思想,才可以产生大师。
因为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我们是学习苏联的“全盘苏化”。
我有一个想法,政治上也许可以有一个指导思想,也应该允许讨论。
但是,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应该是百家争鸣,这样学术才会真正得到发展。
因为自由是一种真正的创造力。
《儒藏》:
一百年都不能替代的典藏
【解说】在汤一介先生的书架上,整齐排列着已出版的33本《儒藏》,藏蓝色封皮,烫金的字,格外悦目。
作为这部集中华儒家文化精髓的浩淼工程的总编纂,汤一介坦言责任重大。
汤一介:
我快到80岁的时候,就提出了编《儒藏》,为什么我要提出编《儒藏》呢?
因为过去有《佛藏》、《道藏》,一直没有《儒藏》。
明清两代的学者都曾经提出要编,但是这个工程太浩大,没有实行。
……
从2002年我提出编撰《儒藏》,2003年教育部批准,2004年我们开始实施了。
经过了五、六年,我们才出版了33本,要全部完成《儒藏》的精华编,一共是330本。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就是现在《佛藏》,各种各样版本的《佛藏》有20多种,但是,现在世界研究佛学的学者通用的是日本的《大正藏》,“大正”是日本皇帝的年号。
为什么大多学者都用《大正藏》?
因为《大正藏》是个排印本,它有句逗,而且有校勘记,所以大家用起来比较方便。
而其他《佛藏》大部分都是影印本,影印本是没有句逗的,也没有多少校勘记,所以用起来不方便。
我们做《儒藏》不是用影印办法,我们大体是找一个很好的本子作为底本,再找两三个本子作为校本,作出简明的校勘记,然后把它做成排印本。
加上通用的标点,让大家容易读,容易利用它,而且可以做电子版。
我们既然做了,就希望大家都用我们这个版本,这是中国人自己编的版本。
我算是编撰首席专家,在我组织下面差不多有400人,400人而且不完全是中国学者,有韩国学者、有日本学者、有越南学者……组织这样大的一个队伍,而且是带有一定的跨国性质的大工程,我不敢说是头一个,至少是非常少有的。
因此,我觉得这方面我也是受父亲影响,应该“义不逃责”!
既然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那么大的作用,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主流,那我们就不应该没有《儒藏》,只有《佛藏》和《道藏》,那不行。
我们要编撰的《儒藏》是一个可信的,可用的,是一个比较规范的,可以传世的版本,至少在一百年内让各国学者都可以利用它来作研究。
【字幕】乐黛云,现任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曾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现代文学学会理事。
乐黛云:
我有八分之一的苗族血统
【解说】和乐黛云先生对话,节奏显然要快了很多,这位时时都将笑意写在脸上的学者,思维敏捷,快言快语,风格和汤一介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乐黛云先生近照摄影晓虹
晓虹:
据说您是有苗族血统的,而且汤先生说这和您现在开朗的性格也有关系,是这样的吗?
乐黛云:
我想可能有一点关系,苗族血统大概只有八分之一,就因为我的祖母是苗族血统,所以可能有一点。
你知道苗族是很喜欢唱歌、跳舞,而且是很开朗的,谈情说爱都是很公开的。
所以当然也有一点影响了,从小我周围都有很多苗族和仲家族,仲家族也是和苗族差不多的,所以总会受到一些影响。
不是像有些大家闺秀那么拘束,或者说非常讲究规范的,不太是那样的。
晓虹:
您的家族当时在贵州的时候也是一个大族,在印象当中,一个大家族的姑娘总是要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乐黛云:
我可不是那样。
(笑)
从小就受到西方文学的熏陶
【解说】乐黛云,1931年生于贵州,她的父亲是贵州大学的英文教授,在当地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乐黛云从小受父亲的影响,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并且在气质、性格乃至未来选择大学的问题上,都深刻地留有父亲的印迹。
乐黛云:
我父亲很年轻就到北大来,他当时考英语系,没有考上,是胡适给他面试的。
他对这一点念念不忘,老说胡适太严格了,说他英语读音有贵州腔,所以不能要他。
当时因为家里比较有钱,(就)在北大旁听了四年……他在北大的时候,正好是1924年、1925年,就是把溥仪赶出故宫的时候,所以当时他每天都去旧货摊上,看看那些太监拿出来卖的东西,他买了好多件很好的古玩,还有一件敦煌的残卷。
因为他喜欢英文,喜欢西方文学,也受了很多特别是浪漫主义的感染……他从北大回贵阳后是当地最开明的,也算是一个很出名的人物。
他教英语,拿了一个stick,人家就给我形容,跟我说你父亲那时候可了不得了,穿着西装,拿一个stick,还开舞会。
这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在贵阳那个闭塞的环境下,是从来没有的。
我从小就在他那个氛围里长大,所以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条条框框压迫之类。
年轻时代的乐黛云风华正茂时资料图
从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从初中开始就念了很多拜伦、雪莱,这样的一些人的诗,特别喜欢,而且也受他们的影响。
我的中学时代正是云、贵、川大后方文化十分繁荣的时期。
我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不光是苗族血统的问题,要不就成了血统论了……我们那时候可以听各种音乐会,有古典音乐欣赏,为了学英语口语,常常去参加英文礼拜,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多条条框框,反而是在一个非常开放的环境下面成长起来。
乐黛云:
那时候我一心一意要革命
【解说】年轻时代的乐黛云,积极进步,充满了革命激情,当时的北大成了她展示才华最好的舞台。
乐黛云:
那个时候我就是一心一意要革命,要上北京大学。
北大是最革命的、最开放的、最能培养自由思想的。
对于北大那些人从胡适到鲁迅,到陈西滢我都非常崇拜,所以我特别想到北大来学西方文学。
而且我父亲要进北京大学没有进成,只是一个旁听生,是一辈子的遗憾。
其实他也很希望我能来北大,可是那个时候正好是1948年秋,北京已经很危急了,所以他也很担心我。
那时,家里也没有很多钱,我同时还考上中央政治大学,中央政治大学不单是提供所有的学费、衣食住行,(还有)零花钱,可以一分钱都不花,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很希望我去。
而且他怀着一种幻想认为会南北分治、划长江为界。
如果是在南京的话,还可以经常见面,还可以回家,如果到了北京以后就更回不去了,永远见不了了,所以他有这个想法。
晓虹:
那您到了北大,当时还是兵荒马乱的,您害怕吗?
乐黛云:
对,形势是很紧张,但我一点都不害怕。
那时候我记得北大的迎新工作组到前门火车站去接我们,一大卡车人,大家唱着革命歌曲进城,高兴得不得了,根本没有什么害怕的感觉。
晓虹:
你怎么胆子这么大呢?
乐黛云:
当时不是我一个人,大家都是这样的。
进城的时候,学生里面都非常兴奋,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在大街上就唱着走。
也没有人敢怎么样。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过很多运动,如“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等,学生运动非常红火。
我来的时候城墙上面还有“反饥饿、反迫害”的旧迹。
那是一个很兴奋、很高昂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害怕的,甚至后来围城,听到炮声隆隆也觉得特别好。
晓虹:
那您到了学校之后,都做了一些什么呢?
我知道您当时和汤先生都是团里面很进步的学生干部。
乐黛云:
那是后来了,刚刚到学校的时候是1948年,那时候我还不是干部。
1948年开始做“面粉银行”,那个时候因为学生都没有钱,可是物价高涨。
今天买了一袋面,明天就只能买半袋了,所以“学生自治会”办了一个“面粉银行”。
就是说学生可以把钱交给这个银行,这个银行马上给你买成面粉。
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涨价以后,你还是有这么多面粉,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利。
当时我也参与这个工作,去买面粉或者收钱等等。
晓虹:
您还做过这个呢?
乐黛云:
这个做的非常有意思,而且很高兴。
然后就参加读书会,读一些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每个礼拜三次。
然后还参加跳舞,对外国民间的土风舞非常喜欢,对新疆的那些舞蹈也很喜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生活。
后来,49年二月迎接解放后,才到青年团工作。
已经是二年级了,二年级就从宣武门的北大四院搬到沙滩红楼那边去了。
乐黛云的年青时代资料图
晓虹:
那您到了北大之后,当时可供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专业呢?
乐黛云:
当时没有什么可选择的,我报名的时候就报的是西语系,因为我喜欢西方文学。
晓虹:
就是因为从小受到的这种影响以及接触?
乐黛云:
对,从小看的就是这类书。
那时候还特别喜欢俄国文学,屠格涅夫的作品,对革命女性是非常崇拜的。
我没有选择,我报的是西语系,可是后来在录取的时候,据说是沈从文先生看到我的一篇入学的文章,觉得这个小孩可以让她参加写作,参加中文系,就把我取到了中文系,所以无所谓选择,那就上中文系。
乐黛云:
我劝沈从文留下来
晓虹:
关于沈从文先生,据我看到的一些报道,当时有一些老师要撤离到台湾的时候,是派您去劝沈从文先生留下的,那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乐黛云:
那个时候我已经参加地下组织了,是民主青年同盟的成员。
那时大家都帮着做一些工作。
我们还被派去调查哪些地方不能炮击,给解放军传过去,如说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建筑,东交民巷使馆区,故宫附近的街道等。
我们还被分配去动员一些教授,希望他们留下来,说共产党政府对他们一定是很好的。
我就是被分配到了沈从文家。
因为沈从文教我的大一国文,而且他也比较喜欢我,所以我就去了。
去了我就劝他,可是我觉得当时我的劝说根本没有什么理论,也没有说服力。
沈从文先生资料图
晓虹:
您当时怎么劝他的?
乐黛云:
我当时就说我们一定保证你不会遇到危险的事情,共产党绝对不会对你采取什么粗暴行为。
其实那时候我心里说我凭什么保证,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晓虹:
那时候实际上对自己说的这些话也是有怀疑的吗?
乐黛云:
没有怀疑,可是觉得有些空洞。
因为只能说这几句,你还能说什么呢?
可是沈先生就是笑而不答,好像说你一个小丫头怎么说这样的大话,凭什么说呢?
我当时觉得他就是这种感觉。
晓虹:
如果现在让您再回过头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劝他的话,您觉得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打动他?
乐黛云:
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从他后来的遭遇来说,可能我就根本不应该劝他。
因为后来他的写作和教学完全停止了,甚至于自杀过一次,没有成功。
生活对他的迫害一定是很严重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压抑一定使他非常痛苦。
所以他后来决定停笔创作,只做服装史,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的服装,我想他的心情一定是很郁闷的。
现在如果历史重演的话,也许我就不会劝他了,这是我现在的看法,应该让他更自由地选择。
晓虹:
不要有一些外力去作用。
乐黛云:
对。
晓虹:
个人意志的自由。
乐黛云:
对,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应该这样比较好。
而且我劝他也没有什么太多道理,也没有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东西。
晓虹:
这也是您当时的一个经历?
乐黛云:
也是在执行一个组织任务吧,既然派你去,你就得好好执行这个任务,就是这个观念。
晓虹:
您年轻的时候,真的觉得您特别地革命,特别地积极。
乐黛云:
对,这个是肯定的。
选择比较文学是机缘巧合
【解说】乐黛云选择比较文学学科,有人认为是受了她的公公汤用彤先生的影响,汤老先生当年在哈佛选的第一门课正是白璧德讲授的比较文学,而实际上,这完全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但也许恰恰是冥冥中的机缘巧合。
晓虹:
那您是怎么样走到比较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上去的?
乐黛云:
因为原来我就比较喜欢西方文学,而且我也喜欢中国的古诗词,两样我都很喜欢。
可是后来走到这个比较文学的路,那是一个机缘。
人的运气有时候会时来运转,或者说你接受一个东西,选择一个东西是有一定的机缘巧合的。
1978年,北京大学第一次接收欧美留学生,要给他们开现代文学课。
我被派去给他们讲现代文学。
当时为什么让我去给他们上课呢?
我想可能是有两点理由,一是因为中文系教师的英文都不是科班出身,我也一样讲不好。
但我爸爸是教英语的,我自己也喜欢英语,所以还能讲一点点,当然也是很差劲的,但可以简单地沟通一下。
与外国友人合影资料图
第二点就是我这个人胆子大,跟外国人接触就接触吧,好多人还是很怕,因为1978年嘛,那时候还是很玄乎的,你要是跟人家讲错了话,讲课出了问题怎么办?
大家都很担心。
可是我觉得反正总得有人去,我注意一点就行了,所以就去了.
去了之后,给这些外国学生讲课,都是欧洲、美国、加拿大来的,有20几个人。
总不能只讲“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吧,多少总得给人讲讲现代文学最基本的东西,所以我就讲了老舍、讲了曹禺、讲了巴金,这在当时都是不能讲的。
可是那些我都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