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群山连绵浑然天成.docx
《第三章群山连绵浑然天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三章群山连绵浑然天成.docx(2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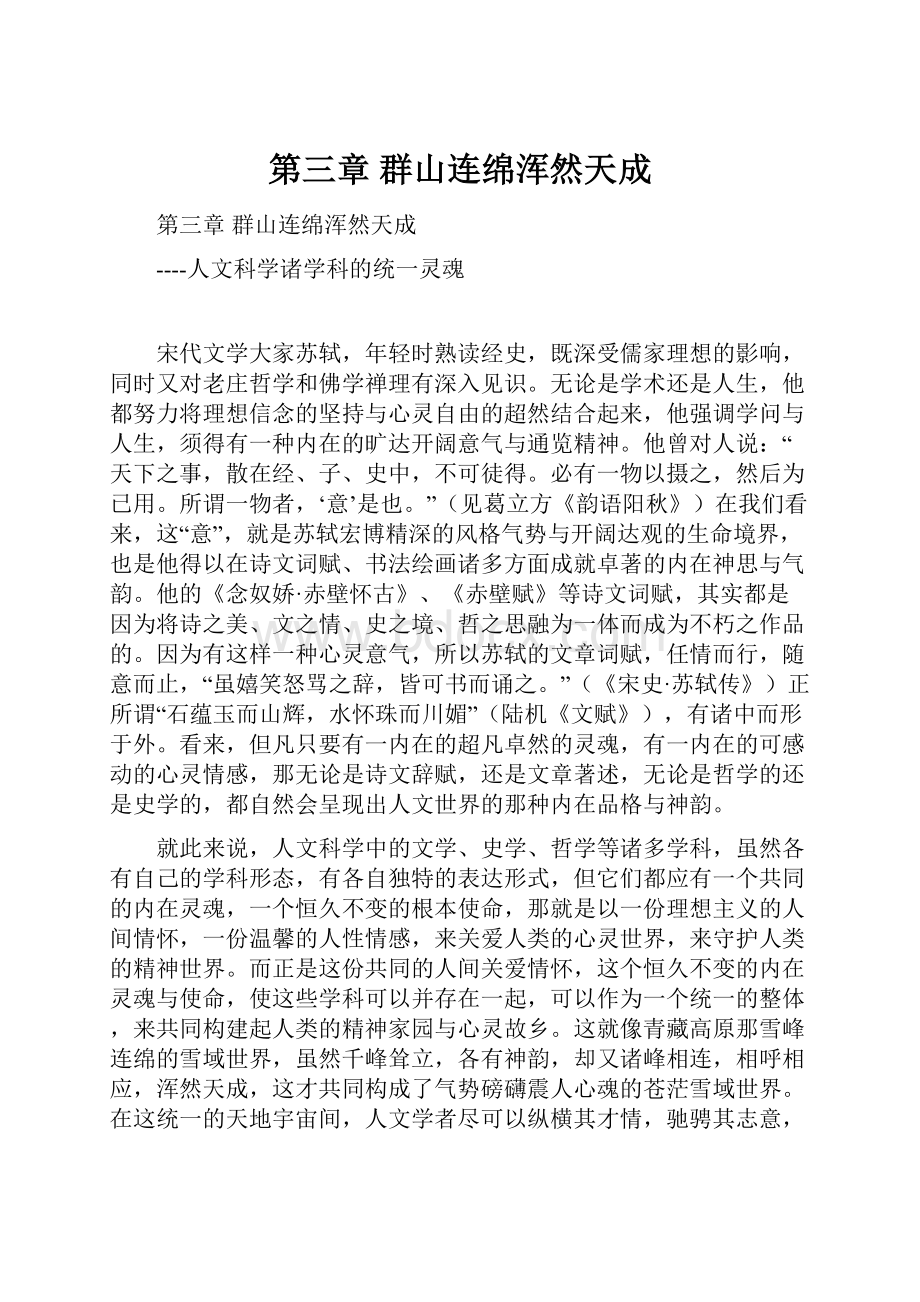
第三章群山连绵浑然天成
第三章群山连绵浑然天成
----人文科学诸学科的统一灵魂
宋代文学大家苏轼,年轻时熟读经史,既深受儒家理想的影响,同时又对老庄哲学和佛学禅理有深入见识。
无论是学术还是人生,他都努力将理想信念的坚持与心灵自由的超然结合起来,他强调学问与人生,须得有一种内在的旷达开阔意气与通览精神。
他曾对人说:
“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得。
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已用。
所谓一物者,‘意’是也。
”(见葛立方《韵语阳秋》)在我们看来,这“意”,就是苏轼宏博精深的风格气势与开阔达观的生命境界,也是他得以在诗文词赋、书法绘画诸多方面成就卓著的内在神思与气韵。
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等诗文词赋,其实都是因为将诗之美、文之情、史之境、哲之思融为一体而成为不朽之作品的。
因为有这样一种心灵意气,所以苏轼的文章词赋,任情而行,随意而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宋史·苏轼传》)正所谓“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陆机《文赋》),有诸中而形于外。
看来,但凡只要有一内在的超凡卓然的灵魂,有一内在的可感动的心灵情感,那无论是诗文辞赋,还是文章著述,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史学的,都自然会呈现出人文世界的那种内在品格与神韵。
就此来说,人文科学中的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虽然各有自己的学科形态,有各自独特的表达形式,但它们都应有一个共同的内在灵魂,一个恒久不变的根本使命,那就是以一份理想主义的人间情怀,一份温馨的人性情感,来关爱人类的心灵世界,来守护人类的精神世界。
而正是这份共同的人间关爱情怀,这个恒久不变的内在灵魂与使命,使这些学科可以并存在一起,可以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共同构建起人类的精神家园与心灵故乡。
这就像青藏高原那雪峰连绵的雪域世界,虽然千峰耸立,各有神韵,却又诸峰相连,相呼相应,浑然天成,这才共同构成了气势磅礴震人心魂的苍茫雪域世界。
在这统一的天地宇宙间,人文学者尽可以纵横其才情,驰骋其志意,正所谓“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
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载。
”(孟郊《赠郑夫子鲂》)
今天,我们能否重建起人文科学的这一整体精神与品格神韵,能否跨越了在文史哲诸学科间人为构筑的那些有形无形的界限,拆除掉造成各学科相互封闭隔绝的某些樊篱,恢复重建起这些学科间的有机内在联系,把那人文科学的内在统一灵魂与整体精神,重又归还给文学、史学、哲学,使文学、史学、哲学重又回归到它作为人类精神家园与心灵故乡守望者本真意义上来,以至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我们的大学还可以培养出如同中国诸子百家时代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文史哲兼通的思想家或学者来呢?
抑或,在这个一切都变化太快的职业化技术化时代,这只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理想,甚或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古老梦想了?
一、文之情、史之境、哲之思:
浑然而天成
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曾讲过一个奇异的故事,说远古之时,这世上有一生命叫“混沌”,庄子说它是中央之帝,它本是一完整的浑然一体的生命,但因无四肢七窍,被别人认为不合常理,北方之帝倏和南方之帝忽便将其凿以七窍。
可日凿一窍,七窍凿成之日,这“混沌”便死去了。
这则寓言,其实是想说,这世上有些东西,本只能是一种整体性的联系性的存在状态,只有在这种有内在联系的状态下,它才是它自己,它才有它的特质与本性。
如果你把它凿空了,成了残片,它就只剩下一个空彀,它的鲜活魂灵与本真生命就失落了。
人文科学的世界,大体也就是这样一个整体性的世界吧,你虽然可以把它分成文学、史学、哲学等几个部分,但它们只有在一种整体性的联系性的状态下存在,它才有生命力,它才是它那本真意义上的人的精神意义与情感世界,才能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与心灵故乡。
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诗人,作家和史学家,可能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文史哲贯通的心胸志意和才华,也才能有所成就吧。
中国儒家文化的奠基者孔子,是一位学识开阔、志意高远的人,他在诗歌、音乐、史学、哲学、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都有广博的志趣与见识。
他创办私人学府,聚众讲学时,“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本人既学识开阔,更有这么多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学生门徒,所以他才能整理集文、史、哲、艺为一体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在诗歌、文学、史学、哲学、艺术、伦理学诸方面多有创造,完成百科全书式的儒家思想文化体系的创建工作。
其实,人类的精神意义世界,人类的心灵情感世界,本是一个气象万千却又浑然一体的统一世界。
虽然,人类追寻守护这个精神与情感世界的努力,在形式上可以表现为有所不同的文学情感、诗性艺术、历史意识、哲学智慧、美学观念等,可以形成为品格与个性有所不同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等学科。
但尽管如此,一个以人类的精神情感世界为关注对象,以人文理想为生命根基的学者,会有一个宽广而丰富的心灵,有一个敏觉而多思的志趣,他往往不会认定自己是某个专业的固定职业者,因为他不会把自己的情感与理想,把自己的治学兴趣与研究工作限定于人为划定的某个学科领域内,他会凭他的情感与理性,凭他的对于人生的理解与期待,在他的心灵所感受视野所涉及的一切关乎到人类心灵情感的地方,做出自己的理性思考与情感体验。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司马迁也是一位光照后世的历史学家。
他的史学著作《史记》,之所以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因为这部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基本精神与品格的著作,乃是一个溶汇了诗之艺、文之情、史之境、哲之思诸多品格神韵为一体的作品。
而其艺之美,其情之切,其境之远,其思之深,堪称达到了将诗人之丰富细腻情感,史学家之通达开阔视野,哲学家之深邃理性智慧,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的境界。
如果我们了解司马迁的生平和志向,我们就会知道,司马迁本是一个有着诗人纤敏气质和文学家横阔才气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有着哲学家严密思维与冷静理智的古哲先贤。
正因为如此,《史记》才得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占有特殊的一席之地,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也有特别的影响。
他著书修史,其实不过是要借了史学这一文化形式,来建造他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人类之文明作总体理性思考与情感体验的一个精神世界,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
因而,他就必然不会将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表达方式局限于纯史学的范围内,只要需要和可能,文学的、诗歌的、艺术的、哲学的各种情感与智慧,都会进入他的视野中,进入他的作品中。
优美的文笔,宏阔的才情,通变的思想,生命与著述互为根基的生存方式,正是司马迁及其《史记》垂范后世名留千秋的魅力所在。
继司马迁之后另一个杰出的史学家班固,写下的《汉书》可以看成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与《史记》双峰并峙的另一作品。
尽管班固作为一个官方化的历史学家,在思想的自由与治史之理想方面,较之司马迁已经显示出某种境界上的消退,但总的来说,班固却依然是一个才华横溢视野广阔的学者,这是他的《汉书》得以流传后世并得到广泛赞誉的重要原因。
我们应该知道,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班固并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史学家而名留史册的,他是一个在文学方面有重要成就,一个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特殊地位的诗人。
班固创作的五言诗,被认为是中国五言诗歌发展史上最早的作品,他对五言诗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的重用。
特别值得注意的,班固还写下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首《咏史》诗,正是从班固开始,最能体现中国古代诗歌之民族精神与审美品格的“咏史诗”,就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一个伟大传统,一个文史哲浑然一体的光辉传统,煌煌然地发展起来了。
很难设想,如果司马迁、班固没有贯通文史的才华情志,没有诗人那样的丰富心灵,没有对人类历史与命运的深沉哲思,他们的史学作品会那样地感动人心,启示心灵,会那样地为后人所世代传诵。
事实上,从那以后的各时代的文史大家,对《史记》和《汉书》的文学成就,对司马迁和班固的诗人才情,都有着很高的评价。
后代的学者们,都努力去继承这一融通文史哲的学术传统与精神品格,因而往往在文史诸领域都多有建树。
唐宋文坛的各位代表人物,无论是“古文八大家”还是刘知几、王安石、朱熹等人,其实也都多是在经史子集等文史哲诸领域深有造诣和成就的学者。
比如说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吴充《欧阳公行状》)是一位在散文、诗歌、词曲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的大家,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开创了宋代诗坛的新局面,其词也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欧阳修其实也是一个专业历史学家,文学诗歌不过是他业余的爱好。
他主持编修的《新五代史》,不仅有很高的史学成就,而且他对于历史,对于历史学,也有许多重要思想,有着独到的治史方法与经验。
然而,正如这位自称为“醉翁”太守的欧阳修自己说的那样,“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之于酒也,”(欧阳修《醉翁亭记》),他所兼备之文章众体,诗文也罢,史学也罢,词曲也罢,都不过是用来表达他的思想、志向、情感的手段或形式而已,所以只要能表达这思想情感,用何种文体也就不必太在意了。
大可不必如今人那样,将自己限制在某个学科中,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归入某个所谓的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之中。
再来看宋代大学者苏轼,人们都将他看成是一个文学家,一个诗词大家,其实苏轼一生,写得最多的关于治国治世的论史文献和政论文赋,他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论史评古、思索生命与天地宇宙的文章诗词,我们可从《贾谊论》、《晃错论》诸文中,便可看出这位诗文大家对历史的独到见识。
而他的“人生到处知何处,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等诗文,却正是一个诗性的哲思世界。
与苏轼并称为“苏黄”的宋代另一大诗人黄庭坚,其诗词才气和艺术灵魂,常常来自《史记》、《汉书》所构造出的开阔深远的精神境界的感染与滋养,他甚至说:
“三日不读《汉书》,便觉俗气逼人,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
”(《汉书评林》)另一著名诗人秦观,与黄庭坚同属“苏门四学士”成员,他在诗词上的成就也很突出,他写下的“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诗句,是中国古代诗歌里最美丽的艺术境界。
而他与黄庭坚一样,在历史领域有深厚的基础,他们都曾熟读经史,或在朝中从事过文献编纂之类的工作。
深厚的儒学功底、历史眼光与经史才识,对他们在文学诗词上的成就,实有着重要的影响。
秦观《踏莎行》中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
桃源望断无寻处”的生命感叹,《望海潮》中的“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的岁月挽歌,其中正透着诗人深沉的历史情怀。
确实,人文世界本是一个有着内在统一精神气质的知识与思想领域,虽然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划分成了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或专业,但它们在本质上应该是血脉相联浑然一体的。
所谓天地有灵本心境,万物有情皆在心,这文史哲内在的灵魂与精神,本是必须用心灵去整体把握去体悟的。
一个优秀的史学家,不仅应有深厚的史学功底,还同时应该有丰富的文学情感、深沉的理性哲思,需得有细腻的诗人气质,超然的哲人心胸。
虽然他未必非要像班固那样有诗歌的才华而留下传世的诗文,未必像欧阳修那样成为一代文坛巨匠,他但却应该有诗人那样的情感,有哲人那样的智慧,只有这样,他在史学领域的成就可能才是与众不同闪耀光亮的。
因为事实上,当一个历史学家进入史学这一人文的世界时,他实际上是很难严格地将自己限定于纯史学的领域内而不涉及文学与哲学的。
同样的,一个文学家,一个哲学家,他所面对的人文情感与意义世界也是这样一个统一的世界。
你读屈原的长诗《天问》: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诗人在这三百多句的长诗中,一连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内容涉及自然、宇宙、历史、哲学、政治、伦理,展示了一个浪漫诗人博大而深广的心胸视野。
如果你再读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樽还酌江月!
”这诗文词赋,你说那是文学的还是史学的?
是哲学的还是艺术的?
其实它们都天然融合在了一起,它不过是用了诗性的语言与艺术的意象,通过对一段惊心动魄的生命往事与历史旧梦的回忆,而发出了对于天地宇宙,对于生命意义,对于历史兴亡成败的深沉哲思与追问。
这其中文史哲浑然一体的境界,这其中宇宙天地、岁月人生交织通揽的情怀,你是可以用自己的内在心灵结构去理解,去体会,去感悟的。
因此,一个文史哲领域的探索者,他的心灵世界本应该是将文之情、史之境、哲之思融为一体而内化于他心灵深处,他的情感是丰富而细腻的,理性而又多情的。
他理解这世界,观察这人生,思考这生命岁月,自然来自于他内心整体的心灵结构。
所以东坡才说,对于人生,对于这宇宙世界,对于这人类的生命与情感,其实都是经过了你内在的心灵世界,才变得可以把握,才变得有意义的,所谓“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苏轼:
《前赤壁赋》)人们都把老子、庄子看作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著名哲学家,智慧的追求者,但他们的哲学思想或哲学观念,却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文学艺术的世界,一个有诗歌之美的哲学世界。
不仅如此,老子对人生,对宇宙,对生命与天地的哲学思考,却又是与他曾是一个史官出身的人有着莫大的关系的。
对于历史内在精神的思考,对于过往时代兴亡成败的参透洞析,对老子的哲学思想的形成,自然是十分重要的。
可见,这种内在的统一灵魂与整体性,是所有优秀诗人、作家、史学家、哲学家思想与情感的核心,是他必须具体的内在素养,所谓“木体实而花萼振”(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如果文学、史学、哲学这些属于人文科学范畴的学科,相互之间封闭隔绝,孤立存在,人文科学的内在精神与灵魂就会逐渐消解失落。
而这精神与灵魂既失,那么它剩下来的那些孤立存在的文学、史学、哲学,就可能只是一些具体的文史哲知识与概念,就可能成为徒有躯壳的僵硬之物了。
既便你把文史哲简单地拼凑在一起,而如果它们之间没有形成内在的联系,那么人文科学内在的统一灵魂与精神气质也不可能生长起来。
正如再多的局部拼凑在一起也永远不会等同于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样,人文科学的内在统一灵魂与整体性精神,是不可能在孤立存在、相互分割的文史哲各学科内生长起来的,你必须贯通了文史哲,你只有从整体上才能把握到文史哲的这种内在灵魂与统一精神。
这正如禅宗对佛性之获得,不能一点一点分割开地渐进地去获得,而只能以一种“顿悟”的方式,从心灵上整体去把握佛性一样。
对于文史哲的这种内在统一灵魂与整体性精神,这种浑然天成的学术气质与思维品格,我们可以从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上来理解,也可以从哲学与史学、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上把握。
就中国古代文学与史学的内在整体性联系来说,人文科学的这种内在精神联系与统一品格的是最为明显的。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文史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与整体性,有着特殊的表达形式与精神意义。
一方面,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具有历史意识,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作为垂训后世资源的民族。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源远流长的专门化历史学、方志学和文献学的传统,来作为实现这种历史垂训功用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许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诗歌、文学、哲学和音乐也部分地是与这一历史情感历史意识主题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诗人,那些在文坛诗坛上长久留下身影的诗人、作家和文豪们,大多都有这样的历史情感与历史意识。
他们将自己的文学情感与艺术才华,同对人类,对生命,对国家、民族、同胞的关爱联系一起,融合在一起。
他们是一些能自由来往于文学与史学、诗歌与史学、艺术与史学之间,能自由地从文学、诗歌、艺术的领域进入史学天地或历史领域,并做出理性思考与情感体验的优秀诗人、作家和艺术家。
而那些优秀的历史学家们,也往往有着优秀的艺术才华与文学诗歌素质,不仅在文学史艺术史上留下他们的一席之地,而且还把他们的文学艺术才华,把他们细腻丰富的文学情感与诗人气质,天然地融合在他们的史学著作里,内在地结合于他们的历史思考中。
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文学诗歌的神思气韵与抒情领域,始终是内在地与中国深远的史学传统,与中华民族特有的那份历史情感与历史意识联系一起的。
一方面,对于在中华大地上生长的诗人与作家来说,他有着一个世界其它国家其它民族的诗人往往不具备的诗歌创作背景,那就是他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有着上下几千年不曾中断历史的国家里的作家诗人,他生来就是作为这个数千年文明史长河中的一员,而进行他们的艺术追求与情感体验的。
在这样历史文化背景下生长的作家诗人,他内在的心灵结构与情感天地,会被这数千年的历史所塑造。
而在他一生的艺术追求与文学创造过程中,他也不可能不面对这份巨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不可能不对这份依然对现实、对作家个体生命产生影响的历史有所思考,有所体验。
这悠悠往事,漫漫岁月,这数千年兴亡之迹,盛衰之运,积淀了多少情感,包容了多少内容,它可以向诗人向作家提供那么多的感受生命、体悟人生并用以进行文学诗歌创作的素材与背景,它足以激起任何一个有才华有细腻情感的作家与诗人的创作激情与诗文灵感。
这使得文学与诗歌,在中华文明这个独特的精神情感与意义世界里,天然地与中华厚重的历史往事,形成了一种难以分解的内在联系。
唐代刘禹锡的一首《石头城》咏史诗: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诗中似乎并没有说太多的东西,但无尽的岁月沧桑悠悠情怀,却已尽在其中,正如后人所评:
“只写山水明月,而六代豪华俱归乌有,盛衰之慨令人于言外思之”(沈德潜语)。
就这样,多少个世纪,一代又一代的文史学者,作家诗人,往往把历史当作了呈示他们的文学情感,展示他们的文学才华,满足他们的文学创作愿望的广泛空间与坚实平台。
而正是因为他们深沉细腻的情感与动人心弦的艺术,使得这些直接关注社会、关注历史、关注人生的咏史诗歌,这些与国家民族兴衰成败相联系的思古抚今、感时伤怀的咏史作品,不再是空泛的政治议论和说教,而是感动人心、有着审美价值的文史作品。
惟其如此,方使得中国古代的文学与诗歌,具有了另外一种特殊的人文意义和社会意义。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就难以真正把握住中国文学艺术的独特意义和精神价值,难以真正体悟到中国古代文学诗歌中那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诗歌的美学神韵,也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华民族的独特性格与生命追求。
就一般的情形来说,文学与史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是相互有别的,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逐渐地分成了经史子集等不同的学术与思想领域。
史马迁之《史记》,自不同于曹雪芹的《红楼梦》,刘勰的《文心雕龙》亦有别于刘知几的《史通》。
但我们却又知道,在中国学术史上,人们常常将《史记》与《红楼梦》对举,将《文心雕龙》与《史通》对举。
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它们都是中国古代文史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而且在于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内在灵魂,一种共同的精神与情感。
《史记》与《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文史领域两座并峙的山峰,就在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两部著作都是它的作者用自己的心灵,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生命的血与泪写成的。
这两部书的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生命,有一个情感丰富才志高远的心灵。
其实,千百年来,中国文学和史学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是从来不把自己从对方那里严格地隔离开来,而提倡“文史不分家”,这可以说是中国学术传统的一大特点。
如果说刘知几的《史通》相对于刘勰的《文史雕龙》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刘知几因过于强调史学与文学的区别而不能像刘勰那样将文史贯通起来,因而刘知几的《史通》就在思想高度与情感丰富的境界上,要比刘勰的《文心雕龙》低了一层。
而刘勰著《文心雕龙》,对“文”的理解与见识,开阔而高远,他把经史辞章等各类文体都放置到广义的“文章”领域当中来考察,统一来把握各种古代经典文献的内在统一精神与共同品格,他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
”他认为所有文章,都应该有深挚情感,有音色文采,而他对“史传”、“诸子”的论述,对后世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也都有重要的影响。
那么,如何来理解古代中国文学与史学间的这一既分又合、既合又分的看似矛盾的现象呢?
其实,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或者说,中国文化的一大魅力,就是差异中的和谐,对立面的统一,就是可以把看似有差异的,不同的,甚至矛盾的两个事物统一在一起,联系在一起,并存在一起。
对于中国传统精神与思维方式来说,合,不是绝对同一,你我不分;分,也不是互不相干,两不相容。
分与合都是相对与辨证的,共存的状况,是在追求差异中的统一,多样性中的和谐,差异中的并存,差异中的互补性共存。
从这样的思维角度上来理解文史哲不分,这三者是一种差异中的统一,统一中的个性差异共存。
我们说文史不分,追求两者的统一,不是说两者就是一会事,混淆在一起,而是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统一,一种灵魂上的统一境界,也即是神合而不是形同。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文史不分家”的理想,可以从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两个方面来理解。
现在人们讲到“文史不分”,往往只是孤立地从文章形式或表达语言这样的层面上理解,认为史学应该有文学一样的文采,有文学那样动人的语言和情节,这样历史学才可以被普通的大众所接受。
这种“文史不分”其实只是技术层面上的不分,是形式与方法上的不分。
这种“文史不分”当然也是有意义的。
从史学的角度来说,史学在不影响它的记事功能、叙事功能的前提下,应该有这样的魅力。
像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称誉为像屈原的《离骚》一样,因为它记事记人、叙物叙事不仅准确,而且语言本身确也写得那样优美,动人,是“无韵之离骚”,因此《史记》也就成了“史家之绝唱”,流传千古。
司马迁成为中国“史学之父”,与《史记》在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是特殊的一席之地,是有很大关系的。
这是就史学应该有文学的文采而言来谈“文史不分”的。
如果只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学对于史学的意义,那它更多看重的主要是文学中的辞章辞藻。
但在这个角度上所说到的“文学”,只是强调了文学中的“文”(文者,纹也,美丽的纹路,即语言之文采),还不是文学中的“学”,即文学中的内在精神、灵魂、理想、意义与价值。
要使这文学中的“学”成为可能,就必须不仅仅停留在“文采”的境界上,而是有“文采”但更超越了“文采”,而进入“史”的领域,将“文”与“史”在理想、意义、价值、道、精神这样的层面上结合起来。
事实上,中国传统学术中所强调的“文史不分家”,自有着另一番深刻的历史情感历史意义的哲思与追求在里面。
这种哲思与追求,是把历史意识、历史情感、历史思维看成是中国学术的特殊内核,不仅是史学要有文学的文采,有文学的情感,同时,文学作品也应该有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
文学情感应该有历史理性的思考与意义的追求的提升,才能成为伟大的文学作品。
从文学角度上来说,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诗言志”品格,便是主张文学作品须以历史之往事为言志的对象与抒发情感的基础,以历史之智慧、历史之情感、历史之超越,来作为这文学情感的文化底蕴,以深沉的历史意识与历史哲思,来言自己志,来抒自己的情,来感受生命的力量与意义。
因而在中国历史上,从事文学的人,更强调如要在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甚至文学阅读与文学鉴赏中有所成就,有所收获,不仅要“文史不分”,更有必要“出文入史”和“由史入文”,即走出纯文学的天地,带着文学的情感进入史学的理性世界中去,以史学之理性、哲学之运思,来提升文学之情感,以史学的开阔眼光和哲学的理性智慧,来审视文学之个人生命,将个人之命运、情感种种上升到人类历史高度上来,上升到宇宙与道的哲思境界上来,那文学中的情感,即是个体人性的,又是宇宙普遍的,即是当下眼前的,又是永恒长存的,如此,文学之境界才高,品格才超然出众,那才可成为文学之“大家”、“上品”。
我们读陶渊明的《饮酒诗》,那“此中有真意,欲辨已记言”的无语境界,我们读苏东坡的词赋,那“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生命感慨,都是将个人之生命境遇,个人之文学情感,提升到一个更高远开阔的历史理性与哲学运思高度上来的努力。
应该说明的是,在中国传统学术的世界里,“出文入史”或“由史入文”,不是不要文学,不是离开文学,“由史入文”也不是以史学来代替了文学,或放弃史学进入文学。
不是漠视史学与文学的区别而将两者混为一谈,而是说,应该在精神境界上将文学、史学、哲学内在地联系起来,沟通起来,把那文学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