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利奥科萨塔尔 正午的岛屿.docx
《胡利奥科萨塔尔 正午的岛屿.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胡利奥科萨塔尔 正午的岛屿.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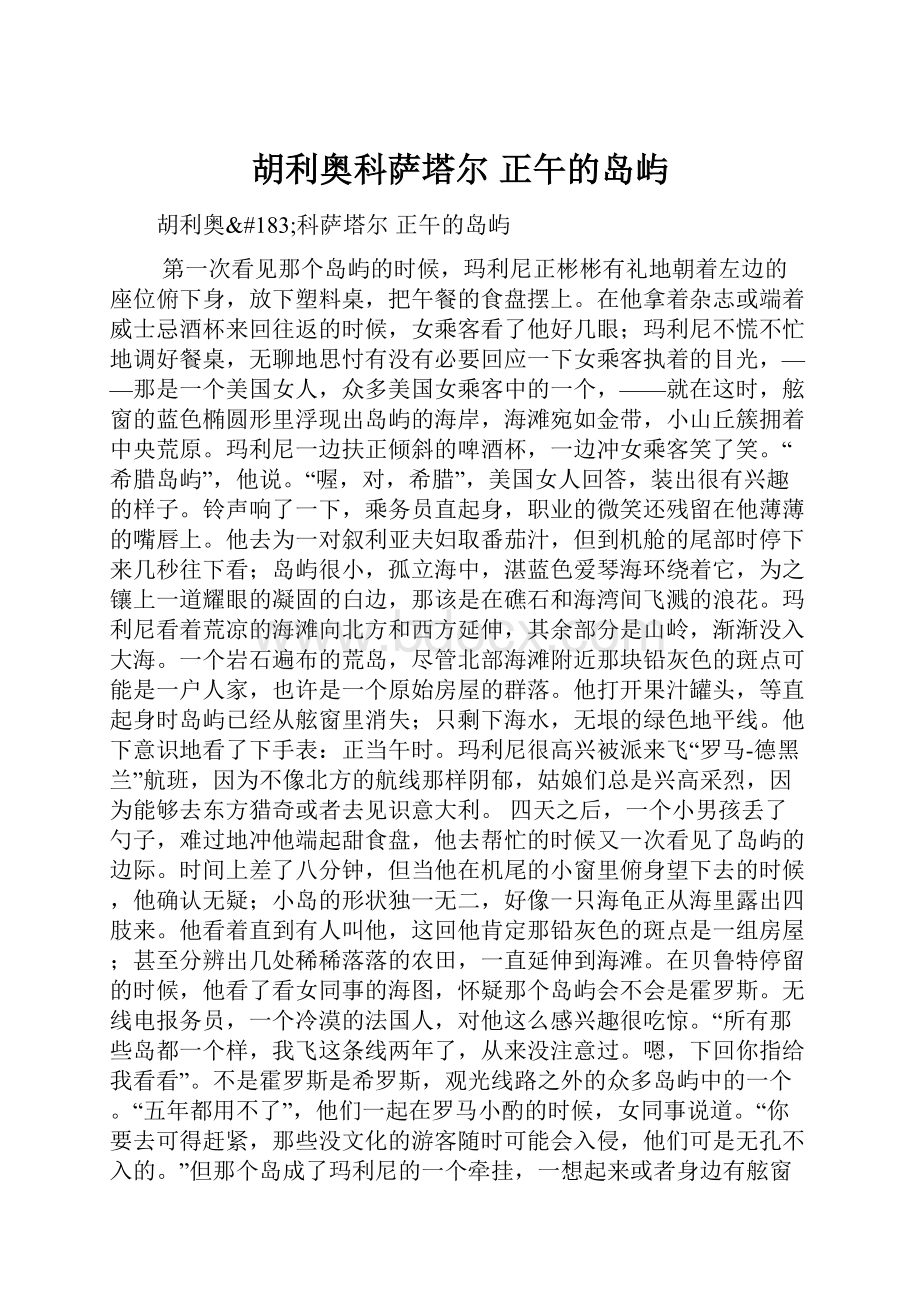
胡利奥科萨塔尔正午的岛屿
胡利奥·科萨塔尔正午的岛屿
第一次看见那个岛屿的时候,玛利尼正彬彬有礼地朝着左边的座位俯下身,放下塑料桌,把午餐的食盘摆上。
在他拿着杂志或端着威士忌酒杯来回往返的时候,女乘客看了他好几眼;玛利尼不慌不忙地调好餐桌,无聊地思忖有没有必要回应一下女乘客执着的目光,——那是一个美国女人,众多美国女乘客中的一个,——就在这时,舷窗的蓝色椭圆形里浮现出岛屿的海岸,海滩宛如金带,小山丘簇拥着中央荒原。
玛利尼一边扶正倾斜的啤酒杯,一边冲女乘客笑了笑。
“希腊岛屿”,他说。
“喔,对,希腊”,美国女人回答,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
铃声响了一下,乘务员直起身,职业的微笑还残留在他薄薄的嘴唇上。
他去为一对叙利亚夫妇取番茄汁,但到机舱的尾部时停下来几秒往下看;岛屿很小,孤立海中,湛蓝色爱琴海环绕着它,为之镶上一道耀眼的凝固的白边,那该是在礁石和海湾间飞溅的浪花。
玛利尼看着荒凉的海滩向北方和西方延伸,其余部分是山岭,渐渐没入大海。
一个岩石遍布的荒岛,尽管北部海滩附近那块铅灰色的斑点可能是一户人家,也许是一个原始房屋的群落。
他打开果汁罐头,等直起身时岛屿已经从舷窗里消失;只剩下海水,无垠的绿色地平线。
他下意识地看了下手表:
正当午时。
玛利尼很高兴被派来飞“罗马-德黑兰”航班,因为不像北方的航线那样阴郁,姑娘们总是兴高采烈,因为能够去东方猎奇或者去见识意大利。
四天之后,一个小男孩丢了勺子,难过地冲他端起甜食盘,他去帮忙的时候又一次看见了岛屿的边际。
时间上差了八分钟,但当他在机尾的小窗里俯身望下去的时候,他确认无疑;小岛的形状独一无二,好像一只海龟正从海里露出四肢来。
他看着直到有人叫他,这回他肯定那铅灰色的斑点是一组房屋;甚至分辨出几处稀稀落落的农田,一直延伸到海滩。
在贝鲁特停留的时候,他看了看女同事的海图,怀疑那个岛屿会不会是霍罗斯。
无线电报务员,一个冷漠的法国人,对他这么感兴趣很吃惊。
“所有那些岛都一个样,我飞这条线两年了,从来没注意过。
嗯,下回你指给我看看”。
不是霍罗斯是希罗斯,观光线路之外的众多岛屿中的一个。
“五年都用不了”,他们一起在罗马小酌的时候,女同事说道。
“你要去可得赶紧,那些没文化的游客随时可能会入侵,他们可是无孔不入的。
”但那个岛成了玛利尼的一个牵挂,一想起来或者身边有舷窗的时候,他就看着它,最后几乎总是耸耸肩作罢。
这些毫无意义,一周三次在正午时分从希罗斯的上空飞过,跟一周三次梦见在正午时分从希罗斯的上空飞过,是一样的虚幻。
在这种无用的重复观看中一切都被扭曲;也许,除了重复的欲望,正午前看表的习惯,耀眼的白边衬着近乎黑色的蓝所带来的惊艳,还有那些房屋,在那里的渔夫们难得抬起头来仰望另一样从他们头上飞过的虚幻。
八九个星期之后,上面要调他去好处多多的纽约航班,玛利尼心想正好借这个机会了断这个无害而烦人的怪癖。
他兜里揣着一本关于希罗斯的书,作者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地理学家,名字像地中海中部的人,书里面有很多一般旅游指南没有的细节。
他回绝了,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避开一位上司和两位秘书的惊愕,他赶往公司的餐厅,卡尔拉正在那里等他。
他并没在意卡尔拉的不解和失望;希罗斯的南部海岸不适宜居住,但往西存留着一些吕底亚,或者克里特迈锡尼殖民的遗迹,古德曼教授发现了两块刻有象形文字的石头,渔民们把它们用作小码头上的桩子。
卡尔拉说头疼,很快就走了;章鱼是岛上为数不多的居民们的主要资源,每五天来一艘船拉走水产,留下一些食物和纺织品。
旅行社的人告诉他得从里诺斯单租一艘船,或者搭乘运章鱼的小艇,但后者只有玛利尼到了里诺斯才能知道是否可行,因为旅行社在那里也没有联系人。
不管怎样去岛上小住不过是六月度假期时的一个计划,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还得接替怀特飞突尼斯航班,然后又发生了一场罢工,卡尔拉回到巴勒莫她姐姐们的家里。
玛利尼住到那沃纳广场附近的一家酒店,广场那边有些旧书店;他有一搭无一搭地寻找关于希腊的书来消磨时间,有时候翻翻一本日常对话手册。
Kalimera这个词让他觉得很好笑,他在一家酒吧里和一个红发女郎演练了一回,和她睡觉,知道她祖父在奥多斯,嗓子疼却找不出原因。
在罗马开始下雨,在贝鲁特总有塔尼娅在等着他,有其它的故事,不是亲戚就是疼痛;一天又飞德黑兰,正午的岛屿。
玛利尼脸贴在舷窗上很久,以至于新来的空姐认定他不是个好同事,还特意记下他送了多少餐盘。
这天晚上玛利尼请那位空姐在菲鲁茨吃饭,轻而易举地使她原谅了自己上午的走神。
露西亚建议他理一个美式发型;他向她说起希罗斯,不过之后他意识到她对希尔顿的伏特加酸橙酒更有兴趣。
时间就在这些事情上消磨,无穷无尽的餐盘,每一盘附送一个乘客有权得到的微笑。
返航途中飞机在上午八点飞过希罗斯,阳光反射在左舷的窗子里,几乎看不清那金色的海龟;玛利尼更期待来时的航班,他知道那时候自己可以靠着舷窗呆上一阵,露西亚(后来是菲利莎)会带着些许嘲弄接下他的工作。
一次他拍了一张希罗斯的照片,洗出来却很模糊;对这个岛屿他已经略知一二,在那些书里零星提及的地方都标了出来。
菲利莎告诉他飞行员们都管他叫“岛疯子”,他也不在乎。
卡尔拉刚来信说她已经决定不要孩子,玛利尼给她寄了两个月的工资,心想剩下的可能不够度假了。
卡尔拉收下钱,通过一位女友告诉他,自己可能会和特雷维索的那位牙医结婚。
比起每个周一、周四、周六(以及周日,每月两次)的正午时光来,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发现菲利莎是唯一能够多少理解他的人;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他一挨近机尾的舷窗,她就承担起午间的工作。
小岛只在几分钟内是可见的,但空气永远是那么澄净,大海以一种近乎残忍将岛屿刻画得分毫毕现,连最微小的细节都与上一次旅行中的记忆全然吻合:
北方海岬的绿色斑点,浅灰色的房屋,沙滩上晒着的渔网。
看不到渔网的时候玛利尼会有一种匮乏的感觉,甚至是一种冒犯。
他曾想摄下经过海岛的过程,可以在酒店里重温岛屿的形象,但他宁愿省下摄影机的钱,毕竟不到一个月就到假期了。
他没怎么去刻意地计算时间;今天跟塔尼娅在贝鲁特,明天跟菲利莎在德黑兰,他弟弟差不多总在罗马,这一切都有些模糊,轻松又亲切,仿佛是某种代用品,借以打发飞行前后的时间,在飞行中也是一样的模糊、轻松和愚蠢,直到在机尾的舷窗边俯身下望的时刻,感觉玻璃的冰冷好像水族馆的边壁,其中有金色的海龟缓缓移动在蓝色的汪洋。
那天渔网正好铺在沙滩上,玛利尼敢打赌,左方那一个黑点,就在海岸边,肯定是一个渔夫正仰头看着飞机。
“Kalimera”,他荒唐地在心里说道。
再等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马里奥·梅洛里斯会借钱给他凑齐旅行费用,用不了三天他就能到希罗斯。
他嘴唇贴在玻璃上,微笑着想象自己爬到绿色的斑点那里,赤裸着身子从北边的小港湾下海,和人们一起打捞章鱼,靠手势和微笑交流。
一旦下了决心就没什么困难,一班夜里的火车,头一班船,再换一艘又脏又破的船,在里诺斯停靠,跟小艇的船长无休无止地讨价还价,甲板上过夜,紧挨着星星,茴芹和羊肉的味道,黎明时已置身于岛屿间。
伴着第一束曙光下了船,船长把他介绍给一位老人,应该是岛上的族长。
克莱伊罗斯握了他的左手,看着他的眼睛,语调缓慢。
来了两个小伙子,玛利尼看出来是克莱伊罗斯的儿子们。
小艇的船长耗尽了他的英语词汇:
二十个居民,章鱼,打渔,五间房,意大利游客付住宿钱克莱伊罗斯。
克莱伊罗斯谈价钱的时候,小伙子们笑了;玛利尼也笑了,他已经成了年轻人的朋友,看着在海面升起来,大海比从空中看起来更明亮,一间简陋但干净的房间,一个水罐,闻起来像鼠尾草和鞣过的皮革。
他们去装船,留下他一个人,他几下脱掉旅行的衣服,穿上泳裤和凉鞋,到岛上游逛。
四下还看不到人影,太阳慢慢焕发出力量,从荆棘丛里蒸腾起一种微妙的味道,有一点酸涩,和海风中的碘混合在一起。
差不多十点钟的时候他来到北边的海岬,认出了最大的那个港湾。
虽然更想到沙滩上沐浴,他还是愿意一个人呆在这里;岛屿涌入他的心,他很享受这种亲切感,以至于不知道该怎样思考或选择。
太阳灼烧着他的皮肤,海风吹拂,他赤裸着身体从一块石头上跳进大海。
水是凉的,感觉很好;任凭自己被暗流挟裹直到某个洞穴的入口,这才转身游回大海,仰面漂浮在水上,以一个和解的姿态接受了一切,也决定了未来。
他确信无疑自己不会离开这岛屿了,会以某种方式永远留在岛上。
他能想象他的弟弟,菲利莎,当他们知道他要留在一块孤零零的大石头上当渔民时的表情。
他收回思绪向岸边游去,那一切已是过眼云烟。
阳光立刻晒干了他身上的水,他朝着下面的房子走去,那里有两个女人惊奇地望着他,随即跑回屋里藏了起来。
他朝空无一人的地方招招手,走向下方的渔网。
克莱伊罗斯的一个儿子在海滩等他,玛利尼指指海,发出邀请。
小伙子犹豫了一下,指指身上的布裤子和红衬衫。
然后便跑进一间房子,出来的时候几乎是光着身子;两人一起跳进已经变得温暖的海水,海面在十一点的阳光下闪闪耀眼。
在沙子里擦干身子的时候,尤纳斯开始列举各种东西的名字。
“Kalimera”,玛利尼说,小伙子笑得直不起腰。
随后玛利尼开始练习新学的词汇,也教尤纳斯意大利语。
汽艇越来越小,几乎在天尽头;玛利尼觉得现在是真的和克莱伊罗斯一家独自在岛上了。
他准备过上几天,支付房钱,也学习打渔;等到某个晚上,等彼此已经熟悉,他会对他们说想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干活。
他站起身,跟尤纳斯握了握手,然后缓步向山丘走去。
坡很陡,他边攀登边享受着每一个高度,频频回头去看海滩上的渔网,女人们的侧影,她们正兴奋地和尤纳斯,和克拉伊罗斯交谈,用余光望着他,笑着。
当他来到那块绿色的斑点,便进入了另一个天地,在这里百里香和鼠尾草的气味和太阳的光焰、洋海的微风浑然一体。
玛利尼看了一眼手表,作了一个不耐烦的表情,把它从手腕上扯下来塞进泳裤的兜里。
抛却旧我并不容易,但在这里,在高处,烈日长天,他感觉这转变是可能的。
他在希罗斯,就在自己曾无数次怀疑能否抵达的地方。
他仰面躺到滚烫的石头上,忍耐着石头的尖棱和火热的背面,直直望向天空;远远传来引擎的轰鸣。
他闭着眼睛对自己说不要再看飞机,不让自己最糟的部分来污染,它就会又一次飞过岛屿。
然而在眼睑的阴影下他不禁去想象菲利莎和餐盘,她就在这时候分发餐盘,还有他的继任者,或许是乔尔乔或者别的线上的新人,也一样微笑着端上红酒或者咖啡。
他无力与这许多的过去做斗争,睁开眼,直起身,就在这时候他看见飞机的右翼,几乎就在他的头顶,无法解释地倾斜着,涡轮机的奇异地轰鸣,飞机几乎垂直坠入大海。
他飞快地跑下山去,在乱石间磕磕碰碰,一只胳膊也被荆棘划破。
岛屿遮住了坠机的地点,但他在到海滩之前拐了个弯,沿着预想的近路翻过第一道山梁,到达最小的那处海滩。
机尾在百余米外渐渐下沉,没发出一丝声响。
玛利尼紧跑几步,一头扎进水中,还抱着希望飞机能够再浮起来;然而只剩下波浪柔和的线条,一只纸盒荒诞地在坠机处附近沉浮,几乎在最后,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游泳的时候,一只手露出水面,只一瞬间,玛利尼改变方向潜进水里,直到抓到那个男人的头发,他正挣扎着想抓住他,声音沙哑地大口吸气,玛利尼让他能够呼吸,但没让他过于贴近。
他渐渐把那人拖到岸边,抱起这具身穿白衣的躯体,平放在沙滩上,看着他脸上满是泡沫,死亡已经降临,鲜血正从咽喉处一处巨大的伤口汩汩涌出。
人工呼吸已经无济于事,伤口每一次痉挛都裂开更大些,仿佛一张令人厌恶的嘴在呼唤玛利尼,把他从岛上短暂时光里微小的幸福中拽出来,在泡沫中向他呼喊着他已经无法听见的话语。
克拉伊罗斯的儿子们飞也似跑来,后面跟着那些女人。
当克拉伊罗斯赶到的时候,小伙子们正围在沙滩上躺着的那具躯体身边,不明白他怎么会有力气游到岸边又流着血爬到这里。
“让他闭上眼睛吧”。
一个女人哭着请求。
克拉伊罗斯看了看海,寻找其他的幸存者。
然而,跟往常一样,他们孤独地呆在岛上,那睁着眼睛的尸体是他们与大海之间唯一的新鲜事物。
评论:
《正午的岛屿》——“我”与“我”的故事这是一个故事,来自科塔萨尔。
很难描述它是一条线还是一个环。
它更像莫比乌斯纸带,你一字一行地走下去,最后发现自己来到了世界的另一面,甚至抖抖索索地进入了另一个空间。
正常的界限被打破,自己惯性的思维成为不能被信任的东西。
科塔萨尔开始讲述的时候,一切都平常。
“我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德黑兰飞往巴黎,中午飞越爱琴海。
”他坐在椅子里,对前来采访的伊夫林·皮孔·加菲尔德女士如是说。
这便是《正午的岛屿》产生的全部背景。
而他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
“第一次看见那个岛屿的时候,玛利尼正彬彬有礼地朝着左边的座位俯下身,放下塑料桌,把午餐的食盘摆上。
”尽管有着纸页内外的本质区别,这两个场景却如此普通,忠于现实,任何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它们串联起来。
接下来是井井有条的动作,薄嘴唇上的职业微笑。
随即主角从舷窗外的蓝色椭圆形中浮现。
那状如金龟的美丽小岛。
我们无法判断接下来的一切是否已经是幻梦。
对于岛屿远景的诗意描绘和舒缓的叙事笔调给了整篇小说一种安静的循序渐进之感。
在被平实地叙出的若干交谈和生活场景之中,玛利尼对那岛屿的迷恋本身就脱离他生活的圆圈,脱离旁人所知。
希罗斯,这座岛屿的影像和玛利尼对它若干细碎的了解处在餐盘和职业微笑的夹缝中,比起希尔顿的伏特加酸橙子酒要来得更加细微和虚无缥缈。
“一周三次在正午时分从希罗斯上空飞过,跟一周三次梦见在正午时分从希罗斯上空飞过,是一样的虚幻。
”在这里我们也许已经可以嗅出一丝端倪,关于印象和感觉的真实与事实的真实的差别。
与希罗斯相关的想象构成了他生活这件外衣的内衬,走在人群中谁也不知道它的材质与颜色,只有他自己能感受到希罗斯的阳光、殖民遗迹和水产在紧贴着他的皮肤时所产生的那种神秘的向往和满足感,为此他甚至不得不倾斜了生活的重心,职业的前途或者女友与别人的婚姻都不能将他拉回。
然后,终于有一天,他来到了岛上。
在文字的游戏之中我们读者只能知道玛利尼终于到了岛上,这是一个结果。
然而它实现的过程却有着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可能——一次悠闲的度假或是一次惨烈的坠机。
矫捷地跃入海水中以和解的姿态浮在水面上的玛利尼,咽喉开裂从高空坠落的玛利尼,哪个才是真实?
在那毫无夸张和神奇色彩的笔调中,幻梦究竟从何时开始?
在这种被刻意模糊的时间中,生活的表层与里层一团混乱,难解难分。
当死者睁着眼睛孤身躺在海滩上,成为渔民与大海之间唯一的新鲜事物时,前文那连篇的温馨朦胧的迷雾消散,完成了幻想与现实的合一——如一张薄纸,却锋利无比。
然而我们却早已被那种飘忽不定的魅力吸引,认清什么是真实反而成为次要的过程。
我们乐于同主人公一同体会那虚幻与现实的分分合合。
这大概也就是让科塔萨尔所着迷的事物中的神秘联系。
或者,它讲述的其实也只是玛利尼与另一个自我邂逅的过程。
那个想象中的自我也成为他最终的救赎者,将濒临死亡的自己拖上朝思暮想的海岛。
岛上的玛利尼和注视海岛的玛利尼,也许这样为故事的两个位面作出区分更为温和。
甚至可以说,那所谓的结局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故事需要一个结局。
两个玛利尼可以无止境地共存下去,只不过在文本中,前者处在思想的明处而后者处在现实的暗处;尽管前者可以作为过程,甚至再构建一个人生,可是只有后者有成为结果的资格。
读到这里,让人不由得有一种宿命的怅然若失——虽然这外延已经离文本本身有些远了。
人人都可以如玛利尼一般生活,在被日常割裂开的众多琐碎的时间段中缔造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世界。
实现这一点的方式多种多样,归根到底我们所需要的不过是一种对思想的形式上的维系。
文字也好,图画也好,特定的事物也好。
玛利尼所看见的正午的小岛恰好是那么美丽,摄人心魂,再加上海天之间的遥远距离,它终于成为了一场幻梦的发生地。
我们也能顺着自己的生活中、那些在过去已经中断的种种可能——也许小到回家路上对一个岔口的选择——在心中编写出一篇篇故事来,仿佛多个自己同时存在于世上,也许也能收获玛利尼那样的轻松与惬意。
尽管那种轻松与惬意都仅存在于自己的内心之中。
刚刚也提到在若干的“我”中成为“结果”的可能性问题。
与博尔赫斯的网状时间不同,在这个既定的世界范围里,无论衍伸出多少种人生,死亡都会将这些自我收束为唯一的可能。
这也许是现实压倒性的优势。
一件外衣的内衬再精彩,路人所能看到的仍然是外在的条纹与颜色。
如同玛利尼。
当他躺在海滩上奄奄一息,克拉罗伊斯一家与其他的岛民也不会知道他就是那个笨拙地学习希腊词汇的旅游者玛利尼吧。
而其他人呢,就算是了解了岛屿上的另一个玛利尼,他们最后毫不怀疑地记得的也只不过是那个突然出现的死者和他最后时刻的悲惨,而会极少犹豫地忽略那幻梦的一层。
现实中,人很难成为自己的仲裁,仲裁者永远在自我之外。
不过,这些随想也已经是处在这个故事本身之外的东西了。
就阅读体验本身来说,魅力仍然在于现实叙事的悄然转变和通向他陌生想象的延展。
科塔萨尔的特殊能力在于能够引导读者在虚境与实境中自由穿行。
“也许,真实的只有那重复的欲望……”人心灵中不可竭止的、对另一个我的向往与渴望——说不定这才是科塔萨尔若干世界中的核心,也是它们能够在他笔下最终合一的关键。
Fin
2012-01-07“正午的岛屿”:
平庸生活中的虚幻追求
——科塔萨尔《正午的岛屿》赏析
“天涯论坛·闲闲书话”的《闲谈》第一期讨论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正午的岛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干热心的网友也讨论得颇热烈,斑竹石中火兄希望我也谈些看法,我当然乐于参与;只不过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在我看来,须得认真品读,再三捉摸,方敢发言,刚巧手头上有些事,这事就给耽搁下来了。
现今虽然已经时过境迁,讨论似乎也已告结束,但是,我对这篇小说的兴趣却正依然浓烈,感触良多;于是,干脆写成专文,作为一种迟到的表态,望石中火兄谅解。
一、
品读再三,觉得这个小说确实特有意味。
浏览了一下参与讨论的网友的发言,觉得大多数都比较浮泛,未能真正进入小说的灵魂;甚至有网友认为这小说是难以解读的,见仁见智就行了,不必有确切的结论。
这种观点当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虽说“一百个读者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可别忘了,这一百个哈姆雷特毕竟还得是哈姆雷特,而不可能会是奥菲利亚。
而在我看来,这个小说的思想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虽说它的隐喻象征意味或许可能人见人殊,但基本思想脉络却是清晰可见、勿庸置疑的。
小说其实是以精确的现实主义手法来结构他的现代主义小说的,这让人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变形记》除了主人翁变形为甲虫具有现代小说先锋意味外,其他所有的描写都可以说是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
这类小说手法完全不同于魔幻现实主义的极度夸张变形手段,相反它几乎是极其写实的,而且写实过程极其克制、极其冷静、极其精确。
其中的克制、冷静展现几乎完全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冷血式叙事,不露喜怒爱憎情感,一种纯客观的新闻报道立场;而其中的精确有时甚至发展到琐碎、无聊的程度,很有些自然主义的意味,几乎很容易被粗心的读者所厌烦以致忽略。
但读者千万别真的认为作者的叙事有些心不在焉,如散兵游勇;其实,这就是科塔萨尔的高明处:
在看似纯客观、波澜不惊的自然主义细节描写中,作者的匠心独运被隐藏得悄无声息,细针密线一直在严密地织就一张小说思想艺术之锦。
这张锦表面看上去朴实无华,清明恬淡,但其实内里波涛汹涌,风谲云诡;其逻辑思想经纬线编织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
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说是精心设计的,不象很多魔幻小说家在耍弄夸张变形手段时为标新立异或耸人听闻都难免玩弄一些虚幻的噱头,半买半送地搭配一些水货;但是,在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正午的岛屿》里,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都可以视为其小说思想逻辑深入发展的严密组成部分,看似琐细庸常的生活细节其实没有一处闲笔,都可以说是作者刻意择取、精心安排的,称得上是藏龙卧虎,大道无形,大师名号,当之无愧!
二、
小说的前半部分的许多描写都是主人公玛利尼在飞机上作为乘务员的庸常生活。
这种生活平静、安宁,甚至让人感到舒心惬意,几乎没有任何烦心事情。
玛利尼一直在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总是“不慌不忙地调好餐桌”,“往返走动”地为顾客送“杂志”或“威士忌酒”,就在这“无穷无尽”的餐盘运送过程中,也从不忘“每一盘附送一个乘客有权得到的微笑”;并随时注意顾客的情绪变化,并同时考虑“有没有必要回应一下女乘客执着的目光”……可以说职业范儿完美无瑕。
另一方面,与同事的相处也应该算得上是融洽和谐的。
尽管有一位新来的空姐因为他“脸贴在舷窗上”看“正午的岛屿”,一度“认定他不是个好同事”,但很快在他的解释下就“轻而易举地”“原谅了”他“上午的走神”;工作中有较密切关系的同事有露西亚与菲利莎,相处都算不错,而后者甚至与他还很“默契”。
生活中唯一的遗憾或许就是与女友卡尔拉的关系出了某种问题,以致卡尔拉对他有一种“不解”和“失望”,甚至“头疼”,并且决定不想要孩子,要和他分手,而“可能会和特雷维索的那位牙医结婚”……但他对此并不“在意”,认为与他的“正午时光”相比,“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而他所谓的“正午时光”,指的是他所服务的的航班在每个周一、周四、周六(以及周日,每月两次)的“正午时光”都会从大洋上空飞越一个小岛,而这个被大洋所包围的小岛风光总是让他着迷,每次飞越它时,他总是要专注的凝望,并渴望了解这小岛的所有信息,他因此被飞行员称为“海岛疯子”。
为了这个“正午时光”,他甚至拒绝了上面要调他去的好处多多的纽约航班。
最后,他利用假期来到了这个小岛,同时决定再也不离开这小岛,并希望“将以某种方式永远留在岛上”。
这里就面临着小说的一个关键问题,玛利尼的“正午时光”或者说“正午的岛屿”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也就是说,前面所有的精确的现实主义描写与铺垫所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这才是小说的耐人寻味处。
在我看来,这里的象征意义就是:
平庸生活中的唯一慰藉,单调沉闷环境中的一点亮光,某种近乎虚幻的理想追求。
虽然玛利尼的生活看上去似乎很稳定很安宁,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对这种生活其实很不满意,或者说这种稳定和安宁的生活让他感到单调和平庸,甚至厌恶。
而在他眼中的“正午的岛屿”却永远充满着一种诗情画意:
“就在这时,舷窗的蓝色椭圆形里浮现出岛屿的海岸,海滩宛如金带,一座座小山丘簇拥着中央荒原”;
“岛屿很小,孤立海中,湛蓝色的爱琴海环绕着它,为之镶上一道耀眼的凝固的白边,那该是在礁石和海湾间飞溅的浪花”;
“小岛只在几分钟内是可见的,但空气永远是那么澄净,大海近乎残忍地将岛屿刻画得分毫毕现,连最微小的细节都与上一次旅行中的记忆全然吻合:
北方海岬的绿色斑点,浅灰色的房屋,沙滩上晒着的渔网。
看不到渔网的时候玛利尼会有一种匮乏的感觉,近乎一种冒犯”。
……
注意第三段引文中“大海近乎残忍”这样的表述,它告诉我们,玛利尼对海岛的疯狂迷恋已经成为了他心中的唯一“牵挂”,成了他心中割舍不下的一种“痛”。
看见小岛,他就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亲切感和痛苦感,而小岛上的每一处细节都已在他心中刻下深深的印记,少了一处细节他都会有一种“匮乏”的惆怅,而“分毫毕现”的真实又让他产生一种隔空相望的触景伤情,犹如“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那种伤感和极大遗憾,以致于让他觉得大海的“近乎残忍”。
而在现实生活中,虽然生活安宁和稳定,但却没有让玛利尼产生生命激情的冲动,生活中几乎没有让他感到兴奋的事物,而所有那些平静甚至安逸的生活,让他产生的最好感觉不过是,“这一切都有些模糊,轻松又亲切,仿佛是某种代用品,借以打发飞行前后的时间,在飞行中也是一样的模糊、轻松和愚蠢”,由此可见,现实生活中完全缺少能引发他生活热情的事物:
女友的亲近或背离对他而言无可无不可;职业上的完美范儿不过是生存的必然前提,一种职业性的习惯使然;虽然同事菲利莎是与他“有一种默契”的唯一能够多少理解他的人,还有一个弟弟也让他有些牵挂,但是,对他们的这种情感在他已经置身于小岛舒适凉爽的海水中并决定再也不离开小岛时,仅仅是使他“想象他的弟弟,菲利莎,当他们知道他要留在一块孤零零的大石头上当渔民时的表情”,如此而已,他们也完全不能成为他新生活选择的阻碍,他很快就“收回思绪向岸边游去,那一切已是过眼云烟”。
这就是玛利尼“正午的时光”的象征意义,在他看来,过上小岛那种原生态的渔民生活是他生活中最理想的选择。
三、
小说解读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读者还必须明白一点,当科塔萨尔在清晰地极有层次地铺垫渲染这个主题时,他依然保持着一种极其冷静的他者立场,不像我们国内的一些类似题材作品那样,总是要在其中加上一些倾向性极强的“套式”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