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沧江边的古盐田.docx
《澜沧江边的古盐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澜沧江边的古盐田.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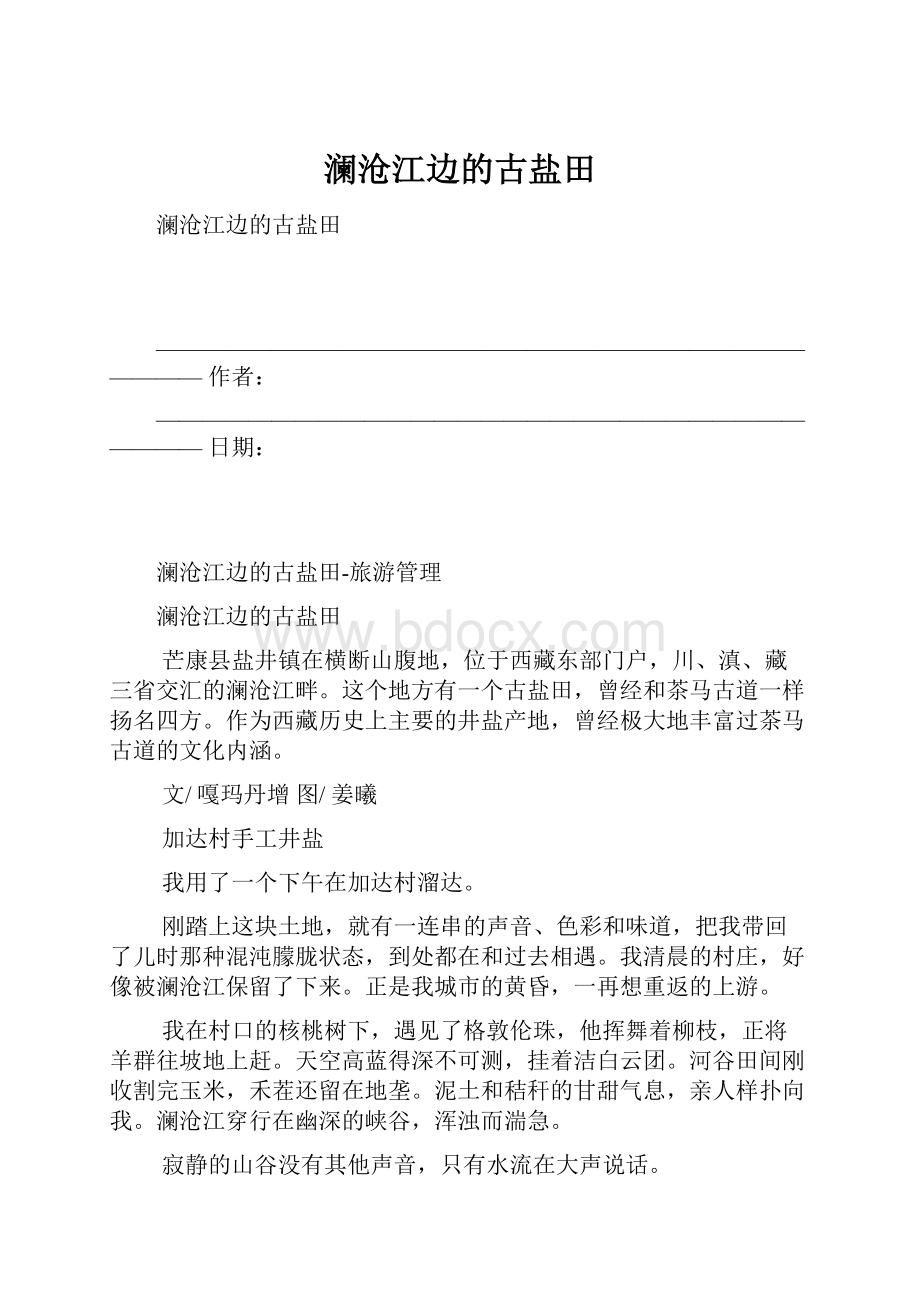
澜沧江边的古盐田
澜沧江边的古盐田
————————————————————————————————作者:
————————————————————————————————日期:
澜沧江边的古盐田-旅游管理
澜沧江边的古盐田
芒康县盐井镇在横断山腹地,位于西藏东部门户,川、滇、藏三省交汇的澜沧江畔。
这个地方有一个古盐田,曾经和茶马古道一样扬名四方。
作为西藏历史上主要的井盐产地,曾经极大地丰富过茶马古道的文化内涵。
文/嘎玛丹增图/姜曦
加达村手工井盐
我用了一个下午在加达村溜达。
刚踏上这块土地,就有一连串的声音、色彩和味道,把我带回了儿时那种混沌朦胧状态,到处都在和过去相遇。
我清晨的村庄,好像被澜沧江保留了下来。
正是我城市的黄昏,一再想重返的上游。
我在村口的核桃树下,遇见了格敦伦珠,他挥舞着柳枝,正将羊群往坡地上赶。
天空高蓝得深不可测,挂着洁白云团。
河谷田间刚收割完玉米,禾茬还留在地垄。
泥土和秸秆的甘甜气息,亲人样扑向我。
澜沧江穿行在幽深的峡谷,浑浊而湍急。
寂静的山谷没有其他声音,只有水流在大声说话。
相机快门的发言,惊动了格敦伦珠。
阳光透过枝叶,散碎的光影落在孩子黑红的脸上,一下子就看到了和高原相关的证据。
他停止吆喝,望着我。
他的身后,就是加达村和色彩丰厚的山林。
一阵热风袭来,树冠飒飒作响。
几片老叶从孩子头顶降落,随即被风掀起,回到空中,好像背着秋天在飞。
他嘿嘿地向我露出了洁白的牙齿,表情友善,一屁股坐到石头上。
孩子让我感到安全。
我说,我是嘎玛。
这个名字,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格敦伦珠成为向导,并一直陪同着我。
芒康县盐井镇在横断山腹地,处于西藏东部门户,川、滇、藏三省交汇的澜沧江畔。
这个地方有一个古盐田,曾经和茶马古道一样名扬四方。
早在唐朝,人们就发现澜沧江岸的岩层里有盐。
我们现今在江岸见到的盐井,就是那时候开凿的,用石头围砌,至今仍在自溢卤水。
加达村坐落于澜沧江西岸,世世代代以传统的晒盐业、农耕、畜牧为生计。
人们用木架做支撑,硬是在险峻陡峭的岸壁上,搭架起数千块晒盐的盐田,看上去奇险无比,蔚为壮观。
如果不了解实情,突然遇见它们,很可能误看作古代悬棺。
据说,加达村的盐田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既是澜沧江流域规模最大、保存完好的古盐田,也是于今世界上唯一活着的手工井盐场。
如今能活着的手工盐场,当然是宝贝,被很多人热捧,成为进入藏区的首席人文景观。
更为奇特的是,这里西岸出产白盐,东岸还出产红盐。
一江之隔,红白相间。
我们都见过白色的盐巴,但不一定见过红盐。
于是,以前供牲畜吃的红盐,被旅游业改变了身份,开始当作纪念品出售。
虽然价格依然便宜,较之于食用商品,还是高出去几倍。
加达村的红盐,和这里的土壤、地质有关。
卤水是红的,晒出来自然就成了红色的盐粒。
事实上,不管你从云南,还是四川方向入藏,进入视觉的除了干蓝天空,澄明阳光,就是群山耸峙、冰川冻土、深壑沟谷。
裸露的巨型山体大多呈赭色,于此逆江而起,一座比一座挺拔险峻。
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将其称为“藏东红山脉”。
红色的山脉你推我拥,一路伸延到了数百公里外的昌都、东亚第一长河澜沧江畔的藏东重镇。
高山大峡里地热资源丰富,夹在岩石褶皱里的盐矿,通过溶岩温泉的加温溶解后,从地底下自溢而出,就成了可以晒出盐粒的卤水。
人们用长木桶装卤水,背到木架上方,倒进10平方米左右的盐田,经两三天时间的风吹日晒,一块盐田就能晒得20多斤的盐巴。
被藏语称为“曲赞”的温泉,在高原地区到处可见。
距离古盐田不远的曲孜卡就有,非常出名,差不多两袋烟时间就能走到。
只是曲孜卡的温泉不是擦卡龙(盐泉),而是供人洗浴净身的矿温泉。
人们于今修了不少舒适现代的客栈和酒店,需要买票进入,才能享用。
不妨想象一下,当你一路风尘来到曲孜卡,找一家藏家餐馆,最好是远近闻名的“加加面”。
那是盐井镇的美食,用小碗盛面,一口一碗。
旁边放着卵石子和陶罐,吃一碗,就往罐里放一块石子,店家以卵石计数结账。
酒足饭饱之后,置身于古远的夜空之下,借着月光泡泡温泉,然后枕着澜沧江奔腾不息的涛声,酣然睡去。
何等安逸舒松的享受!
很多内地人在那里流连忘返。
在澜沧江那几日,我天天晚上泡在温泉池,借着月光吃酒吃茶,附耳澜沧江叫喊的寂静。
什么也不用想了,把自己当成一颗星子,放到天上去。
泡完澡回到客栈,钻进松软的被窝,继续望着星空发呆。
我就这样重返到了仰望时代,整个身心完全摊开,意识风一样在无垠的天穹游弋,瞬间就感到了宇宙的无限,人的渺小和卑微。
格敦伦珠的村庄
我跟着格敦伦珠走进了加达村。
孩子问我到加达村干啥。
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在村子四处转悠,一旦停留,人们很快就围拢过来,不言不语地盯着我,不说话,像看西洋镜。
所有的表情和身体语言,都充满新奇和疑问。
因为,多数游人的行迹,仅至澜沧江东岸古盐田止,少有陌生人愿意参观过盐田后,继续鞍马劳顿地跨越吊桥,步行数公里的羊肠小径,最后走进牲畜出没、道路坎坷、迷宫样的加达村。
加达村因为偏远,传统得以保留。
那些青稞秸秆掺合粘土砌筑的老墙、毛石屋基、杨树门廊和木板瓦片,为我们保管着太多的过去。
走在铺满麦草、马屎牛粪的乱石小径,很容易想起祖先的音容。
容易让人幻信,你的外婆或母亲,就在小巷尽头的屋檐下,满怀希望地等你回家。
溪水在房前屋后哗哗流淌,女人们蹲在水槽边捣衣、洗菜涮锅。
源自高山雪原的清澈水流,成为加达村最有灵性的部分,牛和羊在其间伸脖饮水,人们用来浇灌庄稼、饮用做饭。
不用担心水源安全,村民还停留在相对原始的耕种时代,农药化肥也没有侵入大地肌理。
木作水磨房位于村子的中心地段,旁边是藏地随处可见的白塔和转经筒,虽然舂米磨面的功能已经丧失,仍在日夜吱呀不停。
牛犊趴在路边反刍,偶尔摔摔尾巴,扇扇耳朵,吓唬一下讨厌的蚊蝇。
狗们则伏在草垛小憩,见到生人总要抬起脑袋,装作一副吓人的样子。
穿行在高低错落的加达村,我真的以为回到了从前。
我的父亲或爷爷,或许就在杨树下的人群中间,闲坐唠嗑。
妇女和儿童在院子里席地而坐,很是清闲,唧唧喳喳地说着闲话。
坐在房顶晒台上的大多是孤单的老妪,行动迟缓,慢条斯理地脱粒玉米或瞌睡,远远看去,就像我的祖母,留在记忆里的黑白画像。
眼前的加达村,让我一次次恍惚,连树枝上的鸟巢,檐梁上的玉米草料,以及牲畜间乱七八糟的绳索和农具,都像旧年伙伴。
只是,我身心里的故乡,没有经幡和经筒,也没有白塔和煨桑炉,见不到乡亲沿着时间方向转经祈福,修炼来世。
陪着我的格敦伦珠话语不多。
这个初三年级的学生对我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够去到布达拉宫朝圣。
我被格敦伦珠拉到他们家的时候,看见一家人在院落里忙碌。
家里新买了一台手扶式拖拉机,停靠在柴禾堆码的栅栏内。
父亲和大哥在为拖拉机做雨棚。
母亲卓玛穿着厚重氆氇,围着邦典围裙,站在平房房顶晾晒奶渣。
后来我才知道,新买的拖拉机,是为了方便一家人去拉萨朝圣。
藏历新年以后,格敦一家就会坐上拖拉机,走向漫长的朝圣路。
在通往圣地拉萨的道路上,但凡遇见载满人、食物和帐篷的手扶式拖拉机,大多是前往拉萨或其他古老圣地的朝圣者。
我们知道,上世纪在内地农村满世界跑的手扶式拖拉机,已经不怎么使用了。
这种声音怪异、气味呛鼻的农用交通工具,受到了藏地朝圣者的喜爱,不仅价格便宜,上路还不收过路费。
举家出动去朝圣,比以前一路风尘、风餐露宿简单便捷多了。
我们知道,信仰下的藏地众生,均以朝圣布达拉宫为今生今世的最高理想。
格敦的父亲嘎代热情接待了我。
卓玛不声不吭,专门为我打了一桶酥油茶。
她脸上的皱纹很深,看她安静坐在火塘前加薪煮茶,给人以久别重逢的温暖。
藏族妇女比男人辛苦,除要生儿育女,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还是地头盐田的主要劳动力。
而康巴男人则以剽悍勇猛、喜欢流浪著称于世。
加达村的男人大多从事贩运盐巴的劳动,很难直接关心家庭事物和田间农作,顶多在收割时节,象征性地参与一些田间活计。
格敦家的新居里外都很整洁,室内墙上的挂毯和椅上的羊毛坐垫,绣着传统的吉祥八宝图案,色彩鲜艳明丽。
嘎代大叔不吸烟,安静地和我说话,我问一句,他答一句。
对于这个世界,他没有我那么多问题。
格敦伦珠黑白分明的眼睛在我和嘎代之间转动,很恭敬,不时为我面前的茶杯续上浓香的酥油茶。
醇厚的加达村,让我内心发烫,好像回到了故乡被亲人包围的日子。
旅游开发也是一种破坏
我在加达村走访,受托于一家旅游开发商,做前期旅游规划踏勘。
这个地方,很快就会以千年古盐田为背景,打造西藏东缘第一个人文景区。
我有点担心,自己正在做的一切,会像不明身份的忧伤一样,迅速搅扰原生的静谧。
旅游业的开发,无疑会给加达村带来更多想象空间和利益机会,人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也将得以改善。
房前屋后,至少再也见不到飞行的苍蝇蚊虫、羊屎疙瘩,以及道路上乱发般的麦草。
现代文明的进入,虽然事实上并没有我们期待的那样美好,但可以发展地方经济,带动民众致富,让偏远地区的同胞和我们一样,享受安逸先进的现代生活。
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有牲畜粪便气味的羊肠小径,打满祖先补丁的房子;喜欢充盈于田间地头,那些热气腾腾的粗言秽语。
渴了,不用担心有什么可疑的化学妖怪,跟着牛羊在同一洼泉眼喝水。
急了,也可以和牲畜一样随地大小便。
管它白天黑夜,遇到心爱的女子,双双出入于草垛树林,鸟语花香之下,完全摊开自己……我没有这种生活经验,跟我的感官记忆,也没有必然联系。
我在预谋投靠它的中途,遭遇过太多诗歌培训,对于从前乡村与大地脉息相动的栖居图景,也只在图书馆进行过遥望。
我于今所知道的多数村落,来自于模具工厂,统统一个身份。
一个村落就是所有的村落,就像一个城市式样,就是所有的城市一样。
即便千里万里,很难找到如加达村一样的远方。
在我看来,如火如荼的城乡一体统筹,实为变相剥脱农民的生态空间,其间充满所谓的国家利益和商业阴谋,在事实上分隔了人们和大地世代相生的亲密关系。
而建造美丽新农村的画饼,正在中国大地风卷残云,赶牲口一样把人圈住在一起。
现代化好像就是把一切交给开关按钮、城市下水道、污水处理厂、有毒食品坊和电子脑袋,大家住在一模一样的房子里,邻里间老死不相往来。
你做你的发财梦,我弄我的一亩三分田,再也无需辨识堂前屋后,那些飘着羽毛沾满鸡血的桃符意义。
加达村在奔腾的澜沧江晒盐畜牧,代代传承。
人们用原始的耕作方式,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植青稞、荞麦和玉米。
如果不贪心,糌粑酥油,足够一家人安静幸福地生活。
村边路旁,江畔垭口,还有飘扬的经幡和旋转的经筒,日夜关怀心灵和来世。
人们是否需要增加收成,大量栽种农药和化学作物,在互联网叫卖盐巴核桃?
孩子们不在山上放牧,而是站在冰冷的钢铁吊桥桥头,努力向游人推销手工艺赝品?
因为一张毛票,在厕所门前和游客面红耳赤……破旧立新很容易,但新的结果,我们已经屡见不鲜了,那就是资源、生态、传统、习俗、文化和旧生活的永远结束。
几年前,我去过念青唐古拉山下的纳木错,对当地民众利用自然景观资源胡乱收费的情形深恶痛绝。
有人把牛头羊首放在观景的地方,相机里一旦出现它们的面孔,对不起,请留下照相钱。
甚或,你不经意间拍下了躺在路边睡觉的狗,站立的马,统统都会有人过来找你收费。
这样的情形,让所有游客感到了寒冷。
现代文明对原生文化的强迫和损毁,完全和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
那些为坚守传统生活的人们,无疑为传统文化存在的多样性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生命成本历经数代乃至更加久远。
很多事实都证明过,颠覆和改变传统,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
表面上看,现代文明的进入,使得许多穷乡僻壤发展了进步了,处处油光粉面。
事实上,我们或许正在欢欣鼓舞地伤害自己。
传统和文化,往往就这样被逼迫失语。
有人说,精神贫困的世界黑夜里,无家可归的心灵,可以纸上回乡。
我们漂泊的精神,不仅无岸可依,也面临残酷的现实困境。
问题是,没有人真正愿意回到衣不蔽体的荒野,谁也不会饿着肚子诗歌田园。
上帝不适应高原水土
1865年,有两个法国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加达村对岸的上盐井村,试图于此开始,用西方的上帝取代东方的佛祖,修建了现在看来依然富丽堂皇的天主堂,成为西藏第一个西方教堂。
横断山的天然屏障,曾经有效地保护过藏民族的生活世界。
但盐井天主堂酿制的葡萄酒,一直名声在外,至今仍在愉悦挑剔的喉咙。
当年传教士带来的葡萄种植和酿酒工艺,被当地的藏族人和纳西族人欣然接纳,并传续了下来。
坚守传统,不是非得在一个树上死守,有选择地吸纳先进的现代文明,是一个民族得以长远存续的智慧和创见。
于今的盐井天主堂,用翻译成藏文的圣经传教,大概有600多个教民,这个数据从民国时期开始,几乎没有什么突破。
佛教信仰中的各族人民,已经给予西方的上帝足够宽容。
居住着众多神灵的青藏高原,历来以其纯洁的人文生态傲居在世界高处。
这是一个族群孤净于世的自信。
这种文物级别的自信,藏地坚持了数千年,才有了我们今天还能见识和体验的多种文化式样。
随着道路交通的改善和深入,不同肤色的人群必定陆续到来,新事物新东西也会随之进入。
不难发现,澜沧江沿岸的人们求新求变、发家致富愿望非常急迫。
新的不来,旧的不去。
时间已经证明,新生事物就是对旧生活经验的颠覆和屠戮,照搬人家的生活方式活着。
现今在加达村见到的一切,或许很快就会被挂在博物馆的墙上。
旧生活正在加速腐朽灭亡,就像失血的躯体,再也不会醒来。
千年盐田开发的旅游图纸,已在路上圈点。
我原本不想告诉格敦伦珠家人,但这个准确的消息,让他们很兴奋,十分期待。
想象中的新时代,总会让人期待的。
到时,格敦伦珠也许不再把去拉萨朝圣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他的父亲兄弟,依然会开着拖拉机,奔波在发家致富的道路;家庭中的女性成员,也会一如既往地肩背细长木桶,到澜沧江边盐井打卤。
晒盐的劳动当然要持续,这是加达村成就旅游目的地的看点。
只是原来光照风吹作用下出生的盐巴,不再是生活方式的原形,要变成手工制盐传统的表演,供游人参观。
世界上的事物,一旦成为表演,就会让人疲倦。
我不愿意澜沧江边的古盐田,过早变成史书上的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