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Word文档格式.docx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Word文档格式.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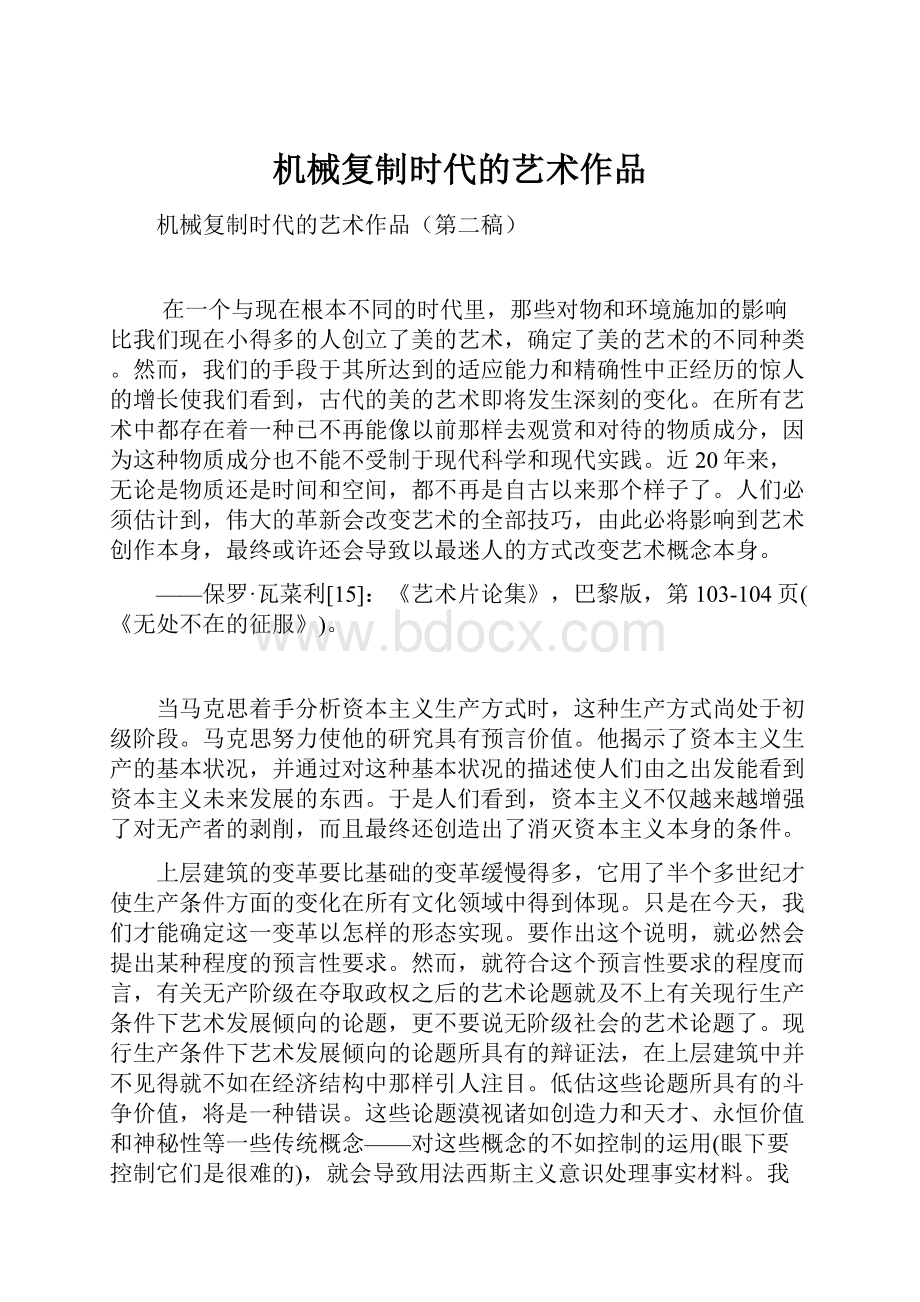
Ⅰ
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总是可复制的,人所制作的东两总是可被仿造的。
学生们在艺术实践中进行仿制,大师们为传播他们的作品而从事复制,最终甚至还由追求赢利的第三种人造出复制品来。
然而,对艺术品的机械复制较之于原来的作品还表现出一些创新。
这种创新在历史进程中断断续续地被接受,虽要相隔一段时间才有一些创新,但却一次比一次强烈。
希腊人只知道两种用技术复制艺术品的方法:
铸造和制模,他们能够大量复制的艺术品只有青铜器、陶器和硬币,其余的艺术品则是独一无二、不可进行复制的。
早在文字能通过印刷复制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木刻就已开天辟地地使对版画艺术的复制具有了可能,众所周知,在文献领域中造成巨大变化的是印刷,即对文字的机械复制。
但是,在此如果从世界史角度来看,这些变化只不过是一个特殊现象,当然是特别重要的特殊现象。
在中世纪的进程中,除了木刻外还有镌刻和蚀刻;
在19世纪初,又有石印术出现。
随着石印术的出现,复制技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这种简单得多的复制方法不同于在一块木版上镌刻或在一片铜版上蚀刻,它是按设计稿在一块石版上描样。
这种复制方法第一次不仅使它的产品一如往昔地大批量销入市场,而且以日新月异的形式构造投放到市场。
石印术的出现使得版画艺术能解释性地去表现日常生活,并开始和印刷术并驾齐驱。
可是,在石印术发明后不到几十年的光景中,照相摄影便超过了石印术。
随着照相摄影的诞生,手在形象复制过程中便首次减弱了所担当的最重要的艺术职能,这些职能便归通过镜头观照对象的眼睛所有。
由于眼摄比手画快得多,因而,形象复制过程就大大加快、以致它能跟得上讲话的速度,在电影摄影棚中,摄影师就以跟演员的讲话同样快的速度摄下了一系列影像。
如果说石印术可能孕育着画报的诞生,那么,照相摄影就可能孕育了有声电影的问世。
而上世纪末就已开始了对声音的技术复制。
这些一致的努力使人可以预见保罗·
瓦莱利在下面这段话中所描述的情形:
“就像我们几乎不显眼地拉一下把手就能把水、煤气和电从遥远的地方引进我们的住宅而为我们服务那样,我们也将配备一些视觉形象或音响效果,为此我们只需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差不多是个手势就能使这些形象或效果出现和消失”2。
19世纪前后、技术复制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品,从而以其影响开始经受最深刻的变化,而且它还在艺术处理方式中为自己获得了一席之地。
在研究这一水准时。
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它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对艺术品的复制和电影艺术——都反过来对传统艺术形式产生了影响。
Ⅱ
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
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
但唯有借助于这种独一无二性才构成了历史,艺术品的存在过程就受制于历史。
这里面不仅包含了由于时间演替使艺术品在其物理构造方面发生的变化,而且也包含了艺术品可能所处的不同占有关系的变化3。
前一种变化的痕迹只能由化学或物理方式的分析去发掘,而这种分析在复制品中又是无法实现的;
至于后一种变化的痕迹则是个传统问题,一对其追踪又必须以原作的状况为出发点。
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
对一件铜器上的绿锈作化学分析,可能有助于确定这种原真性,就像证明了某个中世纪的手抄本源出于一个15世纪的档案馆也许就有助于确定其原真性一样。
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4。
原作在碰到通常被视为赝品的手工复制品时,就获得了它全部的权威性,而碰到技术复制品时就不是这样了。
其原因有二。
一是技术复制比手工复制更独立于原作。
比如,在照相摄影中,技术复制可以突出那些由肉服不能看见但镜头可以捕捉的原作部分,而且镜头可以挑选其拍摄角度;
此外,照相摄影还可以通过放大或慢摄等方法摄下那些肉眼未能看见的形象。
这是其一。
其二,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
首先,不管它是以照片的形式出现,还是以留声机唱片的形式出现,它都使原作能随时为人所欣赏。
大教堂挪了位置是为了在艺术爱好者的工作间里能被人观赏;
在音乐厅或露天里演奏的合唱作品,在卧室里也能听见。
此外,艺术品的机械复制品所处的状况可能不大会触及艺术品的存在——但这种状况无论如何都使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丧失了。
这一点不仅对艺术品来说是这样,对例如电影观众眼前闪过的一处风景来说也是这样。
因此,通过展示艺术品的过程还触及了一个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即艺术品的原真性问题;
而在这个核心问题上,没有什么自然物会如此地易受损害。
一件东西的原真性包括它自问世那一刻起可继承的所有东西,包括它实际存在时间的长短以及它曾经存在过的历史证据。
由于它的历史证据取决于它实际存在时间的长短,因而,当复制活动中其实际存在时间的长短摆脱了人的控制,一件东西的历史证据也就难以确凿了。
当然,也仅仅是历史证据;
但如此一来难以成立的就是该东西的权威性了5。
人们可以把在此排除的东西纳入到光韵这个概念中,并指出,在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韵。
这是一个有明显特征的过程,其意义超出了艺术领域之外。
总而言之,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
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
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
这两方面的进程导致了传统的大动荡——作为人性的现代危机和革新对立面的传统大动荡,它们都与现代社会的群众运动密切相联,其最有影响力的代理人就是电影。
电影的社会意义即使在它最具建设性的形态中——恰恰在此中并不排除其破坏性、宣泄性的一面,即扫荡文化遗产的传统价值的一面也是可以想见的,这一现象在伟大的历史电影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不断扩大。
阿倍尔·
冈斯曾在1927年热情满怀地宣称:
“莎士比亚、伦勃朗、贝多芬将拍成电影……所有的传说、所有的神话和志怪故事、所有创立宗教的人和各种宗教本身……都期待着在水银灯下的复活,而主人公们则在墓门前你推我揉。
”6也许他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但却发出了广泛地进行扫荡的呼吁声。
Ⅲ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感性认识方式是随88看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
人类感性认识的组织方式——这一认识赖以完成的手段——不仅受制于自然条件,而且也受制于历史条件。
在民族大迁徒时代,晚期罗马的美术工业和维也纳风格也就随之出现了,该时代不仅拥有了一种不同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新艺术,而且也拥有了一种不同的感知方式。
维也纳学派的学者里格耳和维克霍夫首次由这种新艺术出发探讨了当时起作用的感知方式,他们蔑视埋没这种新艺术的古典传统,尽管他们的认识是深刻的,但他们仅满足于去揭示晚期罗马时期固有的感知方式的形式特点。
这是他们的一个局限。
他们没有努力——也许无法指望——去揭示由这些感知方式的变化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变迁。
现在,获得这种认识的条件就有利得多。
如果能将我们现代感知媒介的变化理解为光韵的衰竭,那么,人们就能揭示这种衰竭的社会条件。
上面就历史对象提出的光韵概念,值得根据自然对象的光韵概念去加以说明。
我们将自然对象的光韵界定为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
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一边休憩着一边凝视地平线上的一座连绵不断的山脉或一根在休憩者身上投下绿荫的树枝,那就是这座山脉或这根树枝的光韵在散发,借助这种描述就能使人容易理解光韵在当代衰竭的社会条件。
光韵的衰竭来自于两种情形,它们都与当代生活中大众意义的增大有关,即现代大众具有看要使物在空间上和人性上更易“接近”的强烈愿望7,就像他们具有着接受每件实物的复制品以克服其独一无二性的强烈倾向一样。
这种通过占有一个对象的酷似物、摹本或占有它的复制品来占有这个对象的愿望与日俱增。
显然,由画报和新闻影片展现的复制品就与肉眼所亲自目睹的形象不尽相同,在这种现象中独一无二性和永久性紧密交叉,正如暂时性和可重复性在那些复制品中紧密交叉一样。
把一件东西从它的外壳中橇出来,摧毁它的光韵,是这种感知的标志所在。
它那“世间万物皆平等的意识”增强到了这般地步,以致它甚至用复制方法从独一无二的物体中去提取这种感觉。
因而,在理论领域令人瞩目的统计学所具有的那种愈益重要的意义,在形象领域中也显现了。
这种现实与大众、大众与现实互相对应的过程,不仅对思想来说,而且对感觉来说也是无限展开的。
Ⅳ
一件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性是与它置身于那种传统的联系相一致的。
当然,这传统本身是绝对富有生气的东西,它具有极大的可变性。
例如,一尊维纳斯的古雕像,在古希腊和中世纪就处于完全不同的传统联系中。
希腊人把维纳斯雕像视为崇拜的对象,而中世纪的牧师则把它视作一尊淫乱的邪神像;
但这两种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触及了这尊雕像的独一无二性,即它的光韵。
艺术作品在传统联系中的存在方式最初体现在膜拜中。
我们知道,最早的艺术品起源于某种礼仪——起初是巫术礼仪,后来是宗教礼仪。
在此,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艺术作品那种具有光韵的存在方式从未完全与它的礼仪功能分开8,换言之,“原真”的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价值植根于神学,艺术作品在礼仪中获得了其原始的、最初的使用价值。
艺术作品的这种礼仪方面的根基不管如何辗转流传,它作为世俗化了的礼仪在对美的崇拜的最普通的形式中,依然是清晰可辨的9。
世俗的对美的崇拜随着文艺复兴而发展起来,并且兴盛达3世纪之久,这就使人们从礼仪在此后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震荡那里清楚地看到了礼仪的基础,随着第一次真正革命性的复制方法的出现,即照相摄影的出现(同时也随着社会主义的兴起),艺术感觉到了几百年后显而易见的危机正在迫近,艺术就用“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即用这种艺术神学作出了反应。
由此就出现了一种以“纯”艺术观念形态表现出来的完全否定的神学,它不仅否定艺术的所有社会功能,而且也否定根据对象题材对艺术所作的任何界定(在诗歌中,马拉美是始作俑者)。
对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考察必须十分公正地对待这些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在此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决定性的看法:
艺术作品的可机械复制性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礼仪的寄生中解放了出料10。
复制艺术品越来越成了着眼于对可复制性艺术品的复制。
例如,人们可以月一张照相底片复制大量的相片,而要鉴别其中哪张是“真品”则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当艺术创作的原真性标准失灵之时,艺术的整个社会功能也就得到了改变。
它不再建立在礼仪的根基上,而是建立在另一种实践上,即建立在政治的根基上。
Ⅴ
对艺术作品的接受有着不同方面的侧重,在这些不同侧重中有两种尤为明显:
一种侧重于艺术品的膜拜价值,另一种侧重于艺术品的展示价使”1112。
艺术创造发端于为膜拜服务的创造物。
人们可以认为,在这种创造物中,重要的并不是它被观照着,而是它存在着。
石器时代的洞穴人在其洞内墙上所描画的驼鹿就是一种巫术工具。
洞穴人虽然在他们的同伴面前展现了这种驼鹿,但是,这些驼鹿主要是奉献给神灵的。
看来,正是这种膜拜价值在今天变得要求人们隐匿艺术品:
有些神像只有庙宇中的神职人员才能接近,而有些圣母像几乎全年被遮盖着,中世纪大教堂中的有些雕像就无法为地上的观赏者所见。
随着单个艺术活动从礼仪这个母腹中的解放,其产品便增加了展示的机会。
能够送来送去的半身像就比固定在庙宇中的神像具有更大的可展示性。
木板画的可展示性就要比先于此的马赛克画或湿壁画的可展示性来得大;
也许,弥撒曲的可展示性本来并不比交响曲的可展示性来得小,可是,交响曲却形成于一个其可展示性看来要比弥撒曲的可展示性来得大的时机中。
由于对艺术品进行复制方法的多样,便如此大规模地增加了艺术品的可展示性,以致在艺术品两极之内的量变像在原始时代一样会突变其本性的质,就像原始时代的艺术作品通过对其膜拜价值的绝对推重首先成了一种巫术工具一样(人们以后才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个工具视为艺术品)。
现在,艺术品通过对其展示价值的绝对推重便成了一种具有全新功能的创造物。
在这种全新功能中,我们意识到的这些艺术创造功能,作为人们以后能视之为附带物的功能而突现出来13。
现在的照相摄影还有电影提供了达到如上这种认识的最出色的途径,这一点是绝对无疑的。
Ⅵ
在照相摄影中,展示价值开始整个地抑制了膜拜价值。
然而,膜拜价值并不是很乖顺地消失的,它拉出了其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就是人像。
早期照相摄影以人像为中心,这一点绝不是偶然的。
在对遥远的或已消失的爱进行缅怀的膜拜中,画像的膜拜价值找到了其最后的避难所。
在早期照相摄影中,光韵通过人像面部的瞬间表憎还在作最后的道别,构成这最后道别的就是摄影那忧郁的无与伦比之美。
可是,当人像在照相摄影中消失之时,展示价值便百次超越了膜拜价值。
阿特盖的独特意义就在于展现了这个过程,他于1900年摄下了无人的巴黎街区。
然而,人们完全有理由说,他摄下的巴黎街区宛如一片作案现场。
就连作案现场也是无人的。
阿持盖的摄影是为了推定证据。
照相摄制从阿特盖开始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些见证,这样就使摄影具有了潜在的政治意义。
摄影要求有一种特定的接受,它不再与自由玄想的静观沉思相符合。
它使观赏者坐立不安;
观赏者觉得必须寻找一条通向这些摄影的特定道路。
于是,引路人便同时向观赏者展现了一些画报。
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这样,这些图片就首次提出了作文字说明的需要。
显然,这种文字说明具有一种与绘画标题完全不同的性质。
观赏者通过文字说明从画报中直接获知的意旨,在电影中就愈趋精密和愈趋强制;
在电影中,好像对任何单个画面的理解都是由已消逝的所有先行展现的画面所规定好了的。
Ⅶ
贯穿19世纪的绘画和照相摄影,围绕其产品艺术价值所进行的争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不恰当和含糊不清的。
但是,这一点与其说是拒斥了艺术品的意义,不如说是可能强调了艺术品的意义。
实际上,这个争论体现了世界历史所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争论双方都未意识到的。
由于艺术在机械复制时代失去了它的膜拜基础,因而它的自主性外观也就消失了。
可是,由此出现的艺术功能的演化却脱离了19世纪的人的视野,甚至,连经历了电影发展的20世纪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如果人们以前对照相摄影是否是一门艺术作了许多无谓的探讨——没有预先考察一下:
艺术的整个特质是否由照相接影的发明而得到了改变——那么,电影理论家不久就接受了仑卒提出的相应的课题。
但是,这种照相摄影给传统美学所带来的困境,对于电影及其期望来说,不啻是一种儿戏,由此产生了标志电影理论先期特征的那种盲目的牵强性。
于是,阿培尔·
冈斯就把电影与象形文字进行了比较:
“由于我们奇特地例退到了存在物之中,因此,我们又回到了埃及人的表达水平上……形象语言尚未发展到成熟地步,这是由于我们还不具有与之对应的洞察力。
对于形象语言中表达的东西,我们尚没有充分重视,而且也不具有充分的膜拜感情。
”[16]或者正如S·
-玛赫所说:
“哪一种艺术会具有……融虚构和现实于一体的梦幻呢!
从这一立场出发,电影就体现了一种完全无法比拟的表现方式。
只有那些具有高尚思维方式的人,在他们生活经历的那些最完美的、充满神秘色彩的瞬间才能进到电影的氛围中。
”[17]而亚历山大·
阿奴斯[18]正是用如下这个问题结束了对无声电影的幻想:
“我们在此所用的所有大胆描述难道不应导致对默祷的界定吗?
”[19]看到如下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即把电影归结为“艺术”的努力迫使理论家空前武断地硬把膜拜要素注解到电影中。
不过,这个推测付诸公开时,已有了诸如《公众舆论》和(淘金记)这样的作品;
而这并没有阻止阿培尔·
冈斯去与象形文字作比较,而S.-玛赫则像人们论述F.安吉利科的画像那样去论述电影。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今日还有特别反动的作者也同样不是在宗教方面就是在超自然方面去寻找电影的意义的。
在赖因哈特把《仲夏夜之梦》拍成电影之际,威弗尔就指出,这无疑是对这样一个外在世界的无创造性复制,这个外在世界有街道、居室、火车站、饭馆、汽车和海滩。
这个复制迄今为止妨碍了电影在艺术王国中的倔起。
“电影还没有认识它的真正含义,还没有认识它的真正能力……电影的真正可能性存在于它的这种独一无二的能耐中,即用逼真的手段和无与伦比的可信性去表现迷人的东西、使人惊讶的东西,即超自然的东西。
[20]
Ⅷ
肯定地说,舞台演员所作出的艺术成就,对观众来说是由演员用其自身形象得到体现的;
与之相反,电影演员所作出的艺术成就,对观众来说则是由某种机械体现的,后者具有双重结果。
把电影演员的成就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机械并没有阻止把这成就作为整体去对待,它在摄影师操纵下不断对电影演员的成就表态。
电影的这种状态是由剪辑顺序提供给他的材料组接的,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出现了一种由剪辑合成的电影。
它含有一些运动因素,而这必定是摄影机的那些运动因素——我们无需指出诸如特写镜头这种专门的镜头调度。
因此,电影演员的成就受制于一系列视觉检测机械。
这是电影演员的成就由机械来展现所导致的第一个结果。
第二个结果是,电影演员由于不是本人亲自向观众展现他的表演,因而,他就失去了舞台演员所具有的在表演中使他的成就适应观众的可能。
由此观众就采取了一种不再受与演员私人接触影响的鉴赏者的态度。
而观众通过站在摄影机的角度便把自身移入到了演员中。
因此,他又采取了摄影机的态度:
他对演员进行着检测[21]。
这就不是一种能产生膜拜价值的态度。
ⅠⅩ
对电影来说,关键之处更在于演员是在机械面前自我表演,而不是在观众面前为人表演。
最早通过成就检测觉察到这种演员隐形的人是皮兰德娄。
他在其小说《拍成电影》中对此所作的洞察,仅仅使之局限在对过程的否定方面,这并无大碍,而使之与无声电影相联,则更无大碍。
因为,有声电影对过程丝毫末作出什么改变。
在此,关键之处依然在于,演员是为
一种机械——在有声电影中是为两种机械——进行表演。
皮兰德娄指出:
“电影演员觉得自己仿佛是在流放一样。
他不仅从舞台中流放了出来,也从其自身角色中流放了出来。
随着说不清的不适,他感觉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空虚,这种空虚由此而来:
他的身体似乎被分解了,他本人似乎被蒸发掉了,而且通过转变成一个无声形象,他的存在、他的生活、他的声音和他的活动造成的音响似乎被剥夺了,这个无声形象在银幕的某个瞬间中晃动,然后又默默地消失……这种小装置用演员的投影在观众面前表演;
而演员本人,则必须满足于在摄影机面前进行表演。
[22]。
我们可以对类似的情况作如下描述:
人们第一次——在电影作品中正是这样——能够展现他活生生的整个形象,但这必须以放弃他的光韵为条件。
因为光韵来自于即时即地,对光韵无法进行摹仿。
在舞台上麦克白斯一角显现的光韵,在有生气的观众看来不能脱离那依附在扮演麦克白斯演员周围的光韵。
电影摄影棚中拍摄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把摄影机放在了观众的地位上。
这样一来,必然消除依附在演员周围的光韵——而由此也必然消除所扮演的角色的光韵。
正是像皮兰德娄这样的剧作家在描绘电影特征时不由自主地触及了我们看到的戏剧所遭受危机的根源,这一点不足为奇。
因为,彻底地由机械复制去控制的艺术作品——例如电影——与舞台的对立就再明显不过了。
所有深入的考察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有经验的观赏者早就发现:
“在电影中,由于人们尽可能少地去‘表演’,几乎总是获得了最大的效果……”阿恩海姆于1932年看到,“电影的最近发展在于,像人们精心选择的道具一样去对待演员……并把他们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23]而最紧密地与此相联的则是另一些现象。
登台表演的演员进入到了角色中,而电影演员则往往做不到。
他的成就并不是一个统于一体的成就,而是由众多的单个成就组成的。
除了偶然要考虑到的:
如摄影棚的租金、合伙人的调配以及美工等因素之外,这种机械作为本质的必然性,会把演员的表演分割成一系列可剪辑的片断。
因首先还涉及到要安装灯光设备,从而迫使对银幕上统一的快速运动过程要在一系列分别摄制的镜头中去表现,这在摄影棚中则可能要由数小时之久的拍摄来完成,更不要说是在手工的蒙太奇剪辑中了。
因此,跃出窗口可在摄影棚中以脚手架上跳跃的形态来拍摄,紧接着的逃跑也许是几星期之后在外景中摄制了。
此外,制造更突发的情形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以设想是,要求演员被敲门声吓了一跳,也许,这种惊慌并非如人所愿地显得突兀。
那么,偶尔当演员在摄影棚中,导演可让预先埋伏的人从他背后射击,演员在这一片刻的惊慌可被拍摄下来,并被剪接到电影中。
没有比这一点更清楚地表明艺术已脱离了“徒有其表”的境界,而这一境界一直被视为艺术于其中发展的唯一境界。
Ⅹ
正像皮兰德娄所描述的那样,演员在机械面前的诧异,本来完全保人在镜子中看到他的映像时所产生的诧异一样。
而现在,镜中的映像则可以与他相分离,它成了可以移动的东西。
那么,人们把它移到了何处呢?
答曰:
移到了观众面前[24]。
电影演员一刻也没有脱离对这一点的意识。
电影演员知道,当他站在投影机前时,他就站在了与观众相关联的机制中,而观众就是构成市场的买主。
电影演员不仅用他的劳动力,而且还用他的肌肤和毛发、用他的心灵和肾脏进入到这个市场中。
这个市场在电影演员为其作出成就的瞬间很少能为他所把握,就像它很少为企业中所制造出的某件物品所把握一样。
这种情形不就加剧着它的压抑,加剧着照皮兰德娄看来是演员在摄影机前才产生的那种新的焦虑吗?
电影用在摄影棚之外对“名人”的人工制造来补偿光韵的消失。
由电影资本支撑的明星崇拜保存了那种“名流的魅力”,而这种魅力向来只在于其商品特质的骗人玩意儿中。
只要电影资本规定了电影的基调,那么,当代电影一般来说就具有了一种革命贡献,即对传统的艺术观念进行革命的批判。
我们不否认当代电影除此之外在某些独特情形中,也对社会状况即对财产秩序进行了革命的批判。
然而。
这一点就像对于西欧电影生产的重点一样,它也很少是我们现时考察的重点。
电影技巧也同体育运动技巧一样,每个人都是作为半个行家而沉浸于展示技巧的成就中。
为了揭示这个事实,只需倾听一下那些靠在自己自行车上的报童谈论自行车赛结果的情况。
报刊出版商并非徒劳地来组织其报童进行自行车赛,而这却唤起了参赛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