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中国古代哲学心得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中国古代哲学心得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中国古代哲学心得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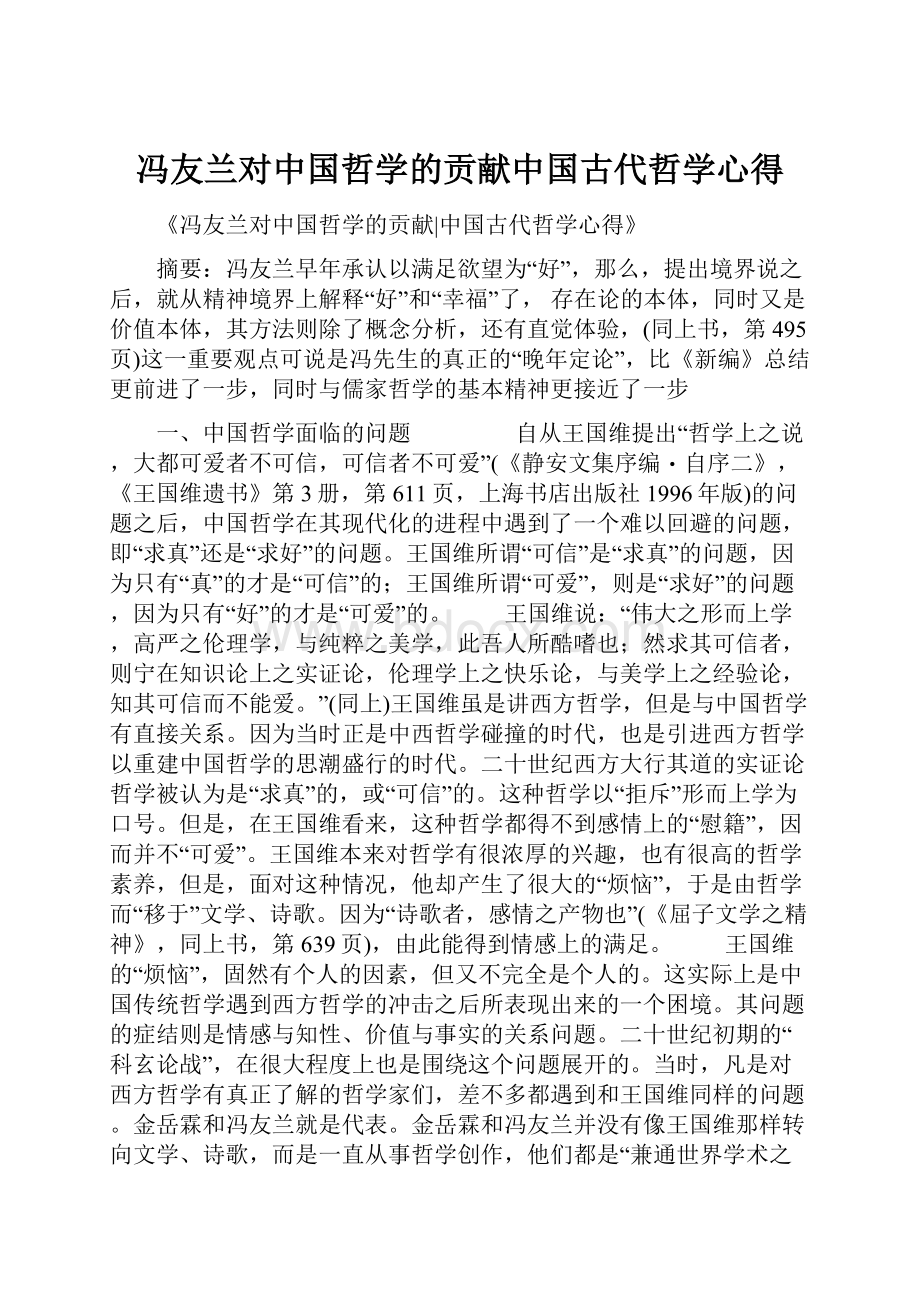
但是,他却将中国哲学中的“道”作为他的哲学的最高范畴,以此与西方哲学相区别。
在金岳霖看来,“道”不仅是理,而且是情;
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价值;
不仅是“真”,而且是“善”和“美”,是合真、善、美为一的全体性的范畴。
为此,他用无极、太极、性、情、体、用这些中国哲学特有的名词去说明“道”,将“道”说成是“元学”的问题,而不是知识论的问题。
由于“道”是“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因此,“情感难免以役于这样的道为安,我底思想也难免以达于这样的道为得。
”(《论道》,第16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这也就是“不仅在研究底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的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
”否则,如果仅仅当作知识去研究,便不能“动我的心,怡我的情,养我的性。
”(同上书,第17页)金岳霖是以哲学的方式解决王国维所提出的问题的,他的哲学的最终日的不是理智的知识,而是“完整的人”(同上),这就是他为什么把中国哲学中的许多情感因素“转移”到他的书的概念中去的真正原因。
金岳霖是将逻辑分析作为工具,而将理想的人生价值作为最终目的,解决事实和价值、认识和情感的关系问题的。
在这个问题上,冯友兰和金岳霖有共同之处,但他更关注中国哲学的固有价值,并做出了独特贡献。
冯友兰对哲学的定义是: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中国哲学史新编・总论》,《三松堂全集》第10卷,第65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以下引文,只注明《全集》卷数、页码)这所谓“精神”,应当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决不只是理智和知识,它应是人的心灵活动的全部内容。
这所谓“反思”,则是哲学专有的。
但“反思”既表现为理论思维,同时又是精神境界。
冯友兰认为,理论思维与精神境界不是工具与目的的关系,“不是以哲学为手段,达到提高、丰富精神境界的目的。
在哲学的反思之中,人的精神境界同时就丰富、提高了。
”(第8卷,第31页)冯友兰所说的“理论思维”,主要是指概念分析和推论等理智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明显的理性主义和认识论倾向。
但是,决不能将其归结为理性主义认识论。
这其中,有“存在”层面的问题,有本体论的问题。
就认识而言,还有直觉感受和情感体验的问题,不单是概念分析。
事实上,冯友兰是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结合上解决存在和价值的关系问题的。
冯友兰自建立哲学体系之日起,就很关注人的精神生活的问题,并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其哲学的根本目的。
境界有不同层次,最高境界即“同天”境界。
“天”是宇宙自然界的全体即“大全”,(他晚年已肯定,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就是自然界。
见《全集》第13卷,第333页)“同天”境界就是与宇宙自然界合一。
其中,又包括“知天”和“乐天”不同层面。
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知天”是认识之事,但非对象认识;
“乐天”则是情感之事,属生命体验。
这样看来,“同天”境界就是认识和情感的统一。
冯先生特别强调,哲学是使人“受用”的,不是使人增加知识的。
“受用”就是“享受”(第10卷,第656页),即精神的快乐,具体地说,就是情感上的“安慰”或满足。
他还强调,哲学的最终目的是使人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这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精神境界,其最终的安身立命之“地”就是“同天”境界,即人与自然的合一。
哲学不仅能使人“自觉”其有这个“安身立命之地”,而且能够使人得到最大的“享受”。
因此,哲学的根本目的是“求好”,而不是“求真”。
这同王国维的“可爱”与“可信”之说是一致的。
但是,王国维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了,冯友兰则试图将二者统一起来,在这一点上与金乐霖更相近。
二、哲学何以是“求好”?
冯友兰在《哲学及其哲学史之一见》中,将哲学与科学作了严格区分,认为:
“哲学与科学之区别,即在科学之目的在求真;
而哲学之目的在求好。
”(第11卷第66页)他将“求真”归之于科学,说明他所说的“真”,是实际的科学知识之真,或“积极的知识”之真。
他将“求好”归之于哲学,说明哲学归根到底是解决人生问题,解决人的价值问题,而不是科学认识问题。
哲学就是求得人生的最大幸福,这个“幸福”不是从信仰的对象即上帝那里去寻找,也不能在科学知识中去寻找,只能在哲学中去寻求。
但在这个问题上,中西哲学是不同的。
中国是“直接地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而希腊和现代欧洲则是“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同上书,第50页),以得到幸福。
冯友兰实际上是沿着中国哲学的价值指向前进的。
不过,他将“在人心之内寻求幸福”变成提高精神境界,认为境界提高了,就会得到一种无比的幸福,而不是通过“征服自然”得到物质享受上的幸福。
这当然不是说,人不需要物质生活,而是说,境界提高之后超越了物质需求而不是禁止物质需求。
真正的幸福在于情感的“安慰”,而不是物质的享受。
如果说,冯友兰早年承认以满足欲望为“好”,那么,提出境界说之后,就从精神境界上解释“好”和“幸福”了。
在《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中,他明确提出:
“哲学不能增进人们对于实际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第10卷,第656页)知识是一种权力,用来征服自然;
境界是一种人生,能与自然和谐相处。
但境界的提高,是要靠“身体力行”而不是靠解释文字的“口耳之学”。
只有“身体力行”了,才能“受用”,才能“享受”。
这与孔子的“成己”之学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他对孔子的“孔颜乐处”很推崇。
“有‘自同于大全’这种精神境界的人,可以有一种最大的快乐。
这种快乐,就是所谓‘孔颜乐处’。
”(第10卷,第657页)这显然是指生命体验而言的。
这种体验离不开具体情感,但又超越了具体情感,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精神状态,决不是知识所能解决的。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冯友兰发展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批评了现代西方哲学。
精神境界不同于知识之处,就在于前者是一种“人生理想”,而后者只是一种“权力”。
境界作为人心灵的存在状态,既包括理智的“理解”,又包括情感的“态度”,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称之为“境界”。
冯友兰一方面批评了现代西方的实证哲学与分析哲学,认为这些哲学家“所着重研究的多半是一些枝枝节节的小问题。
问题越小,越可以称为专门的哲学。
专业哲学家必须讲专门的哲学,在一些枝节问题上,钻牛角尖。
对于可以使人‘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反而不讲了。
解决这些大问题,本来是哲学的责任。
”(第1卷,第222页)冯先生以讲“安身立命的大道理”为哲学的责任,并且能自我承当,这是对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和使命的一种非常积极的肯定和弘扬。
这所谓“大道理”,就是精神境界,这才是人生的根本问题,也是哲学的根本任务。
现代西方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相标榜,以求所谓事实之“真”为任务,以所谓“价值中立”为口号,自以为是最科学的哲学,但是却忽略了人的问题,忽略了人的价值,陷入了“枝节”问题。
冯先生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
另一方面,冯先生对于西方某些人视中国哲学为汉学而非哲学的看法,也提出了批评。
他说:
“中国传统哲学,一直被视为汉学的一部分,认为它与哲学毫无关系。
其实,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哲学是以研究人为中心的‘人学’。
”(第11卷,第665页)称中国哲学为“人学”,这是冯先生的一贯看法,他有时称中国哲学为“人学形而上学”(第11卷,第502页),其实都是讲境界的。
“汉学”本来是西方人研究中国以汉字为载体的古代典籍的学问,是一种“客观知识”,同时,在西方学科分类的背景下,他们认为中国的学问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
后来,“汉学”的研究逐渐细致化、专门化了,其中便有属于哲学方面的内容,但是很多人仍然认为,这不是哲学,只是“汉学”中的一部分。
这里隐含着的意思是,“中国无哲学”,其衡量的标准和尺度,便是西方哲学。
冯先生坚持中国有哲学,而中国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学问,既肯定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又说明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殊性”,但在“特殊性”中,却包含着普遍的价值和意义。
人是理性动物,有理性的分析能力,这是冯先生早就强调过的,并且以此为“人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者”(第11卷,第391页)。
但是,人又决不止于此,人还有存在及其价值方面的问题。
“分析”是哲学与科学共同使用的方法,但哲学之使用“分析”,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提高境界,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中国哲学家则多未以知识权力之自身为其好,故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为权力而求权力……至于无限的控制天然之权力,中国哲学家亦不以为好。
”(第11卷,第132页)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哲学家不重视科学,但另一方面又说明,中国哲学家始终关心人生的大道理。
冯先生所说哲学的功用及目的在于“求好”,就是继承了中国哲学的这一传统精神。
所不同的是,他将“分析”方法吸收进他的哲学之中,使其成为“现代”的,但这并不是目的本身。
有些学者对于“中国哲学是人学”的提法有些保留(如牟宗三先生),还有些人可能更不同意中国哲学是“人学”。
但是,冯先生所说的“人学”决不是孤立的以人为对象的学问,即不是离开宇宙自然界,将人视为孤立的主体,去研究人的“自我”或“自我意识”之类。
人是不能离开宇宙自然界而独立存在的,所以,有些学者称中国哲学为“宇宙人生”之学。
冯先生在论新儒学时说:
“新儒学可以说是关于‘人’的学问。
它所讨论的大概都是关于‘人’的问题,例如,人在宇宙的地位和任务,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性和人的幸福。
”(第10卷,第16页)这不仅是讲新儒学,而且是讲他自己的哲学。
他又提出,中国哲学是研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即“究天人之际”)“这个‘天’,也是泛指自然界。
‘天人之际’,说的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第13卷,第333页)很清楚,哲学不能离开自然界而讨论人的问题,更不是人类中心论的。
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这显然不是纯粹认识的关系,而是人的存在及意义和价值的问题。
那么,人在自然界居于何种地位?
人与自然界是什么关系?
冯先生在晚年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人是从自然界生出来的。
人把自己局限于自己身体范围之内,成为自然的对立物,以自己的身体为内,以其他万物为外,以自己的身体为己,以其他万物为彼。
这就是异化。
如果达到上面所说的精神境界(指“浑然与物同体”或“万物一体”),那就是合内外,同彼己。
这就取消了人和自然的对立,取消了异化。
”(第13卷,第336页)“人是从自然界生出来的”,这是一个本源性的说法,正是这一点确立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冯先生并不否定人的精神创造,他说他的四种境界说,前二者是“自然的赐予”,后二者是“精神创造”,这就充分肯定了人的精神创造。
但是,人的创造不是将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而是与自然界合一,达到“同天”境界,这样才能消除人的“异化”,确立人的地位和价值。
这就不是知识上的事”(同上),而是一个使人如何成为人的生命体验和“身体力行”之事。
人与自然界不是主体与客体、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而是“存在”意义上的价值关系。
人所需要的是对“意义”的“觉解”,而不是单纯的对象认识,是为了“安身立命”,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
这就回答了哲学何以是“求好”的问题。
三、存在与价值的合一 精神境界也就是心灵境界。
冯先生对“心灵”有一个看法,认为:
“我们人的心,有情感及理智两方面。
”(第11卷,第154页)冯先生是理性主义者,他认为,精神境界主要是认识而认识以理智认识为主,但又不仅仅是认识,还要有情感体验。
中国哲学“折中于此二者之间,兼顾理智与情感”,因而“是诗的,艺术的,而非宗教的。
”(同上)他用儒家的丧、葬之礼来说明这一点,一方面与“以情感之想象为真理,而否认理智之判断”的宗教相区别,另一方面又与以理智认识为真,而否认情感作用之科学相区别。
这里涉及到所谓“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这是当代哲学争论中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冯友兰哲学所遇到的重要问题。
他用实在论的“共相”理论,建立了存在论的本体,同时又是价值本体,其方法则除了概念分析,还有直觉体验。
前者是冯先生运用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解决中国哲学问题的主要手段。
冯先生承认,“中国最缺乏理性主义的训练,我们应当介绍理性主义。
”(第11卷,第281页)他一生用力最勤的就是这项工作。
但是,他又继承了中国哲学中事实与价值、求真(非科学知识之真,而是哲学之真)与求善(非狭义的道德之善,而是广义的价值之善)相统一的传统,将理智认识与情感态度相结合,建立起新的“人学形上学”。
冯先生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在朱子哲学中,理是“所以然者”,又是“所当然者”,但“所以然”与“所当然”是合一的。
这个说法代表了儒家哲学的基本观点,即存在与价值的统一。
分析地说,“所以然”是讲存在问题的,是一物之所以成为一物的依据,一物有一物之理,即一物之所以然者。
“所当然”是讲价值问题的,是人们应当遵循的准则。
“所以然”是“本然”的问题,事物本来就是如此存在的;
“所当然”是“应然”的问题,人们应当如此存在。
朱子为什么说“所以然”与“所当然”是统一的呢?
这个问题我另有文章讨论(见《所以然与所当然如何统一?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冯先生是同意朱子观点的,但是做出了新的解释。
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的哲学体系》中,引用《新理学》中的话说:
“朱子以为理是实际底事物之所以然之故,及其当然之则,我们所说理亦是如此。
”(第10卷,第631页)这就是说,他同意朱子将“所以然”与“所当然”统一起来的说法。
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观点看,“所以然”是讲事实问题的,是陈述句;
“所当然”是讲价值问题的,是祈使句。
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决不能统一。
二者的区别就是客观事实(陈述)同主观要求(祈使)的区别。
但是,按照冯先生的解释,理不仅是事物所以存在的“形式”,而且是事物应当存在的“标准”,“所以然之故”同时就是“所当然之别”。
一事物只有按其“所以然之故”而存在,才是符合标准的,也只有按其“所当然之则”而存在,才是“好”的或“善”的。
“所当然”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或者说,虽然具有某些主观性,但从根本上说则是客观的,决不是个人的主观兴趣之类。
拿“太极”来说,“所谓极有两义:
一是标准之义……一是极限之义。
”(同上书,第632页)“极限”可说是事物存在的依据,“标准”可说是事物所要达到的目的。
分开来说,有“所以然”与“所当然”之别,但从实际事物或人的具体存在而言,二者是完全统一的。
事物既然有其所当然的“标准”’,就应当按这个“标准”去做,人应当按人的“标准”去做,真正做到了,就是“好”,就是“善”。
这所谓“好”或“善”,不仅具有道德意义,而且具有超道德的意义;
不仅具有社会意义,而且具有超社会的意义。
人既是社会公民,又是宇宙公民,作为宇宙公民,人应当顺应宇宙法则,如果同宇宙自然界及其法则完全合一,那就是最高的境界,也就是最高的“善”。
我们不必说,在冯先生哲学中,宇宙自然界是“善”的;
但是,我们可以说,与宇宙自然界合一的“天地境界”是“善”的。
其基本的主张是主客合一,而不是主客对立和分离,即承认价值有其客观标准,决不是个人的主观愿望。
这同西方的主观价值论是迥然不同的。
如果说,“太极”是静态的“纯形式”,那么,“自同于大全”的境界就不能这样说了。
“大全”是宇宙自然界的全体,包括实际存在及其共相,即使从理的角度说,正如冯先生所说:
“《新理学》所讲的‘理’,都是抽象的共相,《新原人》所讲的‘大全’,是具体的共相,和《新理学》所讲的‘理’是不同的。
”(第1卷,第228页)如果说,冯先生在写《新原人》时,还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在晚年写《三松堂自序》时,就明确地提出了上述观点。
“具体的共相”只能在具体的事物中存在,在实实在在的自然界中存在。
这就是“有不必存,存而必有”。
但是,“大全”又是不能思议、不能言说的,因为“大全”包括人在内,不可作为对象去思议、去言说。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实现这一最高境界?
在《新编》的最后“总结”中,冯先生提出了他的回答:
必须将概念认识和直觉体验结合起来,而不能缺少其中的任何一方面。
这就意味着,经过概念分析之后,达到一种直觉的体悟,也就是由“知”而进到“觉”。
“真正底形而上学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形式主义底方法,一种是直觉主义底方法。
形式主义底方法以形式主义讲形上学。
直觉主义底方法讲形而上学不能讲。
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二种讲形上学底方法。
”(第11卷,第496页)这所谓“形式主义底方法”,就是概念分析或逻辑分析的方法。
但是,这种方法只讲形式而无实际内容,哲学则是要讲实际的,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上。
“形上学的工作,是对于一切事实作形式底解释”。
“对于事实作解释,此是形而上学所以不同于逻辑算学者。
其解释是对于一切事实,而又是形式底。
此是形而上学所以不同于科学者。
”(同上书,第499页)他所谓“求好”与“求真”的区别,就是形上学与逻辑算学以及科学的区别。
形上学是形式与事实的统一,而不是分离;
逻辑数学与科学则是形式与事实的分离,要么只讲形式,要么只讲事实。
这一说法成立与否,可以讨论,但这是冯先生对“具体共相”的一个重要解释。
这是一层意思。
另一层意思是形式主义与直觉主义的关系问题。
当用形式方法讲形而上学讲到不能讲时,便要用直觉方法,即“讲”其所不能讲。
“讲”其所不能讲,是说不能用形式概念去讲,而不是不讲。
直觉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生命的直接领悟,直觉就是“生活”,就是“真实”,“无论什么感觉,概念,情感,意志,都是互相穿插而成一个不可分的全体。
”(第11卷,第16页)讲哲学讲到这个地步,就实现了哲学的最终目的,即“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
因此,直觉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最重要的方法。
他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明确提出:
“宇宙不能是理性或理智的对象,所以人自身与宇宙同一时,人也就否定理智,这与‘越过界限’的情形相同。
”(第11卷,第596页)所谓“越过界限”,是从康德哲学中借用来的,但他批评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的学说,主张回到真实的人生。
“越过界限”其实就是越过理智的界限,越过对象认识的界限,变成生命的直觉体验,实现“理想人生。
”这就不仅是存在的问题,而且是意义和价值的问题。
这既是人的精神创造,又是人的最本真的存在。
中国哲学所说的“仁”,就是这样的一种境界。
冯先生在去世的前一年,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
《对于孔子所讲的仁的进一步理解和体会》。
其中说:
“被称为全德之名的仁,不是泛指任何一种精神境界,而是确指最高的境界――天地境界。
”(第13卷,第492页)这是对孔子和儒家哲学最高成就的一种概括,也是对他自己的哲学的一种新的表述。
在冯先生看来,仁的基础不是别的,正是人的“真情实感”或“真实的情感”,而仁的境界,则是天人合一境界。
因此,对于仁的认识,“不是一种理智的认识,所以认识的‘仁’也不是一个理智的概念……理智的概念只是一种知识,知识是一种心外之物……对于他的思想情感并无影响。
”(同上书,第495页)这一重要观点可说是冯先生的真正的“晚年定论”,比《新编》总结更前进了一步,同时与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更接近了一步。
仁不仅以真实的情感为基础,而且以自然界为依归,对于仁的认识,决不是一个对象性的理智概念,而是与情感有直接关系的生命体验或“体认”。
这种“体认”是具有价值意义的。
“‘体认’就是说由体验得来的认识,这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一种经验,是一种直观,不是一种理智的知识。
”(同上书,第496页)由“体验”而得的认识,就是具有情感内容的精神境界,是整个生命的直接感悟,与对象性的理智概念有以然”,即人之所以为人者;
而且是价值意义上的“所当然”,即人之所当为者。
正因为仁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因此,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乐”。
这就是他所说的哲学的功用及目的在于“求好”的真正含义。
四、哲学与诗学 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大都关注冯先生的共相理论和概念分析的方法,却很少注意他的哲学中的另一面,即诗学理论。
冯先生的“新理学”,固然是以概念分析为主要特征的形上学,但是,他又很重视中国的诗学,认为与哲学有相通之处。
他不是讲“哲学诗”,即用哲学语言所写的诗,而是讲诗性哲学,即用诗的语言所表达的哲学境界。
他认为,好的诗能达到同哲学一样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也可以是哲学的。
冯先生是重视抽象分析的,是重视形式概念的,而诗则是一种形象思维,使用的是形象语言。
为什么说,诗能表达哲学的境界呢?
正如他自己所说,只用形式主义方法并不能达到哲学的真正目的,即“天地境界”这一“理想人生”,因此,必须用“负”的方法。
而“负”的方法除了他所说的直觉之外,他还特别强调诗学的方法。
其实,诗学方法就是直觉方法之一种,或一种特殊的直觉方法。
就哲学的最高成就和最终目的而言,诗学方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重要的。
冯先生在讲“新理学”时,吸收了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但是并不同意维也纳学派的结论。
为此,他受到维也纳学派在中国的代表洪谦先生的批评。
我们知道,维也纳学派是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他们认为,形而上学的语言都是无意义的,可称之“概念的诗歌”,是一些主观想象,只能使人得到情感的满足,却不能得到确实的知识,即逻辑的“真”。
至于诗歌,更是完全出于主观情感,与哲学毫不相干,从哲学或逻辑的观点看,诗的语言更是一些无意义的话。
冯先生早在撰写《新理学》时,就专辟“艺术”一章,讲艺术的功能及其特点,特别是与形而上学的关系。
接着又在《新知言》中专辟“论诗”一章,讲诗为什么是形而上学的一种方法。
后来,又在《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一文中,用很长篇幅详细论证诗与形而上学的关系。
直到晚年,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全书“绪论”中,又专列“理论思维和形象思维”一章,讲艺术和诗在“人类精神反思”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有限”中如何想望“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