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铁窗十年》2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长篇连载《铁窗十年》2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长篇连载《铁窗十年》2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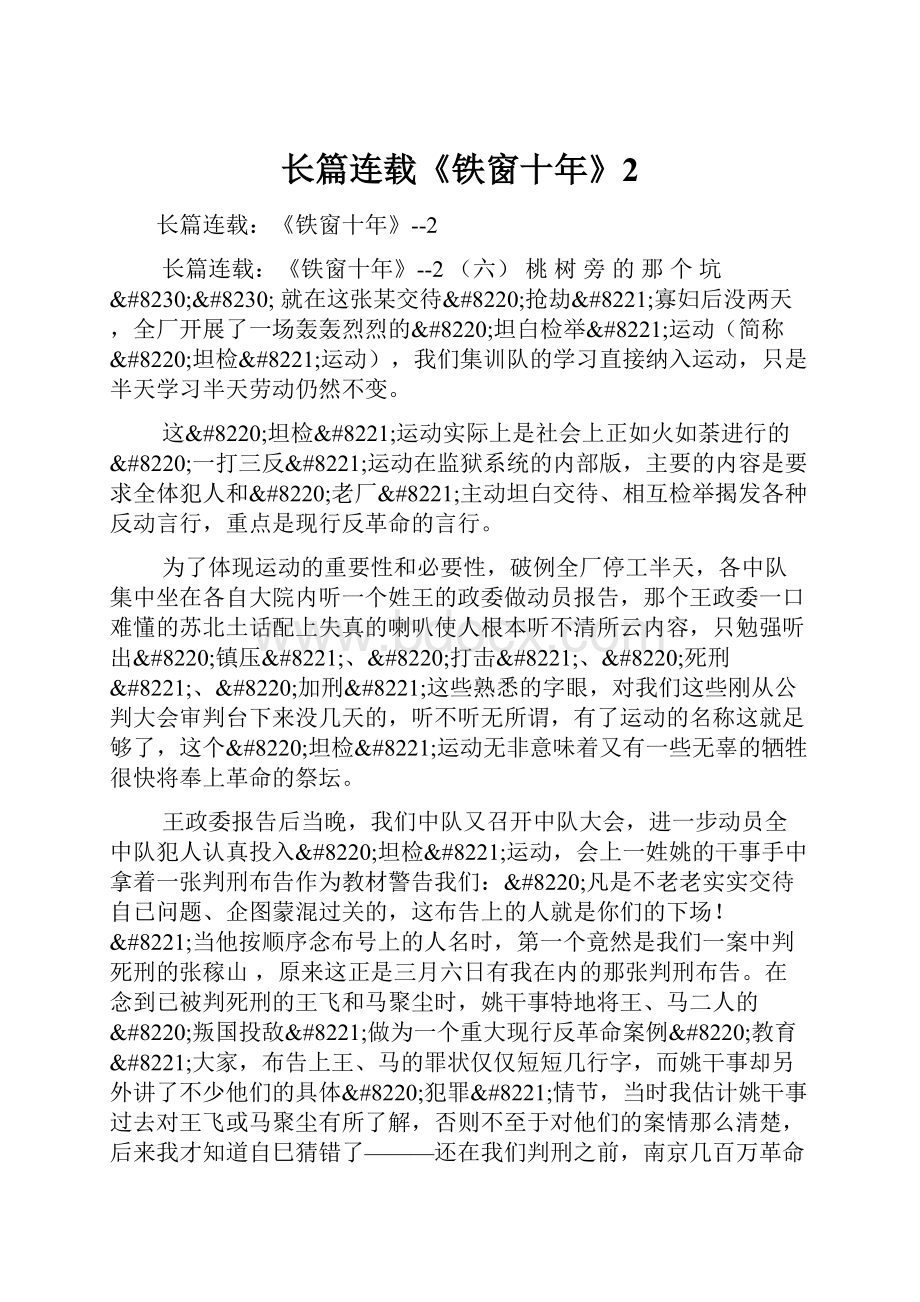
死刑&
加刑&
这些熟悉的字眼,对我们这些刚从公判大会审判台下来没几天的,听不听无所谓,有了运动的名称这就足够了,这个&
运动无非意味着又有一些无辜的牺牲很快将奉上革命的祭坛。
王政委报告后当晚,我们中队又召开中队大会,进一步动员全中队犯人认真投入&
运动,会上一姓姚的干事手中拿着一张判刑布告作为教材警告我们:
凡是不老老实实交待自已问题、企图蒙混过关的,这布告上的人就是你们的下场!
当他按顺序念布号上的人名时,第一个竟然是我们一案中判死刑的张稼山,原来这正是三月六日有我在内的那张判刑布告。
在念到已被判死刑的王飞和马聚尘时,姚干事特地将王、马二人的&
叛国投敌&
做为一个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例&
教育&
大家,布告上王、马的罪状仅仅短短几行字,而姚干事却另外讲了不少他们的具体&
犯罪&
情节,当时我估计姚干事过去对王飞或马聚尘有所了解,否则不至于对他们的案情那么清楚,后来我才知道自巳猜错了———还在我们判刑之前,南京几百万革命群众早就对我们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不但了解,还人人参与了对我们如何处理的讨论,全南京只有我们这一小撮&
现行反革命&
蒙在鼓里。
姚干事参加过讨论,对我们当然不陌生。
在三月六日公判大会前一个月,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就已把我们这些将在&
三&
#8226;
六&
公判大会上亮相者的&
材料&
(每个人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单位以及所犯&
罪行&
的具体情节等)印刷了十几万份分发南京市(包括各郊县)各机关、学校、社会团体、企业、街道、居委会,并统一布署安排全市各单位组织群众开会讨论如何处理我们这些&
,按名单上人头逐个过堂(对某某某该怎么判,杀还是不杀,如果不杀又怎么量刑,死缓或是无期,判二十年还是判十五年、十年、八年&
),人人都得发言,个个必须表态,最后将大家意见统计后逐级上报,一直集中到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按当时的官方说法,这次是根据全南京市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来处理我们这一小撮&
。
四百多万的南京革命群众做梦也没想到要由他们来直接决定我们这些反革命的生死,伟大领袖和革命既然这样信任,岂能错过显示群众专政威力的大好机会?
一辈子从没尝过权力滋味的劳苦大众,昨天还在为吃了上顿没下顿而发愁,今天居然一下子成了操有生杀大权的法官,激动之情可想而知。
一时之间,我们这个民族潜意识中嗜杀、嗜血的优秀传统顿时彻底暴露无遗。
据我在1979年出狱后特意对1970年那几次群众讨论情况的调查,当时至少有90%以上的人不管讨论到哪个现行反革命都是一个字———杀!
好多单位在讨论时,名字才念出来,连犯罪情况都等不及读,下面马上就异口同声地喊杀,念一个杀一个!
那铅印名单上长长的一串姓名,已不再象征着一个个年轻人鲜活的生命,而只是必须立即宰杀的一群瘟鸡!
这当中当然包括少数迫于政治压力违心表态的,也有个别凑闹热跟着起哄的,但是绝大多数人确实是出于本意地在喊杀。
谁叫他们反对伟大领袖?
谁叫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文化大革命?
不杀这些人杀谁?
!
我父亲后来告诉我,我家所在的居委会讨论时,除了对我未能全部一致要杀外,对文件上其余的二十几个现行反革命一致同意全部判处死刑,之所以有人对我&
法外开恩&
,大概只是碍于老邻居的面子。
特别令我吃惊的是一个我们从小对她就很尊重的邻居老太太,多年来一直为人和善,从未得罪过人,属于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老好人一类,可就这么个老好人,在当时的讨论中竟然杀字喊的最响,连我这个她看着长大的孙子辈也不放过!
真不知是疯狂的年代造就了疯子,还是疯子造就了疯狂的年代!
一些学者把历史上某些特殊时期那种民众对领袖和革命的绝对敬畏、绝对盲从称为&
集体无意识&
,我认为这种提法不是很精确。
人的意识本是极为复杂的多元集合,这集合中的诸多元素如果按人的本性来划分则只能有两种,一是善,一是恶。
假使全体民众经过&
洗脑&
已失去个人意识,那构成人性最本质的善恶观念必然也丧失殆尽,与其说&
不如称之为&
集体无人性&
更妥。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何以有那么多人对这种疯狂的戮杀甘心推波助澜?
何以对一个个素无冤仇的青年必欲置之死地?
惊魂囬首,我们当时还真得感谢公检法军管会,要不是把我们象&
野兽&
一样关在笼子里而是放在外面,单就南京四百多万人的&
杀&
声还不得把我们吓的灵魂出窍?
如果真的由几百万南京革命群众来定夺我们生死,哪里还能容我活到现在,让我有机会坐在书房里如此消停地写下这些让人恨得牙痒的文字。
八十年代我在一次政协座谈会上曾公开说过:
以我解放后的经历,特別是57年到79年这二十二年的经历,我这辈子对共产党恐怕是爱不起来了,但是我对人民更爱不起来;
我倒是真心希望共产党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好好执政,切莫再瞎折腾,别再每隔几年捣估一次群众运动,今后万一非得那么干,我宁愿请贵党再次把我送进劳改队去当&
#8216;
二进宫&
#8217;
,也不愿又一次去接受&
群众专政&
就在我写此文前不久的某日,我同两位正厅级老干部在茶舍聊天,老先生离休赋闲后权力少了,牢骚却多了起来,我这人平素最讨厌吃肉骂娘,当即不留情地奉劝他们:
劝您二位别跟着老百姓瞎搅和说共产党坏话,还是多发挥点余热为贵党再卖点命吧,照这样下去万一哪天群众真的起来造了你们的反,别说您二位身家性命难保,连我们这些差点被你们整死的都要跟着倒霉!
你们成天把人民群众挂在咀边,如果真的让人民群众成了气候,那才是全中国的灭顶灾难。
我宁愿你们七千万共产党个个在台上搞腐败,也不愿再出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
这可不是我的牢骚怪话或调侃挖苦,而是确确实实的肺腑之言!
就在姚干事抓住王飞马聚尘这亇典型教育我们时,我还觉得有点奇怪,我们那张判刑布号上有几十个人,单是判死刑的就有11个,为什么独独把王飞、马聚尘挑出作为教材案例呢?
我先前以为之这只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一个偶然,后来我才明白自已过于天真:
这劳改队的干部在同我们犯人打交道时,其所做的每件事都会有一定的用意,从不无的放矢,他之所以选中王飞和马聚尘作为反面教材,是因为这二人比其他被杀的更富含&
价值,更容易被人记住,从而也更符合劳改当局的宣传目的。
尽管用杀人来教育群众是我国宣传部门的优良传统,但用特殊杀人形式教育活人则更加与时俱进地适应新的革命形势。
按照当局的意图,&
六&
公判大会的用意无非是杀11只&
鸡&
以吓住南京400多万只&
猴&
,在这11只&
中,唯王飞和马聚尘和其余9只不一样,是特殊的两只———他们不仅是同案,还是两代亲属,王飞是马聚尘的姨父,马聚尘是王飞的姨侄。
中国的统治者自古以来对&
满门抄斩&
灭族&
之类的残酷株连一直奉为干净彻底消灭政敌的经典手段,同时也是对怀有贰志者的强力震慑,如今到了革命年代,这些过于极端的做法自然不宜照搬,但深谙中国民众心理的当局非常清楚,把一些相互连有血缘关系的&
阶级敌人&
捆在一道杀,其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将会更加突出,更富刺激性,也更能触及人们的灵魂。
文革&
伊始,发动者就公然宣称这将是一场&
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批斗、抄家、游街、关押、进&
牛棚&
,那只是革命的初级阶段,它们触及的仅仅是灵魂的表壳,要真正触及人们灵魂深处,则必须通过杀人才能做到,而杀人又因为过滥从而降低了它的&
吓猴&
威力时,那就得不断提高杀人艺术,翻新杀人花样才行。
既然&
会招致国际&
帝修反&
的诽谤而不宜使用,那又有什么能比退而求其次地把母子、兄弟、叔侄等亲属捆在一起一同杀掉更能触及活人们的灵魂呢?
既然腰斩、车裂、剖心、凌迟这些中国的优秀传统因为不适应革命形势不得不忍痛割爱,那又有什么能比在枪毙之前割喉、穿舌、取活肾、勒脖子更能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慑力呢?
当人们对杀戮已经司空见惯毋足为奇时,当人们看到满街打着红叉的杀人布告就象今天到处张贴的性病广告而不屑一瞥时,只有上述这些特别的&
革命行动&
才能刺激人们的神经,才能彰显专政的威力,从而才能达到&
大多数的目的,这正是当局喜欢精选这些特殊案例进行宣传的原因,姚干事当然也不能免外。
王飞、马聚尘已死去三十六年了,他们的名字早就被遗忘,但只要一提到在&
中姨爹和姨侄一同枪毙的事,南京很多老人马上就能想起来,这,不正是当局所希冀的效果吗?
当然,王飞和马聚尘案件同九个多月后1970年12月10日同遭处决的林舜英、李立荣母子案件比,其影响和效果又略逊一筹,后者那才算是完美的杀人&
杰作&
这件&
即使在神州大地普遍杀红了眼的1970年,也能在全国杀人竟赛中勇夺金牌,最起码能捧回一个&
杀人创意奖&
,许世友,杨广立,这几个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超级刽子手,人们会永远记住它们!
事有凑巧的是,姚干事重点挑出的马聚尘,在娃娃桥看守所恰恰正和我关在一个号子,并且有一段短暂但却永远难忘的难友情谊。
当时我们一同关在东大院7号,我的代号是2605,马聚尘的代号是3419,我坐在进门左侧,他在右侧,彼此正对面。
我在1970年元旦后不久由南京白下区看守所升级到娃娃桥,从进去到判刑共待了两个月左右,其间相处最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原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方征,另一个就是马聚尘。
那天下午我刚跨进7号,面对十几双目光的盯视,尽管已有几个月&
号龄&
了,作为初来乍到者一时之间仍不免有些不知所措。
正当我夹着铺盖立在中间四处寻找容身之处时,一个年青人很热情地过来把我手中东西接了过去,随即帮我在一个年龄较大的犯人旁边匀出一个铺位,接着又告诉我随身物品怎么放置以及看守所的一些规章制度,稍为收拾停当后我赶紧向他道谢并请教他的姓名,他告诉我叫马聚尘,番号3419,同时又把我们7号的号长介绍给我认识了一下。
他约模二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白脸,微胖,背稍有点佝,黑油油的头发略有卷曲,上穿兰色棉袄,下着黑色灯芯绒裤,在我进来之前他己关了不少时间,算的上是个7号的老资格了。
那时的娃娃桥尽管以厉害出名,但有一样规矩比其它看守所好,这就是允许犯人之间随便谈话,不象我原来待的白下区看守所,放个屁声音大点都会有看守过來问咋囬事?
第二天下午,马聚尘爬到我铺位来主动和我聊天,在号子里案情是严禁交谈的,我们只能简单相互了介一下案由,一听都是&
现反&
,彼此不由觉得靠近了一大步。
很快我发现他同我一样也是个个俄罗斯文学迷,看过不少俄罗斯文学作品,两人从普希金、莱蒙托夫一直谈到别林斯基和杜勃罗柳波夫,特别是杜勃罗柳波夫,我们反复谈了他的作品,他的&
多余的人&
理论,他那二十四岁短暂的生命&
晚饭送来时我们才恋恋不舍结束,旁边的老爷子方征笑着调侃我们&
看了那么多&
封资修&
的书,不变成反革命才怪。
我进7号不久,由于拒绝与审讯员&
合作&
,不肯检举揭发我好朋友李立荣母亲林舜英的&
现行反革命罪行&
,经审讯员和我们7号管理员串通,被那个人称&
陈医生&
的管理员以起床动作慢为惩罚借口把我反铐了六天五夜,那手铐深深勒入肉内的痛彻心肺,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酷刑的厉害。
当时我们7号的号长是南京钟山化工厂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技术干部,大概为派性斗争在7号已关了一年多,此人非常正派且富同情心,见我不停的痛苦呻呤,他和马聚尘、方征一道用蘸着水的毛巾在我身后手腕上冷敷,希望能减轻我一些疼痛,他还指定马聚尘和方征两人专门照应我,负责帮我铺被叠被、洗脸刷牙和脱、穿裤子,喂饭喂水,大便小便也全靠他替我解裤子擦屁股。
在帮我料理这些事时马聚尘总是低低安慰我,劝我不要难过,一定要咬牙熬过去。
人到那个地步能有如此关照,内心感激实在难以言表,我这人六十多年来除父母之外在感情上欠人的债不多,而娃娃桥那六天五夜中欠下几位难友的感情,我到死都不会忘却,到现在都因永远无法偿还报答而遗憾不已。
马聚尘就在他遇难前的十天,还被他的提审员&
恶搞&
了一把。
三月六号的前十天左右,一天中午刚吃完饭后马聚尘突然被带出去,直到傍晚才被送回号子,刚一坐下他就带点兴奋的告诉我们,他的案子快要处理了。
下午他被带到原单位和住地所在街道,分别开了两场批斗会,会上也只是一般的低低头、弯弯腰、喊喊口号,完全不象以前那样挨打挨踢,囬来的路上提审员在车中还特地对他进行了一番教育,叫他以后认真吸取教训,转变思想,好好工作,尽早囬到人民队伍中来。
最后要他囬号子后写一份思想检查,以前的问题就不必再写了,主要写通过这段关押和批判后思想认识有哪些提高,今后有哪些打算。
凡蹲过号子的都体验过,除了判死刑的个个都巴不得早日处理,能释放当然最好,就是判刑送劳改队,也总比成天窝在这号子里强的多。
何况根据那提审员的口气,分明是在暗示马聚尘,他最多不过是戴上反革命帽子囬原单位交群众监督,连刑都不会判,见他自由在望,我们都很为之高兴。
在号子里,见到同号难友释放囬家,每个人的情绪都会受到感染,都会点燃对自由的幻想,看别人自由了,似乎自已离自由也随之近了一大步。
那晚我们7号里的气氛非常活跃,几个平时天天侃吃的又开始了&
精神会餐&
,相互争论出去后第一顿大餐究竟是到粤菜闻名的大三元酒家,还是去以维扬口味著称的老正兴菜馆,我也坐在方征旁边津津有味地听他侃当年审犯人的故事。
马聚尘闷着头很快写好了他的&
思想检查&
,微笑着递过来说要我&
斧正&
我看了他那一手苍劲有力的钢笔字后,不知为什么忽然在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就对我讲过字如其人,字的风格、笔力和人的阅历、年龄密切相关,马聚尘这一笔少见的遒劲书法和他二十多岁的年龄实在太不相称了,&
皎皎者易折&
,我隐隐感到此人日后恐非长寿之辈。
在他交了那份&
之后,我们以为他很快就要走人了,上午巴下午,今天巴明天,可一连几天却毫无动静,人没走号子倒又添进了两三亇新来的,睡觉越来越挤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后移,马聚尘开始有点沉不住气,我们也为他着急,但表面上还得编出各种理由来安慰他,那时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切只是那个提审员为了稳住马聚尘而设的一个&
缓兵之计&
,其实早他在出去批斗之前他就已被列入处决名单了!
可怜的马聚尘,十天以来每一分钟都在做着自由的美梦,殊不知死神正在一秒一秒的向他逼近。
我们怎会想到短短的十天之后,他竟然会成为南京首批血腥屠杀的刀下鬼!
那篇为了迎接自由的&
,成了他留在人世的绝笔!
日历很快翻到了1970年3月6日那个令人难忘的血腥日子。
那天清晨,我们刚刚起床正在叠被子,牢门上的老虎窗&
啪&
的一声打开,管理员黑着脸命令我们动作快点,各人洗脸刷牙后都坐在自已位子上,一律不准随意走动,原来每天雷打不动的&
早请示&
背语录也被停止。
早餐还没送来,号子里的喇叭就反复放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几首抗日歌曲,音量大的炸人耳朶。
这一系列反常举动预兆着今天可能会有什么&
大动作&
,喝完麸皮稀饭早餐后,各人无心交谈,都坐在自已铺位上忐忑不安地胡思乱想,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
身旁的方征凑在我耳边告诉我,今天肯定有大行动,喇叭这么响是为了盖住外面大院中的某些声音。
好多年后我才深深体会到这位公检法老前辈的英明,那天包括王飞在内好几个人一出号子门就被按倒在地用绳子紧紧捆起来,尽管事先谁也不知道自已会判死刑,但一看那架势马上意识到今天难逃毒手了,于是一面拚命挣扎,一面竭尽全力狂喊口号,直到喉咙被绳子死死勒住发不出声为止。
各号子里由于喇叭音量大的出奇,没有一个人听到大院中的这些动静。
那天的中饭比往常提前了一个小时,我还记得吃的是咸菜烧豆腐汤,饭才吃一大半,劳动班就在外面敲牢门催我们快点。
等到全部吃完收走饭盆菜桶,我们在自已铺位上才坐下十来分钟,号子门咣珰一声打开,那亇&
背着手站在门口。
————&
2605,出来!
把东西一齐带着!
我愣了一下才领悟是在喊我。
#172;
我赶忙收拾行李铺盖,马聚尘、方征和号长都一齐过来帮忙,趁着低头收拾东西那会,他们悄悄地一再叮嘱我前途珍重,好自为之,希望以后在外面有机会再见面,而我那会由于紧张,什么也没对他们说。
最后马聚尘夹着我的铺盖送到门口,在管理员逼人的目光下,我连表示谢意握手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只是默默地和他对看了一眼,然后接过铺盖跨出了7号牢门。
没想到三个小时之后,我和他在五台山公判大会主席台上又再次见面,在那里却经历了死别。
下午二点多钟,当我被两个身强力壮的军人反架着跪在主席台入口处时,一行被反捆得象粽子似的犯人在一群军人的簇拥下,勾着腰从我身边很快地通过,其中有人大约绑的过紧咀中在不停的呻呤,我一眼就认出了张稼山和马聚尘。
那时我真他妈天真,居然以为用绳子绑的都是马上在会上就要当场释放的,之所以绑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吃点苦头好长记性,只有我们戴铐的才是判刑对象,直到亲历了这次公判大会我才明白了绳子的作用。
绳子,这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用具,到了人类已登上月球的高科技时代,在中国居然仍旧能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判死刑的之所以非得用绳子绑,一是防止死刑犯挣扎,再就是把死刑犯勒得半死非得由人架着才能站立,从而给广大革命群众造成这些坏蛋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吓瘫了的印象,另一个附带作用是可以很方便地将一米多长的亡命牌牢牢地挿在背脊上不会歪倒。
我认识一位和我一样犯&
罪的W君,军管会事先已经决定判他十五年,可他在最后一次提审时不知为了什么事同军代表顶了几句咀,当晚军代表连夜开会将W君的十五年改为死缓;
判刑那天,他和其他判死刑的同等享受了绳子待遇,囬到看守所解开绳子一看,整个上半身都已呈紫酱色,俨然换了个人种。
尽管绑的时间不太长,去老虎桥监狱经过了三个多月才算勉强恢复,但肩胛关节由于紧绑留下的后遗症至今未完全康复。
十分钟后,绳子绑着的、双手铐着的,全部在主席台上低头听宣判,我们是第一起,张稼山判了死刑,我列在倒数第二被判十年,李蔚荣是八年。
王飞和马聚尘好象是第五起或第六起,两人一同判处死刑。
我和马聚尘最后的一点今生缘分是共同游了一次街———从南京广州路五台山体育场北大门出发,在道路两旁数十万人睽睽目光注视下沿新街口、大行宫、杨公井一直到太平路和白下路的十字交叉路口,在那里我们诀别,我囬到娃娃桥看守所,他去了凤凰西街尽头处的刑场。
一小时后,随着十一声枪响,他和他的姨父王飞,我的好友张稼山,还有另外八位不幸的难友,一同化为十一缕冤魂飞向虚无缥缈的太空。
我和马聚尘在一亇号子只相处了短短两个月,而且根据看守所的规定相互之间严禁交谈案情,因此我只知道他犯的是&
,具体情节则不清楚。
直到好儿年后才陆续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一些他和王飞的事。
他的命运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点宿命色彩。
他原是南京第二锁厂的出纳会计,家住南京建邺区明瓦廊富民坊,他的姨父王飞是南京二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长期以来姨侄二人一直对中国的政治现实非常反感,&
开始后更使他们感到无法在这个国家继续待下去。
1968年,经过反复密商他们决定越境去外国,为防止亲属受牽连,他们瞒住了所有家人,直到他们走后,家中任何人仍不知道这姨爹姨侄二人的去向。
大约是王飞曾在云南部队里待过,对边境情况较熟,他们计划从云南边境越境偷渡去缅甸。
当时马聚尘利用出纳之便,私自拿了300元公款,由王飞搞了两张乘飞机的介绍信(那时普通百姓坐飞机比登天还难),二人由南京飞到昆明,再从昆明辗转到了中缅边境。
根据事先约定,为了防止越境时被一网打尽,决定两人分开行动,待过境后再在缅甸边境某小镇碰头,万一有一个被抓获,另一人不必管对方,能逃出去一个是一个。
具体的路径通道,估计他们早就熟记于胸,至于成功的把握到底有多大,只有他们自已清楚了。
分头行动后,王飞很顺利地抵达了缅境内那个小镇,但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马聚尘到来,按事先约定等待的时间早过,他完全可以撇下马聚尘不管单独走掉,也许是担心日后见了妻子和妻妹不好交待,经再三考虑决定返囬中方境内来找马聚尘,然而一直找到他们原先出发点也未见马聚尘踪影。
王飞怕自已在返囬这段时间里马聚尘说不定已过境了,不敢多留,再次沿老路出境,当第二次到了缅方小镇时,还是不见马聚尘在那里。
之后,王飞又反复三次进进出出,直到第五次囬到中方境内才碰到迷路后晕头转向的马聚尘。
合该二人命中该绝,就在他们沿王飞进出几次都平安无事的小道上走到临近界碑只有几百米的地方时,二人被巡逻的民兵一同抓获。
南京方面很快去人把他们带回,此后就一直关在娃娃桥。
多年来,我每当同朋友们怀旧谈起王飞和马聚尘时,总禁不住嗟讶一番,当时假使马聚尘不迷路,假使他们比巡逻民兵早一分钟到达界碑,假使他们选择另一条林中小路,假使&
,有一个&
假使&
能够成立那也是好的呀!
莫非这真的是命中注定?
我不知道他们越境出去究竞想干什么,也不知他们最终去向是哪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和我一样,他们共同追寻的其实仅仅只是每一个人最起码的要求———自由。
任何政治运动的最高表现形式无例外的是杀人,王政委报告之后没两天的1970年3月20日,全厂召开了一次公判大会。
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