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对郭子仪评价不当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资治通鉴对郭子仪评价不当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资治通鉴对郭子仪评价不当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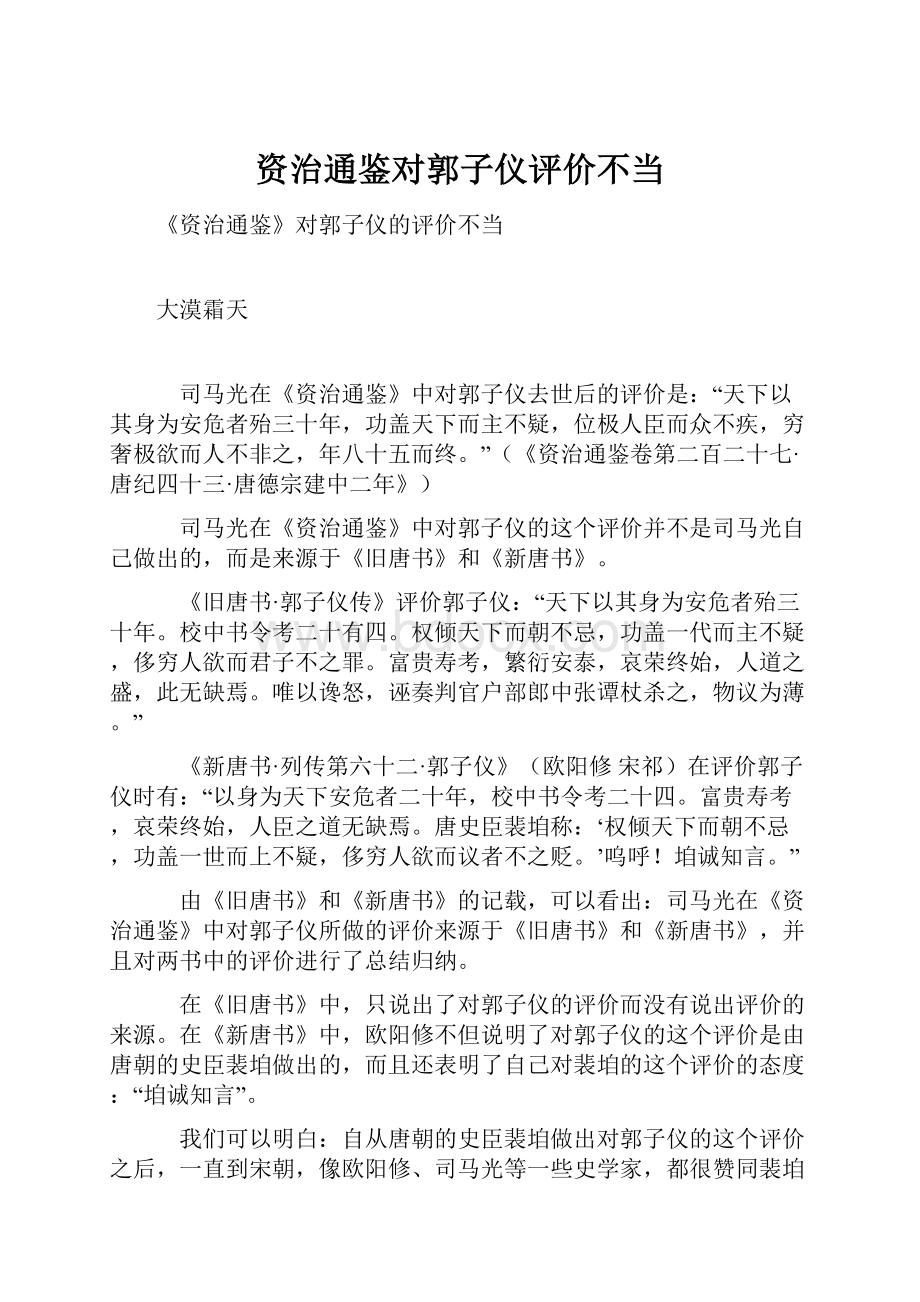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郭子仪所做的评价来源于《旧唐书》和《新唐书》,并且对两书中的评价进行了总结归纳。
在《旧唐书》中,只说出了对郭子仪的评价而没有说出评价的来源。
在《新唐书》中,欧阳修不但说明了对郭子仪的这个评价是由唐朝的史臣裴垍做出的,而且还表明了自己对裴垍的这个评价的态度:
“垍诚知言”。
我们可以明白:
自从唐朝的史臣裴垍做出对郭子仪的这个评价之后,一直到宋朝,像欧阳修、司马光等一些史学家,都很赞同裴垍的评价,并在他们主修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采用了这个评价。
那么,《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所采用的唐朝史臣裴垍对郭子仪的这个评价是否恰当呢?
笔者认为:
这个评价并不是十分恰当的。
下面,笔者以《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有关郭子仪的一些史实为例,来看一看这个评价的不恰当之处:
一
“功盖天下而主不疑”
“上问(李)泌曰:
‘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唐肃宗至德二载》)
“泌曰:
‘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
于人臣乃万世之利也。
’上曰:
‘善!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九•唐纪三十五•唐肃宗至德二载》)
“十一月,郭子仪来自东京,上劳子仪:
‘吾之家国,由卿再造。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
唐纪三十六·
唐肃宗至德二载)
“辛未,以郭子仪为汾阳王,子仪将行,时上不豫,群臣莫得进见。
子仪请曰:
‘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矣。
’上召入卧内,谓曰:
‘河东之事,一以委卿。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二•唐纪三十八•唐肃宗宝应元年)
“郭子仪以仆固怀恩有平河朔功,请以副元帅让之。
己亥,以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二•唐纪三十八•唐肃宗宝应元年)
“仆固怀恩自以兵兴以来,所在力战,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而为人构陷,愤怒殊深,上书自讼,以为:
‘……如臣朔方将士,功效最高,为先帝中兴主人,乃陛下蒙尘故吏,曾不别加优奖,反信谗嫉之词。
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匪虚言。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三•唐纪三十九•唐代宗广德元年)
“冬,十月,吐蕃寇奉天、武功,京师震骇。
诏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以御之。
子仪闲废日久,部曲离散,至是招募,得二十骑而行,至咸阳。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三•唐纪三十九•唐代宗广德元年)
“十二月,甲午,上至长安,郭子仪帅城中百官及诸军迎于浐水东,伏地待罪,上劳之曰:
‘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三•唐纪三十九•唐代宗广德元年)
“二月,癸巳,郭子仪入朝,上言边事。
夏,四月,甲申,郭子仪辞还邠州,复为上言边事,至涕泗交流。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九年)
“八月,辛巳,郭子仪还邠州。
子仪尝奏除州县官一人,不报,僚佐相谓曰:
‘以令公勋德,奏一属吏而不从,何宰相之不知体!
’子仪闻之,谓僚佐曰:
‘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
此无他,乃疑之也。
今子仪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亲厚之也;
诸君可贺矣,又何怪焉!
’闻者皆服。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十年)
“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十四年)
“甲申,诏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二千户,月给千五百人粮、二百马食,子弟、诸婿迁官者十余人,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
以其裨将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以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振武军使浑瑊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分领其任。
由以上记载的一些史实可以看出:
《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对郭子仪的评价之一“功盖天下而主不疑”是不恰当的,皇帝对郭子仪是颇为怀疑的。
理由如下:
(一)皇帝的言论:
“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
(二)皇帝的行动:
(1)以仆固怀恩或其他人代替郭子仪,解除郭子仪的重要职务;
(2)皇帝对郭子仪不但不重用,而且还长期地弃之不用:
“子仪闲废日久,部曲离散”;
(3)郭子仪部将旁观的事实及部将的愤激言词:
“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匪虚言”;
(4)郭子仪言边事,“至涕泗交流”,但皇帝就是不听;
(5)郭子仪举荐的官员,皇帝不批准。
以上的理由,有其中的任何一点,就完全表明皇帝对郭子仪是不信任的,更何况还不止一点呢?
自古以来,皇帝对功臣的疑忌是普遍存在的。
有时,“功高震主者”,杀头就是赏赐!
灭族者,也不在少数!
郭子仪例外了吗?
没有!
郭子仪依然受到了皇帝的猜忌!
二
“位极人臣而众不疾”
“六月,观军容使鱼弼朝恩恶郭子仪,因其败,短之于上。
秋,七月,上召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
士卒涕泣,遮中使请留子仪。
子仪绐之曰:
‘我饯中使耳,未行也。
’因跃马而去。
“光弼愿得亲王为之副,辛巳,以赵王係为天下兵马元帅,光弼副之,仍以光弼知诸节度行营。
光弼以河东骑五百驰赴东都,夜,入其军。
光弼治军严整,始至,号令一施,士卒、壁垒、旌旗、精彩皆变。
时朔方将士乐子仪之宽,惮光弼之严。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一•唐纪三十七•唐肃宗乾元二年)
“或上言:
‘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仪于散地。
’乙未,命子仪出镇邠州;
党项遁去。
戊申,制:
‘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发射生英武等禁军及朔方、鄜方、邠宁、泾原诸道蕃、汉兵共七万人,皆受子仪节度。
’制下旬日,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一•唐纪三十七•唐肃宗上元元年)
“八月,己巳,郭子仪自河东入朝。
时程元振用事,忌子仪功高任重,数谮之于上。
子仪不自安,表请解副元帅、节度使。
上慰抚之,子仪遂留京师。
“冬,十月,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之帅。
上欲以郭子仪为适副,程元振、鱼朝恩等沮之而止。
“十二月,庚辰,盗发郭子仪父冢,捕之,不获。
人以为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
子仪自奉天入朝,朝廷忧其为变;
子仪见上,上语及之,子仪流涕曰:
‘臣久将兵,不能禁暴,军士多发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谴,非人事也。
’朝廷乃安。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四•唐纪四十•唐代宗大历二年)
“郭子仪以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性刚率,谓其武人轻己,衔之;
孔目官吴曜为子仪所任,因而构之。
子仪怒,诬奏昙扇动军众,诛之。
掌书记高郢力争之,子仪不听,奏贬郢猗氏丞。
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仪悔之,悉荐之于朝,曰:
‘吴曜误我。
’遂逐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十三年)
“郭子仪每见宾客,姬妾不离侧。
卢杞尝往问疾,子仪悉屏侍妾,独隐几待之。
或问其故,子仪曰:
‘杞貌陋而心险,妇人辈见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无类矣!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六•唐纪四十二•唐德宗建中二年)
“春,正月,丙子,郭子仪入朝,鱼朝恩邀之游章敬寺。
元载恐其相结,密使子仪军吏告子仪曰:
‘朝恩谋不利于公。
’子仪不听。
吏亦告诸将,将士请衷甲以从者三百人。
子仪曰:
‘我,国之大臣,彼无天子之命,安敢害我!
若受命而来,汝曹欲何为!
’乃从家僮数人而往。
朝恩迎之,惊其从者之约。
子仪以所闻告,且曰:
‘恐烦公经营耳。
’朝恩抚膺捧手流涕曰:
‘非公长者,能无疑乎!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四•唐纪四十•唐代宗大历四年)
《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对郭子仪评价之一“位极人臣而众不疾”是不恰当的,众多朝臣对郭子仪是颇为怀疑的。
(1)鱼朝恩的诋毁;
(2)程元振的诋毁;
(3)元载的诋毁;
(4)郭子仪父亲的坟墓被掘,却不知是谁;
(5)部属的不满,(6)郭子仪自己对其他人的疑忌。
虽然鱼朝恩、程元振、元载是奸臣,但如果皇帝或其他大臣对郭子仪极其信任,那么,鱼朝恩、程元振、元载等奸臣的谗毁是难以实现的。
奸臣的谗毁能够实现,表明郭子仪不是不被众大臣嫉妒的。
郭子仪父亲的坟墓被“盗发”,却无法捕获罪犯,因为一点线索也没有。
没有任何一个人,向郭子仪提供线索,难道不也证明郭子仪是被嫉妒的吗?
部属的不满,以及郭子仪对卢杞的疑忌,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
郭子仪是受人嫉妒的。
疑忌别人,也恰恰证明自己是被别人疑忌的。
倘使郭子仪是人人都不嫉妒的,那又何来部属的不满与郭子仪对卢杞的疑忌呢?
一个功高天下的大臣,受到嫉妒是正常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倘使不被嫉妒,那反倒是不正常的、不合情理的。
后人觉得郭子仪是了不起的,但与郭子仪同时代的人并不完全认为郭子仪是了不起的。
因此,受到嫉妒也是正常的。
所以,《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对郭子仪的评价“位极人臣而众不疾”实在是有点虚夸的。
三
“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
“夏,四月,壬午,以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绾性清俭简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贺。
郭子仪方宴客,闻之,减坐中声乐五分之四。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十二年)
《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对郭子仪评价之一“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是不恰当的。
“穷奢极欲而人非之”,杨绾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呀!
“穷奢极欲而人非之”,还有众多的大臣与百姓呀!
当听说以“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时,众多的大臣与百姓的表现竟然是“朝野相贺”。
“朝野相贺”的原因就是因为“绾性清俭简素”。
从当时的人们对杨绾被任命为“中书侍郎”的欢迎,就可以鲜明地看出当时的人们对“奢侈”是多么地不满。
在物质资料并不丰富的年代,对郭子仪的“穷奢极欲”,大臣们与百姓也是极为不满的。
大臣们与百姓对郭子仪的“穷奢极欲”,之所以不“非”,不是“不非”,而是因为实在“不敢非”呀!
“穷奢极欲而人非之”,还有郭子仪本人。
假使,郭子仪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那又何须在自己宴客时,听到“杨绾为中书侍郎”后,立刻“减坐中声乐五分之四”呢?
倘使一个人做了事情,连自己都认为是错误的,还能够有人认为他做的是非常正确的吗?
御孙曰:
“俭,德之共也;
侈,恶之大也。
”(《左传·
鲁庄公二十四年》)
“杨绾为中书侍郎”而“朝野相贺”,怎么能说,当时的人们不痛恨奢侈呢?
既然当时的人们都痛恨奢侈,那么,对郭子仪的“穷奢极欲”,又怎么可能“人不非之”呢?
所以,《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对郭子仪的评价“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实在是有点不恰当的。
另外,司马光本人极其重视节俭,而且终其一生都提倡节俭。
《宋书·
司马光传》记载:
“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
……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
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司马康说:
“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
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极其重视节俭并强烈反对奢侈的司马光,在告诫儿子应该崇尚节俭的同时,以委婉的口气批评了寇准的子孙因“习其(奢侈)家风”而导致的家业衰败:
“今多穷困”。
可见,司马光是极其反对奢侈的。
寇准与郭子仪,虽然一个在宋朝、一个在唐朝,但同样是对国家有再造之功、同样是极其奢侈,司马光既然委婉地批评了寇准的奢侈,那么,司马光又怎么可能赞同郭子仪的奢侈呢?
司马光一方面身体力行地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一方面却反而赞同郭子仪的奢侈,其前后之言行,何其相反,何其乖也?
无论是于情的角度,还是于理的角度,恐怕也是很难说的通的。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的《郭子仪传》,对郭子仪有一点点美化的地方,是可以理解的;
古代的传记对传主本人,多多少少是存在一点点美化的,这也是读史书的人都知道的事情。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的《郭子仪传》是专门为郭子仪立的传,美化一点点也是正常的事情,更何况郭子仪不但是唐朝极其杰出的人物,就是在古代的历史上也是很杰出的人物。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为治理国家而编纂的一部“有资于治道”的书,其目的是为国家的治理提供一些借鉴。
司马光在《进书表》中说明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时说:
“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倘真的如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郭子仪的“穷奢极欲”的评价,竟然沿用了《旧唐书》中“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和《新唐书》中“侈穷人欲而议者不之贬”的观点,并在《资治通鉴》中表述为“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那么,司马光是不是有悖于自己编写《资治通鉴》时所说的“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初衷呢?
按照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那么,“穷奢极欲”应该属于“恶可为戒”的,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属于“善可为法”的。
笔者的确听说过,古代王朝在治国时有提倡“节俭”的,还从未听说过,古代王朝在治国时有提倡“奢侈”的。
封建时代,大多数的国君都易于奢侈而难以节俭,极少数的国君虽然力求控制自己的欲望而达到了节俭,但“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在历史上,真正达到节俭的君王,并能够坚持始终的,实在是少之又少的;
一些有较大功劳的大臣也是如此。
司马光不但自己终生主张节俭且反对奢侈,而且还告诫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节俭并反对奢侈,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沿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对郭子仪的评价呢?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人来说,无论在什么时期,“奢侈”都是一件极其可耻的事情,那又怎么可能“人不非之”呢?
也许,有人说:
“这是司马光采用的‘春秋笔法’,与他在《训俭示康》一文中对寇准的委婉批评是一样的”。
倘如此解释,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
懂得“春秋笔法”的又有多少人呢?
懂得“春秋笔法”的封建王朝的国君又有几个呢?
在封建王朝,臣子拼死进谏尚且难以获得效果,更何况用“春秋笔法”的方式进谏呢?
诚然,“讽谏”的方式也有一定的效果,但与“直谏”的效果相比,还是差的很多的。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一方面详细地记载了郭子仪“功盖天下而主疑,位极人臣而众疾,穷奢极欲而人非之”的史实;
一方面又在这些详细史实的基础上,得出了与史实相反的结论:
“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
司马光如此的自相矛盾的做法,实在令人费解!
司马光这样做,是疏忽?
还是有意留下这与历史史实相反的结论?
还是真的认为郭子仪就是“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的人呢?
倘说是疏忽,笔者觉得:
不太可能。
治学极其严谨的司马光怎么可能在“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这样的大问题上疏忽呢?
倘说是有意留下与史实相反的结论,那又是为什么呢?
倘说是真的认为郭子仪就是“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的人,似乎也不太可能,如果真的是那样,郭子仪不就是“完人”了吗?
历史上,真的有“完人”吗?
以司马光的博学多闻,恐怕连司马光自己也不可能承认世界上有“完人的”,那又是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总之,笔者认为: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鲜明地表明《资治通鉴》是给皇帝的治国提供借鉴的。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对郭子仪的评价,本来就有一点点偏颇的,但《资治通鉴》在评价郭子仪时,依然沿用了《旧唐书》与《新唐书》中的观点,这多多少少也有悖于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沿用了《旧唐书》和《新唐书》对郭子仪的这个评价,不但有悖于他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而且还会给后世带来不良的影响。
古语有: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宋•张载《经学理窟•义理篇》)
信然乎?
(注:
①《旧唐书》公元945年成书。
②《新唐书》公元1060年成书。
③《资治通鉴》,开编时间公元1066年,成书时间公元1084年,共用十九年。
④本文完成于2008年7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