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与曾国藩李鸿章交往关系探微.docx
《丁日昌与曾国藩李鸿章交往关系探微.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丁日昌与曾国藩李鸿章交往关系探微.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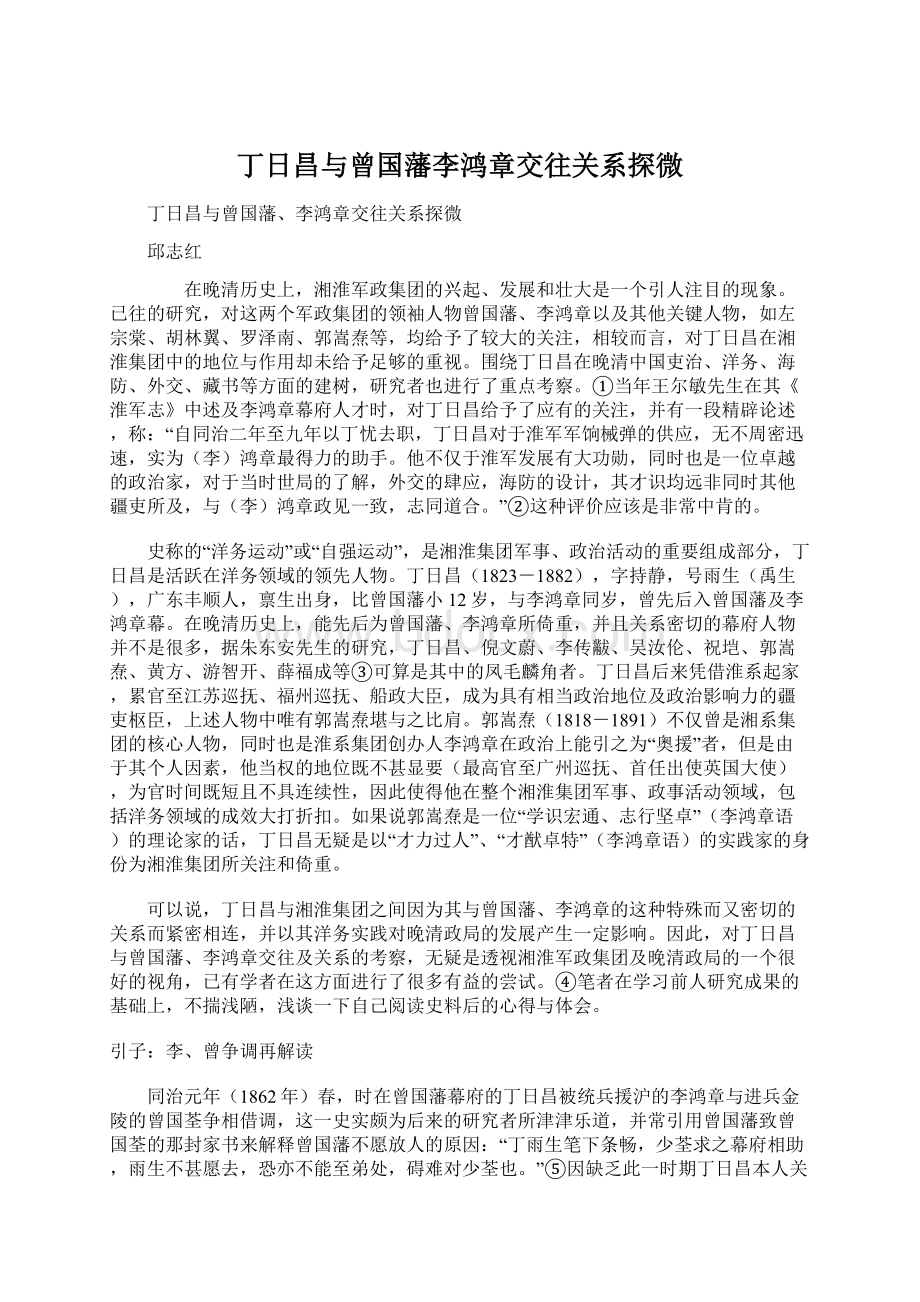
丁日昌与曾国藩李鸿章交往关系探微
丁日昌与曾国藩、李鸿章交往关系探微
邱志红
在晚清历史上,湘淮军政集团的兴起、发展和壮大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已往的研究,对这两个军政集团的领袖人物曾国藩、李鸿章以及其他关键人物,如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均给予了较大的关注,相较而言,对丁日昌在湘淮集团中的地位与作用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围绕丁日昌在晚清中国吏治、洋务、海防、外交、藏书等方面的建树,研究者也进行了重点考察。
①当年王尔敏先生在其《淮军志》中述及李鸿章幕府人才时,对丁日昌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并有一段精辟论述,称:
“自同治二年至九年以丁忧去职,丁日昌对于淮军军饷械弹的供应,无不周密迅速,实为(李)鸿章最得力的助手。
他不仅于淮军发展有大功勋,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对于当时世局的了解,外交的肆应,海防的设计,其才识均远非同时其他疆吏所及,与(李)鸿章政见一致,志同道合。
”②这种评价应该是非常中肯的。
史称的“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是湘淮集团军事、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丁日昌是活跃在洋务领域的领先人物。
丁日昌(1823-1882),字持静,号雨生(禹生),广东丰顺人,禀生出身,比曾国藩小12岁,与李鸿章同岁,曾先后入曾国藩及李鸿章幕。
在晚清历史上,能先后为曾国藩、李鸿章所倚重,并且关系密切的幕府人物并不是很多,据朱东安先生的研究,丁日昌、倪文蔚、李传黻、吴汝伦、祝垲、郭嵩焘、黄方、游智开、薛福成等③可算是其中的凤毛麟角者。
丁日昌后来凭借淮系起家,累官至江苏巡抚、福州巡抚、船政大臣,成为具有相当政治地位及政治影响力的疆吏枢臣,上述人物中唯有郭嵩焘堪与之比肩。
郭嵩焘(1818-1891)不仅曾是湘系集团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淮系集团创办人李鸿章在政治上能引之为“奥援”者,但是由于其个人因素,他当权的地位既不甚显要(最高官至广州巡抚、首任出使英国大使),为官时间既短且不具连续性,因此使得他在整个湘淮集团军事、政事活动领域,包括洋务领域的成效大打折扣。
如果说郭嵩焘是一位“学识宏通、志行坚卓”(李鸿章语)的理论家的话,丁日昌无疑是以“才力过人”、“才猷卓特”(李鸿章语)的实践家的身份为湘淮集团所关注和倚重。
可以说,丁日昌与湘淮集团之间因为其与曾国藩、李鸿章的这种特殊而又密切的关系而紧密相连,并以其洋务实践对晚清政局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因此,对丁日昌与曾国藩、李鸿章交往及关系的考察,无疑是透视湘淮军政集团及晚清政局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已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④笔者在学习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揣浅陋,浅谈一下自己阅读史料后的心得与体会。
引子:
李、曾争调再解读
同治元年(1862年)春,时在曾国藩幕府的丁日昌被统兵援沪的李鸿章与进兵金陵的曾国荃争相借调,这一史实颇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津津乐道,并常引用曾国藩致曾国荃的那封家书来解释曾国藩不愿放人的原因:
“丁雨生笔下条畅,少荃求之幕府相助,雨生不甚愿去,恐亦不能至弟处,碍难对少荃也。
”⑤因缺乏此一时期丁日昌本人关于此事的文字记载,其“不甚愿去”是与曾国藩沟通之后的意见,抑或曾氏个人的主观猜测,这个问题还值得进一步讨论。
对于湘淮军政集团来说,“淮从湘出”已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
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的时间是在咸丰八年底(1859年初),而在12年前,年仅25岁的他已经是丁未科的进士。
其间,李鸿章累充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还奉命跟随吕贤基回安徽办过团练。
和他同岁的丁日昌比他晚三年入曾幕,其时他们都已39岁。
但和李鸿章相比,丁日昌此前的仕途经历只能用“惨淡”一词来形容,不仅进士功名与他无缘,在江西庐陵县令任上不久就因弃城获罪旋被革职。
尽管在太平军兴起后,清朝官员抵抗失利的战役比比皆是,弃城而逃的也非特例,诸如曾经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但弃城革职的这个政治污点还是如影随形,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丁日昌仕途的发展,后来更成为顽固派用来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诟病之一。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曾国藩以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刚被革职的丁日昌即以江西省吏治、漕运等问题向曾国藩大胆建言,旋被曾国藩招揽入府,并正式与李鸿章结识。
从丁日昌入曾幕,到李鸿章、曾国荃二人争调,时间相隔不过半年,也就是说,丁日昌在曾幕时间也就半年有余。
通常情况下,领导对下属的考察,半年时间尤嫌过短,尤其是在对抗太平军需要广揽人才以为重用的特殊时期,曾国藩对下属“德”与“才”的考量就显得更加重要。
在此时的曾国藩看来,丁日昌解决实际问题的才干还是有潜力可挖的,丁日昌在入幕前后所呈的关于处理厘务、漕粮、对付太平军等方面的意见,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认为:
“各条不独于丁漕利弊,确切指陈,且于江省各州县衙门积习,疏剔明畅,足见该令素日留心吏治,实事求是,殊可嘉奖”,⑥因此在丁氏入幕不久他就奏请开复其原职。
但对丁氏在“德”方面的表现,曾国藩此时还没有正式的评价,至少是有所保留的。
湘军初创时,曾国藩领兵出省作战,接连遭受靖港、湖口、祁门屡战屡败的沉重打击,遂几次自杀,以表殉国心志。
⑦这段惨痛经历,曾国藩记忆犹新。
丁日昌却在与太平军李秀成作战时不战而逃,这种做法显然与曾国藩所提倡并实践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死节精神相背离。
吕实强认为曾国藩不愿放人的原因是“可能对日昌出处,已早有考虑”。
⑧其理由是为接济苏浙皖三省军饷,曾国藩在三月、五月间曾先后奏派左副都御史晏端书赴粤督办全省军务,黄冕、李瀚章、丁日昌等9人随同赴粤办理。
笔者觉得这还不能全面解释曾国藩的用意。
他的这种安排恰恰证明在他心目中已经认定丁日昌是可塑之才,只是需要在实践的锻炼中进一步增长其才干,磨练其德行。
他在奏折中称随行人员需“廉正明干、熟悉厘务”之外,还特别指出他们9人“皆才识宏远,条理精详”⑨之人即是很好的证明。
可以说,曾幕时期的丁日昌,以其名干练达的处事风格、切中时弊的建议言论,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为曾国藩所欣赏,并成为曾氏心目中重点培养的对象,只是他在德行方面尚未达到曾国藩理想中的要求,需要进一步考察和锻炼,这一点,曾氏尚未直接发表意见。
这也与他深沉持重、雍容含蓄的性格相吻合。
在二人日后的交往中,随着彼此了解的日益充分,曾国藩对丁日昌在为官处事、进德修业方面真诚的建议时有流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⑩
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李鸿章率初兴的淮军在上海与太平军作战正酣,急需熟悉军火制造的人帮助提供械弹支持,以解弹炮制造“刻不容缓”之急,丁日昌即是不二人选。
经李鸿章再次专折奏调,九月终获朝廷谕准,丁日昌即“起程赴沪”,成为李鸿章部下。
11
风生水起:
“五不胜任”与“六不胜任”
丁日昌无疑是一个善于学习、精明能干,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把握机遇的人。
在李鸿章幕府时,他参与“炸弹三局”的筹建,并制造出能容80磅炮弹的开花炮,使淮军军事装备威力大增;他积极参加战役,屡获战功;他办理与洋人交涉事件,顺利完成李鸿章交办的解撤常胜军一事,表现出色。
凡此种种,李鸿章甚感满意,也极为欣赏。
12在他的推动下,丁日昌开始平步青云,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补用江西直隶州知州、知府;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署苏淞太兵备道;同治四年(1865年),保升两淮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同治六年(1867年),升授江苏布政使;年底,升江苏巡抚。
四年之内连升六级,之后的福建巡抚、船政大臣等职,均是在此基础上的微调。
洋务、吏治事业均做得风生水起的同时,身体的疾病、外界的非议也接踵而至,为丁日昌日后多次请辞埋下了伏笔。
笔者认为,丁日昌近30年的宦途生涯中,有两次比较有代表性的请辞事件,一次是同治四年(1865年)力辞江苏巡抚,一次是光绪五年(1879年)辞以总督衔会办南洋海防,曾、李二人的不同回应,颇能反映丁氏本人政治性格的变化。
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鉴于张宗禹部捻军在河南南阳一带活动频繁,河南防务极不得力,清廷遂于初六日发出上谕,拟派李鸿章督带杨鼎勋等军赴豫,驰往河洛防剿,兼顾山西、陕西门口,其署理两江总督之缺,由漕运总督吴棠接任,其本任苏抚一职,则由时任两淮盐运使的丁日昌递署,署江宁藩司李宗羲递署漕运总督一职,并饬令曾国藩与吴棠、李鸿章彼此函商后复奏。
13其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师剿捻。
一般也都引用李鸿章在九月十四日致曾国藩信中所说:
“雨生洋务既熟,与敝军息息相关,朝廷自有深意”,认为李鸿章基本上是赞成这样的安排,其“惟资望过浅”14的意见只不过是出于对曾的应酬。
一般也都引用曾国藩在回复李鸿章信函中所谓“李、丁二君,资望尚浅,亦不易迁攫太骤,遽跻开府”15以及十九日回奏朝廷意见时所称“丁日昌以江西知县因案革职,三年之内开复原官,洊保府道,擢任两淮运司,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
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16这两句话,认为丁日昌此时未能署任江苏巡抚,主要来自曾国藩的掣肘。
其实曾国藩的反对意见并不是专门针对丁日昌一人。
清廷拟调李鸿章率军远征,由并非湘淮一系的吴棠接署两江,而两江又是湘淮军用武力打下来的最可靠的后方饷地。
曾国藩多次强调过:
“兵以饷为命脉,军火枪械为根本,深虑后路之不可靠,鄙人亦久知饷项关系之重。
”17动一发而牵全身,两江的指挥权岂能轻易旁落。
这才是症结的真正所在。
反对李宗羲、丁日昌的意见只不过是曾国藩为了增加抗疏的筹码而已。
再看一下丁日昌本人的态度。
在九月十八日致曾氏的信中,丁日昌以高姿态力辞江苏巡抚一职,并详述自己难以胜任的五条理由:
一,资格既浅,威望又轻;二,刚攫授运司,尚未赴任,骤然改换,恐洋人“心将有所不甘”而生疑窦,日后办事会有障碍;三,太平军残部及投诚之伍,因曾国藩驻徐州,李鸿章又率部西上,“二三重臣威力”他调,恐有“猝然之变”;四,升迁太快,“物议必多”;五、身体刚愈,恐力不从心,难以胜任愉快等。
18
应该说,丁日昌的这“五不胜任”不失为战略上以退为进的考虑,他对时局的精准分析,同曾氏不谋而合,尤其是他谦虚谨慎、顾全大局的姿态颇能迎合曾国藩的心理,使曾氏深感满意。
曾国藩在二十五日的回信中,对其所提的“五不胜任”尤表赞许,称:
“所筹五端,多中窾隙,与敝疏适相符合。
而自视异然之意,溢于楮墨,尤足征器识之宏雅,所谓君知其难,则易者至矣。
勉蓄光辉,终增位业,且慰且祷。
”19可见此时曾国藩对丁氏的态度已经有所改观。
对于自己对丁日昌的批评,曾国藩在写给安徽巡抚乔松年的信中解释道:
“责备吹求等语,即系代丁雨生预为虑及,若果署抚任,刘松岩(按:
即刘郇膏,时任护理江苏巡抚)必将挂冠先去,而物望民誉,丁亦较逊于刘。
是以稍持正论,以备采择。
”20
由此可见,曾国藩既满意于丁日昌在德行方面的精进,加上丁氏本身在洋务、吏治方面的出色表现,故而对丁氏进行栽培、扶持、提携已是应有之意。
此事之后,二人关系陡然密切,这点从此一时期曾国藩的书札中即有所反映。
曾国藩不仅对丁氏评价越来越高,对其仕途发展也多有建言,如在与李鸿章讨论加紧进行轮船制造时,曾国藩以丁氏熟悉夷务为由,建议将总理江南制造局之事,由丁氏“遥领”。
21同治五年春,曾国藩在了解丁氏在扬州的兴革作为,及闻其即将前往广东协助办理英人潮州进城之事后,便在致李鸿章的信中写道:
“雨生办理盐务,无弊不剔。
开旧河影及清厘场灶二事,似须留渠一手经理,暂缓月余赴潮,当无不可。
自扬州来者,均言雨生操守甚好。
尊处见闻,想更确矣。
”22继而淮军铭、鼎、武毅各部在捻军骑兵的打击下,连遭败绩,饷源的供应问题迫在眉睫时,曾国藩在致李鸿章的信中,清楚地表明了他认为当时只有丁氏才能合理接替后方饷事的看法,他说:
“若雨生不能居留后一席,饷源全无把握,决不肯轻变目前之局。
”23是年冬,曾国藩以剿捻久而无功,决意向朝廷请辞,并希望由李鸿章接替本位,在与李商函后路部署时,点名接替苏抚一缺的候选人,李瀚章之外便是丁日昌。
24当朝廷任命李鸿章为钦差,主持剿捻,曾国藩尊旨将回两江本任时,曾氏再一次以丁日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