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监委组长忆安徽饥荒为封锁消息不许起坟头Word格式.docx
《中监委组长忆安徽饥荒为封锁消息不许起坟头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监委组长忆安徽饥荒为封锁消息不许起坟头Word格式.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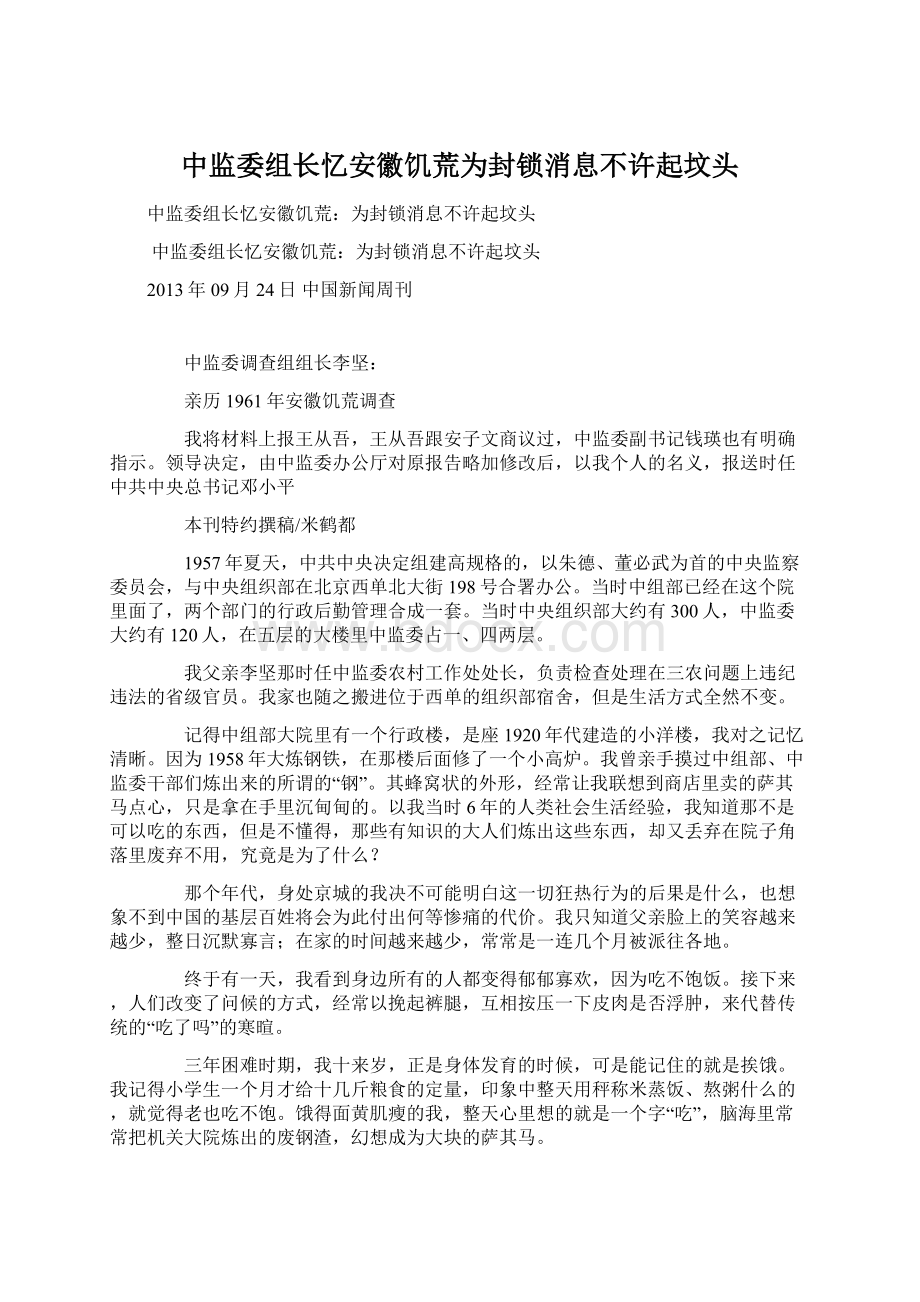
以我当时6年的人类社会生活经验,我知道那不是可以吃的东西,但是不懂得,那些有知识的大人们炼出这些东西,却又丢弃在院子角落里废弃不用,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个年代,身处京城的我决不可能明白这一切狂热行为的后果是什么,也想象不到中国的基层百姓将会为此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
我只知道父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整日沉默寡言;
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是一连几个月被派往各地。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身边所有的人都变得郁郁寡欢,因为吃不饱饭。
接下来,人们改变了问候的方式,经常以挽起裤腿,互相按压一下皮肉是否浮肿,来代替传统的“吃了吗”的寒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十来岁,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可是能记住的就是挨饿。
我记得小学生一个月才给十几斤粮食的定量,印象中整天用秤称米蒸饭、熬粥什么的,就觉得老也吃不饱。
饿得面黄肌瘦的我,整天心里想的就是一个字“吃”,脑海里常常把机关大院炼出的废钢渣,幻想成为大块的萨其马。
那时期,自己感受深的也有几件事。
一件事是中央机关组织到内蒙古打黄羊,大家分黄羊肉。
我父亲是个部门头头嘛,那年头的领导就得照顾点儿别人,所以他分的是羊的肺和脖子,没什么油水。
但是炖出来的那个汤,觉得特别香。
另一件事是那年夏天,我父亲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住在离家不远的民族饭店。
吃早餐前,他特地跑回家,带上我一起到饭店餐厅,把他饿肚子节省下的一张餐票给我用。
饭后他问我,吃了几个花卷,吃饱没有?
我说,我吃了6个,但没有了,所以还没有吃饱。
其实我哪里知道,很多孩子却因为缺少一口粮食而永远失去了生命。
困难时期是何时结束的,我不清楚。
只是有一次学校食堂宣布,从今天开始,又可以敞开吃饭了。
那一顿饭,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也不记得到底吃了多少,总之吃完饭,我已经撑得站不起来了,只能蹲在地上,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回宿舍躺下。
当历史进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说它相当于一颗亿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决不为过。
1967年的北京城,大字报可以说无墙不在。
当时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称:
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很快那张大字报就被人清除掉了。
虽然中组部大院和大字报那时对社会公众开放,但是在短时间内,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在上千张毛笔书写的大字报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
但是,这消息却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我就是那时候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数字,只不过对3500万是个什么级别的“当量”并无感觉,因为在当时混乱多变的环境中,我们全家都面临着自身的生存焦虑。
谁知,这个数字却直接关联着我家的命运。
中组部、中监委院内的大字报写道:
李坚是反党、反中央政策、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李坚是刘邓黑司令部领导下的黑帮分子,思想右倾,主张包产到户,主张在政策制定上考虑农民利益等等。
接着,造反派们重点追查的,就是我父亲当年调查安徽等地饿死人事件的问题。
造反派们认为,查出饿死了那么多人,是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
最为严重的是,以我父亲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被刘少奇拿在了手里,成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质问攻击毛泽东、逼迫毛泽东认错的“黑炮弹”!
我父亲居然是提供反毛主席黑炮弹的人,那还得了!
这是我幼小心灵上的重负,一直是个心结。
当时,我反复追问,父亲都不说。
直到多年以后,父亲在回忆中才把此事详细说了出来。
以下为父亲李坚的讲述。
工作组三赴安徽
从1954年我在华北局纪委任农村工作处副处长算起,到1965年去大连搞四清,整整11年里,我每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
也就是说,我这10年都在全国各地奔波工作。
我们的工作方法主要是跑两头:
一头是各省省委,另一头是农村基层。
省委这一头是开会、听汇报,农村那一头就在公社或者生产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向中央汇报。
当年,中国农村大批患浮肿病、大量死亡的根源,是搞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以及浮夸造假、虚报高产等等。
这些因素如果是在个别时间、个别地点起作用,影响可能有限。
但是在大跃进那么一个特定的形势下一起爆发,造成的合力作用就太可怕了。
1960年春天以来,干部群众不断给中监委写信,反映安徽一些群众生活困难,有些已经得肿病死亡。
之后,安徽省监委副书记刘作垣来中央监委开会,反映了安徽饿死人的问题。
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和中监委常委们对这些群众来信极为重视。
当年,委派审理处处长刘力生、信访科科长张珉和李竹林等同志到安徽潜山县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情况。
8月,派张珉、曹思恒去安徽宿县、萧县、全椒县了解情况。
11月,派审理处副处长李振海去安徽阜阳地区临泉等县了解人口外流等情况。
但是,中央派出的这些工作组仅查出问题严重,却无法查实饿死人的具体数字。
由于安徽的问题极其严重,中监委第二书记董必武曾亲自到阜阳地区调查。
为了对董老封锁消息,当地领导派汽车沿公路来回巡逻,不许死者家属戴孝,不准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坟头标志。
一发现有人死在公路上,就赶快把尸体拉到砖瓦窑场埋掉,其状非常悲惨。
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中监委反映的情况,再派出以中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为首的联合工作组到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
工作组成员由团中央杨海波、内务部朱农、公安部李震、中办王愈明、中监委刘力生和张珉、中组部段学夫等多人组成。
不久,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地委副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肿病死人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
仅仅一个月后,联合工作组就因此而被迫撤回。
1960年12月28日至1961年1月3日,王从吾主持中监委会议,听取赴安徽工作组的汇报。
王维纲、杨海波、王愈明、朱农分别汇报了蚌埠、阜阳、芜湖和安庆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情况。
安徽的曾庆梅、单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之前,王从吾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作了汇报,反映了安徽省委不但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活动、向中央“告黑状”的问题。
因此,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柯庆施一同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并拿出安徽凤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少柏的检举材料,指出了饿死人的问题。
曾、单二人表示承认错误。
1961年1月3日,王从吾在中监委党委会上说:
“1月2日,我与曾庆梅、单敬之谈话指出:
一、你们回去后一定要彻底揭开盖子口。
二、封锁消息不对,单敬之要写出书面检讨报中监委。
三、对张少柏同志应该予以表扬。
党内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说实话是好同志。
你们要保证,不准对他打击报复。
四、安徽省委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情况?
这是违背党章规定的。
”曾庆梅当时表态,称完全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准备检查扣压人民来信的问题,并承认向中央告工作组的黑状是错误的。
但这次会议后,安徽省委仍然认为中央工作组调查了解的问题“不属实”。
于是,中监委再派我带领第四次中央工作组,前往安徽。
实地调查
我从1960年起,担任了中监委农村处处长。
我本来就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加上多年的农村实地调查,让我既了解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也清楚一些共产党基层干部欺下瞒上的各种招数。
因此我们事先就商议好,在前往合肥途中,火车到达蚌埠站之前,就突然提前下车。
我、张珉、刘正荣三人分头行动,搞得前来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干部措手不及。
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里走。
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边。
一个男人头戴皮帽子,好像是从北面走过来后死在那里。
还有一个妇女骨瘦如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进入村庄之后,我说明来意,群众立即向我反映了饿死人的惨状。
随后,闻讯赶来的村镇干部们又提供了书面材料和肿病死人的数字。
这样,我掌握了第一手的情况和这些数字材料,接下来与安徽各级干部交谈就容易了。
当时的安徽控制在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山东、安徽两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手里。
大跃进、放卫星、谎报亩产万斤粮、刮共产风、强行搜刮农民家中存粮等等,安徽都是搞得最绝、最狠的重灾区之一。
待到出现饿死人的后果和责任,曾希圣所做的就是掩盖真相。
他听说我下来调查,就派人秘密监视我们的行动。
安徽发生大批人口饿死问题后,省委常务书记桂临西指示省监委要顶住中央工作组的压力,说不能从省监委这里打开缺口,并派省监委副书记陈×
监督,对我们这次的中央工作组继续封锁消息。
各级政府给农民规定了多项强制性纪律,如死了人不准立坟头,不准穿孝衣;
活人不准逃荒,否则抓住就是流窜犯等。
我调查途中,就亲眼看见一串串被绳子捆住、由武装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这种情况下,我们找当地同志谈话,经常是到野地里个别谈话,这样才能尽量减少当地干部惧怕曾希圣打击报复的心理。
蚌埠地区监委一个叫邓×
才的老红军向我反映,蚌埠地区1960年春天的饿死人数在100万左右。
我们又到了凤阳,找到张少柏,又到了定远,都是采取秘密私访的办法了解情况。
之后我又乘安二飞机到了阜阳,和我同行的是安徽省监委干部李东汉。
他告诉我,曾希圣把持的安徽省委大搞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明明连农民的口粮都不够,还要向外调运粮食。
在阜阳,据地委书记魏超云汇报,当地饿死人数也是100万左右。
即使在高压下,安徽党政军内也有一批有良知、有正义感、为民请命的干部。
时任安徽省监委副书记、老红军翁可业,为人正直刚烈。
他找到我说,要拼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
他说:
他讲出实情后,曾希圣肯定会整他,因为前有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为鉴。
他说他儿子叫翁京生,如果他被曾希圣整死,希望我能够帮他儿子找份工作,给他一条生路。
我答应了他。
翁可业1960年春天已经调查了蚌埠15个县饿死人的情况,他将相关的书面材料(复写底稿)以及其他人搜集整理的材料提供给了我。
他还满腔悲愤地对我说:
“饿死这么多人,安徽已经被曾希圣搞成什么样子了!
”汪瑜(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的夫人)等几位在省监委工作的女同志,也都支持他向中央反映情况。
我根据这些线索,再顺藤摸瓜,下去核实。
由于大搞公社化,办食堂集中吃饭,收缴了各家各户的铁锅炼钢铁,以至于大食堂断炊关闭。
这时,当地老百姓做饭连锅都没有,我看到农民们在家里只能用陶土瓦罐之类的容器煮些野菜树皮吃。
到后来,所有长在地里的植物都吃光了。
我的笔记里当时记载有许多人吃人的事例。
当时那种惨状,今天的人们简直就无法想象。
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这个数字。
经过这些工作,我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最后才到合肥与省委有关领导正式见面。
以个人名义写报告
情况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回到了北京。
我在中监委的办公会上汇报,安徽省饿死人的数字是300多万。
回北京后,我又派张珉、张顺参加了安徽省召开的全省监察工作会议。
他们与各县参加会议的同志逐一核对了饿死人的数字,最后的总数超过了300万。
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中监委常委刘澜涛听了我的汇报后,让我写一个书面材料。
我写出了《关于安徽肿病死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我将安徽饿死人的总数(截至1961年3、4月间)正式上报为300万。
我主要考虑到两点:
一是有少数县、乡我没能亲自去核实,依据的是这些县、乡报告的数字;
二是事关重大,还是以稳妥保守为好。
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多变,中监委、中组部的领导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我这个官儿,古代叫监察御史,要想干好,就不能怕死,一要对百姓负责,二要对历史负责。
万一最高领袖怪罪下来,我作为调查的执行者和报告的写作者,最直接的责任当然要由我来负。
报告同时送交了曾希圣和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阅。
据悉,他们看到材料后大怒,说我调查的情况没有先向安徽省委和华东局汇报,是告安徽省委的黑状。
而且,翁可业等人后来还是挨整了。
好在后来刘少奇同志看了报告后,严令安徽每个县都要如实报告饿死人的情况,有再不报告者,开除党籍。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搞一言堂最终会霸王别姬——主要就是针对曾希圣说的。
有材料披露,刘少奇后来曾手持一份报告对毛主席说:
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那份报告,指的就是安徽饿死人的报告。
“执行了刘少奇路线”
可是刚刚吃上几年饱饭,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
1967年和1968年,中监委的造反派们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了我写的这份报告,他们对我最为愤怒的一点就是:
“李坚在调查安徽饿死人事件时,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为刘少奇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逼着毛主席认错检讨提供了黑炮弹。
”
1969年,由康生的亲信郭玉峰控制的中组部业务组对我所做的干部审查结论是:
“李坚在中央监委工作期间执行刘少奇路线。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革命群众揭发和立案审查,犯了走资派的错误。
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攻击农村合作化,刮单干风,特别是在三年整风困难时期,他到安徽、山东、河南等省,深入了解干部违法乱纪、群众生产生活和整风整社问题。
最为严重的是,1961年3月,李坚根据王从吾的指示,到安徽搜集和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
这个材料经王从吾、钱瑛密谋,以李坚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猖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提供了炮弹。
我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孩子,再苦再累的劳动我也不怕。
可是,说我“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我永远不服。
调查安徽饿死人,我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核实数据,最后汇总出来350多万这个数字。
我反复考虑之后正式上报为饿死人300万,怎么能说是估计出来的数字呢?
况且我作为党的纪检监察干部,当时的想法就是对人民负责,为冤屈饿死的亡灵负责。
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上报给中央,让中央领导知道基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我做农村监察工作的职责所在。
至于真实数据给了中央之后会怎样,那不是我所能预料得到的。
文革结束后,安子文自安徽流放地返京,临时住在北京前门饭店。
我作为下级看望上级,心里想的是问候领导的健康和在安徽数年的生活状况。
不料进门一见面,安部长开口第一句话就说:
“你那个饿死300万人的数字,我核实过了,应该是350万。
我解释说,我调查的数字也是350万,只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出于各种考虑,才正式上报为300万。
★
(本文根据对李坚及其子李卫平的访谈、李坚与李卫平的多次谈话以及李坚当年的几份手稿编写而成。
)
已有361条评论,共17546人参与,相关帖子675057条